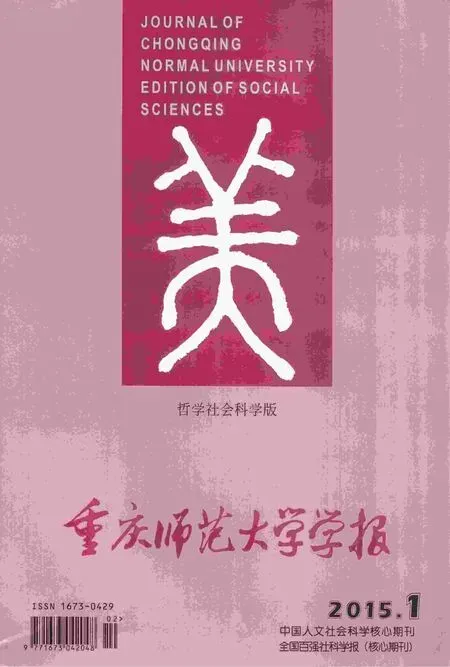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及其纯粹地位特征——基于先验哲学视野的理性语言辨析
2015-03-20肖福平
肖福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39)
“理性语言”的提出区别于常识性的语言学研究对象,它不仅涉及语言现象的经验与认知,而且涉及产生这些对象和认知结果的理性根据,即涉及语言现象存在的先验理性原因。为了凸显这样的根据和原因,我们将它称之为先验语言形式。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纯粹的理性形式存在,既要体现为先验的与自在的特性,又要体现为积极的与实践的特性;只有将自然过程的语言现象同其产生的先验形式和原则联系起来,我们才能更好地接近理性语言和语言存在的真实,从而取得关于理性存在过程的必然性语言遭遇,或作为语言现象存在的遭遇,或作为先验语言形式存在的遭遇。不论是作为“现象”的语言遭遇,还是作为“先验”的语言遭遇,理性主体存在的事实就是无法回避的语言“遭遇”。作为现象的语言形式与作为先验的语言形式统一于理性存在自身,并形成关于理性语言存在的不同“原因性品格”[1]68:立足于语言经验与应用的自然过程,语言存在提供给我们的是关于外在现象的呈现,这样的语言形式是可以直观的和可以认知的,自然过程的语言现象及其文法规律遵循着具有自然特征的因果原则,因此,自然因果联系原则体现于语言现象的过程不容置疑。同时,我们也不会因为语言现象存在所遵从的自然因果律而否认其具有先验形式规定的原因存在,尽管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不可能在作为知识对象的意义上加以提出。理性语言的先验语言形式因为语言行为者的理性存在特征而体现其实践的地位存在,先验语言形式的实践地位必然突破其自身纯粹地位的限制而成为语言现象世界的规定原则。因此,基于先验哲学的理性语言的“理性根源”或“先验形式”指向并不仅仅是对永恒而纯粹的语言原因的眷念,也是对语言存在之先验原因“事实”的确定,这样的确定“事实”不在于语言行为者的认知扩展,也不在于要为认知确立经验对象,而在于说明理性语言自身存在的“事实”。
一、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及其实践特征
如果把语言视为自然过程的现象存在,并把时空视为其存在的形式,那么,这样的语言现象存在便必然地处在受条件限制的自然因果联系系列之中,并成为自然物一样的对象。语言现象的存在除了作为自然对象形式之外就不会再有其他的形式,理性语言及其先验语言形式就不会再有立足之地或存在的可能性,于是,先验语言形式因为自身的“不可直观地表象”[2]184而置于语言范畴之外。相反,如果把语言现象和它的理性原因存在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将经验的语言现象作为我们所具备的理性直观条件下的自然形式对象,那语言现象存在的理性根据就成了一种非经验可能的并作为语言现象之纯粹理性规定的一种语言形式。两个领域的统一事实既是理性存在统一的事实,又是语言存在统一的事实。在确定了这样的关系之后,对于作为自然过程的任何语言现象的存在原因而言,我们便会重寻一种不同于自然因果联系中的原因,即一种源自理性存在的智性原因。语言现象世界的对象因为拥有了智性的原因而区分于自然对象本身。当然,如果我们只是局限于语言现象的认知过程,语言现象就只能处在自然的联系中,它就会以语法规律的展示来体现不同状态形式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先验哲学的思想里,作为理性主体的语言行为者必然是一个二元的统一体。这个二元统一体体现在理性语言的情形里,则表现为语言现象和先验语言形式间的和谐与统一,即语言行为者的语言行为既遵从自然过程经验的文法规律,又遵从关于这种文法规律存在的理性根据,其过程就是将语言存在的先验原因设置于语言现象的存在但又能回归理性主体的自我之内。依据理性的先验论,理性语言的先验形式设定或确立,对于思辨性的语言存在理论建立至关重要。唯有如此,理性语言学的实践经验方面才可以从先验语言形式(理性语言的自由)本身的证明上解脱开来,从而转到理性语言的自由原因的实践环节上。“像这样把自由观念看作是有理性东西依之而行动的基础就足够了,没有必要从理论角度来证明。如若我们不来做这种证明,那么那些约束一个真正自由东西的规律,也就同样适用于只能按照自己对自由观念而行动的东西了。”[3]88
结合康德的理性论来看,人们的语言实践行为应该作为理性存在的必然要求,并与一种来自理性的客观的规定根据相联系,这种客观的规定以“应该”的方式来影响发生于语言现象世界的语言行为经验。因此,对于感性世界的语言现象经验来说,这种理性的原因规定性或来自先验世界的普遍形式原则,在这里是应该予以承认的。正因为先验语言形式(理性存在的纯粹语言原因)所具有的自身特性,一方面,它并不妨碍自然过程中的语言现象的因果作用和表现而固守自己的纯粹理性之域,另一方面,它本身不只是处于一种消极的态势,它在理性存在的要求下必然作为一种积极的先验原因而存在,这种“积极性”的实现条件就是人的“此在”过程的语言实践行为。所以,语言行为者的行动本身应该意味着先验语言形式向实践的语言形式的转变,并在实践的领域获得先验语言形式的作用显现。
于是,在我们转向理性的实践环节时,我们也在从先验语言形式转向其实践的环节,这样的“转向”并非要改变先验语言形式的本身所是,它仍然是作为理性语言的理性属性,仍然是作为理性语言的本质所在。先验语言形式的实践转向在于为自然过程的语言现象确立普遍性原则作用,即纯粹理性世界的原则规定,这样的原则作用不会基于语言行为者个体的经验标准和内容。同时,实践转向也在于为理性语言确立理性原因决定的可能性存在,即语言不仅是现象世界的存在,而且是理性本身的存在;先验语言形式的实践转向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纯粹理性世界中的语言形式规定,显然,语言存在因为分享了这样的规定而真正成为理性的语言。不仅如此,先验语言形式的实践过程总是交织在“先验”与“经验”两个系列的联系之中。先验语言形式一方面作为实践的后果而联系于语言现象世界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又由于作为实践的原因而联系于绝对自主的理性世界。此外,语言行为者所遵循的纯粹理性原因、绝对性规定、普遍律,同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具有同一层次的地位,或者说,在理性语言的形而上学基础建设中,语言存在的本质在于理性存在本身。
二、理性语言存在的统一与先验语言形式的要求
语言问题一旦被视为先验哲学视野下的研究对象,它便应具有了理性存在的特征而成为理性语言的问题,其核心就在于关注理性的纯粹语言之因,即作为语言现象存在的自由之因。当康德将理性存在区分为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时,理性语言的存在也就具备了不同的表现形式,语言现象被归入了认知的领域,而这种现象的纯粹理性根据,即先验语言形式,则被归入了先验世界的存在。不论是康德的理性区分,还是本文的理性语言区分,它都直接对应于人作为理性主体的统一性问题,即人的存在具有两重性的统一“实体”(entity)[2]176,是自然世界和智性世界的完整结合。所以,人作为语言存在的过程既有语言现象的必然性经验,又有先验语言形式(理性语言的纯粹之在)的本质规定,而且只有后者才真正属于理性语言自身的本质所在。因此,就人类的“此在”的语言经验过程而言,只有源自理性世界的先验语言形式规定才是体现理性语言本质的真正原因;只有在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里,我们才有语言意志自由的权利和执行这种权利的语言能力,并体现为语言现象经验中的理性的自我规定。这样的自我规定一旦缺失,我们就不再生活在当下的语言现象经验中,也会失去对语言存在之纯粹理性根据的必然认识。所以,就理性语言所体现的实践过程而言,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理性语言存在的真正核心,一切关于语言现象的理性原因及其绝对性、纯粹性和普遍性的要求只有在这样的“核心”存在条件下才真正具有了构建的可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认为理性的实践的意义高于其纯粹形式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如果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完成了语言地位从理性主体到自然客体的改变,那理性语言的先验形式确立则是重回理性主体的第二次转向,即由关注语言现象的客体性和科学性意识到这种现象的理性根据,意识到没有先验的语言形式就不会有自然的语言现象,以及涉及语言现象的所有意义存在。重回语言存在理性之家的第二次转向就是重回人的“此在”真实的过程,就是重回语言之科学与客观地位得以建立的理性主体基础的过程。作为理性的主体,语言行为者既不是完全受自然律支配的自然对象,也不是任意运用先验理性形式规定的神灵,语言行为者的行为总是被展示为语言的存在过程,语言行为者所从事的语言经验活动过程绝对不可缺少自身如此行为的理性根据与原因,任何离开了理性存在之语言意志或先验语言形式规定的过程都无法谈论语言存在之“真”,因为先验语言形式既是人的本质,又是语言存在的本质。“第二次转向”不仅强调了作为理性原因的先验语言形式在语言存在中的地位,而且把语言现象经验同理性主体的行为必然地联系起来,从而凸显语言现象存在的理性联系必然,并以此将语言现象的认识统一于理性主体的认识之中。
基于理性语言概念的提出,我们在语言方面的“无知”或许体现为对语言本质认识的缺失。但这样的“无知”不同于理性语言原因的非存在,我们的语言认知不仅是关于语言现象的认知,而且是由自然过程转向心灵本源的认知。虽然我们不曾在知识结果上明确认知这样的心灵本源及其在语言实践中的必然性,但这种本源性的地位规定着语言现象的情形可以获得印证,“努斯(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因”成了我们探寻理性语言之理性根据和原因的真实写照。[4]911只要我们遵循康德哲学的理性之路,我们就会在理性语言的探寻中获得语言现象与其先验理性根据的联系必然,语言现象的经验规律就会联系到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原则,先验语言形式原则的至上性地位对于语言行为者的语言经验而言则意味着它对于语言现象世界的超越。在先验哲学的思想体系中,康德强调了理性的实践地位,而在我们的理性语言思考中,康德的启示同样具有指导价值,即作为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不仅处在纯粹的地位上,而且具有积极的实践地位。当然,我们在语言认知方面的“知识”所指向的应该是一个外延广阔的概念,它既有我们直观到的语言现象的内容,也有心灵世界“应该”的先验语言形式“知识”。于是,同样是在“知识”的问题上,理性语言的认知过程可以将人、自然现象、自然语言现象规律和先验语言形式原则清楚地归入理性存在的统一存在之中。在理性语言的全面展示里,由于我们所具有的直观形式只是提供了对语言现象内容的认知而非先验语言形式本身,所以,关于理性语言的先验形式“知识”或原则的“认知”,除了从经验的语言现象世界里获取出发点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路径。
然而,语言现象经验的出发点是否就能保证我们对先验语言形式本身的认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从语言现象开启的认识之路就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的过程,先验语言形式在“是什么”的问题上也会免于无休止的纠缠。就如我们在面对语词“树”时所表达的一样,语词符号“树”就是那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对象,它就在当下的时间和空间里。从“树”这样的语词现象出发,我们自然地获得了关于这种语言现象的认识过程,其中可能涉及了大小、长短、高低、颜色等方面的语言现象描述。然而,我们在这样的语言现象经验过程里,决不可能止步于经验的出发点,否则,语言现象的经验进程就会混同于理性语言存在的整个进程,从而可能将语言现象的经验出发点幻想为纯粹理性根据的实际,其结果就是理性语言存在的理性回归之路被阻断,其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被加以经验式的消解。这样的消解情形在现代分析哲学领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特别是在语言哲学的研究中,当人们永无止境地迷恋于语言现象分析的实证与科学神话之中时,“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就被还原为自然过程的现象问题。在没有了理性之光的语言现象世界中,语言现象虽然被看作完全的自然对象,可我们却无法发现这样的自然对象是如何提供了意义与科学定义的存在。一旦语言现象世界的扩张阻隔了其理性世界的视野和联系,语言存在的功能和价值就只能体现在工具性作用的方面,其理性的源头或原因就会在自然世界的语言现象中淹没,先验语言形式的纯粹原则地位就会因现代语言学的“科学”追求而远离我们的视野。实际上,现代语言哲学对于语言现象世界的分析和凸显,并不可能将作为自然结果或现象的语言始终置于一种自然对象的地位,任何关于这种对象的认知发生,绝非决定于这样的对象本身,除了作为理性主体的语言行为者的决定,我们无法想象其他的出路。那么,如何才能经由现代语言哲学的历程而重塑理性语言的存在呢?不论康德还是其他的理性论者,他们的思想不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远去而离开我们,他们的哲学思想所启示的现代意义必将为我们不断地标示语言存在的理性之家,并将理性之家的先验形式或自由王国带回语言现象世界,带回日常经验的语言之中。总之,踏上理性语言的实践之路既是回归语言存在的理性之路,又是回归我们自身作为理性存在的语言之路。
三、理性的语言意志及其能力
理性语言的纯粹理性根据或形而上学基础一刻也不可离开人的“此在”——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唯有如此,我们才会将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视为人的一种纯粹语言品格;人的“此在”(海德格尔的“此在”具有必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特征,本文使用“此在”在于展示遮蔽中的语言本质、沉沦中的语言现象)及其理性存在的基础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能够描述语言如此存在呈现的根本原因所在。基于理性的人的过程,我们才将语言现象和先验语言形式根据——作为语言知识的对象和作为纯粹形式的对象——第一次统一了起来。这种统一能力表现为语言存在的一种绝对自为能力,它必然地栖居于理性的存在。否则,这种语言存在的自为能力的独立会将理性存在(不论是作为现象的存在还是作为本体的存在)置于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其结果必将导致语言存在原因追寻的非理性之路,或重新回到语言存在的宗教之路。所以,依据理性存在的语言自为能力具有是其本身所固有的特征,即在理性的进程里,语言存在即是语言自为能力的存在,理性语言的存在与其能力之间不作时间上和因果关系上的区分。当然,在理性语言的自为能力方面,我们无法期待这种能力被展示为语言现象经验中的听说读写等行为,理性语言的自为能力联系于理性存在的一种纯粹语言意志。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语言意志结合到康德哲学的意志概念那里,语言意志则表现为一种先验语言形式的原则能力。所以,理性语言的自为能力实际上代表了理性存在中的一种自发的、不断产生的能力,一种“依靠理性存在的原因(性)”[2]188。作为根据表象而带来某物(或结果)的能力,语言意志本身就是为了语言意愿而表象某种可能的决定根据。这样的“根据”只能源于语言存在的先验理性根据,而非任何经验的语言现象。我们不能证实这样的“先验根据”,但也不能否定它。如果理性语言的自为能力的完善能在有一天为我们展示一个完全可以直观的先验语言形式的世界,那我们就会最终明白“语言应该是什么”的本质图景,然而,这样的图景对于人的“此在”而言毕竟还是一种理性的纯粹目标。因此,理性语言的自为能力在自身的决定作用中,除了秉承一种理性的实践规定外,并不会为我们带来关于它自身是什么的语言现象展示。如果我们将语言存在的理性根据及语言意志的自为能力视为本体论的存在,那它与语言现象世界的区分就可以清晰地进行划分。或者说,理性语言的认识所及会因本体与现象的区分而取得不同形式存在的领域,语言存在问题思考的经验论之路和唯理论之路便会拥有各自不同的“合法”领域。
在理性语言的“二元划分”下,我们在语言现象的经验中可以避开先验语言形式及其语言意志的“认知”问题,先验语言形式的存在就会被清楚区分于作为知识对象的语言现象存在,因为在语言现象经验的世界里只有时空形式里的直观的语言现象,而不可能有关于先验语言形式的对象出现。于是,我们处在语言现象的经验直观与认知过程,我们对于先验语言形式却不能直观和认知,因为我们所具有的语言知性和语言感性能力应用一旦超越了有效的经验世界,就会失去经验的“光明”而堕入无限的“黑暗”,先验语言形式的世界里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的言说条件,除非我们有言说幻想的语言根据。当然,我们在语言现象的认知中,可以获得语言现象的知识,可以在“语言现象是什么”的问题上获得人类的答案,以及在自然物的类比中将语言现象言说成什么,等等。然而,这样的“获得”和“言说”在关联于语言现象的“是什么”时却要必然地关联于这些语言行为发生的主体性存在,即语言行为者的存在前提,尽管这样的“前提”存在不可等同于那些作为认知对象的语言现象。因此,在表达理性语言的“二分”情形时,我们可以说语言现象的认知发生在“是什么”的自然世界中,但这样的判断并不意味着语言现象存在之理性原因的消失,这样的“原因”远在“是什么”的认识之上。理性语言存在的“二分”既在于提供其自然形式和理性形式的区分,又在于提供两者存在统一的实现基础,即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基础。一旦将理性语言的存在展示为外在的与内在的两个过程或形式,就是在知识对象和非知识对象的两方面进行语言存在的描述,也就是在宣示作为一种语言能力的存在,而这样的能力源自一种理性存在的语言意志。
四、语言行为者的“中心”与先验语言形式的积极意义
在理性语言建构的先验哲学思考里,不论是先验语言形式之路还是语言形而上学的纯粹意志之路,我们无疑是将语言存在的先验性、必然性和纯粹性同理性存在的本质要求作具有统一性的思考。或者说,我们是在将语言存在的思考对象还原成理性存在的相关项,还原成康德先验哲学的问题内容。语言存在的康德哲学之思在于开启一种从语言现象经验到先验语言形式的联系与统一之途,并凸显语言行为者作为这种“联系与统一”的中心地位。这种人的中心地位一旦被确立到理性语言的思考中,我们所获得的就不仅是关于自然过程的语言现象知识,而且是关于认知主体自身的原因存在,即作为理性自身的原因存在。显然,不论是关于理性语言的康德先验论思考,还是关于其它的本体论思考,一旦离开人的“此在”现实基础,我们的“思考”就会陷入一种空幻的境地而使得“思考”的对象变得遥不可及。那些关于理性语言的本体论成果或先验语言形式就会成为柏拉图似的理念对象,不再具有任何有效说明的起点和入口。“他(柏拉图)的所有努力毫无进展,因为他没有遇到可以帮助他站立的、可以把他的力量施加其上的、可以推进他的知性的阻力。”[5]275
理性语言存在的纯粹理性之思和本体论建构之路,不可离开语言行为者的有效认知世界——语言现象的世界。只有立足于语言现象的世界,我们才能真正体验理性存在下的语言统一,真正地面对先验语言形式的“事实”所在。也只有凭借语言现象的经验现实,我们才拥有了一种基于语言现象认知的类比方式,即由语言现象的认知上升到先验语言形式的确立,以及由语言现象的知识上升到纯粹理性根据的“知识”。不管这种纯粹形式的语言“知识”是否具有经验意义上的可证性,它的存在对于所有理性的语言行为者而言都是要必然发生的。所以,理性语言凭借其在理性主体那里的现象经验而展示为一种统一,一种关于语言的现象与本体、纯粹与经验、有限与无限的存在统一。理性语言的统一也是人的“此在”过程的本质表现,即,语言行为者的本质既在语言现象的经验中,又在先验语言形式的原因存在中。人的“此在”过程永远地同在于理性语言的存在,同在于语言现象与其理性根据的不断展示与体验,同在于语言的知识体系和语言的形而上学体系。一方面,在理性语言的经验统一中,语言行为者在面对语言现象时,他所感知的对象一定属于可以直观经验的对象,它属于自然物对象似的存在,这样的对象就是现代语言科学所涉及的对象。另一方面,理性语言的经验统一在体现具有自然特征的语言现象规律或语法规律时,还要体现具有理性特征的纯粹语言原则,一种具有实践特征的纯粹语言原则或纯粹语言意志的原则。理性语言的统一涉及自然原因与纯粹理性原因的不同领域,而执行这种统一的主体在于语言行为者自身,在于理性主体自身所秉承的先验语言形式及其实践特征。只有依靠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及其实践的特征,语言存在的不同领域间方可具有统一与联系的存在,从纯粹语言意志到语言现象经验间的路径才是可行的。所以,在从外在的语言现象回到我们自身存在的语言根据或原因时,我们也就回到了自身所拥有的先验语言形式或纯粹的语言意志所在。当然,这样的返回不是单纯的经验之旅,也不是对于语言现象的逃离,它是对“语言现象是我们的”的宣示和确认,是为语言现象制定语法规则和知识原则的起点。如果说这里的“返回”“宣示”“确认”和“起点”具有现实的物质基础,那这样的基础除了人的此在之外便不会再有其他的对象了。于是,从语言存在的语言现象中心便可以走向语言行为者的中心,即人的中心;在确定了人的中心之后,理性语言的统一和认知问题才从此获得了一个充盈而奇妙的研究视域。
倘若我们将理性语言的先验形式视为一种“事实”,那这样的“事实”绝非经验之义或现象之义,而应是一种语言存在的“自由事实”,一种属于人类之语言意志存在的“事实”。先验语言形式的原则指向在于理性,在于理性主体的纯粹语言意志的规定。先验语言形式因为理性存在的意志行为而必然地突破自身存在的纯粹地位(这里的“必然”之义源自于先验哲学的实践理性概念),其纯粹性的理性根据就不再因为“消极”而独立于语言现象的部分,先验语言形式作为理性存在原因的地位便从消极转向了积极,从而避免了先验语言形式对于语言现象联系的困难,并进而将当下语言现象存在的原因思考从知性的领域推进到了理性的领域,即推进到了先验语言形式的世界。依据康德哲学的知识论,语言知性概念对于先验语言形式的应用毫无结果,先验语言形式作为语言存在的纯粹理性根据不会为我们提供任何直观和经验意义上的知识对象,在那里没有任何知识确立的坐标,没有方向,没有大小,没有延续,也没有运动。总之,先验语言形式的世界里没有我们熟悉的经验现象,我们只是基于理性存在的本质要求而拥有这样的先验语言形式,只是基于理性存在的实践特征而拥有先验语言形式的作用。理性语言统一下的先验形式和自然形式的划分体现了理性自身存在的要求,我们对于理性语言的认识与对于我们自身的认识具有统一性,理性语言的统一性正是基于我们自身存在的统一性地位特征。我们在经验自然语言形式的内容时,如语言文字,我们不会满足于有限的对象而要寻求理性语言的本源,即寻求语言现象的理性根据。一旦我们回到语言现象的理性之“因”(先验语言形式),这样的理性之“因”在语言现象过程中贯彻自身规定的作用就会发生。尽管这样的“贯彻”还是会缺失经验的直接说明,但它也不是一种假想的过程,因为它是体现“先验统觉”[6]120同其最适合的显现对象相统一的过程,它既是理性存在统一的必然,又是理性语言统一的必然。[7]
总之,在理性世界的语言统一里,语言的世界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理性的,理性语言拥抱着两个完全属于它的世界:语言现象的世界和先验语言形式的世界。如果任何一方缺失,理性语言就不再是当下的语言,也不会再是理性的“存在之家”。[8]1008此外,在理性语言的统一中,语言现象方面的规定所在决定于先验语言形式方面的规定所在,决定于语言意志对于自身纯粹理性命令的贯彻;只要语言行为者拥有纯粹语言形式存在的实践特征,一切关于语言现象知识的准则、规律与意义获取便真正拥有了理性存在的源泉。[9]
[1]肖福平.康德自由理念的理性基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2]Heidegger,Martin.The Essence of Human Freedom[M].trans.Ted Sadler,London:MPG Books Ltd,2002.
[3]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M].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汪子嵩等著.希腊哲学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7.
[5]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葛宇宁.康德的罗辑思想探赜[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
[8]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
[9]刘立东.哲学逻辑的内在要求[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