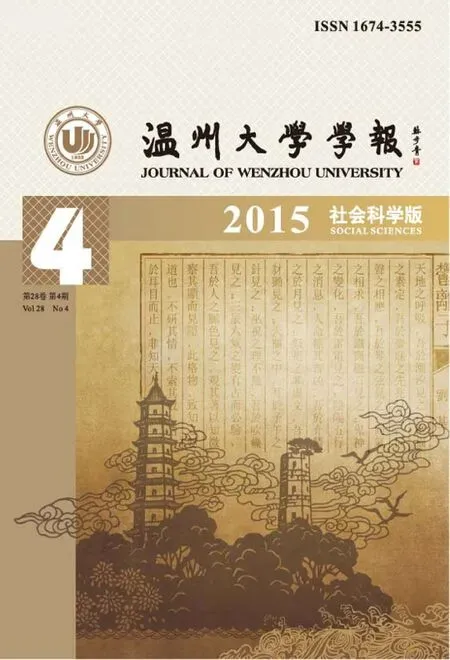论《大浴女》的女性意识
2015-03-17陶丽君金文兵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陶丽君,金文兵(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论《大浴女》的女性意识
陶丽君,金文兵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325035)
摘要:铁凝的《大浴女》通过塑造三位女性人物章妩、唐菲、尹小跳,表现了明显的女性意识。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三位女性以不同的生活姿态和心理历程,反抗着男权文化,彰显着女性的存在:章妩在情欲的享受、母性和妇德的异化中迷失了自我;唐菲在物质依附和性报复的游戏中毁灭了自己;尹小跳走过曲曲折折的成长道路,在与男性的反复周旋中,终于进入了自己“内心的花园”,体会到了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
关键词:《大浴女》;女性意识;铁凝;依附;反叛;自救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1]。在人类文化史上,父权制文化不仅有一种强迫性,迫使妇女处于生活的底层,没有经济地位和闲暇时间,它还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妇女长期在父权文化的熏陶下,逐渐将这种强制的东西内化为自身的价值取向,社会因此只存在一种价值标准,这便是男性价值标准。许多女性也自觉放弃自己在生活、家庭和社会中的主体性地位,沦为男性中心世界的“奴隶”,成了“他者”“第二性”。总之,“女人是男人用以确定自己存在的参照物,另一种补偿性事物,是男人的理想和神话……唯一不是的便是她自己。”[2]
自19世纪8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在西方出现时,妇女物质上的满足让她们更觉精神上的饥渴,于是女性意识逐渐觉醒,这意味着女性被塑造,只能沉默的历史开始出现裂缝,她们开始建立自我意识,自己塑造自己,而不仅仅是充当男性的创造物。这首先表现在“以不同于男性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去感知世界,展现作为女性的心理天空,这里聚集着女性的欲望、成长体验和逐渐稳定的价值标准及行动方式。其次是在自我确立的基础之上,以显在或者潜在的方式去反拨已经稳定成型的父权制文化和男权意识,既创造一种崭新的审美视阈,又确立一种新的价值立场”[3]。只有以新的价值体系和女性自身的文化生理系统去表达女性世界,女性自身的主体地位才能最终确立,女性才能找到“经验世界中的真我”。
铁凝的《大欲女》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作家通过三位女性艰难的心理变化史,为我们呈现出女性依附、反叛男权的复杂矛盾的心态和行为。三位女性在反叛男权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体现了作家的多向思考。章妩在情欲的享受,母性和妇德的异化中迷失了自我;唐菲在物质依附和性报复的游戏中毁灭了自己;尹小跳走过曲曲折折的成长道路,在与男性的反复周旋中,终于进入了自己“内心的花园”,体会到了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
一、搁浅式的累——章妩
章妩虽然是铁凝在文中着墨不多的一个人物,但其位置牵连着各种人物的心境和命运。她的自我享乐意识张扬得最为本我,她的行为对于男权文化中规定的妇德、母性解构得最为扭曲,她的试图回归、赎罪又是那样让人觉得可怜和累心。
在“文革”年代,章妩和丈夫尹亦寻被下放到苇河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生存条件的恶劣和清教徒式的生活让章妩无法忍受。在这里,人的物质、生理和精神上的需求受到压抑,最后出于明显的功利目的和对于性欲释放的渴求,章妩用自己的肉体换来了一纸病症确诊书,从而求得了舒适的生活,同时又兼顾了肉体的享乐。
章妩是打着生病和照顾家中两个尚未成年的女儿的幌子回家的,但她回去后却弃女儿于不顾,不惜一切去取悦唐医生。在这里,传统母性的宽容、关怀、博爱、无私、坚韧、温柔被章妩完全解构了。“男权文化制造的母亲神话,或唆使女性甘于生殖劳役,为养育子女全面牺牲、丧失自我;或把异化了的母性、与男权合谋的母亲,加以神话,致使男权神话继续全面地统治、控制女性。”[4]但章妩的行为看不出一点母德的影子,她没有为女儿做出的一点点的牺牲。恰恰相反,她只懂享乐,在她假装的修养期间是她懵懂的女儿每餐侍候着她,她从尹小跳那里一直索取。因此后来小跳才说“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具备爱抚孩子的能力,尽管世上的孩子都渴望着被爱,并不是每一个母亲都能够释放出母性的光辉,尽管世上的孩子都渴望被这光辉照耀。”①参见: 铁凝. 大浴女[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57. 下引同一作品内容均出于此, 不再一一注出.我们虽然不主张男权社会倡导的母亲要毫无保留地付出,彻底泯灭自我,从而神话母性,但源于母性天然的爱子女和担当责任的品性还是不能一同否定掉的,否则就不仅失去了母性,还是人性的裂变。冰心也说过“一个人要先想到自己是一个人,然后再想到自己是个女人或男人”。章妩是在情欲的迷失中导致了人性的畸变。
章妩不是一个好母亲也不是一个好妻子,她践踏了贤妻良母代表的内容(贤惠),甚至连形式一下都做不到(她用她与唐医生的私生女尹小荃打破了家的平衡),传统的妇德不能约束她。虽然小荃的真实身份没有公而告之,但在那些当事人心中是心知肚明的。丈夫尹亦寻清楚地知道尹小荃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处境,但只能装作不知道,对此无能为力,无计可施。他不愿也害怕这秘密被人揭穿,他以惊人的“内力”承担着妻子带给他的公开羞辱,维持着这个看上去还算体面的家。在这件事上章妩将封建社会中男性三妻四妾,偷情,拥有私生子的合法性颠倒了过来。
章妩对母性和妇德的叛逃,不仅改变了相关联的人物的心境和命运,而且也使自己搁浅在亲情中,亲人异样的眼光带给她精神上的压抑感。私生女尹小荃的出现使女儿小跳陷入了一种恐慌中,小跳害怕正常的家庭伦理关系被破坏,因此小跳亲眼目睹了这个“破坏因素”跌入井中而未出手相救。她自认为这一举动消除了所有相关的人的不安和焦虑,也包括替母亲作了一个了断,她主动地把一切的罪过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在罪过中煎熬着自己,并且一直质问和审视着她的母亲。而章妩的丈夫尹亦寻也因为妻子带给自己的屈辱和阴影,长久的无名之火郁积于胸,无处发泄,一旦机会成熟便会发泄在妻子章妩身上,“他发泄了他想要发泄的却并不显得残忍,他用他的‘不明真相’维持了一个体面家庭应有的正常运转和他本人的尊严,至此他也掌握了章妩对他永远的内疚。他有本领让妻子终生内疚其实是一种极为残忍的能力和一种特别有效地报复手段”。动辄对妻子发脾气、厌烦挑剔、无端指责使尹亦寻从一个稳重谦和的知识分子变成为了一个冷漠霸道之人。而唐菲则因为章妩抢了自己唯一的亲人舅舅唐医生,而加剧了堕落的速度和程度。对于章妩自己而言,随着尹小荃的不幸夭折,她亦陷人了深深的罪恶感之中。然而不可思议的是,她逐渐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怪物”,变态式地热衷于整容,她“幻想把自己变个样子,消灭从前的那个我。消灭了从前那个我就好像也消灭了从前的记忆,从前的很多记忆是不愉快的。”对于章妩而言,与唐医生的那段历史始终是无法面对丈夫和女儿的一个根本症结所在。也正因此,她低声下气地竭力讨好家人。虽然尽到努力,但仍无济于事,她彻底丧失了为自己辩解的能力,也注定了要扛着这份罪责继续沉重地走下去,无论是否会被家人原谅,那个家的伤疤总会不时地“流血”。
这也说明女人除了属于事业和家庭,还属于自己,但在爱自己时,还要勇敢面对不幸和磨难,保持自尊、自信、自强、健康,让自己成为生活的主宰,同时也要明白作为一个人应承担责任,奉献须把握牺牲的尺度。这样才能促进人性的全面发展,从而真正地实现女性的自我价值,而享乐、纵情、抛弃责任则只会削弱和销蚀这一目标的实现。
二、扑火式的死——唐菲
相对于章妩来说,唐菲纵情得更彻底,反叛的目标更明确(不会伤及无辜),其行为更悲壮。她是堕落的天使,美丽与邪恶,善良和淫荡,聪明与心机并存。在父权社会里,女人的价值基本上是由“女性美”来控制的。而唐菲这个人间尤物,因为美貌而备受男性“青睐”,但男性对她的美的欣赏并不会让她“站立”起来,成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相反,这只意味着男性渴望占有这种美,而唐菲却将男性对自己的“青睐”当作生存和报复的武器。
唐菲的出生就是个美丽的错误,她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的呵护,父亲角色在她的生命中始终是空白的,她从别人的眼光中读到的只有轻视、嫉恨,憎恶。因此,她从小就学会了利用美貌“征服”男性来进行自我保护。她与白鞋队长的交往,无关爱情,纯粹是出于生理的本能,再加上一点儿青春的虚荣,一点儿无处宣泄也无处填充的寂寞。她指挥操纵着这“威风凛凛的男人”,他和她在大街上面对人们的各种眼光。对于白鞋队长来说,唐菲是件最值得夸耀的特殊财产。唐菲有着一种挑衅世俗、挑衅社会、挑衅道德的魄力,她渴望别人的瞩目,她就是要让人们成为她存在(更多是负面存在)的确认者。她努力变得坚强,有着极强的支配欲望。她陷入了一种怪圈之中:实际能力和心理欲望的不协调。但她却能借他人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
虽然从传统男权社会的观念来看唐菲已不洁,但她心中仍然是渴望纯洁和爱情的。当舞蹈演员用形容莲花“出污泥而不染”的“出落”一词形容她时,竟让她的心猛跳了两下。对于她来说,这是一种遥远而又理想,甚至接近空想的一个词,这是她永远藏于心中的一个梦。对于这位俊美又体贴的男人,她付出了真感情,甚至当她怀孕后还幻想着他能娶她。她一厢情愿地将自己全部奉献给对方,甚至于不向这个男人提出任何人都会要求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平等,只希望他能接受自己的依附。但男人的海誓山盟,与子偕老的誓言在一遇到责任时就粉碎成了灰尘。当唐菲用性取悦男性,当她附属于男性时,她是美丽的天使,当她为自己考虑,想争取幸福的权利时,在男人眼中她俨然是魔鬼,男人对她唯恐避之不及。
她渴望家庭,渴望安稳,当她和小崔结婚后,别的男性感觉到的是一个所有权归公的女人突然变成了小崔的私有物,因此他们感觉心里很不平衡,他们公开污辱小崔,也陷害唐菲,小崔在流言蜚语中动摇了,感觉到自己的男性尊严,丈夫的权利受到了挑战,深陷于“所属物”被别人觊觎时的恐慌中。在强大的夫权阴影的笼罩下,唐菲的精神处于萎缩状态,因为无端的谣言使唐菲受到丈夫的性虐待。起初,唐菲竭力解释,当解释无效时,她承认了这种欲加之罪。并不是唐菲不想从良,而是整个男权社会不给她这个机会,甚至联合毁灭了她想走的正途。她只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去生存,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去报复男性。
俞大声是一个假定性的人物,是可以任意填充内容的人物,你既可以认为他是一个有爱的领导,又可以认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懦弱的父亲。但种种迹象表明,他极有可能是唐菲的父亲。唐菲一生都在寻觅自己的父亲,尽管无法享受父爱,却依然渴望着、期盼着。但俞大声却表现出一种略带冷酷的淡定,难道是怕这个私生女毁了他现在的生活,毁坏他的名声、地位吗?抛妻弃女,难道是父权制文化中男性可以私下享有的权利?唐菲的人生最终惨败,尽管不奢望有父亲疼,但临死之前她连家的归属感都不曾有,是谁让她的人生和灵魂如此悲哀、不安、动荡?除了她自己的原因外,还有整个男权社会对她的戕害、遗弃和合围。
唐菲最后终于认清了男人的虚伪,以及他们的“相貌要美,灵魂要空”的玩物标准。唐菲的灵魂是躁动不安的,依附的不稳定,精神的危机感使她愈加想利用自己的美貌和青春来为自己谋求利益。无论白鞋队长、舞蹈演员还是小崔、俞大声,她都是用性来征服他们,获得一时的主动权,而同时,与她接触的男性则在她身上获得肉欲的满足。但是她却永远只是被损害、被霸占的对象。她以一个荡妇的形象去挑战规矩的传统女性形象,去反叛男权社会,她不是什么性解放的代言人,她是社会畸形性别制度的产物。她身上体现出的并不是真正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而是以恶抗恶的报复心态。而这种对男性的攻击最后只能是害人害己,唐菲的人生只能以飞蛾扑火般的姿态悲剧收场。
尹小跳的成长正是女性一步步从男权文化的藩篱中痛苦脱身而出的涅槃史。无论是女性唐菲,还是男性方兢、父亲、陈在,他们都在小跳浴火重生的“火堆”中加上了一把重重跳跃的火焰,让她最后“焚烧”得干净,“重生”得彻底。
小时候尹小跳对唐菲身上那股子无以名状的颓废激动不已。不谙世事的她崇拜这位颓废的美女,其实就是下意识中女性意识的萌发,是对传统女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质疑。正如铁凝对勃鲁蒙尔的油画《疯狂玛格》所评价的那样:“我宁愿相信这是勃鲁蒙尔描绘的一场中世纪女性的彻底革命,一场女性的集体狂欢,因为她们是底层,她们的痛苦便双倍十他人。她们一旦革命,便也格外具有爆发力。”[5]
在接触中,尹小跳迷恋上了方兢,但在她这个年龄,以她的阅历,她一时还无法区别崇拜和爱,才华横溢的方兢正好满足了小跳的虚荣心。当他们看完电影后,小跳躺在家里的床上,却发现根本就忘了他的长相,害怕和焦虑的情绪如潮水般涌来,并且伴有不详的预兆。方兢此时只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是一种男权社会的符号,是一种才情和地位的象征。小跳的偶像崇拜,她所迷恋的只是一个影子,是千百年来女性对于自己在文化和知识方面权利缺失的一种想象性补足,她想通过靠近方兢,从而靠近男权中心,这是小跳对传统的认同和自觉的追求。当小跳坐在沙发上静静地听着方兢的谎话,“觉出一种亲近的默契。她感谢他这一串串熟练而又油滑的谎言,感谢他为她拒绝了他(她)们。那是他为她而撒的谎,一切都是为了和她的相聚。”她处于方兢用语言编织出来的华丽但又赤裸(真实的残酷)的圈套之中。因其华丽,让她沉沦;因其赤裸,让她越发痛苦,越想挣扎。年轻的女子心中也许都渴望着一位“神”人,尽管跟这位神发生关系有诸多的不合时宜,但对年轻的女子来说,这种交往充满了离经叛道的意味。年轻女子和这样一位“神”人的交往过程中,因只能仰望他,只能跟在他的“思想”和“境界”后面,由此便产生了错误和悲剧。也许这是女性成长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炼狱。
其实我们深入思考后就会发现,小跳对方兢的无条件容忍和服从是为了另一个目的:减少罪责,荡涤灵魂。小跳在小荃事件中有了道德上的污点,那以后很长时间,她的思想就一直处在迷雾中,她一直在错误的地带寻找着救赎的道路。小荃的死带给她痛苦和折磨,让她一直有一种受虐的心理,方兢伤她越深,越是悲痛欲绝她越感觉到轻松。小跳想通过方兢的“他虐”,依靠男性来进行“他救”,通过肯定男性的力量和权威来摆脱自己灵魂上的不安,但这种道路是行不通的,男权社会当然不会主动让渡权利给女性,也不会主动去救赎女性,让女性有更多的精力去争取女性的地位。所以小跳后来渐渐清醒了,终于明白了方兢的“坦率”与其说是对对方的尊重信任,还不如说是一种不把任何人当人看的霸道。于是她开始“尖刻”“婆婆妈妈”,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方兢意识到了小跳对自己的抱怨,看到了小跳在思想上的成长,知道小跳不会再简单地臣服于他,于是开始对小跳产生畏惧感。方兢为了给自己留更多的退路,为了让自己孱弱的内心不被心智渐渐成熟的小跳窥破,他冠冕堂皇地甩掉了小跳。但小跳居然一点儿也不恨他,没有爱哪有恨,她意识到她的平静和超脱可能正来自于方兢的折磨。因此,表面上看是方兢抛弃了她,实际上是小跳利用方兢带给她的折磨、痛苦来进行赎罪,利用男性来进行道德的自我完善,从而回到无罪的本初。
身处父权制文化中的小跳,小时候对父亲是依赖、亲近的,她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信告诉正在劳改中的父亲,对自己的母亲逃避养育子女的责任,背叛丈夫出轨的事情,小跳一直挣扎着是否借父亲之手惩罚这个违背了父权社会中“贤妻良母”角色设定的女性。虽然她最后放弃了这种惩罚方式,但父亲尹亦寻以他自己的方式一生都在惩罚妻子。他的惩罚方式并不暴力,但却让人觉得持久和闹心,在家庭琐事中他处处挑妻子的刺。成年后的尹小跳逐渐原谅了母亲的过错,因为“千百年来,在一代代女性对自已的母亲身份和命运的深刻认同中,隐藏的是一个个对父权制微笑着的脸谱后哭泣着的女性。”[6]所以她对于父亲后来表现出来的睚眦必较,心胸狭窄的品性在言语中多有顶撞。这意味着,父亲并不是永远高高在上的,并不是完美的存在,并不是永远能给自己成长导向的航标。小跳学会了用人类普遍的道德标准去评价男性和女性,这也意味着女性有了独立思想的能力。
小跳与陈在虽然是灵与肉的完全结合,虽然是男女平等、互相爱慕的真正爱情,但他们却在不恰当的时机袒露了相互的心意,违背了道德原则,伤害到了无辜的人。陈在承诺与合法妻子万美辰离婚,娶小跳,并付诸了行动。其实对于陈在和万美辰这段只有单方爱情的婚姻来说,离婚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是陈在和小跳自私的对于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万美辰的伤害。陈在、小跳、万美辰似乎都是受害者同时又是施害者。但小跳看出了万美辰对陈在的依赖和执着苦恋,也看到了陈在对十年发妻的惦念。她深刻地意识到爱一个人并不是要占有他,陈在对妻子的惦念显示了他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而这点让小跳发疯地爱上了他,但是也因为这点小跳又不顾一切地把他推走。自己则选择在灵魂的安宁中走向自己内心的花园。铁凝在这里构建了一种和谐的两性关系,彼此承担,相互独立的男女关系。这是具有了独立主体人格意识的女性对自我性别角色的体认。小跳更注重于女性伦理道德的拷问,在这种拷问中升华自我,尽管可能会使自己孤独地承担命运,但却是一身的轻松、清明恬静。
四、结 语
“成为自己”是伍尔芙对现代女性意识的形象阐释,其实质是重建女性自我,是对菲勒斯中心文化的率先解构。铁凝笔下的章妩和唐菲在“成为自己”的道路中迷失了方向,导致了价值取向的错位。作家在尹小跳身上则寄予了更多的厚望,并让她真正“成为自己”,并且同时成全了别人。所以铁凝追求的妇女解放的思路应是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使男性和女性更好协调地发展自我,使女性在真正意义上进行自由的思考和行动,实现两性关系的和谐维系和共同发展,因为人类社会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构成,缺一不可,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参考文献
[1]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309.
[2] 西慧玲. 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8.
[3] 栾建民. 建构丰富的艺术世界: 铁凝小说论[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9: 1-50.
[4] 盛英. 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04: 115.
[5] 铁凝. 遥远的完美[M].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03: 15.
[6] 闫红. “疯狂玛格”: 神话窥破之后的镜城突围: 论铁凝作品中女性主体身份的现代性诉求[J]. 理论与创作, 2006, (4): 55-59.
(编辑:刘慧青)
On Female Consciousness of The Bathing Woman
TAO Lijun, JIN Wenb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325035)
Abstract:In Tie ning’s The Bathing Woman, the image of the three women Zhang Wu, Tang Fei, Yin Xiaotiao, clearly reflects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s the heroes of the novel, they own different life attitudes and mental process, which react against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and manifest the existence of the female. Zhang Wu lost herself in the enjoyment of flesh and the dissimilation towords the maternal instinct and female moral. Tang Fei destroyed herself by material attachment and the game of sexual revenge. Through the tortuous growing path in the course of the repeated intercourses with men, Yin Xiaotiao finally reached her own “inner garden”, got to know a harmonious sexual relationship.
Key words:The Bath Female; Female consciousness; Tie ning; Attachment; Rebel; Self-save
作者简介:陶丽君(1990- ),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4-08-04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4.002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4-0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