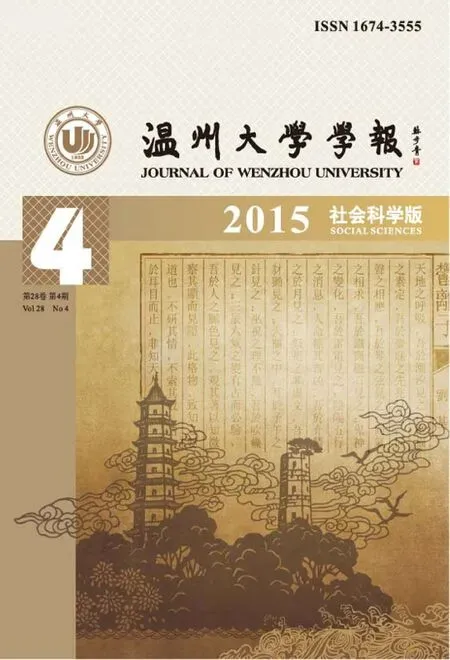《公理日报》和《热血日报》之比较考证
2015-03-17罗文军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何 霞,罗文军(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公理日报》和《热血日报》之比较考证
何霞,罗文军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0)
摘要:《公理日报》和《热血日报》经常被相提并论,但是由于两份报纸的不同政治背景,其编辑、发行、命运还是有相当大的不同。《公理日报》在闸北印刷,《热血日报》先是按照惯例在公共租界印刷,此印刷所被封后也改成在闸北印刷。《公理日报》的发行所在郑振铎的家里,《热血日报》由于销量增大而易地发行,两者的发行所都在闸北。《热血日报》分工合理,经费充足,领导重视,它停刊主要是外部原因。而《公理日报》经费不足,成员组成复杂,政见不一,停刊原因是内外交加。但两份性质不同的日报都为宣传“五卅”爱国运动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公理日报》;《热血日报》;瞿秋白;郑振铎
《公理日报》和《热血日报》都是在1925年“五卅惨案”背景下诞生的,前者发行时间为6 月3日,后者为6月4日,离“五卅”仅三四天。两份报纸都极为短寿,前者6月24日停刊,共出版22期,后者6月27日停刊,共出版24期。但两份报纸都对“五卅运动”作了详细报道,起到了反帝急先锋作用,在当时也极其畅销。正因为起止时间、报道内容以及题名上的极其相近,两份报纸不管在当时还是在当今学界经常被相提并论。《热血日报》编辑之一郑超麟在回忆当年办报经过时说:“五卅运动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资本家为了表示爱国或其他原因,拿出一万元给职工办一张小报,职工们于是出了《公理日报》,固然是爱国的,同情当时轰轰烈烈的运动的,但态度温和而稳健,瞿秋白看了后对我说:‘那里有什么公理,我们自己来办一个《热血日报》罢’。几日之后就办起来了。”[1]《上海新闻史(一八五〇 - 一九四九)》论及此也说:“同《热血日报》协同作战的有《公理日报》等报刊”[2]事实上,两份报纸的政治背景、内容意旨、编辑发行、命运遭际都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两者之间的差别及相关史实做出辨析,厘清一些相关问题,在当下学界的研究中也就显得尤为必要。既往研究多集中在这两份报纸的内容等方面,笔者认为针对报纸经费、发行等进行的外部研究有时更能揭示本质,溯本追源。
一、编委组织与经费来源
作为重要的社会事件,“五卅”惨案的发生,理应在报界引起及时关注并被详细报导,但事实并不如此。外国报纸在驻北京公使团的密令之下纷纷鼓噪说“五卅运动”是“赤党”搞起来的,是“赤俄”煽动的。而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则畏惧工部局的政治经济压力,为求自保,有的对事件轻描淡写,有的回避或歪曲事实,有的甚至连罢工罢市的消息都不敢报导。
惨淡发生后的第二天清晨,中共中央在闸北横滨桥附近一幢旧式楼房里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领导全上海人民起来罢工、罢市、罢课。针对当时上海的中外报纸不作为的情况,决定出版《热血日报》,由瞿秋白负责,并从中央宣传部抽调郑超麟,上海《民国日报》抽调沈泽民、何味辛组成编辑委员会。据郑超麟回忆录说:“每日社论几乎都是秋白一人手笔。我和泽民写一般的论文,兼编辑区委和总工会交来的新闻,何味辛专编辑新闻”[3]关于分工,在《关于瞿秋白办〈热血日报〉的一点回忆》这篇文章里,郑超麟又说,“秋白写社论,我写文章,沈、何二人编新闻,有时也写文章”[1]沈泽民从专写论文变成专编新闻的了,大约分工没太明确。当时陈独秀也在上海,瞿秋白与陈独秀几乎每日碰头,所以他写的社论反映了中央的意见。一直以来,学界都默认《热血日报》的发刊词是瞿秋白所写,近年来有学者考证应是陈独秀手笔[4]。负责发行的张伯简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卅”时期创办的国民通讯社的领导之一,同时也负责机关周刊《向导》的发行。可以说,《热血日报》的编辑和发行负责人都是当时上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工作中的精兵良将,而且分工合理,有利于发挥个人优势。
根据郑超麟回忆,“我们新有一笔经费做‘国民运动’之用的,中央决议要办一个通信社和一个小型报,本在筹备之中,事情发生都提前成立了。”[3]“通信社”即国民通讯社,“事情”自然是指“五卅”惨案。为什么中央决议要办一份“小型报”和“通信社”,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民国日报》改组失败。1924年5月6日瞿秋白致信鲍罗廷里面提到“《民国日报》”“新机器”和“每月的经费”。同年10月8日他再次致信鲍罗廷:“《民国日报》必须彻底改造。您是否已经同中派及孙本人谈过?中央已决定自十月中起停止付款。”[5]165中央一直致力于改组《民国日报》,投入了金钱、机器、人力,但1925年孙中山北上途经上海时,叶楚伧又开始掌握该报,“改造”宣告失败。而当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机关刊物《向导》是周报,显然不能满足每天变幻莫测的革命形势需要,所以中央不得不筹备一份日报,其经费可能也是原来提供给《民国日报》那笔资金中的一部分。
北洋政府时期中共中央经费主要来自共产国际提供的党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没自己的武装,经费主要用于联络宣传,宣传的重点是出版报刊杂志。《向导》在第15期发表文章《敬告本报读者》,公开向社会募集资金,可见经费十分紧张,不能完全满足报刊的出版发行。1924年12月7日,维经斯基在与陈独秀交谈后给加拉罕写信,“请从国民党经费中拨给我们一定的数额用来实现国共合作两党提出的口号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我请求为了整个这项工作给我拨1万卢布,由我负全责报账。”[6]郑超麟说“新有一笔经费”可能有一部分来自这笔“国共合作”专款。
与此同时,其他民主爱国人士也被“五卅惨案”激怒了。6月1日,郑振铎在自己家里召开“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联合会是由当时上海的一些学术团体组成。会上,大家对上海报纸“对如此残酷的足以使全人类震动的大残杀案,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7]表示极大愤慨。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等人倡议自己来办一份报纸,这个倡议当即得到一致赞同。经郑振铎提议报纸就叫《公理日报》,报头由叶圣陶书写。当时很多报纸发表评论,要群众保持冷静,提出“诉诸公理”“法律解决”等口号。《公理日报》的名字可能受此启发而来,显得理性而公正。
《公理日报》的经费由各团体募捐,但显然远远不能满足日常运营。张元济的传记里提到6 月2日高梦旦、王云五来访,说郑振铎想要办份报纸,三人商议以个人名义每人捐款100元,另外商务印书馆还以公司名义认捐[8]。据《公理日报》停刊宣言,最初筹措到的资金也仅有三四百,这么算来商务印书馆公费资助可能也就100元左右。《公理日报》的经费虽名义上由各团体募捐,其实主要来自商务印书馆,郑超麟回忆所说商务印书馆拿出一万元办《公理日报》应为误传。
为筹措资金,《公理日报》登刊启事要求各界捐助,捐助人姓名数目在报上登出,一段时间后还公开账目。这些做法既解决了问题,又与读者进行了充分的互动,只有这群富有创造性思维的爱国青年才想得出这些办法。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曾经高度评价郑振铎的人格魅力和胡愈之的聪明有主意,“郑振铎先生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能把朋友们团结在一起。”“胡愈之先生是极会出主意的。《公理日报》有些做法在当时是非常新鲜的,很可能就是胡先生的主意。”[9]
《热血日报》是中共办的第一份日报,也是机关报,编辑成员都是中共党员,因此组织性很强,分工合理,各尽其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直接为《热血日报》撰稿,甚至具体负责报刊的编辑。《热血日报》经费充足,组织完备,领导重视,它停刊的主要原因来源于外部。而《公理日报》的成员组成相当复杂,虽名义上为学术团体,但其政治倾向大不相同,编辑成员之间意见不合乃至分道扬镳应是常事,这为日后《公理日报》停刊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公理日报》是募捐筹集的资金,来源不稳定,随时面临经费不足的危险。但是,各方政见不同的团体能迅速地筹措资金,组织编委,早于《热血日报》一天就印出《公理日报》,这也是因为爱国人士被“五卅”惨案激怒的结果,正如《热血日报》发刊辞所言:“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而大革命的高潮也即将来临。
二、报社地址与出版发行
有关《公理日报》的计划虽然大家一拍即合,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最棘手的经费问题解决后,时值“三罢”斗争的高潮,纸张、印刷、发行等都是大问题。大家商议的结果是,发行由职工和学生们自愿担当,发行所就设在宝山路宝兴西里9号郑振铎家。当时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由于郑振铎和商务印书馆的特殊关系,所以很多资料包括《郑振铎传》都提及《公理日报》的“纸张和印刷完全由商务印刷所的广大职工包了下来”[10]131。郑超麟在回忆《热血日报》的报名时也提到:“因为已经有一个《公理日报》出版了,那是商务印刷所印的”[3],其实不然。
6月2日张元济对来访的高梦旦、王云五说:“事关爱国,我们不能阻止。至于代印报纸,翰翁与鲍先生有顾虑也有道理。闸北在奉军张宗昌控制下,发行所处于租界中心,总商会又不支持抗议活动,公司在夹缝中求生存不能不小心谨慎。我看捐助郑振铎他们一些款子,让他们到别处去找印刷。”[8]最后《公理日报》选择了闸北一家小印刷所,据《公理日报》最后一期《停刊宣言》,“本报因种种的便利,不得不在闸北印刷”,这里所说“种种的便利”,至少有三条:第一,闸北位于华界,在反帝方面言论相对自由。第二,闸北是工人聚居地,人工费相对租界便宜得多。第三,郑振铎的家也在闸北宝山路,从印刷所到发行所的距离很近,也是为了节约运输成本。
于此相对的是《热血日报》,《热血日报》不在闸北印刷,而是在公共租界印刷。据郑超麟回忆,中共中央那时也决定办一个印刷所,但来不及开工。《热血日报》是由梅白格路(今名新昌路)明星印刷所承印的。每天黄昏,郑超麟把全部稿子带回梅白格路,排出后他再校对。明星印刷所是一家比较大的印刷所,老板徐尚珍是同情共产党的党外人士,他同时还承印《向导》《中国青年》《解放周刊》等进步刊物。到后来明星印刷所被封后,“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勉强印了一期,以后《热血》就停刊了。”①参见: 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 上卷[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225.“自己的印刷所”是指“五卅运动”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地下印刷所,设在闸北中兴路西会文路的一条弄堂里,为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用“会文堂印书局”招牌作掩护。印刷厂的具体负责人是倪忧天[11]。也就是说,《热血日报》第1期至第23期是在公共租界明星印刷所印刷,该印刷所被封后,最后一期是在闸北自己的印刷所印刷的。
至于《热血日报》的报馆地址也就是编辑部地址,可以说是众说纷纭。郑超麟回忆:“报馆设在闸北香山路近旁”。杨之华则回忆:“编辑所设在闸北中兴路,一间破旧的平房,窗子很低,写字台是几块木板拼起来的。”[12]郑超麟说地址在闸北香山路近旁,杨之华说是在闸北中兴路,香山路先改名为象山路,1980年又更名为临山路②参见: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本市部分公社(镇)、市区、近郊道路更名的批复(沪府[1980]137 号). 1980-10-28.,查阅当时上海地图,其实两者是相隔平行的,离得很近,他们指的应该是同一地点。但是,瞿秋白研究专家陈铁健则认为,“报社设在闸北浙江路底华兴路56号一间客堂里”[13]。的确,翻阅《热血日报》,从第2期起到11期报头左边以小号字体刊登的通讯处地址为“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六七号转”。从第12期起,通讯地址改成“社址 上海北浙江路华兴路五十六号”,陈铁健当是据此断定《热血日报》的社址在北浙江路华兴路56号。北浙江路是南北走向,中兴路和香山路都是东西走向,中间整整隔了一条会文路,大概五六百米。由此问题来了,郑超麟和杨之华都是当事人,他们回忆中的地址高度吻合,那为何又和《热血日报》刊载的通讯地址不在一个地方呢?陈铁健根据报纸上的“社址”认为《热血日报》的地址在北浙江路又是否准确呢?
据《热血日报》编辑部6月16日(是时该报已发行至第13期)在上海《民国日报》头版刊登的启示:“兹为扩大销行的范围起见,特设发行所于北浙江路底华兴路五十六号。”可见,北浙江路56号仅仅是发行所,《热血日报》头版上刊登发行处地址,应该是出于保护编辑部的目的,这也是特殊年代的特殊情况。另,“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六七号转”“转”也就暗示了此地址可能只是代收稿件、邮寄订阅函和读者来信,而非编辑部或曰报社。而后期的“社址 上海北浙江路华兴路五十六号”特意把“转”去掉并且加上“社址”应该是一种欲盖弥彰,迷惑敌人的手段。
《公理日报》和《热血日报》都是八开大小,每天四版,可容一万多字,售价一个铜板,都是采用编写合一的形式。销量都很大,《公理日报》大概在一万五千至两万,而《热血日报》则在三万左右。《公理日报》的发行所在郑振铎的家里,《热血日报》由于销量增大而易地发行。由于《热血日报》上刊载的“社址”是发行所地址,造成了一些学者错把发行所当成报社地址。两者的发行所都在闸北。《公理日报》因为种种便利选择在闸北印刷,《热血日报》先是按照惯例在公共租界印刷,此印刷所被封后也改成在闸北印刷。
三、停刊原因与社会影响
《郑振铎传》里说《公理日报》停刊的原因是,“当时唯一承接印刷的商务印书馆已经复工,无力再承印每天两万份的报纸”[10]132。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第一,当时正值商务印书馆极盛时期,各类办事机构一千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资金雄厚,员工众多,不可能“无力”印刷一份每天两万份的报纸的。第二,在《公理日报》停刊后不久(7月初),商务印书馆旗下的《东方杂志》出版了《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商务印书馆既然有能力承印《五卅事件临时增刊》,那么至少《公理日报》的停刊和商务印书馆的承印能力应该无关。第三,如前所述,《公理日报》为商务印书馆承印系误传,商务印书馆只是暗中给予了经济支持而已。
在《公理日报》最后一期(第22期)由郑振铎执笔写了一篇《停刊宣言》,称报纸停刊的两大“致命伤”是印刷费入不敷出和没有印刷所敢承印。报纸每日印刷费用约在八十元以上,而每日的广告收入加上捐助收入至多不过三十余元。“此外尚有几种别的关系,但不大重要,这里不必絮说”。在《宣言》中提及的几个“此外尚有几种别的关系”中,茅盾认为是《公理日报》揭露上海各报不敢报导“五卅”惨案真相,态度甚为激烈。“此在左、中、右三派混合之学术团体联合会中,惹起右派之反对,中间派之不安;然因编辑实权操在文学研究会在沪会员之手,右派及中间派无可奈何。”[14]叶至善也回忆说,1964年秋天他跟父亲去福建参观,在福州,有一位先生来探望他父亲。朋友走后,父亲对他说:“这位先生是在商务的旧友,从前是国家主义派,参加过《公理日报》的工作。有一篇文章,我用了一句‘打倒帝国主义’。这位先生说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公理日报》不该用。两个人还吵过几句。”[9]后来,叶至善查到这篇文章应该是6月28日第18期的社论,题目是《无耻的总商会》,文章最后号召说:“打翻了无耻的卖国的总商会,我们的步调才可以整齐,才可以打倒外来的帝国主义。”这是《公理日报》第一次明确提到“打倒帝国主义”。之前不提,可能参加的各个团体是有默契的,右派忌讳的就是这个“反帝”的口号。隔了五天,叶圣陶写的社论中又出现了这个口号,公开争吵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结果,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叶圣陶常用署名“秉丞”发表的文章了。《公理日报》最初被“五卅”惨案激怒,成员混杂,政治立场不同,后来矛盾显露并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6月23日,《热血日报》《公理日报》同时被禁售,次日《公理日报》主动停刊。《热血日报》坚持了几天,终于在27日清晨被查封。“早晨七点,梅白格路(今新昌路)186号明星印刷所,突然被大批巡警包围,巡警查获印刷所承印的大量《热血日报》和《劳动青年》、《陈独秀演讲》小册子,查封印刷所。”[5]189郑超麟提供了更为详细的史料:“二十几日后被巡捕房发现,老板吃了二日官司,工厂被封,罚款了结。这些损失由我们赔偿。我们自己的印刷厂勉强印了一期,以后《热血》就停刊了。”③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 上卷[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225.“自己的印刷厂”在闸北,相对安全,办了三个多月才因来取纸型的一位同志被捕而暂时停产关厂。那为什么《热血日报》没继续办下去呢?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热血日报》作为一个急先锋式宣传日报,已经基本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群众“热血”已经沸腾起来,罢工层层扩大,“由外国工厂,到西崽和阿妈;点灯和自来水等待总工会命令,但为市民需要着想没有下命令。有一部分巡捕也到总工会来接头,说他们可以运动罢岗。总工会分好多部办公,几乎不能应付。”④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 上卷[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222.第二,人手不够。瞿秋白作为罢工行动委员会重要成员和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行政工作越来越繁忙,渐渐脱离了他曾经醉心的文艺工作。随着《向导》的编辑彭述之、蔡和森相继病倒,编辑责任逐渐落到郑超麟头上,他也越来越忙,已经没有余暇时间编辑《热血日报》。沈泽民也于1925年结婚,被中央派往莫斯科。《热血日报》的编辑们都忙于其它事情去了。
郑超麟曾经分析过“五卅”运动的爆发的原因,“并非惨案能爆发革命。比此次更惨的案,历史上还多呢,但并未爆发革命。”⑤郑超麟. 郑超麟回忆录: 上卷[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1: 222.他认为革命能借“五卅”惨案而爆发,首先因为此时上海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实力不断壮大,对租界当局的不满越来越强烈,要求多享一点剥削权。其次是因为无产阶级已准备好战斗组织,“上海总工会”仿佛一夜之间出现并向全上海工人发号施令。他主要分析了政治背景,其实他还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报刊的舆论导向。历史上多少惨案因为没有进行及时报道而淹没在历史中,刽子手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而《公理日报》和《热血日报》以大量篇幅对“五卅”事件进行连续报道,把报刊的宣传作用发挥到了极致,让更多的上海人了解到事实的真相,从而积极投入“五卅”爱国运动之中。瞿秋白曾经说过,假使“五卅”前只有几千几万人知道国民革命的必要,“五卅”后就至少增至几百几千万人了。在转变过程中,《公理日报》《热血日报》以正确的舆论思想引导运动的方向,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瞿秋白一向热心办报,他认为“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的多”。
可以说,“五卅”运动中以《公理日报》《热血日报》为代表的刊物是整个革命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一代报人在国家民族危难时挺身而出、大义凛然是值得整个新闻史乃至中华民族铭记的。
参考文献
[1] 郑超麟. 关于瞿秋白办《热血日报》的一点回忆[C] // 史习坤. 瞿秋白研究资料史.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2: 45.
[2] 马光仁. 上海新闻史(一八五〇 - 一九四九)[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66: 540.
[3] 郑超麟. 史事与回忆: 第1卷[M]. 香港: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240.
[4] 龚景春.《热血日报》“发刊词”作者之我见[C] // 刘福勤. 瞿秋白研究文丛: 第6辑.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2: 208-219.
[5] 丁言模, 刘小中. 瞿秋白年谱详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6] 朱洪. 陈独秀风雨人生[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4: 176.
[7] 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 《公理日报》停刊宣言[N]. 公理日报, 1925-6-24(4).
[8] 柳和城. 张元济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205.
[9] 叶至善. 五卅运动中的《公理日报》[J]. 新文学史料, 1982, (2): 23-30.
[10] 郑尔康. 郑振铎传[M].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8.
[11] 王润泽. 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112.
[12] 杜宁(杨之华). “热血”重温: 纪念秋白同志死难二周年[N]. 救国日报, 1937-6-17(3).
[13] 陈铁健. 瞿秋白传[M]. 北京: 红旗出版社, 2009: 162.
[14] 茅盾. 五卅运动与商务印书馆罢工: 回忆录(七)[J]. 新文学史料, 1980, (2): 1-25.
Comparative Textual Research of Gongli Daily and Rexue Daily
HE Xia, LUO Wenjun
(School of Literature , 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China637000)
Abstract Gongli Daily and Rexue Daily are mentioned frequently in the same breath, but they are considerably different in their different political background, compilation, distribution and destiny. Gongli Daily was printed in Zhabei District while Rexue Daily used to be pri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s customary, but after the printing house was closed down, it also moved to Zhabei District. Gongli Daily was issued in Zheng Zhenduo’s home. Rexue Daily moved its sale room as its larger sales. Both of the sale rooms were located in Zhabei District. Editors of Rexue Daily cooperated well and the fund was adequate. Leaders paid a lot of attention. Its suspension of publication results chiefly from the external reasons. The expenditure of Gongli Daily was inadequate and the members came from all walk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views. Its suspension of publication results from the reasons both inside and out side. Anyway both of them have made enormou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 the May Thirtieth patriotic movement in 1925.
Key words Gongli Daily; Rexue Daily; Qu Qiubai; Zheng Zhenduo
(编辑:刘慧青)
作者简介:何霞(1991- ),女,江苏常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4-09-14
DOI:10.3875/j.issn.1674-3555.2015.04.017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中图分类号:G216;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55(2015)04-009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