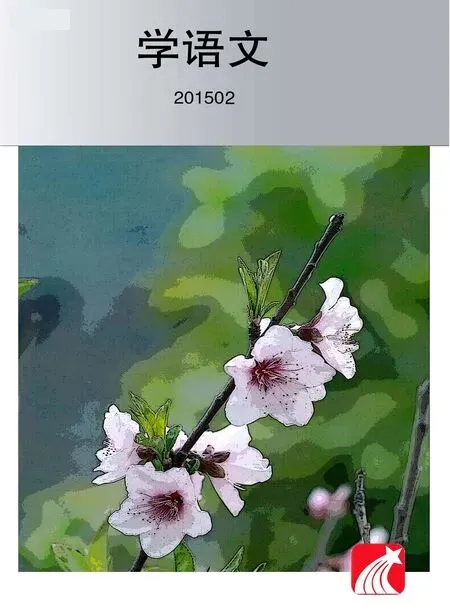“境界”之“真”:中西诗学的化合与汇通
——王国维文学真实观念的建构
2015-02-27刘康凯
□刘康凯
“境界”之“真”:中西诗学的化合与汇通
——王国维文学真实观念的建构
□刘康凯
“真”是王国维“境界说”的核心概念。通过这个概念,王国维化合与汇通中西诗学,建构起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真实观念,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建构。
王国维;境界;诗学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诗学体系最重要的建构者之一,其最具影响的诗学观念是他在《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境界说”。此书开篇明义地指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嗣后又谓:“然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那么这个作为最“上”与“本”的“境界”究系何物呢?王国维没有直接为其下定义,而是从不同角度对境界的各种诗学特征加以描述,根据境界的标准对历代词作、作者、现象加以解释与评判。由于词话采用了传统的印象式、感悟式、片断式的批评方式,对“境界”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理论表述,因此留下了很大的模糊性,也因此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文论界始终在探讨的一个重要诗学问题。本文无意对这些浩繁的讨论结果加以评述,只拟对王国维的文学真实观念做一些探讨。
一
“境界”本来是一个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概念,但在王国维这里,其内涵已悄然发生变生。“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一切景语皆情语”,“词家多以景寓情”,但也可是“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可见,王国维所谓的“境界”不仅指景物,也可指情感。这样,传统诗学意境论的“情景交融”说就得到了重新解释,被注入新的内涵。在写于此前的一篇文章中,王国维还提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在这些现代概念的解释下,境界说就进一步与传统诗学意境论拉开了距离,具有了现代性特征。如果说,王国维通过对构成境界的内容作出了新的界定,从而使境界论具有了诗学上的创新性,那么这还不是这种创新性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是“景物”与“情感”在性质上的“真”。或者说,“真”才是境界之有无的决定性的因素。那么“真”怎么理解呢?它与中国传统道家真论美学所主张的性情之真是否一回事?
王国维在词话中数度用到“真”这个概念,在一处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大作家抒发的情感扣人心弦,描写的景象鲜明生动,用词朴素自然,这与中国传统诗学对优秀作品的要求似乎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我们不要忘了,王国维深受康德、叔本华、歌德与席勒等德国哲学家与诗人美学思想影响,他也有意识地运用西方文学思想来对中国文学进行阐释,在《人间词话》表面上的中国传统文论风格下,掩藏着诸多西方哲学和文学思想的影子。他所采用的概念往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词汇,却暗暗注入西方哲学、美学的内涵,这一点往往很容易为人所忽略。
比如在上引这段话中,所谓的“见”与“知”就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有密切联系。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体,世间万物包括人都无一例外地受意志的支配与驱迫,无往而不生活在欲望的枷锁中。人对世界的一般认识都是服务于意志、受根据律支配的,只能看到意志客观化的各种现象,却无以看到意志的整体。人只有在某种特殊的契机下,或本身秉有的超常的禀赋,悟性(知解力)胜过了意志或挣脱了意志,“不再按根据律诸形态的线索去追究事物的相互关系……也不是让抽象的思维、理性的概念盘踞着意识,而代替这一切的却是把人的全副精神能力献给直观,浸沉于直观,并使全部意识为宁静地观审恰在眼前的自然对象所充满……人们忘记了他的个
体,忘记了他的意志,他已仅仅只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客观的镜子而存在”,主客体都摆脱了一切依附关系,合二为一,这时候,“所认识的就不再是如此这般的个别事物,而是理念,是永恒的形式,是意志在这一级别上的直接客体性”,从某种意义来说,“意志在这里是自己认识到自己”。叔本华认为,科学是遵循根据律的考察方式,其对象只是较低级的现象;而艺术则是独立于根据律之外的考察方式,其对象则是“这世界唯一真正本质的东西,世界各现象的真正内蕴”、“那不在变化之中因而在任何时候都以同等真实性而被认识的东西”,也就是理念;“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对理念的认识,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传达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艺术的审美直观才能够抵达最高真理。王国维深受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上述引文中,“所见者真,所知者深”就不能纯粹在中国传统文论语境中加以理解,其中的“见”与“知”应具有叔本华的审美直观之义,而“真”与“深”相通,都指向把主客体融合为一的理念之真;王氏的“境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即叔本华的“理念”。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也阐释过叔本华关于审美直观的思想:
自一方面言之,则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而后其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即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自他方面言之,则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而观物与其描写之也,亦有无限之快乐伴之。要之,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
“胸中洞然无物”,也就是认识主体挣脱了意志之缚纯粹无欲的状态,“观物也深”、“体物也切”也就是纯粹认识主体在完全的自由中对通过审美直观把握到了对象的本质。此处的“物”严格地说应是“物之种类的形式”,也即理念。纯粹认识主体在凝神观照中把对象从时间的洪流中拔出来,使“在那洪流中本只是微不足道的一涓滴”的对象,“在艺术上却是总体的一个代表,是空间时间中无穷‘多’的一个对等物”,上升到理念的高度,从而获得了最高的真实。“客观的知识,实与主观的感情为反比例”,也就是指主体越能够排除一己的欲望与外物的功利关系(感情也是欲望的表现),实现更高的客观化,就越能够达到理念之真的认识;反之则这种认识的深度就要受到影响。王国在这里所表达的文艺观念和叔本华思想是高度相似的。其境界说中所体现的文学真实观念已经打上西方现代文论的烙印。
二
当然,王国维并非只从西方那里寻找理论资源,作为一位深通国学的学者,他也从中国传统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持。比如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中,他在介绍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无功利思想及纯粹认识观念之后,又说:“苏子瞻所谓‘寓言于物’;邵子曰:‘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此之谓也。”苏轼与邵雍的观念其实都是可以上溯到老、庄的论识论(邵雍虽是理学家,但在认识论上比较多地接受了道家的思想),老、庄认为功利、欲望、理知(理知也是为欲望服务的)会碍妨对道之“真”的认知,人需要通过“涤除玄鉴”、“心斋”、“坐忘”,“外物”、“外身”,“外天下”,在一种凝神状态中实现主客体的合一,才有够获得“朝彻”、“见独”的智慧,从而能够见道、体道、合道。中国老庄思想的认识论与康德、叔本华等的审美认知观念在对功利与理知、概念的否定上是一致的,因此王国维是在坐拥中西两种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它们的化合与汇通,从而建构新的美学与诗学观念体系。就王国维的文学真实观念来说,就不再是中国传统真论与诚论诗学所能范围的了,他的文学之“真”是中西文论汇通之“真”,特别是中国道家真论与德国现代主体性美学真实论相融合之“真”。
然而中西美学与文学思想毕竟在总体上是异质的,在王国维的化合与汇通的努力中,必然会遭遇种种困难。比如叔本华哲学的“意志”或作为其完美而直接的客体性的“理念”,与中国道家思想的“道”均是超验本体,体现最高真实,也是纯粹主体或体道者所要认知的终极之物。但对于叔本华来说,意志是人的枷锁,人只有挣脱意志的牢笼才能够获得卓越的纯粹直观能力,并在对理念(意志的客体性)的直观中体验到一种宁静的喜悦。而对道家来说,道不是人的枷锁,而是人的自由之路,人只有循道而行,才能够获得无限无待的自由,并体验到与道合一的“至乐”。意志是盲目的,而道则循行有常,“有大美而不言”。也就是说,叔本华哲学与中国道家思想虽然在认识论上是一致的,但在本体论内涵上是截然相反的。叔本华的意志论必然导致悲观、厌世的人生论,其理论中的直观能力所能给人带来的愉悦也是有限
的。道家思想虽是超越的,但并不脱离存在,而是一种“即在的超越”;这种超越给人带来的的“至乐”是无限的,因此道家思想是乐观的、肯定人生的。叔本华哲学要求审美认识主体排除欲望和情感,但情感恰恰是文学的核心因素,这样在认识与情感之间就形成了对立,在逻辑上有难以圆通之处。道家思想虽然一方面要求主体排除欲望和一己私情,但另一方面又肯定发乎本心的真情,因为这种自然无伪的情是合于道的,体现在文论上就给文学中的情感留下了余地,从而较圆通地解决了认识与情感可能的矛盾。王国维在汇通中西的尝试中肯定意识到中西思想差异所带来的问题,因此他有时候会忽略这些差异而只求其同,从而留下一些理论上的矛盾。
比如在写于1906的《文学小言》中,还较多地体现叔本华审美直观论的影响,认为认识与感情是对立的。那么如何解释文学中的情感因素?王国维试图在叔本华哲学的框架中解决这个问题,他给出的解释是“激烈之感情,亦得为直观之对象、文学之材料”。这自然是较合理的观点,但并没有解决文学为何需要情感的问题,“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的结论也就落不到实处。在该文的另一处他又写道:“‘燕燕于飞,差池其羽’,‘燕燕于飞,颉之颃之’,‘晛睆黄鸟,载好其音’,‘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诗人体物之妙,侔于造化,然皆出于离人孽子征夫之口,故知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把情感真作为观物真的一个前提条件,这样,认识与感情之真就形成正对例关系,与前文说法颇有相矛盾之处。这个矛盾其实也是叔本华哲学本身逻辑矛盾的反映。在对文学类型的看法上,叔本华根据他的直观论和理念论,认为抒情诗、长篇小说、史诗、戏剧在地位上依序是从低到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客观性是从低到高的;因为客观性越强文学表现理念的真实性程度就越高。“戏剧是最客观的,并且在不止一个观点上,也是最完美、最困难的一种体裁。抒情诗正因为主观成分最重,所以是最容易的一种诗体”。然而在另一方面,叔本华出于他非理性的直观论,推崇文学创造的天才与灵感(在叔本华的解释中灵感就是天才的审美直观状态),而灵感的产物总是一气呵成的作品,如速写、即兴曲、抒情短诗等,它们是“瞬间狂喜、灵感和天才的自由冲动的纯粹作品,不掺入任何反省和思考”,因而“是纯粹令人赏心悦目的,比那些需要缓慢而审慎地制作的长篇巨制,效果要可靠得多”。叔本华的这两种说法显然有矛盾之处,这些矛盾之处也在王国维的诗学体系中留下的印迹。
三
王国维并非不假思考与选择地接受西方思想,当他发现后者与中国具体的文艺实践有难融之处,也会对后者加以去取与修改。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把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两者在价值上无分轩轾。这样,主观情感在诗歌中的表现就有了合法性。那么何以“有我”的诗依然“有境界”呢?王国维给出的逻辑是,虽然作为创作者的“我”没有摆脱主观情感和欲望,但这个“我”因其情感的真实、肫挚、深沉,就可能上升为普遍情感和永恒人性的一个典型,成为整个人类心灵的一个映像,从而获得崇高的地位和价值。比如他在比较宋徽宗与后主词时说: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王国维这里对尼采的引用,颇有断章取义之嫌,这里且存而不论,那么何以徽宗词不及后主词?王国维认为前者“表达的只是个人的身世之慨,这种个人的身世之慨未能上升到人类普遍情感的高度”,而后者的“身世之感融汇了人类生存中的失意悲伤,是他个人的,也是人人的”,因此它们在价值上的“大小”不同。固然两者的情感的真实性都不能否认,但显然在真实的深度上有不同,徽宗表达的只是浅层的哀戚,不具有普遍性意义;而后主表达的则是深沉激烈的悲怆,仿如用血写成的一样,从而成为人类悲剧性命运的一个典型,因此更具普遍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称后主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因此,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实际上已经对叔本华的理论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和去取,不再把直观的客观性要求与情感的主观性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统一、协调起来,认为两者可以形成互相促成、相得益彰的关系,其理据就是情感的高度真实可以具有普遍性意义,从而成为整个人类心灵的一个象征。在高度真实的情感状态下,人虽然依然可以保有强烈的欲望,但这欲望上升为整个人类的欲望,而不是一己的私欲。这样,主体由于摆脱了作为个体与世界的功利关系,依然可以成为纯粹主体,从而拥有
直观的能力,见出最高真实。
通过这一取舍和修正,王国维就把叔本华理论与中国传统道家真论诗学观念融通起来,从而能够更圆满地解释中国传统诗歌的各种现象和特征。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间词话》里,王国维反复强情感真实的意义和价值,他所赞赏的词人如李煜、冯延巳、欧阳修、苏轼、秦观等都是典型的“主观诗人”,词作中都表现了强烈而真挚的情感。尽管他也强调“景真”的价值,但“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情感真实还是第一位的。也正是以此为价值标准,王氏崇五代、北宋而抑南宋,对吴文英、张炎、史达祖、周密、陈允平等极尽贬损,认为他们雕琢文绣,缺少性情,“同归于乡愿而已”。在评价《古诗十九首》时他说: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坎轲长苦辛”,可为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读之但觉其亲切动人。非无鄙词,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病,而游词之病也。
“淫词”“鄙词”本是正统儒家诗学的大忌,但王国维却对《古诗十九首》的“淫词”“鄙词”发出由衷赞赏,因为这其中体现了情感的真挚和生命的鲜活,具有动人的力量。与表现了“真”的诗句相反,则是所谓“游”词,也即“哀乐不衷乎性,虑叹无与乎情”的刻板模拟之词章,这种词章不但不能动人,反而令人生厌。“游”即是浅薄与虚假,与“真”恰相对立,是诗的大忌。《删稿》里也表达了类似观念,如“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儇薄”也就是无情,“忠实”也就是有情。情感的真实无疑是《人间词话》的最高美学尺度。持此尺度,王国维打破了正统的儒家道德化文论体系,汇通与化合中国传统真论诗学与以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现代诗学,把批评标准完全建立在情感真实的基础上,有力推进了中国现代文论体系的建构。
[1]王国维:《人间词话》,见刘锋杰、章池编《人间词话百年解评》,黄山书社2002年。
[2]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全集》第一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97年。
[4]王国维:《孔子之美育主义》,《王国维全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
[5]AthurSchopenhauer.TheWorldasWilland Representation,vol.2.PayneE.F.J.(trans). NewYork:DoverPublication,1966.
本文系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中国现代‘文学真实’观念的发生”(项目号SK2013B321)”、巢湖学院科研基金启动项目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巢湖学院文学与传媒系)
[责编曲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