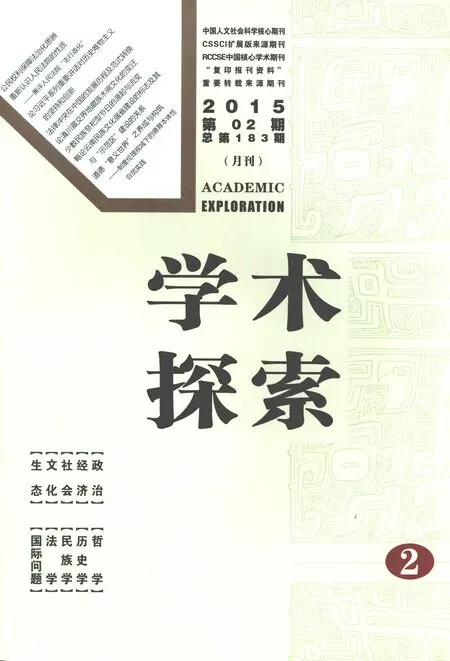重新认识人民法院的性质
——兼评人民法院“去行政化”
2015-02-26沈寿文
沈寿文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重新认识人民法院的性质
——兼评人民法院“去行政化”
沈寿文
(云南大学 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我国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将人民法院定性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但这一定性并不能解释人民法院现实生活中承担的非审判职能,也无法回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人民法院“去行政化”改革的目标。只有正视人民法院同时具备司法(审判)机关和司法行政(审判管理)机关的双重性质,才能为司法改革提供出发点,也才能理解人民法院“去行政化”的实质。
人民法院;性质;司法行政
一、问题之提出
现行《宪法》(1982年制定、2004年修正)第132条和《人民法院组织法》(1979年制定、2006年修正)第1条均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按照一般的理解,“国家的审判机关”当然是国际社会意义上的专司司法裁判的“司法机关”。①本文所谓“司法机关”,特指负责司法裁判的法院;“司法”,特指法院的裁判活动。因而,“人民法院”在性质上便是国际社会意义上、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相提并论的“司法机关”。源于当前人民法院的实际运作存在着与这种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的运作“规律”相背离、不利于“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的“中国问题”意识,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学者忙于阐释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的基本特征和运作规则,其中不乏真知灼见;②参见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载《法学》1998年第8期;王利明著:《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苗连营:《宪法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研究》,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张千帆:《转型中的人民法院——中国司法改革回顾与展望》,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对普及“司法机关”知识、启蒙法治功不可没。也正是站在“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机关)这一法
律文本定性的前提下,理论界发现了当前中国司法(人民法院)存在着“地方化”和“行政化”两大严重的问题。[1](P111~116)这种理解意味着,只要法院“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人民法院的国家审判机关”的性质便能得到彰显,司法公正和司法理性便可能得到实现。然而,至少在“去行政化”的问题上,到底什么叫作“行政化”和“去行政化”,人民法院能否“去行政化”,如果能够,如何“去行政化”等问题,本身值得进一步思考。当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揭橥的新一轮司法改革中,改革的剃刀似乎同样挥向司法(人民法院)的“地方化”与“行政化”这两根刺眼的“杂毛”;然而,“去地方化”与“去行政化”本身可能面临着内在的张力——至少在“去地方化”的阶段,可能恰恰以强化某种垂直层面的“行政化”为代价;而改革的这种内在的张力同样根源于对“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法律文本上的定性。在这个意义上,澄清人民法院的“实际”性质、而不是“概念”性质,是全面理解当前司法(人民法院)改革存在问题的基础,也是司法改革能否成功的前提。
二、人民法院的“非审判”职能设计
如果一国的法律制度是严肃且尊严的,那么该国的法律制度便不应当是相互矛盾、甚至表里不一的。当前,《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性质定位,至少在人民法院“非审判职能”的制度设计——尤其是人民法院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关系的制度设计上难以得到合理解释。从宏观上看,《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将人民法院定性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按照这一定性,人民法院的职权便是与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的职权相同或类似,即裁判各类案件、解决法律纠纷的机关,这种法律纠纷可能是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民(表现为公民及其集合体)诉人民(表现为公民及其集合体)的民事案件;①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殊情况下,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可以提起刑事诉讼案件,即所谓的“刑事自诉案件”。可能是由检察机关代表政府(Gov ernment)诉人民(表现为特定的公民或者公民的集合体——如我国的所谓“单位”)的刑事案件;还可能是人民诉政府的行政案件或者宪法案件;或者是政府某一分支或者某一部分诉政府(Gov ernment)另一分支或者另一部分的宪法案件;甚至是由检察机关起诉人民或者行政机关的“公益诉讼案件”。②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按照这一制度设计思路,检察机关将有权对诸如污染环境、侵害公共利益的公司、企业提起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将有权对诸如行政不作为导致有关公司、企业环境污染、侵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主管部门提起环境公益行政诉讼。而裁判各类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首先意味着人民法院作为一种“法律技术性机关”的司法机关,应当与作为“政治性机关”的立法机关,以及作为兼具“政治性和行政技术性机关”的行政机关之间存在着“结构功能”上的差异。[2](P15~19)其次,意味着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应当远离“政治”,而非卷入“政治”,因为“政治”只有立场不同、无所谓法律上的“对错”,因而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无法(也无能力)解决“政治”问题。再次,它还意味着,为了法律纠纷理性、公正地解决,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不仅“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26条),而且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更应当“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立法机关等政治部门的干涉”,因为“审判权”的客观、中立品性要求司法机关在个案中对少数派意见与多数派意见应当一视同仁,[3](P1571~1574)否则案件的审判通过民众的投票来决定胜负即可、从而没有设立司法机关之必要。然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和有关法律关于人民法院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关系的制度设计,却背离了“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性质。
一方面,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议会至上”的体制之下,[4](P36)由于人民法院这一“国家审判机关”由同级人大产生(《宪法》第3条第三款)、其组成人员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任免(《宪法》第62条、第67条、第101条第二款,《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4条),因而,必须对产生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接受它的“监督”(《宪法》第3条第三款、第128条,《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6条第一款)。然而,这里所谓的“负责”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是法律责任还是政治责任?这里所谓的“监督”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是法律行为还是政治行为?显然,如果这里的“负责”所应承担的是一种法律责任的话,那就意味着人民法院需要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承担法律责任,而法律责任从类型上看,则有所谓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违宪责任,[5](P172~173)它是以存在宪法或法律上的是非(违宪或者违法)为前提的。但是,当作为人民法院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的体现之一的人民法院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6条第一款),没有被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时,③极端的例子有:“2001年2月14日上午,沈阳市第12届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按预定程序进行大会表决。一项项议程顺利通过。当进行到对关于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决议表决时,电子屏幕上的投票结果却让人大吃一惊:人大代表应到会509人,实到474人,赞成218人,反对162人,弃权82人,未按表决器9人。赞成票没有过半,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未获得人大代表通过。”资料来源:http://www anyangrenda gov cn/Article/ShowArticle asp?ArticleID=991(访问时间:2014年3月15日)。人民法院并没有触犯《宪法》或者哪一部具体法律的哪一个条款,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法律责任”;人民法院所谓的“负责”仅能指承担某种“政治责任”而已。如此一来,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实践中由法院院长代表本级人民法院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没能被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谁来承担这种“政治责任”?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13条所明确规定的“人民法院……的负责人”吗?这里所谓的“人民法院……的负责人”就是人民法院院长吗?假使就是人民法院的院长,那就意味着人民法院的院长必须对整个法院的“司法审判”后果承担“政治责任”,也就意味着既然人民法院的院长肩负着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这种“政治审查”的重任,自然能够(也应该)直接干预本院单个法官(独任审判)和合议庭法官(合议庭审判)的个案审判,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司法性质便演变为那种行政首长有权干预下属的行政性质。与之类似,作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监督”方式之一的“询问”和“质询”,面临同样的困境。如果“询问”和“质询”这类“监督”行为属于法律行为,则意味着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询问”或者“质询”不满意,人民法院院长或者相关人员(比如所谓的“人民法院……的负责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显然十分荒谬;因而,“询问”和“质询”这类“监督”行为只能属于政治行为,但是它同样面临难题:如果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人民法院的“询问”或者“质询”不满意,这种政治责任是否由人民法院院长或者相关人员(比如所谓的“人民法院……的负责人”)来承担?如果是这样,同样便意味着这些负有“政治责任”的人员可以干预到本级法院的个案审判之中,因为毕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本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实施监督”,目的就是要“促进……公正司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第5条),而这样一来,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性质同样演化为行政首长可以干预下属的行政性质。或许正因存在这样的隐患,在“询问”的设置上,现行《宪法》并没有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对最高人民法院询问的规定;在“质询”的规定上,现行《宪法》仅仅将国务院及其部委列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质询对象,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为质询对象;①现行《宪法》第73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在常务委员会开会期间,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提出对国务院或者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质询案。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然而奇怪的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却突破了现行《宪法》的规定,增补了人民法院作为质询的对象。事实上,人民法院与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的“负责”与“监督”这种“政治责任”和“政治行为”,来源于人民法院院长等相关组成人员由人大及其常委会“政治产生”这一高度政治行为之中,根源于人大及其常委会这一“由按照严格的法定程序产生出来的各行各业的社会精英组成的、集意见建议与政策表决于一身的政治咨询与法定表决机构”[6](P27)的高度的政治性之中。
另一方面,根据现行法律规定,与国务院、中央军委等宪法机关相同,最高人民法院也有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各自职权内的法律案和其他议案(《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21条第一款,《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11条第二款,《立法法》第12条第二款、第24条第二款)。这一规定与最高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的性质同样格格不入,因为尽管立法提案权与立法权(审议、通过权)并不相同,但立法权的行使(立法行为)属于高度政治行为,任何法案或多或少必定存在政治上的争议;当法案进入到立法机关立法审议阶段后,代表不同选区和阶层的国会议员(人民代表)便可能针对法案产生分歧,而作为本应远离政治纷争的司法机关却卷入到了立法这种政治纷争之中,司法机关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地位将遭到削弱。
然而,现行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是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就自己“职权有关的事项行使立法提案权”,乃是因为它“不仅了解立法需求,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制定什么法律,而且掌握起草法律案所必不可少的人力、信息等丰富资源”,规定它“可以提出法律案,有利于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7](P115)而且认为国外也存在一些“司法机关”行使立法提案权的事例,比如南美的“秘鲁最高法院对司法问题有立法提案权”“巴拿马最高法院对民法典、商法典、刑法典的修改有立法提案权”,[7](P127)“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俄罗斯最高法院和俄罗斯最高仲裁法院”等也有“立法动议权”。[8](P221)不过,这种理解可能并不全面,因为在上述国家中,表面上看最高法院这样的“司法机关”也可以提出法案,但实质上它们的最高法院并不是以“司法机关”的身份行使立法提案权(动议权),因为这些国家的最高法院(所谓的“最高司法机关”)同时也是行使着司法行政权的“司法行政机关”,比如俄罗斯最高法院内部便设有“司法行政管理局”[9](P188);换言之,这些国家的最高法院之所以可以5立法机关(国会或者其他称呼)提出法律案(立法动议),并非以“司法机关”的身份,而是以“司法行政机关”的身份提出的。这一现象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绝大多数的国家、特别是法治发达国家,并非由司法机关(哪怕是同时兼任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机关”,比如韩国大法院和日本最高裁判所[10](P356)),向最高立法机关提出议案的原因;这一现象也印证了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被赋予立法提案权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它是“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的司法性质,而是因为它事实上也充当着“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角色,这就是它“不仅了解立法需求,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制定什么法律,而且掌握起草法律案所必不可少的人力、信息等丰富资源”的原因。
三、人民法院“非司法主体”现象
不仅在宏观制度设计上,人民法院的性质与现实存在不协调现象,从微观上看,实践中也出现了人民法院“非司法主体”现象,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的人民法院成为诉讼案件中的被告。比如,2001—2003年“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支付工程款纠纷案”、①该案一审和终审判决书分别见:http://www fabang com/a/20110826/395562_2 html(访问时间:2014年3月15日);http://chi na findlaw cn/fangdichan/fcjfal/jzgckal/2740 html#p1(访问时间:2014年3月15日)。2005年“广东八建集团装饰工程公司诉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口县人民法院建筑工程款案”、②案件信息见:http://news 66wz com/system/2009/01/20/101123069 shtml(访问时间:2014年3月15日);另见尹鸿伟:《法院欠债成被告》,载《南风窗》2006年第1期(上)。2006年“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涉嫌单位犯罪案”、③案件信息见:http://bt xinhuanet com/2006-07/24/content_7591099 htm(访问时间:2014年3月15日);另见秦前红:《法院成为刑事诉讼被告引发的思考》,载《法学》2006年第9期。2008年“李然诉广东省海丰县人民法院追讨债款案”。④案件信息见:http://news dayoo com/guangdong/200810/27/53873_4312813 htm(访问时间:2014年3月15日)。在这些案件中,作为审理诉讼案件、解决法律纠纷的“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却沦落为个案中诉讼当事人一方,更是对“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性质的巨大挑战。
从理论上说,有侵权便应当有相应的救济。在上述案件中作为民事案件的当事人之一的人民法院,因拖欠建筑(装饰)公司工程款,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涉嫌单位犯罪的人民法院,触犯了刑律、符合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似乎是天经地义之事,只要将人民法院视为与一般社会关系的主体相同的主体即可。诚然,这种人民法院能够成为诉讼案件中的被告(或原告),根源于人民法院作为“机关法人”这一特征之中。从实践上看,似乎也不存在人民法院这一“机关法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制度障碍,正如上述人民法院成为被告在实践中的操作那样,一审毫无例外地采用异地管辖的司法管辖原则进行处理:海南省第二建筑工程公司与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院建筑工程施工合同支付工程款纠纷案,一审由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审理;广东八建集团装饰工程公司诉云南省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口县人民法院建筑工程款案,一审由云南省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审理;新疆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涉嫌单位犯罪案,一审由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审理;李然诉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民法院追讨债款案,一审由广东省汕尾市城区人民法院异地审理。从理论上看,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成为被告,如果抛开最高人民法院可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外,同样也可能通过级别管辖的方式,避开作为诉讼当事人的最高人民法院自己成为案件法官的尴尬。然而,人民法院沦为诉讼当事人,却与现行《宪法》和有关法律关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的定性相背离,它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尊严,也暴露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定性的危机。如果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那它就不应成为诉讼当事人——至少不应成为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这是因为:从抽象角度看,无论是民事诉讼的原被告、行政诉讼的原告、还是刑事诉讼的被告,⑤按照诉讼原理,行政诉讼中,被告只能是行政主体;刑事诉讼中,刑事自诉案件的原告仅能是自然人,而公诉案件中的原告仅能是代表国家的检察机关(检察官)。其“私”的立场均与“国家的审判机关”的公共服务机关的性质相违背;从具体层面上看,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成为诉讼当事人,谁代表人民法院参加诉讼,具有法官身份的人民法院院长、其他法官还是其他人员?他们凭什么可以作为代表“国家的审判机关”出庭应诉?如果作为诉讼当事人一方的人民法院在诉讼中败诉、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者应当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费用由谁支付?人民法院的财政经费吗?如果是人民法院的财政经费,这种为了保障“国家的审判机关”正常运转的“公共财产”能否支付作为诉讼当事人的人民法院“私”(含本单位利益)的目的?显然,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只能审案子,不能够修房子,修房子是另外的国家机关的事情;法院修房子只能用计划内税收再分配的资金,绝对不能‘自筹资金’,因为一旦‘自筹资金’,就违反了国家机构设置的非经济性原则,就使得法院自己成了债务人,埋下了沦为被告当事人的伏笔。”[11](P18)实践中人民法院成为被告,极端地反映了“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司法主体”的“非司法主体”化现象。而“人民法院作为机关法人以民事主体身份参与市场活动,作为政府行政管理的对象而成为行政相对人,为筹措经费而触及法纪红线,是法院成为‘被告’的重要原因”。[12](P50)换言之,人民法院成为诉讼当事人是因为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上行使的不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司法职能”,而是行使了《宪法》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的“司法行政职能”。
四、人民法院的性质与人民法院的“行政化”
由上述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看,《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关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的定性是不全面的,这种单一的定性与人民法院事实上行使的“司法职能”和“司法行政职能”这两种相互关联而本质不同的职能不相协调。因此,在现行《宪法》体制之下,还原人民法院同时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和“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的性质,能够有效解释一些具体制度设计,比如人民法院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询问”或者“质询”同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列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会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第17条、《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第7条)、最高人民法院有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法律案和其他议案等,均是以人民法院事实上充当着“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这一角色为基础的。与之类似,实践中之所以出现人民法院成为诉讼案件中的当事人(尤其是被告),同样是以人民法院同时是“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这一性质为前提的。换言之,人民法院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关系的上述制度设计,以及实践中出现的人民法院“非司法主体”现象,并不是因为“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性质的产物,而是“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这一角色的结果。
澄清了人民法院同时具备“国家的审判机关”和“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两种性质,才可能为进一步剖析当前倍受诟病的人民法院的“行政化”问题提供原点。显而易见,如果站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的“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显性的性质上、而忽略“人民法院也是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这一隐性的性质的话,便可能在“人民法院的‘行政化’”或者“司法的‘行政化’”的宏大叙事中迷失方向,对当前司法改革也将无所裨益。
从人民法院司法性质和司法职能出发,通过比较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司法机关的性质、特征和运作规则,进而发现人民法院体制存在着严重背离司法性质和司法职能的问题,并希望朝着符合“国际标准”的模式转变,成为一段时间以来国内理论界的主流。实际上,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性质出发,论证人民法院应当具备国际社会意义的法院之所以为司法机关的品性,对于澄清“司法机关”应有面貌当然意义重大,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横向比较的视角,以直观的形态揭示中国司法存在着的“非司法”特征。这些“非司法”被“概念化”为“人民法院的行政化”(或者“司法的行政化”),即“法院在整个体制构成和运作方面与行政管理体制和运作方面有着基本相通的属性,是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建构和运行”。[13](P4)比如有学者指出,“从背景上分析,司法权的类行政化,或者说司法行政化,一直是我国现行司法体制的重症顽疾。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的司法体制带有极强的行政管理色彩,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不仅在外部,即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上依附于行政机关,……而且在内部管理体制方面也仿效行政建立起一套上命下从的金字塔形权力架构,法院院长就是该级法院的首脑和最高长官,接下来是庭长,院长、庭长与所属法官之间是一种‘长官’和‘属吏’的上下级关系,他们对下级法官具有指挥、命令的权力。”[14](P35)诚然,从“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显性的定性审视中国当前的法院体制,的确能够得出“人民法院的行政化”或者“司法的行政化”的结论。按照这种思路,似乎只要人民法院铲除这些“行政化”要素(所谓的“去行政化”),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便能够实现;按照这种思路,只要祛除人民法院的“行政化”要素,实现了纯粹意义上的司法独立,便能够有效地实现“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的“司法职能”。然而,有三个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追问:人民法院的“去行政化”是否意味着人民法院只能行使“司法职能”,不能行使“行政职能”?人民法院的“去行政化”到底应祛除什么内容?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化”的体制根源何在?
从宏观角度上看,人民法院的“去行政化”(或者司法的“去行政化”)命题以权力分立(尤其是司法与行政分立)原则为前提。由于纯粹的“权力分立”在实践上是不可行的,正如英国宪法学家维尔(M J C Vile)所说的“纯粹权力分立学说隐含着的是,可以在政府的各部门之间对政府职能做独到的划分,做到任何部门都不再需要行使其他部门的职能。在实践上,这种职能划分从来也没有实现过,即使可能,事实上也不可遇,因为它涉及政府活动的中断,而这是无法容忍的。”[15](P303)因而,司法能否彻底地与“行政”相分离,本身便值得质疑。实际上,德、美等法治国家的实践均表明,权力分立原则并非意味着每一权力能够单独自我运行。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早在1953年12月18日的判决中,对权力分立原则进行阐释:权力分立的“意义在于政治上的权力区分、三权的相互交错与由此产生的对于国家权力的抑制。但这个原则在任何国家都没有被完完全全的实现过。毋宁,即令是承认权力分立原则的国家,在其宪法秩序里头,某程度的功能重叠与一权对另一权的影响,其实都是相当普遍的。”[16](P46)而美国的实践也表明,“政府的一个行为,最少必须获得二个政府权力部门的认同,才有可能进行。故而,一个政府部门要顺利地行使其权力,必须寻求至少另一个政府部门的合作。在这个分权制衡的权力分立原则之下,三个权力部门彼此之间既是相互独立的,也是相互依存的关系。”[17](P136~137)因此,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相同,司法机关的运作同样需要其他机关的适当配合,正如苏永钦教授所说的,“司法不可能成为一个自主运转的体系,在司法和社会其他体系互动的过程中,必须不断调整资源的配置,不断做制度更新,甚至尝试做长中期的规划。司法支撑许多部门的运作,却也需要争取其他部门的回馈。因此和任何其他部门一样,司法也需要负责而有效的行政。”[18](P207)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自然离不开“行政”的配合。所谓“人民法院的去行政化”(或者“司法的去行政化”),显然并不能消除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正常运转所必要的“行政”内容,否则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也将无法正常运转。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站在“国际标准”立场上笼统地主张中国人民法院(司法)“去行政化”的思路本身虽然值得肯定,但同样需要正视的是:人民法院的“行政”(司法行政)其实是不可避免的。众所周知,比较法意义上的制度比较借鉴,以整体性观察而非局部了解为前提。换言之,国际社会意义上的司法机关之所以称其为司法机关,除了司法机关内在的品性外,还应同时考察其相关的配套制度和法治的生态环境:前者最为重要的是支撑司法运作的司法行政制度;后者最为核心的是存在督促司法行政不得不依法积极、有效支撑司法运作的制度环境。一方面,在国际社会上(尤其是欧美法治国家),司法机关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有一套有效的司法行政制度的支撑和保障,大体上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司法行政机构隶属于一般行政部门,并对国会负责,具体又分为两种,即设立统一的司法部负责法院司法行政事务,如奥地利模式;以及不同行政部门负责不同类型的法院的模式,比如德国除联邦宪法法院自身行使部分司法行政事务外,联邦普通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由联邦法务部负责、联邦行政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由联邦内政部负责、联邦财物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由联邦财政部负责、联邦劳工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由联邦法务部和联邦劳工部共同负责、联邦社会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由联邦劳工部负责;二是采用合议制、独立于一般行政机关且不对国会负责的司法行政机构负责司法行政事务,具体又分为两种,即纯粹的法律专业自治机构的模式,如西班牙和挪威的法官任命委员会;以及混合专业与政治部门的代表的模式,如荷兰、丹麦、南非的司法委员会;三是在司法部门建立行政组织,负责司法行政事务,具体又分为两种,即整合各法院建立的行政组织的模式,如美国的联邦和各州的司法会议(Judicial
Conference of the U.S.);以及由终审法院兼理司法行政的模式,典型的有日本的最高裁判所和韩国的大法院承担司法行政职能。[10](P359~364)无论采取何种司法行政体制,司法机关(法院)的正常运转、司法职能的发挥均离不开相应司法行政机构的积极、有效的配合。按照常理,由司法部门建立行政组织——尤其是其中由终审法院兼理司法行政的模式,比起司法行政机构隶属于一般行政部门、并对国会负责的模式和独立于一般行政机关且不对国会负责的司法行政机构负责的模式,在司法外部独立(External Independence)上似乎更加具有保障,因为这种制度上的司法独立,“就是要保障法院、司法部门及所有法官,于司法事务之实践上,如法官选任与评鉴、法官之风纪、相关司法经费之补助与司法预算等,不会受到不当控制上的独立,包括法院及司法部门就其人员、设施及内部管理方面,拥有相当之自主性及独立性,不能受行政与立法不当的干预,以求自内部管理之有效运作来实现制度上的独立。”①美国全国州法院国家中心主席Roger K.Warren法官(于2003年1月17日在台湾“司法院”专题演讲).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J].司法周刊,1119(2003年1月29日),第2-3版;转引自陈靖华.我国法院组织与诉讼制度变革之研究(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硕士在职专班2004年硕士论文;指导教授:徐正戎博士)P55.最高司法部门本身就是司法行政机关,恰恰有助于排除政府其他部门——尤其是行政部门的干预。中国人民法院的司法体制,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的改革目标之一,如果真的实现了“去地方化”,那么人民法院兼任“国家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角色,比起这种由终审法院兼理司法行政的模式在部门独立(branch inde pendence)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这种司法行政不仅存在于最高人民法院的层面,而且充斥于各个层级的人民法院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法院自己行使司法行政职能,并不一定需要改变为由政府的行政部门来行使司法行政职能,毕竟“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外部而非内部。……其不当影响或控制可以包括恫吓、贿赂、单方接触、非法免职、拒绝执行法院判决以及其他一些可能。它可以像暴力一样残酷无情,也可以像请客吃饭一样温良恭俭让。它可以损害单一法官或整个司法体系的独立或二者一并毁之。”[19](P125)实际上,上文提及人民法院因拖欠建筑工程款而成为民事诉讼被告的极端例子,原因之一正是人民法院财政严重依赖外部行政部门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政府(Government)职能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司法(审判)本身并非自足的独立体系;即使是法治国家的“司法独立”也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能够从法官人员选拔、审判法庭设置、办公场所和设施配备、经费保障、裁判执行等各个环节完全不依赖于立法和行政部门;而法治欠发达的国家,作为政府(Government)三大部门中“既无强制、又无意志,而只有判断”[20](P391)的“最小危险部门”[21]的司法机关,自然更是最为孱弱的政府部门,更有赖于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而其他政府部门(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能否合作,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政治的民主机制能否得以发挥作用,并最终取决于民众普遍的觉醒,否则,“即使有司法独立,也不可能实现该独立应有的社会职能。”[19](P131)因此,当前人民法院“去行政化”改革乃至整个司法改革,并非司法部门自身所能实现的,它实质上是整个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仅仅是一个附带的组成部分,因为“包括纳粹德国和‘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在内,许多的外国经验告诉我们,司法不够独立是政治不够民主的必然结果。期待司法变成政府中的灰姑娘,不仅不受制于政府,反倒去促成政府的民主,是多么的不切实际。独立的司法充其量只能在民主化得到初步成果之后,发挥一点巩固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就司法体制而言,独立的保障有其合理性的局限,独立不是司法唯一需要维护的原则,过度保障独立很可能降低司法的效率——包括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因此非常吊诡的地方是,当政治不够民主而改革者期待以提升独立保障的手段来加速民主化时,成果通常十分有限,拉美国家司法改革乏善可陈就是最好的例子。”[22](P423)
显然,既然司法部门离不开包括行政部门在内的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司法的正常运作离不开司法行政的配合,而司法行政职能又可以由司法机关本身予以行使;那么,所谓“人民法院的去行政化”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就一定需要剔除实践中事实上的“国家司法(法院)行政机关”的角色、以维持现行《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所确定的“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单一的“司法机关”性质。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应当在理解司法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一般原理基础上,厘清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司法性质对应的“司法职能”,与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这一司法行政性质对应的“司法行政职能”的关系。①可喜的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已经明确提出“改革司法机关人财物管理体制,探索实行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管理权和审判权……相分离”的目标。
就司法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关系而言,司法行政是服务于司法目标的一种派生性的行政职能。由于司法机关(法院)和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之下进行,司法活动以及司法的每一个环节需要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支持和配合,这种支持和配合司法活动的公共行政便是司法行政。其事项十分广泛,“举凡审判以外有关司法之行政事务均属之。是以,凡关于各级法院……之设置配备、司法管辖区域之划分调整、司法经费之筹拨分配、司法人员之任免考核、司法裁判之执行、司法风纪之整饬、司法效能之促进、监所之设施、律师之登录等事务,其性质均属司法行政事项。”[23](P322)这些司法行政事项,按照与司法核心职能(裁判)关系的“亲疏”,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司法案件审判所不可分离的司法行政事项,比如司法规则的发布、案件流程安排、案件审判的组织、法庭的指挥调度等,这是保障司法权作用得以完整发挥而应由司法机关(法院)本身拥有的司法行政事项,即司法机关(法院)的“核心司法行政事务”,这就是“在各国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或必须由法院自己承担,尽管由于各国的制度不同,各国法院所承担的这类工作的总量会有所不同”的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事务;[24](P36)二是司法机构正常运转所不可或缺的司法行政事项,即司法机关(法院)的“非核心司法行政事务”,比如人事行政方面涉及的相关人员的选拔和配备、绩效考核、监督奖惩、在职培训等,财物行政方面涉及的司法经费的预算决算、办公场所和设施的建造维修等,公务行政方面涉及的案件统计、卷宗管理等等。这类司法行政事项未必全部由司法机关(法院)自己来行使。
当然,无论是什么样的司法行政事务,都是以服务于司法职能为目的的,因而以不损害“司法独立”(审判独立)为前提。因而,从司法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法院)关系的角度,“司法行政机关主要目的在于有效支援协助审判……须受……法官独立审判之限制”;[25](P36)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台湾“司法院大法官”解释的支持和印证。“释字第530号”“解释文”指出:“审判独立乃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权力分立与制衡之重要原则,为实现审判独立,司法机关应有其自主性;本于司法自主性,最高司法机关就审理事项并有发布规则之权;又基于保障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诉讼,受充分而有效公平审判之权利,以维护人民之司法受益权,最高司法机关自有司法行政监督之权限。司法自主性与司法行政监督权之行使,均应以维护审判独立为目标,因是最高司法机关于达成上述司法行政监督之目的范围内,虽得发布命令,但不得违反首揭审判独立之原则。最高司法机关依司法自主性发布之上开规则,得就审理程序有关之细节性、技术性事项为规定;本于司法行政监督权而发布之命令,除司法行政事务外,提供相关法令、有权解释之资料或司法实务上之见解,作为所属司法机关人员执行职务之依据,亦属法之所许。惟各该命令之内容不得抵触法律,非有法律具体明确之授权亦不得对人民自由权利增加法律所无之限制;若有涉及审判上之法律见解者,法官于审判案件时,并不受其拘束”;该号“解释理由书”进一步指出:“司法行政机关为使人民之司法受益权获得充分而有效之保障,对法官之职务于不违反审判独立原则之范围内,自得为必要之监督。法官于受理之案件,负有合法、公正、妥速及时处理之义务,其执行职务如有违反,或就职务之执行有所懈怠,应依法促其注意、警告或予以惩处。诸如:裁判适用已废止之法令、于合议庭行言词辩论时无正当理由径行退庭致审理程序不能进行、拖延诉讼积案不结及裁判原本之制作有显著之迟延等等。至承审法官就办理案件迟未进行提出说明,亦属必要之监督方式,与审判独立原则无违。对法官之办案绩效、工作勤惰等,以一定之客观标准予以考查,或就法官审判职务以外之司法行政事务,例如参加法院工作会报或其他事务性会议等行使监督权,均未涉审判核心之范围,亦无妨害审判独立问题。”[26]“释字第539号”“解释文”指出:“凡足以影响因法官身份及其所应享有权利或法律上利益之人事行政行为,固须依据法律始得为之,惟不以宪法明定者为限。若未涉及法官身份及其应有权益之人事行政行为,于不违反审判独立原则范围内,尚非不得以司法行政监督权而为合理之措置。”[27]
上述台湾“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表明:在司法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的关系上,司法行政职能存在的依据和目标便是协助、支撑司法职能;因而司法行政——无论是台湾“最高司法机关”就审理事项发布规则这种“核心司法行政”,还是包括人事行政监督在内的司法行政监督这种“非核心司法行政”,均以不侵害审判独立这一核心司法要求为前提。反观中国大陆,人民法院同样存在着司法(审判)职能与司法行政职能这两种在《宪法》和法律上一明一暗的不同职能。然而由于人民法院“国家司法(法院)行政机关”的性质没有明确定位,法院司法行政职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12](P52)二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并没有制定法上直接的依据。因此,在应然的层面上,只能从人民法院“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司法性质和司法职能出发,按照司法与司法行政两种职能的“主从关系”原理,来推导它们与之对应的司法行政机关的性质和司法行政职能的关系。而在实然的层面上,一方面,在对外交往上,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由各级法院的名义自行管理;另一方面,在内部,人民法院没有合理区分内部具体承担司法职能和司法行政职能的具体机构或者组织,将审判机构与司法行政机构混为一体——比如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既是司法审判人员、又是司法(法院)行政人员,而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又大致等同于国家行政管理的组成部分,采用的是命令与服从的官僚体制管理模式;如此一来,“司法行政权由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庭长以及有关行政部门的领导行使,而司法审判权则由每一个法官具体行使……司法行政权在行使过程中,要实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因此,普通法官要服从享有司法行政权的有关领导的安排”,[28](P181~182)导致的结果是将司法行政中的行政模式直接渗透到司法模式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侵入了司法的“核心功能”,①美国宪法学界关于权力分立原则的功能论(functionalism)认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权力部门均有宪法所赋予的“核心功能”,这些“核心功能”或“核心权力”是不能被其他权力所侵夺的。参见林子仪、叶俊荣、黄昭元、张文贞著:《宪法——权力分立》,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38-139页。危及了审判独立。正如有的学者所揭示的:“中国法院行政化的问题出在法院系统内部的这两套分别用来处理两类不同问题的制度,即为履行国家赋予的审判职能的审判制度和从规范上看应是为保证和支持法院审判职能之实现所不可缺少的法院内部行政管理制度,在实践中发生了职能的交错和混合”。[24](P40)因此,人民法院的“去行政化”所应祛除的并不是人民法院内部的司法行政职能本身,而是以司法行政名义,不当地附着于人民法院司法职能之上、渗透到司法职能之中、干预司法职能正常发挥的行政思维和行政手段。
五、结语:人民法院“去行政化”的思路
当前人民法院“行政化”,在体制上根源于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和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的两种相互关联而本质不同的性质,被笼统而含混地附着于名字叫作“人民法院”这一单一的机关实体之中。在这一体制之下,人民法院改革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一单一性质与人民法院的两种职能(司法职能和司法行政职能)不协调之间的矛盾:以人民法院的单一性质为基础来理解人民法院改革问题,而不是以人民法院的两种职能为前提来理解人民法院改革,实际上是颠倒了问题的关键;只有厘清人民法院的两种职能,研究两种职能的差异(各自的特点)及其关系,揭示人民法院的两种性质——国家的审判机关和国家的司法(法院)行政机关,进而明了因两种性质集于一身的角色混同导致的弊端,才可能为人民法院的改革提供正确方向。
在此前提下,作为司法改革目标之一的人民法院“去行政化”需要重新予以考虑: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同时兼有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双重性质,必然带来行政职能干预司法职能的“司法行政化”,这是因为,它意味着不仅最高人民法院履行着与采用最高司法机关兼司法行政机关的国家那样的司法行政职能,而且也意味着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不仅履行着与国际社会法院类似的必不可少的“核心司法行政职能”,同时还履行着国际社会法院所鲜有的管理本级法院人、财、物的“非核心司法行政职能”;它意味着管理人员与审判人员紧密地交叉重叠(至少对于人民法院的“院长”和作为“长官”的其他法官们而言是如此),而具备管理人员(“长官”)身份的法官承担着大量的司法行政事务,必然在精力上无法与其他普通法官(司法人员)那样全身心履行司法职责;而且更值得忧虑的是,由司法行政管理职能带来的行政隶属关系难以避免地渗透到由平等人(法官独立且平等)组成的司法组织(合议庭)中,扭曲了司法审判的职能。因此,司法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将地方各级人民法履行的“非核心司法行政职能”剔除掉,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置一个有地方各级法院法官、律师、法学家和相关行政官员组成的相对独立的复合的司法委员会来负责各级人民法院人、财、物等“非核心司法行政”事务。如此,才可能真正实现人民法院的“去行政化”(既去除地方党政干预的“地方化”,同时也去除法院行政事务垂直管理后出现新的“行政化”)。
[1]刘安荣 我国法院体制的行政化及改革对策[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6)
[2]沈寿文 政府权力横向配置新论——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的分析[J] 政法论丛,2011,(1)
[3]See Louis Michael Seidman AMBIVANENCE AND ACCOUNT ABILITY[J].61 S Cal L.Rev.(1988).
[4]沈寿文.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功能及制度困境[A].周永坤.东吴法学[C](2011年秋季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5]张文显.法理学[M].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沈寿文.中国国家权力机关性质新论[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3,(4).
[7]乔晓阳.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讲话(修订版)[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
[8]曹海晶.中外立法制度比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9]肖扬.当代司法体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10]苏永钦.寻找共和国[M].台北: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11]秦少华.当法院成为被告[J].民主与科学,2006,(6).
[12]苏泽林.人民法院司法行政管理体制的困境和改革设想[A].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编.大法官论审判管理[C].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13]张卫平.体制、观念与司法改革[J].中国法学,2003,(1).
[14]蒋剑鸣,等.转型社会的司法:方法、制度与技术[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8.
[15]M.J.C.维尔.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16]林宇光.论我国法官考绩制度——现行法制及其兴革[D].私立东海大学,2004.
[17]林子仪,叶俊荣,黄昭元,张文贞.宪法——权力分立[M].台北: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18]苏永钦.司法改革的再改革[M].台北:月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
[19]葛维宝(Paul Gewirtz).法院的独立与责任[A].葛明珍,译.张明杰.改革司法——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0]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1]亚历山大·M.比克尔.最小危险部门——政治法庭上的最高法院[M].姚中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2]苏永钦.飘移在两种司法理念间的司法改革[A].张明杰.改革司法——中国司法改革的回顾与前瞻[C].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3]史庆璞.法院组织法[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24]苏力.论法院的审判职能和行政管理[J].中外法学,1999,(5).
[25]吕丁旺.法院组织法论(修订四版)[M].台北:一品文化出版社,2005.
[26]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530号”[M/OL][2014-03-15]http://lawyer.get.com.tw/Justices/detail.aspx?no=25615.
[27]台湾“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539号”[M/OL][2014-03-15]http://lawyer.get.com.tw/Justices/detail.aspx?no=25624.
[28]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New Understanding on the Nature of the People′s Court——And Some Comment on Its De-adm inistration Reform
SHEN Shou-wen
(Law School,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The People′s court is characterized as“the judiciary organ of the State”by China′s current“Constitution”and“the People′s Court Organization Law”.However,it can neither explain some non-judicial functions ithas performed in reality,nor respond to the objectives of the people′s court reform by the Third and Fourth Plenary Sessions of the CPC′s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Actually,it is now both the judicial organ and adm inistrative authority(trial management).The understanding on such a dual nature of the people′s court can provide a starting pointand help learn what to be changed in its de-administration reform.
the People′s curt;nature;judicial administration
D926 2
:A
:1006-723X(2015)02-0006-10
〔责任编辑:左安嵩〕
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重大项目(276405)
沈寿文,男,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宪法学(含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