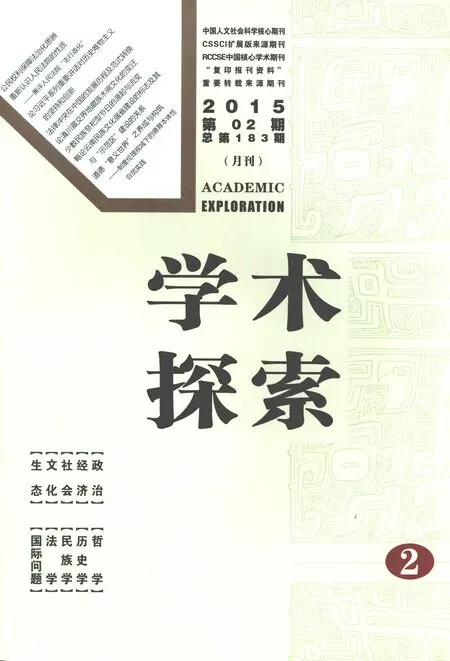昆明形象的文学书写
2015-02-26芦坚强
芦坚强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昆明形象的文学书写
芦坚强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昆明在文学书写中主要呈现为三种形象:抗战时期的故乡、新时期的栖息地和新世纪的传奇之城。它们的逻辑结构呈现为“昆明是什么”“昆明在怎样”和“昆明将要成为什么”。抗战时期的故乡指向抗战时期的昆明,是对昆明历史的思考与怀旧;新时期的栖息地指向现在的昆明,是对昆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之反映,新世纪的传奇之城是由昆明历史出发的对未来的一种期待。与这三种形象相关的是怀旧、日常生活和传记式三种书写方式,它们都是对昆明认同的一种话语塑造或表意实践。
昆明形象;文学书写;认同
20世纪80年代,①之所以将文本考察时间界限放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这是我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几位作家将他们的书写对象同时锚定在昆明这座城市:汪曾祺和宗璞抗战时期曾学习、生活于昆明,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写了一些回忆昆明的散文;宗璞开始写作野葫芦引系列(获茅盾文学奖);昆明本土诗人于坚以书写昆明的日常生活开始在诗坛崭露头角;到新世纪,海男、杨杨等作家加入书写昆明的队伍。这些作家书写的昆明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昆明在文学书写中呈现为三种形象:抗战时期的故乡、新时期的栖息地和新世纪的传奇之城。这三种形象各自具有不同内涵,但却存在一定的逻辑结构,若从西方哲学中人对自我反思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和“我要到哪里去”来看昆明形象,它就呈现为“昆明是什么”“昆明在怎样”和“昆明将要成为什么”。“昆明是什么”指向抗战时期的昆明,是对昆明历史的思考与怀旧;“昆明在怎样”指向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昆明,是对昆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之反映;“昆明将要成为什么”是由昆明历史出发对未来的一种期待。这三种形象分别对应了怀旧、日常生活和传记三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因此本文以昆明形象的文学书写为对象,分析文学中昆明形象是如何形成和书写的?这样的书写有何特点?这些形象书写蕴含怎样的文化与美学意义?
一、抗战时期的故乡
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和宗璞将书写的对象同时锚定于昆明。在昆明的生活使他(她)们将昆明当作第二故乡,这样书写也使其作品充满怀旧气息。
汪曾祺1939年只身一人来到昆明最终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七年的生活使他将昆明当作故乡,在这里他虽遇上了生活最艰苦的状况但却接受了堪称教育奇迹的西南联大的教育。他曾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1](P109)由此可见西南联大的自由氛围和严谨治学传统给他以及其他西南联大学子的重要影响,这令他们终生无法忘怀。杜运燮曾说:“如果有人问我,像一些记者最爱提的那个问题:‘你一生中印象最深、最有意义的经历是什么?’我会随口用四字回答:西南联大。我想,其他许多‘联大人’也会这样。”[2](P1)鹿桥为了挽住行将退尽的梦潮,将逐渐黯淡下来的“那种又像诗篇又像论文似的日子”[3](P1)记录下来,在毕业后不久奋笔书写了描绘西南联大生活的洋洋洒洒之作《未央歌》。因此,西南联大的学习、生活情景就是汪曾祺回忆书写的重点,西南联大校舍的简陋、杂乱,先生们讲课的认真、风趣,学子们的独特个性、校风的自由等都呈现于其笔下:如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们迥异的教学风格:“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罗庸先生讲杜诗,不带片纸,将诗背写于黑板……唐兰先生讲词,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一遍……朱自清先生上课则很严格。”[1](P10~13)教授们的魅力形象在其叙述中跃然纸上;另外其笔下风度翩翩的陶光、清秀聪明的朱南铣、平静自然的蔡德惠等学子形象亦让读者感觉栩栩如生。
基于爱屋及乌的缘由,与西南联大相伴的城市空间——昆明成为汪曾祺喜爱的对象。离开昆明30多年以后,昆明成为汪曾祺越来越无法忘怀的地方,怀旧的情感使他将笔触反复集中于对昆明的书写。从昆明的雨、翠湖的绿到西南联大校园的生活、教室、学子再到昆明的草木、吃食、蔬菜,都是汪曾祺怀旧的对象:“我想念昆明的雨。……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1](P109)正如普鲁斯特由小玛德莱娜甜饼引发的回忆一样,汪曾祺以昆明的雨为引子,回忆的是在昆明生活、学习的种种场景、人物和事件。他的作品也成了记录抗战时期昆明民风世俗和自然风光的“浮世绘”,逛翠湖时的茫无目的、跑警报时的从容不迫、泡茶馆时的悠闲自在、听曲会时的恬淡冲和等构成一幅诗意自然的昆明生活场景。昆明在汪曾祺的回忆中已然具有了家的温暖和平静,他的书写也成为对故乡美好怀旧的书写。
汪曾祺的回忆在建构昆明的同时完成了对昆明的一种审美追求。首先,回忆是他作品的特征之一。他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都是对故乡高邮的回忆之作,他认为小说是一种回忆,只有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才能形成小说。”[4](P461)回忆就是写作的过程,这样的写作也是一种怀旧式的书写。其次,怀旧指向时间上过去的美好时光和空间上远离的故土家园,汪曾祺离开昆明时隔四十年后的回忆文章指向的是抗战时期的昆明。时空的阻隔加深了对昆明的情感,故乡是他的精神寄寓所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异乡者在他乡寻找能够安于其中的位置时,其心灵“已经在通向其本己家园的道路上追随着那种召唤着它的呼声了。”[5](P28)虽然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内涵不同于海德格尔的“家园”,但是二者的意义是等值的,它们能够让诗人感受到生命的本真存在,并保持生命的一致性不被割裂。正因如此,汪曾祺在书写中对昆明的回忆也就转化为对故乡的怀旧,①赵静蓉认为回忆与怀旧有联系,但也有着根本的不同:回忆属于心理学范畴,回忆的往往是形而下的、经验事实,而怀旧式美学范畴,有较强的价值取向,怀旧是指向过去的一种现实诉求,是形而上的、想象的重构。见赵静蓉:《想象的文化记忆——论怀旧的审美心理》,《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2卷第2期。第54-57页。并在怀旧书写的“诗意美学创造中达到了一种生命的回归与超越。”[6]
昆明也是宗璞的故乡。她在昆明生活了八年,半个世纪后她依然想找出半个多世纪以前昆明的图像:昆明蓝的无底的天,乡下路旁没有尽头的木香花篱,几百朵红花聚于一树的山茶,搅动着幽香的海的腊梅林,抑扬顿挫的昆明语调等都是她寻找的对象,[7](P112)她不仅在记忆里寻找昆明,也曾几次返回昆明寻找在时光中落下的印迹。
宗璞的小说《野葫芦引》系列是对抗战时期生活的怀旧。小说以“葫芦”为引子和主题类似于《红楼梦》以石头为引子进行的梦幻回忆,“且不说葫芦里迷踪,原都是梦里阴晴。”(序曲·[望太平]),以怀旧的方式进行书写。稍有不同的是《红楼梦》以家族荣衰为主线,《野葫芦引》是以家、校、国为结构的怀旧故事。
家在宗璞的小说中有双重含义,一是物质的、空间的家,一是象征意义的家。物质的、空间的家主要是孟嵋(嵋即是现实中的宗璞)的家,由于战乱她多次搬家,家的意象在小说中有多处表现:北平校园中的方壶、北平城姨妈绛初的宅院、小城龟回芸豆街小院、昆明小东门腊梅林祠堂、家祠旁的戏台、城外龙尾村干栏式房屋、宝台山文科研究所侧院、城东腊梅林(已重建)。家给幼小的宗璞带来的安全感和稳定感不言而喻,但她总是不断地搬家,搬家意味着安全感的消逝与重新获得,对家的表现反映了人们对安全感和稳定感的追求。因此家所象征的安全感和稳定感就是另一重含义。战乱时期人人都渴望拥有一个充满安全感与稳定感的家,当外省人们来到昆明之后其祥和、安定给了很多人稳定感:冯至到昆明之后看到美丽的山水和古朴的民风,将漂泊、凌乱的思绪安顿下来写了《山水》系列文章和隽永优美的《十四行诗》,他说:“我不能不感谢昆明七年的寄居。昆明附近的山水是那样朴素,坦白……任何一棵田埂上的小草,任何一棵山坡上的树木,都曾给予我许多启示,在寂寞中,在无人可告语的境况里,它们始终维系住了我向上的心情,它们在我的生命里发生了比任何人类的名言懿行都重大的作用。”[8](P80)老舍感觉昆明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昆明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9](P18)昆明的静与战区的乱形成鲜明对比,反映战时人们对静所带来的稳定的追求。这些都说明昆明在战时给外省作家带来的安全与稳定感,因此有不少作家都将昆明当作北平。①许多人来到昆明后,如闻一多、冰心、老舍、陈纳德、屠诗聘等都有“昆明像北平”的感觉,详细论述见:《“昆明像北平”考》,余斌:《西南联大·昆明记忆》(第二卷《学人与学府》),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38-147页;杨杨:《昆明往事》,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15页;明飞龙:《作为“北平”的昆明——抗战时期作家笔下的昆明形象考察》,《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第173-177页。关于“昆明像北平”的原因,除几位研究者认为的昆明的建筑、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昆明像北平一样具有田园都市的氛围情调之外,还与本文所分析的昆明生活的平和、舒缓使诸多外省人有了家的安全与稳定之感有关。因此,“昆明像北平”之说,确切而言是昆明像抗战前的北平,像抗战前北平的平和与稳定。
学校也是宗璞的书写重点。她是随父亲及西南联大来到云南的,没有西南联大就没有她的昆明之行与成长历程。她的父亲冯友兰先生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是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大的筹建者之一。她的小说就是围绕父亲、家庭、学校、国家而讲述的故事。因为战事学校搬迁,众多教授及家眷也都搬迁昆明,《南渡记》描写北平战时爆发学校搬迁至昆明,《东藏记》描写西南联大的发展,《西征记》围绕学校讲述学子们披上戎装慷慨赶赴前线的故事。学校在这里是小说书写的重点所在,教授和学子们在国难之时仍然坚持写作、学习,保持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与各种不利于战争的思想做斗争,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等在作品中都有表现。
国家同样是小说的叙述中心。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国家为战事所做的妥协、反复与努力,可以看到军人们在战争面前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可以看到战争的残酷、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与执着,可以看到前方战事僵持之时后方的混乱、争斗和坚持……当然,国家和战争总是与个人联系在一起,在国难当头、战争残酷的环境之下书写普通人的真实感受,并将普通人的命运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样的书写手法使得小说本身具备了史诗的特性,也使其具有了一种与《战争与和平》同样宏大而悲怆的基调。
宗璞以家、校、国为结构的怀旧和汪曾祺对故乡象的怀旧同时完成了抗战时期昆明的怀旧书写。这样的怀旧书写是一种集体记忆,虽然写作是一种个人行为,但写作对象与抗战时期众多书写昆明的作品具有同一指向——抗战时期的昆明:昆明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结合展现的是民族国家的一种地方性,展现了民族国家的状况,也完成了自身“是什么”问题的回答。这里对昆明的怀旧式书写体现的是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也是对昆明的认同,因为“怀旧是我们用来不断地建构、维系和重建我们认同的手段之一。”[10](P105)对同一性、连续性的内在需求,使人们不断将目光转向过去,怀旧也始终保持着对过去的基本诉求,在想象中完成对同一性的重建和自我的认同。汪曾祺和宗璞对昆明的怀旧书写,既是追求个人自我的认同,又是追求民族国家的认同,同时完成了昆明的认同建构。
二、新时期的栖息地
新时期对昆明的书写中诗人于坚是非常独特的,他对昆明的书写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书写。于坚作为出生于昆明的诗人,他的写作和思考从未离开过昆明,昆明既是他的故乡也是感知世界的窗口,诗歌则是他表达情感的手段。他认为诗歌“像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精灵一样,忽然醒过来,然后又睡过去。”[11](P185)他希望通过诗歌寻回日常生活的神性并“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11](P218)那么于坚诗歌的日常生活究竟是怎样的日常?这样的日常生活与昆明形象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的诗歌是如何书写昆明的?这将是下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于坚认为诗歌与日常生活的关系并非割裂而是融为一体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一首诗,诗歌也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不会死去。诗歌描述的是人对生活的体验,反映的不是事物的表象(这并非否认事物表象的重要性)而是一种永恒的、基本的东西,诗人“要把握的就是在每一个时代的喧嚣里面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诗人……只是在告诉你最基本的东西。”[12](P16~17)这些永恒的、基本的东西就是日常生活,诗歌就是要将日常生活“敞开”,让事物走向读者,这是诗歌存在的方式,若是离开了日常生活走向诗坛、选本或文学史诗歌只能走向死亡,因此,诗歌应该回到日常生活中去。
于坚书写的重点是昆明的日常生活。对日常生活的选择首先是他反抗或纠正“朦胧诗”的一种策略,但随着写作的进行,日常生活成为他写作的信心和动力,他既希望破除“朦胧诗”的宏大叙事,又希望将一种神圣性赋予日常生活。因为日常生活是人感知世界的对象和方式,同样也构建了人与世界的关系,对日常生活的认知和表现就是对人自身和自然(道)的认知。恰如波德莱尔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中提出美具有双重结构①波德莱尔认为美具有双重性:“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把永远存在的那部分看作是艺术的灵魂吧,把可变的部分看作是它的躯体吧。”见[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6页。一样,于坚也认识到了“寻常事物背后,皆有目不可见的神秘秩序”,[13](P304)诗歌的目的既要表现事物表象的、物质的面目,又要深入其基本的、永恒的精神:在他《尚义街六号》那法国式的黄房子中,一群年轻人琐碎又充满理想的日常生活,也是昆明富有生机和理想的形象;《罗家生》简单、平凡的一生,也是芸芸众生的命运;《0档案》枯燥理性的档案记录,希望还原的是“他”以及每一个人的鲜活的生命;“事件××”系列是企图表现事件发生时的生命体验。于坚的日常生活书写方式与哲学家西美尔的方式相同——“孜孜不倦地关注的是关于残缺不全的日常世界的经验以及这样一个世界中包含的微不足道的对象。”[14](P59)诗歌在对普通的、日常的场景和事物进行审美观照过程中,揭示了其后的本质性力量和永恒的东西。
因为书写策略的选择,昆明在于坚诗歌中呈现出的是充满诗意的形象——故乡。故乡意象在其诗中的含义与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的栖息地”是一致的,是人类心灵的故乡和精神的栖息地。正如费里尼在电影中重建了一个“人类基本的故乡,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个故乡”[15](P386)一样,于坚也重建了一个人类的故乡。在这里,人们过着诗意的生活“在我故乡/人们把滇池叫作海/年轻人常常成群结伙坐在海岸/弹着吉他/唱‘深深的海洋’/那些不唱的人/呆呆地望着滇池/想着大海的样子/恋爱的男女/望见阳光下闪过的水鸟/就说那是海鸥”(《滇池》);哼着春天的咏叹调“春天你踢开我的窗子一个跟头翻进我的房间/你满身的阳光鸟的羽毛和水还有叶子/你撞翻了我那只穿着黑旗袍的花瓶”(《春天咏叹调》)。昆明被诗人书写成为诗意的地方,在其“少年时代,故乡那永不结束的金色黄昏,使我对世界产生了一种天堂般的感受”,[16](P245)这天堂般的故乡使昆明对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最能心领神会。[17](P85)因为这里缓慢的生活使人们能够关注更多的细节,能够有时间把生活精雕细刻,置时代那气喘吁吁的列车于不顾,昆明也如普鲁斯特和费里尼作品中的故乡一样充满了平凡的诗意。
然而,这样诗意的栖息地、人类的故乡也因时代而改变。外婆因新家的搬迁而去世“那一年春天高楼盖起来了/老四合院大树上最后一个鸟窝/鸟儿已经飞走拆房子的人在树下闲聊/那是外婆浇水的地方……我们搬家/外婆坐在驾驶室抱着水壶……完美而自在安静而慈祥/当家人把她抬到床上她已逝去多时/她睡在新房子里四壁洁白/显得非常陌生”(《外婆》);诗人诗歌的信心、无意识依赖的故乡明珠——滇池才20多年的时间就死去,如屈原写下《哀郢》的心情一样,[18](P77)他为滇池而写的第三首诗是《哀滇池》:“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为什么天空如此宁静?太阳如此温柔?/人们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般继续着那肥沃的晚餐?/出了什么可怕的事?/为什么我所赞美的一切忽然间无影无踪?/为什么忽然间我诗歌的基地/我的美学的大本营我信仰的大教堂/已成为一间阴暗的停尸房?/我一向以你的忠实的歌者自封/我厌恶虚构拒绝幻想/哦出了什么事我竟成为一个伪善的说谎者/我从前写下的关于你的所有诗章/都成了没有根据的谣言!”外婆因为搬新家离开生活的故居而死去,滇池因为时代的变化而死去,诗人曾经诗意的栖息地变成埋葬死者的墓地,初恋般的河流“口痰和粪便糊在上面/是他自己的口痰/是他的城市的口痰/泡沫抱着鼠尸旋转”(《那人站在河岸》)。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流行无神论的时代/对于永恒者我没有敬畏之心”,在这一刻神已离我们远去,故人也离故乡而去“列车载着你跑向天边外/我们这群有家的人/在人海中悄悄走散”(《送朱小羊赴新疆》),“一些人结婚了/一些人成名了/一些人要到西部/老吴也要去西部”(《尚义街六号》),因此“在落日中我的心充满怀念/这空掉的城/怀念着谁”(《作品55号》),可以认为,诗人在这里怀念的是远去的人、远逝的神、古老的时代、人类的栖息地和美好的家园。
昆明的诗意栖息地和美好家园形象消逝的罪魁祸首是现代化。尽管现代化给人们带来了文明与物质,却摧毁了传统与日常生活,“现代化……只建立观念性的现代蓝图,它不关心日常生活。每个现代化的城市最后摧毁的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凡俗世界。”[11](P217~218)于坚最感同身受的是由于城市发展自己连曾经的居住地都已无法找到,“我的一生是从武成路上的某个房间中开始的。但我无法向人们证明我是在这个城市出世的,因为这个城市没有武成路,我陷入一种口说无凭的尴尬境地,我怀疑我是一个我自己尚未意识到的谎者。”[16](P306)现代化蓝图的理性机制发展摧毁了普通人的生活,于坚无法证明他曾经出生、成长的地方存在过,老昆明已被现代化进程摧毁了,城市现代化割断的是人们与城市空间的连接纽带,摧毁的是人们的身份认同感,人们无法再找到自己曾经居住的街道、门牌和房间,自己与过去的联系被割断,身份认同无从找寻。现代主义的理念蓝图仍然继续向前:街道上,冒烟的推土机一天到晚不停地拆,在《?戈布丁》中于坚以“拆个不停”和“?戈布丁”两个声音非常相近的词语引导了一句句、一组组不同的意象,从青铜鼎到秋菊之落英,从祖母的老棺材到爱情、牙刷、童年等统统被拆掉;工程师们依然在规划着昆明的未来,“未来的工程师长着玻璃眼球胸怀一家伟大的拆迁公司/在虚空中比划着圆规铅笔盒橡皮擦头/精确计算着数据梯级效益考虑着如何安排1+1”(《马雄山》)。
现代化问题不仅是昆明所面对的,这是一种普遍状况,所有城市人都面临身份认同的焦虑。在现代化进程中,于坚仍然以日常生活的书写来表现最基本的、永恒的东西,他所做的与列斐伏尔希望“进行一场对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彰显出日常生活的本真性和原始性……让日常生活变成一件艺术作品”[19](P162)是一致的,他要通过昆明的日常生活书写,记录并表现昆明的点滴变化,反映出“昆明在怎样”,同时构建昆明作为人类精神的家园与栖息地的形象并重建“日常生活的尊严”。
三、新世纪的传奇之城
新世纪昆明的书写出现了一种新方式——传记式书写,主要是为昆明书写传记。一般而言,传记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主要是为人而作,记述人物生平事迹,传记须以史实为基础、不虚构,但可以运用文学的手法对所写材料进行组织,亦可对所记对象进行评论;方志才是记录地方之事,“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周礼·地官·诵训》),它所记述对象是地方而非人物,同样须照史而录、不虚构。书写城市的传记性文学是传记与方志的写法结合起来,以传记方式书写方志对象由此为城市记史写传,这样的书写是对城市进行的一种文学性、记传性写作。传记式书写的昆明的代表作是海男的《新昆明传》《滇池传》和杨杨的《昆明往事》。
海男作为著名作家、诗人,近年将写作对象转移至昆明,她先后出版了《新昆明传》和《滇池传》,并为《名城往事记忆之旅》(杨杨的《昆明往事》是其中一员)系列丛书写了总序。海男的目的是为昆明书写传奇,《新昆明传》就是献给昆明的人文造城传奇,《滇池传》则是书写滇文化传奇,希望通过书写让城市的凡俗面貌在作家的叙述中重生,同时“在这些灿烂而沉郁的诗学符号中,我们寻找到了我们的生命在前世的城池中穿越的时间暗道——因寻找而滋生的忧伤,将带我们回到从前;回到被时间之魔咒所笼罩和演绎的那些生与死的秘诀中去的灵魂,则是永生不灭的。”[20](P1)
在《新昆明传》和《滇池传》中,海男用散文片段的形式追溯了昆明的历史,以素描和连线的形式勾勒了昆明城市发展简史。在这两本书中,书写了庄?入滇的神秘、昆州图像的呈现、拓东城和鄯善城的流变、赛典赤对滇池的治理。这些画面构成了古代昆明的简约图像,盘龙江、滇池、翠湖、南屏街、正义路等空间是昆明的核心所在,阁逻凤、郑和、聂耳等人与昆明的历史紧密相连,大观楼、讲武堂、滇越铁路、重九起义、护国运动、西南联大等则是昆明的文化底蕴所在,鸡枞、饵块、汽锅鸡、大头菜等作为特色美食经历了昆明的千年春秋。围绕滇池的蔚蓝、凡俗、苦难、造城等事件经历的是数千年的历史演变,滇池作为昆明城成长、变幻的见证者,无数历史渊源、人文景观、社会事件在海男恣意汪洋、想象丰富、饱含情感的文字中逐一呈现。
海男为表达对昆明和滇池的热爱采取了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十四行诗。在《滇池传》中她用57篇十四行诗对滇池与昆明进行了书写。1940年代,面对昆明美丽的山水,冯至曾写下27首十四行诗,这些诗虽是其生命感悟却与昆明的自然山水、美丽景象密不可分,客体景象、主体感悟与十四行诗优雅、舒缓的节奏完美结合使冯至吟出抗战时期最美丽的诗篇。冯至之后也有诗人(如于坚)面对昆明山水写下十四行诗,但是以十四行诗大量书写昆明的诗人却没有,因此可以认为海男就是继冯至之后以十四行诗书写昆明的那个人。阅读海男的十四行诗,发现无论是风度翩翩的历史人物还是美轮美奂的昆明风物都成为被吟诵的对象,这样的想象和吟诵将昆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起来赋予了昆明一种永恒意义。
杨杨的《昆明往事》以“往事”为题将笔触指向昆明的历史与记忆。古滇王国的青铜之光、南诏国的东京、大理国的陪都、元代中庆城的壮丽、明代昆明龟城的建造、滇越铁路与近代化的进程、护国运动、西南联大、昆明之恋等构成了作者絮说昆明历史的线索;昆明名胜金马碧鸡、滇池、西山、翠湖、地藏寺经幢、金殿、筇竹寺、大观楼、圆通寺、黑龙潭和讲武堂等成为定位昆明的细微空间;阳光之城、彩云南现、后花园、西便门、民族村、世博园等自然与人文景观成为古老传说和现代生活的交汇点;这是古老弥新又令人心醉的昆明。徜徉于《昆明往事》会发现杨杨有着与海男相似的感觉——惊讶于昆明的历史文化遗迹,感叹于昆明的自然人文景观,奋笔于敬畏触动之际。他们希望通过为昆明书写传记,将昆明与神话、传说、历史连接在一起,将昆明构建成为一座“新世纪的传奇之城”。
为昆明纪史写传,与其说他们希望梳理昆明历史,毋宁说他们希望完成对昆明的认同。新世纪最显著的特征是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地方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地方文化也在反抗全球化的过程中显现出自己的力量,周宪认为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关联围绕着双重轴心:“一是空间轴,它体现为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是时间轴,它呈现为本土的当下(现在)与过去(传统)的相关性。……在空间轴上,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对自我的体认。在时间轴上,当下的变化催生了我们对自己过去的体认和乡愁,对传统流失的忧患和反思。”[21](P227~228)新世纪的昆明面临着地方文化被全球化的遮蔽与摧毁,城市的外部景观正在变得与其他城市趋于一致,城市精神文化也在流行文化、商业文化的冲击下逐渐被遗忘,无论空间还是时间上昆明都出现了差异与断裂,在这样的状况下梳理昆明历史文化、挖掘传统特征就是地方文化对全球化的一种回应,是昆明对自身连续性和传统性的书写与认同。
地方化对全球化的回应中,地方必然成为一种方式、成为一个认同的空间。大卫·哈维认为我们“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追求个人的或集体的认同,追求安全的支撑物。在内聚于我们身上的附加于各种空间形象之上的这种拼贴画之中,场所的认同成了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每个人都占据着一个个性化的空间(一个身体,一个房屋,一个家,一个正在形成的社群,一个国家)以及我们如何使自己个体化而塑造认同。”[22](P379)近年兴起的城市文化研究就是以空间认同为目的的一种研究,当传统的故乡含义改变之后,对当下生活空间的认同成为一种新的认同方式(这并非指对故乡认同的消失,而是指它的转移),对当下生活空间的认同,需要营造出一种类似于故乡的家园感,“全球化的进程激发了许多复杂的地方性反应,其中之一就是对家园感丧失的焦虑和重构的冲动。”[21](P235)重构家园感的冲动需要对家园的历史文化特点有很好的认知。《新昆明传》《滇池传》和《昆明往事》对昆明的书写就是以文学的表意实践进行重构家园的一种努力。海男和杨杨虽非土生土长的昆明人,但他们对昆明的热爱、认同之情俱体现于对昆明的自然景观、历史人物、名胜古迹、家乡味道的痴迷中了。对昆明而言这样的书写还有一种意义,昆明作为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吸引着诸多国内外游客的目光,传记式书写的往事发掘和怀旧想象都以生动的文学形象和浓郁的故乡情感满足了游客对于美和家园感的需求,使其更易倾心于昆明。
传记式书写立足于昆明的过去,其目的却是对昆明现在和未来的认同建构,“真实地建构的过去总是与从今天向明天的转变有关。”[23](P199)正如威廉斯认为乡村是被虚构和美化的田园、城市是被丑化的罪恶之地,霍布斯鲍姆认为传统是被发明的一样,霍尔认为认同是一个从未完成的建构过程,这个建构的过程关心的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来自哪里,更多的是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我们是如何被表现的以及与此相关的这些问题如何影响到我们将怎样表现我们自己。”[24](P4)因此,传记式书写昆明关心的问题是由认同出发的“昆明将要成为什么”的问题,这是由昆明历史出发对昆明未来的一种期待书写。海男和杨杨书写的“新世纪的传奇之城”①需要注意的是,于坚在二人之前就已写了《昆明记》,他在文中也采用了对昆明纪史写传的手法,不过文中表达的态度却与二人不同:于坚认为昆明虽有辉煌、灿烂的历史,但是昆明这个故乡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昆明,他甚至在这座城市无法找到自己的出生地,可见于坚是对昆明的变化持批判态度。海男则认为新世纪的昆明尤其需要变化,“在这座城市的上空,除了光荣灿烂的史迹之外,还遗留了无以尽数的不和谐的前历史。它们在各种视觉中以建筑、道路、陈旧落伍的景物损伤着21世纪的审美和城市摇篮。”(海男:《新昆明传》,广州:花城出版社,第47页。)她认为昆明需要一种快速度的旋律来改变以适应新世纪。已经给予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昆明将会成为阳光之城、魅力之城、魂牵梦萦的后花园和中国的西便门,这些词汇不仅会增强人们对昆明的认同,更会建构昆明的未来。
三种书写方式建构的昆明形象回答了关于昆明的三个问题——“昆明是什么”“昆明在怎样”和“昆明将要成为什么”,这些问题虽然指向的时间有所不同,但是指向的空间都是昆明,可见围绕昆明的文学表意实践之复杂与丰富。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种形象只是昆明城市空间表征的一部分,昆明还有更多的差异性及丰富性有待梳理与揭示。
[1]汪曾祺.昆明的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2]杜运燮,张同道.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书前)[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3]鹿桥.未央歌(前奏曲)[M].合肥:黄山书社,2008.
[4]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5]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张永杰.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J].云南社会科学,2006,(2).
[7]先燕云.三千里地九霄云——宗璞与云南[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
[8]冯至.阳光融成的大海[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9]朱自清,等.流亡三迤的背影[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10]弗雷德·戴维斯.怀旧与认同[M]//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于坚.还乡的可能性[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2]于坚,谢有顺.于坚、谢有顺对话录[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13]陆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14]本·海默尔.日常生活与文化理论导论[M].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于坚.我述说你所见:于坚集1982—2012[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16]于坚.人间笔记[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17]于坚.于坚思想随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8]于坚.于坚大地随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19]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0]杨杨.昆明往事(序)[M].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21]周宪.全球本土化中的认同危机与重建[M]//周宪.文学与认同:跨学科的反思.北京:中华书局,2008.
[22]大卫·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23]乔纳森·弗里德曼.文化认同与全球性的过程[M].郭建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4]Stuart Hall,Paul du Gay.Ques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y[M].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6.
Literary W riting of Kunm ing′s Image
LU Jian-q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Yunnan,China)
Since 1980s,Kunming has been represented as three kinds of images in literature writing:the hometow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War,the habitat in the new period and the legendary city in the new century,which correspond to the questions of“what is Kunming”,“what is Kunming being”and“whatwill Kunmingbe”.Thehometow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refers to Kunm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which is a nostalgia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ty;the habitat in the new period today′s Kun ming,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hange of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city;the legendary city in the new century Kunming′s fu ture,which is a kind of expectation to the city′s future starting from the history.The three images are related to three kinds of writingmode:nostalgia,daily life and biography,which are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r signifying practice of Kunming identity.
image of Kunming;literary writing;identity
I022
:A
:1006-723X(2015)02-0136-07
〔责任编辑:黎 玫〕
芦坚强,男,云南大学人文学院2011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理论、空间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