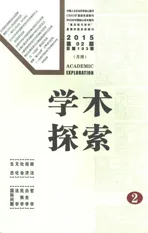超越理性限度:教育变革的内在诉求
2015-02-26李孝川
李孝川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超越理性限度:教育变革的内在诉求
李孝川
(云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教育场域里效率至上单一育人理念的追求,学校程序化学习方式的灌输以及标准化学校生活模式的塑造,导致了学校教育重知识轻经验,重认知轻情感和重整体轻个体现象的出现。致使教育从“人的教育”转向了“工具的教育”,陷入貌似理性的行为实则却遮蔽了其实质的非理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教育的本义,探寻一条新的教育变革发展路径,使教育走出形式理性实则非理性的误区。
理性;限度;教育变革;内在诉求
一、理性及其内涵解读
由上海纪实频道播出的六集电视专题片《教育能改变吗?》,描述与分析了教育领域里的诸多问题,提出教育变革势在必行的呼声。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思考,为什么教育变革势在必行?是否是目前教育领域过分追求理性,忽视或否定非理性成分的作用与价值诉求所带来的弊端造成的?那么实现教育变革又何以可能?在一系列的追问中,最核心问题在于对什么是理性?什么是理性的教育?
何为理性?根据《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解释,“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成分时,它才成为有价值单独讨论的特定思想方法。无论直觉、想象、试错法这类思想活动有着怎样出色的成果,都是被排除在理性之外的。”[1](P344)由此可见,理性是指个体按照逻辑思维合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理论、学说等。理性构成人类主体意识的标志,是个体理智的运思,做出合理性、合规律性判断的过程。
那么什么是理性的教育呢?所谓理性的教育,其目的在于培养完整意义上的“人”,一个完整的“人”所拥有的世界既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理性成分,也包括本能、需要、情感、想象等直接与生活世界联系紧密的非理性成分。只有最大效度地促进人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的融合,才能真正培养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正如自然主义哲学的倡导者卢梭所说:“在人的一切官能中,理智这个官能可说是由其他各种官能综合而成的。因此他最难于发展,而且也发展得最迟……一种良好教育的优异成绩就是造就一个有理性的人,正因为这个缘故,人们就企图用理性去教育孩子!这简直是本末倒置,把目的当手段。”[2](P89~90)
长期以来,在理性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教育领域里出现了理性泛化趋势。教育活动基本着眼于人的理性因素的发展,把理性知识的传授,理性能力的培养作为至高的价值追求。导致在教学活动中,重认知记忆轻情感熏陶,重知识传授轻经验习得,重教师主导轻学生主动,重科学程序轻灵活变通,使教育领域陷入看似理性实则非理性的境地。
二、形式理性的呈现形态及原因阐析
人的本性决定了人是一个感性、理性及非理性的统一体,要发展和完善人的统一性需要完整的教育来实现。但是现实情境中的教育却是一种片面强调理性,忽视感性和非理性发展的理性主义倾向的教育,使学生在学校中过着一种不完全并有缺陷的生活。从不断前移的起跑线到奥数班、英语班、各种文体艺术竞赛班,以及各种考试、排名、升学……教育场域里的社会化情境,到处充斥着理性主义的气息。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发展的可能向度,陷入形式理性的险境,导致教育场域里一些扭曲现象的发生。
(一)重知识轻经验:效率至上单一育人理念的追求
在效率优先的观念引领下,无论制定何种教育目的,无论采用何种教育方式,无论传授何种教育内容,一切均以“效用”为最高价值尺度。[3](P20~21)整个教育形态无论是教育内容,还是教育形式基本都是围绕理性因素展开,教育就是一个不断追求理性的领域,主要着眼于学生理性因素的培养和发展,注重理论性、系统性知识的传授,注重基本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培养。过分关注知识的系统性、高效性以及学生掌握知识的逻辑认知能力培养的快捷性。导致教师在教学中普遍采用灌输法,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把知识以条理化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学生依靠记忆来摄取知识,学生对知识是否透彻理解是值得怀疑的,而且学生无法获得理解知识所需具备的感性认识,学生没有时间亲自参加实践体验知识,更无法在实践中锻炼与发展获得知识的逻辑分析能力,限制了学生兴趣、灵感的发展。这种对效率优先价值观的偏爱,注重手段的有效性,可预测性、可控制性,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人的多样性、创造性,脱离人所生活的意义世界,实质是一种形式上的理性。这种形式理性注重对普遍规律的追求,对技术操作的盲从,导致背离理性设计的预设,造成行为方式僵化、常规化,使丰富的生活世界处于单一化、停滞化的危险状态,导致学校里一切教学活动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进行,教学秩序越来越固定化和模式化,教育过程成为一种“装饰的形式”,缺乏对人性的关怀。
(二)重认知轻情感:学校程序化学习方式的灌输
教育场域对理性的追求,对固定的模式和程序过分盲从,导致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过分强调和片面理解,不自觉地将科学的价值观与精神排斥在科学文化之外。这一价值观指导下的科学教育仅限于科学知识与技能等层面的传授与认知,忽视科学文化内在精神和人文价值。使教育处于一种纯粹“与人无涉”的境地,不是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在终极关怀层次上驾驭科学和技术的主体,而只是使其成为科学技术运行中的一个环节,一种为机器所摆弄的“工具”,消解了科学文化对学生成长所能发挥的价值,为此也导致科学教育与人文精神的割裂和对立,使培养的学生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4](P6~8)这种理性的强调具体表现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上,过分重视传授知识,训练智力,轻视或忽视没有列入高考必考范围之内的德育、体育、美育等学科的教授,或者直接把其作为发展学生智育的手段,导致学校教育中重理轻文现象的出现,导致学生感受力衰退、精神生活贫乏、情感冷漠。[5](P14~16)学生与其生活的周围世界被书本知识隔离开来,学生只能囿于非常有限的“理性”领域,多数时间是与单调的文字符号进行交流,其精神生活也因此变得贫乏。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的“学生在学习、在掌握知识,然而实质上却没有精神生活。”[6](P18)忽视教育的过程除了是理性活动和逻辑思维活动,也是一种感悟和体验的活动过程,教育过程除了育智、育理,还应该育心、性、情,重视人文精神的陶冶。教育领域里重视理性能力培养否定感性知识的养成,试问这样的状况理不理性?
(三)重整体轻个体:标准化学校生活模式的塑造
学校对程序性、标准化模式的追求,对准确答案的膜拜,对听话、安分守己且考试分数高的学生的偏爱,对升学率的盲目追捧等,都体现了对追求投入与产出相等的评价理性的价值取向。对学校和教师来说这无疑不是一件坏事。但对于发展中的学生而言,却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其创造力和想象力,学生被视做纯粹的“实现目标的既定人”的客体被打磨和塑造,遗忘了学生的生成性和过程性,学校成了复制、生产标准化的“单面人”的“加工厂”,“教育”也沦落为宰割学习者全面性和差异性的“普罗克拉斯提斯铁床”,最终导致人性中最有活力的创造性、情感、个性等特征丧失殆尽。[7](P30~31)学生成为从标准化生产线上出来的“商品”,被“物化”,甚至被“异化”,异化为“知识的容器”“分数的奴隶”,异化为早熟的“成人”。[8](P119~124)标准化模式遵循的实践逻辑,强调知识掌握的数量与精确性,把教学活动简单地理解为知识的积累,并以知识掌握的数量和精确性作为评价的标准,给学生贴上标签,分出等级。学生为了适应这样的理性教育,成为应付考试的机器。这种机械主义的形式理性教育扼杀了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学校里培养出来的人,与其说是充满个性和创造力的人,不如说是像从一条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无多少差异的“产品”,缺乏应有的直觉、灵感、想象力和情感体验等。导致人所特有的理性特质,只是把人与动物进行了区分,却没有把个人与他人明显进行区别,反而使个体的思想在经过理性教育之后更趋于同质化。
三、教育变革内在诉求的路径分析
对理性的过分追寻使得理性成了“工具理性”的代名词,甚至工具理性在教育场域里被直接冠名于功利主义,教育从“人的教育”转向了“工具的教育”,强调对效率的追求,疏远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强调对外在规范的遵循,忽视对生存状态的体验。这种以剥夺世界的意义与人类自由为代价的形式理性,丧失了教育的本义,看似理性,实则可能造成价值迷失的危险,导致貌似理性的行为实则却遮蔽了其实质的非理性。
(一)通过认知教育的复杂性情景来提高经验水平
教育是有自身特殊性的社会现象和鲜明社会历史性的活动,它的实践模式显著地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与活动。如果不顾自身特色、抛开具体的情境简单地套用其他社会领域的活动方式去追求所谓的普适性,依后现代主义者格里芬所说就是“祛魅”了,即“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9](P2)教育是以意向性、生成性的方式展开,充满实践智慧、富有探究色彩的活动,基本特征是行动性,基于问题解决的特定的教育情境和当下所能利用的资源、条件等都是解决问题的手段和工具。[10](P7~12)这些都充分显示了教育系统的复杂性。
教育系统的复杂性带来对教育系统变革的分析应基于复杂性情景的认知。教育变革的实施和深化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这种非线性特征衍生了教育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变革是非直线的,充满着不确定性,有时还违反常理。”[11](P30)很难用实证科学的严密逻辑思维对教育变革进行直接的演绎推理,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经验水平来实施应对。
教育变革的复杂性情景强调对教育的认知,不是对简单性理论的遗弃,而是在对简单性思维整合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实现思维范式由系统思维转向复杂思维。意识到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组织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一个复杂性新范式正在各个领域酝酿成形。尽管这个范式可能在某些领域还没有成为主流范式,但是作为一种替代范式或替代范式的候补者已经不可避免。”[12](P20~24)教育变革实践的复杂性需要用复杂性的思维去重新审视教育变革过程,关注系统在进程中的非线性特征和非平衡状态下的复杂性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于认识系统演化和生成的重要价值,从而对教育变革的真实过程形态有更为深入的洞察和理解。
(二)通过建构学习型社会来培养情感梯度
以往的教育观念秉承一种工程思维,追求的是工具理性与目标线性的教育方式。教育追求的是短期的效率,关注的是投入产出的收效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把教育的对象看作是被动的工具,忽视了人的主观性和能动性,制约了人的情绪的自然流露,抑制了教育主体双方在教育过程中的互动,使教育过程失去应有的生成性,教育对象明显缺乏灵活性、创造性、类推性、非逻辑性推理能力等,尤其在创造性和想象力上表现欠佳。
要克服工具理性的弊端,就要着眼于建构一个对人、对人性及对人生真正价值的培养与实现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倡导学生主体地位的回归,鼓励学生情感的培养。认为教育是作为个体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学校的任务在于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资源和场所,教育目的在于追求学生的健康成长、人格塑造和自我实现。学习型社会赋予了教育新的内涵,认为教育不仅是取得学历、获得生活技能的一种手段,更是一个人实现和谐发展与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不是对学校教育存在的合理性进行否定,也没有走伊里奇提倡的“非学校化教育”路线,也并非是对传统教育的简单延续和重复,而是在价值转换的基础上,客观地认识到现代人所面临的挑战,看到学校领域里的制度化学习并不能让人终身受益且一劳永逸,强调终身学习、自主学习将成为每个公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以及个体情感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价值和作用。
学习型社会的理想图景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生命情怀,不局限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一致的“人力资本”的理论内涵,更是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所需的情感诉求。其内涵也表现出它是一种特定的教育价值选择,是人类社会渴望在一种人性化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教育而实现自我完善的理想价值追求。[7]正如赫钦斯所说的:“人是有理性、有道德、有情感的,人达到完善的境地即意味着其理性、道德和情感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学习型社会就是希望使每个人的这种力量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13]
(三)通过呼吁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来彰显个性
受形式理性的影响,教育成为发展科技与促进工业生产的途径,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培养“技术人”,学校教育逐渐与日常生活疏离,仅仅关注生活的某一方面,而忽视了其完整性。过分强调人对知识的掌握,忽视其情感、价值、美德等个性方面的发展。在工具理性的制约下,生活的意义被界定在对某种外在生活样式的依从上,教育的规定性是从外在的、抽象的、绝对化的观念中获得的,结果是教育与生活及其关系被模式化,个体出现趋同化倾向,个性被磨灭。
然而完整“人”的培养离不开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人生活于其中的,人作为价值主体和意义主体存在的源头,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的人的世界。而不是对“科学”和“理性”盲目地崇拜,不是把“科学世界”和“理性世界”的教育当作人的全部教育的世界,更不是把科学世界的教育与生活世界的教育进行割裂的世界。而是更注意到作为人的历史性、个体性、创造性和生成性,更关注使人具有“完人”的特征,使教育真正回归生活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理性化”的机器世界。
一旦教育不能走进生活,就会变成学习者的一种负担和压力。因此,只认识到教育是什么?为什么?或怎么样是不够的,还应了解日常生活世界,呼吁教育回归生活世界,使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并不是要把当下的生活不加选择地照搬到学校,而是强调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社会体制化的产物,其目的在于使人不断摆脱各种外在羁绊,走向自由,体现个性,使教育真正关注与靠近人的心灵与情感。如《学会生存》中所强调的,“现代
教育的实质在于追求良好的生活质量……影响一个人内心精神状态的教育革命,堪与人类在外界空间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成就相比。”[14](P61)由此可见,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价值诉求是以日常生活为依归,力求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并通过对生活疆域的开拓来改造和彰显个性。
[1]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New York 1968,Vol13~14.
[2]卢梭.爱弥儿[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刘锦平.重建理性与教育的融合点[J].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1,(6).
[4]刘春燕.当代教育中的工具理性主义[J].江西教育科研,2004,(8).
[5]何齐宗.当代教育的理性主义倾向评析[J].中国教育学刊,2002,(5).
[6]苏霍姆林斯基.关于全面发展教育的问题[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7]张良.论“学习型社会”视野下成人教育观念的转变[J].成人教育,2010,(7).
[8]于伟.论技术理性时代“完善的人”的消解及其对教育的负面影响[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3).
[9]大卫·格里芬.科学的返魅[A].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C].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10]刘旭东,吴银银.超越理性主义:实践的教育理论的发展路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11]迈克尔·富兰.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12]吴彤.复杂性范式的兴起[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6).
[13]R.Hutchins.The Learning Society[M].London:Pall Mall,1968.
[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Transcend Rationality Lim itation:Intrinsic Aspiration of Educational Change——Based on the Thought that Can Education Change?
LIXiao-chua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Management,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650500,Yunnan,China)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the pursuitof efficiency first,routinizational learning styleand standardizedmodel of school life have led to the school attachingmore value to know ledge and less to experience,more to cognition and less to affection and more to the whole and less to the individual.Education ofman has changed into education of tool.The seemingly rational action covers the virtual non-rationality.It is,therefore,necessary to re-examine the originalmeaning of education and explore a way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school in order tomake the education out of present non-rationalm isunderstanding.
rationality;limitation;educational change;intrinsic aspiration
G40-02
:A
1006-723X(2015)02-0153-04
〔责任编辑:李 官〕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3XMZ071)
李孝川,女,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