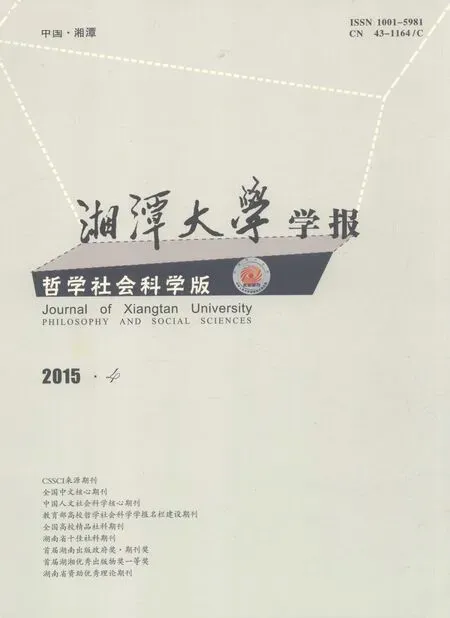《红楼梦》中的性政治及其建构*
2015-02-22赵炎秋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红楼梦》中的性政治及其建构*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红楼梦》中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贾府的地位与权势主要来源于其男性祖先的军功,其家族的权力建构主要依据性别、父系和母系三大原则进行。不过,《红楼梦》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不是通过暴力和压迫,而是通过一种强调等级、秩序的亲情关系。为了得到女性“自愿的赞同”,男性对女性施行了包括权力让渡在内的各种策略。在这种父权制社会的性政治现实中,性别的模糊、性方面的洁身自好和男女角色的颠倒都是不被允许的。
关键词:《红楼梦》;性政治;父权制社会;男性;女性
米利特认为,凡是“人类某一集团用来支配另一集团的那些具有权力结构的关系和组合”都是政治,性则“是人类的一种具有政治内涵的状况”。在这种政治权力的结构中,作为集团的女性是受压迫的,但却没有被表现出来。而“正是由于在若干显而易见的政治结构中有些集团没有被表现出来,这些集团的地位才如此永无变化,它们所受的压迫才如此没有尽头”。[1]36,37这种情况在《红楼梦》研究中似乎也存在着。本文试图通过对《红楼梦》性政治及其建构的探讨,增进我们对这部世界名著的理解,并以此作为个案,进一步了解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男女政治关系。
一
《红楼梦》描写了贾史王薛四大名宦世族,其中“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家又是重点描写对象。自宁国、荣国二公之后,这个家族共有20个分支(房),其中宁荣亲派8房住在京城,主子几十个,仆从几百人。那么,贾家的地位、权势、财富来自何处。笼统地说,当然是皇帝赐予的。具体地说,则主要来自军功。贾府的祖宗贾太公生二子,长子贾演,次子贾源曾出生入死地带兵打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大难不死,功勋赫赫,被封为宁国公和荣国公,为贾府创下基业,并且庇荫着贾府后人。贾赦、贾珍两房犯事,家产查抄、爵位削去、流放站台、海疆。但由于皇上“想起贾氏功勋”[2]1588,“念伊究属功臣后裔,不忍加罪”[2]1442,仍陆续给还了家产、爵位(贾赦的爵位由贾政承袭)、并最终赦免回家。
自然,就贾府的权势、地位与财富而言,应该提到的,还有贾元春的作用。元春很年轻时便被选入宫中做女史,后加封贤德妃。元妃的入宫,使贾家与皇帝成了姻亲,进一步巩固了贾府的权势和地位,也增加了他们的财富。①《红楼梦》中,皇上因元妃之故,曾多次赏赐贾家。仅元妃省亲,就赐了不少财物。参见《红楼梦》第249页,253页。小说中元春出现的次数虽然不多,但其存在本身就是贾府的福音。而且,死去的元妃也在冥冥中护佑着贾家。皇上的宽恕、赦免贾家,小说虽未明说,但与元妃也有或明或暗的关系[2]1588。后来宝玉和贾兰的举业高中,与皇上知道他们是“贾妃一族”亦有关系。
然而尽管如此,在贾府的权势、地位与财富的建构中,贾元春很难说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是因为,元春并不是贾氏家族的奠基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贾氏家族的地位与权势的受益者。正如宝钗随母兄进京备选“才人赞善”,是因她具备“仕宦名家之女”的条件,当年元妃选入宫中做女史,与她出身贾府这一先决条件和早年所受的教育是不无关系的,这是她腾达的基础。而更重要的是,元春对贾府地位和权势所做的贡献,并不来自她本人,而是来自皇帝,实际上是皇帝对她的赏赐。恩格斯在论述中世纪封建主之间的联姻现象时曾指出:“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借一种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3]91-92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春只是贾府与男权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之间,也即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交换物。皇帝得到了性和服务,而贾府则得到了他们需要的权势、地位与荣誉。在这种格局中,元春不过是个利益交换的棋子。在这种交换中,贾府是积极的,而元妃个人的意志与幸福则没有被考虑进去。
二
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权力的建构。《红楼梦》中的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父权制社会。其权力的建构依据着父权制社会的三大原则。
第一,是性别原则。所谓性别原则是指将社会成员依据其解剖学特征分为男女两性,并让其承担不同的角色、享受不同的权力、行使不同的功能。美国学者波普诺认为,“性别是不平等的一个主要源泉——不仅仅由于男人和女人承担着不同的角色,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角色受到了不平等的评价和对待。”[4]372《红楼梦》中,男性是社会的参与者和管理者,男性并且只有男性,才能与社会公共领域发生直接的关联,女性则只能通过男性,间接地与外面的世界发生关系。贾府内眷居住的三门之内,整天有人看守,无人叫的话即使管家也不能进去。[2]1505从表面看这似乎是在保护女性,实际上是阻断了她们参与公共领域的权力,阻断了她们在公共领域中崭露头角的机会。
女性无法成为社会正常的一员,更不可能进入社会的管理层。贾府中许多才高八斗、富有管理能力的女性如宝钗、黛玉、探春、熙凤等,只因她们是女性,便只能囿于家门,无法在社会的大舞台施展自己的才干。而像贾政这样外不能齐国、内不能治家,只知一味清高的庸碌之徒,或者贾赦、贾珍这样不学无术、胡作非为的荒淫之属,却占据了高位,成为国家的栋梁、家庭的主宰。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设想莎士比亚有一个同样有天赋的妹妹,然而她受不到正规的教育,还只十几岁就被她父亲强迫嫁给一个羊毛商的儿子,她逃跑到伦敦,想像哥哥一样靠演戏谋生,但没有人相信一个女人能够成为一个演员。她走投无路之下成为一个戏子兼经济人的情妇并怀了孕,她的诗人的心无法接受这一点,于是在一个冬天的夜里自杀了。[5]46-51贾府里这些才高八斗的女子,虽然没有自杀,其遭遇与那个假想中莎士比亚的妹妹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另一方面,从家族的角度看,只有男性,才能成为家族的代表、掌握家族的实际权力。贾府中,族长是贾珍,两个爵位由贾珍、贾赦(后由贾政)承袭,在朝廷做官的是贾政,家族的财产由男性掌管。男性负责贾府中的与政治、经济、社交相关的活动,承担养家糊口的重任。《红楼梦》第53回,宁府黑山村庄头乌进孝来宁府交租,贾珍看了租单,不满地说:“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五千两银子来,这够了作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真是又教别过年了。”[2]721这段话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宁府的经济是由贾珍掌管的,一是养家的责任也是由贾珍负责,因此他才担忧无法过年。而同一回里,贾母等女眷则只管过年、听戏、赏钱,似乎并不为整个贾府的经济状况操心。
第二,是父系原则。父系原则就是根据父系方面的血缘关系,决定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尊卑和继承的权力与顺序。《红楼梦》中,贾府大小几百号人,根据父系方面的血缘,划分为主子与奴才。奴才功劳再大、再有钱,仍是奴才,低于主子、听命于主子。贾府的仆人焦大,跟随太爷征战,功勋赫赫,只因说了几句主子们不喜欢听的真话,被人捆翻在地,喂了一嘴的土和马粪。而贾环这个卑劣委琐、人人讨厌的家伙,在贾府屡做坏事。却只因他是贾政与赵姨娘所生,是个主子,便每每化险为夷,王夫人等往往只是将他责骂一顿,事情便不了了之。[2]335,1585,1591他仍是主子,有机会时,仍可作恶。
第三,是母系原则。所谓母系原则,就是根据母系方面的血缘关系,将同父的子女分为正出和庶出,并将权利赋予正出。贾宝玉在贾府之所以万千宠爱在一身,就是因为他是贾政和其正妻王夫人的儿子,而贾政虽然只是荣府的二子,却是贾府权力的实际掌管者,后又袭了爵位。而探春,虽然也是贾政所生,但由于母亲是赵姨娘,因此虽然聪明有能力,仍不免时常受些闲气,无法上升到权力的高位。
除了上述三大原则之外,《红楼梦》的权力建构还有一些次要的原则,如长子继承原则、父系至上原则和正妻通吃原则。父系至上指父亲方面的亲属关系要高于母系方面的亲属关系。正妻通吃指正妻地位高于所有的妾,一个家庭所有的子女不管是正妻所生还是侍妾所生,理论上都归父亲和正妻所有,由父亲和正妻管理教育。《红楼梦》第20回,贾环同宝钗的丫环莺儿玩耍,输了钱耍赖,舍了脸面,向他母亲赵姨娘诉苦,赵姨娘骂他,恰好被凤姐听见,教训赵姨娘道:“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作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2]275而赵姨娘的女儿探春更不把她当回事,宣称自己“只管认得老爷、太太两个人,别人我一概不管。”[2]369贾环和探春虽是赵姨娘所生,但无论是在别人还是他们自己眼里,这两个孩子首先都是老爷和太太的,与他们的生母没有多大的关系。
《红楼梦》中的人物众多,家族之间的权力关系纠结复杂,但认真分析,都是由这三主三次原则决定的,是其综合运用的结果。而贯穿这些原则的红线,仍是男尊女卑这一父权制社会的基本准则。性政治在《红楼梦》中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
三
不过,如果仅仅将《红楼梦》中的性政治理解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也是不准确的。托尼·本尼特在解释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时说,“统治集团的支配权并不是通过操纵群众来取得的,为了取得支配权,统治阶级必须与对立的社会集团、阶级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谈判,这种谈判的结果是一种真正的调停。换言之,霸权并不是通过剪除对立面,而是通过将对立一方的利益接纳到自身来维系的。”[6]17100多年前,穆勒就曾指出:尽管妇女处于被压迫的地位,但“她们仍处于不同于其他从属门类的地位,她们的主人要求她们的,有比实际服务更多的东西。男人并不只是需要女人的顺从,他们还需要她们的感情。除了最残忍的男人之外,所有男人要求于同他们最亲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女人的,不是一个被迫的奴隶而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奴隶,不只是个奴隶,还是他们所宠爱的。”[7]268人类社会的任何阶层或群体都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男女这两大群体更是如此。由于家庭的组合,生理、心理的相互依赖,经济、利益的高度融合,男女的相互依存比人类社会任何其他群体之间的依存都更加紧密、更加稳固、更加长久,也更加不可分割。因此,男女之间的政治关系更加具有调停和协商的性质。《红楼梦》中也是这样,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不是通过暴力和压迫,而是通过一种强调等级、秩序的亲情关系。
为了维系对女性统治,《红楼梦》中男性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创造有利于男性的制度和文化观念。如前面讨论的《红楼梦》权力建构中的性别、父系、和母系三大原则,它们无疑是维持和巩固着男性对女性的统治的。无论是谁,只要他(她)认同这些原则,也就等于认同了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与这些制度配套的,则是相应的文化观念。《红楼梦》中,男子需要有才。这种才是仕途经济的才,而不是诗词歌赋的才。自然,诗词歌赋的才不是不需要,但不是主要的,更不能以其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据。至于女性,则无需有才,只要有德就行。《红楼梦》第42回,宝钗听黛玉说出《牡丹亭》、《西厢记》中的句子,告诫她说:“咱们女孩子家不认得字的倒好。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一席话说得黛玉“心下暗伏,只有答应‘是’的一字”。[2]568作为《红楼梦》中的闺阁典范,宝钗完全接受男权社会规范,被男权社会所同化,这不奇怪。奇怪的是,作为宝玉的同道、仕途经济反对者的黛玉,对宝钗的话也只有点头称是的份。这说明父权制文化影响的深广,即使是它的叛逆者,也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受其左右,即使那些规则实际上是有违她们的利益的。
其二,是保证女性的生活条件并给予其适度的尊重。统治阶层要取得被统治阶层的赞同,首要的条件之一是要让其能够生存并且是较好的生存。在性政治领域更是如此,男女中的一方在待遇方面如果不能与另一方大致相等,这个契约的结合体就会面临崩溃的危险。《红楼梦》中,虽然经济权在男性手中,但经济的管理权则是由女性和男性分享的,甚至在某些方面女性还管得更多一些。荣国府的家政由贾琏和凤姐夫妇负责,名义上是贾琏为主,但实际上则是凤姐管得更多。一个女人,只要与男人结了婚,那么不管她以前什么出身、家庭是否贫穷,理论上她都能享有与这个男性大致相当的待遇,如香菱、平儿都是如此。自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能给自己的妻妾以荣华富贵,但是他必须为她们提供大致相当于他自己的生活水平的生活,否则,妻妾就有理由不满,而这个男人也会受到社会的指责。
除了生活的保证之外,适当的尊重也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人的心理需求,也是对其地位的肯定。《红楼梦》中,常常用到“体面”二字。第44回,贾琏与鲍二家的偷情,被凤姐撞破,两下撕打,平儿也受了委屈。贾母强令贾琏向二人陪不是,于是“平儿自觉面上有了光辉,方才渐渐的好了”。[2]593凤姐“争足了光”,[2]597也不再闹。鲍二家的因偷情事发而自杀,贾琏给了鲍二一些银两,答应为他再娶一个媳妇。“鲍二又有体面,又有银子,有何不依”。[2]598这里的所谓体面,也就是处于优势的一方给劣势一方的一种尊重。袭人之所以死心塌地的服侍宝玉,除了她与宝玉的暧昧关系和她尚未言明的妾的身份之外,与宝玉对她的尊重也是分不开的。
其三,是让渡出一定的权力。稍加注意,我们就能发现,《红楼梦》中,男性是大权独掌,但却不是大权独揽。在保证大权不旁落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也让渡出一定的权力,如家政权、经济的管理权等。因此,《红楼梦》中的太太、奶奶和姑娘,甚至一些大丫环们,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但是她们也都知道,她们的权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男性。《红楼梦》中的姑娘,在娘家时地位虽然尊贵,但却无权,权力都掌握在已婚女性手中,只有成为了某位“奶奶”,她们才有掌权的可能。因此,王熙凤防贾琏像“防贼似的”,[2]288固然有妒忌的因素,但也不无利益的考量。因为她的权力来源于她和贾琏的婚姻。一旦婚姻消失,权力也就会跟着消失。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父权制社会的规则所决定的。
在《红楼梦》中,男性让渡权力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孝的名义,让女性长辈得到一定的尊荣与权力。“孝”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维持社会秩序、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红楼梦》中,孝是贯穿始终的基本准则。晚辈孝顺长辈,年轻的尊敬年长的,至少在显性层面上是必须遵守的。自然,所谓孝顺,首先是孝敬男性长辈,但夫妻是一体,孝敬男性长辈的同时,对于女性长辈必然也得孝顺。在贾府,贾母的地位是最尊贵的,主要原因就是她从“进了这门子作重孙媳妇起,到如今我也有了重孙子媳妇了,连头带尾五十四年”[2]622,是贾府主子中年纪最大、辈分最高的人,其他的人都是她的晚辈,因此,她也就具有了最高的地位和尊荣。不过,她仍小心地遵循着父权制社会相关的规则。她只管内不管外,而且即使内部事务,比较重大的仍然征求男性成员的意见,由他们最后决定。《红楼梦》第96回,贾母、王夫人、薛姨妈商量好了宝玉和宝钗的婚事,但最后拿主意的仍然是贾政和薛蟠。
权力让渡的另一种方式是权力的转移,即男性把自己的部分权力转移到某个或某些自己认可的女性身上。这种转移依据的原则主要有两个:出身和服务。出身使女子天然地具有某种权利,如贾府中的姑娘们。不过,出身带来的权力无法伴随终生。因为女子总要出嫁,而出嫁之后,出身带来的权利也就终结,继之的是婚姻带来的权力。当然,出身可以对女子的婚姻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使女子得到与其出身相应的婚姻和权力。但事情并不总是如此,婚姻权力的获得和大小,最终还得由女子的丈夫和丈夫的家人所决定。迎春的遭遇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权力的让渡中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服务。这种服务自然首先是性服务。性服务正规而体面的形式是婚姻,但是并不局限于婚姻,它也可以通过偷情或通奸的方式提供。而提供了这种服务的女子的地位与待遇也自然随之有一定的改变。此外,女子还可通过为男性提供其他的服务来获取一定的权力。如宝玉的奶妈李嬷嬷,因为替婴幼儿时期的宝玉提供了奶水,便取得了比其他同龄妇女更大的权力,甚至可以对袭人这样的大丫头指手划脚,指责批评。
上述措施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女性作为被统治性别的付出,因此,《红楼梦》中的女性对于男性的统治并没有激烈的反抗,许多女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自觉地维护着这种统治的,如袭人、宝钗、王夫人、贾母等。这实际上是有利于父权制社会的稳定的。
四
在《红楼梦》这种性政治的现实中,性别的模糊、性方面的洁身自好和男女角色的颠倒都是不允许的。因为《红楼梦》中的性政治是以男女性别的区分与角色分工为基础的,性政治的建构又是保证社会、家庭秩序与人际关系,维持社会运转的重要基础之一。性别的模糊、性的洁身自好和男女角色的颠倒不仅不符合父权制社会规范,也对贾府和“红楼”社会的性别政治构成了威胁。因此必须坚决反对。
男女各有自己的角色与定位,这是《红楼梦》性政治的基础。在这种角色与定位的范围之内,男女出点差错,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但违背了这种角色与定位,则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贾府的男人大都偷鸡摸狗,但当权者都只一笑了之。而对于贾宝玉的女性气质与双性倾向,贾府的长辈却进行了残酷的纠正。《红楼梦》第33回,贾政的痛打宝玉,直接的原因主要不是他与金钏儿的调情,而是他与身为男性的戏子交往,而且有着不正常的暧昧关系。宝玉与秦钟的暧昧关系,也被顽童金荣们拿来作为嘲笑的把柄(第9回),秦钟更因此丢了性命①秦钟死的直接原因是因其与女尼智能的来往被其父责打,但内在原因还是因为他有双性倾向且不求上进,鄙视功名。这都不是男性应具有的。参看《红楼梦》第16回。。而贾琏的拿小厮出火[2]286则并无大碍。原因在于,贾琏与小厮开后庭花,是为了解决性欲的问题,性别身份没有模糊;而宝玉与秦钟、琪官的暧昧,则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一种性别的模糊。因此,尽管前者有实际的行动,却未出什么差错;而后者只是互相喜爱,却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下,任何男性要发展自己的女性气质与双性倾向都是困难的。宝玉最后的离家出走,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贾府的父权制度和父权文化的反抗。
与男人的滥情不同,《红楼梦》中女性的角色与定位则只允许她们许身一人。《红楼梦》中,男性可以偷情,女性则需要贞洁。与公公偷情的秦可卿、与主子偷情的鲍二家的、试图勾引小叔子的夏金桂,最后都以身死为结局。而女子维护自己贞洁的行为则受到肯定,如第12回的贾瑞之死。贾瑞之死的关键不是贾瑞因“见熙凤起淫心”,而是因为熙凤不接受他的“淫心”。贾瑞的死彰显了凤姐的“贞洁”。王熙凤的“毒设相思局”虽然歹毒,却是符合父权制社会规范的,因此付出代价的是贾瑞,凤姐则没事人一样。
除贞洁外,女性的角色与定位的另一原则是贤惠。从性政治的角度看,《红楼梦》中贤惠的主要涵义就是女性对男性的服从,“善解”男性之意。女子可以有才,甚至可以比男性有能力,但女人不能扬才露己,更不能违反男人特别是丈夫的心意。“河东狮”夏金桂因为辖制丈夫,不尽妻子、媳妇的本分,最后中毒身死。凤姐虽然孝顺,八面玲珑,但过于扬才露己,把贾琏管得服服帖帖,最后也只能是“哭向金陵事更哀”。
性政治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建构的,而家庭的基本结构是夫妻。因此,《红楼梦》对女子独身是反对的。因为女子独身意味着家庭的无法组建,家庭无法组建则意味着性政治没有实行的条件。《红楼梦》中,女子独身主要源于对现实的失望,妙玉、惜春、紫娟、鸳鸯等莫不如此。但结局均很难说是善终。惜春、紫娟是做了尼姑,鸳鸯、妙玉则是命赴黄泉。妙玉是《红楼梦》中女子独身的代表。宋人范成大诗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妙玉自称“槛外人”,以明自己试图蹈于铁槛之外,超越生死,超出名利场之意。又自称“畸人”,②语出《庄子·内篇·大宗师第六》:“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突出自己的特立独行,纯真无伪,通天道,远尘俗的性格。但由于其带发修行,无涉婚姻,《红楼梦》对她的态度是严峻的。“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2]77这是诛心之论,指出妙玉虽然自许真洁,其实内心仍有世俗的欲望,无法战胜身体的诱惑。既然如此,她的那种单身的标榜也就只是一种姿态,无法贯穿始终。“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2]77妙玉最终被贼人掳去,后被杀于海边,是十二钗中结局最为悲惨的一个。《红楼梦》之所以给她安排这样一种结局,不能不说与小说的整体构思与思想倾向有关。
在一次访谈中,著名学者乐黛云在肯定文化多元主义的时候指出:在多元文化发展中存在两种危险:文化部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文化部落主义只强调本文化的优越,而忽略了本文化可能存在的缺失。只强调本文化的“纯洁”,而反对和其他文化的交往,导致文化孤立主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结果是本身文化发展的停滞。而文化霸权主义,强调“文化吞并”、“文化一体化”,历史证明这样的企图只能带来灾难性的悲剧结局。[8]108男女两性和两性文化也应是这样,和而不同。在两性关系上,文化部落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1][美]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2]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第十版).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英]伍尔夫.一间自己的房子[M].王环,译.沈阳:沈阳出版社,1999.
[6]罗钢等,主编.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M].王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8]乐黛云,蔡熙.“和而不同”与文化自觉:面向21世纪的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教授访谈录[J].中国文学研究,2013(2).
责任编辑:万莲姣
The Sexual Politics and Its Construction i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ZHAO Yan-qiu*(Liberal Arts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Abstract:The society of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is a typical patriarchal society.The main source of Jias’position and power is military exploit of its male ancestor.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mily power mainly based on three principle,that is gender,paternal line and maternal line.But i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the rule of male to female doesn’t based on violence and oppress,it is based on the relation of family affection that emphasize rank and order.In order to get female“voluntary approval”,the male apply various strategies to female including power demising.In the reality of sexual politics of patriarchal society,the vague of gender,the abstinence in sexual and the perversion of gender role are all prohibit.
Keywords: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sexual politics; patriarchal society; male ; female
基金项目:本文是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明清小说叙事学研究”(项目编号: 12A0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炎秋(1953-),男,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1-20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5) 04-009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