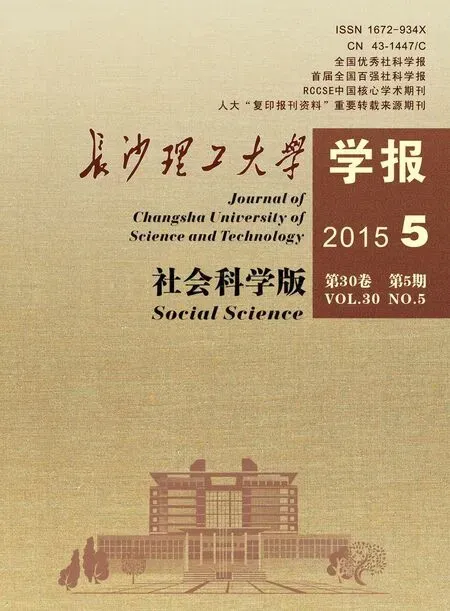三个船喻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启示
2015-02-22陈幼堂张掌然
陈幼堂,张掌然
(1.广东医学院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东莞 523808;2.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三个船喻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启示
陈幼堂1,张掌然2
(1.广东医学院生命文化研究院,广东东莞 523808;2.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文章从比较的视角探讨了“提修斯之船”“纽拉特-奎因之船”“毛泽东之船”这三个隐喻的含义及其在生命文化学研究中的作用。就本体论而言,“提修斯之船”这个比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关注文化的本质、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文化的连续与断裂、文化的继承和创新等四个问题。就认识论而言,“纽拉特-奎因之船”这个隐喻要求在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注意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历史性和整体性。就方法论而言,“毛泽东之船”这个隐喻要求生命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主体的能力水平相适应。
生命文化学;隐喻;提修斯之船;纽拉特-奎因之船;毛泽东之船
在众多与文化有关的隐喻中,有一类隐喻关系到文化研究的根本问题,它就是船喻。在西方文明中,“船”是一个基本的意象和一个根隐喻。“船”的形象经常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一再受到文学家和哲学家的青睐。如,德国文学家塞巴斯蒂安·勃兰特用“愚人船”隐喻罪恶之舟——容纳人类一切罪恶的邪恶之船;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船”隐喻“国家”,以“大海行船”隐喻“统治国家”,以“航海术”隐喻统治国家的艺术[1]等。
在中国文化中,船也是一个重要的模型,被用来作出不同的比喻,有明喻,也有隐喻,有关系比喻,也有实体比喻。在中国成语中,与舟或船有关的成语著名的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破釜沉舟”“刻舟求剑”等等。
而在国内外诸多船喻中,有三个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船喻:“提修斯之船”(The Ship of Theseus)、“纽拉特—奎因之船”(The Ship of Neurath-Quine)和“毛泽东之船”(The Ship of Mao Zedong)。本研究将探讨它们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启发意义。
一、提修斯之船及其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一)作为本体论比喻的“提修斯之船”
“提修斯之船”是从希腊神话中提炼出来的一个著名哲学论题,也称“提修斯悖论”,它被认为是一个古老的思想实验。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提修斯木船,由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直至船上的每个零件都被换成新的。这一思想实验引发了如下问题:最终产生的这艘船是原来的那艘提修斯之船?抑或是一艘完全不同的船?如果它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后来对此进行了延伸,并提出如下问题:如果用提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提修斯之船[2]?
上述问题可从集合论的角度进行表述:如果逐一替换集合A中的所有元素,并以替换出的元素构成集合B,那么对由A中的所有元素被替换之后形成的A'和由替换出来的全部元素所构成的集合B来说,哪个集合是原来的集合A?就上述船喻而言,“这艘船是不是原来的那艘船?”这个实际上就是事物的同一性问题。
关于同一性,有观点认为,能够作为一个事物依据的东西,不是组成这一事物的元素,而是这一事物的内部结构——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事物的时空连续性[3]。结构相同的定义是:事物A和事物B由相同元素构成,且元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同(一般将其中不影响整体性质的细微区别忽略不计)。时空连续性的定义是:事物A的时空轨迹是唯一的,且在时空坐标a和b点之间连续分布,没有间隔。仅仅结构相同,并不表明他们就是同一事物,还必须同时具备时空连续性才行[4]。同理,仅仅具有时空连续性,结构完全不同也不行。比如说,把一辆汽车砸碎,炼成铁块,然后用这铁块制成其他物件,比如说一尊雕像,虽然它具有时空的连续性,但是由于它的结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所以该尊雕像已经不是原来的汽车。
根据上述对时空连续性和结构相同性的理解,可以把提修斯之船所涉及的关于同一性的四种情形分析如下。
1.提修斯之船(A)不断更换部件,最后所有的部件都换了一遍(即从A到Ax)。在整个过程中,它显然具有时空连续性,更换的船板和以前的船板质料不同,但结构关系未变(或变化不大,可以忽略不计,不影响同一性),且功能完全一样,因此Ax与A是同一的,提修斯之船还是提修斯之船。这种同一性是结构-功能的同一性。
2.用从提修斯之船(A)上更换下来的全部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B),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提修斯之船?对霍布斯问题的回答是:B不是提修斯之船。因为B不具有A所有的时空连续性,尽管B的质料与A相同,且结构关系相同。
3.假定提修斯之船(A)不断更换部件,最后所有的部件都换了一遍。在整个过程中,它显然具有时空连续性,但如果结构关系有变化(即从A到Ay),而Ay与A的功能完全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Ay与A是否同一?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Ay与A虽然结构有差异,但功能相同,即异构同功,Ay与A具有同一性。
4.假定提修斯之船(A)不断更换部件,最后所有的部件都换了一遍。在整个过程中,它显然具有时空连续性,但如果结构关系有变化(即从A到Az),且Az与A的功能也有所不同,那么这种情况下Az与A是否同一?从功能主义的角度看,Az与A不具有同一性。
(二)“提修斯之船”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生命文化学是一个晚近才出现的概念,而此前类似于生命文化学的事物往往被称为生命文化研究。据董国安的定义,具有了明确的研究规范——由各种理论预设或假定、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等构成的体系——的文化研究,可以被称为生命文化学[5]。从该定义可以看出,生命文化学离不开对文化尤其是与生命有关的文化的研究。
“提修斯之船”以隐喻的方式从本体论角度提出了文化“同一性”问题。文化的演化和提修斯之船的变化有其相似性,都会发生修补和置换,文化演化置换下来的东西不可能完全重构成该文化。因为文化的时空发生了变换,所以,即使把原来的文化元素按照原来的结构关系重新组装,也是无法得到原来的“文化”的。
与“提修斯之船”不同的是,文化的演化很难保持结构-功能的同一性,除非这种文化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系统并且在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海洋中航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一些文化的演化基本上保持了结构-功能的同一性。某种文化在封闭的环境中演化或许可以保持其结构同一性,而在开放的环境中,由于难以避免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和相互渗透,所以它难以保持结构同一性。在这种环境中,文化演化更多地表现为功能同一性。
文化自身的惯性力图保持其同一性和稳定性,但文化也会在外部压力下发生被动改变,或者在文化先行者和改革者的推动下发生主动变革。因为当一种文化中的某些成分制约着社会发展时,该文化中的一些成员就会试图改变文化中的陈旧思想,置换腐朽的、失去活力的文化成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新的元素产生,从而改变原有的结构(元素之间的关系),进而改变系统的某些重要功能。因此,不论是被动改变还是主动变革,都会对文化的同一性提出挑战,使文化难以保持功能同一性。在一种文化演化的同时,该文化中的成员也在演化,文化成员的演化与文化的演化是相互作用的,这使得文化演化之路呈现一种不可逆的态势。
总之,“提修斯之船”提出的同一性问题要求生命文化学在研究中关注文化的本质问题,文化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问题,文化的连续与断裂问题,文化的继承的创新问题。
二、“纽拉特-奎因之船”及其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一)作为认识论比喻的“纽拉特-奎因之船”
奥地利哲学家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曾经提出一个被后人称为“纽拉特之船”的隐喻:在认识世界时,我们就像海员一样,如果船有漏洞或者有损坏的部件,只能在船中,也就是在浩瀚的大海中修补它,绝不可能一发现问题就立即回到船坞中拆卸船只,用最好的构件把它重新组装起来,或者干脆换一艘更坚固的船[6]。美国哲学家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对“纽拉特之船”这个隐喻进行了扩展,因此,后人把他们提出的隐喻称为“纽拉特-奎因之船”[7](P3)。
奎因借用“纽拉特之船”这个隐喻表达了他的意义整体论立场:首先,我们不能为我们语言中的各个词项或语句独立地指定意义,使整个世界的语言整体地具有意义,而是相反,我们所有的科学信念都处于一个“信念之网”(web of beliefs)中,它们构成一个互相连接的网络;网络中的单个语词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而是整个信念之网具有经验意义。用船喻来说,船里的每一个部件都有整只船作支撑,它的功能和位置是由整条船所赋予的,修理或者撤换一个部件并不会影响整条船的功能,无需因为一个部件的损坏而拆卸整条船或者干脆换另一条船。船里有些部件比另外一些更为重要。同样,信念之网中同样有一些最抽象却最确实的信念,比如数学和逻辑。
奎因之所以提出这种“意义的整体论”,是为了驳斥分子主义意义理论:每个语词和语句有其独立于信念之网的意义,语段的整体意义依赖于语词和语句,而不是相反。最近在学界大力倡导生命文化学的学者江文富在谈到生命哲学中的审美观点时也提出了类似的整体论的观点。他提出,现代社会分工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人们对艺术的鉴赏力,而为了修复此类审美能力,必须以从生命整体的视角来审视生命现象。他提出,“正是由于工具化、专业化、精确化、制度化及合理化,人们原本丰富多彩的生命被磨平了棱角,这就是现代性所面临的矛盾和困境。因此要拯救这种危机,我们必须要回到生命本身,试图去达到生命的整体和大全。”[8]
其次,船已经航行在海上,如果每有一个部件损害都要回到船坞重新组装,那么极有可能永远到达不了航行的彼岸;在认识活动中,我们不可能抛弃现在的方法,在某种更可靠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新的方法论体系——我们仅有的方法就是脚下这条船。正如纽拉特所言,“我们与公海上驾船的水手类似:必须修补船只,但是无法从零开始。当一块船板被取走,另一块新船板必须取而代之,而整条船可以用作支撑。”[9]这是一种反基础主义观点。
最后,对每一名船员来说,这是他们当下仅有的一条船。在认识论中,我们也仅有一张信念之网,此外没有选择的余地。不存在彻底另起灶炉从头再来的另外一个概念框架或者信念之网,也不存与另一套理论相对应的真理或事实。这是一种反相对主义的观点。奎因主张,“即使在作批判性反思时,我们也会一直持有并使用当下的某些信念,并且依靠所谓的科学方法不断改进它们。”[7](P22)信念之网是可以修正的,就像船体可以被修补一样,在我们不断演进的学说之内,可以进行认真的批判性反思,但不会再有另一条船让我们重新启航,不会有从另一个信念体系中重新衡量真理的机会。
(二)“纽拉特-奎因之船”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生命文化的演化历程可以类比为文化之船在文化的海洋里航行。在大海中航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有可能倾覆,有可能被撞击受伤,像提修斯之船一样,文化之船也会腐蚀、局部腐朽,需要更换材料,需要修复和置换损坏的构件。
提修斯之船的隐喻,帮助我们思考对文化系统中的概念进行修复的置换后,能否保持文化的同一性问题,但该隐喻并没有讨论文化之船中构件如何修复和置换的问题。由于纽拉特和奎因关注的不是文化的同一性问题,而是文化之船中构件如何修复和置换的问题,即修复和置换应该和能够采取何种方式的问题,因而“纽拉特-奎因之船”是一条认识论的船。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只能逐渐地替换我们的文化,而不能彻底地换一种全新的文化,如同在海中航行不能换一条新船。
文化之船一旦启航,就意味着它彻底失去了重新再来的机会。这个事实可能会让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人很无奈,因为他们必须忍受特定文化的种种缺憾和不如意在惊涛骇浪的文化海洋中航行。对于一个文化整体而言,难以回到起点,重新开启文化之旅,或者重新换一种文化,我们只能在某一种文化中一边生存、生活、生长,一边查漏补缺,在既定的文化基础上做一些修复和局部置换工作。文化之旅只能是一次充满风险的、有着显著的不确定性的历程。
奎因借用“纽拉特之船”表达的意义整体论对生命文化研究有着重要认识论意义,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怎样修复信念之网呢?渐进式修复还是激进式修复?在什么基础上修复和置换文化系统的构件呢?奎因认为信念之网是可修复的。“他(奎因)教导我们,‘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是由相互关联的信念和意义所构成的结构,是松散的和动态的……当关于世界的重大信念发生改变,概念的意义显然也会发生改变。”[7](Pxii)信念体系中的诸概念并非同等重要,而是有层次、有等级的。修复或置换核心概念比修复或置换非核心概念更重要也更困难,产生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概念修复和置换的次序、方式就是需要思考的认识论问题。
从原则上说,提修斯之船的修复可用同质的材料来修补,以保证同质性,即使不用同质的材料,也可在保持结构、功能不变的前提下来修复受损的船。然而,文化之船的修复,由于外部的或内部的原因往往需要用不同质的材料来修补,即吸收其他文化的概念、观念、方法来修复。事实上开放的文化大都采用过不同质的材料来修补自己的文化之船。这种异质替换是否会产生排斥反应和冲突?是否会导致词语的多义和歧义?是否会导致语言的误用和概念混淆呢?这些都是生命文化学要思考的问题。
文化之船的构件不断被替换就带来了语言的误解和误用的问题。人们在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不仅意义模糊和饱含争议,而且也包含了因不同用法而导致的各种矛盾。解构主义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认为,“词语误用”不仅是哲学和语言学上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其核心是凸现出被语言掩盖的他者的存在。诸如“人民”“女性”等总体化词汇都是词语误用的典型,它们被用作服务于特定的政治斗争,但实际上这些词汇并没有具体所指,至少作为全称不可能真正指向具体的个体。她认为,如果我们忽视这些词语的“词语误用”性质,忽视具体的他者的存在,那么解放的目的就不可能真正地完成,斗争的结果必然造成新的压制,甚至存在革命的果实被盗用的危险[10]。
“纽拉特-奎因之船”提醒我们,在文化研究中,要注意文化概念的复杂性、历史性和整体性。要批判性地反思文化概念及其内部结构,对文化概念进行切分时要有整体的视野,不能只见林木不见森林。正如当代中国著名学者谢地坤所主张的那样,在研究生命文化或生命哲学时,我们不得把生命当作孤立的现象,而是“……我们在生命哲学或生命文化研究中,不仅要关注生物学、医学方面的问题,也要关注文化的、宗教方面的问题,甚至还要关注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层面的问题。”[11]
奎因的意义整体论把人类文化装到一条船上,推衍出人类文化之船只能在永无归途的前行中渐进式地修复和置换船上的构件。与之相应,人类只有一个信念体系,人类不会有从另一个信念体系中重新衡量真理的机会。把奎因的意义整体论坚持到底,将使文化系统之间的比较成为空谈。实际上,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系统,不同文化系统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重大差异;它们之间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它们之间可以比较和融通,取长补短,共达彼岸。
三、“毛泽东之船”及其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一)作为方法论比喻的“毛泽东之船”
船是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也是生活和生存的工具和载体;把方法比喻为涉水、渡河、航海的船,是很自然的,也是很有启发性的。毛泽东对作为方法论比喻的船有过简洁的描述,他在1934年1月27日发表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里用船作了如下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2]
毛泽东借助类比,在方法问题和船的问题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从而把抽象的方法问题形象化,即把方法的生成和运用类比为船的制造和使用。在此基础上可以讨论方法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问题。显然,这是一种理解和认知问题解决方法的有效途径。
(二)“毛泽东之船”对生命文化学研究的意义
不同的水与不同的船相联系。从客体方面来看,船的选择要与水文、距离、气候、等因素联系起来思考。不同的水需要不同的船。从主体方面来看,船的选择要与船长、舵手、水手等因素联系起来思考。显然,在海上航行与在河(或江)上航行和湖上航行对船的要求是不同的,对行船的主客观条件的要求也是有明显区别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就明确指出:“其实,真正的航海家必须注意年、季节、天空、星辰、风云,以及一切与航海有关的事情,如果他要成为船只的真正当权者的话;并且,不管别人赞成不赞成,这样的人是必定会成为航海家的。”[13]
关于方法的船喻表明,方法要与所要解决的问题相适应。与解决问题的主体的能力水平相适应。当人们把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其解决之道显然有别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意义生成过程。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变异性。正如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说,“在过去,‘文化’指心灵的状态或习惯,或者说一些智性和道德活动,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生活方式。正如‘文化’的本来含义以及这些含义之间关系的演变一样,这一演变并非偶然,而是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意义。”[14]
解决动态过程问题的方法有别于解决静态结构问题的方法。“刻舟求剑”讽刺的正是用静止的眼光看待发展变化的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舟、水与剑的关系,用静态分析的方法解决动态过程问题的错误做法。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认为,使新思想得以生长和滋养的日常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僵化的,而是在不断地改变着自己,不断用科学的理想和融入日常生活的哲学思想丰富自己。”[15]
总之,“提修斯之船”“纽拉特-奎因之船”和“毛泽东之船”从不同层面为理解复杂的文化现象提供了启发性思路。生命文化学在面对生命文化这一特殊研究对象时,有必要借助上述比喻和其他比喻,对生命文化现象作出创造性理解,进而作出细致的分析和系统的综合,从而更加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生命文化的发展规律。
[1]Plato,C D C Reeve.Republic[M].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Inc.,2005.
[2][英]费恩.哲学:对最古老问题的最新解答[M].许世鹏,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7.
[3]L R Baker.Why Constitution is Not Identity[J].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7,94(12):599-621.
[4]袁建新,刘大早.提修斯之船:对物质构成的千古之谜的重新理解——从量子相关性与物质构成的拓扑结构化来看[J].科学经济社会,2007(4):100-103.
[5]董国安.生命文化学:可能的研究域、方法和价值[J].广东医学院学报,2013(6):641.
[6][奥]纽拉特.社会科学基础[M].杨富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43.
[7]W Van Orman Quine.Word and Object[M].Massachusetts:MIT Press,2013.
[8]江文富.西美尔生命哲学中审美救赎的理论来源[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3.
[9]O Neurath.Anti-Spenglerl:Dedicated to the young and the future they shape[A]//Marie Neurath,Cohen R S.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M].Dordrecht:Springer Netherlands,1973:199.
[10]汪民安.文化研究关键词[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29.
[11]谢地坤.尊重生命卫生济世:关于“生命哲学”的思考[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0.
[12]毛泽东选集(一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25.
[13][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5.
[14]R Williams.Culture and Society:1870-1950[M].New York:Doubleday&Company,Inc.,1960:16-17.
[15][英]英格利斯.文化[M].韩启群,张鲁宁,樊淑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42.
The Implications of Three Metaphors about Ships for the Studies of Bioculturology
CHEN You-tang1,ZHANG Zhang-ran2
(1.Research Institute of Life Culture,Guangdong Medical University,Dongguan,Guangdong 523808,China; 2.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China)
This paper in a comparative way discusses the meanings of the three metaphors about ships,namely,the Ship of Theseus,the Ship of Neurath-Quine and the Ship of Mao Zedong,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ies of bioculturology respectively.Ontologically,the metaphor about the Ship of Theseus demanded that bioculturolog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related to following aspects:cultural nature,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ultural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unctions,cultural continuation and rupture,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Epistemologically,the metaphor about the Ship of Neurath-Quine held that studies of bioculturology should focus on the complexity,historicity and wholeness of culture.Methodologically,the metaphor about the Ship of Mao Zedong required that the methods used by bioculturology should be suitable for the problems to tackle and the subjects'abilities to solve problems.
bioculturology;metaphor;the ship of Theseus;the ship of Neurath-Quine;the ship of Mao Zedong
B821
A
1672-934X(2015)05-0051-06
10.16573/j.cnki.1672-934x.2015.05.008
2015-08-15
陈幼堂(1973—),男,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生命哲学研究;
张掌然(1953—),男,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与心理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