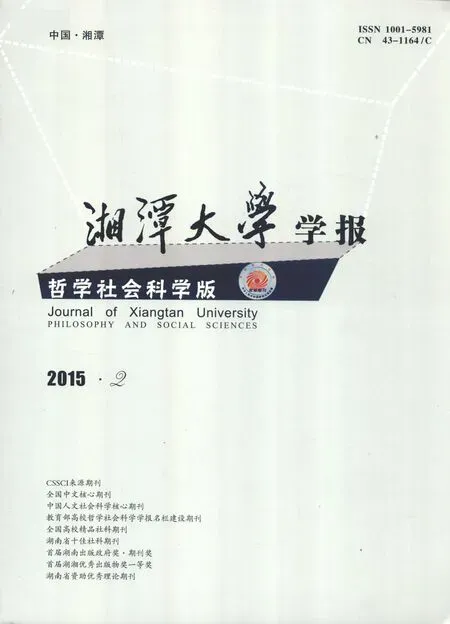象征的浪漫之维——冯至的诗学及其文体建构*
2015-02-22胡继华
胡继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跨文化研究院,北京 100024)
冯至(1905-1993)16岁作诗,少年出道,跻身身中国诗坛,曾被鲁迅称之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虽赞之过誉,但隐含于新文化运动主将言辞之下的那份拳拳之心、殷殷之望却路人皆知。冯至在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大,但同“五四”时代其他作家诗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是英美文学芳泽滋润下的淡淡花草,而是德语浪漫诗风浸润下的萧萧玉树。沿着浪漫诗风吹拂的道路,冯至高张哲学诗帆,开启象征诗学初航。航程开启之时,奥地利象征主义诗人里尔克与他不期而遇,生死纠结的哲思与浪漫象征的灵知就相伴他直至生命的终点。带着象征诗学的眼光,凝视德国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的浪漫化象征世界,冯至运用“类比”范畴建构了象征诗学。以象征主义观浪漫主义,浪漫诗学辐辏于象征。以浪漫之灵点化象征丛林,象征主义遂得心灵之唯美。40年代,战争,败落的时代及其人类普遍的生存境遇,让冯至诗兴二度神秘地爆发。深情凝视“灵魂山川”,洗耳静听心灵的韵律,冷眼观照远古忧患之人的生命节奏和精神流亡之路,冯至一口气写下了商籁诗27首,《山水》散文诗15篇,诗化教养小说《伍子胥》1部。践行象征主义诗学,冯至在诗体、文体、叙体等文体探索上对中国现代文学新传统的形成可谓居功甚伟。仅就其象征诗学建构而言,其浪漫与象征的互照互释,尤其彰显了象征诗学的浪漫之维。
(一)饰哲理以诗情——象征诗学初航
1925年,他与杨晦、陈翔鹤、陈炜谟一起创办“沉钟社”,奉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诗学主张。“沉钟”一名,得自德国象征主义作家豪普特曼的剧作《沉钟》,不过冯至及其同侪却比戏里铸钟人亨利更加坚执地抗拒日常生活和政治风潮的影响,捍卫诗学的自律性——将铸就的大钟沉入湖底,直到有朝一日在幽深的水中再次鸣响。鲁迅向来惜言如金,尤其不善嘉赏他人,可是对“沉钟社”却刮目相看,对冯至及其同侪的诗学视野、艺术风格、欧西渊源和历史局限性做出了深邃而准确的论断:
1924年中发祥于上海的浅草社,其实也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团体,他们的季刊,每一期都在表示着努力:向外,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要发现心灵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个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浅草季刊改为篇叶较少的《沉钟》周刊了,但锐气并不稍衰,第一期的眉端就引着吉辛(G.Gissing)的坚定的句子——
而且我要你们一齐都证实——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
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烈烈,然而悲凉的,即是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因营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acar Wilde),尼采(Fr.Nietzsche),波特莱尔(Ch.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沉自己的船”还要绝处逢生,此外的许多作品,就往往是“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却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虽是冯至的饰以诗情,莎子的托辞小草,还是不能掩饰的。凡这些,似乎多出于蜀中的作者,蜀中的受难之早,也即此可以想见了。
鲁迅意犹未尽,引用陈炜谟小说集《炉边》中的话语:“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们……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怯懦得连黑夜也要躲避呢?”冯至及其同侪作诗为文,也许完全是为了完成自我,慰藉灵魂,为茫然不可知的未来留下一些可以眷念与忆念的踪迹。不过,鲁迅笔锋一转,随后指出时代大限使然,“沉钟社”诗人作家无可奈何,行之不远,注定是明日花黄,昨日涛声:
自然,这仍是无可奈何的自慰的伤心之情,但在事实上,沉钟社却确是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扎根得最久的团体。它好像真要如吉辛的话,工作到死掉之一日;如“沉钟”的铸造者,死也得在水底用自己的脚敲出洪大的钟声。然而他们并不能做到,他们是活着的,时移世易,百事俱非;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一片茫茫白地,于是也只好在风尘澒洞中,悲哀孤寂地放下了他们的箜篌了。[1]242-243
深谙象征主义个中三味的鲁迅,不仅是冯至及其同侪的知音,而且更是他们的导师,超越于团队之上,又可谓旁观者清。一方面,鲁迅辨析他们的热烈悲凉的情感,揭橥他们掘发灵魂、摄取“世纪末果汁”的内外两向,赞美他们为艺术自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诗学精神。另一方面,鲁迅更觉察到,他们远离民众,游思于国族史诗的宏大叙事之外,将抒情的“小我”与史诗的“大我”区隔开来,就注定他们无奈于时移世易,百事俱非,无奈于听者的睡眠、槁死与流散,注定了他们将要面对茫茫大地而悲哀孤寂。不用说,这样的命运即是象征诗人的命运,这一点无分中外古今。象征诗人坚执守护自律的诗神寺庙,用心灵之眼凝视外部世界,用气韵生动的诗文再现心灵律动,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但观音自善,罂粟自恶,言者谆谆而听者邈邈。纯情、纯诗、纯爱,总是无人喝彩,诗人寂寞地放下箜篌。
“沉钟社”奉行“为艺术而艺术”的诗学精神,其诗歌实验以浪漫主义为情思,而以象征主义为诗魂。在这种氛围中,冯至开启了象征诗学的初航。
第一,冯至坚持与主流思潮无涉,而写作非政治的诗篇。
面对滚滚红尘、浑浑俗世,他用新诗体表现对现实的觉醒,挥洒对生命的哲思,忧郁委婉,音韵清新,境界隽永。冯至早期的两部诗集《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同名噪一时的郭沫若《女神》,可谓风格异类而相映成趣。郭沫若摹制德国狂飙突进诗风,而冯至摹制德国早期浪漫诗风。郭沫若的诗,情感汪洋恣肆,意象繁复缭乱,意境狂放如醉;冯至的诗,则处处表现出理性节制,含蓄不露锋芒,诗思冷静明澈,而意境倾向于“沉思的抒情哲理化”。冷静、沉思而非热狂、纵情,冯至少小出道,即有“诗国哲人”之称,难怪鲁迅对他呵护有加,关怀备至。因为,正是冯至之诗作,体现了鲁迅的诗学理想:“感情最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1]97
第二,冯至创作,与欧洲现代派达成了共识。在“五四”之后的诗人阵容中,冯至属于较早踏入象征诗国的诗人,而同“自由派”、“格律派”均分秋色。踏入象征诗国,即表明他同现代派心有灵犀。鲁迅说冯至及其同侪向外摄取了“世纪末的果汁”,也就暗示了这种同现代派的共识。冯至的名篇《蛇》就是“世纪末的果汁”喂养出来的象征诗之珍品。从英国画家比亚兹莱(Aubrey Vincent Beardsley,1872-1898)的一幅画作获得诗兴,他写出自己寂寞乡愁和凄美梦境:“我的寂寞是一条蛇,/静静地没有言语……它想那茂密的草原——/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它月影一般轻轻地/从你那儿轻轻走过;/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像一只绯红的花朵。”[2]1,77冯至自己曾解释说,18 世纪欧洲的维特热,19 世纪的世纪末情绪,虽然相隔一个世纪,但性质很不相同,但比亚兹莱的画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20年代风行一时,好像有一种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是一种超越时代和地域的隐性遥契,在此不妨理解为一种同现代派的共识。[2]5,198当然,表现在冯至早期诗作中,这种现代共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主义的倾向,那就是情理交融而至冷至热,将心灵的律动诉诸诗歌的音韵。
第三,冯至同德国浪漫派精神相通。荷尔德林、诺瓦利斯、莱瑙、海涅之类的薄命诗人令他难以释怀,蒙着浪漫色彩的森林、骑士、城堡让他梦系魂牵,而晚唐诗风、北宋词风同德国浪漫诗风涵濡他的诗心艺才,让他模拟异国诗词的主题、情调、语言结构以及格律节奏,创作抒情诗与叙事诗,缘情述事。
1927年,冯至在《沉钟》上发表论文,论说柏林浪漫主义代表人物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1776-1822),赞赏他在丑恶的现实后寻求美丽,在阴暗的人生中寻求美的灵魂,梦想光明的精神王国,浪漫的光华。接受勃兰兑斯对霍夫曼“离魂重影”(Doppelgängerei)的评价,冯至从这位浪漫作家身上读出了“自我分裂”,“人生冲突”,“人性二元”。冯至认为,分裂、冲突、二元,及其所引起的焦虑与渴望,乃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让灵魂燃烧起来,驱动感官超越感性世界进入彼岸的奇境。冯至最后得出结论说,在霍夫曼所生活的时代,对于丑恶与悲哀,人们避犹不及,但霍夫曼却反其道而行之,欲举一人之力去征服人生,深深走进人生的深处。“他在浪漫派的作家中是惟一的爱着生活的人,他不曾去追逐‘蓝花’(Eine Blaue Blume),也不曾去听取森林的寂寞(Waldeinsamkeit);在他的窗外是市场的喧哗,——他在真实的后面发现了伟大的神奇的阴影。”[2]7,268,277,280这种论述已经预示着冯至以象征主义诠释浪漫诗学的思路了。尤其值得强调,他笔下的浪漫派作家霍夫曼却颇有几分象征派作家波德莱尔的气质,在他们的人生与诗艺之中,冯至发现了一种唯美的灵知:在丑恶中寻求美丽,在阴暗生活中寻求美的灵魂,在污秽不堪的俗世瞩望光明浪漫的诗国,在紊乱迷茫的世界上营造和谐中道的精神秩序。而这,确实是浪漫精神,却又不只是浪漫精神,而是寄托于象征主义诗情雅韵之中的灵知精神。
《昨日之歌》中包含一组叙事诗,取材于本国的民间故事与古代传说,但他以西方叙事谣曲的形式与风格去再现古代意蕴。古事蕴今情,而异域诗体道出民族精神。这种诗学实验同样发生在浪漫象征化、象征浪漫化的涵濡汇通中。新诗风气得以振荡,而象征建构从此开端。
第四,冯至诗歌生涯的开端,便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不期而遇。正是这位用德语和法语写作的诗人,将德国浪漫诗风导入象征轨道,以商籁体传达渺远幽深的神秘主义,同时复兴了欧洲古老的哀歌,延续着荷尔德林、诺瓦利斯的新神话象征体系建构的大业。1926年,冯至读到里尔克的《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心灵为之一震:“在我那时是一个意外的、奇异的得获。色彩的绚丽,音调的和谐,从头至尾被一种幽郁而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像一阵深山中的骤雨,又像一片秋夜里的铁马风声。”[2]4,83色彩、音调和幽郁而神秘的情调,便是象征主义诗风的特有韵致。将这种象征主义的韵致注入到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诗作与诗学中,冯至在理论上完成了浪漫主义诗学的象征重构。在里尔克《奥尔菲斯十四行诗》的激发下,置身于战时40年代的冯至突然兴感,带着这种象征主义的韵致为中国商籁体诗体奠基,而在中国现代诗史上犹存硕果,诗情雅韵泽被后世,流兴不息。同样是怀着这种象征主义的韵致,冯至用象征的书写方式重构两千年前的中国传说,写出忧患中人伍子胥的复仇与流亡,及其心灵的抗争与慰藉的史诗。由此可知,冯至的诗歌实验,诗学建构,诗体创化,以及文体探索,举凡一切诗学行为,都无不笼罩在象征主义的韵致之中。
(二)浪漫诗学的象征建构——冯至论诺瓦利斯
1930年至1935年,冯至负笈欧西,留学德国。在此期间,他心中的诗神似乎沉默了。不过,在诗兴冷寂的时刻,他距离歌德和里尔克更近了。而正是里尔克净化了瀑布一般的浪漫激情。因为里尔克认为,诗不只是激情,而是“经验”,而要抒写经验则必须静观默察,学会观看——观看城市,观看人情物象,观看植物动物,感受小鸟飞翔,体会花朵在早晨开放的姿态,同时还要“回忆许多爱情的夜晚”。冯至先生逝世后20年,他的长女冯姚平女士在2013年初夏的一次纪念研讨会上,这样描述里尔克的影响:
父亲初到德国,里尔克的作品使他欣喜若狂,认为终于找到自己寻求已久的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他马上认真地翻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完一封,寄出一封,要杨晦在国内发表,介绍给国内的青年。他觉得这些言论对他,是对症下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缺陷,我虚心向他学习”。他认真研读里尔克著作,选定《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作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论文提纲都写好了,却因为导师阿莱文教授是犹太人被撤职而作罢。但纵观他的一生,里尔克对他在做人和作文两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不难看出,他的风格变了。他观察、体验,懂得了寂寞同忍耐,严肃认真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他从婉约的抒情变为富于哲理的沉思。[3](冯姚平,2013)
阴差阳错,因为欧洲反犹政治倾向殃及学界,冯至不得不割舍己爱,放弃博士论文选题。但带着里尔克的精神而走进诺瓦利斯的世界,便对浪漫诗学进行了一度象征主义的重构。浪漫诗风艺韵因象征主义而从朦胧变得清晰,而象征主义的灵知灵见亦因浪漫诗学而显得亲切丰盈。
诺瓦利斯(Novalis,Friedrich von Hardenberg,1772-1801)是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在其诗作中美化夜晚与死亡,把梦当做现实,把生活当做梦境。其诗体教化小说《奥夫特丁根》将“世界浪漫化”的纲领具体化,而在一个颠倒紊乱、功业居首的时代用词语建构一个牧歌式的天堂,预示已经云烟消散的黄金时代在欧洲再度复兴。诺瓦利斯将“自然”看成心灵的“另一体”,把茫昧的神话时代写进一目了然的当代世界,而把当代现实升华到绚丽纯净的童话中。诺瓦利斯笔下的少年梦见一朵蓝花,而这朵蓝花便是早期浪漫主义的图腾。蓝花芳香馨人,纯洁高雅,柔情若梦,便是浪漫主义慕悦及其绝对悲情的象征。少年穿越沧桑,追寻梦中蓝花,因为它是真、爱、美、信以及诗的象征。在诺瓦利斯及其缀梦少年的眼里,苍天厚土,草木虫鱼,日月山川,以及风俗人情,一切都是象征符号。整个宇宙就是神秘幽深、高飘玄远的灵知之象征。[2]7,334
冯至的博士论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诺瓦利斯的文体原则》,扣紧“类比”修辞,聚焦文体原则,探索“主体与客体、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精神与自然在诺瓦利斯作品中是如何渗透和交流的,以及他的诗歌风格是如何由此产生的”。[2]7,5首先应当注意,冯至的论题是“类比”,是“文体原则”,早期浪漫主义的感性神话、浪漫宗教以及民族主义意识被淡化了。而这一论述理路恰恰就是里尔克象征主义明示给他的。里尔克象征主义诗学之论旨,恰恰在于解放语言符号的能指潜能,让诗人回避情感,而创作一些非个人的超然诗篇。里尔克强调,象征主义倾向表现出“纯粹修辞手段”的诗学特征,“诗中的象征物之特殊结构无需任何外在话语即可被当做一种修辞手段”。因而,象征主义不向往浪漫主义的繁复与艰深,而尤为喜爱简洁与澄明。里尔克的那些貌似简单实则幽深的诗篇,真正代表了象征主义的成就,所以里尔克、特拉克尔和保罗·策兰一起,振荡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诗风。[4]48-49冯至对诺瓦利斯诗学的象征主义重构,也尤其关注童话原则、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在类比修辞、文体原则之中的体现。
(1)童话原则,即诗化世界建立童话世界。诺瓦利斯谴责歌德失落童心,撰写出《麦斯特》那样的理智作品,而在诗的活体上生长出“毒瘤”。诺瓦利斯深信,小说应该逐渐过渡到童话。因而不足为怪,《奥夫特丁根》的高潮便是克林索尔童话,完全超越了世俗红尘而进入冰清玉洁的象征世界。就童话的诗学与文体价值而言,冯至看得非常清楚:“梦和童话是联想和使人所崇拜的偶然的产物。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存在,在这里想象可以任意驰骋,使一切都生动活跃起来。童话既是真实世界的镜子,又是它的原朴状态。”[2]7,21童话乃是浪漫主义最为适宜的散文形式,它让一切充满生命,使整个自然以神奇的方式与整体的精神世界融合起来。
(2)语言形式,即比喻修辞。首先,冯至看出,浪漫主义的比喻不是语言的美化与装饰,也不像巴洛克式的作为修辞工具而徒有其表的比喻,而是更类似于中世纪神秘主义者,将“比喻”看作是“自然与精神结婚而生育的女儿”。其次,冯至认同诺瓦利斯的泛化语言观,认为不仅人言说,宇宙也言说,语言是一次诗意的发现,语言符号先验地产生于人的天性。最后,冯至追溯比喻的渊源,从意大利思想家维柯到德国狂飙突进诗人赫尔德,德国哲学家哈曼,浪漫主义的精神领袖施莱格尔兄弟,论述比喻、象形文字与浪漫主义的语言之间的血肉关联。语言事实上是精神的召唤与精神的显现,一个由符号和声音构成的象征世界,而语言的力量就深深潜伏在比喻形式之中。[2]7,26
(3)思维方式,即类比思维。追根溯源,冯至将类比思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其公式是A和B的关系正如C和D的关系。类比是神秘思想家的工具,他们借此实现内心与外在的综合,外在的东西内心化,使缥缈的精神具象化。类比也是科学家把握世界奥秘的工具,他们借此把自然世界视为一个巨大的生命有机体,同一、近亲而且彼此相依。诺瓦利斯更是发挥类比思维,将人与人之关系推展到整个宇宙:“我的爱人是宇宙的缩写,宇宙是我的爱人的延伸。”浪漫诗人因此而成为不折不扣的象征诗人,因为他相信“人是宇宙的类比性之源”。[2]7,30
冯至最后得出结论说:“自然的生命化、语言的比喻以及类比性的形成和滋养了诺瓦利斯的独特风格,而以上三个方面又深植于魔幻唯心主义,魔幻唯心主义则产生于神秘主义的思维形式。”[2]7,30在论文的主体部分,冯至将“世界是精神的一种包罗万象的比喻,是精神的一种象征的形象”这一原理贯穿于分析诺瓦利斯风格的始终,从光、颜色、火、水、海、河、泉、天空、星星、太阳、月亮、空气、风、云、夜、朦胧、植物、动物、矿物、物理、化学等方面,重构出诺瓦利斯的象征体系,从而创建出一个万象互相关联、万物同时存在的有情宇宙。尤其意味深长的是,冯至将浪漫诗人诺瓦利斯称为“游戏诗人”,将浪漫世界营造为“游戏式的严肃”,从而看透了宇宙象征体系之中那些幽暗玄远的意义。[2]7,138-139而这种对浪漫诗学的象征主义重构,同波德莱尔的普遍契合论、马拉美的情感炼金术、韩波的语词炼金术、瓦雷里的“纯诗”境界遥相呼应,并同艾略特规避情感寻求“客观对应物”的诗学主张有了对话的可能。
(三)文体建构——象征诗学建构的完成
40年代的战火与硝烟中,缪斯女神再度降临于冯至的灵台,诗人触物兴感,联类无穷,诗情一发而诗坛精彩迭出。以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为媒介,冯至完成了象征诗学的建构,为中国文学新传统添加了悠扬的韵味与迷人的风采。
1941年早春或冬天,冯至漫步昆明乡间小道,诗神遽然降临,从此世间便有了冯氏的商籁体,诗史之内便有了不朽的《十四行诗集》27首。朱自清说这部诗集“建立了中国十四行诗的基础”,[5]238陈思和说这部诗集乃是中国现代诗“探索世界性因素的典范之作”。[6]156诞生于抗战伟大的史诗时代,《十四行诗集》可谓中国诗人面对普遍的世界难题以及人类生存之共同困境而同世界进行对话交流的结晶。而里尔克可谓冯至对话的首选伙伴,因为冯至认定,里尔克是一个能够驱散寂寞荒凉、滋润人类于世衰道微的伟大的优美的灵魂,甚至同现代中国的命运隐秘相连。冯至于昆明乡间清贫节俭的环境下作《十四行诗集》,恰如里尔克客居亚得里亚海滨的古堡创作《奥尔菲斯十四行诗》。在象征主义诗人幽美的灵知之光的烛照下,冯至将浪漫悲情化入严密的意大利商籁体格律之中,深邃意蕴与亮丽格律凑泊无间,但依然延续着至冷至热、以理节情的象征诗风,对生命过程、灵魂蜕变、宇宙演化、历史兴衰进行凝视默察,展开深邃反思。《十四行诗集》交织着对生死的沉思,暗示人情与天道相对,而显得脆弱无常,惟有通过诗的创构,生命才显得璀璨无比,亮丽无比,珍贵无比。诗集之中第十三首诗献给了歌德,不过诗人一如既往地以象征主义灵知之眼去观照古典主义诗人,平凡市民与一代雄主相对茫然,平静的岁月与历史的沧桑映照无碍,沉重的病与新的健康互相转化,绝望的爱与新的营养彼此依存。诗人用飞蛾投火喻说生死悖论,最后将万物之意义归结为“死与变”。诗集的压轴之章,乃是象征诗学的诗化表达:
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
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
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
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
……[2]2,242
秋风里飘扬的风旗,泛滥无形的水注入椭圆的瓶中。旗之于风,瓶之于水,恰恰就是媒介之于信息,诗体之于诗情,有限之于无限,有形有迹之物之于无形无迹而且不可把握的事体。而这正是浪漫主义诗人的类比思维,以及象征主义诗人的普遍契合。诗人之使命,就在于忍耐、劳作、艰辛,将风与旗、水与瓶融合无间,将无形的鸿蒙转化为有形的雁迹。
1942年到1943年,冯至重拾16年前初触里尔克时的坠愿,将两千年前的忧患中人的传奇写入当代现实之中,塑造出退去神秘外衣的现代“奥德赛”。《伍子胥》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化教养小说”,诗人用象征主义的观照灵魂的现象学方法,呈现流亡、复仇的主人公的灵魂之旅,而不是描写事件,或者执着于戏剧情节。叙述的节奏随着心灵的律动而展开,最后与自然合一,融入乐境,蜕变而且升华。因而,作为诗化教养小说,《伍子胥》传承的不是浪漫主义的诗风,而是象征主义的灵韵,与其说摹仿了诺瓦利斯的《奥夫特丁根》,不如说神似里尔克的《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伍子胥》与里尔克诗学精神的融通之处,还在于“颠覆神话诗”。“支配里尔克的是神话意识中的‘自我忘却’,里尔克借助他高度风格化的艺术,成功地在现在没有神话的时代,将人类心灵的经验世界提升到神话——诗的层次。”[7]569伽达默尔如此概括里尔克《奥尔菲十四行诗》的“颠覆神话”程序。冯至褪去了伍子胥意象的浪漫衣裳,让他“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通过神话人物的当代化,而“反映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2]3,427、428在此,冯至建构的诗化教养小说,本质上是自我生命塑造的叙事,迎接神圣灵知的象征书写。昭关夜色,江上黄昏,丽水阳光,渔歌悠扬,涴女风姿,一切风俗人情景物情思无不是个体灵魂与宇宙精神合一的象征,象征符号在流动,而汇入渺远的乐境。“江上”一节,尽显象征主义诗学的音乐境界。船夫唱道:“日月昭昭乎侵已弛,与子期乎芦之漪。”伍子胥不理解渔夫的歌词到底含有什么深的意义,而只是逡巡在芦苇旁。而此时此刻,西沉的太阳把芦花染成金色,半圆的月亮也显露在天空,映入江心,是江里边永久捉不到的一块宝石。子胥正在迷惑不解身在何境时,渔夫的歌声又起了:
日已夕兮予心忧悲,
月已驰兮何不渡为?[2]3,405
在渔夫神秘的歌声之召唤下,伍子胥上了船,一路观照清淡云水,而把思绪放逐到了远方,将孤独融入乐境,以至于生命与宇宙同流,个体与永恒同在。
如果说,《十四行诗集》是运用西方象征诗学原理进行诗歌实验的典范之作,是对西方诗歌格律的成功移植,那么,《伍子胥》则是将神话当代化展开叙事探索的开创之作,是用中国诗学精神对西方象征主义的成功涵化。无论是移植还是涵化,冯至的诗体探索与文体建构都是在全球化问题意识的引领下,并在文学变革的语境下完成的,因而他的象征诗学建构一样传承着中国古典诗学的流兴余韵,同时负载着世界文化要素,具有相当的普世意味。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冯至对象征主义渐生厌倦,一种超越象征的愿望自然而然地萌生。在一组诗学断章之中,他指责中国新诗不仅不成熟,而且还陷入摹仿西方诗风的莫焉下流,成为“mannerism”(仿制主义)的牺牲:“追溯病源,一部分由于摹仿西洋象征派的诗的毛病,一部分由于依恋词里边狭窄的境界。”[2]5,295时移俗易,大化流演,往后冯至就再也没有走出象征主义的“mannerism”,拿不出《十四行诗集》和《伍子胥》那般的力作,而作为诗学建构的《论歌德》只以未竟之章示人,以残缺之篇传世,他的诗歌实验与诗学建构在1948年前就止步了。
[1]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冯至.冯至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冯姚平.纪念冯至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在歌德学会年会上的发言[J].中国歌德学会通讯,2013(1).
[4]Paul de Man,Allegory of Reading[M].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5]朱自清.文艺常谈[M].北京:中华书局,2012.
[6]陈思和.中国文学中的世界性因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7]伽达默尔.神话诗的颠覆[M]//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