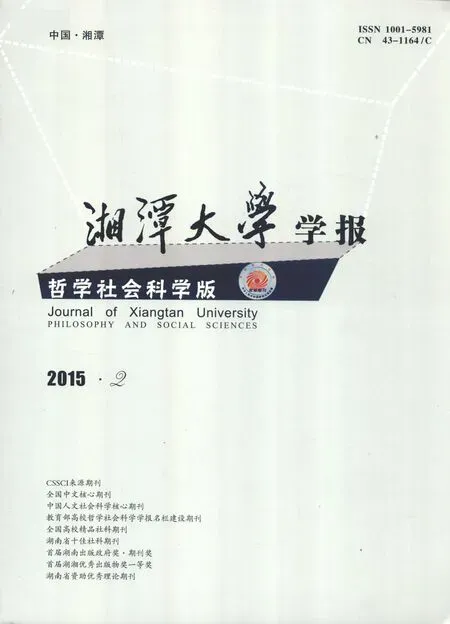论古代灾害诗歌的立意构思之法*
2015-02-22张静
张 静
(防灾科技学院 人文社科系,北京 101601)
“天火曰灾”(《左传·宣公十九年》),灾害是自然造成的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人类在灾害面前心灵充满震撼,情感深刻纠结,这是一类攸关生死存亡的遭遇与记忆,必然会进入到文学的殿堂进行书写描摹,中国古代有大量的灾害诗歌作品,就是明证。对于灾害诗这种题材,古人是如何构思立意呢?其实,灾害诗歌的构思是有章可循的,主要包括直呈伤痛与苦难、凸显伤痛的美学价值、注入悲悯情怀与运用卒章显志等几种基本手法。
一、直呈伤痛与苦难
灾害的最大特点是带来痛苦与创伤。呈现伤痛与苦难,便成为这类诗歌在构思立意方面的重心所在。
例如陶渊明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云:“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1]976即使是淡泊悠然的诗人,也将在旱灾、虫灾、风灾与雨灾折磨下的痛苦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出来。杜甫诗中有近70首灾害诗,真实细致地记录了天灾之下人们的苦况,所以这些灾害描写,也是他“诗史”创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晚唐皮日休《三羞诗》其三全篇的主要内容就是直叙蝗灾、旱灾之下的苦难本身:“天子丙戌年,淮右民多饥。就中颍之汭,转徙何累累。……一金易芦卜,一缣换凫茈。荒村墓鸟树,空屋野花篱。儿童啮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傍,枕土皆离离。”[3]7016史上诸多的灾害诗歌尽现当年灾难的苦况,在没有摄像机、照相机的古代社会里,这些文学图景具有丰富珍贵的纪实价值。
《全宋诗》中有关灾害的诗作“据我们初步统计有六千余首”[4],这些灾害诗歌的突出写作手法就是直呈伤痛。北宋庆历五年(1045)扬州暴雪,韩琦《广陵大雪》云:“罾鱼江叟冰透蓑,卖炭野翁泥没辐。闾阎细民诚可哀,三市不喧游手束。牛衣破解突无烟,饿犬声微饥子哭。”[5]3966苏舜饮《城南感怀呈永叔》主要篇幅都是陈述水灾、旱灾与雪灾轮番肆虐下的惨状:“去年水后旱,田亩不及犁。冬温晚得雪,宿麦生者稀。前去固无望,即日已苦饥。老稚满田野,斫掘寻凫茈。此物近亦尽,卷耳共所资。昔云能驱风,充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厉,肠胃坐疮痍。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5]3900……古代灾害诗歌擅于运用各种语言手段来表现灾荒频仍、哀鸿遍野的人间惨剧,这就使得生动的文学书写较之简单的正史记载更为震撼人心。
对于灾害,人们相对应地拥有厌恶、恐惧等强烈感情,这些不适的情感在文学创作中能够得以祭奠与舒解,所以作家倾向于在灾害诗歌中的直呈伤痛,这其中既有肉体的残害之痛,也有惶恐与绝望等情感伤痛。北宋淳化二年(992)关中大旱,王禹偁《感流亡》云:“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年关辅旱,逐熟人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5]660再如王炎《太平道中遇流民》:“丁男负荷力已疲,弱妻稚子颜色悲。亲戚坟墓谁忍弃,嗟尔岂愿为流移。春蚕成茧谷成穗,输入豪家无孑遗。丰年凛凛不自保,凶年菜色将何如。但忧衔恨委沟壑,岂暇怀土安室庐。故乡既已不可居,他乡为客将谁依。”[5]29694诗中充满了心理上的恐慌与绝望,是用镜头画面无法记录的,这也恰恰体现了文学的价值所在。正如左春和所言:“在灾难中必须看到伤痛,必须把伤痛作为一种价值进行严肃的叩问和追寻才能接近生命的密码。在伤痛中又必须抚摸到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创伤,才能用文字的形式记录这一切,否则,真正的痛苦会像泥石流一样被宏大的主题所淹没。”[7]
二、凸显伤痛的美学价值
充满血泪的文字也具有审美的价值,梁启超云:“诗是歌的笑的好呀,还是哭的叫的好?换一句话说:诗的任务在赞美自然之美呀,抑或在呼诉人生之苦?……依我所见:人生目的不是单调的,美也不是单调的。为爱美而爱美,也可以说为的是人生目的;……诉人生苦痛,写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说是美。”[8]12古代灾害诗歌中,会极力凸显伤痛的美学价值。
首先,古代灾害诗歌中的灾难描写会强烈唤醒读者的人生体验与情感共鸣。如北宋陈襄《通判国博命赋假山》云:“县官哀怜发赈救,一饭才得一盂尔。出门未暇充喉咽,已有数十填沟水。”[5]5071对饥饿的紧张不安,早已沉淀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灾害诗此际又通过文学语言,复活了人们心中千百年来的灾荒集体记忆,从而读者会产生与作者类似的情感激荡,审美活动便由此发生。
朱光潜曾说:“它(悲剧)所表现的情节一般都是可恐怖的,而人们在可恐怖的事物面前往往变得严肃而深沉。”[9]31灾难诗歌的主要篇幅都是在直呈伤痛,这就在立意与构思上体现出悲剧的美学特征。直呈灾害本身,首先有利于人们对命运、自然、政治与民生等进行严肃的叩问与深沉的思考。而且,作者全面客观严肃地直呈伤痛,也是帮助我们战胜苦难,获得坚强,正如钱钢在《唐山大地震》中所云:“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10]84
另外,灾难诗歌中的苦难最触目惊心的还是对伦理危机的暴露。人类的求生本能在灾害的残酷压力之下,会复活残暴、野蛮的动物性,发生卖儿鬻女、偷盗哄抢,甚至人食人的惨剧。人类几千年来苦心经营的社会规范、法律道德以及伦理观念,都会变得不堪一击。如皮日休《三羞诗》其三云:“夫妇相顾亡,弃却抱中儿。”[3]7016陈襄《通判国博命赋假山》:“鬻妻弃子人不售,价例不复论羊豕。白日市井闻号叫,夜堆廊庑如虫豸。”[5]5071父母天伦在天灾面前开始变得冷漠无比,人命也不如牲畜。清人陈沆又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地狱图:“汝南人瘦万狗肥,前有饿者狗后随,忽然堕落沟中泥,狗来食人啮人衣。顷刻血肉无留遗,残魂化作风与灰。狗饱狗去摇尾嬉,余者尚充鸦雀饥。”[11]8786灾害之后的伦理危机,真实揭示了危难之中的人性本质,值得我们作深刻的反思。“灾难引发的伦理危机恰恰是灾难文学写作的最佳切入点,人性的光辉与阴暗都可以得到集中的展现,可以发掘生命的价值和人性的深度。”[12]“灾害中展示的种种在正常情形下无法表现的人性深度和社会问题,构成民族秘史的一部分,折射着民族的内涵。”[13]以至于灾害诗歌中伦理危机的暴露,又具有人类学与民族文化史的研究价值。所以,凸显伤痛的美学价值,正是灾害诗的立意关键所在。
三、注入悲悯情怀
在灾害诗歌中仅呈现苦难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投入悲悯情怀。这就涉及到灾害诗歌的写作动机。极少诗人写灾害是为了展示灾难壮景或者炫耀诗技,更多是“目击异灾,迫于其所不忍,而饰之以文藻。当人心肃然震动之时,为之发其哀矜痛苦,而不忘天之降罚,且闵死者之无辜;而吁嗟噫歆,散其冤抑之气,使人无逢其灾害,是《小雅》之旨也,君子故有取焉。”[14]469例如,面对贞元初(785)的“螟蝗蔽野,草木无遗”,白居易作有《捕蝗》诗。陈寅恪分析云:“夫兵乱岁饥,乃贞元当时人民最怵目惊心之事。乐天于此,既馀悸尚存,故追述时,下笔犹有隐痛。”[15]188此“隐痛”,正是悲悯情怀,即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同情之感。诗人们对苦难的人们,不轻视不蔑视,而是充满慈悲与关怀。
在古代的大量灾害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大地的失陷、建筑的损毁、生命的消逝等,诗人伤心倍切且极富悲悯,表现出文化传统中仁民爱物的怀抱、厚生好德的情怀。公元前132年春,黄河在河南濮阳的瓠子口溃决,洪水“东南注钜野,通于淮泗”,汉武帝亲临现场治水,并作《瓠子歌》二章。洪灾的紧急、人畜的伤害、救灾措施的实施,在诗中都有艺术化的记录,其中更流露出忧虑悲悯、痛恤爱民的帝王情怀:“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1]94诗人们大部分都是脱离农田的士人,但在灾害面前,却和受灾者感同身受,充满哀叹与怜悯。晚唐皮日休《三羞诗》其三诗序中说“丙戌岁,淮右蝗旱……见颍民转徙者,盈途塞陌,至有父舍其子,夫捐其妻,行哭立丐,朝去夕死”,于是“呜呼!天地诚不仁耶?皮子之山居,椸有袭,鍑有炊,晏眠而夕饱,朝乐而暮娱,何能于颍川民而独享是?为将天地遗之耶?因羞不自容,作诗以唁之!”[3]7016南宋知县董嗣杲《甲戌武康大水净林寺山门殿屋悉皆倒敝》云:“就食难下咽,酸恨彻心膂。”[5]42674
正如约翰·多恩的诗中写道:“没有人是与世隔绝的孤岛,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都让我受损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因此,别去打听钟声为谁鸣响,它为你鸣响。”[16]142在灾害诗歌中,随处可见这样哀怜不已的诗句,如张耒《粜官粟有感》:“哀哉天地间,生民常苦辛。”[5]13326真德秀《浦城劝粜》:“我闻父老言,痛切贯心肺。”[5]34843李琪《赈荒到天台有作二首》:“我亦田夫偶得官,深知茅屋有饥寒。纷然遮道呻吟状,一作同胞疾痛观。”[5]33330而且,连草木的折毁、牛马的困厄、鸟虫的失所,都令灾害诗歌的作者心有不忍。杜甫有《柟树为风雨所拔叹》,面对一棵树在风雨之中连根拔起,悲悯情怀何等真切。王禹偁有《霪雨中偶书所见》,对微小蚯蚓活生生的逝去也充满悲悯。
虽然直呈伤痛是灾害诗歌写作的最大篇幅所在,但悲悯情怀的注入却是灾害诗歌最有情感力量的体现。在严酷灾害面前,人与人之间不再冷漠麻木,共同面对废墟与创伤,沟通那些从前隔膜的情感,守护内心人性的光辉,用悲悯情怀驱散灾难的残酷阴霾,这一写法也是古代灾害诗歌中最扣人心弦的所在。古代灾害诗这种写作向度,也成为当代灾害文学写作的重要法则,王晖《中国式灾难写作的精神向度——以当代中国地震题材报告文学为例》中就曾指出中国式灾难写作的精神向度应当表现出的第一点就是:“要表现出人类的普泛价值观,即慈悲、怜悯、良知、博爱、惜生(生命至上)等。”[17]6
四、运用卒章显志法
通观古代灾害诗歌,一般会在诗歌的结尾,用一两句来点明主旨,进行议论与抒情,表露胸怀与志向,传统的“卒章显志”法获得了广泛的运用。
例如杜甫的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之后,写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3]2310文天祥《五月十七夜大雨歌》在详尽描述“大雨复没床”的困境之后,卒章写道:“但愿天下人,家家足稻粱。我命浑小事,我死庸何伤。”[5]43054古代灾害诗歌描写伤痛的目的不是为了渲染灾难,骇人听闻,而是通过灾害叙述之后来议论抒情。“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18]157诗人在写作灾害诗歌时,最终目的都希望能够引起一定的社会反思。
大江健三郎在回答“面对巨大灾害,文学何为”这个问题时,认为文学“需要告诉人们如何从巨大的悲惨中恢复过来以及如何重建遭到破坏的文化”。[19]面对人类生存发展中必须要承担的且无止境的苦难,灾害诗歌的最终任务是帮助我承担苦难,并超越苦难。而古代灾害诗歌的卒章显志,也就是试图实现这一担当与超越。这就使得灾害诗歌在描写与抒情功能之外,又具有了认识功能与教化功能。
灾害诗歌最后所显之志,有暴露社会矛盾与政治弊病,有对当权者的讽刺与劝诫,有作为封建官吏的自疚与惭愧,也有对社会底层的深切关怀,还有思考生与死的辩证关系,思考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等等,其中的情感都是真诚而充沛的。例如,高适《东平路中遇大水》开篇先直呈伤痛:“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最后卒章显志:“我心胡郁陶,征旅亦悲愁。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3]2214白居易《贺雨》开篇先言:“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最后还是写道:“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3]4654……这种写法和《左传》中的“君子曰”,汉赋中的“乱曰”、《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异曲而同工。而且,在古代灾害诗歌的卒章显志中,也涉及到了一些新的现代精神向度,如公益意识、公民意识、减灾防灾意识、科学救援意识、生态意识、契约意识等。
古代大量的灾害诗歌用艺术化的手法展示了人类在灾害面前的苦难与心灵创伤,虽然还不具备科学的解释与应对灾害的有效途径,但却以诗性的描述启发人们思考人生与命运的无常与磨难,又用悲悯的情怀彰显了人文关怀。最后的卒章显志,使得古代的灾害诗歌又深富哲思性。这些立意构思之法,将对当代灾害文学的写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同时,它们也是一声声生态警示钟,提醒当代人类努力保护与建设生态文明。
[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J].杜甫研究学刊,2013(1).
[3]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王宇飞.宋诗与宋代灾害探研[D].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
[5]全宋诗[M].北京:中华书局,1991.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范藻.“道是无情却有情”的美学还原——从姜明的《万物生长》看灾难文学的价值选择[J].中华文化论坛,2011(5).
[8]梁启超.情圣杜甫[M]//中华书局,编.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一辑)[C].北京:中华书局,1962.
[9]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10]钱钢.唐山大地震[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
[11]钱仲联.清诗纪事[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12]向宝云.灾难文学的审美维度与美学意蕴[J].社会科学研究,2011(2).
[13]尹奇岭.评张堂会著《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2).
[14]汪中.新编汪中集[M].扬州:广陵书社,2005.
[15]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北京:三联书店,2001.
[16]约翰·多恩.丧钟为谁而鸣:生死边缘的沉思录[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17]王晖.中国式灾难写作的精神向度——以当代中国地震题材报告文学为例[M]//“抗震文艺与中国精神”研讨会论文集.2009.
[18]帕斯卡尔.思想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9]大江健三郎.面对巨大灾害,文学何为?[N].文学报,2008-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