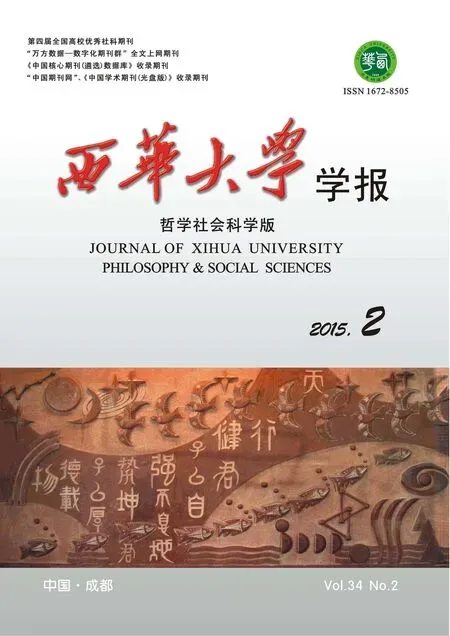《将军》的叙事结构与芥川龙之介的反侵略意识
2015-02-20张思齐
张思齐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在日本有两项文学大奖,它们均设立于1935年。一是直木三十五奖,简称直木奖,为纪念大众小说家直木三十五(1891—1934)而设立。直木奖是日本大众文学的最高奖,颁赠给无名作家或通俗文学的新秀。一是芥川龙之介奖,简称芥川奖,为纪念日本文学一流大家芥川龙之介(1892—1927)而设立。芥川奖不仅是日本纯文学奖的最高奖,而且还是整个日本文学最权威的奖项。换言之,日本的芥川奖,相当于中国的茅盾文学奖,它标志着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极其令人欣羡。由此可知,芥川龙之介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
芥川龙之介能够娴熟地运用近二十种文体进行创作,不过他最擅长的还是短篇小说、小品、随笔和游记。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其数量比中国作家鲁迅大得多,大约与普列姆昌德(Premchand,1880—1936)相仿佛。普列姆昌德既是采用印度的国语印地语来进行创作的小说家,被誉为印度的鲁迅;又是采用巴基斯坦的国语乌尔都语来进行创作的小说家,因而被誉为巴基斯坦文学之父。小品、随笔和游记这三类文学样式都可以统归为散文。芥川龙之介的诗歌,其创作量虽然不大,但是质量上乘。芥川龙之介的评论,其中一部分理论性较强,可以归入日本现代文论的大范畴。对芥川龙之介的战争小说进行研究,无疑对于我们认识日本的战争小说具有启迪意义。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作家,他具有浓郁的反侵略意识。芥川龙之介曾经在中国做过广泛的游历,他熟悉中国,对中国有深厚的感情,也直言不讳地指陈旧中国的种种社会弊端和丑恶现象。可以说,芥川龙之介是一位真正热爱中国的日本作家。
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将军》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反侵略意识。为了深刻地认识芥川龙之介的军人观、军队观、战争观和反侵略意识,我们有必要解剖这一短篇小说。芥川龙之介的《将军》具有特殊的叙事结构,是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大约合中文两万字。《将军》是这篇小说的总标题,其下包含《白襷队》、《间谍》、《阵地上的演出》和《父与子》一共四篇小说。换句话说,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将军》是一个故事组。这四篇小说均可以单独成篇,因为每一篇均首尾完具,具有时间、地点、场景、人物、情节等小说必须的各种要素。这四篇小说又相互联系,一气灌注,具有美国短篇小说家、诗人与文论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所主张的统一效果(unique effect)。为了论述方便,我们不妨将《白襷队》、《间谍》、《阵地上的演出》和《父与子》这四篇小说分别命名为A文本、B文本、C文本和D文本,这四个文本都指向同一个总文本E,即《将军》。就E文本而言,它本身并没有一个字,它只不过是A、B、C、D四个文本的总体效果罢了。不过,既然作者把这四个文本归于同一个总标题之下,那么在他的心目中E本身毕竟还是一个文本。而且,在芥川龙之介的各种文集中,这四篇小说也还是只算作一篇的,而并无选录其中任何一篇来单列的情形。通过考察这五个文本的关系,我们可以见出芥川龙之介那高超的叙事艺术。将这四篇小说串联为一个整体的因素有三个。第一个因素是小说中的人物“N将军”,他在四个单篇中均出现。因此,N将军不仅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而且也起着主题道具的作用。第二个因素是弥漫在该故事组中的一种氛围,或者说,一种统一的效果,它将小说中的事件粘合在一起,这就是小说中的感伤主义情调,它是日本人那挥之不去的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情结在作者行文时的自然流露。第三个因素不那么明显,它潜藏在小说的情节和事件之中,也潜藏在小说家的心中,这就是作者的反侵略意识。可以说,反侵略意识是芥川龙之介小说《将军》那感伤主义情调的内核。
A文本《白襷队》。
它描写日本帝国军队的一支敢死队在松树山麓的一次战斗,他们的目标是攻克一座炮台。白襷队的战术并不稀奇:以士兵的身躯为炮弹向前猛冲。经过激烈的战斗,白襷队最终取得了胜利,不过有的士兵因头颅中弹而神经失常了。
这场战斗开始于明治三十七年(1904)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拂晓时分。第X师第X联队的白襷队为了夺取位于旅顺港松树山上的俄国军队的备用炮台,从九十三高地的北麓出发。这场战斗结束于当天夜里。
“白襷队”一语中的“襷”,究竟是何含义?各选本和注本,均语焉不详。兹略说一二。襷,在较古老的日文中也写作“手繦”。繦,同襁,背负婴儿时所使用的带子。在现代日语中,襷有两种含义。一,“日人在劳作时为了挂起和服的长袖,斜系在两肩上面而在背后交叉的带子”[1]1247。这种含义的襷,其式样与作襁褓用的那种长布带扎起来的时候是很相似的。在古代,日本贵族穿戴的和服上有襷,它主要是做装饰用,而不是为了活动方便。《日本认知事典》:“‘肩上斜挂着带子在干活儿’,甚是勤快。虽然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但是实际上身著长袖而劳作并不是指真正的劳动,而是让人感受到一种服饰华丽的气氛。襷在古代与袖子并不相干,而是具有装饰乃至咒术的意味。”[2]287在这部厚书中有插图,可知襷究竟是如何系在身上的。如果从前面观看,襷与今日西方各国的总统候选人胸前所佩戴的绶带是差不多的。当然,随着商业气息的浸染,今日餐馆大门口迎宾的小姐,商场招徕生意时的小伙也挂绶带了。显然,宽衣博带不便于活动,更不用说打仗了。二,“斜挂在肩上的窄布条”。[1]1247其实,这篇小说中的襷,就是斜挂在肩上的窄布条。日本群众在游行、罢工或参加选举等活动的时候,往往系上一根襷,其用意在于醒目。由此可知,白襷队的襷,当是第二种含义,即斜挂在肩上的白色的窄布条。白襷的作用在于标志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决死队,即敢死队。在日本文化中,白色具有冷静地面对一切事情的象征意义。
芥川龙之介的《将军》是一篇具有纪实文学性质的小说。在日军中真有这么一支叫做白襷队的特别支队,兵力多达3100人,由少将中村觉(1854—1925)担任支队长。在旅顺总攻的时候,白襷队担任主攻,执行夺取俄国军队的备用炮台之任务。中村觉是明治和大正时期日本陆军的职业军人,他生于滋贺县。1872年,中村觉进入日军教导队,后来历任第十连队大队长,第一师团参谋长等职,并从1900年起任台湾军总督府陆军参谋长。驻军台湾的经历使中村觉对中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因而他作为步兵第二旅团长被派往中国参加日俄战争。从1906年起,中村觉历任教育总监部参谋长、第十五师团长、侍从武官长、东京卫戍总督等职。1907年,中村觉晋升大将。1917年,中村觉任军事参议官。1919年,中村觉转为预备役。
日本士兵是愚忠的士兵,这是A文本的中心思想。A文本的大背景是日露战争,即日俄战争,因为日本称俄国为“露西亚”。这是日本和俄国为了争夺东亚的霸权,重新瓜分中国东北,并进一步侵略朝鲜,在中国东北领土上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即1904年2月8日,日俄战争爆发。那一天日本舰队突然袭击停泊在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清政府屈服于日俄两国的压力,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地区划为“交战区”。战争历时一年多,结果是俄军水陆俱败。经过美国的斡旋,日俄两国于次年八月七日,即1905年9月5日,在美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根据此条约,日本获得对中国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以及库页岛南部等地的支配权。俄国是横跨欧亚的大国,日本是悬于海中的小国,日本打败了俄国,犹如小松鼠咬伤了大狗熊!为什么战争的结果会是这样呢?笔者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日俄两国当时的国势不同。一边是十月革命爆发前夕处于垂暮之中的沙俄帝国,它气息奄奄,朝不保夕。一边是明治维新之后处于上升阶段的日本帝国,它欣欣向荣,欲上天衢。当时的日本早已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日俄战争又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史学家这样写道:“这次战争的结果,日本的重工业得到了飞跃的增长,资本主义的基础得到了巩固。”[3]380然而,日本赢得这场战争也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的。“日本在战争中动员了110万兵力,伤亡人数超过20万,军费开支18亿,相当于政府年度预算的8倍。”[4]133在旅顺包围战中,沙俄军队战死四万四千余人,日本军队战死六万余人。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日方这六万余人的炮灰是怎样“炼成”的呢?《白襷队》:“听着听着,在堀尾一等兵那酒意未消的眼睛里,竟然平添了一种光芒,那是对眼前这个温厚战友的轻蔑表情。‘豁出性命,算得了什么?’——他就这样在心中嘀咕着,抬起头凝目仰望天空。并且,他暗自下定决心,为了报答将军的握手之恩,今晚一定抢在众人前面充当炮灰……”[5]161在我们中国人的语汇中“炮灰”一词明显地具有贬义。然而,这个日本一等兵堀尾却心甘情愿,他要争先恐后地去充当炮灰。这不是愚忠,又是什么呢?在日文原文中,炮灰,作“肉弹”。肉弹,以人体为弹丸向敌人的阵地突进,即人肉子弹,这是N将军在日俄战争中的一大发明。
那么,我们不禁要追问,是什么精神支配着愚忠的日本士兵去充当肉弹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大和魂。《白襷队》的第二自然段:“道路沿着山阴伸展,队形在今天也特别,以四列纵队行进。在无草的昏暗道路上有扛着枪的一队士兵。只有白襷在闪露,他们的靴声轻轻,真是悲壮的光景。以指挥官M大尉来说吧,从站在队伍前头时起,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话也少了,阴沉着脸。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士兵们个个都未失去平时的精神。所以如此,一来是日本魂的力量,二来是酒的力量。”[6]46这一段话,系笔者根据《日本近现代战争文学选读》中的日文原文直译。日本魂和酒在这里是互文的关系。这样的互文手法可以产生讽刺意味:日本魂犹如日本清酒一般。这样的讽刺,犹如汉语所云:某人像打了鸡血一般!由此可见,鼓动日本兵去充当肉弹的是日本魂。日本魂,又称大和魂。大和魂指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其核心为神国意识:日本列岛由大神长矛上滴下的水珠凝结而成,日本人是神的子孙。大和魂的具体内容分为两部分。一为伦理的美德:坚韧、淡泊、忠诚、勇武、不屈。作为伦理美德的大和魂并没有什么不好。一为神学的美德:忠诚于神,忠诚于国家,忠诚于天皇。这是因为天皇、国家和神,乃是三位一体的。至于那被标榜为神学美德的大和魂,我们则必须十分警惕。当大和魂在日本列岛内部运作的时候,它具有凝聚人心、尊王攘夷、鼓舞民众积极向上的作用。但是,一旦大和魂被运用到国际事务中,那么它就会变成日本对外扩张的精神支柱,甚至演变为战争的口号,驱使日本军人去充当炮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神学的美德就蜕变为十恶不赦的罪孽了。作为战争口号的大和魂是我们必须批判的。
C文本《阵地上的演出》。
这个标题,日文原文作“陣中の芝居”,直译为:军营中的剧场。它描写一支日本部队的军营文化。尽管军营文化的层面很多,但是文艺演出无疑是军营文化的集中体现,所以C文本便聚焦于一场文艺演出。“明治三十八年五月四日,在驻扎于阿吉牛堡的第X军司令部里,上午刚刚举行了招魂祭,又决定下午召开表演大会了。会场用的是那种中国乡村常有的露天戏台。”[5]169C文本就这样开头了。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演出的地点,它是日本某军司令部里的一个会场,而这个会场竟然是中国乡村常有的露天戏台。这就一语道破了这支日本部队的侵略性质。该军的司令官N将军做了巧妙的安排:上午在司令部里举行招魂祭,下午就在同一地点进行文艺演出。招魂祭,即招魂仪式。古人信奉有灵论,他们认为人的死亡,只不过是灵魂离开躯体罢了。躯体会腐烂,但是灵魂永不死。灵魂离开躯体之后,就在空中游荡。为了让灵魂有个归依之处,就得举行仪式,让灵魂回家。这就是招魂仪式产生的缘由。在东方各民族中大都有招魂仪式,但繁简不一。在《楚辞》中有《招魂》篇,它记载了战国时期的招魂仪式。已有学者指出,在第一批传播到日本的中国经典中就有《楚辞》。日本将《楚辞》所载招魂的程式与其固有的神道学说相结合,再添加一些佛教的仪轨,便营造出了一套复杂的招魂仪式,称为招魂祭。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对外征战增多,战死者也相应地增多,于是设立了许多纪念那些为国牺牲者的专用神社,叫做招魂社。本来,在日本各地都建有招魂社。招魂社太多,不便于管理,于是后来统一规定为一县一社,其规模增大不少,带有官方色彩。在全国还有一个总的招魂社,即靖国神社。靖,日语他动词,使安定。靖国,安国。靖国神社,字面意义为安国神社。为战死者招魂,毕竟是一件悲伤的事情,于是接着便进行文艺演出,目的在于使大家迅速走出悲伤的阴影,以便重新斗志昂扬地走上战场。这就是司令官N将军的思路。
且看文艺演出是何等热闹!第一个节目:主人与女佣相扑。“每当舞台上开始一场闹剧,从坐在草席上的观众那儿,就会爆发出一阵阵哄笑。不,甚至后面那些军官们都发出了笑声。而就像是与这种笑声较着劲一样,演出越来越增添了滑稽的成分。最后,终于出现了穿着丁字形兜裆布的主人与只穿一条红内裙的女佣扭揪在一起,进行相扑的场面。”[5]170这也滑稽得可以啦!舞台的恶俗每一加増,看客们便数度发出笑声。可不,连后面的将校们,也浮泛出了盈盈笑意。俄而笑声竞逐,愈发滑稽重生。这样终于到了尾声,主人一枚越中褌,下女一条赤汤卷,开始相扑啦。芥川龙之介的幽默讽刺,大约如此。日本接受中国文化较早,日语中蕴含着大量的与古代中国有关的文化因素。褌,兜裆布。越中褌,在长约一米的白棉布上缝有细带的兜裆布,得名于越中太守忠兴,他首先穿用这种兜裆布。汤卷,一作汤文字,本为日本宫中女官用语,指洗热水澡时穿用的内裙。如此表演,那还了得!正在军需部的一个大尉准备带头鼓掌的当儿,突然传来了一声叱责:怎么搞的?如此丑态!拉幕!拉幕!原来是N将军的声音,他神情严肃地盯着舞台。怎么能表演这样的节目!还有外国武官在场观看哪!其实,在场的法国军官看得也挺舒服的,他还想继续看下去呢。于是,这位法国军官问坐在旁边的一位中佐:为什么将军下令停止演出?“因为过分粗俗呗。——要知道,将军讨厌粗俗的东西。”[5]171在浪漫的法国人看来,军营里表演性感盎然的节目并没有什么不好。君不见,在欧洲,美女台上唱歌,一边唱一边脱衣么?歌女将胸罩、袜子等都一一脱下来,抛向军官和士兵们,他们还抢着要呢。坐在旁边的美国武官对此也颇为感慨,他说:“N将军也真够累的,因为既要当司令官,又要当检察官……”[5]172堂堂司令长官亲自充当新闻检查官!这几句感慨的话,道出了日本军队对于意识形态控制的严密程度:最高首长亲自抓意识形态工作。而且,大凡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事无巨细,最高首长都亲自过问。原来,日本兵的愚忠是这样培养起来的。
下一个节目:《巡警捕捉瞎眼盗贼》。内容是一个瞎眼盗贼持枪与巡警的打斗。盗贼举起手枪,频频开火。巡警英雄无畏,终于用绳子套住了盗贼。原来,盗贼并非瞎子,只是伪装成瞎子罢了。这时台下的观众群情激奋,不过他们却不敢鼓掌,也没有欢呼。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在等待N将军的反应,不愿受到他的呵斥。N将军紧盯着舞台,他没有发话,不过他的表情已经比刚才温和得多了。这说明,表演进行到目前为止,N将军并不反对,只不过他也不觉得这样的节目有多么好。表演继续进行。这时警察署长带领部下从舞台的一侧冲了上来。巡警依然在搏斗。不幸得很,那巡警因为中弹现已处于弥留之际。署长一边安排送医院抢救,一边询问他有何遗嘱。那巡警说,故乡尚有老母,怕是照顾不到她老人家了!署长叮咛说,别担心,有大伙儿呢!巡警说:“我没什么牵挂了,抓住了盗贼,俺死而无憾!”这时,在鸦雀无声的场内三度响起了将军的声音。不过,这一次可不是叱责之声,而是感佩万分的叹息之声。“了不起的家伙!正因为如此,才堪称日本男儿呐。”[5]174在N将军看来,粗俗的日本军营文化这才走上了正轨。
演出到此结束,大家原地休息!不过,半小时之后,演出又开始了。原来N将军叫来演出的负责人,叫他追加一个节目。大家揣摩N将军的心理,估计下一个节目肯定是《赤穗义士把酒话别》。N将军喜欢忠勇嘛。其实不是,下一个节目不再是小话剧,改为评书了,题目是《水户黄门巡游诸国》。这位水户黄门名叫加藤清正(1562—1611)。有日文资料云:“加藤清正,安土桃山时代的武将,幼名虎之助,家住尾张国爱智郡中村。他的祖先为藤原氏。由于他拜丰臣秀吉的从父姊妹为母,因而从幼年起他就成了秀吉的家臣。1583年,他在贱岳之战中立有战功,因而被任命为主计头。在九州征伐之际,他坚守肥后的宇土城,从而得以领有半个肥后国。在文禄·庆长战役中,他作为先锋而远征咸镜道。之后,他在蔚山固守城池。关原之战时,他属于东军一方,并获封肥后一国。1601年,他大兴土木,修筑熊本城。此外,他还奖励文教事业,大有政绩。”[3]93显然,在 N 将军的心目中,惟有像加藤清正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臣。N将军的人生理想,就是做一个忠君的人臣。他也以加藤清正来教导其部下。
日本军队的军营文化是粗俗的文化,这是C文本的中心思想。用粗俗的兵营文化来培养军人的愚忠意识,这是日本军队的传统。其实,粗俗的舞台表演只是日本军营文化的冰山一角罢了。到了二战时期,日本甚至发明了慰安妇这一臭名昭著的制度。慰安妇制度,这是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日本才想得出来的主意。总而言之,整个日本军队就是一个愚忠的养成所。
D文本《父与子》。
这个标题在日文原文中作《父と子と》。在日语中,“父与子”这一概念,既可以用“父と子”来表达,也可以用“父と子と”来表达。根据日语的语法,后者具有强调的意味,指二者同等并列,完全同然。这样的标题,其含义是说,这一对父子,乃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半斤八两!D文本叙写中村少将与其儿子之间的谈话。叙事场景是中村少将的西式客厅。叙事时间为大正七年(1918)十月的某个夜晚。这一年距离日俄战争结束(1905)已经十三年,沙俄帝国早已灭亡,日本帝国正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奔驰。这位中村少将就是C文本中的那位中村少佐。当时他跟随N将军参加日俄战争,任军部参谋,随侍在N将军的左右。现在,中村少将过着优裕的生活,嘴上叼着哈瓦那雪茄,厅壁上挂着名人的肖像。目前他最关心的是如何培养他的儿子。举止文雅的儿子刚参加完追悼会回来,原来他的同学,一个叫河合的文科大学生,自杀了。父子间的谈话,起因于父亲发现厅壁上悬挂着一幅年轻人的肖像,那是河合,而原来悬挂的名人肖像有了变动:N阁下的肖像被取下来了。这位N阁下就是N将军。父亲要求儿子把N阁下的肖像挂回去。儿子敷衍了事,他把N将军的肖像与壁炉上方的荷兰画家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1606—1669)的肖像挂在一起。父亲不同意。他认为,虽然伦勃朗是大画家,但是他却没有资格与N将军相提并论。不过,儿子还是不想将亡友的肖像取下来。
按常理说,父亲必定勃然大怒。出人意料的是,D文本的叙事并未这样进展。芥川龙之介笔锋一转,这样写道:“少将轻易地就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他却又一边吐着烟圈,一边静静地继续说道:‘你——不如说你们这辈人,究竟对阁下作何感想?’”[5]177儿子被问住了。他只好回答,说不上什么感想,大体说,也还算是个了不起的军人吧。以此为契机,父亲向儿子讲述了N将军的一件逸事。父亲,温文尔雅,娓娓道来。他讲起了日俄战争之后,前去别墅拜访N将军时的一则趣闻。
穿棉袄的N将军和夫人伫立在后山上,一站许久,怎么也不肯离开那里。少将觉得纳闷,便问道,难道发生了什么大事吗?不料,N将军立刻笑了起来。他说,哪里,哪里,刚才他老伴想解个手。于是跟随他们的一大群学生便分头去找地方,大家刚才忙得不亦乐乎。原来,N将军夫妇久久伫立在后山上,乃是为了回报学生们对于为师者的那一份情。
那是怎样的一份情呢?
讲到这里,父亲眯缝起了眼睛,回忆美好的往事,他微笑了。父亲,温文尔雅,娓娓道来。他接着说,这时,四五个精神抖擞的学生,同时从色彩斑斓的树林中跑了出来,他们把将军夫妇包围起来,纷纷报告各自为夫人找到的地方。为了让夫人选择前往他们各自找到的地点,他们竟然争执不下。最后,还是用抽签的办法来做了决定。儿子,憨厚本质,托腮细听。听到这里,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他说,一群学生为师母找撒尿的地方,这故事倒是无伤大雅,但不适合讲给西洋人听。父亲说:“就是这样。即便是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只要说是N阁下,就会像对待叔叔那样亲近他。阁下决非如你们想象的那样,只是一介武夫。”[5]178说完这番话,父亲不再言语,他把视线转到伦勃朗的肖像之上。如何对待N将军的肖像?父亲将这个问题留给儿子自己去处理。
按常理说,儿子势必马上将N将军的肖像挂回原来的位置。出人意料的是,D文本的叙事并未这样进展。芥川龙之介笔锋一转,径直记录了父子之间的另一番对话。对话的焦点是,为什么年轻人河合,在自杀之前,还有闲情逸致,找人给自己拍照。窗外飒飒作响,下雨了。父亲呢喃,转入另一个话题:“但愿榅桲果不要再掉才好……”[5]180
D文本到此结束。至于儿子究竟将N将军的肖像挂回原位否,芥川龙之介根本就没有写。
在D文本中,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榅桲,也就是木瓜,它在D文本是一种象征。《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7]59《木瓜》篇三章,每章四句,共十二句。《木瓜》虽然篇幅短小,却是《诗经》中脍炙人口的名篇。大意是说,别人赠我以微小的礼物,我当报之以贵重的珍宝。其实,无论多么贵重的宝物,其本身也不足以为报。人们相互间的赠送礼物,表达的是一种期望,但愿情深谊长。这里说的木瓜,又名文冠果,主要生长在偏北的地域,其学名正是榅桲。榅桲的果实,在秋季成熟,如大鸭梨一般大小,有浓烈的香气,味道涩口。榅桲可入药,也可蒸煮来吃,还可以做成蜜饯。在重庆一带,还有人将七八分熟的榅桲果实,用来做泡菜。《诗经》传入日本很早。大约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日本人就了解《诗经》,并能够习《诗》、明《诗》和用《诗》了。由此可知,在D文本中榅桲的象征作用是告诫日本青少年,要他们懂得回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外征战频繁。对日本青少年来说,需要回报的对象很多,然而最大的回报,就是回报所谓大日本帝国。
N阁下,亦即N将军,这一人物的原型是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1849—1921)。这一点,从“乃木”这一姓氏的发音上而得到了暗示。乃木希典出身于藩士家庭,为家中的第三子,其父亲为长州藩士乃木十郎希次,其母亲为常陆国土浦藩士谷川金太夫的长女寿子。乃木希典就学于藩校明伦馆,因而他具有很好的汉学基础,也会做汉诗。明治维新后,乃木希典进入亲兵营,镇压过荻之乱。1871年他担任陆军少佐,参加过西南战争。1886年乃木希典赴德国学习军制和战术。留学归来后,乃木希典曾一度赋闲。甲午战争时乃木希典复出,担任步兵第一旅团长。1896年乃木希典担任台湾第三任总督。日俄战争时期,乃木希典为第三军司令官,他具体指挥了旅顺总攻,并因战功而晋升为大将。此后,乃木希典回到日本,历任军事参议官、学习院院长等职。乃木希典的一生可以概括为四句话:明治天皇的忠勇亲兵;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日俄战争的急先锋;愚忠思想的鼓吹者。在日本,乃木希典被称为“军神乃木”,被奉为神话般的英雄。明治天皇去世的时候,乃木希典与其妻子一道自杀以殉死。在乃木希典的时代,殉死这一古代的习俗早已过时,然而他却刻意为之。由于乃木希典为日本军国主义立下了赫赫战功,因而在当时的日本几乎家家户户都挂有乃木希典在自杀前特意请摄影师拍摄的照片。
总之,在日本老军人看来,愚忠意识需要培养,愚忠意识要由一代又一代的日本青少年来传承,这就是D文本的中心思想。由D文本可知,在日本,愚忠意识不仅在教科书、新闻传媒等公开渠道中得到提倡,而且还变成了家教的一部分。在日本的军人家庭中,愚忠意识主要是以父子相传的方式来进行灌输和培养的。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在今天还有不少日本人责骂年轻的一代缺少武士道精神。
本来,A文本、C文本,以及D文本已经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组了。此故事组以愚忠意识为中心而展开。A文本描写愚忠意识在战争实践中的展开,C文本描写愚忠意识在军营文化中的培养,D文本描写愚忠意识在父子间的传承。这样的叙事结构不是很完整吗?出人意料的是,大文豪芥川龙之介并不这样安排叙事结构。芥川龙之介还精心安排了一个B文本。其他三个文本均以日本军人为行动素。B文本则不同,它以中国军人为行动素。我们不禁要问,小说家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原来,愚忠意识具有指向性。对内,它要求日本军人耿耿忠心于天皇,对外它要求日本军人毫不犹豫地斩杀敌方的人民。日军那样重视愚忠意识,究竟为什么呢?原来,愚忠意识是一种理念,它可以展开,它可以物化,它还可以演变为一个过程。在战争中,愚忠意识一旦展开,就是残暴。残暴是日本军队对外征战时的基本属性。这一点,大凡受到过日本侵略的那些国家的人民,都有深刻的体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是有不少日本军人把杀人当作一种乐趣吗?
B文本《间谍》。
原文标题如此。所谓间谍,实际上指大清国的两名侦察兵。B文本的中心思想,就是通过描写两名“间谍”的被捕并遭到日军杀害,以揭露日本军人残暴的本质。B文本《间谍》的背景为奉天(沈阳的旧称)会战。奉天会战是日俄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陆军决战。为了奉天会战,沙俄动员的兵力为三十六万人,日本动员的兵力为二十五万人。B文本叙事开始于明治三十八年(1905)三月五日。这一年是日俄战争的第二年。“1905年1月1日,俄军旅顺要塞司令施特塞尔(A.M.Cтecceль,1848—1915)开城投降,旅顺攻克后,日军第三军立即北上,与后备第一师合编成鸭绿江军,以川村景明大将为司令官,积极准备在奉天附近进行会战。”[8]520三月五日,日军动用三个军的兵力,从正面对奉天发起总攻。三月十日,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А.Н.Куропткин,1848—1925)担心被包围,于是下令全军向北撤退。日军立即全线进击,并迅速占领了奉天。至此,奉天会战以日方大胜而宣告结束。
那天上午,日军某骑兵团的参谋,在司令部某个昏暗的房间里审讯两个中国人。他们因有间谍罪嫌疑而被捕。中国人按照翻译的提问一一给与了明确的答复。有时,还等不及翻译完毕,他们就主动说明了问题。然而问题在于,他们给出的答复越明确,那参谋便越怀疑,于是他认定这两名中国人是间谍。间谍之所以被抓住是因为他们前来兑换纸币。纸币经检查,毫无问题。间谍被要求脱光衣服,他们马上就脱了。衣服经检查,毫无问题。他们被要求解下系在肚子上的腹带,那本是北方人为防寒才系上的兜肚般的东西。腹带经检查,发现一根针灸用针,因为他们中有一人是针灸医生。此外,一切也都毫无问题。他们被要求脱掉鞋子,他们马上就脱了。至此,这两名中国人全身赤裸。他们的衣服、裤子、腹带、鞋子和袜子统统都被仔细检查过了,毫无问题。“可就在这时,突然从隔壁的房间里走过来一大帮人。前头是军部的司令官,还有司令部的幕僚和旅长等人。原来,为了协商某件事情,恰好将军与副官、军部参谋一起,前来约见旅长。”[5]165见此情形,那将军问,他们是否为俄国的间谍。参谋简要地向将军报告了整个事件的始末。参谋还说,事到如今,只能用严刑拷打来迫使他们招供。将军冷峻地指着地上的鞋子说道,把那鞋子剖开来看。大家眼盯着,鞋子被剖开。哇喔,四五张地图和秘密文件一下子散落在地上!二十分钟后这两名中国人被处决了。
在B文本中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五点。
第一是审讯的地点,即日军的司令部,它设在一栋低矮的中国房子里。请看日文原文:この棟の低い支那家の中にほ,勿論今日も坎の火つ气が快い温みを漂わせていた[6]52。(在这栋低矮的中国房子中,当然今天也如此,地火炉的火气正散发出令人快慰的温热。——笔者译)坎者,凹陷也。地火炉,并非堆垒在地板之上,而是与地面齐平,只有火膛孔洞凹陷。地火炉的掏灰处为一方形的深坑,称为火炉坑,平时用木板覆盖,也与地板平齐。在笔者家乡重庆南川,直至文革期间,家家户户还都使用地火炉。地火炉大约在元代由元军从北方传到重庆一带。那是一种既节约又科学的取暖方式。那时候的民居为平房,采用泥土地板,建造地火炉容易。有了地火炉,整个地板都是暖和的。回看日俄战争,那是一场肮脏的战争。沙俄和日本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狗咬狗,战场却在中国的东北。《间谍》所描写的那个日军司令部,位于全胜集。这一地名表明,它显然是一个中国东北的集镇。
第二是日本将军的偏执狂特征。当那位将军,在询问了被审讯的中国人是否为俄国间谍之后,便不再作声了,他只是紧盯着他们那裸露的身体看。将军的这一细节,被一位美国人注意到了。这位美国人还有所评论。“将军这样问了一声,然后就那样在中国人跟前停住了脚步。只见他把锐利的目光一动不动地投落在那两个赤裸的身体上。后来曾有一个美国人毫不客气地评价道,说在这个著名将军的眼睛里,有着某种近似于Monomania(偏执狂)的特征。——那种近于偏执狂式的眼神,在这种场合下更是平添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光芒。”[5]165这位美国人的评价,非常客观。从二战期间日本军人在中国的行为表现来看,他们多数都因军国主义而神经中毒,他们也大都具有偏执狂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讲究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要想人物的性格来得真实,那么就不仅要求环境的描写必须真实,而且还要求细节的描写也必须真实。这一点在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得到了事实上的体现。
第三是中国人的视死如归。从鞋子中抖落出地图和文件后大约二十分钟,那两个中国人就被带到村子南端的道路旁去了。他们的发辫被捆在一起。他们木然地坐在干枯的柳树根上。临刑前他们是怎样的表现呢?“两个中国人不约而同地回头望着他,但脸上却没有流露出半点惊慌的表情,而只是朝着各自的方向开始接二连三地叩头。‘他们在向故乡告别呐。’——田口一等兵一边做出动手杀人的架势,一边如此解释着叩头的意义。”[5]166杀头不过头点地,有什么好害怕的呢?中国士兵绝大多数来自农村。人来自泥土,又回归泥土,这自然得很哪。这两名中国人在临刑前平静地告别自己的故乡,他们是何等地视死如归!
第四是日本兵的极端残暴。田口尚未来得及下手,便见一个骑兵策马而来。那骑兵要求,让他也动手来斩掉一个。田口说,两个都交给你好啦。那骑兵尚未来得及下手,又见三名军官策马而来。他们当中有一位正是将军。将军的眼中倏然掠过偏执狂似的光芒,他说,斩掉,斩掉!“骑兵当即挥动大刀,一下子朝那年轻的中国人头上砍去。只见那个中国人的脑袋翻滚着,飞落到干枯的柳树根下。瞬时间,鲜血在发黄的泥土上漫延出一个个巨大的斑点。‘很好!干得不错!’将军一面喜形于色地点着头,一面驱赶着马儿走远了。骑兵目送将军离开之后,又提着沾满鲜血的大刀,站到了另一个中国人的身后。他的一举一动给人一种感觉,似乎比将军更喜好杀戮。”[5]168这样的描写绝非魔幻现实主义的笔法,而是事实。日本兵的残暴,堪称世界之最。在二战中,日军的残暴越演越烈。“原日军第59师团团长滕田茂战后揭露,他曾多次奉命下令‘俘虏要在战场杀掉,算入战果’,‘以实敌刺杀作为对新兵之试胆教育’。”[9]73由此可知,推行愚忠教育的日本军队,其极端残暴乃是必然的。
第五是日军勋章的含金量。军人看重荣誉,这在世界各国都是一样的。表彰军功的方式有多种,授予勋章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它有着将军人的功勋物化和固化的特殊作用。因而我们看见,老军人常常把自己的勋章从珍贵的秘藏的盒子中翻出来看看的情景。我们还看见,军人的子孙,哪怕是若干代之后,仍然视其先辈的勋章为传家宝。勋章的质地有多种,有金质勋章,有银质勋章,有铜质勋章。在沙皇俄国,甚至还有铁十字勋章。勋章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质地,而在于它所体现的意义。功勋本身才是勋章真正的含金量。勋章的价值在于功勋的大小。那么,日本的军功勋章,其含金量有多少呢?且看,跟在将军身后的军部参谋,在马鞍上望着春寒的旷野。“然而,不管是那些遥远的枯木,还是倒立在路旁的石碑,都没有进入他的视线。因为他的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一度爱不释手的司汤达作品中的一句话:‘一看见那些戴满勋章的人,我就禁不住想,他们为了得到那些勋章,做了多少 XX的事情……’”[5]168突然,军部参谋发现自己落后了,打了个寒战,他又策马追随将军去了。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将军》中,有不少语句被新闻检查官删掉了,被删掉的字就用X来表示。兹不妨尝试补出。在法国作家司汤达(Stendhal,1783—1842)的原作中,那XX可能代表“卑鄙”二字。在这位日本将军那里,XX最有可能代表的是“残暴”二字。B文本中的那位将军,并没有点明为N将军。不过,从上下文看,那位将军其实就是N将军。笔者所以如此判断,乃是因为二者在精神面貌上具有完全的一致性。N将军是日本众多将军本质的集中体现,其他的日本将军则是其分身。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两个中国人究竟是否为俄国间谍。笔者以为,他们当为大清国的侦察兵,他们服务的对象是自己的祖国。理由如下。在日俄战争中,清朝政府处于尴尬的地位,两只恶狗在自己的地盘上抢食!这极其可恶,却又奈何不得。清朝政府不得不预作打算。清朝政府必须弄清楚,日俄双方中究竟哪一方可能取胜。派出侦察兵去打探交战双方虚实,这是清朝末年积贫积弱的国势所造成的无奈之举,目的在于避免国家主权进一步的丧失。
总之,B文本正面写的是中国清朝军队的两名侦查兵,他们是不屈的战士,不幸遭到杀害。B文本对大清国侦察兵的描述较多,但最终还是落墨于描写日本军人的残暴。
B文本的延伸。
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将军》作于大正十年(1921)十二月,此见于小说末尾作者自己的题署。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中,直接描写战争的作品不多。尽管如此,芥川龙之介的反侵略意识却是浓厚的,而且是一以贯之的,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芥川龙之介还著有一本书《中国游记》,约合中文十万字,作于大正十四年(1925)年底。写成此书之后两年,芥川龙之介就去世了。《中国游记》可视为《将军》故事组中B文本的延伸。从叙事学的角度看,《中国游记》是一种文本之外的文本(a text beyond the text in question)。《中国游记》所表达的是芥川龙之介成熟的思想。在《中国游记·自序》中,芥川龙之介谈到了此书的缘起:“我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命,大正十年(1921)三月下旬至同年七月上旬,一百二十多天的时间里,游遍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回到日本之后,便执笔写作《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每天一节供《每日新闻》连载。《长江游记》也一样,那是接在《江南游记》之后刊载的,也是每天一节,只是没写完。《北京日记抄》却未必按每天一节的进度撰写。记得总共用了两天左右的时间。而《杂信一束》基本上抄录了旅途中所写美术明信片上的文句。”[10]613《中国游记》是序文中所说的各种游记、日记和书信的一个总称。
《中国游记》内容丰富,它具体而微地描写了民国初年旧中国的社会面貌。芥川龙之介坦率地描写了旧中国社会的五个侧面。它们是民众不讲卫生、妓院青楼林立、礼乐文物衰败、生态破坏严重,以及外国势力横行。芥川龙之介来中国游历访问,接待他的是驻各地的日本机构。在每一座城市,在每一个港口,都有日本的公司、商行、洋行、会馆、记者站等,也有中国人抵制日货的运动,甚至还有勾引英美水手的日本女人,这些他都如实记录了。这说明芥川龙之介有一颗真热爱中国的心。在《长江游记·溯江》中,他写道:“但是长江上来去的,不用说,并不只是这类木筏那种原始时代留下的遗物。有一次,也曾看见一艘美利坚的炮舰,正在对由一艘小汽艇牵引的目标进行实弹射击。”[10]739美利坚合众国是旧中国时期最大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书信一束》的末尾,他写道:“南满铁路犹如一条蜈蚣在高粱的根部爬行。”[10]761南满铁路原是帝俄所修中东铁路的一部分,日俄战争后为日本所占,改称南满铁路。由此可知,身为日本人的芥川龙之介对日本在中国的作为并不认同。他深深地知道,帝国主义的侵略才是旧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于是,芥川龙之介对此进行了揭露。在《中国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芥川龙之介的审美情调。每当他叙及中国的山川、田野、大自然和生命的时候,他总是以优雅的笔调来描述,而且他的笔端还带有一种淡淡的忧愁。在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中,多种文体往往交替使用,其主体为散文,偶尔也穿插一些诗歌、对话和评述。他的诗歌有汉诗,也有俳句。散文、诗歌、对话和评述四位一体,这是芥川龙之介的总体行文风格,故而《中国游记》具有明显的复调特征,几个声部,共同发声。
在《上海游记》第十三节中,芥川龙之介写道:“如若不信,不管是谁,请各位自己到中国去看看好了。只要呆上一个月,便会莫名其妙地谈论起政治来。那准是因为现代中国的空气里,包孕着二十年来各种政治问题的缘故吧。”[10]642芥川龙之介写作《中国游记》的那一年,即1921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而她成立的地点就是上海。对此,芥川龙之介未必知晓,但是,作为一个敏感的知识分子,他毕竟对此有所感受。从那一年起,中国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了。从那一年起,经过中国共产党人二十八年的奋斗,到了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里试就《将军》的主题思想做一总说。
从芥川龙之介小说《将军》的分野看,它属于具有反侵略意识的战争小说。从叙事结构看,《将军》由A、B、C、D四个文本组成,因而它不是一个单篇小说,而是一个故事组。在这四个文本中,总有一个无处不在的行动素,那就是N将军。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将军》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描写N将军对一支日本部队的巧妙的指导来实现的。它表现了日本士兵的愚忠,展示了中国侦察兵的牺牲精神,暴露了日本军营文化的粗俗,谴责了日本青少年接受愚忠思想时的不自觉,从而把忠实执行军国主义路线的日本军人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欣赏小说那近乎荒诞的描写时,读者的思想也自然而然地发生倾斜,并进而认识到军国主义违背人性,委实要不得。作品的思想倾向暗传于叙事之中,这是芥川龙之介叙事艺术的精要所在。
[1]陈涛主编.新版日汉词典[K].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5.
[2]大岛建彦,大森志郎,后藤淑.日本を知る事典[K].东京:社会思想社,1982.
[3]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编.日本史辞典[K].大阪:创元社,1954.
[4]王新生.日本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高慧勤,魏大海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宋再新,杨伟,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6]何建军编著.日本近现代战争文学选读[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7]程俊英,蒋见元注译.诗经[M].长沙:岳麓书社,2000.
[8]吴廷缪主编.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9]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
[10]高慧勤,魏大海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3卷[M].宋再新,杨伟,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