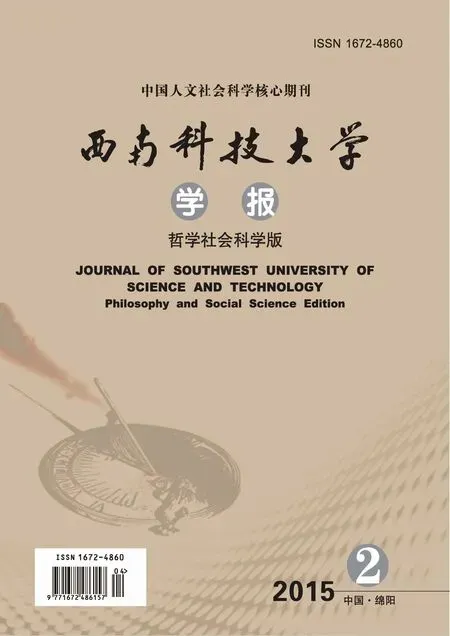《坠落的人》中主要女性人物形象解读
2015-02-20罗姣惠
罗姣惠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坠落的人》中主要女性人物形象解读
罗姣惠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在小说《坠落的人》中,德里罗刻画出一些女性形象。结合文本细读法,从女性气质视角来解读妮娜、弗洛伦斯、丽昂这3位女性,她们是理性、坚强勇敢、有责任感的新时代的女性代表。德里罗通过对女性形象的描写,塑造了“9·11”事件之后,在男性创伤者受到该事件冲击而自甘堕落的情况下,敢于承担各方面责任的新时代的女性形象。
《坠落的人》;理性;坚强;有责任感
唐·德里罗( Don Delillo,1936-) 是美国著名的后现代小说家,被哈罗德·布鲁姆列为与菲利普·罗斯( Philip Roth) 、托马斯·品钦( Thomas Pynchon) 以及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 齐名的当代4位最杰出的美国小说家。其小说《坠落的人》(2007)一经出版,在美国好评如潮。《娱乐周刊》评论员詹妮弗·里斯(Jennifer Reese)认为德里罗准确地把握了“9·11”事件的本质,称《坠落的人》是德里罗自《地下世界》以来最好、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新政治家》评论员史蒂文·普尔(Steven Poole)称该作是作者创造天才喷薄而发的艺术结晶,表现出宏伟的力量和节制。该小说主要讲述了39岁的律师男主人公基思,在“9·11”那天,他大难不死,从废墟中逃了出来,并重新回到已经分居的妻子丽昂的家中的故事。书中,尽管妻子试图与基思重归于好,但经历灾难之后的基思再也无法回到从前,转而沉溺于扑克。然而,妻子丽昂却没有因为丈夫的堕落而堕落,她选择了一个人担当起对家庭、社会的责任。国外关于《坠落的人》的研究成果相对丰硕,主要着眼于创伤、恐怖主义、叙事手法及政治等角度。相比国外的德里罗小说研究热潮,国内关于德里罗《坠落的人》的研究则稍显单薄,主要从创伤记忆和平复创伤主题、人物特征及后现代创作手法等方面来进行:第一,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研究较多。张加生通过对德里罗的两部恐怖题材小说《天秤星座》、《坠落的人》进行解读后发现,德里罗在向人们预示和闪回着“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必然性的同时,表达了作者对美国“9·11”前后社会心理创伤的关注[1]。第二,李静从这部作品中的3个主要人物和其他角色不同的特征入手,透视了其中暗含的后“9·11”民众疗伤方式,能够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灾难带给美国社会和民众的巨大冲击[2]。第三,张丽丹和张薇从这部作品的语言特征、叙述特点和人物特征3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德里罗所使用的后现代写作技巧[3]。但汉松通过对德里罗《坠落的人》和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的对比阅读,认为“9·11”小说的基本叙事场域在于“悼歌”和“批判”的两轴[4]。然而,鲜有论文从女性气质的视角来研究《坠落的人》中典型女性人物。因此,本文结合文本细读法,从女性气质视角来解读妮娜、弗洛伦斯、丽昂这3位女性,认为她们是理性、坚强勇敢、有责任感的新时代的女性代表。
一、为人理性,独具一格的妮娜
根据一项跨文化研究显示,人们对性别气质都存在刻板印象,“如一般人认为男性具有工具性特质,坚强、独立、大胆、冒险、理性,适合从事竞争工作;女人具备情感性表达特质,温柔、体贴、胆小、感性、脆弱、母性,适合从事家庭内照顾幼儿、料理家务等工作”[5]14。在《坠落的人》中,妮娜曾在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大学里教书,被基思戏称作二流高校的二流教授。大学教授分析问题相对全面、透彻,妮娜也不例外。她看问题、处理事情倾向于理性。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理性”特质是男性所特有的。然而,在该小说中,作为大学教授的妮娜,却持与该观点截然相反的态度,她认为女性也能够像男性那样理性地处理事情。在德里罗的描述中,与她的情人马丁一样,妮娜总是以长远的目光来理解、处理事情。她利用已有的认知能力对“9·11”恐怖袭击事件从全球性和可理解性角度来解读,她和马丁经常讨论一些与“恐怖活动”有关的话题,为什么会发生恐怖袭击活动?这些恐怖袭击是怎样完成的?当然,这些讨论一般都不涉及个人情感。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研究这个问题。退回一步,思考有关的要素,”他说。“如果有可能,冷静地、清楚地思考。不要让它把你给打垮了。理解它,思考它。”
“思考它,”她重复着。
“有事件,还有人。思考它。让它告诉你什么东西。理解它。让你自己可以面对它。”[6]44
从以上对话可以得知,马丁特别关注“9·11”恐怖袭击事件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试图解读恐怖袭击事件背后的原因并理性看待该事件。当妮娜在与女儿丽昂讨论与“9·11”事件相关的话题时,她与情人马丁一样,理性分析“9·11”事件。在与妮娜的一次对话中,丽昂了解到她母亲已经理性接受了“9·11”事件的发生。
丽昂站在窗户旁边。
“我知道。”
“我以为他死了。”
“我也是这样想的,”妮娜说。“那么多人看着的。”
“以为他死了,她也死了。”
“我知道。”
“亲眼看见双子塔楼倒下。”
“先是一幢,后来是另一幢。我知道,”她母亲说[6]11-12。
妮娜在短短的几句话中便连续使用了3个“我知道”。众所周知,“知道”一词意指一个人掌握了某些知识或是有一定的了解才能对某事从认知的角度进行阐释。德里罗通过对“我知道”3个词的重复使用,旨在强调妮娜总是能够冷静、清晰地处理事情,这一点与马丁极为相似。这说明妮娜也能够像男性一样,理性处事,不感情用事。
最后,夏季玉米单产能够达到600 kg/亩,拔节肥以及基肥和种肥只占总施肥量30%,而攻穗肥要占50%。
相比弗洛伦斯被动地接受男人的怜悯及被男人的随意抛弃,妮娜则更有自己的想法,她主动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人和事,表现出她自己独具一格的特性。丽昂的父亲杰克由于不堪忍受老年痴呆带来的痛苦,用一支老式步枪结束了生命,那时丽昂才22岁还未成家立业。丈夫的自杀并没有让妮娜一沉不振,妮娜选择“坚强”而不是“脆弱”,她积极自我调节。后来,她和一个德国艺术品商人、收藏家马丁保持了20多年的情人关系,尽管妮娜连马丁的真实姓名都不清楚。她和马丁有着同样的爱好,他们两个人对画作的欣赏有着共同点。他们喜欢一起谈论乔治·莫兰迪,“给他看了一本书。漂亮的静物画。形式、色彩、深度。”“他看到形式、色彩、深度、美”[6]157。在丽昂准备和基思结婚的时候,妮娜极力反对女儿接纳基思,拒绝视基思为女婿。妮娜用她理智的头脑去分析:“基思希望遇到一个将会后悔和他在一起的女人。这就是他的风格……他天生就是度周末的”[6]13。妮娜认为基思是一个不负责任、不敢担当的懦弱男人。后来基思的表现应证了妮娜的看法。在“9·11”发生之前,基思沉溺于赌博,不顾妻子和儿子,后来竟然搬出他们共同的家,住在离双子塔——基思办公室所在地,不远的单间公寓。每天下班后,基思就约上几个牌友一起玩扑克,沉浸于赌博的世界中,将丈夫、父亲的责任统统卸下交由丽昂一个人来承担。“9·11”事件发生后,基思脸上还残留着玻璃碎片,但他却选择第一时间回到已经分居的妻子身边,试图修复关系,并与丽昂破镜重圆,过上正常的居家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基思将他捡到的公文包送至其主人时,与公文包的女主人,一名中年黑人妇女弗洛伦斯发生了婚外情,这使丽昂产生了更大的心理阴影。从“9·11”事件发生前后的这一切可以看出基思是一个懦弱的男人,不敢承担一个丈夫、父亲该承受的责任。这些都应验了妮娜的看法,证明妮娜对基思个性的理性分析是正确的。
二、历经灾难,摆脱创伤的弗洛伦斯
与小说的男主人公基思一样,弗洛伦斯同为“9·11”事件的目击者、幸存者。从双塔废墟中逃生后,弗洛伦斯情绪低落,意志消沉,对生活丧失了信心,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一切都被埋葬了,一切都失去了”[6]54。她每天独自待在房间里,“没法见人,没法和别人说话,无法走动,无法让自己离开椅子”[6]117。待情绪稍微稳定后,她意识到自己的公文包不见了,但是她并没打算把信用卡挂失和把驾照注销。在她看来,她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双子塔的倒塌而失去意义,再也没有必要去花心思来整理这些东西。正如丁玫所言,“创伤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个体无法在生存中获得自身存在的证明,从而处在一种迷失的状态”[7]21。
对现代人来说,通讯工具十分重要,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必不可少的工具,尤其是电话。对于弗洛伦斯来说也不例外。可是尽管电话响不停,但她却拒绝接听,拒绝与外界的联系。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事件对创伤主体的影响不是即时的,其反应往往是延后的。它时常主动地以如梦魇、幻觉、闪回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突袭受创主体以提醒自身的时刻存在”[8]11。从双子塔废墟中幸运逃生后,塔楼坍塌、达维娅的死等创伤记忆并没有给弗洛伦斯造成即时的心理创伤。但是,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创伤记忆却挥之不去,如幻觉、梦魇般重复地、持续地入侵,激起弗洛伦斯对往事的恐惧。每当看到贴在墙壁上和橱窗里到处可见的照片,弗洛伦斯总有几分焦虑。她担心白天别人会接听她的电话,便经常在半夜里打电话给意象中的达维娅,并让电话响着。在受到巨大的创伤之后,弗洛伦斯试图与外界隔绝,置身于自己的“孤独世界”之中,痛苦地忍受创伤记忆的折磨。
在受到创伤之后,弗洛伦斯的记忆不像“普通记忆那样编码,不同于日常生活的线性语言叙事”[9]156-57。当她在回忆那场恐怖袭击事件时,她的表达显得混乱、断断续续:“我现在仍然在楼梯上,我想母亲。如果我们活到100岁,我也仍然在楼梯上”[6]60。当她与基斯谈话时,她的表达也同样缺乏逻辑性 :“为什么你的录音机比我的好?”“我看我用过两次”[6]56。当她与其他人交流时,她也不能够准确地分析说话者传达出的意思。除此之外,弗洛伦斯描述事情时语无伦次,时态混用、句式简单、重复啰嗦,言语之间缺乏关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的这些描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而仅仅是她记忆碎片的随机堆积。
创伤带来的阴霾使弗洛伦斯产生了深刻的无力感和绝望感,但是她力图建构起新的自我,并希冀走出创伤。对创伤的治疗起到关键作用的方式是“将创伤的情形和后果通过叙述语言讲述出来,以获得一种宣泄”[10]72。而此时与弗洛伦斯同样经历了灾难的基思的出现,让她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感觉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弗洛伦斯巨大的安慰,她的精神状态有了很大改善。后来,她与基思维持了一段仅有几周时间的婚外情。与普通的偷情相比,他们的这段婚外情是基于对这场灾难有着共同感受的叙述与分享。“他们所共知的,就是在长长的螺旋式阶梯上无尽的漂移”[6]60。她向他倾诉个人情感与内心,将满脑子令人揪心的东西都倾吐出来,如释重负。“创伤主体会留意或寻找环境中的威胁性信息,并处于高度敏感的状态……对相关事件或信息的刺激过度反应”[11]7。他们共同分享那次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忆,死人、燃烧的建筑物、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城市。“那时,有人被埋在瓦砾堆中,到处是变形的钢铁和玻璃碎片,受伤的人坐在那里做梦,他们仿佛是正在流血的做梦者。……我看见一个女人头发被烧了,头发在燃烧、冒烟”[6]62,此时的基斯是一个真正的倾听者,他的倾听让弗洛伦斯重新振作起来。在情感的倾诉过程中,弗洛伦斯逐渐忘记过去的伤痛体验,解建构起新的自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走出了创伤的阴霾,实现了自我救赎。
三、走出创伤,服务他人的丽昂
著名的女权主义者波伏娃指出,“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和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她会表现出和男孩子同样的活力、同样的好奇、同样的开拓进取、同样的坚强”[12]263。与前面两位女性人物不同的是,丽昂的女性形象更加让人折服,面对丈夫基思受到创伤后的一蹶不振,丽昂勇敢地摆脱创伤,表现出如同男性一般的坚强、进取。她不仅承担起自己家庭每一位成员的责任,而且还负责对“9·11”间接受害者的无偿心理疏导工作,勇敢地面对过去、挑战未来。
作为女儿,她秉承孝义,对母亲百般照顾。由于父亲杰克害怕老年痴呆发生在自己身上,选择了用枪自杀,这对丽昂造成了很大的刺激。父亲去世后,留下母亲一人。因担心母亲的种种生活问题,丽昂把母亲接到纽约来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却并没有去干涉母亲妮娜和其情人马丁的生活,尽可能的满足母亲的一些愿望。
作为妻子,她贤惠聪敏,全心全意。“9·11”事件发生前,丽昂的前夫基思就选择与其分居,沉溺于扑克游戏,对家庭不闻不问。但“9·11”发生之后,基思却毫不犹豫的带着满身的创伤,“一个满身尘土、满身碎片的男子”[6]6回到分居多年的妻子家中。对于基思的回归,妮娜强烈反对丽昂再次接受,“小心点儿,他现在情况很糟糕”[6]10。但是丽昂却没有丝毫犹豫,欢迎丈夫的回归,帮助他疗伤、照顾他,并尝试了解基思的思绪,试图让他恢复以前的形象,最后被她的母亲妮娜认可。眼见基思受伤的模样,丽昂倍感心痛,“后来,我们步行去了医院。步行,一步一步地挪动,就像牵着学步的儿童”[6]9。“对他来说,动手写名字有点儿困难,伸手从背后系病员服难度更大。丽昂在一旁帮忙”[6]15。基思回归家庭的几个星期后,丽昂试图谈论起他们复婚的事。当丽昂主动提议“我们有很多话要说”[6]30我们有必要讨论我们复婚的事宜, 基思一口否认道:“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过去常常无话不说……所有的问题,实际上这些都抹杀了我们的关系”[6]30。基思认为,如果他和丽昂复合,他们两个都有可能因为某些行为而“死”。但是,丽昂认为,既然基思重新回归,他一定是想重温家庭生活带来的幸福。因此,丽昂并没有因为基思说出的这些刺耳的话语而放弃复婚的打算。尽管她知道,把丈夫和男人放在一起完全是另外一个词。于是,丽昂明确表明她的态度:为了家庭,他们两个能够避免摩擦而拥有幸福的生活。
作为监护人,丽昂同时扮演着“父亲”和“母亲”的角色。一方面,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她必须努力工作;另一方面,为了儿子在父亲缺席的情况下能够健康成长,她时刻关注儿子的思想动态,尽管有时会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而劳累至极,但她从未放弃过。她会时常带儿子去书店,享受凉爽和清净,“他们乘自动扶梯上了二楼,待了一会而,浏览了科学、自然、国外旅行和文学图书”[6]202。也会时常关心儿子的学习状态,“你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呢?从你开始上学以来”[6]202。自从双子塔倒塌后,儿子贾斯廷的心里也受到了创伤,和他的小伙伴时常用望远镜观察天空,看是否会有恐怖活动发生。“这事儿肯定和比尔·洛顿有关……因为望远镜是这帮孩子所卷进去的整个秘密综合征的组成部分”[6]37。为了尽可能减轻儿子的焦虑,丽昂及时了解儿童眼中的“比尔洛顿”,试图引导儿子少说单音节词语,和儿子调侃、开玩笑。“太阳是一颗恒星。……这可不是你在学校里学的哦。我告诉你的哦……”[6]203。这样的调侃看似有一点戏谑的意味,实际上包含着母亲对儿子深深的爱。在丽昂和基思的引导下,贾斯廷逐渐减少了单音词词语的运用,词与词之间几乎没有停顿,说话也变得顺畅、流利。
作为一个社会人,丽昂在关注自己家庭成员的同时,更是毫无怨言地做起社区义工工作。面对一群阿尔茨海默病人时,丽昂扮演着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在面对基斯的时候,她仍然扮演着同样的角色,因为她清楚地知道 :“倾听和讲述现在是挽救他们的办法”[6]112。她努力帮助别人走出创伤,她经常组织那些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讲述个人经历,并将这些内容一一记录下来,“通常,她和组员们讨论,谈一谈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和他们生活中的事情,然后分发印有格子的便签纸和圆珠笔,让他们写作文”[6]30。她尊重这些老人,与他们建立联系并互相理解。在一次又一次的倾诉中,老人的焦虑得以释放,精神获得解脱。在倾听的过程中,老人们同样要求丽昂将她自己的经历说出来。通过相互倾诉,丽昂也得到了释放。正如心理学家奈杰儿·亨特(Nigel Hunt)说的那样:“人都善于叙事,并且成为一种需要。而正是通过讲述,可以建立叙事、自我和身份的联系,并有助于创伤者在社会环境中形成对自我和身份的认识”[13]115。
结论:
“9·11”事件的发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对普通的美国人造成了严重的创伤。在面对这些创伤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态度。其中,大部分女性不是自甘堕落而是积极治疗创伤。在男性不负责任甚至缺席的情况下,女性们勇敢承担起对个人、家庭、社会的责任。妮娜保持了乐观向上、自得其乐的状态;弗洛伦斯忘记过去的伤痛体验,建构起新的自我,重拾对生活的信心,走出创伤的阴霾,实现自我救赎;在其他人的鼓励及自我救赎的作用下,丽昂看到重生的希望,重构自我,和贾斯廷一起恢复“9·11”事件以前的生活。这3位女性虽然受过创伤,有过迷惘,但是她们能鼓起勇气振作起来,重构自我,回归正常生活,在家庭、社会、人类等不同的舞台中展现出了女性应有的风采与价值。
[1] 张加生. 从德里罗“9·11”小说看美国社会心理创伤[J]. 当代外国文学, 2012 (3): 77- 85.
[2] 李 静. 论《坠落的人》中的人物特征及意义[J].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 2013 (1) :149- 51.
[3] 张丽丹, 张薇. 德里罗新作《坠落的人》的后现代写作技巧[J]. 时代文学, 2011 (12): 116- 17.
[4] 但汉松. 9·11 小说的两种叙事维度: ——以 《坠落的人》 和 《转吧,这伟大的世界》 为例[J]. 当代外国文学, 2011 (2): 66- 73.
[5] 方刚, 罗蔚,主编: 社会性别与生态研究[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6] 唐·德里罗.坠落的人[M]. 严忠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7] 丁玫. 艾·巴·辛特小说中的创伤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2.
[8] Caruth, Cathy.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 11.
[9] Herman, Judith. Trauma and Recovery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10] 柳晓. 通过叙事走出创伤─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J]. 外国文学, 2009 (5): 68- 74.
[11] 赵冬梅. 心理创伤的理论与研究 [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12] 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13] Hunt, Nigel. Memory, War and Trauma [M] .Cambridge, UK. New York: Cambridge UP. 2010.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in Female Images in Don DeLillo’sFallingMan
LUO Jiao-hu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Hunan, China)
DeLillo portrays some typical female images in his novel,FallingMa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ree main female characters, namely Nina, Florence and Lianne through the close reading to the novel, pointing that the three females, who are rational, strong, brave and responsible,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New Ag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se females, DeLillo reveals tha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9/11”, males are inclined to become slattern. However, females have the courage to undertake responsibilities of all aspects. The novel is aimed at praising females’ new image.
FallingMan; Reason; Strongness; Responsiblity
2014-10-05
罗姣惠(1989- ),女,湖南邵阳人,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本论文是湖南科技大学2013年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德里罗‘9·11’小说中的女性气质研究”(编号:S130041)的阶段性成果。
I106.4
A
1672-4860(2015)02-005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