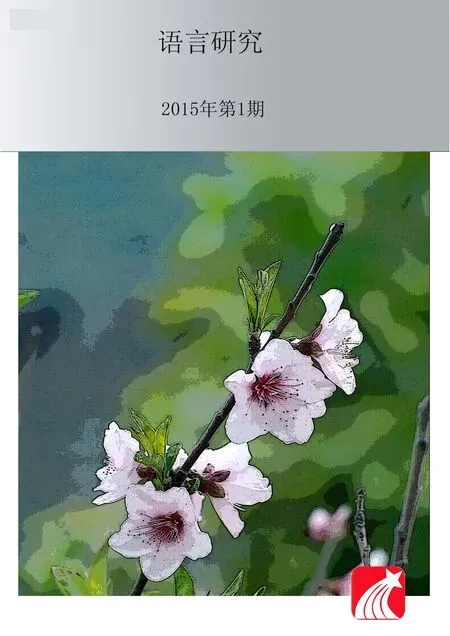方以智“謰语”问题辨察
2015-02-09沈怀兴
沈 怀 兴
(宁波大学 中文系,浙江 宁波 315211)
近20多年来常有人以明代方以智“謰语”比“联绵字-双音单纯词”,用方氏謰语说支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虽有人提出疑义,然片断之言终未引起学界注意,而“謰语”疑案成。又由于人们现代联绵字观念之成见在胸,多不深入考察方氏的謰语研究,致令一些误传日渐流行,本来悬而未决的“謰语”疑案又添几重疑云。特别方氏“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之说,更是众说纷纭,而未见确诂。本文拟在区别中国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语言学①本文“传统语文学”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前研究汉文献中语言文字应用问题的学问;“现代语言学”是狭义的,特指1898年以来研究汉语本体的学问。的基础上,考察方氏謰语观及其謰语研究。
一 各类现行辞书对“謰语”的误释
术语“謰语”是明代方以智创造的,今人又给予解释,却与方氏之释很不同。下面先选录几部较有代表性的辞书对“謰语”的解释。辞书释义简明而力求反映共识,引它们的解释具有普遍意义,且可节省篇幅,同时讨论起来也可以更自由些。
(1)謰语,也作连语。这个词见于明代方以智《通雅》卷六《释诂》。方以智说:“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謰謱即接连不断的意思。指两个字合成为一个词,不能拆开来讲。《通雅》书中所讲的都是双声词,但是两个字为叠韵的也属于“謰语”一类。例如“黾勉”、“玲珑”、“慷慨”、“消息”都是双声词;例如“苍茫”、“从容”、“殷勤”、“婆娑”都是叠韵词。这些都是不能分开讲的。“謰语”现在通常称为“联绵字”或“联绵词”。(《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2)謰语,即“联绵字”。(《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其释“联绵字”曰:“由两个音节联缀表达一个整体意义、只含一个词素的词。”
(3)謰语:连语。也叫联绵字、联绵词。(《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3年)其释“联绵字”曰:“旧称由两个音节联缀而成的单纯词。”
(4)謰语,同“联绵词”。如明代方以智《通雅》卷六:“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其释“联绵词”曰:“除叠音词、象声词、叹词以外的汉语固有的双音节的单纯词。”
(5)謰语,有时指“联绵字”。明方以智《通雅·释诂·謰语》:“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并指出理解的途径是“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古汉语知识词典》。中华书局,2004年)
以上选录了近20多年间出版的各类较有代表性的辞书对“謰语”的释义。前四家都认定“謰语”即“联绵字/词”,指一个词素构成的双音词。解释(5)说“謰语,有时指‘联绵字'”,表明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流行观点持保留态度。但从它认为“謰语,有时指‘联绵字'”、只是抄下方以智部分话语而不作必要的解释、更不说明“謰语”一般指什么等表现看,似乎并没有弄明白“謰语”的实际含义(“謰语”含义详后),没有把握解释清楚,所以读者也只能见仁见智,至少笔者所询问同行的情况是这样。这说明,虽然方以智“謰语”在2003年之前各家解释都是“謰语=联绵字=双音单纯词”,但仍有不同认识,因为解释(5)是1996年版的修订本。再向前考察,还可发现对这个“謰语”的理解,早有人提出不同于主流派学者的认识,如李运富(1991)认为方以智的“謰语”指复音词。但由于未进行穷尽式考察分析,亦未作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主流派学者继续坚持“謰语=联绵字=双音单纯词”的认识,上引解释(3)、(4)的解释都反映了这一事实。以上种种情况表明,方以智“謰语”问题在目前汉语言文字学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还是一桩疑案。
其实,只要弄清了传统语文学与现代语言学的根本区别,就可断定方氏“謰语”不指双音单纯词,方氏謰语观不支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1)古今联绵字观念截然不同。方以智类聚謰语的目的是为了方便求学者“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方以智《謰语》题解),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从复音词中辨认出单纯词来。(2)“单纯词”、“词素”等都是现代学者研究语言本体的概念。研究语文应用问题的方以智本不需要这类概念,现代语言学未出现以前的汉文献中也找不到这些概念①曾有人从前人著作中搜寻了不少说法,支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但那都是对前人之说的误解(沈怀兴2007、2008a、2008b、2008c、2011a)。,方以智“謰语”没有指双音单纯词的可能。(3)词素理论引入我国还不到一个世纪,辨认汉语词素更是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难题(沈怀兴2009a、2010a、2010b)。照理说,明代方以智没有可能掌握词素理论并准确地用于謰语词素判断。如果“謰语”今释不误,人们无法知道方氏是怎么从复音词中辨认出单纯词而名之曰“謰语”的。(4)方以智謰语研究走的是辨通假而因声求义的训诂学道路,与现代词汇学分析词的词素构成没有相通之处,由此决定了其“謰语”与“联绵字-双音单纯词”无可比之处。
另外,在中国语文学史上,从方氏《通雅》到朱起凤《辞通》,近300年间有清魏茂林《骈雅训纂》、清陈仅《诗颂》、清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清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清邹汉勋《敩艺斋文存》、清黄遵宪《与官严又陵总办书》、民国刘大白《辞通序》与林语堂《辞通序》等都用过“謰语”这一术语,但没有一家用“謰语”指双音单纯词。如果说方以智所创“謰语”指称双音单纯词,为什么这个“謰语”在后人笔下却无一指双音单纯词?而今已考见方氏謰语中合成词和词组占91%以上,就更该对此前流行观点进行认真反思了。下面公布对方以智《通雅》所辑謰语的考察结果。
不包括其卷八《謰语》中“钩章棘句”一节②“钩章棘句”一节所收的词,方以智批评它们“皆对《广韵》抄撮而又颠倒用之”,故不宜统计在内。,《通雅》中共收 534个/组謰语③仅算其常体是534个,包括其变体是534组。这个数字比此前各家统计的355个/组多179个/组。盖因此前各家按方氏之书的章节统计的,一节书算一个/组謰语,实际上方氏之书中不少章节不止一个/组謰语。,其中只有镗鞳、萧瑟、呕喁、隐振、邪揄、拨剌、呫嗫、讘吺、劳利、唅呀、砰磅、訇礚、澎湃、噌吰等14个单纯词。但它们都是拟声词及拟声而来的词,不是“汉语中特有的一种语言现象”,《现代汉语词典》释“联绵字”不包括这类词,上引解释(4)释“謰语”还明确排除这类词,所以它们不支持上引各家之释“謰语”。现在把其余520例謰语的考察情况一一录下,其中合成词和词组486例,依它们在原书中的先后顺序是:
仿佛、恍惚、彷徨、仓皇、惝恍、洸洋、徘徊、寂寞、寂寥、拉杂、旖旎、俯伏、匍匐、逍遥、招摇、飘摇、譸张、犹豫、坎坷、纷纭、坱圠、怗懘、晻霭、奄忽、嘈杂、夸毗、依违、栖迟、陵夷、咇茀、旁薄、参差、彳亍、颠覆、夷犹、怫郁、绰约、屏当、龃龉、蓬勃、浩瀚、风采、憔悴、抑郁、慷慨、岂弟、陵厉、从容、闪灼、专一、迫蹙、侵寻、辜较、料简、臬兀、累丸、功苦、杳眇、落魄、条畅、离娄、谅阴、旁历、陪游、不庭、蒂芥、径庭、峰距、旅距、销距、储置、狥齐、锲薄、秒忽、闵勉、佚荡、槁暴、逢俉、寤生、晤谢、朗悟、侘傺、漫衍、舛驳、奊诟、屑越、彫攰、恇扰、偃仰、辟倪、遮迾、阿邑、璀璨、刓弊、负兹、窊隆、背依、怐瞀、涵流、磋磨、墟厉、卓荦、渗漓、卉歙、軋忽、流落、剥落、寥落、磊落、脱落、濩落、彫落、篱落、薄落、错落、孟浪、茬蘖、由蘖、憋怤、怀挟、句驳、驳异、缧绁、淫佚、慢侮、沖澹、赘顤、巽懦、柔耎、怯懦、骏厖、赘瘤、窈窕、窈纠、窥窬、离纚、捉搦、蹑蹀、遵循、缺望、宴嬉、抵巇、皮附、收债、债家、踵继、仰繋、雁行、証向、证辞、辩诉、马逸、轶事、硕画、石交、目击、慑服、局促、仓卒、零落、总揽、濯灶、木偶、夙夜、夙心、摇刖、雍睦、迫急、小极、砥砺、渐靡、堆髻、肥硗、跂匡、蔽山、傍河、元祺、奇辨、奇人、奇事、剺面、拳握、抹杀、惰懒、笞骂、靡节、弭耳、敉定、神宅、黎民、良民、兆民、海滨、沉霾、勉咨、分别、蠲洁、磨鑢、履隟、辜穰、回遹、孕育、释荣、盥洗、斋肃、决骤、遥度、遥谓、遥言、妖冶、桃棓、操棓、踊跃、纰缪、疑怍、悚慄、疲惫、渐渍、绸缪、掊克、裒取、亵凟、惯黩、讙哓、凿说、襍错、举错、狃恃、周流、虚廓、肥遯、畏用、无垠、南讹、笄纚、是正、相徇、斥执、踶跂、缀兆、宝祠、保就、专己、呪诅、蓑城、冀幸、希觊、序正、裁察、裁哀、资材、廉倨、贵倨、倨傲、解后、豁达、失策、襐饰、布护、才諝、消灭、败秽、淫湎、晕、华洞、宛卷、畜积、诋诃、鹵莽、拮据、露袒、附娄、崔巍、崎岖、嶻嶪、嵚崟、巉喦、渟瀯、磝硗、较.若.、沱.若.、介.然.、撊.然.、坦.然.、憮.然.、魁.然.、肸.然.、揣.然.、洒.然.、侐.然.、瞿.然.、萧.然.、释.然.、尘.如.、率.然.、确.然.、嶷.然.、巍.然.、侃.然.、骚.然.、喟.然.、慨.然.、煟.然.、蹙.然.、茫.然.、俯.然.、赩.然.、累.然.、颓.然.、铿.尔.、莞.尔.、率.尔.、皤.如.、翰.如.、勃.如.、俛.焉.、宣侈、婚姻、恭寅、亲巡、亲戚、馨香、百穀、长宝、山陵、喷玉、阴阳、倔强、万物、归藏、礽坤、峻峭、牵挽、潮湿、平燥、萧晖、固辞、职方、比蹤、黎庶、民隐、景响、硺磨、壅遏、络绎、駌雏、谭恩、苞组、后昆、遮几、奈何、铄灼、典坟、庭坚、张掖、图籍、儒术、一篑、胪占、左股、盇簪、淫朋、平章、平秩、有蠢、迈相、洮頮、庶狱、楙迁、审核、楙简、楙建、乃逸、乃谚、既诞、无皇、耿光、惩忿、室欲、拖绅、三嗅、孚尹、嚚讼、犒饫、孳尾、掌讶、吉凶、耗斁、耗殬、执竞、朵颐、滂沱、竹秘、溢我、载旆、小雅、朋淫、朋来、绿衣、宜饇、见晛、渥赭、靡膴、治兵、贯女、协用、谟训、尹告、姻娅、无竞、无斁、设席、绿竹、盱豫、如燬、大诰、拾级、陨穫、刊木、棐忱、咏号、雠敛、沉潜、煴隆、调飢、觞之、跋涉、重乔、子衿、鸣鴃、小弁、栗薪、奏假、拯马、有奭、用圭、裒多、撰德、新台、大眚、渝平、要会、终始、得失、排斥、戾、提携、忧愁、惠爱、率由、散乱、审视、周旋、假借、鬼神、畴咨、称谓、微细、中逵、甄陶、勇敢、怀抱、徒从、徂往、饕餮、敷施、移予、徵羽、照耀、飞扬、性情、周匝、廉纤、庄逵、玄纁、流苏、斑阑、秋千、表著、讹言、古冢、嗟咨、酬酢、期颐、扬之水、勿剪勿扒①所录謰语均按它们在原书中先后顺序排列,且多录其常体。但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常体有僻字时录其变体。“常体”、“变体”二术语下文将多见。如《通雅·释诂》卷七《謰语》:“偃佒即偃仰,古作偃卬”、“旦宅即神宅”、“孕育,一作嬴育”等,其“偃仰”、“神宅”、“孕育”等是常体,“偃佒”、“旦宅”、“嬴育”等是变体。除了方氏订误者,其变体主要由近音或同音假借而来,少数是异体字。如果不与“常体”相对,“变体”指一个謰语的所有书写形式。
待考者34例,依它们在原书中的先后顺序是:
逶迤、徜徉②若依古注,“徜徉”和下面的“盘桓”都是合成词,但还要做补证,为节省篇幅,也为了不引起无谓的争论,暂把它们归入待考类。、傝䢇、次且、靉靆、戚施、蹒跚、盘桓、肸蠁、萧条、萧森、茈虒、酩酊、龙锺、优游、愺恅、扊扅、胶葛、混沌、汍澜、毰毸、䀒瞑、劻勷、抢攘、征营、絜楹、扶疏、氤氲、岣嵝、峥嵘、嵻崀、閜砢、蹁跹、斯赵
上录《通雅》中謰语多是复合词,其次是词组和派生词(上录謰语中加着重号的37例都是派生词)。《通雅》中謰语共534例,上录合成词和词组共486例,占其全部謰语的91.0%以上。其余48例,即上录拟声词及由拟声而来的词14例,待考者34例。至此,只能说上引各类辞书反映流行观点而对“謰语”的解释与事实不符。
也许有人问:会不会在待考的謰语中有合“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的謰语?不会。(1)以“謰语”比“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而91%以上的謰语是合成词或词组,很难想象唯独那34个(仅6%强)待考者可支持其观点。(2)所谓待考,是因为材料不足,暂时不能确定其语素构成情况而存疑,条件具备之后会弄清楚的。如本文第一稿中待考者37例,近一个多月以来又考见夷犹、拮据、饕餮三例是合成词,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有新材料证明待考者中哪个謰语也是合成词,所以没有理由拿它们来比附时下流行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3)以“謰语”比“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者多相信上古汉语里有一种创造双音单纯词的特殊构词法之说,而不知此说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想象,一直未得到确证(沈怀兴2009a、2010c、2011a、2011b)。就《通雅》所辑謰语说,其待考者现在虽有34例,但随着材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的深入,最终即使还有个别词继续待考,而一种构词法也不可能只创造出个别词。(4)原来被认作“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而后来被证实是合成词的例词很不少(白平2002:172-208;沈怀兴2009a、2009b、2010a、2011a、2011b),连上引解释(1)的例词也无一靠得住。
上引解释(1)所举的“黾勉”、“玲珑”、“慷慨”、“消.息.”、“苍.茫.”、“从容”、“殷.勤.”、“婆娑”等八个例词中带点的三个都是合成词,一看便知,无需考辨。“慷慨”和“从容”也都是合成词(沈怀兴、周秋江2007,沈怀兴2006)。黾勉,《诗·邶风·谷风》:“黾勉同心,不宜有怒。”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黾”字下认为“黾勉”的“黾”是“忞”的假借字。《说文·心部》:“忞,自勉强也。”《力部》:“勉,强也。”据此,“黾勉”乃是同义词联用构成的合成词①还有,《尔雅·释诂》:“勔,勉也。”《经典释文》卷二十九《尔雅音义上》:“勔,字本作‘僶',又作‘黾',或音泯。”据此,“黾勉”也是合成词。另外,据清王玉树《说文拈字》所引孙季昭《示儿编》之说或李谨(1987)的观点,或周啸天主编的《诗经楚辞鉴赏辞典》的观点,“黾勉”都是合成词。。“玲珑”由拟玉击声而来,拟声词不为汉语所独有。婆娑,《诗·陈风·东门之枌》:“不绩其麻,市也婆娑”。其“市也婆娑”,《说文·女部》“娑”下引作“市也媻娑”。《说文》无“婆”字。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释“媻”曰:“或作‘婆'。”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通检》于“婆”字下曰:“篆作‘媻'。”《广韵》戈韵释“婆”、“媻”同音,均为薄波切。以上证据表明:“婆”是“媻娑”之“媻”的后起字,亦即“媻”之“奢”义的后起分化字。《说文·女部》:“媻,奢也。”“娑,舞也。”《奢部》:“奢,张也。”然则“婆娑”即“奢舞”,亦即大舞、尽情舞。据此,“婆/媻娑”也是合成词,也不支持上引例解释(1)释“謰语”的观点。这样说来,上引解释(1)释“謰语”所举例词都不支持其观点。
至于“不能分开来讲”之类的说法,乃是对前人“不可分训”说的误解(沈怀兴2008b),故不能做辨认一个双音词是不是单纯词的标准。否则,就难免误用合成词词义的整体性证明合成词是单纯词,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其实,以“不可分训”为标准辨认词素没有可操作性,于实践中行不通。吕叔湘(1984:490)说:“辨认语素跟读没读过古书有关系。读过点古书的人在大小问题上倾向于小,在异同问题上倾向于同。”那么,究竟是哪些“不能分开来讲”的词可判作双音单纯词?实际上,联绵字词素判断需要很多方面的知识,是一种理论性较强、专业功夫要求较高、难度较大的工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至今学界未能彻底解决双音词词素判断问题。上引吕先生的话大致反映了这一事实。又如《现代汉语词典》1960年出试印本,本着现代联绵字观念解释“联绵字”,所举六个例词,到1965年出试用本就发现“匍匐”、“凤凰”、“砝码”不是双音单纯词而换掉了。试用本的六个例词至今未换,但《汉语大词典》卷八(1991)释“联绵字”抄了它五个例词,发现“妯娌”不是单纯词而未抄,让非双声非叠韵的“联绵字”只一个例词。可是,为什么浩瀚的汉语词汇里只有一个非双声非叠韵的联绵字?是补不出呢还是不敢补?其实,《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公认的那五个联绵字例词实际上一个也靠不住(沈怀兴2010b)。
综上所述,上录较能反映“共识”而较有代表性的各家现行辞书对“謰语”的解释都靠不住,目前学界流行的“謰语”指双音单纯词的观点不成立②本文只论事,不对人,凡所否定的学人观点暂不列出处,但为避免无中生有之嫌,同时也为了方便欲核实引文或继续研究者,被否定的著作将在参考文献中一并列出。下文此类情况不再作注。。
二 方以智对“謰语”的解释
方以智《通雅·释诂·謰语》共三卷:卷六至八。卷六之首有167字的《謰语》题解:
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新书》有“连语”,以许氏加“言”焉。如崔嵬、澎湃。凡以声为形容,各随所读,亦无不可。升庵曾汇二字,楚望亦列双声,弱侯略记骈字,晋江苏氏韵辑骈复,俱宗杨本。江右张氏《问奇》特编而定其音读,谷城从而广之,朱氏《指南》、艮斋《字学》皆揭此例,然多抄升庵,守以字学钩釽之说。惟郝公主通,然未免强合。故因摲其支离,补其遗漏,前后见者,偶从部居。此举成例,列于左方,以便学者之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也。
近20多年来对这段话多节引者,其说解则与方以智本意或不沾边,或相去甚远。其实,方氏这段话是先给“謰语”下定义,指出謰语的特点(详后),继而交代“謰语”名称的由来,并举了两个謰语之常体为例。接着又侧重謰语变体指出:“凡以声为形容,各随所读,亦无不可。”意思是说:凡以声通义的謰语变体,只要依据其音转规律知其所通之义,即使各随所读也可以。如《通雅·释诂》卷八《謰语》:“崔嵬,一作陮隗、隗、嵲隗,或用畏隹。平声。亦上声。崔,别作㠑、陮、;嵬,别作隗、囗、畏。《庄子》:‘山林之畏隹。'乃倒用‘嵬崔'也。司马注:‘隹如崔字。'可知皆声通形状之辞也。”“皆声通形状”即“陮隗”等均“以声通义”,以其读音通“崔嵬”之所指。因此,只要照“崔嵬”之所指理解,而不“守以字学钩釽之说”,即使“各随所读”也没关系。很明显,方以智这里讲的是文字通假问题。又如:“澎湃,一作滂沸、滂沛、澎濞。《文选·上林赋》:‘汹涌澎湃。'《史记》作‘汹涌滂沸'。又与‘滂沛'通。司马彪又引‘澎濞'。”方以智的考证是说,这“滂沸”、“滂沛”、“澎濞”都是“澎湃”之通假体,只照“澎湃”之所指理解就可以了。有人认为方氏“凡以声为形容……”云云是在讲一种语音造词法,并与“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扯上关系,曲解联绵字多种书写形式。果如其解,便是方以智不惜割裂文义,在举謰语之例词与叙述前人研究情况之间硬插进一段讲造词法的话了。其实,其“声”指字音(“各随所读”的只能是字音),这里指謰语各变体读音。方氏此言是从用字角度说的,不是从造词角度说的。一个词造出只有一次,时移地异而用字标记则有多种,所以如果像方以智研究謰语重在辨通假而不计时地之别那样,一般复音词都可能列出不止一种书写形式。如上文统计结果表明,《通雅》所收謰语中 91%以上是合成词和词组,而无一不具有多种变体,即其最少的两种,最多的 32种,而像卷八《謰语》收词组“一篑”四个变体、收复合词“平秩”五个变体、收派生词“较若”五个变体者很不少。从“一篑”、“平秩”、“较若”都被方以智列为謰语看,方氏“謰语”不指“双音单纯词”,其“凡以声为形容……”云云也不是在讲一种语音造词法。实际上,如果研究者不受现代联绵字理论观念的束缚,则很容易理解方以智的话:立足謰语常体之所指看其变体之所指,都是“以声为形容”,亦即都是以声通义,故“各随所读,亦无不可”。至于上录《謰语》题解中两个例词:“崔嵬”是联合式合成词(白平2002:181-182);“澎湃”照一般的说法是个拟声词,由拟波浪撞击声而来①这里是暂从众。如果从方氏所录“澎湃”的三个变体“滂沸”、“滂沛”、“澎濞”看,也许将它判为联合式合成词好一些。但为了不在此末节上引起无谓的争论,这里暂从众,把它算作拟声词。。它们都不能证明“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
接下来,方以智简单叙述了前人的研究,指出一些人习惯守以字学钩釽之说,只有郝敬主通假,但“未免强合”。于是方氏本郝敬“主通”思想而纂辑謰语,同时避其“强合”,“摲其支离,补其遗漏,前后见者,偶从部居”,以便求学者“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这“前后见者,偶从部居”是说把一个謰语不同的变体列在一起。如上引“崔嵬”,方氏把前后所见的五个变体依次列在一起,分别指出出处;上引“澎湃”各变体亦如此安排。所以把一个謰语的各种变体列在一起,是为了方便求学者“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方氏言“以声为形容”、“声通形状”,均与“以声通义”意思相近,都是在讲文字通假问题,亦即在讲用字问题。
现在来看方氏“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之说。就现代学者的解释看,大多在对其“双声相转”的理解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这个“双声相转”其实是站在謰语变体与常体之对应字声韵联系角度说的,应当作整体理解,而且不限于今所谓声母不变韵母变的“双声相转”。方氏遵循“主通”思想类聚謰语,“前后见者,偶从部居”,“以便学者之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因此,从传统语文学之辨通假而因声求义的角度看,这个“双声相转”的“双声”只能是就謰语常体与变体对应字之语音联系说的。参考前贤的理解(详后),这个“双声相转”指(大部分)謰语常体与变体对应字间有音转关系,就用字而言则是近音通假关系①《通雅·疑始》:“音有一定之转,而字随填入。”指出了音变字易规律,但方以智在辑录謰语时没有细分通用与假借,只是在“主通”思想主导下将謰语各变体“前后见者,偶从部居”。这里暂不区别通用、假借,一律称“通假”。。它既包括謰语常体与变体对应字之声母不变而韵母变的双声相转,也包括其声母变韵母不变的叠韵相转。否则,如果遇到(卷六《謰语》)“混沌,一作……困敦”之类常体与变体对应字声转者则不容易解释。考察《通雅·謰语》,可知其“主通”思想主导下“偶从部居”的謰语之常体与变体对应字也的确多有音转关系,就文字而言即多为近音通假关系(参看后文各例)。另一部分謰语常体与变体对应字间主要是同音通假关系,如卷八:“葆祠即宝祠”、“绪正即序正”、“财察即裁察”、“淫缅即淫湎”等。少数变体是用了异体字,极少数是被古人写了错字,方以智给予指正,严格说来它们不是謰语变体。至于其总说“双声相转”,而实际上有些謰语常体与变体对应字同音,原因可能是这样的:(1)除了少数变体用了异体字之外,这些同音变体都由同音通假而来,在通假这一点上,它们与近音通假之性质是一致的。(2)有音转关系者居多,可举以赅其余,毕竟方以智研究謰语的目的是辨通假以“便学者之因声知义,知义而得声”,考察其对应字间的语音关系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上引解释(1)《中国大百科全书》解释“謰语”曰“《通雅》书中所讲的都是双声词”,大概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于是望“双声”而生训,致令“相转”无着落。它没有发现方氏《謰语》题解里第一个例词“崔嵬”就是叠韵词,也没有发现正文中收了那么多叠韵謰语和准叠韵謰语,同时还收了一些非双声非叠韵的謰语,如其马逸、骏駹、飘忽、畏用、总揽、渐靡、虚戾、比踪、协用、萧然、确然、骚然、蹙然、俯然、扬之水等。至于有人说《通雅》所收謰语中的双声词或叠韵词之声韵联系都由“双声相转”而来,亦缺乏可靠的证据:(1)方氏书中没有交代,也无从交代,因为多数謰语上下字的语音联系早在造词之初就确定了。(2)汉语言文字学史上第一篇研究“异音复词”转变为双声词或叠韵词的文章是沈兼士的《联绵词音变略例》(1941),此文主要得力于作者掌握了现代语音学的同化理论,而这在方以智却无法做到。另外,这样说对《通雅》中所收的非双声非叠韵的謰语也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因为方以智的“双声相转”是管着所有謰语的。
方氏“謰语,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之说中的“而”是连词,表示轻微转折。因此,“双声相转”、“语謰謱”不能颠倒顺序理解和解释;有颠倒作解者,必是没有深入研究“双声相转而语謰謱”的意思,甚至是现代联绵字观念之成见在胸而没有注意推敲此处“而”字的用法和意义。
“謰謱”也较费解。上引解释(1)《中国大百科全书》之释曰“接连不断的意思”,代入“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之中则不成话。联系它前面说“《通雅》书中所讲的都是双声词”,说明它把“双声相转而语謰謱”理解为“双声词而接连不断”了。这显然不是方以智的意思,而是比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的结果。其他各家解释均不见于方以智“謰謱”其他用例,也都不能代入“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之中,故此“謰謱”当另有解。清俞樾《群经平议》卷二十三议《春秋公羊传》“夫人不偻不可使入”云:“人相牵曳谓之偻,犹丝相牵曳谓之缕也。《说文·辵部》:遱,连遱也。《言部》:謱,謰謱也。行步相连谓之遱,言语相连谓之謱。”《说文·言部》:“謰,謰謱也。”然则“謰謱”是同义词联用构成的合成词,义为“相连;连在一起”。古代文献中“謰謱”用例较多,作“相连;连在一起”讲的不少。如清祁寯藻《中秋感怀》诗:“两篇謰謱手自写,相见肝肺森槎牙。”俞樾《德清重建留婴堂碑》:“可怜语謰謱而莫辨。”方以智著作中也不乏“謰謱”用例。如《跋直之弟所临颜帖》:“噫,屋漏痕,岂徒以书法謰謱哉?”又如《东西均·尽心》:“上者解悟,其次证悟。不能,必大困而后彻。不至悬崖,又安有复苏之事哉?此虽謰謱,听者无益。”上述各例中的“謰謱”都是“相连;连在一起”义。其“双声相转而语謰謱”的“謰謱”含义同此,作“相连;连在一起”讲较好。然则“语謰謱”即謰语各字须连在一起,依其音转规律照其常体之所指作整体理解。这是对“守以字学钩釽之说”错误做法的纠正,在正文中也有反映,如《通雅·释诂》卷六《謰语》“逶迤”条下列出“逶迤”32种变体后指出:其形体“各异,其连呼声义则一也”。这分明是在强调词义的整体性,是对前人训诂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明代朱郁仪《骈雅序》有“联二为一,骈异而同。析之则秦越(一本作“吴越”),合之则肝胆”之说,清人魏茂林《读〈骈雅〉识语》解释说:“郁仪自序所称‘联二为一,骈异而同',此即古六书同音相代,同义互训之旨。”那么,本来两个字同义,只是为适应表达的需要而“联二为一”,所以不可分训,亦即不能对其二字作出不同的解释;或者本来“同音相代”,是假借字,所以不可“守以字学钩釽之说”,而望文生训。
到了方以智,认识到一般多字组合(复音词或词组)都有词义的整体性特点,于是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派生词、多音节词(或词组);而且研究方法也不同于前人之“守以字学钩釽之说”,即以其各变体对应字的音转关系类聚其謰语变体,于是放弃已有的“骈字”、“联绵字”等术语不用,将其研究对象名之曰“謰语”。还在《謰语》题解中指出謰语常体与变体对应字有音转关系,但不是单字表义,而是复字“语謰謱”,不可望文生训,以免破坏了词义的整体性。又于正文中对前人解释复音词而有悖于此者予以指正。如《通雅·释诂》卷六《謰语》第一条“彷彿……方物”下批评“旧说‘不可方物'为‘不可比方其物'”为“臆决”,第二条“逶迤……委迆”下对不知“逶迤”不同变体均“以声通义”而望文生训的表现作了批评,稍后在“飘摇……票鹞”条下又批评杨慎“主荀悦去声,以‘票鹞'取名武猛,不知古人不拘”,等等。不难看出,方氏“语謰謱”就是继承和发扬朱郁仪训诂学思想,强调謰语词义的整体性。特别其变体,定要各字连在一起照其常体之所指作整体理解,而不可望文生训。其实,方氏强调謰语词义的整体性,道理很简单,即任何一个复音词的含义都不是其各字意思的简单相加,词义的整体性与词素构成的非单一性正是合成词相互依存的两个基本特点。从这个角度说,以方氏“謰语”比“联绵字-双音单纯词”,不经意间是把合成词词义的整体性作单纯词的判断标准了。
顺便一提,释“语謰謱”为“两个音节、两个字共同表义,不可分训”,容易被误解。因为今持“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者多不知道前人是从词义的整体性角度讲复音词不可分训的,不知道在前人意识里并非只有双音单纯词不可分训,不知道造成大量的双音词不可分训的原因有很多(参看下文)。
总之,“謰语者,双声相转而语謰謱也”是说:謰语变体与常体对应字有音转(或同音)关系,从用字角度说是近音(或同音)通假关系;构成謰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须连在一起照其常体之所指作整体理解。要之,謰语是变体与常体对应字间有音转(或音同)关系、其各字必须连在一起作整体理解的复音词或词组。
上面的理解对不对呢?试看《通雅》謰语实例:
1) 木禺即木偶。《刘表传》:“表欲卧收天运,拟踪三分,其犹木禺之于人也。”《汉·郊祀志》:“木寓龙,木寓车马。”寓即偶也。《史·殷记》“武乙为偶人”,《孟子》作“俑”,则“寓”之转声也。
例 1)中“木禺即木偶”、“寓即偶也”、“‘俑',则‘寓'之转声也”等数语体现了方氏对其音转关系的观察。方氏据以说明“木禺”、“木寓”都是“木偶”的变体。从读音方面说,“禺”、“寓”等都是“偶”的通假字,“木禺”、“木寓”与“木偶”是同一謰语,可照“木偶”之所指作整体理解。这个例子特别对正确理解方以智的“双声相转”的“声”很有帮助。如“偶”虽从“禺”得声,但魏晋时已同声不同韵,方氏认定《刘表传》中的“木禺”即“木偶”,就是因为它们同义,且其对应字“禺”、“偶”有双声相转关系。再说例中谓“‘俑',则‘寓'之转声也”,其“声”指字音,不只指声母。方氏“双声相转”中的“声”同此,指字音,不只指声母。特别“寓即偶也”、“‘俑',则‘寓'之转声也”等表明其“相转”指变体与常体对应字间有音转关系,而不是謰语上下字间有音转关系。下面各例多有这样的表述。
2) 黎萌即黎民,良萌即良民,兆蒙即兆民。《管子》:“其人力同而宫室美者,良萌也,力作者也。”《乐毅传》:“施及萌隶。”《三王世家》:“奸巧边萌。”《后汉·宦者传》:“剥割黎萌。”《汉·礼乐志〈郊祀歌〉》:“兆蒙祉福。”注:“即‘兆氓'。‘氓'与‘民'同。”
例2)中“黎萌”、“良民”、“兆民”都是非双声非叠韵词,为什么也归謰语?从方氏“主通”而“前后见者,偶从部居”之方法看:“黎萌”与“黎民”义同,“良萌”与“良民”义同,“兆蒙”与“兆民”义同;“萌”、“蒙”与“民”双声相转,都是“民”的通假字,故“黎萌”即“黎民”,“良萌”即“良民”,“兆蒙”即“兆民”:分别为同一謰语。编列在一起,便于读者正确理解。
3) 皤如,一作燔如、波如、槃如。“贲如皤如”,郑、陆作“燔”,荀作“波”,董作“槃”。
例3)中“燔如”、“波如”、“槃如”都是“皤如”的变体,这可从不同作者书写“贲如X如”用字不同看出;“燔”、“波”、“槃”与“皤”有音转关系,故可通,所以它们都是“皤”的通假字。
上面三例謰语,其常体与变体均义同,只是其对应字有音转关系,其变体所变之字乃近音通假。前两例是复合词,这类謰语占多数。但其中“兆民/蒙”结构松散,很像词组。例3)是派生词。《通雅》謰语中共有37例派生词(详前面所录謰语中加点的词)。上面各例常体与变体之间或声转,或韵转,但都被方氏目为“双声相转”。可以肯定地说,方氏“双声相转”是为辨通假而就各变体对应字的音转关系说的。
《通雅》所收謰语变体中还有少数含义发生变化的例子。例如:
4) 蓬勃……总言勃郁蓬起之状。因义增加,蓬勃之声又转为旁勃。见《尔雅疏》。
例 4)“旁勃”即茵陈。照方以智的解释,盖其状勃郁蓬起,故换喻而名“旁勃”,方氏谓“因义增加,蓬勃之声又转为旁勃”。这是由换喻而致謰语义变的例子。又如:
5) 参差,一作槮差、参縒、篸差、柴池、差池,又转为蹉跎、崔隤之声。……差池转为蹉跎,古池、佗互从可证也。《左传》:“子产曰:‘何敢差池?'”注:“一音蹉跎。”又作蹉跌。赵壹曰:“蹉跌不面。”盖失(跌)与池转也。又转为崔隤,一作摧颓。《汉书·广川王传》:“日崔隤时不再。”注:“崔隤犹言蹉跎。”
例 5)“参差”有几种变体。其中“差池”音转为“蹉跎”,由隐喻而致义变。又说“蹉跎”音转为“蹉跌”、“崔隤”,音虽变而义未变。但不管其含义是否发生变化,一旦读音发生变化,则往往随之字变,即所谓“音变字易”。《通雅·疑始》:“音有一定之转,而字随填入,无如后世定为典要,则不得不重考究以通古今耳。”这话对深入考察方氏謰语研究很有帮助。
综上所述,方氏“謰语”指古代文献中常体之外还有变体的复音词或词组。这种复音词或词组的变体与常体对应字有音转(或同音)关系,就文字而言绝大多数是近音通假或同音通假之关系,少数使用了异体字。謰语常体与变体含义多相同,如例1)-3);少数含义不同是由语言使用中采用了换喻或隐喻手法,如例4)、5)“蹉跎”之于“差池”。謰语各变体“以声通义”,故放在一起,方便求学者“因声知义”。謰语各字须连在一起作整体理解,这是由复音词词义的整体性决定的。
三 前贤对方氏“謰语”的理解和使用
前面在考察讨论过程中,重要地方受了前贤观点启发,但为避枝蔓,只在必要处说了句“参考前贤的理解(详后)”,而未作详细说明。这里另辟一节,简单考察前贤对方以智“謰语”的理解与使用情况。
由于同是注重语文理解和应用,而且方以智从事謰语研究的语文学思想方法具有一定的开拓性、指导性和适用性,前人多主动接受方以智謰语观,遵循方氏謰语研究的思想方法考察文献中双音词各变体,编著成书,如清吴玉搢《别雅》、民国朱起凤《辞通》。清俞樾《读隶辑词》也大致属于此类著作。
前贤具体论及《通雅·謰语》者主要有刘大白、林语堂和吴文祺等人。他们多有些现代语言学知识修养,传统语文学功夫也较深厚,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的路数娴熟,因此能够较为中肯地评价传统语文学著作。他们是在为朱起凤《辞通》作序或写《重印前言》时论及方氏謰语研究的。《刘序》与《林序》分别写于1932年和1933年。那时《辞通》作者还健在,序中有关作者謰语研究的评论比较客观,对我们今天解决方以智“謰语”疑案很有参考价值。吴氏《〈辞通〉重印前言》写于1982年,评介《辞通》尚能实事求是,其相关认识对解决方氏“謰语”疑案也很有帮助。下面摘引上述三家的相关认识。
《刘序》说:跟《辞通》相同的,有明代方以智《通雅》。《辞通》所搜集的全部是謰语、重言,《通雅》是它的大辂椎轮。所谓謰语,往往从双声叠韵上转变。
《林序》说:《辞通》以謰语为主。所谓通者,通其异文之谓。古人用字每多假借,假借即别字。因古今异写或方俗不同,一字常有异文,而考异之学遂为学者注重。其对于经史载籍文字通假作综合之搜罗者,如明方以智的《通雅》。
吴文祺《〈辞通〉重印前言》说:《辞通》搜罗古籍中的通假词和词组之多,远远超过前人的著作,如明代方以智《通雅》、清代吴玉搢《别雅》之类。
上举三家均视《辞通》与《通雅》同。刘大白还对二者作了简要对比,所论甚是。《辞通》中合成词占91.0%以上(沈怀兴2007),与上文所见《通雅》謰语中合成词与词组的比率91.0%一致。这有点儿像DNA检查,检查结果是此二书“遗传基因”相同,两书的确是同类作品,刘大白等三人视《辞通》与《通雅》同的观点可为确论。
《林序》认定“《辞通》以謰语为主”,《辞通》就是贯通謰语之异文的一部书,与《通雅·謰语》一样,都是因为“古人用字每多假借”,“古今异写或方俗不同,一字常有异文”,需要帮助读古书的人破假借、通异文而写的,都是“对于经史载籍文字通假作综合之搜罗者”。然则考释謰语的基本任务就是辨通假,因声求义。这辨通假的工作只有通过考察其对应字的语音联系才能完成。这么说,方氏“双声相转”就好理解了:搜集经史载籍之假借,贯通謰语之异文,需要依据其对应字的语音联系,依其“双声相转”之关系,而不需要考察它是否单纯词,也不需要管它是否双声词或叠韵词(否则不会有那么多非双声非叠韵的謰语)。所以林语堂“所谓通者,通其异文之谓”一语破的,对正确理解方氏“双声相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与刘大白“所谓謰语,往往从双声叠韵上转变”之说相互参看,就更不会误解方以智“双声相转”和误释其“謰语”了,因为其“从双声叠韵上转变”只能理解为謰语常体与变体对应字有双声相转或叠韵相转的关系(参前文对“双声相转”的讨论)。其实,考辨多字词或词组通假情况的方法与考辨单字词通假情况的方法并没有本质性区别,而考辨单字词通假情况是不需要考察它与前后字是否存在语音联系的;只是多字词或词组“语謰謱”,而理解时需要注意词义的整体性罢了。
特别是吴文祺,助其父编纂《辞通》,有些见解亦录入书中。《辞通·释例》中也说:“儿子文祺颇究心音韵训诂之学,有所陈述,间亦采录。”而今说《辞通》“搜罗古籍中的通假词和词组”远远超过明代方以智的《通雅》、清代吴玉搢的《别雅》之类,更能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方氏“謰语”。因为这话透露出以下信息:(1)《通雅》《别雅》《辞通》是同类作品;(2)它们搜罗古籍中的通假词和词组离不开辨通假;辨通假的依据只能是看其对应字有无同音或近音关系;(3)方氏“謰语”是指他从古籍中搜集来的各变体对应字有通假关系的复音词或词组,而不是部分学者所说的“联绵字-双音单纯词”。
总之,上录各家均认为《通雅·謰语》《辞通》同是“考异之学”的著作,而不是研究謰语上下字语音联系或结构特点的著作。他们都认定謰语变体所变之字为通假。这种认识很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理解方氏“双声相转”,正确地理解“謰语”,正确地解决“謰语”疑案。
就现有文献资料考察中国传统语文学史,可知方以智的謰语研究揭开了训诂学新的一页。他把因声求义的方法广泛用于复音词和词组之常体与变体的考察及系联,拓宽了训诂学研究领域,其训诂学思想方法不仅在传统语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至今仍可帮助我们对汉语文进行深入实际的研究。同时,方以智继承和发扬前人训诂学思想,研究謰语而强调词义的整体性,不仅对我们今天正确理解古书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从事汉语词汇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白平 2002 《汉语史研究新论》,书海出版社。
陈瑞衡 1989 当今“联绵字”:传统名称的“挪用”,《中国语文》第4期。
方平权 2004 “謰謱”源流考,《古汉语研究》第2期。
方以智 《通雅》,台湾商务印书馆(库本影印),1986年。
郭珑 2006 《〈文选·赋〉联绵词研究》,巴蜀书社。
胡正武 2005 《训诂阐微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海霞 2004 联绵词的来源和定义,《庆祝刘又辛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海霞 2005 《汉语动物命名考释》,巴蜀书社。
李瑾 1987 “冥”字与“黾勉”词两者音义关系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第3期。
李运富 1991 是误解不是“挪用”——兼谈古今联绵字观念上的差异,《中国语文》第5期。
李运富 2011 汉语学术史研究的基本原则,黎千驹主编《当代语言学者论治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福根 1997 历代联绵字研究述评,《语文研究》第2期。
吕叔湘 1984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吕叔湘《汉语语法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沈怀兴 2006 “从容”释略,《汉字文化》第2期。
沈怀兴 2007 中国现代语言学早期的联绵字观念,《语文建设通讯》总第88期。
沈怀兴、周秋江 2007 由“慨而慷”看“慷慨”的构成,《汉字文化》第2期。
沈怀兴 2008a “联绵字语素融合”说疑义,《汉字文化》第1期。
沈怀兴 2008b “联绵词不可分训说”辨疑,《汉字文化》第5期。
沈怀兴 2009a 王力先生联绵字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
沈怀兴 2009b 从王筠连语说看现代联绵字理论,《汉语史学报》第八辑。
沈怀兴 2010a “联绵字-双音单纯词”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兼及先秦汉语构词方式问题,《汉字文化》第4期。
沈怀兴 2010b 试用历史考证法判断联绵字语素,《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沈怀兴 2010c 现行联绵字语素判断方法的局限性,《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3期。
沈怀兴 2011a 与衍音说相关的几个问题,《语言研究》第3期。
沈怀兴 2011b 双声叠韵说辨疑,《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3期。
沈兼士 1941 联绵词音变略例,《辅仁大学语文学会讲演集》。又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王伟丽、张志毅 2011 联绵字诸说研究,《语言研究》第3期。
魏建功 1996/1935 《古音系研究》,中华书局。
吴文祺 1983 关于《辞通》和《辞通补编》,《辞书研究》第4期。
谢纪锋 2011 联绵词浅说,龙庄伟等主编《汉语的历史探讨——庆祝杨耐思先生八十寿诞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
许惟贤 1988 论联绵字,《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第2期。
徐振邦 1998 《联绵词概论》,大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