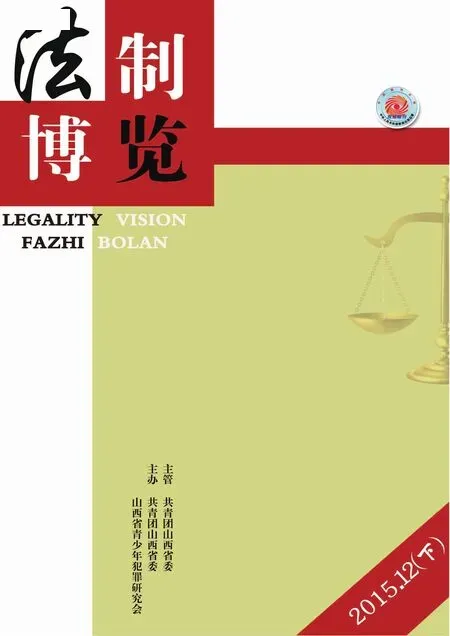论“盗窃罪”中“扒窃”的认定
2015-02-07杨源
杨 源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5
论“盗窃罪”中“扒窃”的认定
杨源
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陕西西安710125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扒窃”的界定,并分析“扒窃”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
关键词:“扒窃”;既遂;未遂
中图分类号:D92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6-0273-01
作者简介:杨源(1986-),女,西安培华学院人文学院法学系,研究方向:刑法学。

《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罪进行修改,并首次将扒窃行为明文写入刑法。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两院解释”),并对扒窃行为进行界定。然而,由于该解释存在一定模糊性,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扒窃行为认定存在分歧。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达成共识。
一、扒窃的界定
关于扒窃的概念,人们一般理解为“掏兜”,即盗窃被害人贴身财物的行为。因此《现对汉语词典》对“扒窃”的定义也是“从别人的身上偷窃(财物)。从这一理解可以看出扒窃的财物紧密附着于身体,在窃取财物的同时极易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造成侵害,使其具有比一般盗窃行为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司法机关为了加大对扒窃行为的打击力度,“两院解释”第3条第4款规定:在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上盗窃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应当认定为“扒窃”。在这个解释中不再要求“贴身携带”,而是强调了“公共场所”及“随身携带”,但对于何为“公共场所”,何为“随身携带”没有进一步解释,因此如何理解“公共场所”、“随身携带”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公共场所”范围的界定
根据“两院解释”,扒窃发生的领域必须限定为公共场所或公共交通工具。对于公共场所,有学者认为是指对公众开放,具有满足各种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带有公益或商业性质的场所。但基于刑法用语的相对性,此处的公共场所并不完全等同于“扒窃”中的“公共场所”,比如火车站、汽车站、人行道很难说能满足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但也被公众认为是公共场所。另外,公共场所往往具有高流动性、高密集型、人员陌生性的特点,但并不要求一定有多数人停留在现场。比如公园中极为偏僻很少有人去的角落也属于扒窃中的公共场所。因此,扒窃中的“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的人可以进入、停留的场所,而且并不要求有多数人停留在现场。
(二)“随身携带的财物”理解
根据财物与人身体的远近,可以分为贴身的财物、近身的财物和远身的财物。随身携带的财物范围,是仅指贴身的财物或是贴身和近身的财物还是贴身、近身和远身的财物。《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把扒窃行为列入刑法条文,除了扒窃案件在实践中存在着发案率高、侦破难度大、团伙作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稳定外,还由于扒窃的近身性特征导致其比一般盗窃更容易转化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犯罪,人身危险性比一般盗窃罪严重。通常情况下,盗窃被害人的贴身财物,由于财物紧密附着于被害人的身体,盗窃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存在潜在的危险;盗窃被害人近身且随时可能使用的财物,由于财物与被害人的身体距离非常近,盗窃行为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的潜在危险仍不容忽视;盗窃与被害人身体比较远的财物,盗窃行为并不会对被害人人身造成潜在危险,因而没有必要对这种情形从严处理。因此,根据扒窃罪的近身性特征,对“随身携带”理解时,不应仅仅局限于贴身的财物这一日常生活的解释,应该对其进行扩大解释,即包括贴身和近身的财物,否则就违背《两高解释》的制定初衷和《刑法修正案八》的立法意图。
二、扒窃既、未遂的认定
不少学者认为,根据《刑法修正八》盗窃罪的规定,扒窃并没有数额的规定,应当属于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扒窃行为,即使分文未取,也应当构成盗窃罪既遂。对此,笔者认为,扒窃行为存在未遂形态,理由如下:
第一,对于占有型的财产犯罪而言,被害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控制,是判断犯罪既未遂的根本标准。扒窃虽是一种特殊的盗窃形式,但不能改变其是盗窃行为的本质,其仍然是占有型的财产犯罪。因此,对于扒窃而言,同样要求被害人是否丧失对财物的控制作为既未遂的标准。
第二,行为犯也存在未遂形态。刑法条文在规定盗窃罪时,将扒窃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没有对扒窃数额进行要求,因此扒窃属于行为犯。从刑法原理上分析,行为犯分为过程行为犯和即成行为犯(举动犯)。扒窃应当属于过程行为犯,而过程行为犯往往根据行为人犯罪行为实施进度区分不同的犯罪形态。如抢劫罪作为一种财产犯罪,也没有犯罪数额的规定,却同样存在未遂状态。
因此,扒窃的既遂标准是被害人丧失了对财物的控制,但由于扒窃行为近身性的特点,扒窃物品通常包括身份证、银行卡甚至是照片、信件等,这类物品是否是刑法所包括的有价值的物品?
众所周知,财物的价值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即为经济价值,是物品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交换;而使用价值是指所有者、占有者经常使用该物品或对该物品有一定主观感情。日本等很多国家的刑法并没有规定盗窃罪的成立必须达到数额较大,而且在对盗窃罪的财物价值判断时,认为即使不具有经济价值,只要有使用价值,便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刑法修正案八在规定扒窃时,并没有要求数额较大,而且由于扒窃行为盗取贴身和近身财物的特点,将没有经济价值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作为扒窃的犯罪对象是合理的。比如具有纪念价值的老照片,有珍藏价值书信。
总之,扒窃存在即遂与未遂形态,只要行为人窃取值得刑法保护的财物,即使没有交换价值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就可以认定为既遂。
[参考文献]
[1]闫帅,刘鹏.新型盗窃罪的司法适用问题研究[J].河北法学,2013(12).
[2]李广齐.论<刑法修正案(八)中“扒窃”的认定>[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