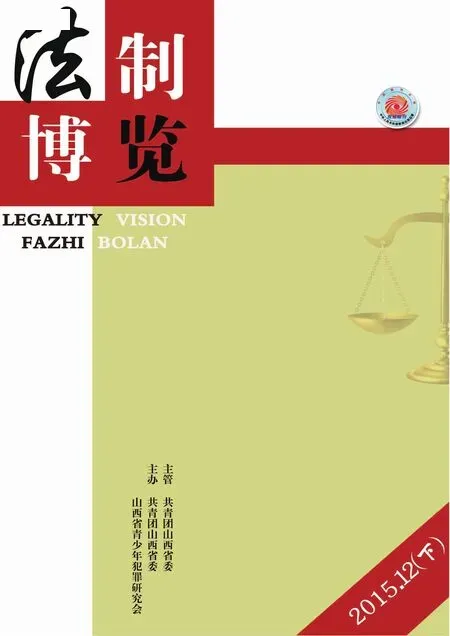从亲亲相隐原则看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构建
2015-02-07刘畅
刘 畅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4
从亲亲相隐原则看我国亲属拒证权制度的构建
刘畅
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130024

摘要:亲亲相隐原则的发展历程与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演变相呼应。现代法治是否需要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本文试图阐述亲亲相隐原则的演变历程,分析其合理性,进而主张亲亲相隐与现代法治的契合,探讨刑事立法的相应改进。
关键词:亲亲相隐;亲属拒证权;人性;人权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36-0204-02
作者简介:刘畅(1988-),女,汉族,黑龙江大庆人,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刑法学。

亲亲相隐原则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它经历了复杂的发展历程,从思想走向法律,从单向规制走向双向规制,从粗疏走向完备,又从肯定走向否定再次走向肯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领域一直是个空白,直到《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告人的近亲属有拒绝出庭作证的权利,使得亲属拒证权制度又成为了学界讨论的热点。
一、亲亲相隐原则的流变与向近代亲属拒绝作证制度的转变
亲亲相隐或亲属容隐,是人们熟知的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一项制度,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履行互相隐瞒罪行的义务而不受法律制裁的制度。
中国的亲亲相隐观念和制度萌芽上溯至春秋时期。在西汉时期,亲亲相隐制度正式以法令形式确立。自此,亲亲相隐进入古代法律制度领域。到了唐代,亲亲相隐又得到了进一步细化。从清末变法至民国末期,在大规模的法制变革中,亲亲相隐制度经改造后被保留下来。受西方法律的影响,其内容基本上只剩下容隐权利的规定。从清末到民国近半个世纪,逐渐形成一个因亲属身份而获得特免权的系列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传统社会重视家庭伦理价值的民情。
在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原则是一种基于亲情伦理的立法,而现代法律一般认为它是亲属权利立法,是一种基于天然的亲属身份而享有的例外特权。不可否认,在我国“我们的法律不再承认‘核心家庭’以外的家庭、家族的任何正当作用,认为其必定是封建宗法势力的残余,必定有碍于社会进步。”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我们过分强调国家对社会成员的控制和动员作用,而不合理的忽视了亲情伦理对社会和谐的纽带作用。
从立法上看,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贯彻亲属权利立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与犯罪人有密切联系的亲属最有理由被当成“知道案件情况的人”。这种作证义务是法定义务。第84条第l款和第45条也规定了相关内容。此外,当司法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的亲属知道真实案情而又拒绝吐露或说假话时,以包庇罪、伪证罪来拘捕嫌犯的亲属,在法律上完全没有障碍。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正式通过。其修订的内容之一是第188条:“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该内容显然是法治人性化的又一次进步。根据此条,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大义灭亲”的司法政策可能会被“部分”颠覆。规定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彰显了立法对伦理纲常和人文道德的尊重。
需要明确的是,新刑诉法规定的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并不等同于证人拒绝作证权。证人拒绝作证权是指知悉案件情况的人在法定情况下可以拒绝充当证人或对某些问题拒绝陈述。[1]设立证人拒绝作证权的目的在于保护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或利益。因为从长远来看,各种利益的重要性并不是等价的,某些利益更为重要,而在利益的衡量过程中,亲属之间的信赖关系比要求证人履行作证义务以发现事实真相更为重要,此为设立证人拒绝作证权的一方面原因。
虽然此次修改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法学界对此却非常不满,因为并没有禁止公检法机关在出庭以外的其他场合强迫近亲属作证。30多年来学术界无数有识之士不断呼吁与努力才换来这种结果,难免令人失望。[2]
二、对亲属拒证权进行立法的合理性
首先,传统理论主要将家庭本位作为根本和基础,而近代家属身份特免权立法也同样如此,将家庭成员基本权利作为根本出发点,必须明确的是,二者均承认亲情源于天性,法律不能够脱离人性及天理。
其次,就本质而言,现代刑法建立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对犯罪行为的惩罚,而达到挽救或者预防犯罪的目标,以最大程度上降低或者避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如果法律必须要强迫“大义灭亲”,那么对罪犯及其家人的人性的毁灭是无法弥补的,与刑法设立的初衷相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罪犯回归社会及家庭的难度。就更加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将会对人类的天性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再次,从刑罚的效果看,否认亲属特免权实际上并不能预防亲属间窝藏、包庇罪的发生。我国半个多世纪来刑事司法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该类犯罪的事实也反证了亲情不可违的合理性[3]。
综上而言,我们应将对人性的爱护、保护亲人作为家属的根本权力,并以法律制度明确表明,同时要设计严密的制度来尽可能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
三、亲亲相隐原则的现实影响
(一)亲属拒证权的立法化倡议
确立亲属拒绝作证制度具有其正当性基础。第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均衡性的要求。亲情、人性是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最根本的自由及需求,然而,自由位于法律价值的最顶端,诉讼程序已然为人类自由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司法保障。实现权力自由的根本在于不能够阻碍他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即便存在阻碍现象,也不应该具备均衡性,否则自由权利将会被法律否定。第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犯罪嫌疑人的近亲属拒绝作证,是对其自身做出的利他选择性的合理诉求,在刑事诉讼当中,控辩双方之间的举证不平衡性始终存在,一旦在此过程中,控方依靠其优势地位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做出对其不利的指控,这将会与以审判为中心,控辩双方平等的法律精神背道而驰。而强制近亲属作证,在一定程度对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产生的精神打击,不利于二者之间亲缘关系的稳固,基于此就人权保障角度而言,在程序上规制近亲属拒绝作证权具有科学性、合理性。
(二)亲属拒证权的制度设计
确立我国的亲属权利制度绝不是纲常礼教的简单复活,而应该是建立在现代人权保障理念上的理性立法。亲属拒证权的设计应强调以下方面:
首先,要明确界定“亲属”概念及范围,避免亲属身份特免权的滥用,影响法律公平性。当前,我国法律制度尚处于完善阶段,可以立足于自身实际情况,积极借鉴各国立法例,将我国享有的拒绝作证特权的亲属归纳为特定成员,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配偶、直系血亲、兄弟姐妹、共同居住的其他亲属,一般来说,与当事人之间具备近亲属关系的主体,其拒绝作证的权利具有当然性,而在非正常情况下,亲属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应当进行综合衡量。
其次,有必要对亲属身份特免权适用的范围做出具体的限制。行使权力对自身利益产生的影响应具备一定的限度,不能够违反社会属性。因此普通刑事犯罪可以适用亲属身份特免权,但是一旦涉及到危及国家安全时,不得适用该特权,主要是由于国家安全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这种利益远远超过亲属权利。再次,需要对亲属特权的性质予以明确。由于特权是一种权利,那么权利人就可以选择行使或放弃权利。在实践中,不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选择行使或者放弃该权利,司法机关都应当应予以尊重和保护。
(三)刑法窝藏、包庇等相关罪名的修正
在刑法上,应对我国刑法分则相关条款作出相应修改。《刑法》第105、107条第二款等内容中应添加“但书”条款,即“为替配偶、直系血亲等亲属隐匿罪证而实施上述行为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另外,还应在《刑法》分则第6章第2节“妨害司法罪”中设立例外性条款。该条可以表述为“配偶、直系血亲等亲属为了犯罪嫌疑人的利益,采取暴力等手段贿买他人,并触犯本法第305条等规定之罪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但危害国家安全罪除外。”
立法例可参考《日本改正刑法草案》的相关规定。
[参考文献]
[1]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释义与点评[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3.
[2]范忠信.亲属拒证权:普世与民族的重合抉择[J].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12-1-5.
[3]俞荣根,蒋海松.亲属权利的法律之痛——兼论“亲亲相隐”的现代转化[J].现代法学,2009,5,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