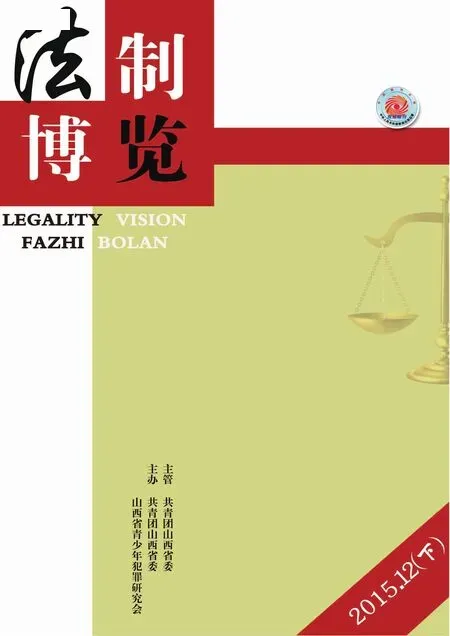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股权众筹”的刑事法律风险防范
2015-02-07汪涛
汪 涛
浙江华盛律师事务所,浙江 杭州310005
一、引言
股权众筹(crowd funding)是一种起源于美国的金融产品,其价值在向公众募集资金,以确保现金流较为短缺的企业完成筹建或得以顺利发展。[1]随着当下我国鼓励金融创新的政策背景、以及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等客观现实,众筹制度得以被引入中国。合法的众筹的实施,应当是由发起人跟投人等以一定的方式组成的投资群体,共同向确定的投资对象进行投资的过程。对于投资人而言,众筹是在一定的期限内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投资方式;而对于被投资对象而言,众筹行为可以为被投资对象在短期内募集大量资金或用于企业设立或用于企业发展。
众筹在我国落地初期,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盈利性众筹多于公益性众筹。[2]众筹投资人参与众筹项目的核心约定,在于以一定的期限获得一定比例的回报,在实践中回报期限和比例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框架性的。但无论在众筹实施初期采取哪一种方案,至少都表明了众筹的行为性质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捐赠行为。
(二)股权众筹多于债权众筹。对于参与众筹的投资人而言,其追求的法律后果或是从被投资人处获得一定的股权,或是获得一定的债权。证监会于2014年12月起草的《私募股权众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作为指导现阶段众筹实施的纲领性文件,其规定也是以股权众筹的方式为主线,对众筹这一创新金融产品加以规范的。同时考虑到刑事司法界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案件形式的严峻性、债权众筹和非吸类犯罪形式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因素一并注定了股权众筹的使用频率将高于债权众筹。
二、众筹过程中的刑事法律风险
(一)众筹过程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类”犯罪的防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指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的行为。在众筹这一金融产品的实践中,有以下方面需要加以注意以避免:
1.特定时期内的“资金池”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表象。众筹的过程从形式上看是一个资金募集过程,投资资金从募集到投资到位自然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在众筹资金从各投资人处开始归集,到完成向投资对象的投资之前,众筹所涉资金客观上一直由众筹的组织方收取、保管甚至使用,[3]客观上产生了一个资金池。此类模式下,资金归集后投资完成前的期间内,众筹组织方占有资金额进行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众筹实施人全部或部分地改变资金的用途,众筹存在向集资诈骗罪转化的倾向。众筹制度本身是为了解决实施人资金短缺的难题,因此在众筹的实施过程中实施人往往就资金的使用目的向投资人作出了承诺。[4]而实践中因准备期过于漫长等因素,临时改变资金用途的做法也大有所在,或在短期内将资金投向其他市场,甚至将资金出借赚取利差,如因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外在风险导致资金最终无法回收的,众筹实施人的行为面临着向集资诈骗罪转化的风险。
3.众筹过程中的宣传方式往往难以把控,亦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之表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宣传的不法性,集中表现在宣传行为的“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5]而众筹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往往又会结合互联网金融的概念,通过网络的平台进行宣传,在宣传了投资内容的过程中还一并宣传了投资的盈利性,因互联网平台针对的对象是不特定的主体,[6]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直接抵触,《私募股权众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也正是基于这一司法解释的法义,对股权众筹中的网络宣传模式作了禁止性规定。
(二)众筹过程中对非法发行证券罪的防范
根据《证券法》的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公开发行证券:(一)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二)向累计超过二百人的特定对象发行证券;(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该规定对股权众筹模式构架的启示在于:第一、股权众筹的宣传过程中,既要在宣传中注重宣传对象的特定性,还要在确保特定性的前提下严格控制投资人的人数,《私募股权众筹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在此基础上,对参与股权众筹的人数、投资额度有更为严格的限制,其意图也是为了避免股权众筹这一金融产品滑向非法发行证券罪的边缘;第二、在众筹模式的选择上,如通过公开向投资人出售被投资对象的股权的“自上而下”方式进行众筹的,必须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即便采用“自下而上”类似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的方式进行众筹的,也应履行报批程序。
三、众筹过程中的民事法律框架构建
(一)借鉴私募基金的模式构建股权众筹的模式
当下较为流行的股权众筹方式,即借鉴私募基金的模式来完成股权众筹的构建。由众筹的投资人成立有限合伙企业,再由有限合伙以增资入股的方式向被投资企业进行投资;被投资企业进行利润分配时,先将收益款分配至各有限合伙企业,再有有限合伙企业分配给各投资人。
该方案的实施通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筹备募集阶段。众筹实施人与有意向参与众筹的投资人签订众筹意向协议,协议的核心内容即为成立以众筹为目的的有限合伙企业。随着众筹协议的签订,投资人将众筹投资款汇入有限合伙企业的专用账户;第二阶段为实施和投资阶段。在以众筹为目的的有限合伙企业完成设立后,有限合伙企业与被投资企业签订增资扩股协议,以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增资扩股的股东,并以先前从各众筹投资人处获得的众筹投资款作为增资的资金,支付给被投资企业,完成众筹。
(二)该构架的合理性
该模式的相对合理性在于:第一、在设立方式上,参照私募基金的设立方式以“自下而上”的流程先设立有限合伙,再由有限合伙向目标公司进行投资,从整体上看无论是设立有限合伙的过程,还是向目标公司投资的过程,在人员范围上都有一定的封闭性,确保了众筹实施过程的非公开性,从形式上与以自上而下方式公开发行证券行为有所区别;第二、从资金流动的过程看,投资人向有限合伙企业交付款项时,已将该款项定性为“最终需投降目标公司的投资款”,资金的特定使用目的贯穿着众筹活动的始终,最大程度地避免了众筹所涉资金在某一阶段形成无特定使用目的的“资金池”,从而和资金拆借混为一谈。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众筹项目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发行证券罪的界限。
(三)众筹过程中其他需要注意的理论与实务问题
1.在“自下而上”的众筹模式中尽可能地突出众筹的自发性,淡化被投资人的组织角色。从行为实施的目的看众筹项目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众筹项目究竟是一个由众筹投资人自行发起的投资行为,还是一个完全由被投资人组织策划的资金募集行为。前者在动机上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发行证券罪的主观方面,而后者从动机上更接近于一个民事行为。因此在众筹实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投资协议签订时,应淡化被投资企业的策划、组织职能,相反应尽可能地在协议文本中强化众筹投资人的自发性,这也正是股权众筹从模式上不宜采纳“至上而下”的股权转让模式,而应当尽可能地采纳“自下而上”的私募基金股权投资模式的必要性。
2.引入第三方监管,回避“资金池”中资金被挪用的法律风险。股权众筹过程中,在众筹投资人将众筹投资款投入新设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但有限合伙企业暂未将资金投入被投资企业的这段时间内,客观上会形成一个“资金池”。这段时间内,如将众筹资金随意交由一方保管,尤其是交由被投资企业保管,即容易产生形式上涉嫌“非吸”,后果上极易被挪用的法律风险。为避此嫌,实践中可采用第三方监管模式,这类第三方监管既可通过商业银行的支付监管来确保资金使用的定向性和安全性,还可通过保险公司出售的保险产品来保障众筹投资人的利益。3.严格控制规模和人数,谨慎看待形式变通的合理性。实践中,部分股权众筹项目往往采用分期、分批的方式实施众筹,试图以此规避法律对人数的限制。但无论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视角、还是从非法发行证券罪的视角,法律对参与人数的限制绝不仅仅局限于某一次特定的投资,而是把被投资企业作为一个特定的行为对象,来全盘审查被投资企业所涉的所有投资行为是否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相冲突。因此,即便采取分期、分批的方式进行众筹,依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项目本身在规模和人数上的违法性。与分期、分批次众筹相比,分设形式上无关联的多家企业作为股权众筹中的被投资对象,往往能起到更好地效果。
四、结论
股权众筹项目的复杂性在于民商事、刑事的高度交叉,即在对被投资企业进行充分地法律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巧妙地使用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公司等作为众筹过程中的工具平台,以第三方监管、混合式众筹等方法为补充,通过构建一个合同投资框架的方式来实现众筹,且最大程度上地避免形式风险。在实践中,对股权众筹涉嫌的两个罪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发行证券罪的理解和防范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要件上,而是要以金融的法律政策的导向为抓手,结合被投资企业的实际经济情况作进行实质性判断,在金融创新的同时确保实体上、结果上的合法性。
[1]余政.众筹与非法集资之分野探究[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5(3):2.
[2]彭冰.非法集资行为的界定[J].法学家,2011(6):15.
[3]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新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35.
[4]邵向霞.众筹及风险分析与防范[J].经营管理者,2015(3):66.
[5]周学东.民间借贷辩法[J].新世纪周刊,2012(8):16.
[6]殷明波.众筹模式在中国的发展[J].时代金融,2005(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