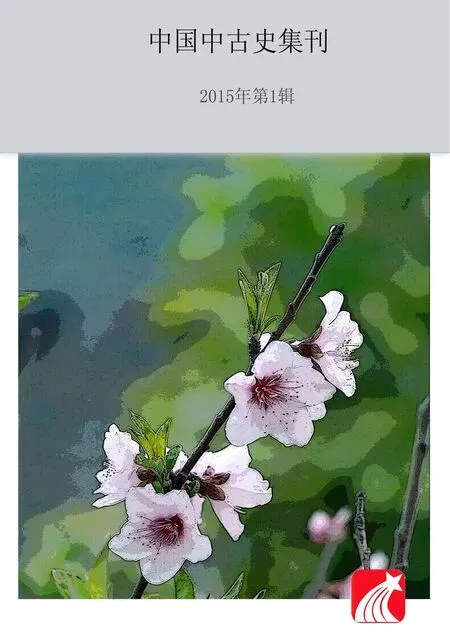杨坚诛五王史实补考
——从《大周故滕国间公墓志》说起
2015-01-30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杨坚诛五王史实补考
——从《大周故滕国间公墓志》说起
牛敬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关于隋文帝杨坚在北周末年迅速夺权之事,古今史家有多种评论。[1]唐太宗评杨坚是“欺孤儿寡妇以得天下”,吴兢著,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2,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31页。赵翼评“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证》卷15《隋文帝杀宇文氏子孙》,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2页。袁刚认为关陇勋贵倒向杨坚是杨隋代周的根本原因,参见氏著:《说北周大象二年杨坚假黄钺杀五王克平三方构难》,《大同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13卷第4期。今人吕春盛不满足于从杨坚家世背景、婚姻关系解释杨坚迅速崛起,他认为杨坚充分利用北周政权自身弱点才是问题关键。参见吕春盛:《关于杨坚兴起背景的考察》,《汉学研究》2000年第18卷第2期。但已有研究多从大处着眼,对周隋禅代之际的史实细节关注不够。如杨坚于大象二年(580)陆续杀宇文泰诸子,即赵、越、陈、代、滕五王[2]参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此一剪除宇文氏中流砥柱之举,事关周隋禅代成功与否,其中原委尤值得发掘。[3]《隋文帝传》对此事有相关描述,详参见韩昇:《隋文帝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2—84页。与《周书》、《隋书》等所载北周诸王事迹相对,诸王墓志也多有保存、发现。如《庾信集》有齐王宇文宪墓志[4]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庾子山集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31—753页。,1993年出土谯王宇文俭墓志(已公布)[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2001年出土冀国公宇文通墓志(未公布)。[1]邢福来、李明:《咸阳发现北周最高等级墓葬》,《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第1版。新近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收得《大周故滕国间公墓志》拓片,志主是滕王宇文逌,乃杨坚所杀五王之一,因其身份特殊,故该志意义颇大。宇文逌墓志正文极短,虽仅五行六十六字,其中却不乏补史之处。现结合传世文献与已有研究对该墓志及相关杨坚除五王事试做考察。
一、墓志简释
墓志整理如下:
1.大周故滕国间公墓志
2.公讳逌字尔固突,河南洛阳人也。
3. 太祖文皇帝之第十五子,以大象二年
4. 十二月廿一日,遘疾,薨于京第。时年廿
5. 五。有诏赠滕国公,谥曰间,以其月廿
6. 七日窆于京兆万年县。
墓志题名为“大周”,所记滕王死葬日详细(其薨日与《周书》所记“辛未”[2]《周书》卷8《静帝纪》。即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只差一日)。墓志字数极少,笔法极拙,可知墓志应为滕王下葬时草草所刻。志文信息有限,关于宇文逌之事详细不及《周书》本传,但其中有两条重要信息值得注意。
(一)宇文逌谥号
《周书》宇文逌本传记为“滕闻王”[3]《周书》卷13《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而墓志题名谥号为“间”,墓志正文为“闲”,乃“间”字异体。查诸谥法,未发现谥“间”者。《周书》记大象二年(580),杨坚所杀五王为赵僭王宇文招、越野王宇文盛、陈惑王宇文纯、代奰王宇文达、滕闻王宇文逌,五王皆得恶谥。[1]参见《周书》卷13《文闵明武宣诸子传》。按《谥法》,“色取仁而行违曰闻”[2]汪受宽:《谥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80页。。其他四王谥号,据《谥法解》、《谥法》等“言行相违曰僭”,“自下陵上曰僭”,“质胜其文曰野”,“敬而不中礼曰野”,“满志多穷曰惑”,“不醉而怒曰奰”。[3]同上书,第437—438页、第401页、第413—414页、第451页。“闻”乃恶谥,与其他四王恶谥相一致,故杨坚谥滕王为“闻”,《周书》滕王本传所记“滕闻王”有理。但《隋书·经籍志》又有“滕简王集”[4]《隋书》卷35《经籍志四》。,据《史记正义·谥法解》,“一德不懈曰简”,“平易不訾曰简”,“简”为美谥。“间”比“简”只少一竹字头,二字可通假。[5]参见王辉编著:《古文字通假字典》,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07页。据《隶辨》,汉魏以来“诸碑皆以蕳为简,相仍积习,有所自来”[6]顾南原撰集:《隶辨·上声·产韵》,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404页。,北周独孤宾墓志即以“蕳”为“简”[7]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独孤宾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5期。,同时草头字在史志碑刻诸文献中又不乏夺“艹”头者。[8]如茅、葬、薤、薦等碑别字中便有去艹头的,参见秦公辑:《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5页、第261页、第392页。姚薇元先生也指出《魏书·官氏志》“仆闌氏”即《广韵》等引《官氏志》所见“仆蘭氏”,参见氏著:《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1页。故笔者以为宇文逌墓志中的“间”应为“简”之别字,墓志与《经籍志》记载可视为一致。“简”为美谥,“闻”为恶谥,宇文逌一王而有两谥号,墓志与《周书》有别,殊为可疑。
与滕王类似,赵王宇文招死后也有两个谥号。一即《周书》赵王传所记“赵僭王”。而据《新唐书·艺文志》,北周有《赵平王集》十卷[1]《新唐书》卷60《艺文志四》。,《隋书·经籍志》记为“赵王集八卷”[2]《隋书》卷35《经籍志四》。,此是赵王又谥为“平”。据汪受宽所集谥法,“平”多为美谥,其中“执事有制曰平”,“分不求多曰平”[3]汪受宽:《谥法研究》,第297—299页。,与“僭”字恶义不同。至此可推测,滕王“闻”“简”二谥相对,赵王“僭”“平”二谥相对,此必非偶然。联系二王生平可知,在宇文政权中,赵滕二王并无失德之事,且二王文学水平于诸贵中为最高。二王皆有文集,“招所著文集十卷,行于世”[4]《周书》卷13《文闵明武宣诸子传》。,“逌所著文章,颇行于世”[5]同上。。对于《周书》所记北周五王恶谥,《史纠》批评道:“周氏诸王间不乏贤,代王不迩声色,滕赵俱能文章,或谥以僭,或谥以奰,或谥以惑,或谥以野,累累恶谥,皆隋志也。出于隋志而登之《周书》,史官不加一辞焉,载事之笔,焉用彼为?”
清人李清发现《隋书》诸王传与《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在二王谥号上的矛盾,曾发出疑问:“不知改闻为简者谁?”[6]朱明镐:《史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第487页。“不知改僭为平者谁?”[7]李清:《南北史合注》卷145,续修四库全书第28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6页。此是李氏认为杨坚先予二王恶谥,“滕简王”“赵平王”为后人所改。笔者以为,滕王宇文逌墓志所见“间”字或即“简”字异体,又该墓志应为滕王葬后不久所刻,特别是墓志有“诏赠滕国公,谥曰间”,可以推知:滕王死后,杨坚还未行禅代,北周礼官或念及滕王为皇叔祖,便谥以“间”(“简”);不久隋代北周,杨坚即予以五王恶谥。[1]李清:《南北史合注》卷168,续修四库全书第282册,第181页。如这种推论正确,则墓志所见谥号“间”应为《经籍志》“滕简王”之源头。《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滕简王集”“赵平王集”,成书应在二王死后不久的周隋之际,二集所用谥号或即北周所赠。当然,还可以确定《经籍志》之“滕简王”与杨坚所谥“滕闻王”曾在隋代并行。与恶谥“闻”代表隋代官方态度相对,美谥“简”代表为滕王结集的文人之态度,其源头或即滕王墓志所见北周所赠谥号。综上分析,可以推论:“简”与“平”或是滕王、赵王最初于北周所得谥号,而《周书》所记“闻”“僭”应是杨坚即位后针对五王所改之恶谥。[2]以上释滕王谥号并未对《周书》“闻”字有所质疑,一是因自宋本《周书》既已作“闻”,二是因“闻”字乃恶谥,与其他诸王恶谥语境相通。但古书抄刻或有将“閒”(間)误为“闻”例,如《史记·张汤传》有“罪常释闻即奏事”,而《汉书·张汤传》则作“罪常释。间即奏事”,齐佩瑢以“间”字为确(参见齐佩瑢:《训诂学概论》,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31页)。如《周书》将“间”(简)误刻为“闻”,则滕王谥号或自与其他四王谥号不同,五王谥号在周隋之际或不存在改谥,至于赵王谥号由“僭”至“平”,或是入唐后所改。正是将《隋书·经籍志》与新发现宇文逌墓志相配合,才得以揭开这一被遮蔽的历史细节。此外,宇文逌墓志记其薨时降爵为公,其他几王或也如此,这应出自杨坚之义,为《周书》所不载。
(二)宇文逌为“河南洛阳人”
众所周知,北周文帝宇文泰为武川镇人,《周书》记宇文泰为“代武川人”[3]《周书》卷1《文帝纪上》。,宇文泰诸子纪传均不言籍贯,此当是史家以子从父籍,以宇文泰诸子皆为武川人。而将宇文逌墓志与《周书》对比,可发现宇文逌与其父异籍。不唯如是,庾信为宇文泰之子齐王宇文宪所撰神道碑称其乃“恒州武川人也”。[4]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庾子山集注》,第732页。宇文宪死于宣政元年(578),宇文逌死于大象二年(580),二人墓志所记籍贯一为武川,一为洛阳,此是兄弟二人又异籍。
与此类似,正史、墓志所见家庭成员异籍现象还出现在其他北周贵族家庭中,如独孤氏和尉迟氏两家。《周书·独孤信传》记“独孤信,云中人也”[1]《周书》卷16《独孤信传》。,《隋书》记独孤皇后“河南洛阳人,周大司马、河内公信之女也”[2]《隋书》卷36《文献独孤皇后传》。,此是独孤氏父女异籍。同样是独孤信,其墓志(557)则说:“公姓独孤,讳信,字期弥头,河南洛阳人”[3]韩理洲:《全北齐北周文补遗·全后周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此是一人而有两籍。而至独孤信之子独孤藏,其墓志(578)又说“公讳藏,字达磨,朔州人也”[4]同上,第39页。,独孤信另一子独孤罗墓志(600)也说其是“云内盛乐人,后居河南之洛阳县”[5]韩理洲:《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北魏时期朔州云州先后共治一城[6]参见《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故“云中”“朔州”实指一地,“盛乐”则将独孤氏籍贯指向盛乐郡。父子三人墓志相较,可知独孤信籍贯被系于洛阳,二子籍贯被系于代北云中之地。独孤罗墓志所言“后居河南之洛阳县”是指北魏末年独孤信因戡乱立功徙居至洛阳[7]参见《周书》卷16《独孤信传》。,但该墓志并未以徙居之洛阳为籍贯,而仍称墓主为云内盛乐人,这与《周书》将独孤皇后定为洛阳人截然相反。再以尉迟氏为例。《周书》记尉迟迥“字薄居罗,代人也”[8]《周书》卷21《尉迟迥传》。。而尉迟迥女墓志(574)则称“河南洛阳人”[9]庾信:《周仪同松滋公拓跋競夫人尉迟氏墓志铭》,《庾子山集注》,第1065页。,尉迟迥之侄尉迟运墓志(579)也称“河南洛阳人”[10]韩理洲:《全北齐北周文补遗》,第46页。。
论及北族定籍为河南洛阳人,一般会提及孝文帝迁洛定族姓事。《隋书·经籍志》载:“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1]《隋书》卷33《经籍志二》。
孝文帝此举让大量北族家庭特别是南迁北族家庭得获河南洛阳籍,其后北朝分立,仍有大量北族叙本家籍贯为河南洛阳者。论者可能会据上文提及的宇文、独孤、尉迟三家个别成员的“河南洛阳”籍推论,认为三家或早已因孝文改革而得河南洛阳籍。但不难发现,此三家仍有大量人物传记证明其籍贯在代北之地,言之凿凿,三家洛阳、代北籍贯并存现象,绝非孝文定籍可以简单解释。其实,正如《经籍志》所载,孝文定籍改革实际与定族姓互相配合,而定姓族有严格标准即以官爵定姓族。孝文太和十九年(495)诏书定姓以三世高官为标准,定族标准低于定姓标准,如下: “诸部落大人之后,而皇始已来官不及前列,而有三世为中散、监已上,外为太守、子都,品登子男者为族。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来,三世有令已上,外为副将、子都、太守,品登侯已上者,亦为族。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其此诸状,皆须问宗族,列疑明同,然后勾其旧籍,审其官宦,有实则奏,不得轻信其言,虚长侥伪。”[2]《魏书》卷113《官氏志》。
由上文可知,孝文所定姓族其实是官姓官族,欲得姓族必以祖宗三世为官得爵高低为标准。同时审定姓族程序有“勾其旧籍”,此暗示一旦得官定姓族,便可弃其旧籍而得河南洛阳籍。综合这两点可以得知,并非所有北族家庭都能因孝文定姓族而获河南洛阳籍。以北朝诸宇文氏为例,检索正史,得以河南洛阳为籍的有四人。其一北魏宇文福,“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为拥部大人。祖活拨,仕慕容垂,为唐郡内史、辽东公。太祖之平慕容宝,活拨入国,为第一客”[1]《魏书》卷44《宇文福传》。。其二为北魏宇文忠之,“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世据东部,后入居代都。祖阿生,安南将军,巴西公。父侃,卒于治书侍御史。忠之猎涉文史,颇有笔札,释褐太学博士”[2]《魏书》卷81《宇文忠之传》。。以上二人父祖辈皆有北魏显宦,应是符合孝文定姓族之标准,得以定籍洛阳。其三是由周入隋的宇文庆[3]《隋书》卷50《宇文庆传》。,其兄为宇文神举。《周书·宇文神举传》称“高祖晋陵、曾祖求男,仕魏,位并显达。祖金殿,魏镇远将军、兖州刺史、安吉县侯”,其父显和为孝武帝藩邸之旧,历任孝武帝亲卫长官自阁内都督至帐内大都督,终于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兼资文武,已为元魏贵族。[4]《周书》卷40《宇文神举传》。按理神举兄弟家世已满足孝文定族姓标准,其父祖辈应可得河南洛阳籍,但二人之父宇文显和墓志称显和为“上党武乡人”[5]庾信:《周车骑大将军赠小司空宇文显和墓志铭》,《庾子山集注》,第953页。。此或是宇文神庆一支虽历代显宦但发迹过晚,未及孝文太和十九年定族姓之事,如此则更见北魏得河南洛阳籍之难。[6]周一良以神举兄弟原籍河南洛阳,当误。参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3页。其四为由周入隋的宇文弼,“其先与周同出。祖直力觐,魏钜鹿太守。父珍,周宕州刺史。”[7]《隋书》卷56《宇文弼传》。宇文弼家世不及宇文庆,故其与宇文庆在《隋书》中的“河南洛阳”籍应非北魏旧籍。以上四个宇文家族为参考,宇文泰之高祖宇文陵仕燕:“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魏道武将攻中山,陵从慕容宝御之。宝败,陵率甲骑五百归魏,拜都牧主,赐爵安定侯。天兴初,徒豪杰于代都,陵随例迁武川焉。陵生系,系生韬,并以武略称。韬生肱。”[1]《周书》卷1《文帝纪上》。
宇文陵以五百士兵自燕降魏,并非部落大人之属;其官仅拜都牧主,此官不见《官氏志》,亦当与领民酋长同类且等而下之,当然它更不合孝文诏书所定的正式文武职官标准。此外,宇文陵虽有侯爵,而其子孙皆无官职爵位,此不合定族之三世标准。又,孝文诏书虽将定族标准放宽至缌麻亲,但宇文泰一支似仍不能缘附以定族。与北魏两支宇文家族以及宇文庆家族相比,宇文泰家族实为宇文部之下等族属(宇文弼家族或因缘附宇文泰而入仕,亦不能与其他三支宇文家族相较),未得孝文定姓族,当然不得改籍入河南洛阳,故《周书·文帝纪》、宇文宪神道碑称父子二人为武川人。独孤、尉迟两家与宇文泰家类似。独孤信祖先虽为部落大人,但其祖“和平中,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2]《周书》卷16《独孤信传》。,仅为普通戍卒;至其父始为领民酋长[3]同上。,但仍非正式职官,可知独孤信一家应不合孝文定族姓标准。因此《周书·独孤信传》、独孤藏墓志、独孤罗墓志以父子三人为代北云中人。尉迟迥家世不详,仅知其父娶宇文泰之姊[4]《周书》卷21《尉迟迥传》。,可推知其家世当与宇文泰等夷,亦非元魏大姓,不得定籍洛阳。总之,宇文泰、独孤信、尉迟迥三家世居代北,皆为微族,家世不符合孝文定族姓标准,不得有河南洛阳旧籍。
然而,何以史书、墓志中三家成员拥有“河南洛阳”籍?我们知道,宇文泰入关后以关内诸州为有功诸姓之本望[1]《隋书》卷33《经籍志二》。,此举被视为“关中本位政策”之要素。[2]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9—200页。而北周三个顶级家族竟有人以“河南洛阳”为本望,此与关中本位说相抵牾。究其原因,宇文氏定诸姓本望为关内诸州确实推动了关陇集团的形成,然而此政策并非波及所有族群特别是已有美籍之家,如诸元、长孙氏等北魏旧族皆保留“河南洛阳”之籍。[3]参见《周书》卷38《元伟传》、卷26《长孙俭传》、《长孙绍远传》。“河南洛阳”籍在北朝为官民相尚,深入人心,特别是在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对立之际,“河南洛阳”籍又兼有正统微义,此当是三家成员传记中有以“河南洛阳”为郡望之文化原因。如果说北周权贵以关内郡望赐诸姓是主观塑造关陇集团之政治举动,那么这些权贵传记中不经意表露出的“河南洛阳”情结,则表现出了他们的文化潜意识。[4]松下宪一已注意到北周勋贵有附会河南洛阳籍的可能,参见氏著:《北魏胡族体制论》,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发行2007年版。此点承权家玉博士指出,特此致谢。其实与乃父类似,北周明帝对关中权贵中泛滥的河南洛阳籍颇有意见,曾明确下诏令新老鲜卑贵族们放弃河南籍贯,“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5]《周书》卷4《明帝纪》。,可惜事与愿违,连他自己兄弟的墓志都刻上了“河南洛阳”的烙印。此外,宇文氏在其另一塑造关陇集团的举措即赐功臣胡姓时,也有可能赐以美籍,其中便有“河南洛阳”。如《周书》记北周名臣辛威为“陇西人”[6]《周书》卷27《辛威传》。,北周命他改姓为普屯,庾信为其作神道碑则记“公讳威,字某,河南洛阳人也。旧姓辛,陇西人。”[7]庾信:《周上柱国宿国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庾子山集注》,第879页。史籍所载北朝辛氏几乎无一例外为陇西人[1]参见林宝撰:《元和姓纂》卷3,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55—365页;杜斗城:《汉唐世族陇西辛氏试探》,《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辛威神道碑亦言辛威旧籍为陇西,且其祖孙三代未有赴洛阳迹象[2]《周书》卷27《辛威传》。,因此其河南洛阳籍必是西魏北周时期所赐。如这一推断正确,那么上文提及宇文、独孤、尉迟三家成员出现“河南洛阳”籍便不仅仅只有文化动因,而是更有制度背景。其实西魏北周赐胡姓与赐关内诸州籍(甚至可能是洛阳籍)可算作是对孝文迁洛定族姓定河南籍的模仿,只不过孝文改革主要针对代北旧族,而宇文泰赐胡姓赐新籍改革则泛及胡汉各族,最大限度地巩固了关陇社会。
宇文逌墓志除透露以上两点重要信息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墓志称宇文逌为文帝第十五子,《周书》只记文帝有十三子。从《周书》文帝诸子排列顺序,应是以宇文逌为最小第十三子,而墓志以为第十五子,则宇文逌或还有另两位长兄,未见史籍。又据《周书》,谯孝王宇文俭在诸子序列中排第八位,其墓志亦称其为“太祖文皇帝第八子”[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3期。,则《周书》失记宇文泰二子年龄当在宇文俭与宇文逌之间。其二,宇文逌葬于京兆万年县,而已知北周皇室多葬于咸阳北原一带。[4]参见周伟洲:《陕西北周墓葬主死葬地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辑;倪润安:《西魏北周墓葬的发现与研究述评》,《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滕王既葬于万年,代王以及其他三王或许也葬在万年。
最后,与宇文逌墓志密切相关的一通墓志是《马称心墓志》,马氏为雍州扶风人:“ 乃祖乃父,并官前周……夫人六郡豪家,五陵贵族。貌美东姝,妍华西子,来应策命,入选王宫。□滕王帝子帝弟,连星连日。地居显贵,位极人臣。……儿封怀德,继室允仪,母以子贵,着书左史。天厌周德,大隋启运,龙飞践祚。开皇初,征召清贤,用充内职,即任尚宫。”[1]韩理洲:《全隋文补遗》,第315页。
墓志交代马称心出自关内大族,入选北周王宫。文中“儿封怀德”即《周书》所记宇文逌之子“怀德公佑”[2]《周书》卷13《滕闻王逌传》。,如此可知马称心乃宇文逌之妻,墓志“滕王”前所缺字应为“配”字之类。马称心死于大业十年,时年六十,其生卒年为555—614年;通过宇文逌墓志可知宇文逌生卒年为556—580年,马氏长其夫一岁。宇文逌遇害时,其与马称心所产怀德公宇文佑也罹难,马氏得以保全,或因法不从坐。但她不计夫子之仇,欣然任职于隋朝后宫;同时杨坚也不忌讳马氏为政敌之妻,任其为高品女官,出入后宫。这种现象更可以用关陇集团说来解释,即杨坚顾及马氏出自关中大族,故灭其夫家而存其命。与时刻身处险境的宇文皇族相比,保护并决定马氏命运的是其更加稳固的关中大族身份。
二、又一场鸿门宴?
以上对宇文逌墓志做了简要分析,从宇文诸王谥号变动、降爵为公、纳王妃为尚宫等微妙现象,可以隐约感到主宰宇文五王命运的幕后之人—隋文帝杨坚。
大象二年(580)五月,北周宣帝驾崩,杨坚依靠内侍郑译、刘昉而入总朝政。半年内杨坚外平尉迟迥、司马消难、王谦叛乱,内除宇文诸王,十二月称隋王,翌年二月即隋开皇元年(581)二月移周祚称帝。与王莽代西汉、曹魏代东汉、司马氏代曹魏等经过较长时间运作以及复杂的政治博弈不同,周隋异代之快,古所罕见,多为后世史家注意。杨坚夺权既速,其禅代合法性资源也就极为缺失。北周静帝加杨坚九锡策命文有:“朕在谅暗,公实总己。盘石之宗,奸回者众,招引无赖,连结群小。往者国衰甫尔,已创阴谋,积恶数旬,昆吾方稔。泣诛罄甸,宗庙以宁。此又公之功也。”[1]《隋书》卷1《高祖纪上》。这是将杨坚为夺权杀宇文诸王事列为一功,而与策文大书杨坚平四方之战功相比,此功记叙用墨极少,不言及实名实事,手法虚与委蛇。杨坚为丞相后,其篡权最大绊脚石便是宇文氏诸王,特别是宇文泰诸子即赵、越、陈、代、滕五王。此五王中,年纪最小的滕王也已二十五岁,诸王皆有总管统军经历且多有战功,赵、越、陈、代诸王曾为灭齐战争主要将领,其中赵王宇文招一度统领后三军。五王皆是北周武帝有意扶持之宗室重臣[2]参见吕春盛:《关陇集团的权力结构演变》,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页。,但周宣帝于大象元年五月命五王就国[3]参见《周书》卷7《宣帝纪》。,这给杨坚夺权创造机会。诸史中,《隋书·高祖纪》与《隋书·元胄传》记杨坚除五王事最详。
《高祖纪》共记录大象二年杨坚杀五王的五个关节点:
1.(五月)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悉恐其生变,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
2.(六月)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滕王逌并至于长安。
3.雍州牧毕王贤及赵、陈等五王,以天下之望归于高祖,因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寝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七月)五王阴谋滋甚,高祖赍酒肴以造赵王第,欲观所为。赵王伏甲以宴高祖,高祖几危,赖元胄以济,语在《胄传》。于是诛赵王招、越王盛。
4.(十月)诛陈王纯。
5.十一月辛未,诛代王达、滕王逌。[1]以上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
杨坚初掌大权即夺诸王在外军权,命之归京,这表明杨坚与五王之间本质上是权力竞争关系,无涉政治正义。但五王至长安后,便与毕王宇文贤(周明帝之子)勾结,欲谋害执政;杨坚虽斩毕王,可他却以德报怨,宽恕五王,赐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至此,五王一方已为制造祸端的非正义一方,而杨坚则表现出宰相气度,谦和退让。之后,五王继续搞阴谋诡计,而杨坚继续持以德报怨之心态,自带酒肴探望赵王,赵王却欲在宴会谋害杨坚。此时五王与杨坚矛盾递进至高潮,有德的杨坚只得反击,杀赵越二王,最后陆续诛杀另外三王。
在杨坚除五王过程中,两个情节最为关键,即五王勾结毕王杀杨坚和赵王在宴会谋害杨坚。这两个情节让杨坚有了杀五王的充分理由,让他站在了正义一方。不唯如此,《高祖纪》还指导读者去读《元胄传》,该传详细描绘了赵王宴会谋害杨坚的场景:“周赵王招知高祖将迁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赵王引高祖入寝室,左右不得从,唯杨弘与胄兄弟坐于户侧。赵王谓其二子员、贯曰:‘汝当进瓜,我因刺杀之。’及酒酣,赵王欲生变,以佩刀子刺瓜,连啖高祖,将为不利。胄进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赵王诃之曰:‘我与丞相言,汝何为者!’叱之使却。胄瞋目愤气,扣刀入卫。赵王问其姓名,胄以实对。赵王曰:‘汝非昔事齐王者乎?诚壮士也!’因赐之酒,曰:‘吾岂有不善之意邪?卿何猜警如是!’赵王伪吐,将入后阁,胄恐其为变,扶令上坐,如此者再三。赵王称喉干,命胄就厨取饮,胄不动。会滕王逌后至,高祖降阶迎之,胄与高祖耳语曰:‘事势大异,可速去。’高祖犹不悟,谓曰:‘彼无兵马,复何能为?’胄曰:‘兵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辞死,死何益耶?’高祖复入坐。胄闻屋后有被甲声,遽请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床,趣而去。赵王将追之,胄以身蔽户,王不得出。高祖及门,胄自后而至。赵王恨不时发,弹指出血。”[1]《隋书》卷40《元胄传》。
此次宴会堪称是鸿门宴的搬演。[2]韩昇已指出《元胄传》赵王宴会之伪,参见《隋文帝传》,第84页。赵王对应项羽一方,杨坚对应汉高祖刘邦一方,而传主元胄则对应樊哙。在元胄的保护下,杨坚逃过一劫,日后诛五王、移周祚而称帝。该故事通过模仿《史记》、《汉书》书写,影射鸿门宴故事,充分发挥了历史叙事的隐喻功能,使人认为赵王为强势无德一方,杨坚为弱势有德一方,以更隐蔽的手段为杨坚代周称帝寻找合法性。至此,《隋书·高祖纪》与《元胄传》的配合,已完全将杨坚诛五王事塑造为有德伐无德的正义合理之举。
然而历史真实的多面性往往是揭穿被构建的“历史逻辑”的利器。《周书》及其他历史资料可用来反思《隋书》所记杨坚诛五王事。
(一)杨坚杀五王之细节谳疑
首先,依据《周书·静帝纪》,对《隋书》所记三个关节点展开分析。
第一,《静帝纪》载,大象二年六月甲子至己巳(初十至十五)之间,“上柱国、毕王贤以谋执政,被诛”[3]《周书》卷8《静帝纪》。。至七月庚子(十七日),“诏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1]《周书》卷8《静帝纪》。。两事相隔逾一月,中间相隔数事。同时《周书》五王传也不言五王与毕王有所联系。故加五王殊礼虽或有“用安其心”之意,但据《静帝纪》,毕王谋杀杨坚为独立一事,应与五王关系不大;而《隋书·高祖纪》竟将二事缀合,直谓五王参与毕王杀杨坚计划,甚为可疑。
第二,《静帝纪》载十月“陈王纯以怨执政,被诛”[2]同上。,此揭露陈王应是以言语腹诽之类而获罪,杨坚竟予以极刑,其待宇文诸王之酷烈可见一斑。而《隋书·高祖纪》记此事仅四字“诛陈王纯”,有为杨坚讳之嫌。
第三,《静帝纪》载十二月辛未“代王达、滕王迥并以谋执政被诛”[3]同上。。而《隋书·高祖纪》则记杀二王在十一月辛未。宇文逌墓志的出土,证明《高祖纪》有误,代滕二王确实死于十二月。岑仲勉先生指出:“据罗校朔闰考三,是年十一月癸未朔,月内无辛未,隋书此条,盖误与下文十二月甲子一条相倒错,同时复误系十一月于辛未之上也。”[4]岑仲勉:《隋书求是》,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页。此虽可备一说,但其以《隋书》该条先倒错至十二月之前,又误系于十一月,推论失于机巧。笔者以为杨坚杀五王为大事,唐初修《隋书》应本隋朝国史实录,《周书》不误而《隋书》误,其中或有蹊跷。《隋书·高祖纪》十一月杀二王条后,便是周帝三大策命诏书,即十二月诏杨坚为王,大定元年二月策杨坚加九锡建台置官,不久即下诏禅让。[5]参见《隋书》卷1《高祖纪上》。历史事实是杨坚称王后便杀掉代滕二王,但《高祖纪》若将此事系于杨坚称王—加九锡—称帝这一递进的完美的禅代程序之间,便有损杨坚之德,这或许是隋朝史臣错系杀二王在杨坚称王之前的初衷。
其实,《隋书》本书所记杨坚诛五王事也有破绽。赵翼指出:“《隋书·文帝本纪》,周五王谋隋文帝,帝以酒肴造赵王招,观其指趣,王伏甲于卧内,赖元胄以免。是文帝知招欲谋害,故以酒肴赴之以观其意也。《元胄传》则云,招欲害帝,帝不之知,乃将酒肴诣其宅,则已与纪异矣。《周书·赵王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则又非隋文之以酒肴赴之也。”[1]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277页。
赵翼此处引《元胄传》“招欲害帝,帝不之知”,实出自《北史》。[2]《廿二史札记校证》已指出,见该书第288页。参见《北史》卷73《元胄传》。但《北史·元胄传》以《隋书·元胄传》为本,李延寿既据《隋书·元胄传》衍生出“帝不之知”,又通过《隋书·元胄传》杨坚“犹不悟”、“复入坐”,可知《隋书·元胄传》确实在努力塑造“帝不之知”的状态,这与《隋书·高祖纪》杨坚知五王谋而“欲观所为”也确实相抵牾。同时赵翼还指出,据《周书·赵王传》杨坚参加赵王宴会也并非自带酒肴。此两处虽为诸史之间细节差异,但杨坚是否知赵王之谋、是否自带酒肴,皆事关杨坚诛五王之合理性塑造,不可不察。总之,《隋书·元胄传》(《北史·元胄传》)与《高祖纪》之抵牾让杨坚赴赵王宴会事变得扑朔迷离,此正如刘知几所批评:“今之记事也则不然。或隔卷异篇,遽相矛盾;或连行接句,顿成乖角。”[3]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此外,《周书·静帝纪》与《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记杨坚杀五王事也有差异。如《静帝纪》与《隋书·高祖纪》一致,记杨坚杀五王皆为“被诛”。[1]参见《周书》卷8《静帝纪》。而《文闵明武宣诸子传》除言赵王被诛外,其余几王多言“时隋文帝专政,翦落宗枝”,“为隋文帝所害”[2]参见《周书》卷13《文闵明武宣诸子传》。。两篇对待杨坚杀五王事,态度截然相反,必非出自一人之手。刘知几言令狐德棻以牛弘《周史》为底本,不过“重加润色”而已。[3]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第468页。牛弘为隋代重臣,故《静帝纪》言五王被诛应出其意;而《文闵明武宣诸子传》言诸王被害,更直呼“隋文帝”,此必非牛弘所书,应是经令狐德棻润色,或者是德棻别有所据而书。[4]令狐德棻祖令狐整为北周重臣,得赐姓宇文,其“宗人二百余户,并列属籍”。参见《周书》卷36《令狐整传》。这一特殊家世给令狐德棻为周室诸王作传提供便利,且更能保证《周书》诸王传之真实性,《周书》记代滕二王被害时间比《隋书》准确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杨坚杀五王之政治背景
为解决以上疑点,需要深入了解杨坚杀五王的政治背景。杨坚突然总揽朝政与中央军权后,最担心的便是地方出镇五王与诸军事总管叛乱。故他立即对外采取措施,一派亲信夺地方兵权,二即引五王进京。此种高明的政治策略与史书所言“高祖性猜忌”、“任智而获大位”[5]《隋书》卷25《刑法志》。相契合。
关于五王进京方式,《隋书·高祖纪》明言“称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词以征之”[6]《隋书》卷1《高祖纪上》。,此时不言赴宣帝之丧(或宣帝不豫)[7]《隋书·高祖纪》记宣帝死后征五王入朝,而《周书·宣帝纪》(《周书》卷7)则言宣帝死前两天追五王入朝,当从《周书》。而借口赵王嫁女,足见杨坚之诈。同时五王进京也并非顺利,《隋书·崔彭传》载:“ 及高祖为丞相,周陈王纯镇齐州,高祖恐纯为变,遣彭以两骑征纯入朝。彭未至齐州三十里,因诈病,止传舍,遣人谓纯曰:‘天子有诏书至王所,彭苦疾,不能强步,愿王降临之。’纯疑有变。多将从骑至彭所。彭出传舍迎之,察纯有疑色,恐不就征,因诈纯曰:‘王可避人,将密有所道。’纯麾从骑,彭又曰:‘将宣诏,王可下马。’纯遽下,彭顾其骑士曰:‘陈王不从诏征,可执也。’骑士因执而锁之。彭乃大言曰:‘陈王有罪,诏征入朝,左右不得辄动。’其从者愕然而去。”[1]《隋书》卷54《崔彭传》。
由此可知,杨坚虽诈,纯王亦非愚,故最后崔彭只得押解陈王至长安,杨坚与五王斗争此时已正式开始。五王被引诱威逼入京后,自然得知宣帝已死与杨坚之诈,但此时杨坚已掌控京城兵权,五王行踪应在其监视之下。故《隋书·高祖纪》所言五王与毕王勾结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其实杨坚除毕王,应另有原因。在赵王宴会上,杨坚说道:“彼无兵马,复何能为?”此言既道出五王入京后,几乎已被解除武装,又可知杨坚对宇文诸王手握兵权极为提防。而大象二年六月五王入京,五王再无兵权,此时宇文诸王中唯明帝之子毕王宇文贤还任雍州牧。据《北周六典》,雍州牧为九命,地位权力甚高[2]参见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37—640页。,且雍州不设总管府[3]参见严耕望:《北周总管区图》,《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04页。,雍州牧应有发动组织乡兵权力。史载宇文贤建德年间(572—577)已出任刺史、出镇荆州。[4]《周书》卷13《毕剌王贤传》。至大象二年,他应与赵王招等五王一样,已成长为一员具有权力角逐能力的宇文宗室。五王被杨坚夺权后,身为明帝之子,手中掌握一定武装的毕王自然成为杨坚在长安首要消灭的势力,这是意料中事。从《隋书·高祖纪》载高祖“执贤斩之”,《周书》记毕王被害“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1]《周书》卷13《毕剌王贤传》。,可知杨坚除毕王(明帝一支)何其果断残忍,绝非《高祖纪》所塑造的谦和有德之辈。此外,《周书》记毕王死因是“贤性强济,有威略。虑隋文帝倾覆宗社,言颇泄漏,寻为所害”[2]同上。,此见毕王与十月陈王受害一样,因言获罪,未及付诸行动即被杨坚察觉。
清人黄恩彤评价杨坚诛毕王:“周之宗王,坚所忌也。坚欲篡周必先翦落其枝叶而后拔其本根。贤与五王,与坚势难两立也。坚既杀贤父子,若同时并诛五王,则尉迟必声罪致讨,师更有名矣。阳置不问,而阴为之防,五王直机上肉耳。”[3]黄恩彤:《鉴评别录》卷34《陈纪二》,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辑第2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11页。
查毕王谋泄事,其时毕王别驾为杨坚族子杨雄,“(杨雄)知其谋,以告高祖”[4]《隋书》卷43《观德王雄传》。,毕王杀身之祸正因杨雄告发。此知毕王行踪也早已被杨坚监控,他与五王一样,也已是“机上肉耳”。只不过杨坚顾及内外,杀毕王后又加五王殊礼,然后再找机会次第杀之。
五王未必与毕王同谋,但也绝不甘受杨坚摆布。赵王为诸王之长,资历威望最高,在宣帝驾崩之际曾被认为是静帝元辅的第一人选[5]《周书》卷40《颜之仪传》。,故他成为五王反杨坚之核心。刚到长安,赵王曾试图联络梁州刺史李璋与内卫反攻杨坚,可未及谋划好便被杨坚得知。[6]《隋书》卷50《李安传》。
至此,杨坚赴赵王之宴的前提已越发明显:五王已无兵权甚至被杨坚监控;杨坚灭毕王一支使其与宇文诸王矛盾已发展至兵戎相见;杨坚已成功消解赵王一次政治图谋,他占有绝对优势,灭五王只欠借口而已。在此前提下杨坚赴宴,不能再如《北史·元胄传》所说“帝不之知”。而详辨《隋书·元胄传》,可知赵王欲杀杨坚,只有父子三人,赵王自为项庄;至杨坚逃离,一元胄便阻挡赵王,赵王势孤可见一斑。综合诸史对杨坚杀五王事进行细节分析与政治形势分析后,可以推论:毕王应确有害杨坚之谋,赵王应确有宴会害杨坚之举;但毕王应非《隋书·高祖纪》所载曾与五王通谋,有汹汹之势,赵王更非《元胄传》所载曾以杨坚为“鱼肉”,其余诸王亦仅牵连受害而已。[1]据《隋书》卷64《李圆通传》,圆通为杨坚侍卫,“周氏诸王素惮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图为不利。赖圆通保护,获免者数矣”。查诸王与杨坚关系,诸王曾以兵刃近杨坚之事或仅赵王宴会一次,其余谋划大抵皆胎死腹中,《李圆通传》盖有虚言。《隋书》之《高祖纪》、《元胄传》所记杨坚诛五王事是史官在相关史实基础上,经润色加工甚至改动而成,它们试图掩盖杨坚杀五王的政治动机,并努力将其塑造为杨坚代周“合法”历程的重要环节。
三、结语
宇文逌墓志的再现,为后世提供了杨坚杀五王事件的重要信息。它向后世表明,《周书》所记五王恶谥可能非最初谥号,极有可能是后来杨坚所改。墓志所记宇文逌死于大象二年十二月,再次证明了《周书》记载正确,《隋书》记载之误。该墓志还提供了周隋之际的重要政治文化信息,如记宇文逌为“河南洛阳人”,表明与宇文氏着力塑造关陇集团相对,当时权贵阶层依然有浓厚的洛阳情结,此一情结可能与西魏北周的北魏(洛阳)正统观有一定联系。
借助宇文逌墓志,当我们再次审视《隋书》所记杨坚诛五王事时,可以发现《隋书》、《周书》对于相关细节多有不同描述。在《周书》记述中,杨坚杀毕王可能与赵王等五王关系不大;据《周书》,赵王邀杨坚赴宴,未提杨坚自带酒肴,同时结合诸史,赵王之宴也绝非《隋书·元胄传》所描述,似是鸿门宴的简单搬演;据《周书》和宇文逌墓志,代滕二王应死在十二月杨坚封王之后。而《隋书》先将毕王之谋与五王结合,构成五王之恶端;再叙杨坚以德报怨,带酒肴赴宴,至赵王之恶彰显才次第诛杀五王。正是通过这种“情节化解释”[1]海登·怀特说:通过鉴别所讲述故事的类别来确定该故事的“意义”,这就叫作情节化解释。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如果史学家赋予它一种悲剧的情节结构,他就在按悲剧方式“解释”故事;如果将故事建构成喜剧,他也就按另一种方式“解释”故事了。情节化是一种方式,通过它,形成故事的事件序列逐渐展现为某一特定类型的故事。参见氏著,陈新译:《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隋书》试图将杨坚杀五王事塑造为一种正义压制邪恶、有德伐无道的历史正剧,以为杨氏代周这部历史喜剧张本。《隋书》为唐初魏征等人所修,他们自然不会为杨坚掩恶,可面对隋朝史官对杨坚杀五王的“情节化解释”,至少他们在甄别史料时表现得并不谨慎。余嘉锡先生谈到“古书多造作故事”时说道:“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也。”[2]余嘉锡:《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6页。此言小则切合《元胄传》吸收鸿门宴故事,大则切合《隋书》、《周书》诸纪传中有关杨隋代周合法性的历史书写。
隋文帝杨坚杀五王事是周隋之际重要的政治事件,人们往往把五王之死与天象天命联系。如《周书》自《宣帝纪》始,便努力营造杨氏代隋天象,大象二年:七月,“月掩氐东南星”、“月掩南斗第六星”伴随着五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岁星与太白合于张,有流星大如斗,出五车,东北流,光明烛地”伴随着赵越二王被诛;十月“有流星大如五斗,出张,南流,光明烛地”伴随着陈王被诛;在滕代二王被诛的十二月亦有天象“荧惑入氐”。[1]参见《周书》卷13《文闵明武宣诸子传》。《北史》删诸天文事。月行失道、流星坠地、荧惑现,这些或暗示大臣执权、君道不明,或暗示地下有兵。[2]参见《隋书》卷20《天文志中》。
《隋书·天文志》也有两则五王之死的预言:“(宣政元年,578)八月庚辰,太白入太微。占曰:‘为天下警。’又曰:‘近臣起兵,大臣相杀,国有忧。’其后,赵、陈等五王,为执政所诛,大臣相杀之应也。[3]《隋书》卷21《天文志下》。(大象元年)四月戊子,太白、岁星、辰星合,在井。占曰:‘是谓警立,是谓绝行,其国内外有兵丧,改立王公。’又曰:‘其国可霸,修德者强,无德受殃。’其五月,赵、陈、越、代、滕五王并入国。后二年,隋王受命,宇文氏宗族相继诛灭。”[4]同上。
隋人王劭曾言符瑞以媚杨坚,其中言及建德六年(577)亳州白龙与黑龙斗事有:“死龙所以黑者,周色黑。所经称五者,周闵、明、武、宣、靖凡五帝。赵、陈、代、越、当五王,一时伏法,亦当五数。”[5]《隋书》卷69《王劭传》。此足见杨坚杀五王在隋人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政治印象。
面临着屠杀宇文子孙的强大道德压力,诉诸天文,或许是杨隋对周隋禅代这部悲喜剧的另一种情节化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