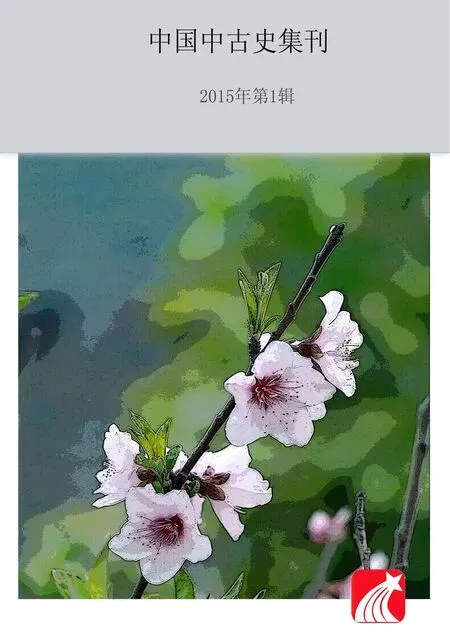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
2015-09-11毋有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毋有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
毋有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关于拓跋鲜卑部建魏之前的地域发展过程,最为重要的文献材料毫无疑问当属《魏书·序纪》。《序纪》源自北魏早期邓渊所作《代记》,而《代记》应是邓渊根据对拓跋部史诗《真人代歌》辑集、译释、解读、整理而成的著作。[1]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国史之狱的史学史考察》,《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217—243页。《序纪》包含有丰富的拓跋部社会发展与地域转移的真实信息,其内容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学工作与现代遗传学研究所确认。[2]参见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1980年米文平等人在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发现拓跋部先祖旧墟石室,首先确证了《魏书·礼志》中北魏太武帝天平真君年间官员在石室中举行祭奠的记载,也进一步印证了《魏书·序记》,对宿白之前根据考古学资料所做的推断亦是一个重要补充。这一重要发现经过及相关研究后收入米文平论文集:《鲜卑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另依据考古学家提供样本所做的现代遗传学研究,也倾向于认证《魏书·序记》的说法。参见于长春、谢力、张小雷、周慧、朱泓:《拓跋鲜卑与四个北方少数民族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东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拓跋鲜卑和匈奴之间亲缘关系的遗传学分析》,《遗传》2007年第10期。北魏之前拓跋部及其活动地域的情况,历史学界多有研究和论述,但看法也有不一致之处。[1]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如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97页;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5—238页;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72—307页;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康乐:《从草原游牧封建制到家产制》、《“帝室十姓”与“国人”》、《拓跋魏的国家基础》,《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稻禾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9页;何德章:《鲜卑代国的成长与拓跋鲜卑初期汉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1年第1期;张继昊:《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勋臣贺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白部和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二》、《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匈奴刘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分见《空大人文学报》第5、6、7期;田余庆:《拓跋史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姚大力:《论拓跋鲜卑部的早期历史》,《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安介生:《试论拓跋鲜卑的早期迁徙问题》,《历史地理与山西地方史新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8—81页;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79页。学术界更详细的研究概况可参见倪润安:《拓跋起源问题研究述评》,《文物春秋》2011年第1期;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这里结合前人相关研究,对北魏之前拓跋部的活动地域进行考察,探究后来形塑北魏王朝最初地域的空间结构及其互动机制,为理解北魏国家提供历史政治地理方面的思路。这一时期拓跋部及其所领导的部落结合体具体的政治组织形态,学界讨论甚多,但依据材料究属有限,限于个人学力,本文不做讨论。在文中,为契合所据文献材料的表述习惯,对拓跋鲜卑本部与由拓跋鲜卑支配下不同部族构成的政治实体没有加以刻意的区分,除非有特别说明,概以“拓跋鲜卑”、“拓跋部”来称呼。
一、试释“匈奴之故地”
《魏书·序纪》:“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匈奴曾经在蒙古高原建立起自己的游牧帝国,地域辽阔。拓跋部后来活动所及的漠南草原地区,包括古阴山山脉(即今乌拉前山—大青山山系)沿长城一线,河套及其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以及今河北省张家口北部的坝上高原一带,都是“匈奴之故地”。[1]唐晓峰认为,战国秦汉时期,匈奴巢穴多据山地,匈奴善于山地作战,山地物资是匈奴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在与匈奴有关系的山地中,被认为匈奴本体起源地的阴山可能是最重要的。参见唐晓峰:《山地对于匈奴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侯仁之师九十寿辰纪念文集》,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98页。辛德勇认为,匈奴活动的古阴山山脉,指的是今天的乌拉前山—大青山山系,参见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1—255页。唐晓峰据此进一步指出,古阴山山脉乌拉山以西的河套地区,应该属于战国赵长城修筑之后的塞外,是匈奴活动的地域,与乌拉山以东在人文地理上应分属于不同的区域。参见唐晓峰:《河套乌拉山在战国时期的人文地理意义》,武汉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石泉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330页。从文本的时代性角度考虑,匈奴曾经活跃过的大漠、阴山南北在《魏书》里恐怕均可称为“匈奴之故地”。诘汾和之后力微所居的“匈奴故地”,具体在哪里呢?
阴山山脉是今天中国一条重要的自然界线,南北两侧在水文、地貌方面的差异比较显著。山南为外流区,属黄河、海河水系,流水侵蚀为主,以海平面为侵蚀基准面,河流溯源侵蚀与分割作用比较强烈,沟谷深切,地面比较破碎,在砂质黄土覆盖区,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山北为内流区,河流稀少,水量小,各个内陆洼地都有它自己的侵蚀基准。侵蚀基准面的升高,削弱了侵蚀作用,所以沟谷浅缓,地面平坦而较完整。地貌外营力以风蚀为主,机械风化强烈,风蚀、风积作用明显,分布着大面积沙丘和盐沼,植被明显稀疏。阴山南北两侧在景观和农业生产上也有显著差异。山南年均温5.6~7.9度,山北为0~4度;山南≥10度,积温为3000~3280度,山北为900~2500度;山南无霜期130~160天,山北为95~110天;山南风小而少,年平均风速2米/秒,山北风大而多,年平均风速4~6米/秒;年降水量东经110°以东,南北相差70~100毫米;东经110度以西,因位于干旱区,年降水量都很小,南北相差25毫米左右。因而在农业生产上山南为农业区,山北为牧业区,山区则为农牧林交错地区。[1]孙金铸:《阴山山地地貌及其地理意义》,《内蒙古地理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45页。阴山为一不对称的断块山,北坡平缓,逐渐倾没于高原之中;南坡陡峭,以巨大的东西向断层与河套平原截然分开。阴山山地间有许多山间盆地。在山间盆地中,地下潜水丰富,埋藏较浅(2~5米),水质良好,便于人畜饮用和灌溉。[2]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与开发整治》第9章,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8页。《魏书·序纪》:“初,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从阴山一带的自然条件来看,圣武皇帝诘汾当已带领拓跋部南移至阴山山地一带。但是阴山山脉东西绵延数千里,诘汾驻牧之地还需进一步考索。
《序纪》又云:“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生而英睿。元年(220),岁在庚子。先是,西部内侵,国民离散,依于没鹿回部大人窦宾。始祖有雄杰之度,时人莫测。后与宾攻西部,军败,失马步走。始祖使人以所乘骏马给之。宾归,令其部内求与马之人,当加重赏,始祖隐而不言。久之,宾乃知,大惊,将分国之半以奉始祖。始祖不受,乃进其爱女。宾犹思报恩,固问所欲。始祖请率所部北居长川,宾乃敬从。积十数岁,德化大洽,诸旧部民,咸来归附。二十九年(248),宾临终,戒其二子,使谨奉始祖。其子不从,乃阴谋为逆。始祖召杀之,尽并其众,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马二十余万。”这是一段拓跋部政治发展的重要材料。拓跋部在诘汾末期遭受“西部内侵,国民离散”,力微与部落成员一度转而投靠没鹿回部的首领窦宾,后在窦宾支持下北居长川。长川,《水经注》卷13《漯水注》:“漯水又东,左得于延水口,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于延水即今东洋河,东洋河源出内蒙古兴和县东北部山丘,在兴和县一段的干流又叫后河。《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兴和县文物图》在后河东北标注有叭沟墓群。叭沟墓群在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叭沟村,位于与河北省尚义县交界的大青山西坡,面积约1万平方米,墓葬年代为北魏,属鲜卑文化遗存。[1]《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之《兴和县文物图》,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52—253页;《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61页。又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叭沟东北的大青山内有“北魏魔崖石硅(当作摩崖石碑)”古遗迹。[2]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制印院编著:《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之《兴和县》,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16—217页。大青山即东汉时檀石槐“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的“弹汗山”,是很早就有鲜卑活动的地方。又《魏书》卷3《太宗纪》明元帝泰常八年(423)“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3]在叭沟墓群西北,《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所标战国赵北长城的内侧,兴和县民族团结乡治所黄土村西南2.5公里有五号村遗址,常谦以为即北魏长川城所在(他称为土城子遗址),见常谦:《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笔者认为力微居长川时拓跋部尚处于游牧状态,“长川”与“长川城”有关联,但所指并非完全相同。。结合上述材料,笔者认为长川可能就在今兴和县民族团结乡一带。民族团结乡今有公路自东通往河北省尚义县县治,尚义县再往东就是张北高原,而张北高原正是后来拓跋禄官一部驻牧的地方。
没鹿回部,《魏书》卷113《官氏志》:“次南有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周书》卷30《窦炽传》:“窦炽字光成,扶风平陵人也。汉大鸿胪章十一世孙。章子统,灵帝时,为雁门太守,避窦武之难,亡奔匈奴,遂为部落大人。后魏南徙,子孙因家于代,赐姓纥豆陵氏。累世仕魏,皆至大官。”《新唐书》卷67《宰相世系表一下》云:“(窦)统字敬道,雁门太守,以窦武之难,亡入鲜卑拓拔部,使居南境代郡平城,以间窥中国,号没鹿回部落大人。后得匈奴旧境,又徙居之。生宾,字力延,袭部落大人。二子:异、他。他字建侯,亦袭部落大人,为后魏神元皇帝所杀,并其部落。他生勤,字羽德。穆帝复使领旧部落,命为纥豆陵氏。晋册穆帝为代王,亦封勤忠义侯,徙居五原。生子真,字玄道,率众入魏,为征西大将军。”抛开《窦炽传》与《宰相世系表》中的伪托部分,可知纥豆陵部的前身即为没鹿回部,窦宾时居于“匈奴旧境”,神元皇帝力微时拓跋部并其部落,穆帝猗卢时该部始称纥豆陵氏,西晋册封猗卢为代王后徙居五原。按《魏书》又记有纥突邻部。《魏书》卷2《太祖纪》:“(登国)五年(390)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慕容垂遣子贺驎率众来会。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与贺 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大破之。六月,还幸牛川。卫辰遣子直力鞮寇贺兰部,围之。贺讷等请降,告困。秋七月丙子,帝引兵救之,至羊山,直力鞮退走。八月,还幸牛川。遣秦王觚使于慕容垂。九月壬申,讨叱奴部于囊曲河,大破之。冬十月,迁云中,讨高车豆陈部于狼山,破之。十有一月,纥奚部大人库寒举部内属。十有二月,纥突邻大人屈地鞬举部内属。帝还次白漠。”《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柔然等部》图将鹿浑海标在今蒙古国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将意辛山标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面中蒙边境的哈德廷敖包一带。牛川是一个很重要的路线参照点,虽然现在很难完全指实,但正如前田正名所说,可能是位于白道岭与地当盛乐与平城交通要冲的善无(今山西省右玉县)之间的一条河流。在今内蒙古凉城县附近。[1]〔日〕前田正名著,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126页。羊山、囊曲河地点不明。但已经可以看出,纥突邻部活动在阴山以北的乌兰察布高原一带。姚薇元与陈连庆均认为纥突邻部即纥豆陵部,属于高车部落。[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175—180页。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123页。沿乌兰察布高原东南行,相继可达力微曾经居住的长川一带、禄官曾经驻牧的张北高原一带。但《序纪》说力微是“北居长川”,如没鹿回部即纥突邻部,方位不合。除非《序纪》所记方位可以作别的解释,否则很难理解这些材料之间的关系。这里需要留意阿尔丁夫的相关研究。阿尔丁夫认为,在中国北方民族、上古中原民族,甚至欧亚大陆的其他民族发展的早期,曾经流行过以依据面向日出方向者的体位确定四方的方式及由这种方式确定的四方概念。与“依据太阳运行的轨迹”或“太阳在一昼夜间的不同位置”相对应,具体而言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前胸(日出方向)为前,后背(日落方向)为后,右手(日中方向)为右,左手(日没方向)为左;另一种是以前胸(日出方向)为南,后背(日落方向)为北,右手(日中方向)为西,左手(日没方向)为东。后一种方式与我们今天通行的方位概念东西南北不合,但它可以解释一些历史文献(包括《魏书》里的一些材料)以及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材料里面的方位说法。[2]阿尔丁夫:《匈奴史研究暨其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131—189页。另见阿尔丁夫:《日出、日落方向并非从来就被称作东方、西方—从北方民族方位观念发生、发展和演变谈起》,《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浅谈北方民族空间方位观念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古代蒙古文化史上方位问题之我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如果阿尔丁夫的说法可以成立,没鹿回部可能曾驻牧在张北高原一带,那里有丰美的牧场,在战国、秦汉时代亦属于“匈奴旧境”。力微吞并没鹿回部之后,张北高原转而成为拓跋部的驻牧地。这与力微之前“北居长川”(其实是自张北高原向西到长川),后来禄官以拓跋大宗驻牧在张北高原相合。[1]不过毕竟《序纪》源自早期拓跋部口耳相传的材料,不论对北魏早期的邓渊来讲,还是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讲,在译释、解读、整理材料的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文化上的误读。尽管还可以找出一些材料佐证阿尔丁夫的结论,但《序纪》里面也有很多与今天方位观念相合,而与阿尔丁夫的解释不一致的地方。拓跋部和北魏史料中有不少窒碍难通之处,这也是笔者在解释时应当有所保留的地方。诘汾南迁后可能驻牧在今天乌兰察布高原东侧的阴山山地一带,与没鹿回部相邻。
二、试析“定襄之盛乐”
《魏书·序纪》:“(力微)三十九年(258),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于是与魏和亲。四十二年(261),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景元二年也。”盛乐即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土城子遗址。从盛乐镇东行,今有路可达内蒙古凉城县,而在《魏书》里多次出现的牛川,如上所说,很可能就在凉城县。凉城继续往东经内蒙古丰镇市或丰镇北面的察哈尔右翼前旗,可达力微曾经驻牧过的长川,即今兴和县民族团结乡一带。这条路线在明长城和阴山山地之间。如前所述,阴山山地间有许多山间盆地,地下潜水丰富,埋藏较浅,水质良好。从今天地图上还可以看到沿这条线有不少湖泊,便于过往的人畜饮用[2]这条路线处于孙金铸所说的察哈尔湖区一带。察哈尔湖区东起赛行坝和大马群山,西以凉城山地与土默特平原相接,北部以羊群庙至温都尔庙一线与乌兰锡林湖区分界,共约有160个湖泊,分布比较普遍。参见孙金铸:《内蒙古高原的湖泊》,《内蒙古地理文集》,第64页。,这条路线可能早在拓跋部经行之前就已经被开辟利用。力微当是沿着这条路线迁到了“定襄之盛乐”,并从此开始与中原王朝发生关系。力微在258年迁居盛乐,自此直到北魏天兴元年(398年)道武帝迁都平城,拓跋部的经营重心才再次发生大规模的地域转移。[1]据《魏书》卷2《太祖纪》:天兴元年(398)“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但《水经注》卷13《漯水注》:“(漯水)迳平城县故城南……魏天兴二年(399),迁都于此。”似乎与《太祖纪》有矛盾。可能《水经注》这里的“二”是“元”的残字;如果《水经注》记载无误,也可能迁都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经营和准备的过程,即便确定在平城一带建都,具体地点的选定也会有一个过程。如上所述,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始于力微,力微在《序纪》里被尊为“始祖”。一百二十多年后的“登国元年(386)春正月戊申,(道武)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夏四月,改称魏王”[2]《魏书》卷2《太祖纪》。,从此开始北魏的历史。可以说,盛乐不论对拓跋部本身的发展,还是对后来北魏王朝的肇建,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3]包文胜结合前人研究,对盛乐时期拓跋鲜卑部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历史学的梳理。参看包文胜:《盛乐时期拓跋鲜卑历史初探》,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在拓跋部政治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两个主导南迁的部落首领“推寅”。根据《魏书·序纪》:“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这个大泽一般认为就在今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到了“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过去有学者把《序纪》里提到的献皇帝邻所号的“推寅”与檀石槐部落联盟时期的西部大人日律推演联系起来,据此认为拓跋部早在东汉桓帝时就已经迁到了蒙古高原的西北部,并在圣武皇帝诘汾时南迁到了汉五原郡一带。[1]马长寿:《乌桓与鲜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73—174页。黄烈以为不论是第一推寅,还是第二推寅,在年代上均与檀石槐时的西部大人日律推演不相当,不宜混同,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77—278页。但这正如罗新所说,推演或推寅不过是一种常常作为北族官号使用的美称,檀石槐时期的日律推演和拓跋历史上的两个推寅之间不一定存在相关性。[2]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第68—69页。从《序纪》文本里提示的时空逻辑来说,力微当是沿长川—牛川—盛乐一线,即今日兴和(长川)—丰镇—凉城(牛川)—和林格尔(盛乐)一线或兴和(长川)—察哈尔右翼前旗—凉城(牛川)—和林格尔(盛乐)一线自东向西发展[3]386年,拓跋珪在牛川举行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建元登国。同年,徙居定襄之盛乐,拓跋珪改称魏王,这是北魏国家历史的开端,据此也可以看出这条路线的重要性。,由此进入肥沃的土默特平原,在这里确立自己的部落领导地位,并开始有了沿盛乐—善无—平城一线自西向东发展的企图。[4]在北魏道武帝之前一直驻牧在善无、豺山之间的“白部”或曰“和(素和)氏”,因为居于盛乐与平城、拓跋部与内地中原王朝的交通关节点上,所以《序纪》云;“(力微)三十九年(258),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拓跋部西迁盛乐伊始,白部就成为重点关注的部落。参见张继昊:《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白部和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二》,《空大人文学报》第6期。
258年,力微率部迁居“定襄之盛乐”后,拓跋部经历了一段较为平静的发展时期,《序纪》所谓“始祖与邻国交接,笃信推诚,不为倚伏以要一时之利,宽恕任真,而遐迩归仰。魏晋禅代,和好仍密”。但到了力微五十八年(277年),拓跋部领导的部落联盟发生内乱,“诸部离叛,国内纷扰”[5]曹永年:《拓跋力微卒后“诸部叛离,国内纷扰”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汉文版)》1988年第2期。。尽管拓跋部衰落,但并没有放弃对盛乐一带的经营。昭皇帝禄官时,“分国为三部”,“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猗卢部当在今和林格尔县盛乐镇一带。305年猗㐌、307年禄官相继死后,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向大同盆地发展的企图日益明显。“六年(313),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实际上是把平城和盛乐均作为拓跋部发展的中心,“城盛乐”一句,也让我们想到拓跋部游牧社会风尚的某种流变。猗卢末年,拓跋部又陷入内讧,政治发展再次出现波折。[1]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拓跋史探》,第9—61页。但对盛乐的经营并未止步。337年,烈皇帝翳槐重新领导拓跋部时,“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到昭成帝什翼犍领导拓跋部时,虽于建国三年(340)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但在次年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显示拓跋部虽然在土默特平原四处拓展,盛乐在政治与交通上依然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局面要一直延续到北魏前期。[2]《魏书》里除有“定襄之盛乐”,尚有“云中之盛乐”。“云中之盛乐”其实就是“昭成帝”什翼犍迁居的“云中之盛乐宫”。参见〔日〕松下宪一:《拓跋鲜卑的都城与陵墓—以呼和浩特为中心》,《草原文物》2011年第1期,该文系由王庆宪译自日文《“定襄之盛乐”与“云中之盛乐”—鲜卑拓跋国家的都城与陵墓》,《史朋》2007年第40号。吕阳结合考古资料认为,盛乐宫的地理位置应在今天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和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之间,并靠近古城村。参见吕阳:《“盛乐城”与“盛乐宫”地理位置考辩》,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土默特平原也称土默特—达拉特平原、土默川平原、呼和浩特平原和前套平原,位于大青山南麓,黄河北岸,北部为阴山山前洪积倾斜平原,南部为黄河和大黑河等河流的冲积—洪积平原。[1]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与开发整治》第9章,第379—380页。平原整体地势东南低,西北、北、东北高,自然排水条件比河套平原(狭义的河套平原只指后套)要好,特别在大黑河地区潜水含水层较薄,多数为3~10米,且下层又普遍分布着大量承压水,适宜灌溉。[2]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综合考察队:《内蒙古自治区及东北西部地区地貌》,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117—119页。土默特平原历史时期就是一个宜农宜牧的好地方,在今天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业区。盛乐处于今天土默特平原的东南边缘。盛乐所在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在地貌上是土默特平原向晋西北黄土丘陵和蛮汉山过渡带,地势自东南向西北倾斜。属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5.6度,年日照时数3000小时,年降水量418毫米,无霜期118天。[3]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制印院编著:《内蒙古自治区地图集》之《和林格尔县》,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34—35页。拓跋部从张北高原沿长川—牛川—盛乐一线迁到此地长期驻牧,首先应该是因为这里有较之张北高原与阴山一带更为优良的游牧条件。盛乐位于和林格尔县盛乐镇(原名土城子村)北。这一带在战国时属云中郡,汉为定襄郡成乐县,唐代在此设立单于大都护府,辽代为振武县,元代为振武城,明代属红城卫,是内蒙古地区保存最好、沿用时间最长的城址之一。[4]《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之《土城子城址》,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98—299页。以盛乐为中心,自此向西、西北、北、东北诸方向,经阴山山地可与大漠南北相通;向南通过黄河岸边诸津渡,可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自此经善无县(山西右玉县)南下或东行,可与桑干河流域以及中原地区发生联系。[1]参见王凯:《北魏盛乐时代的道路交通》,《北魏盛乐时代》附篇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36—245页。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篇柒“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篇捌“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篇玖“天德军东取诺真水 通云中单于府道”,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229—287页,图六“唐代关内道交通图”;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篇叁柒“太原北塞交通诸道”,第1335—1396页,图十八“唐代河东太行区交通图(北幅)”。这是长城内外诸种政治势力在盛乐一带多次建城或经营的重要交通背景。[2]对盛乐的地理区位,其他学者也有论述,参见张殿松、赵军:《浅析北魏的第一个都城盛乐的选址原则》,《山西建筑》2008年第3期;李凭:《盛乐成为漠南中心的历史背景》,《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3期。
三、从“分国为三部”到“总摄三部”
阴山山脉向东绵延至今河北省康保县,康保以南为坝上高原。坝上高原在地貌分区上属于内蒙古高原的南延部分。河北的坝上高原从地貌上还可以细分为两个亚区:围场高原亚区和张北高原。张北高原北延至今河北省康保县,康保以北属于阴山山地的范畴。[3]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北省志》第三卷《自然地理志》第三章第一节,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1版,第28—32页。《资治通鉴》卷82和《魏书》卷1《序纪》,晋惠帝元康五年(295),“昭皇帝讳禄官立,始祖之子也。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西晋时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南面的官厅水库一带,又据《水经注》卷14,濡水即今滦河,濡源应指今滦河上游闪电河源头一带,则禄官一部驻牧地正在张家口北部的坝上高原—张北高原上。张北高原除东部闪电河一带属滦河流域外,其他都为内流区。地表多由喷出岩流覆盖。低洼部分有大小不等的湖泊(蒙古语称“淖尔”、“诺尔”),湖泊周围多为沼泽滩地,湖水面积只占湖盆的一小部分。区内地势一般在海拔1400~1600米之间。南北均有山岭与丘陵分布,北部多为残丘状态,但所占面积不大,高原大部为波状起伏、滩淖棋布的景观。河流大都是短浅、系统紊乱、以湖泊为尾闾的内陆河。湖泊周围属台地状态地貌,台地上沉积物很薄,剥蚀强烈,甚至岩石裸露。湖泊附近的地下水位距地面多在3米左右,因而形成丰美的草滩。[1]邓绶林等编著:《河北地理概要》第二章第二节,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54—55页。地表丰美的草滩是禄官一部在此驻牧的重要自然条件,而舒缓的地势与短浅的河流也为该地的游牧人群与拓跋鲜卑另外两部以及周围其他部落的交往创造了较好地理条件。按照《序纪》里的表述,“昭皇帝讳禄官立……分国为三部”,拓跋部三分时禄官应处于部落大宗的地位。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拓跋部对前面提到的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的控制,之前平皇帝绰因为“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七年(294),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为其下所杀,更立莫槐弟普拨为大人。帝以女妻拨子丘不勤”。宇文部正在濡源以东。295年,“昭皇帝讳禄官立……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㐌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以桓帝之弟穆皇帝讳猗卢统一部,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代郡之参合陂”,严耕望以为当在汉代参合县故城,即今山西省阳高县东,可从。[2]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附篇八“北魏参合陂地望辨”,第1397—1402页。关于参合与参合陂,本文后面尚有详细讨论。自此参合陂穿后来的明长城北上,正可抵达力微曾居之长川一带。这条路线西接土默特平原,东合张北高原,北贯乌兰察布草原,南通大同盆地,亦农亦牧,区位优势明显。正是得力于对此沿线地带的控制,力微才能在盛乐领导拓跋部平稳发展将近二十年;297—301年,桓帝猗㐌才能“度漠北巡,因西略诸国”,并取得“诸降附者二十余国”的成果。
拓跋部自猗㐌和猗卢时开始主动介入中原内地的政治、军事斗争。《魏书》卷23《卫操传》:“卫操,字德元,代人也。少通侠,有才略。晋征北将军卫瓘以操为牙门将,数使于国,颇自结附。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及刘渊、石勒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东瀛公司马腾闻而善之,表加将号。”得力边地晋人的怂恿与帮助,拓跋部向大同盆地及其以南发展的势头明显。《魏书·序纪》云:“十年(304),晋惠帝为成都王颍逼留在邺。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并州刺史司马腾来乞师。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大破渊众于西河、上党。会惠帝还洛,腾乃辞师。桓帝与腾盟于汾东而还。”这里需注意“桓帝率十余万骑,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一句,这时禄官尚在并且还是拓跋三部中的大宗,所以“帝亦同时大举以助之”中的“帝”,应该指的是禄官,说明驻牧在濡源以西张北高原一带的禄官一部亦介入了中原内争。《序纪》又云:“十一年(305),刘渊攻司马腾,腾复乞师。桓帝以轻骑数千救之,斩渊将綦毋豚。渊南走蒲子。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水经注》卷3《河水注》:“皇魏桓帝十一年,西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曰:子封送之。渡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求父丧,发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津长不受。事闻于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为君子济。”君子津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喇嘛湾镇附近。这里的榆中,指的应是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至偏关间的黄河两岸地区。[1]参见辛德勇:《阴山高阙与阳山高阙辨析》,《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第204—208页。如《水经注》记载属实,则猗㐌活动范围已经到达土默特平原南面的黄河两岸。联系《序纪》提及的同年“晋假桓帝大单于,金印紫绶”,“桓帝”猗㐌这时起的作用应该最为关键。
猗卢一部驻牧在“定襄之盛乐”一带,因与后来政治局势演变关系密切,更值得注意。295年禄官“分国为三部”,“是岁,穆帝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2]《魏书》卷1《序纪》。。可以看出,猗卢一部在猗㐌与禄官挥部南下并州时并没有跟随,而是将重点放在对土默特平原、河套平原以及鄂尔多斯高原一带的争夺与控制上。这种状况在猗㐌与禄官相继死后发生了变化。“穆皇帝天姿英特,勇略过人,昭帝崩后,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穆皇帝猗卢如何“总摄三部”,史无明文,但结合这一带的复杂族群关系,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3]田余庆先生对代北地区拓跋鲜卑部与乌桓诸部的互动关系曾有很好的分析,可惜对猗卢如何“总摄三部”,由于与他的论述主题关涉不大,没有着墨。参见田余庆:《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魏书·序纪〉有关史实解析》,《拓跋史探》,第108—216页。
前述禄官“分国为三部”,三部的分布范围大致在濡源—长川—牛川—盛乐一线附近。从地理位置上说,驻牧在“代郡之参合陂北”的猗㐌一部与驻牧在“上谷北,濡源之西”的禄官一部位置相邻,距离较近,前述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前来乞师时,猗㐌“率十余万骑”,禄官“亦同时大举以助之”,就有这方面的因素。但猗㐌与猗卢同为文皇帝沙漠汗妻“封后”所生,禄官则是力微之子,猗㐌与猗卢之叔,比较起来,猗㐌与猗卢血缘关系最近。猗㐌因为在地理上居三部之中,又紧傍并州地区,与中原交通较多,受晋人影响较大,三部并存时发展势头可能最好。《魏书·序纪》:“(昭帝)二年(296),葬文帝及皇后封氏。……晋成都王司马颖遣从事中郎田思,河间王司马颙遣司马靳利,并州刺史司马腾遣主簿梁天,并来会葬。远近赴者二十万人。”同事又见《北史》卷13《后妃传上》:“文帝皇后封氏,生桓、穆二帝,早崩。桓帝立,乃葬焉。文成初,穿天泉池,获一石铭,称桓帝葬母氏,远近赴会二十余万。”正说明猗㐌一部的政治影响。
305年,猗㐌死。“(桓)帝曾中蛊,呕吐之地仍生榆木。参合陂土无榆树,故世人异之,至今传记。”这里的参合陂,是不是今山西省阳高县东“代郡之参合陂北”呢?《水经注》里有参合县、参合陉,《魏书》里有参合县。《水经注》卷3《河水注》:“沃水又东,迳参合县南,魏因参合陉以即名也。北俗谓仓鹤陉。道出其中,亦谓之参合口。陉在县之西北,即《燕书》所谓太子宝自河西还师参合,三军奔溃,即是处也。魏立县以隶凉城郡,西去沃阳县故城二十里。”但卷13《漯水注》,如浑水“右会羊水,水出平城县之西苑外武州塞,北出东转,迳燕昌城南,按《燕书》,建兴十年,慕容宝自河西还,军败于参合,死者六万人。十一年,垂众北至参合,见积骸如山,设祭吊之礼,死者父兄皆号泣,六军哀恸。垂惭愤呕血,因而寝疾焉。轝过平城北四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即此城也,北俗谓之老公城”。同卷又有:“雁门水又东南流,屈而东北,积而为潭。其陂斜长而不方,东北可二十余里,广一十五里,蒹葭藂生焉。敦水注之。其水导源西北少咸山之南麓,东流迳参合县故城南。《地理风俗记》曰:道人城北五十里有参合乡,故县也。”可见郦道元是把燕魏参合陂之战定在北魏参合县(即今内蒙古凉城县一带),在卷13《漯水注》叙述上也否认了参合陂之战发生在汉参合故县一带。另《魏书》卷106《地形志上》恒州梁城郡(东魏天平二年,即535年置)下有参合、裋鸿(一本作祇鸿,当作旋鸿)二县。在参合县下注云:“前汉属代,后汉、晋罢,后复,属。”这个参合县当是东魏在汉参合故县附近重新设立的一个县,与《水经注》卷3提到的北魏参合县是两个地方。严耕望则力辨参合陂之战在汉参合故县附近,即今山西省阳高县东。[1]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附篇八“北魏参合陂地望辨”,第1397—1402页。
在严耕望列举的材料中,禄官“分国为三部”,“以文帝之长子桓皇帝讳猗㐌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是一强证。因为内蒙古凉城县在秦汉属雁门郡,魏晋时虽流入化外,但与代郡相距甚远,不大可能有隶属关系。而且今凉城县与和林格尔县为邻县,游牧民族活动半径一般都较大,猗㐌不大可能紧傍猗卢所在的盛乐而驻牧,正如严耕望所说:“若在参合陉,则距盛乐太近,事必不然。”但是1956年,在蛮汉山中的沙虎子沟内(行政区划上属今凉城县东十号乡小坝滩村)发现窖藏,出土有西晋王朝赐给的“晋乌丸归义侯”金印、“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鲜卑率善中郎将”银印、兽形饰金戒指、金耳环及兽形金饰牌等。其中一件兽形金饰牌背面錾刻有“猗㐌金”三字。[2]《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上)之《凉城县文物图(西部)》,第248—249页;《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57—558页。说明猗㐌历史上与今凉城县的参合也存在某种联系。
牛川也在今凉城县附近。前面我提到拓跋部对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的控制问题,认为这是拓跋部南向发展的关键。而在拓跋三部中,南进大同盆地与并州地区最热心的是猗㐌部,其次是禄官部。至于猗卢部,虽然也曾“出并州”,但其目的是“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自杏城以北八十里,迄长城原,夹道立碣,与晋分界”,发展重心并不在此。所以猗㐌部可能实际控制着牛川—长川一线,沙虎子沟窖藏就是猗㐌部控制凉城县附近的牛川、参合、参合陉留下的一处痕迹,这也是在拓跋三部中,猗㐌部虽非大宗,但在政治军事方面表现最为活跃的原因。参合、参合陉可能是拓跋部从东边带过来的地名,就像蛮汗山这个地名很可能源自弹汗山一样。《魏书》里用“代郡之参合陂”的地名表述方式,其实也是暗指参合陂在当时不止有一处。[1]这种表述在《魏书》里还有。譬如前面提到过的“定襄之盛乐”、“云中之盛乐”,是一种避免读者混淆的表达方式。这样说来,不管燕魏参合陂之战究竟发生在何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在北魏分幅图《并、肆、恒、朔等州》里把参合陂标在今凉城县岱海不一定算错。[2]其实严耕望先生胪举的很多材料,“代郡之参合陂”除外,其他也不是不可以另作解释的。参合陂地望一直众说纷纭,这是因为信息非常明确的材料很有限的缘故。国内学者的一些观点,也可参见王凯:《参合陂等地望考》,《北魏盛乐时代》附篇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246—252页。
总括上述,虽然禄官“分国为三部”时其部处于大宗地位,但当时主导拓跋三部发展的却是中部的猗㐌部。而猗㐌一部之所以能够主导拓跋部整体的发展,凭恃的是对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关键地段的控制。305年猗㐌死,“子普根代立”[3]《魏书》卷1《序纪》。,猗㐌一部仍然独立存在。直到307年禄官死,猗卢“总摄三部,以为一统”,普根领导的原猗㐌部才开始接受猗卢的领导。
穆帝猗卢一部原先以盛乐所在的土默特平原为活动中心,“总摄三部”以后,开始东进大同盆地,与并州一带的政治势力发生联系。猗卢的政治、军事活动对拓跋部整体地理空间的扩展意义重大。《魏书·序纪》:“三年(310),晋并州刺史刘琨遣使,以子遵为质。帝嘉其意,厚报馈之。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晋怀帝进帝大单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国悬远,民不相接,乃从琨求句注、陉北之地。琨自以托附,闻之大喜,乃徙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民于陉南,更立城邑,尽献其地,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方数百里。帝乃徙十万家以充之。”自此猗卢全面控制了今山西大同盆地。[1]据《宋书》卷95《索虏传》:“晋初,索头种有部落数万家在云中。惠帝末,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于晋阳为匈奴所围,索头单于猗 遣军助腾。怀帝永嘉三年(309),弟卢率部落自云中入雁门,就并州刺史刘琨求楼烦等五县,琨不能制,且欲倚卢为援,乃上言:‘卢兄 有救腾之功,旧勋宜录,请移五县民于新兴,以其地处之。’琨又表封卢为代郡公。愍帝初,又进卢为代王,增食常山郡。”拓跋部在西晋初年已“部落数万家在云中”。到了西晋末年,面对拓跋部雄心勃勃的南进计划,并州刺史刘琨的处境和态度是“不能制,且欲倚卢为援”。虽然事情发生的时间,两书的表述有点差异,但从内容上,《宋书》这条记载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晋末年雁北大同盆地一带的政治形势。在北魏时代,桑干河流域的河流和地下泉水比现在要丰富得多。[2]〔日〕前田正名:《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第一章“北魏时代桑干河流域的自然地理”,第1—22页。这种情况应该同样适用于猗卢时代。同卷:“六年,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帝登平城西山,观望地势,乃更南百里,于灅水之阳黄瓜堆筑新平城,晋人谓之小平城,使长子六修镇之,统领南部。”新平城,从地望上看可能就是今天山西省怀仁县金沙滩镇安宿疃村的安宿疃城址。[1]安宿疃城址位于山西省怀仁县金沙滩镇安宿疃村东北约2000米,考古年代定为北魏。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380米,南北宽约200米。城墙残高2~3米,墙体夯筑,夯层厚0.08~0.09米。采集有布纹瓦残片。安宿疃城址周边尚有金沙滩墓群、古城地遗址、安宿疃墓群、安宿疃遗址、翰林庄遗址、南阜遗址等汉代和汉代以前的文物古迹,面积均在一两万平方米以上,安宿疃墓群甚至有约50万平方米,说明这一带早在汉代时就适宜人类居住。在安宿疃村东南,有黄花岭海拔1153米。安宿疃城址正在“灅水之阳”。“黄瓜堆”,可能就是今天的黄花岭。详参《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上)之《怀仁县文物图》,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186—187页;《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第188—192页。山西省和山西省军区测绘处编制:《山西省地图集》《怀仁》图,上海中华印刷厂1973年版,第29页。这里有“北都”、“南都”、“南部”的概念。沿用前引阿尔丁夫的说法,由于北方民族曾经流行过以依据面向日出方向者的体位确定四方的方式,以前胸(日出方向)为南,后背(日落方向)为北,右手(日中方向)为西,左手(日没方向)为东,所谓“北都”、“南都”、“南部”,其实就是“西都”、“东都”与“东部”。
六修“统领南部”,有“南部(东部)”则必有“北部(西部)”。北部(西部)当以盛乐为中心,由猗卢直接统领。《魏书》卷113《官氏志》:“魏氏世君玄朔,远统□臣,掌事立司,各有号秩。及交好南夏,颇亦改创。”“交好南夏”是从力微开始的,“颇亦改创”则应始自猗卢。禄官“分国为三部”,拓跋部主体尚不见有制度性的重大变革,这是因为拓跋部的发展仍沿袭力微以来的格局,以“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为轴心。其后猗㐌与禄官两部积极南进大同盆地和并州地区,但猗卢一部的政治步调并未与之一致,“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依然是维系拓跋部整体的地理纽带。猗卢“总摄三部”后,在西晋并州刺史刘琨配合下完全占领大同盆地,东向开拓取得成功,拓跋部活动的轴心由“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自此一变而为“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官氏志》载,什翼犍时,“其诸方杂人来附者,总谓之‘乌丸’,各以多少称酋、庶长,分为南北部,复置二部大人以统摄之。时(昭成)帝弟觚监北部,子寔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这种局面,其实是从猗卢开始的,“复置”一语也暗示了这一点。虽然二部大人统摄的是作为“诸方杂人来附者”的“乌丸”,但从地理空间来看,拓拔鲜卑出现南、北两部的地域分野应当是这种制度出现的另一现实背景。这种局面甚至还延续到了北魏建国初期,“太祖登国元年(386),因而不改,南北犹置大人,对治二部。”[1]《魏书》卷2《太祖纪》:“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可与《官氏志》相参证。猗卢“总摄三部”的政治地理意义,可由此加以理解。
四、猗 一系势力消长与拓跋部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
猗卢“颇亦改创”造成了拓跋部内在的社会裂变。“先是,国俗宽简,民未知禁。至是,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魏书·序纪》把这段话放在穆帝猗卢八年(315),“晋愍帝进帝为代王,置官属,食代、常山二郡。帝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之后,似在暗示猗卢“改创”与拓跋部“交好南夏”之间的联系。《魏书》卷111《刑罚志》亦云:“穆帝时,刘聪、石勒倾覆晋室。帝将平其乱,乃峻刑法,每以军令从事。民乘宽政,多以违命得罪,死者以万计。于是国落骚骇。”拓跋部游牧生活传统与“交好南夏”的政治发展战略产生冲突,不自猗卢始。始祖力微时,与曹魏和亲,“遣子文帝如魏,且观风土”,“魏晋禅代,和好仍密”。而文帝沙漠汗也在洛阳“聘问交市,往来不绝。魏人奉遗金帛缯絮,岁以万计”,“在晋之日,朝士英俊多与亲善,雅为人物归仰”,华风渐染。力微五十八年(277),沙漠汗自并州返归,“始祖闻帝归,大悦,使诸部大人诣阴馆迎之。酒酣,帝仰视飞鸟,谓诸大人曰:‘我为汝曹取之。’援弹飞丸,应弦而落。时国俗无弹,众咸大惊,乃相谓曰:‘太子风彩被服,同于南夏,兼奇术绝世,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国诸子,习本淳朴。’咸以为然。且离间素行,乃谋危害,并先驰还。始祖问曰:‘我子既历他国,进德何如?’皆对曰:‘太子才艺非常,引空弓而落飞鸟,是似得晋人异法怪术,乱国害民之兆,惟愿察之。’自帝在晋之后,诸子爱宠日进,始祖年逾期颐,颇有所惑,闻诸大人之语,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当除之。’于是诸大人乃驰诣塞南,矫害帝。”随后力微“寻崩”,“诸部离叛,国内纷扰”,拓跋部的政治发展一度陷于停顿。到了猗卢时代,拓跋部在地域上已经有南、北部之分,猗卢长子六修“统领南部”,直接担负着“交好南夏”的重任。猗卢九年(316),“帝召六修,六修不至。帝怒,讨之,失利,乃微服民间,遂崩。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卫雄、姬澹率晋人及乌丸三百余家,随刘遵南奔并州”,刘遵是西晋并州刺史刘琨的儿子,这时在拓跋部做人质。细绎文句,这场冲突与力微时代并没有实质的不同,但是里面也掺杂了一些新的因素。一是前述拓跋部首领猗卢的“颇亦改创”,另外一个就是“晋人”已经深入到拓跋部社会内部,并直接造成拓跋部内部的社会裂变。晋人介入拓跋部内部政治斗争,始自西晋征北将军卫瓘,他在沙漠汗自洛阳返经并州时,因为沙漠汗“为人雄异,恐为后患,乃密启晋帝,请留不遣。晋帝难于失信,不许。瓘复请以金锦赂国之大人,令致间隙,使相危害。……于是国之执事及外部大人,皆受瓘货”,从而直接诱发了力微晚年拓跋部的内乱。但这种介入是利用了拓跋部所统政治实体内部的矛盾,尚不是直接参与。到了禄官“分国为三部”,猗㐌一部积极南进,《魏书》卷23《卫操传》载卫操在“始祖崩后,与从子雄及其宗室乡亲姬澹等十数人,同来归国,说桓穆二帝招纳晋人,于是晋人附者稍众。桓帝嘉之,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及刘渊、石勒之乱,劝桓帝匡助晋氏”。可以说,猗㐌的政治功业,与卫操等晋人有莫大关系。穆帝猗卢亦受晋人很大影响,同卷《莫含传》:“刘琨为并州,辟含从事。含居近塞下,常往来国中。穆帝爱其才器,善待之。及为代王,备置官属,求含于琨。……含乃入代,参国官。……含甚为穆帝所重,常参军国大谋。”晋人直接影响拓跋部政治发展的方向,也使得晋人难以避免受拓跋部政治内讧的直接影响。《卫操传卫雄姬澹附传》说“六修之逆,国内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雄、澹并为群情所附……与刘琨任子遵率乌丸、晋人数万众而叛”,在新人中,晋人充当的应是骨干和中坚。
普根领导的原猗㐌部在猗卢一部“总摄三部”、成为拓跋部大宗之后实力依然不容小觑。从地缘角度来看,禄官死后,禄官一部的势力范围已转而由普根控制。[1]禄官一部在禄官死后寂寂无闻,这可能与禄官一支男丁不旺有关。今本《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只有望都公颓(道武帝封望都侯,太武帝“进爵为公”)是“昭帝之后也”。《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载,慕容廆“以辽东僻远,徙于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颇为东部之患,左贤王普根击走之,乃修和亲”。据此可知,普根在猗卢时代政治地位仅次于猗卢,而“东部”,笔者以为应囊括禄官一部原先驻牧的张北高原一带。这可能也说明,原猗㐌部已完全控制了牛川—长川—濡源一线。据《魏书》卷2《序纪》,312年,匈奴汉国刘聪“遣其子粲袭晋阳,害琨父母而据其城,琨来告难,(穆)帝大怒,遣长子六修、桓帝子普根,及卫雄、范班、姬澹等为前锋,帝躬统大众二十万为后继”。这里的“卫雄、范班、姬澹等”,此前也是桓帝猗㐌倚赖的边地晋人。316年,猗卢与其长子六修发生冲突并因此身死,“普根先守外境,闻难来赴,攻六修,灭之。……普根立月余而薨。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猗卢一部遭受重创,从此一蹶不振,猗㐌一部地位再次上升。但是,“其冬,普根子又薨。……平文皇帝讳郁律立,思帝之子也”。思帝弗是文皇帝沙漠汗的少子,278年在位,“聪哲有大度,为诸父兄所重。政崇宽简,百姓怀服。飨国一年而崩”。弗死之后,才有禄官继承大宗并“分国为三部”之事。说明弗一部很早之前就有相当的政治实力,只是弗死得过早,所部政治实力只能在他部卵翼下潜滋暗长。《序纪》又说郁律“姿质雄壮,甚有威略”,这是郁律能够在普根之子死后凭借本部实力继承大位的重要原因。
六修之乱使猗卢部元气大伤,失去了角逐部落领导权的实力。拓跋鲜卑的部落首领位置主要在部落内部的桓帝猗㐌一系和思帝弗一系间摇摆。据《序纪》,321年,平文帝郁律“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惠皇帝讳贺傉立,桓帝之中子也。以五年为元年。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时人谓之女国使。”“四年(324),(惠)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五年(325),帝崩。……炀皇帝讳纥那立,惠帝之弟也。以五年为元年。”“三年(327),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时烈帝居于舅贺兰部。帝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宇文众败,帝还大宁。”“五年(329),帝出居于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烈皇帝讳翳槐立,平文之长子也。以五年为元年。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七年(335),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炀皇帝复立,以七年为后元年。烈帝出居于邺,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三年(337),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烈皇帝复立,以三年为后元年。城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一年而崩。”猗㐌部活跃到翳槐复立,才彻底退出政治发展前台(见表1)。
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母后”、“母族”和“妻族”干预拓跋部部落首领位置传承与政治发展方向问题,这方面由于田余庆的出色研究而使得问题的探讨大为深入。[1]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关于子贵母死制度研究的构思问题》,《代北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文献所见代北东部若干拓跋史迹的探讨》,分见《拓跋史探》,第9—61页,92—107页,108—202页,244—260页。“母后”、“母族”和“妻族”当然很重要。北族游牧社会和中原农耕社会一样是以男性继承为中心。作为男性的配偶,女性生育健康男性后代的多寡,所抚育男性后代社会习得能力的高低,都会对夫系子孙在家族或部落中的地位产生影响。而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首领的婚姻,往往是部落实体间社会政治关系直接互动的现实表达。“母族”和“妻族”影响本部落首领位置传承与政治发展方向,本身也是社会政治关系互动的一个侧面。但这个也未必一定如此。田先生对拓跋部历史上曾发挥作用的几位女性,比如猗㐌妻(所谓桓帝后)祁氏,郁律妻(所谓平文帝后)王氏,讨论至为深入,但是祁氏和王氏所出部族的情况,即便能够肯定是乌桓,现有材料尚不能直接肯定“母”、“妻”部族对拓跋部首领位置传承与政治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2]《魏书》卷13《皇后传》:“桓帝皇后祁氏(《北史》卷13《皇后传》作‘惟氏’),生三子,长曰普根,次惠帝,次炀帝。平文崩,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后性猛忌,平文之崩,后所为也。”强调的似乎是祁氏个人的政治能力。而同卷:“平文皇后王氏,广宁人也。年十三,因事入宫,得幸于平文,生昭成帝。”王氏是“因事入宫”,也看不出原部族有多强的政治实力。“母后”在政
局变动关键时刻的作为,可能还需要从其他角度理解。

表1 《魏书·序纪》所见猗卢死后拓跋鲜卑政治发展大事表
交错变动的政治局势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桓帝猗㐌一系与思帝弗一系各自的活动中心。猗卢死后,政局之所以在桓帝猗㐌一系和思帝弗一系摇摆,笔者以为除却猗卢一部的式微,思帝弗一系的现实政治实力,平文帝郁律本人的杰出才干这些因素之外,猗㐌在世时为本部累积的政治实力在其死后并未遭受削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猗㐌一系的实力,笔者以为既来自猗㐌在世时的经营,更重要的恐怕在于猗㐌一系对“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关键地段的控制。前已提及,禄官死后,普根率领的原猗㐌部势力已东扩至濡源以西。《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提到猗卢时代普根为左贤王,说明“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的东段可能是普根活动的中心。321年,桓帝后祁氏害死平文帝郁律,虽立子贺傉,但“后摄国事,时人谓之女国”,祁氏政治活动能量惊人,田余庆判断祁氏“必出于东方部族”[1]田余庆:《代北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拓跋史探》,第131页。,从猗㐌一系以“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东段为活动中心的思路来看,是可以理解的。324年,贺傉正式开始领导拓跋部,“帝始临朝。以诸部人情未悉款顺,乃筑城于东木根山,徙都之”。这里提到“东木根山”。拓跋部和北魏时代尚有木根山。木根山当指今内蒙古乌海市附近的桌子山。[2]莫久愚:《〈魏书〉木根山地望疏证》,《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第4期。东木根山,颇疑即今内蒙古兴和县与河北尚义县接壤之大青山(即东汉时的弹汗山),力微曾经驻牧过的长川,就在今大青山西北附近;而猗㐌在禄官“分国为三部”后驻牧在“代郡之参合陂北”,从地图来看,其活动中心也应在大青山一带。贺傉因为“诸部人情未悉款顺”而徙都于东木根山附近,也是与把“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东段视为猗㐌一系活动中心的看法相吻合的。思帝弗一系则是以盛乐一带为中心,活跃在“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的西段,这一点在下面的分析中会详细谈到。也就是说,思帝弗一系在地域上承继的是猗卢部的活动范围。猗㐌一系与弗一系政治上的分合,说明自始祖力微西迁“定襄之盛乐”,“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在地理上仍然远较“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为重。
在猗㐌一系与弗一系东西对峙格局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拓跋部活动地域周边政治形势的变化。自进入“匈奴之故地”以来,拓跋部的政治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周边政治环境变化造成的后果。这里面又可以分成几个侧面来分析。一个是西晋王朝的影响。在此之前,由于西晋的积极介入,造成了力微末年拓跋部的政治动荡。由于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刘琨相继的支持与配合,猗㐌、猗卢兄弟积极南进,并最终获得对整个大同盆地的支配权,但是如前所述,这也铸就拓跋社会内部的裂变,酿成猗卢末年拓跋部的再次动荡。318年,平文帝郁律“闻晋愍帝为(刘)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321年,“僭晋司马睿遣使韩畅加崇爵服,帝绝之。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1]《魏书》卷1《序纪》,以下如未注明,引文出处同此。。西晋的沦亡,刺激着拓跋部政治发展的野心。
由于“五胡乱华”,周边其他胡族政治实体对拓跋部的政治影响亦不容忽视。特别要注意的是石赵政权的政治介入。思帝弗一系政治上原来是对石赵政权持对立态度的。319年,石勒自称赵王,“遣使乞和,请为兄弟”,平文帝郁律“斩其使以绝之”。桓帝猗㐌一系在祁氏主导下则与石勒通好,“惠皇帝讳贺傉立……未亲政事,太后临朝,遣使与石勒通和”。居于东部的桓帝猗㐌一系在地缘上与石赵关系密切,祁氏通好石勒,更主要的还是出于稳定拓跋内部局势的需要,双方并非没有大的矛盾与冲突。到了贺傉的弟弟“炀皇帝讳纥那立……三年(327),石勒遣石虎率骑五千来寇边部,帝御之于句注陉北,不利,迁于大宁”,桓帝猗㐌一系自此与石赵关系迅速恶化。思帝弗一系再度掌控拓跋部后,转而与石赵通好。329年,“烈皇帝讳翳槐立,平文之长子也。……石勒遣使求和,帝遣弟昭成皇帝如襄国,从者五千余家”。这也使弗一系在政治失势时获得了遁避的场所。335年,由于炀帝纥那复立,“烈帝出居于邺,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到了337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自此由思帝弗一系继承拓跋部首领(包括后来北魏皇帝)位置的传统开始形成。
宇文部、贺兰部与慕容部对拓跋部的政治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先说宇文部。宇文部与拓跋部的政治关系发生甚早。《北史》卷98《匈奴宇文莫槐传》:“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莫槐虐用其民,为部人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普拨死,子丘不勤立,尚平帝女。”《魏书》卷1《序纪》亦有“七年(293),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为其下所杀,更立莫槐弟普拨为大人。(平)帝以女妻拨子丘不勤”的记载。平帝绰是力微之子,这是宇文部与拓跋部通婚的最早记载。295年,昭帝禄官“分国为三部”,“帝自以一部居东,在上谷北,濡源之西,东接宇文部”。由于禄官一部“东接宇文部”,禄官一部在拓跋三部中与宇文部关系一度最密切。“五年(299),宇文莫廆之子逊昵延朝贡。(昭)帝嘉其诚款,以长女妻焉。”禄官死后,禄官管辖的范围转而由猗㐌之子普根控制。猗㐌一部与宇文部的关系也因而密切起来。猗㐌一系与弗一系相争拓跋部主导权。327年,由于贺兰部帅拥护弗一系的烈帝翳槐,猗㐌一系的炀帝纥那大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329年,纥那在政争中失败,“出居于宇文部”。335年翳槐与贺兰部发生矛盾,纥那则“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但这个时候的宇文部,因为与慕容部相争中屡次败北,气势已是日薄西山。所以当337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国人六千余落叛炀帝,炀帝出居于慕容部”,大宁即今河北省张家口市一带,纥那再次出奔已改为慕容部。穆帝猗㐌一系自此也从左右政局的关键地位消失。
在猗㐌一系与弗一系相争时,对拓跋部政治影响最为关键的还是贺兰部。贺兰部与拓跋部的关系深远。《魏书》卷113《官氏志》:“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贺赖氏,后改为贺氏。”“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别自有传。……南方有茂眷氏,后改为茂氏。……次南有纥豆陵氏,后改为窦氏。……西方尉迟氏,后改为尉氏。……凡此诸部,其渠长皆自统众,而尉迟已下不及贺兰诸部氏。北方贺兰,后改为贺氏。……凡此四方诸部,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贺赖氏,姚薇元以为贺赖即贺兰,“本一氏也”。[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2—38页。《魏书》以不同的汉字音译“贺赖”、“贺兰”,单从《官氏志》的叙述逻辑上说,似乎在暗示“贺赖”、“贺兰”两支与拓跋部的关联有时间上的远近和关系上的亲疏之别。同时据此亦可以推断,贺兰部当居于阴山以北。从《魏书》卷1《序纪》和卷2《太祖纪》的记载来看,贺兰部活动在阴山一线偏东的地方,紧傍阴山一线偏东的,就是穆帝猗㐌一系控制的“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东段,这种地理上的联系耐人寻味。今本《魏书》卷83《外戚贺讷传》:“贺讷,代人,太祖之元舅,献明后之兄也。其先世为君长,四方附国者数十部。祖纥,始有勋于国,尚平文女。父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贺讷祖父“尚平文女”,在《魏书》卷1《序纪》里没有对应的叙述。[1]贺兰部似乎不是力微以来拓跋部领导之部落联盟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今本《魏书》卷83《外戚贺讷传》:“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太祖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苻坚假讷鹰扬将军。……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按指拓跋珪)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当]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这里贺兰部与拓跋部政治上的区隔甚为明显。又卷13《皇后传》:“献明皇后贺氏,父野干,东部大人。”贺讷“总摄东部为大人”,只是前秦利用了贺兰部在东部的影响,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有政治联盟关系。《魏书》卷103《匈奴宇文莫槐传》:“匈奴宇文莫槐,出于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以宇文部的情况相参照,《官氏志》区分“贺赖”与“贺兰”可能有历史事实上的考量。《序纪》说平文帝郁律“姿质雄壮,甚有威略”,一度曾“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贺纳的祖父纥“有勋于国”,是否与此有关,不得而知。但《贺讷传》至少说明在平文帝郁律时思帝弗一系已经与贺兰部建立了政治上的联系。联想穆帝猗㐌一系对“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特别是该线东段的控制,笔者以为郁律此时与贺兰部缔结政治婚姻,可能有扶持贺兰部、打压原猗㐌部的意图。据《序纪》,郁律被“桓帝后”祁氏害死后,贺兰部成为支持弗一系的政治中坚。327年,猗㐌一系的炀帝纥那因为弗一系的烈帝翳槐“居于舅贺兰部”,“遣使求之”,“贺兰部帅蔼头,拥护不遣。帝怒,召宇文部并势击蔼头。宇文众败,帝还大宁”。翳槐是平文帝郁律的长子,“居于舅贺兰部”,说明两部互为姻亲。329年,炀帝纥那出奔宇文部,“贺兰及诸部大人,共立烈帝”。但是“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是拓跋部居“匈奴之故地”以来潜心经营的战略轴心,形势一旦稍加稳定,弗一系从拓跋部整体利益出发,还是会顾忌到贺兰部在此一线东侧势力的滋长。“七年(335),蔼头不修臣职,召而戮之,国人复贰。炀帝自宇文部还入,诸部大人复奉之。”贺兰部对拓跋部部落首领位置的稳固意义于此可见一斑。若不是因为337年石赵政权的介入,桓帝猗㐌一系利用贺兰部与弗一系的矛盾,很可能还将继续影响拓跋部部落首领位置的传承。昭成帝什翼犍继位后,拓跋部与贺兰部的关系似乎已经大为缓和。《贺讷传》记载贺野干“尚昭成女辽西公主”,而据今本《魏书》卷13《皇后传》,贺野干之女又为什翼犍子献明帝寔的皇后,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生母。贺兰部与拓跋部的密切政治关系,一直持续到北魏早期。
拓跋部与慕容部的政治关系可能始于宣帝推寅,在穆帝猗卢时期开始密切起来。[1]《魏书》卷113《官氏志》:“东方宇文、慕容氏,即宣帝时东部,此二部最为强盛。”而宣帝就是《序纪》里提到的“第一推寅”:“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一般以为,“大泽”就在今天内蒙古的呼伦湖。据《官氏志》,在宣帝推寅时拓跋部可能就与宇文部和慕容部发生了联系。《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载,慕容廆“以辽东僻远,徙于徒何之青山。穆帝之世,颇为东部之患,左贤王普根击走之,乃修和亲。……平文之末,廆复侵东部,击破之”。由于拓跋部与宇文部相邻且关系友好,而宇文部与慕容部则存在敌对竞争关系,拓跋部与慕容部的关系并不算太和睦。宇文部在与慕容部相争中一直处境不利,到昭成帝什翼犍建国二年(339),“帝纳元真(即慕容皝)女为后”。“四年(341),元真遣使朝贡,城加龙城而都焉。元真征高丽,大破之,遂入丸都,掘高丽王钊父利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钊单马遁走,后称臣于元真,乃归其父尸。又大破宇文,开地千里,徙其部民五万余家于昌黎。”[1]《魏书》卷95《徒何慕容廆传》。建国八年(345),慕容晃伐宇文逸豆归,“逸豆归拒之,为晃所败,杀其骁将涉亦干。逸豆归远遁漠北,遂奔高丽。晃徙其部众五千余落于昌黎,自此散灭矣。”[2]《魏书》卷103《匈奴宇文莫槐传》。慕容部征服高丽,破灭宇文部,为其逐鹿中原扫除了后顾之忧。自昭成帝什翼犍始,慕容部才逐渐成为影响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五、从什翼犍建代到拓跋珪建魏
据《魏书》卷1《序纪》:“烈帝临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诣邺奉迎,与帝俱还。”什翼犍是“平文之次子也”,“生而奇伟,宽仁大度,喜怒不形于色。身长八尺,隆准龙颜,立发委地,卧则乳垂至席”。烈帝翳槐大概是考虑到桓帝猗㐌一系的势力尚在蠢蠢欲动,才选择了什翼犍继承自己的位置。[3]田余庆已经注意到桓帝祁后一系人丁较盛,见《拓跋史探》,第165页。《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载有曲阳侯素延(道武帝时封)、顺阳公郁(文成帝时封)、宜都王目辰(文成帝时封南平公,孝文帝时封宜都王),均为“桓帝之后也”。《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高凉王孤,平文皇帝之第四子也。……烈帝之前元年,国有内难,昭成如襄国。后烈帝临崩,顾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在南,来未可果,比至之间,恐生变诈,宜立长君以镇众望。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孤曰:‘吾兄居长,自应继位,我安可越次而处大业。’乃自诣邺奉迎,请身留为质。石虎义而从之。昭成即位,乃分国半部以与之。”卷113《官氏志》:“时(昭成)帝弟觚监北部,子寔君监南部,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此处之“觚”,即《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里的“高凉王孤”。在孤等人的拥戴下,338年“十一月,帝即位于繁畤之北,时年十九,称建国元年”[1]《魏书》卷1《序纪》。。这是拓跋代国成立的标志。繁畤,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四册北魏《并、肆、恒、朔等州》图,在今山西省应县东。自此沿今浑河向西,可达猗卢长子六修曾经镇守过的新平城。“二年(339)春,始置百官,分掌众职。”此时出居慕容部的炀帝纥那似乎已经失去了政治影响力,所以同年不但“东自濊貊,西及破洛那,莫不款附”,什翼犍还“娉慕容元真妹为皇后”,与慕容部建立了友善的政治联系。拓跋部声势复振。[2]拓跋部重新回复一统,在南朝史籍里也有记载。《宋书》卷95《索虏传》:“(猗)卢孙什翼鞬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南齐书》卷57《魏虏传》:“猗卢孙什翼犍,字郁律旃,后还阴山为单于,领匈奴诸部。”拓跋部的政治发展似乎又有由“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转向“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的趋势。“夏五月,朝诸大人于参合陂,议欲定都灅源川,连日不决,乃从太后计而止。语在《皇后传》。”[3]《魏书》卷1《序纪》。灅源川当指猗卢、六修曾经营过的新平城一带。据今本《魏书》卷13《皇后传》:“昭成初,欲定都于灅源川,筑城郭,起宫室,议不决。后闻之,曰:‘国自上世,迁徙为业。今事难之后,基业未固。若城郭而居,一旦寇来,难卒迁动。’乃止。”“国自上世,迁徙为业”,强调的是拓跋部游牧社会的传统;“事难之后,基业未固”则指出了拓跋部面临的政治形势。
自桓帝猗㐌开始,南进大同盆地、并州地区甚至中原似乎已经成为有进取心之拓跋部首领政治发展的重要企图。“总摄三部”的穆帝猗卢曾“忿聪、勒之乱,志欲平之”。318年,“姿质雄壮,甚有威略”的平文帝郁律闻晋愍帝为刘曜所害,顾谓大臣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什翼犍欲定都灅源川,无非是想实现前代拓跋部首领的政治蓝图。350年,石赵政权发生重大内讧,“魏郡人冉闵,杀石鉴僭立”。次年,“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再次燃起政治发展的雄心。但是,“诸大人谏曰:‘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帝乃止”。而“是岁,氐苻健僭称大位,自号大秦”[1]均见《魏书》卷1《序纪》。。五胡争竞,拓跋部却流连游牧社会传统,逡巡不前。面对这种部族社会政治的实际,什翼犍大概想到,若欲避免穆帝猗卢末年以来的纷争,稳定内部显然优于南向发展。所以,“三年(340)春,移都于云中之盛乐宫”。“四年(341)秋九月,筑盛乐城于故城南八里。”土默特平原成为什翼犍关注经营的中心。什翼犍虽然有政治野心,却一时难以改变自力微以来“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的地理轴心地位。他复置南、北两部大人,维系拓跋部对“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的政治控制,但这种控制同时也借重了其他部族的政治地位与实力。
什翼犍时期,拓跋部与东方的贺兰部、慕容部政治关系良好,这也有助于拓跋部把政治中心重新转移到土默特平原。拓跋部把政治中心重新转移到土默特平原,除了南进中原内部动力不足之外,还因为铁弗部的崛起。[2]关于铁弗部和它所建立的夏国,相关的研究其实不少,本文着眼于拓跋部与铁弗部的政治关系,对于铁弗部没有专门进行研究。最近一次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请参见吴洪琳:《铁弗匈奴与夏国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死,虎代焉。虎一名乌路孤。始臣附于国,自以众落稍多,举兵外叛。平文与晋并州刺史刘琨共讨之,虎走据朔方,归附刘聪,聪以虎宗室,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魏晋时期的新兴郡在今雁门关南侧的忻定盆地上,虑虒在今山西五台县附近。“平文与晋并州刺史刘琨共讨之,虎走据朔方”,据卷1《序纪》载,穆帝猗卢“三年(310)……白部大人叛入西河,铁弗刘虎举众于雁门以应之,攻琨新兴、雁门二郡。琨来乞师,帝使弟子平文皇帝将骑二万,助琨击之,大破白部;次攻刘虎,屠其营落。虎收其余烬,西走度河,窜居朔方”。这是铁弗部政治发展中的一件重要事情。在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和拓跋部联合打击下,铁弗部离开忻定盆地“走据朔方”。刘虎所据的“朔方”,应该就是今天的鄂尔多斯高原一带。鄂尔多斯高原位于土默特平原和狭义的河套平原之南,其西、北、东三面为黄河环绕,南以长城为界。高原海拔高度大多在1100~1500米之间。西北部略高,向东南缓缓倾斜,地表起伏不大,为近似方形的台状干燥剥蚀高原。西部桌子山一带地势比较高峻,平均海拔在1500~2000米左右。东部有沙黄土丘陵,河谷地带海拔常低于1000米。高原上河流稀少,盐湖众多,风沙地貌发育,无流区与内陆区面积很大。但地下水丰富,并且有承压性质,可自溢流出井口。其中尤以白垩系地层地下水最佳,质好、量大、面积广(约占鄂尔多斯高原的2/3)。[1]任美锷、包浩生主编:《中国自然区域与开发整治》第九章,第380页。可见鄂尔多斯高原具备从事游牧社会活动的自然条件。这一带也确实有着从事游牧活动的历史传统。“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历史学家研究后认为至少到战国后期这一带已经全面游牧化了,“长城的建立,与长城外的全面游牧化互为因果”[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民族认同》第五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73—93页。。由于鄂尔多斯高原地势较为舒缓,便于骑马民族纵横驰骋,铁弗部政治整合这一地带并没有自然地理上的重大障碍。但是鄂尔多斯高原毗邻拓跋部活动的中心区域—土默特平原,铁弗部与拓跋部两部之间仍然存在政治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态势甚至持续到拓跋部与铁弗部相继建立北魏与大夏国家之后。《资治通鉴》卷118载,晋恭帝元熙元年(419),大夏国群臣请夏王赫连勃勃定都长安,勃勃讲了如下一段话:“朕岂不知长安历世帝王之都,沃饶险固!然晋人僻远,终不能为吾患。魏与我风俗略同,土壤邻接,自统万距魏境裁百余里,朕在长安,统万必危;若在统万,魏必不敢济河而西。诸卿适未见此耳。”“风俗略同,土壤邻接”,这样的地缘政治特点,在两部实力相当的条件下,拓跋部和铁弗部很难避免政治上的缠斗。而拓跋部在北魏建国前似乎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一政治势力的实力。《铁弗刘虎传》又云:“(刘虎)复渡河侵西部,平文逆击,大破之,虎退走出塞。昭成初,虎又寇西部,帝遣军逆讨,又大破之。虎死,子务桓代领部落,遣使归顺。务桓……招集种落,为诸部雄。潜通石虎,虎拜为平北将军、左贤王。务桓死,弟阏陋头代立。密谋反叛……后务桓子悉勿祈逐阏陋头而自立。悉勿祈死,弟卫辰代立。卫辰,务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后,遣子朝献,昭成以女妻卫辰。”从材料中还可以看到,铁弗部不时受到地域之外的政治强权(相继有刘汉政权、石赵政权、苻秦政权和姚秦政权)的怂恿与支持。据《魏书》卷1《序纪》,建国四年(341),“冬十月,刘虎寇西境。帝遣军逆讨,大破之,虎仅以身免。虎死,子务桓立,始来归顺,帝以女妻之”。“十九年(356)春正月,刘务桓死,其弟阏头立,潜谋反叛。二月,帝西巡,因而临河,便人招喻,阏头从命。”“二十一年(358),阏头部民多叛,惧而东走。渡河,半济而冰陷,后众尽归阏头兄子悉勿祈。初,阏头之叛,悉勿祈兄弟十二人在帝左右,尽遣归,欲其自相猜离。至是,悉勿祈夺其众。阏头穷而归命,帝待之如初。”二十二年(359),“悉勿祈死,弟卫辰立。秋八月,卫辰遣子朝贡”。二十三年(360),“秋七月,卫辰来会葬,因而求婚,许之”。“二十四年(361)春,卫辰遣使朝聘。”“二十八年(365)春正月,卫辰谋反,东渡河。帝讨之,卫辰惧而遁走。”“三十年(367)冬十月,帝征卫辰。时河冰未成,帝乃以苇絙约澌,俄然冰合,犹未能坚,乃散苇于上,冰草相结,如浮桥焉。众军利涉,出其不意,卫辰与宗族西走,收其部落而还,俘获生口及马牛羊数十万头。”“三十七年(374),帝征卫辰,卫辰南走。”从整体趋势来看,拓跋部似乎越来越占上风。但是两部地域之外的政治强权遏制住了这种趋势,“三十八年(375),卫辰求援于苻坚。三十九年(376),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彤、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卷95《铁弗刘虎传》:“昭成末,卫辰导苻坚来寇南境,王师败绩。”在铁弗部的配合下,前秦灭亡了拓跋代国,也为拓跋部后续的政治发展留下了新的问题。
如上所述,昭成帝什翼犍在位39年,铁弗部败而复振,首鼠两端,叛服无常,显示了顽强的政治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拓跋部一方面不得不采行军事征服与政治怀柔相济的手段,另一方面,则积极扶持独孤部,抗衡铁弗部。据《魏书》卷113《官氏志》,“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丘穆陵氏,后改为穆氏。步六孤氏,后改为陆氏。贺赖氏,后改为贺氏。独孤氏,后改为刘氏。”独孤部自神元帝力微时就与拓跋部发生了政治联系。但卷23《刘库仁传》:“刘库仁,本字没根,刘虎之宗也……母平文皇帝之女。昭成皇帝复以宗女妻之,为南部大人。”刘库仁是独孤部的首领,此条材料暗示独孤部与铁弗部在种属上存在亲缘关系。姚薇元比勘史料后认为独孤部出自匈奴之屠各种,独孤当即屠各之异译。[1]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38—52页。前引《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载,郁律与西晋并州刺史刘琨征讨铁弗部首领刘虎,“虎走据朔方,归附刘聪,聪以虎宗室,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匈奴汉国的刘聪以铁弗部首领刘虎为宗室,刘虎出自屠各种应该没有疑问。尽管刘库仁与刘虎的具体亲缘关系可能还需要讨论,但独孤部与铁弗部同出匈奴屠各种应该没有疑问。[2]相关讨论参见张继昊:《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匈奴刘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空中大学人文学报》第7期。独孤部与铁弗部同源政治立场却更倾向拓跋部,这与独孤部杂处拓跋鲜卑南、北两部之间,政治实力又常弱于强大时的拓跋部有很大关系。拓跋部通过扶持独孤部,至少可以减少铁弗部从黄河西岸直接冲击本部。什翼犍的这项策略,也为代国灭亡后拓跋部保存后续发展实力提供了条件。卷95《铁弗刘虎传》:“坚遂分国民为二部,自河以西属之卫辰,自河以东属之刘库仁。……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魏书》卷23《刘库仁传》:“建国三十九年(376),昭成暴崩,太祖未立,苻坚以库仁为陵江将军、关内侯,令与卫辰分国部众而统之。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可以看出,前秦虽然利用铁弗部控制拓跋部,但是并没有忽视独孤部对拓跋部的影响。其实苻坚在灭代之前,对铁弗部叛服无常的政治性格是领教过的。卷95《铁弗刘虎传》:“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遣使请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去,坚许之。后掠坚边民五十余口为奴婢以献于坚,坚让归之。乃背坚,专心归国,举兵伐坚,坚遣其建节将军邓羌讨擒之。坚自至朔方,以卫辰为夏阳公,统其部落。卫辰以坚还复其国,复附于坚,虽于国贡使不绝,而诚敬有乖。帝讨卫辰,大破之,收其部落十六七焉。卫辰奔苻坚,坚送还朔方,遣兵戍之。”将这些内容与前述灭代后的政治安排结合起来分析,前秦意在通过铁弗部与独孤部分部管理拓跋部,提高独孤部的政治地位,扶持独孤部的发展,并借助独孤部实力与地位以及铁弗、独孤两部之间的矛盾成功抑制铁弗部的趁势扩张。卷23《刘库仁传》:“苻坚进库仁广武将军,给幢麾鼓盖,仪比诸侯。处卫辰在库仁之下。卫辰怒,杀坚五原太守而叛,攻库仁西部。库仁又伐卫辰破之,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库仁西征库狄部,大获畜产,徙其部落,置之桑干川。苻坚赐库仁妻公孙氏,厚其资送。库仁又诣坚,加库仁振威将军。”前秦的政治意图得到了实现,但是拓跋部也因为独孤部的呵护保存了自身的政治实力。同传在“自河以西属卫辰,自河以东属库仁”一语后载:“于是献明皇后携太祖及卫秦二王自贺兰部来居焉。库仁尽忠奉事,不以兴废易节,抚纳离散,恩信甚彰。”这也是昭成帝什翼犍生前扶持独孤部战略布局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
拓跋部在政治上的再度崛起也离不开贺兰部的支持与帮助。今本《魏书》卷83《外戚贺讷传》:“昭成崩,诸部乖乱,献明后与太祖及卫、秦二王依讷。会苻坚使刘库仁分摄国事,于是太祖还居独孤部。讷总摄东部为大人,迁居大宁,行其恩信,众多归之,侔于库仁。苻坚假讷鹰扬将军。”贺兰部在东部影响力的增强与弗一系为打击猗一系而行的扶持策略有关,已如前述。前秦灭代以后扶持贺兰部,则有抑制独孤部势力东扩的意图在里面。这对进一步加强贺兰部在东部的实力与地位应该有所帮助。但不管前秦扶持的是独孤部还是贺兰部,从拓跋部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由于之前较为良好的政治联系,两部的政治成长,对拓跋部还是有利的。至少在灭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独孤部与贺兰部发挥了翼护拓跋部的作用。《魏书》卷2《太祖纪》:“登国元年(386)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复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以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班爵叙勋,各有差。二月,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三月,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奴真率所部来降。夏四月,改称魏王”,卷83《外戚贺讷传》则云:“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讷)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在贺兰等部的支持下,拓跋部自此开启了建立北魏王朝的历程。
六、结论
最后,将本文主要结论简述如下:
(1)诘汾和之后力微最初所居的“匈奴故地”,可能在今天乌兰察布高原东侧的阴山山地一带,与居于张北高原的没鹿回部相邻。力微吞并没鹿回部之后,张北高原转而成为拓跋鲜卑的驻牧地。
(2)力微当是沿长川—牛川—盛乐一线,即今日兴和(长川)—丰镇—凉城(牛川)—和林格尔(盛乐)一线或兴和(长川)—察哈尔右翼前旗—凉城(牛川)—和林格尔(盛乐)一线自东向西发展,由此进入肥沃的土默特平原,在这里确立自己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并开始有了沿盛乐—善无—平城一线自西向东发展的企图。
(3)禄官“分国为三部”,沿袭的仍是力微以来的政治地理格局,以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为轴心。其后猗㐌与禄官两部积极南进,但猗卢一部的政治步调并未与之一致,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依然是维系拓跋鲜卑整体的地理纽带。猗卢“总摄三部”后,在西晋并州刺史刘琨配合下完全占领大同盆地,拓跋鲜卑出现了“南”、“北”两部并行发展的政治地理格局,这种格局也是有远大企图心的拓跋鲜卑首领由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转向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经营的重要现实因素。
(4)猗卢死后,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主导权一直在桓帝猗㐌一系和思帝弗一系摇摆,直到思帝弗一系什翼犍建立代国,这种局面才告终结。什翼犍为了平衡内部分歧,将政治发展中心重新转向土默特平原,但是在土默特平原却必须面对来自鄂尔多斯高原的铁弗部的政治竞争。铁弗部利用其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撼动着拓跋部在北方的政治主导地位。为维系拓跋部在阴山南北的政治主导权,思帝弗一系积极扶植与拓跋鲜卑政治关系较为良好的贺兰部与独孤部,让这些部族分担自己来自内外的政治压力。
(5)思帝弗一系扶植贺兰部与独孤部,与拓跋鲜卑经历内耗后实力有所削弱也有关系。贺兰部与独孤部地位和实力增强后,它与拓跋部的关系渐渐变得复杂微妙起来。围绕怎样对待拓跋部,独孤部内部出现了分化。《魏书》卷83《外戚刘罗辰传》:“刘罗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眷(据卷23《刘库仁传》,刘眷为刘库仁之弟),为北部大人,帅部落归国。……后库仁子显杀眷而代立,又谋逆。及太祖即位,讨显于马邑,追至弥泽,大破之。后奔慕容麟,麟徙之中山,罗辰率骑奔太祖。显恃部众之强,每谋为逆,罗辰辄先闻奏,以此特蒙宠念。”贺兰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外戚贺讷传》:“后刘显之谋逆,太祖闻之,轻骑北归讷。讷见太祖,惊喜拜曰:‘官家复国之后当念老臣。’……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其祸心。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独孤部刘显“恃部众之强”,“谋为逆”,贺兰部贺染干“常图为逆”,显示长期由拓跋部主导的代北政治发展格局出现了某种松动、解体的征兆。
(6)猗卢死后,政局之所以在桓帝猗㐌一系和思帝弗一系摇摆,从政治地理的角度来说,与猗㐌一系控制着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的关键地段有很大关系。思帝弗一系借助贺兰部打击猗㐌一系,虽然极大削弱了猗㐌一系左右政局的实力,促成了什翼犍建立代国,但贺兰部因而坐大并在一定程度上与拓跋部分享对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的控制,对拓跋部控制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东侧和阴山以北的草原地区有负面影响。北魏建国后为稳定北方、重新控制这一线,不得不展开对贺兰部的斗争与征服,所以离散贺兰部落,对确立北魏新的政治地理格局意义重大。[1]张继昊:《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勋臣贺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空中大学人文学报》第5期。田余庆:《贺兰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一》,《拓跋史探》,第62—76页。
(7)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在地位上虽长期不能与盛乐—牛川—长川—濡源一线相提并论,但由于猗卢开创的拓跋鲜卑“南”、“北”两部并行发展的政治地理格局以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为轴心,拓跋鲜卑后续的南向发展要依赖这条线,所以对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的重视程度会随着拓跋部政治上的强大而加深。从这个角度来说,拓跋部扶持在拓跋“南”、“北”两部中间活动的独孤部,虽然有助于抑制铁弗部,也对前秦灭代后拓跋鲜卑政治实力的保存起到了良好效果,但是独孤部的政治成长毕竟不利于拓跋部控制盛乐(北都)—平城(南都)—新平城一线,从长远来看则威胁着拓跋鲜卑“南”、“北”两部的政治整合。所以在北魏建国过程中,独孤部要先于贺兰部被离散。[1]张继昊:《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白部和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二》,《北魏王朝创建历史中的匈奴刘氏—北魏建国时期重要氏族研究之一》,分见《空中大学人文学报》第6、7期。田余庆:《独孤部落离散问题—北魏“离散部落”个案考察之二》,《拓跋史探》,第77—91页。
(首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8辑)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魏政治地理研究”(批准号:09CZS002)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