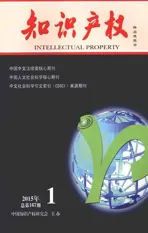对知识产权行政授权行为性质的再探讨
2015-01-30王烈琦
唐 艳 王烈琦
对知识产权行政授权行为性质的再探讨
唐 艳 王烈琦
关于知识产权行政授权的性质,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学说: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准司法行政行为。这一论题涉及行政法学与知识产权法学两方面的知识。考察行政法学知识,准司法行政行为以存在纠纷为前提,与知识产权授权行为明显不相符合;行政许可与行政确认的主要区分在于前者赋予申请人新的权利,而后者仅为对既有权利的确认,因而论题之核心在于知识产权授权本身是否产生新的权利。实证考察专利与商标制度,专利权之授予和商标注册,事实上都使申请人获得了新的权利:禁止权,即专利权人禁止(或许可)他人实施其专利的权利,商标权人禁止(或许可)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权利。因而,知识产权授权行为在性质上更接近于行政许可。
知识产权授权 商标权 专利权 行政许可 行政确认
一、归类——一个看似远离实践的教义学问题
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本文所欲探讨的问题,也即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知识产权的授权行为①当笔者使用这一术语时,即存在预设了结论的可能。然而,一则,多数学者都使用该术语,甚至有学者一方面在探讨知识产权的“授权”行为,另一方面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这种“授权”并不产生新权利而只是对既有权利进行确认;另则,笔者没有找到更好的术语来对这样一种包括商标注册、专利授予在内的知识产权法律现象进行更好的概括,因而延续了其他学者在中性意义上使用“行政授权”的方法,即我们并不预设这种知识产权授权是否产生新权利。在具体行政行为里如何归类,仍旧主要是一个纯学术领域的问题,暂时在实践中并未引发过多的困惑:因为,不论将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的授予归入何种具体行政行为,都不太影响现实中权利人申请权利、获得权利乃至在必要时寻求行政乃至司法救济。
于此,本文以为更有学术价值的论题乃是:我们如何看待知识产权的行政授权行为或者知识产权权利的获得,从话语实践角度,将反过来影响我们如何看待知识产权的属性,从而影响到我们下一步对知识产权相关制度的构建与改进。
具体而言,该问题之所以重要,恰在于这种授权行为中,作为一方的政治国家与作为另一方的民事主体同时在场,而这两者之间究竟如何互动使一种权利进入了民事领域(也即市民社会领域)。这里面至少存在两种可能性:政治国家赋予了民事主体相应的权利;政治国家只是认证、确认了民事主体的相应的权利。这两种不同的可能性标示了政治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两种不尽相同的功能:按照前者,政治国家是权利的授予者;按照后者,政治国家只是现存或者先验权利的确认者。这两种不同的定位将对政治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内可能的作为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权利授予者的定位将在理论上赋予政治国家更多在知识产权领域活动的主动性,如强制实施、主动介入保护知识产权、制定知识产权战略等;而权利认可者的定位将在理论上相对束缚政治国家主动行为的可能性,此时的专利权、商标权,将更类似于其它民事权利,更依赖市民社会的自治与司法的被动介入来运作维系。
当然,尽管指明可能的后果对于探讨问题非常重要,但仅仅指明后果在法学论证中是不够的,法学依旧需要从实定法乃至教义学,从事物本身的逻辑进行必要的规范分析,这正是下面将要探讨的。
二、梳理——几种不同的行政行为之特征
我国行政法学界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类,而相关知识产权学者的论述以及相应的行政法学教材中,主要有三种具体行政行为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授权行为: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相关学者的表述为准司法行为)。
(一) 行政许可
关于行政许可,我国《行政许可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根据这一定义,行政许可乃是行政机关应申请,而赋予申请者从事特定活动的行政行为。之所以申请者从事相关特定活动需要向行政机关申请并得到行政机关的许可,则是因为对于该相关活动,存在法律上的一般性的禁止。因此,申请人未得到许可之前,从事该活动是不能获得法律支持的。这一点上,国内主要的几种行政法的教科书并无太大分歧,因而可以视为一种行政法学界的通说。至于法律的一般禁止,有学者将之细分为法律的明确禁止与非明确禁止。②罗豪才、湛中乐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本文以为,这种法律上的非明确禁止,至少可以解读为如未得到行政许可,则行为人的相应行为不能受到法律的积极保护。也即,即便实施这种行为不必然导致法律的制裁,但最低限度上行为人的相关主张是不能仅依据法律的规定而得到政治国家的肯认与支持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基于现代市民社会自治理念,法律对违法行为的制裁与法律对合法诉求的支持之间存在一个市民社会自治的广泛空间。
基于“法律上的一般性禁止”这一通说,行政法学界通常认为行政许可是一种赋权行为,既赋予相对方为某种行为的权利的行为。同时认为,行政许可的效力具有后及性,而没有前溯性,③同注释② ,第217页。因为相对人是基于行政机关的赋权才获得权利的,此前并不应然存在相应的权利。
(二)行政确认
行政确认的概念主要来自于教义学对于某种具有类似性质的行政行为的总结。综合几本教科书④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注释4,第215页。可以认为,行政确认只是对既有法律事实或关系的甄别宣告,并不能直接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或者法律关系。如马怀德教授书中专门用一段文字探讨了这一点,其标题即为:“行政确认不直接创设新的权利义务或者法律关系”。⑤马怀德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第194页。湛中乐教授则认为,“行政确认是对既有的身份能力、权利、事实的确定和认可,其法律效果具有前溯性。”⑥同注释② ,第217页。从而强调了行政确认只涉及对既有权利之甄别确认,而本身不能创设新权利,并以此来区分于行政许可的法律效果仅有后及性。而杨建顺教授认为:“行政确认是羁束行政行为。行政确认是对特定法律事实或者法律关系是否存在的宣告,而某种法律事实或者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是由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决定的。”⑦同注释④ ,第250页。这一表述亦强调了行政确认只是对客观既存法律事实或法律关系的甄别与宣告,并无创设新权利之功能。
综合以上论述,可以认为,行政许可与行政确认最基础的分野在于:前者赋予新权利,而后者仅是对既有权利的认证与宣告。亦需注意的是,有学者不仅探讨了二者的区别,亦探讨了二者在现实中的关联:有时同一行为既有确认性质又具有行政许可性质;有时行政确认是许可的前置程序,这种情况下的确认是准行政行为;有时确认是基于已完成许可的授权。⑧同注释② ,第216页。
(三)行政裁决
至于行政裁决,学者们的表述亦无太大分歧,一般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⑨同注释② ,第269页。注释⑤ ,第249页。可见,行政裁决处理的是民事纠纷,也即,以纠纷的存在为前提,并且,行政裁决依照的是准司法程序。⑩同注释② ,第280页。注释⑤ ,第251页。
(四)行政法学界对知识产权授权行为的探讨及解读
就目前学界的研究而言,行政法学界及知识产权学界虽然视角不尽相同,但都对专利、商标授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归类有所涉及。
行政法学界,杨建顺教授在阐释行政确认行为时,将专利权的确认归入了行政确认中对法律关系的确认之一种。然而,他的具体表述为:“授予专利权是行政机关的专属权利”,“授予专利权需要对专利权进行确认,包括是否职务发明的专利权确认等”。①同注释④ ,第252页。对于这一段文字,似可做两种解读:一种为授予专利权是一种行政确认;另一种为对专利权相关事宜进行行政确认只是授权的前置程序。湛中乐则认为“在颁发专利证书、商标专用证书中确认专利权、商标权等”为行政确认。②同注释② ,第217页。这一表述亦隐含着两种可能的解读:一种为颁发证书,也即授权行为本身为行政确认;另一种为仅仅颁发证书这一法律行为为行政确认,但与其前提相关的授权行为本身不属确认范畴。上述学者的论述就单一语句而言,确有两种理解之可能。然而,如若我们结合上下语境以及相关学者对行政确认、行政许可的整体论述,本文以为,事实上无论是杨建顺教授还是湛中乐教授,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分别将行政确认作为授予专利等权利的前置程序(如杨教授所述的是否包括职务发明等的确认),或者授予专利权的形式程序,或者完成程序(如湛中乐教授所述的颁发证书行为)。
与此同时,行政法学界探讨主要的准司法行为——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时,尽管涉及到知识产权的纠纷及确权,但都未涉及到知识产权本身的授权问题。正如下面将要论述的,用准司法行为来表述相应的知识产权授权行为的论述来自于知识产权学界。
以上是本文对于行政法学界相关知识积累的一个总结。事实上,专利、商标的行政授权行为的属性问题,本身就涉及到行政法与知识产权法两个领域。要精准地回答该问题,既需要对行政行为相关理论的梳理,更需要对专利权、商标权深刻的认知。由此,下面将转入对知识产权学界的相关理论的探讨。
三、分歧——知识产权学界的观点
(一)观点汇总
知识产权学界对上述问题的探讨,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单一讨论专利权或者商标权的授权属性,另一种是将二者作为类似制度统一探讨。多数学者只探讨了单一的专利权或商标权。关于专利权的行政授权,厉宁、刘强等学者认为属于专利权的授予,属行政许可的范畴;③刘强:《从行政许可法看授予专利权制度的改进》,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99页。厉宁:《专利制度的行政许可属性》,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5期,第24页。郁峰将专利授权行为归之为行政确认;④郁峰:《授益行政行为与专利权保护研究》,载《行政与法》2010年第11期,第87页。而梁志文则在否定专利授权属于行政许可的基础上,认为其“属于根据权利人的申请而为的一种司法性行政行为”。⑤梁志文:《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性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33页。关于商标授权行为,沈俊杰等认为其属于行政确认;⑥沈俊杰、曹蕙:《行政法视角下商标局核准注册商标行为定性之争: 是商标授权,还是商标确权》;载《电子知识产权》2012年第7期,第71页。冯术杰亦认为“商标注册不是行政许可或赋权而是行政确认”。⑦冯术杰:《论注册商标的权利产生机制》,载《知识产权》2013年第5期,第19页。至于统一讨论专利权与商标权的杜颖博士则认为:“知识产权行政授权及确权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具有准司法行为的行政”。⑧杜颖、王国立:《知识产权行政授权及确权行为的性质解析》,载《法学》2011年第8期,第92页。
(二)观点审视
对于此等林林总总的观点,本文以为,首先需审视的是这些来自知识产权界的学者对于行政法相关知识的理解与行政法学界对相关术语的使用是否一致,因为毕竟探讨的是关于知识产权的行政行为归类问题。
先看专利方面,当学者郁峰论述“行政确认是赋予创新技术专利权的程序,是专利权保护的基础。”⑨同注释⑥。他所使用的“行政确认”这一术语显然与前面所述的行政法学的通说不同,他已然将专利权的授予看成了一种“赋权行为”,因而他的实质观点更接近认为专利是行政许可的观点。而梁志文所提出的“民事司法性行政行为”,在行政法学中通常无此表述,比较接近的是行政裁决。但无论梁文提的“民事司法性行政行为”,还是行政裁决,都主要指行政机关依准司法程序居中裁决民事当事人关于权利的纠纷,这就预设了民事纠纷的存在,但问题是现实中的专利授权都会导致利害关系人的纠纷。这显然已脱离现实逻辑太远。至于杜颖博士对行政确认的定义引述是非常准确的。然而,她用以证明相关行为属行政确认而引述的行政法学家的观点(杜文引述了前文所引述过的杨建顺等老师的论述以证明相关行为属行政确认),则存在两种可能性:或者如本文上面所分析的,可以解读为行政确认是一种前置或者完成程序,而非赋权本身,因而杜博士本身存在着对话语表述的误读;或者杜博士没有误读这些学者的观点,但这些学者的观点由于缺乏对于知识产权性质的深入阐述而缺乏必要的权威性。总之,杜颖博士的这一引述从严格的学术层面,很难真正意义上构成证成她本人观点的有效论据。厉宁的观点虽发表于行政许可法颁布以前,但其文章对行政许可的理解基本是准确的;而刘强对行政许可的引述也是比较准确的。
再看商标权方面,沈俊杰等对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的概念引述是准确的。而冯术杰关于行政确认概念的引述是准确的,但他对行政确认本身的理解似乎仍不够充分,因为从他引述的“多数行政法学者均认为,工业产权的确认属于对法律关系的确认”⑩同注释⑦。的表述,从逻辑上根本无法推导出他所认为的商标注册属行政确认的观点。如本文前面所述,商标权的获得过程中肯定存在行政确认,但有可能仅是作为前置程序的行政确认,也可能是作为完成程序的行政确认,而不能排除这一过程中有行政机关赋权的可能。
(三)小结
对以上观点学说进行总结,本文认为,梁志文所探讨的“民事司法性行政行为”,按照今日中国的法教义学逻辑,是不太能够有效解释专利权经由行政行为获得这一现象的,尽管这一概念本身或许还有更多有待探讨的学术价值;杜颖博士在具体探讨时谈及“具有准司法行为的行政”,亦以争议之发生为前提,同样缺乏必要的解释力。因而本文认为首先可以排除的是对知识产权行政赋权行为的准司法行为行政行为的定位。由此下面的探讨将聚焦于相关学者对行政许可说和行政确认说是如何进行探讨取舍的,以及他们探讨取舍的根据在行政法与知识产权法这两学科领域能否经得住一些常识性知识的检视。
四、澄清——专利权、商标权究竟为何
(一)对行政许可说批判之辩驳
有意思的是,持行政确认论者,以及持“民事司法性行政行为”,都将他们的观点置于对于行政许可说的批判之上。然而,通过细致的辨析,本文认为,他们的观点都存在一定的瑕疵,甚至有的观点存在对商标权、专利权的根本性误解。
首先,也是最基础的,大多学者显然忽视了商标与商标权、技术与专利权之间的巨大差距,因而存在着一种对于商标权、专利权权利内涵的错误理解。确实,如很多学者所言,即便没有注册商标、没有申请专利,仍不妨碍相关主体生产商品甚至使用商标、运用相关技术。
然而,商标权的内涵是赋予权利人使用自己商标的权利么?这一点,我国实定法表述得非常清晰,注册商标获得的是“商标专用权”,何谓注册商标专用权?显然不仅仅是一种自己可以使用商标的权利,更是一种可以禁止(或许可)他人使用商标的权利,这才是商标权相对完整的内涵。正因为如此,学界已将商标权的具体权能划分为使用权和禁用权。也即,唯有通过注册,商标权人才能够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自己的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并以禁止为前提有偿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商标,也即获得商标权中的禁用权。因而注册前后,尽管不妨碍商标权人自己的使用,但与商标权人能否禁止他人使用截然不同。禁止他人使用才是注册人注册的动因及所欲发生的法效果。因而,通过行政授权获得的商标权本质上是一种禁止他人使用某种商标的权利。立基于“不论是否获得商标专用权都不妨碍商标权人自己使用”,因而推论出注册商标不是行政许可或者注册商标没有获得新的权利的学者显然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一点。
再看专利权,专利权的内涵显然也不在于对其技术的使用权。专利权之要义与商标权类似,同样不是自己可以实施相应技术的权利,而是自己能否禁止他人实施该技术的权利。在某些情形,专利权人甚至不能实施自己已享有专利权的技术,如其专利的实施有赖于他人的专利,而自己尚未得到他人的专利授权的情形。因而专利获得授权前后的根本性不同不在于专利权人可否实施自己的技术,而在于专利权人可否禁止他人实施其专利。对于这一点,反对行政许可论的学者显然也缺乏清晰的认识。
因此,将商标权、专利权解读为一种仅仅是自己可以使用某种商标或者技术方案的权利,是对以上两种权利的根本性误读,甚至可以说这种误读曲解了上述权利设定的根本性初衷,尤其是专利权。
其次,沈俊杰等学者试图从自然权利论的角度来证明商标权是先于行政注册而存在的。他们认为,“商标权作为一项民事权利,应当自创造活动发生这一事实行为而产生,法律规定的有无并不是民事权利产生的依据。”①同注释⑥。本文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其却忽视了商标与注册商标之区别。商标本身的权利正当性,可以从自然权利的视角来进行有限的论证,如消费者对商品区分的需要等;但注册商标所具有的商标专用权的正当性就很难从自然权利角度证成了,因为注册商标专用权可以许可、可以转让,这种适应现代社会商业运作的权利运作模式因而带有明显建构痕迹的制度安排,已经很难从自然权利的角度得到证成,而需依赖于激励论等功利主义视角。因此,简单地认为注册商标所产生的商标专用权是自然权利的观点,至少在本文看来,是缺乏理论支撑的;而认为法律规定的有无不影响商标权(当然此处当指商标专用权)的存在,则明显违背了基本经验事实。因而从自然权利角度否定商标注册为行政许可,同样是不能成立的。
再次,梁志文的几个论据同样值得商榷。“各国专利法仅将专利授权结论作为权利有效的表面证据, 而非最终效力。”这本身并不能推导出专利授权非行政授权行为,因为其隐含的逻辑前提“行政授权行为是具有最终效力的”这一点在我国行政法律框架下并不成立。与所有的具体行政行为一样,已获得的行政许可也可能基于利害关系人提起的行政复议或诉讼而丧失效力。而至于梁文提到的“将专利授权行为视为行政许可行为, 仍属于将专利权视为特许权思维的延续”则尤其值得商榷。梁志文认为,“自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 专利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将专利权视为民事权利成为共识。”②同注释⑤。然而,实证地考察法史,所谓专利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制度本身的变迁上根本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转折点;而转变的只是为专利权辩护的法意识形态,但能够由法意识形态变迁反推权利内涵的变迁吗?例如著名的《安娜女王法》,其最早基于功利规定了著作权。然而,几十年后英国法官才开始用洛克的天赋人权理论为著作权辩护,③肖尤丹:《英国早期司法判例中的作者权利》,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由此,我们能反推出引入了洛克理论著作权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的确,不同时代,人们不止一次地改变了为专利权辩护的理论,这一点,达沃豪斯的《知识财产法哲学》里有过非常详尽的论述④[澳]彼得·德霍斯著:《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然而,本文认为,权利安排本身的属性并不依托于人们如何从外在对其正当性进行辩护;而是需要实证考察其制度安排本身有没有改变。专利权无论上溯至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还是更早的1474年威尼斯的《专利法》,其一个基本内核并没有改变:专利权人从政治国家获得一种禁止他人使用自己的专利技术的权利,不管我们给这种权利贴上的标签是“特权”还是“民事权利”。因而,本文认为,梁文对于行政许可说的批判仍旧是不能成立的。
(二)行政许可说之证成
本文逐一讨论了上述学者对于行政许可说的批判。但行政许可说是否就能成立呢?
首先,关于行政许可的前提“一般性禁止”,本文认为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如某些学者理解的那样是禁止商标权人、专利权人使用自己的商标、技术,而是对这样一种行为的一般性禁止:某主体去禁止或者说不允许其他人使用自己的商标或者技术。也就是说,原则上,法律是不保护一个非注册商标持有者或者技术持有者,去禁止别人使用自己已使用的商标或技术方案的。当然,这种禁止属于上文所述的非明确禁止,也即行为人的相应行为不能受到法律的积极保护。
其次,行政许可意味着许可获得后相对方获得了新的权利,那么商标注册与专利授权能使申请人获得新的权利么?本文认为,通过实证考察,结论是肯定的。在获得商标注册后,商标专用权人取得了一系列非注册商标持有人所不具有的新权利,如禁止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相同或近似商标的权利。而专利权人则可以获得禁止他人未经自己许可实施相应专利技术的权利。因此,商标注册及专利授权绝不仅仅是对既有权利的确认,而是一种新权利的赋予。此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商标拥有者有选择是否注册商标的权利,技术拥有者有选择是否申请专利的权利,这恰恰佐证了商标注册与专利授权不是简单的对既有权利的确认,而是应申请对新权利的授予。否则,商标拥有者、技术拥有者在不发生纠纷时,根本没有必要去注册商标、申请专利,因为相关行为是有代价的,尤其是专利是需付费且有年限的。如果权利已经存在,仅仅为了确认一下而不获得新的权益就支付不菲的代价,则太不符合常理。
由此,本文认为,商标注册、专利权授予的过程中,申请人获得了新的权利应无疑义。当然,这种权利的获得是以申请人的意思表示与行政机关的相关行政行为为共同前提的。然而,即便我们通过法学理论或者实定法尽量压缩行政机关自由裁量的空间(现实中恰恰相反,这种自由裁量的空间很大),扩大申请人的申请意思表示的作用,也不能否认一点,没有相对应的行政授权,申请人是无法获得商标专用权与专利权的。因而,认为商标注册、专利权授予是行政确认的观点明显不能成立。而相关行为至少更符合行政许可的特征。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商标、专利的申请过程中,可能会涉及行政确认,但不能由此否认在商标注册、专利授予所导致的新的权利的产生,因而整体上更符合行政许可的特征。至于杜颖博士提到的国务院法制办《行政许可法有关问题解答》,谈的是基于行政管理视角的实定法适用问题,而本文是基于事物本身内在机理所作的一种学理上的剖析与归类,因此该文件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按照我国目前的法教义学相关定义以及专利权、商标权的相关特征,将专利权之授予、商标权之注册归入学理意义上的行政许可更为妥当。当然,其是否应适用《行政许可法》则另当别论。
As to the natur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ct of gran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re are three theories in our current academia: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dministrative confi rmation, quasi-judicial administrative act. This problem concerns knowledge from both administrative science of law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science of law. From knowledge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 of law perspective, Quasi-judicial administrative act is based on disputes, so it is evident that the act of gran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does not belong to this category.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nd administrative confi rmation lies in: the former grants a new right to the applicant, and the latter confi rms a right that exists. So the key issue is whether gran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generates a new right. Through empirical survey of patent and trademark system, the act of patent granting and trademark registration both enable the applicant to gain a new right. The patentee then have a right to prohibit others from exploiting (or license others to exploit) his patent and the trademark owner then have a right to prohibit others from using (or license others to use) his trademark. So, the nature of gran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more approaches to administrative license.
grant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mark; patent; administrative license; administrative confi rmation
唐艳,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王烈琦,重庆理工大学重庆知识产权学院讲师,西南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2013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信息权、传播权与著作权的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2013PYFX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