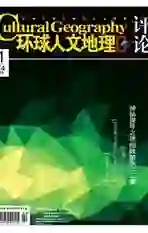人类学纪录片《最后的山神》的人类学思想
2014-12-08李欢
摘要:人类学纪录片是民族学纪录或者民族志纪录片,是对民族文化进行记录的一个文化现象。《最后的山神》表现老一辈鄂伦春人的传统的山林生活和心灵世界,反映出山林狩猎这一人类童年时期的生活方式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将最终消失的命运。人类学纪录片就是对这方面进行抢救的独特方式而存在。通过其真实的记录让人们去反思,分析传承交流文化价值、浓厚的审美艺术价值以及引领观众的社会价值。
关键词:人类学纪录片;最后的山神;文化内涵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说过,文化是公众可获得的符号形式。人类学纪录片所承担的就是文化责任。纪录片以媒介的形式记录人类的不同文化,并非只是简单的说教传播,它通过最为真实的画面声音对人的内心产生强烈的冲击,从而引导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人类长久以来都认为高大的山中是神灵所栖的地方,如罗马的朱庇特、犹太的耶和华、北欧人的奥丁都在山上。《最后的山神》便是中国鄂伦春族对山神的崇拜。
在《影视人类学概论》当中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人类学纪录片是科学成果以及艺术形式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是纪录片的手段在人类学研究中进行运用,以记录作为表现内容的一个形式,而人类学则是内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类学的研究成果。”[1]由于在速度上比较快或者是事物比较小,这对于人们的观察以及通过文字而无法进行准确的把握的时候,人类学纪录片就成了这一时刻的关键记录工具而存在;另外就是人类学纪录片是在共时性以及跨文化的对比以及历史性的文化变迁的研究过程中进行的运用。
一、《最后的山神》的简介
鄂伦春民族自古是一个崇拜大自然的民族,信奉的是原始自然宗教。由于他们世代在大小兴安岭的原始山林中狩猎捕鱼,所以他们把山神供奉为保障他们衣食的最主要的神灵。因此,老萨满雕画出来的山神像在他眼里就不再是现实中一尊古朴的偶像了,而是一种象征、一种意蕴,一个浓缩鄂伦春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化形态等诸多社会因素的象征体。
纪录片是一门现在进行时的艺术,要表现鄂伦春民族的过去,只能通过图片资料、当事人的同期声回忆及解说词旁白介绍等方式。天赐良机,编导发现了一位恪守先辈遗风的老萨满及他顶礼膜拜的山神像。[2]于是,镜头把观众的视野引向了鄂伦春民族历史的纵深。
二、人类学的运用
(一)万物有灵观
孟金福确信自然万物是有灵性的。正月十五需要拜月神。他每次狩猎,都要对山神头像顶礼膜拜地叩首祈祷。更多的场合,山神在他心中,是神灵与人性混为一体的情感在支配他的行为。比如,他发现冰雪覆盖下的小草,总要带回到他的“仙人住”窝棚里给老伴看,他们喜爱绿色。他不肯换新式猎枪,不肯下套子捕猎,怕误伤了年幼的动物,这是山神不允许的。他有意用大眼渔网打鱼,为的是让小鱼跑掉。总之,这就是孟金福——鄂伦春民族最后一位萨满的个性特点。他是鄂伦春民族仅存的一位能通神的人。
(二)对神灵的敬畏
孟金福的母亲是鄂伦春族最高领者,她知道很多关于山神的故事。当编导询问有关神灵之事时候。她却闭口不谈,她说那是神灵,是不能随便讨论的。当儿子为编导跳萨满时,她说没有神了。萨满是鄂伦春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精神领袖。萨满沟通人神的作用主要是以跳神的形式出现的。在跳神过程中,萨满被神“附体”后,萨满的说、唱、舞等动作通常就被看作是神的旨意。在跳神的过程中人们将自己的心愿和要求告诉神,而神则通过萨满之口发布自己的指令。在老一辈的鄂伦春族人心里是存在敬畏之心的。当新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对传统进行冲击后,树林越来越稀,猎物越来越少,山神离他们越来越远。
(三)对树的崇拜
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是中国主要的林业基地。森林为居民提供了燃料、食物。他们的生活与其有密切的关系,将树木视为崇拜对象也就成为了可能。在没有人创造庙宇之前,人类就用森林当庙宇的祭司的。英文中庙宇(temple)的意思就是树木。孟金福每到新的地方狩猎,总要拣一棵最粗、最直的树砍出白茬,用斧子和木炭雕画出一个山神头像来,然后顶礼膜拜。狩猎成功后会将食物放入山神的嘴中,与其分享。既是没有获得猎物也会对山神头像进行膜拜。在做桦皮船时候,割桦树皮,他总是特别的小心,怕伤着桦树的木杆,为的是使桦树来年能长出新皮。[3]当他看见画有山神的树木被砍伐所表现出来的伤心、落寞是直击人心的。在它看来树是有生命力的,它们也会感到刀割的痛苦。神灵寄居于木中,对树的砍伐也就是对神的不敬。一旦树死,灵魂便消散。《最后的山神》让人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鄂伦春人对树的敬畏,对山神的崇拜。
(四)风葬
风葬是鄂伦春族的传统,神秘而隆重。他们认为只有风葬才能使灵魂随风飘回山林。在《最后的山神》里一位老人逝世,孟金福为其举行了风葬。而在《最后的萨满》中孟金福去世,没有人再懂得风葬的具体仪式,为他人进行了一辈子风葬的他,最后不得不掩埋在黄土中。这就是让人觉得最痛心最悲哀之处。
三、最后的山神
在展示这对鄂伦春民族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活标本”时,首先是把他们作为一对洋溢着生机、充满个性活力的鄂伦春族人的老夫妻来描绘的。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孟金福,是一个在不同场合充当不同角色,呈现不同性格内涵的鄂伦春老人。他敦厚善良、平和而又固执,虔诚而又骁勇。他就是他,一位做过萨满的鄂伦春族传统猎手——孟金福。他又不是他,因为他和他所信奉的山神一起被摄人了摄像机,被赋予了形而上的内涵。他便从一个有血有肉的孟金福被升华成为一种象征,象征着已经结束了的鄂伦春民族的旧时代。于是,孟金福又变成了一个视觉性符号——最后的山神。
通过孟金福一家老幼之间的思想碰撞、对过去的依恋和对未来的向往,表现了他们从传统的山林文化向现代文明的转化过渡,揭示出鄂伦春人的内心世界。社会在前进,文明将占领任何一个角落,鄂伦春人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这种改变与人们思想上的演进和冲突有机地结合起来,给人以深刻的启示。作品后半部分,老萨满孟金福的侄女现代化的穿着和她在接受采访时流露出的想回来拍山林里动物,以及孟金福的小儿子随父亲去打猎却连马都上不去,孟金福敬山神时他又表现得心不在焉、东张西望等镜头所谓抓拍,新一代鄂伦春民族的精神面貌、志趣爱好略见一斑。鄂伦春人顺其自然地向过去告别。他们崇拜森林与山神,但如果说有山神的话,孟金福就是,他的子女是不会再过这样的生活了,可以说这位老猎人就是最后的山神。endprint
四、人类学纪录片的意义
在孟金福夫妇的心目中,山、林、水、火、日、月自然万物皆有神。他们自认为是山林之子、自然之子,每到一处总要在树上刻下一尊山神像,祈求保佑,祈求山神与他们共享欢乐,分担不幸,还时时给山神敬烟、喂食。这种行为模式,从人类文化学上说,都是文化心理的外显形态。所以,当他们发现一尊山神像被砍伐之时,便默默坐在秃树两旁,相对无言。此时,编导用了一个有剪影效果的较长固定镜头,把他们内心的哀伤与痛苦表现俱足。主人公上述活动都是在高寒的林区那样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当我们看到那新奇而颇具魅力的自然景观——或银装素裹,或雾霭茫茫,或月夜迷蒙,或天高云淡,还有那多次出现的夕阳、晨曦,无不感受到其中的灵性和意境,仿佛是“人化”了或“神化”了的自然。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代老猎人,对山林、山神的迷恋、敬重自然也被人们所理解。这种美好的心理既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的继承,又易于同当今国外“地理村民”保护环境、回归自然的心愿息息相通。
文化是一个内容比较丰富的概念,而人类学纪录片又是比较具有文化品格的电视作品,在现实意义方面具有文化价值。同时也方便于文化的传播以及交流。严格来说文化也是生活的一种方式,通过影像来对文化加以了解,在纪录片的展示下能够对于民族的文化传播有着促进作用,人类学纪录片作为是对信息负载的载体,它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了民族的文化。在人类学纪录片的文化反思表现上主要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以及现代文明的批判和对边缘文化的关注。对边缘文化的关注。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会存在差异,文化也不是固定的,少数民族的文化属于边缘文化的范畴,在当前的工业社会发展中,工业生产和边缘人群的距离越来越大,纪录片就重新把这一记忆在人们的面前重拾起来。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人类学纪录片《最后的山神》的分析,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希望能够让这一形式的影像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共鸣,对民族文化得到重视以及反思。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依附于多种的媒介技术,并不断的得到扩散,这使得文化的交流得到了加强,而人类学纪录片以它独特的方式正在发挥着其自身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雷建军,梁君健.当代北方狩猎民族人类学纪录片的文化叙述[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08):64—65.
[2]柳邦坤.眷恋山林、热爱自然的鄂伦春人的心灵之歌——纪录片《最后的山神》的人物形象塑造赏析[J]. 电影文学. 2009(22)
[3] 柳邦坤. 纪录生活习俗 纪录内心世界——纪录片《最后的山神》浅析[J]. 黑河学刊. 2006(05)
作者简介:李欢(1991——)女,土家族,湖北建始人,在读研究生,单位: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研究方向:人类学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