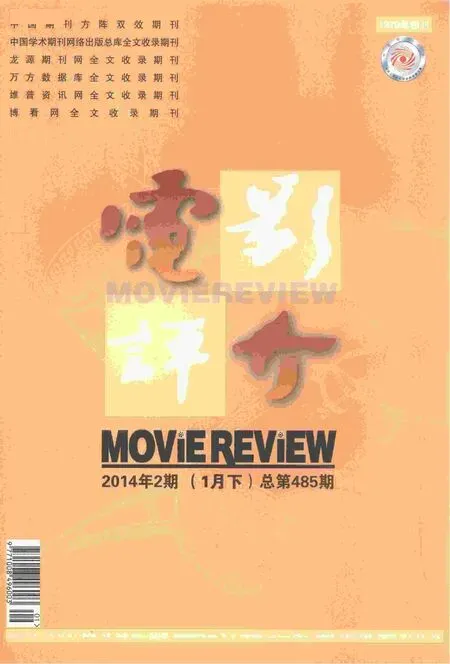追求“艺术的真实”——浅析纪录片的“真实观”
2014-09-19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文/路 越,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

纪录片《风的故事》导演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夫妇
从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完成《北方的那努克人》起,从格里尔逊在《太阳报》上首次使用“DOCUMENNTARY(纪录电影)”一词起,近百年来,关于纪录片“真实”的争论就从未止休,而这也成为了关乎纪录片本质、界定纪录片边界的根本命题。结合纪录片发展历史的语境,许多纪录片大师也对这一命题做出了较为深刻的论断,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推动着纪录片的不断向前发展。
在纪录片发展长河中,有四位丰碑式的人物——弗拉哈迪、格里尔逊、维尔托夫和伊文思。他们通过对纪录片的切身实践与理论探索,为我们提供了多样性的纪录片“真实观”。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四位大师关于纪录片创作“真实观”的厘清梳理,探求纪录片真实的本质,探索纪录片的边界。
一、弗拉哈迪:重现昔日的真实
“我执意要拍摄《北方的纳努克人》,是由于我的感触,是出自我对这些人的钦佩。我想把他们的情况介绍给人们。”在谈到为什么要拍摄这部影片时,弗拉哈迪这样说道,“我想在尚有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遭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在人们面前。”[1]
源于内心感触的动力及对历史还原的渴望,弗拉哈迪几次进入寒冷的北极,为了拍摄,他在哈德逊湾居住了15个月,同纳努克一家共同生活。对于当时已不存在的生活场景,他进行导演或搬演。这部纪录片的开山之作获得了“比石头还多”[2]的人的观看,但诟病和质疑也随之而来:在《北方的纳努克人》中,弗拉哈迪使用了搬演手法来记录早已不存在的事情,这使得一些人认为这部影片是弗拉哈迪和纳努克一家人共同排练的成果。例如,纳努克是用步枪狩猎,而不是用鱼叉;在亚兰岛,50年前人们就不再捕捞鳖鱼了,而纳努克睡觉的场景是在切开的半个雪屋中拍摄完成的等。对此,弗拉哈迪说:“我尽可能地试图通过重新搬演的手法纪录下这些人的活动影像资料,旨在让人们看到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人类光芒。”[3]这充分说明了弗拉哈迪纪录片创作的“真实观念”。
在后面的诸多作品中,弗拉哈迪也并不避讳“浪漫再现”的纪录片创作手法,他大胆地摒弃了此前人们呆板记录原始资料的拍摄手法,主张必须以人类的眼光(而非昆虫的视角)观察事物。在这种创作思路下,他对现实素材进行“创造性处理”,赋予它还原历史的真实的功能,让人们感受到已逝的文明带来的震撼。
毫无疑问,对已经消失的历史进行还原,搬演是无奈之举;但对于有很强文献性质的纪录片题材来说,对于一个搬演完成的纪录作品来说,它究竟是还原了历史,还是创造了历史?但如果苛求纪录片的“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素材”和“非虚构”的原则,我们无疑又将割裂现实和历史的系联。弗拉哈迪跨出了“即拍摄现实,又表现过去”的第一步,同时也把纪录片真实性标尺的确定问题留给后人。
二、格里尔逊:电影讲坛与打造真实
“纪录片”一词是纪录片大师格里尔逊首次使用的,格里尔逊也是第一个对“纪录片”有过明确定义的人。1932年,他对当时的英国纪录电影运动提出了这样的纲领:“我们相信,纪录电影就其所触及的、所观察的以及选自生活自身的容量,足以开发成一种新的和极端重要的形式。摄影棚在极大程度上不顾及在真实世界之上揭开银幕的可能性。他们拍摄搬演的故事,并以人工布景为背景。纪录片将拍摄活生生的场景和活生生的故事;我们相信,原生的(或土著的)角色和原生的(或土著的)场景能比较好地引导银幕解释现实世界。它们给电影提供了巨大的素材宝藏。它们使每一幅影像的力量陡增百万倍;它们促使对于真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的说明比影棚里利用魔术盒,依靠机械重演更有力量、更丰富和令人惊讶;我们相信,从这样的自然状态下获取的素材和故事,可以比搬演的东西更好。”[4]
尽管如此,格里尔逊在《夜邮》中对于一些拍摄难度较大的场景依然使用了搬演和人工布景的方法,在影棚中拍摄完成。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在急弛而过的机车上,邮递员准确地把邮包抛向目的地。由此可见,格里尔逊并非反对搬演,而是强调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和“打造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格里尔逊早年曾赴芝加哥大学学习,在这个传播学最早发端的圣地,他深受拉斯韦尔、李普曼等传播学大师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的电影讲坛理论。他曾直言道:“我把电影看作讲坛,用作宣传,而且对此并不感到惭愧。”[5]这种讲坛式的创作动机、将纪录片作为宣传手段的创作思想无疑也会在影片中留下更多组织的痕迹,更加凸显了其“打造真实”的理念。
格里尔逊的纪录片无不透出他“让公民的眼睛从天涯海角转向眼前发生的事情,转向公民自己的事情上来,转向门前石阶上发生的戏剧性事情上来”的主张。这些取材于自然和当下的作品在构成他的影片风格的同时,也让我们窥见他之于纪录片真实的理解,但他“电影讲坛”和“创造性处理”的思想又让他在“纪录电影运动”中所倡导的真实蒙上了太多个性和主观色彩。
三、维尔托夫:电影眼睛的整体真实
维尔托夫是20世纪20年代苏联电影艺术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电影眼睛”理论的创始人。1923年,维尔托夫以“电影眼睛”的名义发表了题为《电影眼睛:一场革命》的宣言,标志着苏联纪录电影史上的“电影眼睛”学派的成立。
在宣言中,维尔托夫认为,摄影机比人的肉眼更加完善,他强调了电影摄影机的许多超人的才能,主张“我们无法改善自己的眼睛,却能不断改进摄影机”,“我的使命是创造一种对新世界的认识,用新方法向你展示未知的世界。”[6]对于纪录片的真实观,他曾这样阐述:“在银幕上仅仅映出一些真实的片段和真实的分隔镜头是不够的。这些画面要用一个主题贯穿起来,使其整体也成为真实的。”[7]正如他的代表作《带摄像机的人》开篇字幕所言:“……旨在创造一种真正的国际电影语言,一种全然不同于戏剧和文学的纯粹的电影语言。”他强调对现实的即兴观察,认为电影的巨大力量就在于摄影机具备观察和获得人的肉眼所不能注意到的现实的意义。
对于之前讨论的搬演、导演手法,维尔托夫与之明确地划清了界限,他反对表演,抛弃了摄影棚、演员、布景甚至剧本,然而,这种与剧本“全然不顾”的割裂,对于纯净电影语言和真实的追求不免使得作品变得形式化。就连支持维尔托夫的爱森斯坦也认为万花筒般的《带摄像机的人》陷入了毫无动机的“摄影机的恶作剧”和纯粹的“形式主义”[8]中。
通过电影眼睛理论以及《带摄像机的人》,我们能够看出维尔托夫对于纪录片真实的追求不仅在于对每一个事实实实在在的观察,更在于通过蒙太奇记录使影片整体产生“事实之积”的效果。这种“真实观”是饱受争议的,很多人认为尽管它取材于真实,却早已不是生活的本来面目。但无论怎样众说纷纭,维尔托夫的这种拥有纯净的电影语言和明确边界的“纪录片真实观”,奠定了纪录电影长河中的初始探索。
四、伊文思:虚构和真实的解放
有着“飞翔的荷兰人”之称的伊文思与弗拉哈迪、格里尔逊、维尔托夫并成为“纪录片之父”,他终其一生心血,将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纪录片事业,足迹遍布五大洲,艺术生命历时持久。
伊文思的纪录片“真实观”确定于20世纪30年代,他将“重拾现场”和“复原补拍”视为纪录片的合理手段。在《英雄之歌》中他组织了一次“突袭夜”的演出;在《博里那奇》中,他找来一名矿工扮演警察;至于记录印度尼西亚海员大罢工的《印度尼西亚在呼唤》则是一部完全搬演的影片。
作为一个严谨的纪录片导演,伊文思对于“搬演”和“真实”提出了自己的论述。他指出,“重拾现场应该始终是在事件发生的现场并由当时在场的人来重演。如果脱离了现在而在摄影棚里或在制片场内的外景场地上表演场景,由一些感情上脱离了真实情境的演员和临时演员来扮演真人真事,就陷于危险境地了,就有可能使影片失去真正纪录片的实质,就会丢弃纪录片形式的一个最必要的武器:真实感。这不仅是一个光线和运动配合的问题,它也是一个风格和态度配合的问题。”[9]在他的观念中,“分寸”与“被摄者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成为该手法的使用前提。
对不可能回到的过去进行“复原”,这仿佛又回到了对弗拉哈迪《北方的纳努克人》真实性的探讨之中。在这里,伊文思在“真实”和“搬演”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导演的正直”。他要求纪录片制作者必须对“真实”有着深刻的理解和坚定的态度,他必须饱含着说出主题基本真理的意志。显然,不同的导演有着“不同的正直”,在对纪录片真实的探讨中,伊文思认为客观的纪录片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英雄之歌》、《博里那奇》、《印度尼西亚在呼唤》讨论的还是形式上的真实,那么伊文思的遗作《风的故事》则是对虚构和真实的解放。晚年的伊文思来到中国,执着地等待“风”、寻找“风”、得到“风”,对自己的一生创作的心路历程反观回望。整个影片充满了虚构、梦境、幻象,充满了多义和复指,已经很难将其归为“纪录片”或者“故事片”的行列。正如伊文思的妻子、《风的故事》合作者玛斯琳·罗丽丹所言:“我们想通过《风的故事》这部影片表现故事片和纪录片是一家子,实际上是一样的,它们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我所说的纪录影片并不仅指那些新闻影片或充满画面的专访式的纪录片,而是真正的探索——代表风格的、充满戏剧想象力的真正的探索……我想这也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意味着解放的影片。”[10]
伊文思用《风的故事》实践了用玄学和梦境也可以构建出真实。在他的影片中,真实本质也许并非是对“搬演/非搬演”、“虚构/非虚构”的形式上的苛求,而在于对题材所含真理的深刻挖掘与反映。如他所言:“每个题材和每个艺术家的特殊才能将决定每部影片有多少虚构,有多少记实。”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
五、追求艺术的真实
纵观四位纪录片大师对于纪录片“真实”的认识与理解,“真实”和“虚构”在“螺旋”中推动着纪录片不断向前迈进,也让我们不断地面临着选择。20世纪50年代盛行于西方的“真实电影”极力否定“虚构”的手法,认为纪录片不应当是故事片,也不应与故事片混为一谈;另一方面,伊文思《风的故事》却在另一个高度解放了“虚构”和“真实”,消解着故事片和纪录片的界线。
智如伊文思,他将“真实”交给了创作者的“良心”。伊文思看到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并不是存在于形式之中、理论之中的,而是存在于纪录者倾听现实的感悟之中。对于现实题材而言,非虚构是创作的原则,而虚构则可以提升对现实的理解。虚构不等于虚假,非虚构也不等于真实,真实的言辞,在时空的具体文本中才真正有效,而“真实”作为纪录片的“灵魂”和“生命”,是在纪录者对现实的记录中形成的,这同样是纪录者的“灵魂”和“生命”。
[1]埃里克·巴尔诺.世界纪录电影史[M].张德魁,冷铁铮,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2:42.
[2][4][8]单万里,张宗伟.纪录电影分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4,7,23.
[3][5][6][7]单万里.纪录电影文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209 -210,210,215,217.
[9]费凡.伊文思纪录电影观研究[J].科技信息,2008(04).
[10]张巍.纪录与虚构[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