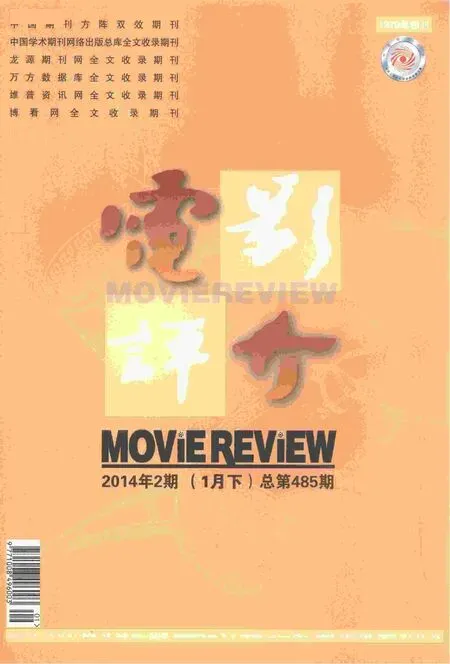被文明奴役的女人及其解放——论《金陵十三钗》的拯救
2014-11-25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
□文/杨 柳,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生

电影《金陵十三钗》剧照
一
在卢梭对人类原初生活状况的猜想中,男女虽有别,但独立而平等,坚强而孤单,他们从大自然丰沛的物产中各取所需,获得维持自己存续的给养,即使在执行了繁衍种族的功能后,他们也并不由此就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男女的生活方式没有差异。由于人拥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因适应环境变化而发展出各式生存工艺和技巧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大、小、强、弱、快、慢、胆小和胆大等之类的关系,原始人的生活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中的强者建立了家庭并拥有某种财产。这时,开始出现了两性生活方式的差异,女人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看守住所和孩子,而男人则出外去寻找大家吃的食物。这也成了男女不平等发展的起点。
卢梭认为在人类当中存在着两种不平等,一种是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这是由于年龄、健康状况、体力、智力或心理素质的差异而产生的。另一种是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它依某种习俗,经过人们的同意或至少经过人们的认可而产生。自然的不平等起初并不显明,只是随着原初状态向文明状态的演进逐渐产生并扩大,这种不平等最终在社会制度上得以确认,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
男女不平等肇始于家庭中的角色分工。男人由于承担为整个家庭谋取食物的重任使他在与自然的生存斗争中具备至少比女人更好的体质,女人则因操持家政和长期居家而变得柔弱。换句话说,男女因面对环境和事务的不同造成了他们在体力、技巧和才能上的差异。最终,这种因角色分工而来的性别差距在社会范围内得到认可,并在政治上得到体现,由此导致了妇女的屈从地位。[1]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又用一系列的社会习俗和规则来保证和维护这种关系的稳定与合理性。
这在人类的创世神话中得到了体现。在古希腊版本中,最初,只有永恒的、无边无涯漆黑一团的混沌,从中产生了世界和众神,大地女神盖娅便是从混沌中产生的,她未与其他神祇结合便诞下了天神、山神和海神。按理说,大地女神应为人类之母,主宰世界,形成母系社会。然而吊诡的是,在一个最初并无男性神祇的世界中,天神乌兰诺斯娶母为妻,后来又在这个神的家族谱系中诞生了统治人类和众神的宙斯。宙斯不仅握有主宰世界的生杀予夺之权,还享有满足其强烈情欲的特权——他可以任意和只要他看上的某位美丽女神幽媾,延嗣子孙,其妻赫拉——维护婚姻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的女神——却要忍受丈夫的一再背叛。[2]无独有偶,在日本版的创世神话中,日本据说是这样诞生的:
“天神下了一个诏书给依邪那歧命、伊邪那美命两位尊神,要他把那个飘荡的国土修理坚固。又赐他一根‘天沼矛’。这两个尊神领了诏书,站在天浮桥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里一搅,抽起来的时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积了起来便成了一个岛,这就叫做淤能棋吕岛。”[3]
从这一带有明显的男性生殖崇拜的创世神话不难看出,何以在日本民俗中一贯有男尊女卑的现象。由此看来,当无力给予人类社会起源问题确切的回答时,文明社会的人们便展开想象,冀图在虚构的神话世界中为现实的男权社会及其带有偏向的性道德寻找合理性根据。
二
男女不平等现象的最极端表现就是仅仅将女人视作满足男人兽欲的工具,甚至将她们宠物化。这一现象甚至随着文明社会的发展愈演愈烈,因为私有产权的确立将一切都纳入资本运转的逻辑,它把所有满足人们永无止境的欲望的对象都变为商品,女性身体也不例外。而在作为文明产物的战争中,女性更是深受其害。从这个角度来说,将《金陵十三钗》视作一个反映战争中野蛮兽性,唤醒善良人性、历史记忆与民族大义的影片文本,它与《南京!南京!》、《拉贝日记》等以同样的历史事件为背景的影片相差无几,但它的意义不止于此。整部影片围绕一群女性的拯救与被拯救而展开。南京城沦陷之时,十四名(准确说是十五名)女学生与十四名青楼女子为躲避战祸,逃至教堂以图从神圣的宗教那里寻求庇护。然而,宗教的神圣在战争的野蛮面前不堪一击,更何况是面对如同禽兽的日本兵。已经暴露的女学生没有退路,她们宁可有尊严地去死,也不愿屈辱而生。青楼女子们挺身而出,以无畏的替死展现出她们“永恒的力与美”。当她们摔碎玻璃,怀揣利刃,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慷慨赴死的那一刻,她们做出的是与女学生们同样的选择。她们以直面死亡的坚毅(以及玉墨对约翰买春的坚定回绝)表明,女人不是满足男人兽欲的工具,而是平等的、有尊严的人!就此而言,将《金陵十三钗》视为一个女性反抗文明中野蛮兽性的攻击侵害,维护女性尊严的影片文本,它在题旨上与《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有几分相似。
《金陵十三钗》是光影中的国殇,是一幕战争的悲剧,也是一曲女性的赞歌。
秦淮河女人的拯救壮举是女性自我觉醒的宣示,女学生的被拯救则是女性解放的希望所在。女性的拯救与解放不仅要靠她们的自我觉醒,也需要这个世界中像陈乔治、李教官、约翰这样的男人爱她们、疼她们、尊重她们、保护她们。这种爱与尊重源于人的天性中的同情(怜悯)之心。同情是人天生的一种不愿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这种心理使人不至于过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因而可以在某种情况下克制自己的强烈的自爱心,也使人能深切体会他人的痛苦与不幸,并且为努力阻止或排除这些痛苦而给予同情支援。卢梭与叔本华把这种同情(怜悯)之心视为人类惟一具有的天然的美德,也是最普遍的和最有用的美德,是其他一切德行的根源所在。叔本华依据同情的程度差别区分了两种元德。当同情心抵制自私自利与怀有恶意的动机,使我们不给另一人带来可能有的痛苦,使我自己不给人增添也许会有的麻烦时,这是最低级程度的同情;当同情心积极地影响我,激发我主动给以援助时,这是另一较高级程度的同情。前者是公正的德行,后者是仁爱的德行,两者根源于自然的同情。这两种元德训导人们摒弃“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这样富于理性和符合公正原则的处世格言,而遵循“不要损害任何人,并尽你力之所能帮助一切人”的德行规则。[4]在叔本华看来,男性推理能力较强,在理解和坚守普遍法则以及把它们当作行为指导线索方面要优于女性,因而公正多是男性的美德;女性在仁爱德行方面则超过男性,因为通常对仁爱的刺激是直觉的,所以直接引起同情感,女性对此感受比男性锐敏得多。因此,如果说男人对于女人的解放还有些许助力的话,那么重要的是克制他们那略显冷漠的理智能力,提升他们对痛苦不幸的感知度,尤其是提升他们对女性——为这个世界的另一半人创造幸福的人——在社会中所承受的痛苦与艰辛的敏感度,激发他们的同情和怜爱之心。这种同情与怜爱之心能够削弱男权社会中男人素有的优越感,让他们尊重和珍视女性,因为,“当一旦另一人的痛苦不幸激动我内心的同情时,于是他的福与祸立刻牵动我心,虽然不总是达到同一程度,但我感觉就像我自己的祸福一样。因此我自己和他之间的差距便不再是绝对的了。”[5]
文明的进程已不可逆转,男女之间因为文明社会的演进而形成的在体力、技巧等方面的差异是显见的事实。但这种自然的差异与精神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并没有实质性的联系,而是文明社会的特权、习俗和规则将女性框定在受奴役的弱者地位。一些女性寄望通过获得在家庭事务中的形式主导权来彰显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地位,但如果没有女性的觉醒与独立,没有男性对她们真诚的尊重与疼爱,而且只要她们还抱有依赖心理,那么她们仍将是柔弱的,而家庭中话语权的些许让步甚至倒序也就只意味着妇女对男性忠诚的善良期许,这不仅不会改变妇女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反而会使得她们在感受尊视的虚假幸福中在社会层面继续遭受奴役。当然,随着文明的发展,女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已有很大的改善,但女性要真正解放,赢取男性与社会的尊重,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地位,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1](英)亚当·弗格森.道德哲学原理[M].孙飞宇,田耕,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0.
[2](俄)H·A 库恩.古希腊的传说与神话[M].秋枫,佩芳,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22.
[3]戴季陶.日本论[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22.
[4][5](德)叔本华.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M].任立,孟庆时,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34-259,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