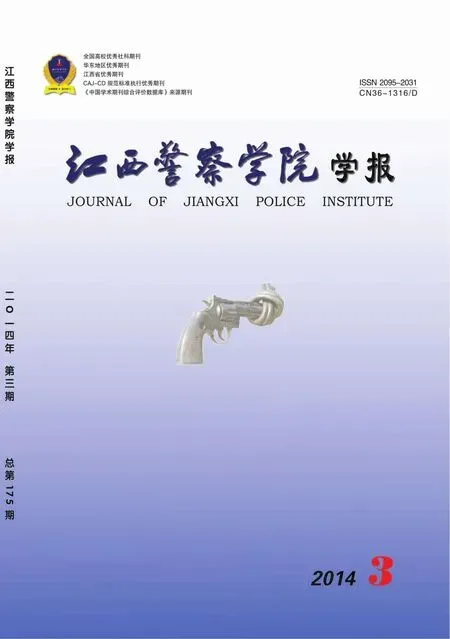论我国古代拷讯的法律限度
2014-04-16蔡艺生
蔡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论我国古代拷讯的法律限度
蔡艺生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拷讯,又称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中国古代拷讯的主体呈现出广泛性,具有审判权的主体也就具有了拷讯的权力。拷讯对象包括人犯、告人和证人。拷讯的启动包括以刑讯替代刑罚和法定必须刑讯的绝对启动,以及必须因为拒不供认、合理怀疑或连署审批的相对启动。拷讯的实施限度有:时间限度、刑具限度、次数限度和执行人限度。拷讯的终结指的是拷掠的停止,其原因为拷讯实现了预期目的,或者拷讯因为被刑讯人死亡、大赦、无罪、“赃状露验”或“限满”而没有继续的必要性。拷讯的责任体系包括绝对及相对的无责任;以及因为拷掠致死、锻炼成狱或违制拷掠而产生的相应责任。
刑讯逼供;拷讯;拷讯对象;拷讯启动
拷讯,又称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拷讯始盛于秦,而“汉承秦敝,考囚之法盖亦甚酷”。后,梁朝、北齐加以发展。宋承唐法,一度严格禁限刑狱之弊,但官吏“擅置狱具,非法残民”。辽代“拷讯之具有粗、细杖及鞭、烙法”。[1]元朝对蒙古之外的其他民族人尤其是针对汉人,滥施刑讯。明朝厂卫审案,集前朝刑讯之大成。清朝的审讯制度继承唐宋,刑讯继续施行,直到20世纪初的晚清修律,刑事诉讼制度上才注意吸收西方近现代的一些法制成果。民国,刑讯依然盛行。尤其是国民党中统、军统审理各类“党国要案”,更是滥施刑讯,酷刑逼供。纵观拷讯的历史,可见法定拷讯与法外拷讯相互交织、拷讯的限制与拷讯的泛滥如影随形。笔者试考察中国拷讯的历史源流,厘清其脉络、探求其规律、还原其本质,以求助益于当下的侦查法治化进程。
一、拷讯的对象限度
在古代刑讯的对象上,首先是案件限度。如,唐朝规定对如下案件不得刑讯:一是赃罪如果赃物和罪状已查获证实,杀人罪的证据,事实已经查清,又在事理上没有可疑之处;二是像犯罪情事,本刑已经赦免,虽然还须再追查究问者,不应拷刑。元朝规定:指告不明,无证佐可据者,不可刑讯。《明史·刑法志》规定:“凡内外问刑官,惟死罪并盗窃重犯,始用刑讯。”即,对于死罪或盗窃重犯之外的案件,不得使用刑讯。其次是人员限度。拷讯的对象当然包括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是,在漫长的拷讯历史中,这并不是唯一的对象。当时,拷讯不仅是为了让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服罪,还有获取证人证言、防止滥告、炫耀政府威权等目的。因此,拷讯的对象不仅包括当然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还包括原告和证人。
(一)人犯
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在古代统称 “人犯”、“囚犯”或“犯人”,是拷讯的当然对象。拷讯的概念即是运用肉刑或变相肉刑获取人犯的口供——“刑讯者,讯问狱囚以刑求之之谓”,即通过行刑的方法来讯问犯人。[2]在古代,整个诉讼过程往往也就是“威服”人犯,或者让人犯“服输”的过程。而对人犯施行刑讯是让其“屈服认罪”的最便利的方式,也是体现政府维护自身统治力和社会秩序的最佳宣示与标志,也符合被害人的复仇心理和社会大众的心理预期。
(二)原告
古代拷讯的对象并不限于人犯,同时还包括“告人”,即原告。因为,一旦某人提起告诉,被告人就要承受刑讯的痛苦和被定罪量刑的风险。为了防止滥行告诉或者诬告,各个朝代给原告规定了相应的责任,而最直接的就是“诬告反坐”。而诬告事实一旦成立,原告就成了被告,因此,对其刑讯亦属情理之中。
秦朝明确规定“诬告反坐”。《唐律·拷囚限滿不首》载:诸拷囚限满而不首者,反拷告人。其被杀、被盗家人及亲属告者,不反拷。被水火损败者,亦同。《唐律疏议》载:囚拷经三度,杖数满二百而不首,“反拷告人”。即,被告被刑讯的次数和杖数已达到法定数量,却仍然没有招供时,必须对原告进行刑讯,对原告刑讯的数量同被告被刑讯的数量。但是,被盗、杀、防水或纵火毁损财产生命的,不反拷,因为此类事情往往疑点诸多,反拷的规定可能使得被害人不敢告诉。
(三)证人
在侦查技术极端落后的古代司法,言辞证据对于案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为获取证词,“拷讯逼证”即成为我国古代司法官审讯证人之常用手段。同时,我国古代对刑讯对象的年龄和身体状况也有些限制。如,规定年幼、年老、残疾或者疾病者不得刑讯。
二、拷讯的启动限度
古代的司法审判中,虽然拷讯基于其合法性和社会的许容性而泛滥。但是,各个朝代对于拷掠仍有所律例规范。如,其启动有所限制与区别。根据其启动的缘由,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一)绝对启动
绝对启动指的是凡审讯必须进行拷掠,拷掠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获得口供,而被赋予了其他目的与意义。如,被赋予了刑罚的功能,或者成为一种慑服的手段。
1.刑讯替代刑罚。在某些时期,特别是新朝初立,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急需用严刑峻法来震慑社会。但是,基于传统法律或惯例,其罪名与刑罚的现有设置“束缚”了统治者的行为。因此,统治者就广泛施行拷掠,用拷掠替代刑罚,以达到其“威服”的目的。如,隋文帝诏令:“据律乃轻,论情则重”者,“听于律外斟酌决杖”,[3]即,根据现有律例,犯罪人罪行并不严重的,则可以由主审官员法外斟酌拷掠。因此,隋朝一时之间拷掠成风,各级官员都以拷掠为能事,而以仁慈为怯弱无能。
2.法定必须刑讯,即,律例规定审讯中必须施行拷掠。如,明《问刑条例》载:“内外问刑衙门,一应该问死罪并窃盗、抢夺重犯,须用严刑拷讯。”意思是对于该判死罪,或者窃盗、抢夺的重犯,必须严刑拷讯。同时,在明朝的某些上诉程序中,也规定了上诉人必须先行接受酷刑,然后再重审其所申诉案件。此时,刑讯的目的发生的变异,不再是单纯为了获取口供,而是被赋予了“炫耀”公权力、制约滥诉或者宣泄民愤的功能。
(二)相对启动
相对启动指的是司法审判中,并不必然使用拷掠,而是根据一定的前提条件而启动。一般而言,其前提条件有“拒不供认(不服)”、“合理怀疑”或“连署审批”。
1.拒不供认,又称“不服”,即,只要人犯拒不认罪或者不服判决的,都可以拷掠。古代司法鲜有人权保障之说,对于犯罪嫌疑人往往进行有罪推定,只要人犯不招供,即行拷掠,直至其认罪伏法。
2.合理怀疑,即刑讯的启动必须有相应的证据线索,而且该证据材料达到了某种标准,即,依据理性和常识都会认定人犯有所隐瞒而应予以拷掠的地步。各个朝代都有类似先行以情理、物证等验证人犯是否犯罪,形成了合理怀疑后,人犯仍不招供的,才可以进行刑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合理怀疑前提下的拷讯为拷掠提供了某种合理性和正当性。不过,由于拷讯的便利性和合法性等,使得拷讯屡屡突破法律和道德的限界。
3.连署审批,即,拷讯的启动必须经过上级审批或者多名同级(同职)官员同意。宋代规定,各州捕获的罪犯,如果还没要验查明白,不得先进行拷打;如果必须拷问,要向上一级官府请示,得到批准后才能进行。《元典章》载:“若或事情疑似,赃仗已明,而隐讳不招,须与连职官员立案同署,依法拷问“。即赃物等证据已经明了,而人犯仍然不招供的,审判官员联名立案后,才可以拷掠。
三、拷讯的实施限度
拷讯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不仅在于其“便利性”与“实用性”,也在于其具有相应的符合社会预期的限度而具有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对合理性与正当性。同时,统一的限度也体现着中央对地方拷掠的控制,符合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和道德宣扬需要。因此,虽然拷讯在历史上经常泛滥,但是,合理的限制亦是如影随形。正是限制与泛滥的博弈,构成了我国拷讯的历史脉络。拷讯的实施限度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时间限度
1.拷讯的整体时间安排。现存的拷讯最早记载是《礼记·月令》载:“仲春之月……母肆掠,止狱讼。”因为“是月止狱讼,助其生气,止其刑狱。”意思是在春天的第二个月,各地不得进行拷掠等司法活动,因为该月是万物勃发的季节,不适宜进行肃杀的司法活动。这是对拷讯的时间限制之一。
2.单次拷掠的时间规定。南朝梁武帝时,创立“测罚”逼供之法,即对拒不招供者先断食三天,再让家人送粥进食,如此循环往复,直至招供为止。这是通过禁止进食的方式逼迫招供,而每次刑讯的时间不得超过三天。陈朝陈武帝时,在“测罚”之法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更为野蛮的“测立”之法,即先对受审者分别鞭打二十下、笞捶三十下,再强迫其身负枷械刑具,站立于顶部尖圆仅容两足的一尺高小土垛上,以折磨逼供。根据具体情节,每次“测立”时间为七刻。
3.拷掠的间隔时间规定。唐律规定在两次拷打之间要相隔二十天。陈朝陈武帝的“测立”之法规定,两次鞭打之间的时间间隔是七天。
(二)刑具限度
在古代的拷讯制度中,法律往往对刑具有明确限制。如,《魏书·刑罚志》载:“其捶用荆,平其节,讯囚者其本大三分,杖背者二分,挞胫者一分,拷悉依令。”该规定对拷掠所使用的荆条平滑度、宽度有着相应的规定,杜绝法外滥施酷刑。《唐律》中规定的刑讯方式是笞杖,不允许用“杖以外他法拷掠”。《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刑法志三》规定:“热审得用掌嘴,跪磁等刑,强盗人命酌用夹棍,妇人夹指,通不过二。”即,热审可以用掌嘴和跪瓦质碎片等方式,强盗人命案件可以用夹棍,而对于女人犯则可以用夹指。
(三)次数限度
对拷讯的次数限度主要表现在笞杖的数量和拷掠的回合。《唐律》规定:“诸拷囚不得过三度,数总不得过二百,杖罪以下不得过所犯之断。”即,拷掠总数不得超过三回,三回当中笞杖的总数不得超过两百鞭(杖);如果是所犯之罪最多应予以杖刑的刑罚,则杖责的数量不得超过其罪名成立所应判处的杖刑数量。北魏规定,“鞠囚限于杖五十”,即使用杖刑审讯囚犯的,其杖刑数量不得超过五十。同时,北魏对于拷掠的次数限度还有着更为灵活而原则的规定。如“量人强弱,加之拷掠”,即根据被拷掠对象身体的强弱程度,通过对于刑具尺寸、次数和力度的把握进行相应的刑讯。陈朝陈武帝时 “测罚”之法规定:鞭打的当天上垛二次。
(四)执行人限度
对拷讯执行人的限度表现在行刑人中途不得换人。汉朝景帝刑制改革:颁布《令》,改革刑具,规定行笞刑不得换人。唐朝《唐令拾遗·狱官令》载:诸讯囚,非亲典主司,皆不得至囚所听闻消息。其拷囚及行决罚者,皆不得中易人。
五、拷讯的终结
拷讯的终结指的是拷掠的停止,其原因不外乎为拷讯实现了预期目的或者拷讯已经没有必要或可能了。前者主要是被刑讯人已经顺利招供,而后者则包括被行刑人死亡、大赦、被证实无罪、“赃状露验”或拷掠“限满”。具体如下:
(一)拷讯实现预期目的
拷讯之所以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人们查清案件事实的能力不足,只能寄期望于相关人的言辞证据。而口供作为“亲历”案件事实的当事人的证词,其真实性自不待言,使得口供成为了证据之王。当然,统治者大量使用拷讯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炫耀权力,威服天下。在一顿棍棒之下,其权力的强悍性掩盖了其权力的虚弱性,达到了慑服的目的。因此,拷讯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查清犯罪事实、终止百姓对政府权力的怀疑,更是为了实现对自身统治力的证明。
如上所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被刑讯人一旦招供,拷掠便也实现了其所有的目的,也就宣告了该次拷讯的终结。
(二)拷讯失去必要性
拷讯的终结的另一个原因是,虽然被刑讯人没有招供,但是,由于其他情况的出现,拷讯已经失去了继续进行下去的必要或可能。
1.被刑讯人死亡。由于拷掠而导致被刑讯人死亡的情况在古代并不鲜见,法律也明文规定在相应的情况下,刑讯致死免责等。特别是在各个朝代的后期,或者在政权不稳定时期,刑讯致人死亡的情况更是常见。如明朝刘瑾当权时期,其首创“重枷”,重至一百五十斤,活活把人压死。而被刑讯人一旦死亡,便也无法再行拷讯,而该案可能也因此了结。
2.大赦。大赦指的是以国家命令的方式对某个时期的特定罪犯或一般罪犯实行免除或减轻罪责或刑罚。古代封建帝王以施恩为名,常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更换年号、立皇后、立太子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大赦之后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罪行被赦免,同时不需要再行追究责任的;一是虽然被大赦,但由于情节严重等,仍需要追究相应责任的。对于前者,则其罪行已经被赦免,也不需要再行追究其他责任的,则拷讯自然失去了必要性。而对于后者,虽然仍需要追求相应责任,不过,由于经皇帝大赦,人犯也因此被赋予了相应的特权——免于刑讯。即,因大赦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的情况下,不得刑讯。
3.无罪。顾名思义,无罪指的是被刑讯人由于其他证据的出现,而证实无罪的。如,其他人证物证已经清楚表明该被刑讯人无罪,或者指明了真正的犯罪人的。此时,刑讯也就失去了继续进行的必要性。
4.“赃状露验”。即,虽然被刑讯人尚未招供,但是,根据其他物证或人证已经可以确认其罪行的,而且达到了“理不可疑”的标准的,则可以直接定罪量刑而不必再行拷掠。《唐律·讯囚察辞理》载: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所谓“赃状露验”,指的是“谓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检得实状,赃状明白”。
5.限满,指的是刑讯次数达到了法定的上限,而不得再行拷掠的。如上,笔者在论述拷讯的次数限度中所列拷掠的次数,一旦达到法定次数,则不得再次施以拷掠。甚至,一旦拷掠次数达到法定标准而被刑讯人仍无招供的,则即被证明清白,随之而来的是对“告人”(即原告)的“反拷”。
四、拷讯的责任
古代对于拷讯的责任规定往往针对的是 “拷掠致死”或“锻炼成狱(屈打成招)”的情况。因为刑讯本身即是肉刑或变相肉刑,而肉刑肯定会导致身体的伤害,这是为法律所允许并为社会所认可的。如秦有名的“大痍”,即囚犯经刑讯后,肢体将断,不能行走,须长官令人扶回的,谓之“大痍”。此种情况下,刑讯官员的所谓责任也就是必须令人将其扶回,一般只有在出现了被刑讯人死亡的情况下,法律才会考虑刑讯官员的责任问题。但是,即便是法律如此规定,刑讯官员仍然经常逾越法律的限界而未遭遇任何处罚;或者法律对于刑讯致人死亡的责任规定相当宽泛与宽松。同时,对于屈打成招而导致的冤假错案或违制拷掠的情况,律例也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体系。
(一)无责任
无责任即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此种情形包括:绝对无责任和相对无责任。
1.绝对无责任,即根据法律或当时政策等而无论是否存在故意或过失,一律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此种情况往往出现在各个朝代初立,需要依赖严刑峻法来巩固统治的前期;或者后期朝政紊乱纷争不断的情况下。如,隋朝皇帝明令“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以致“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能干,以守法为懦弱”。一时之间,刑讯肆虐,屈死之人无数。
2.相对无责任,即根据法律规定刑讯而导致人犯等死亡的,官员不需要承担责任。如,《唐律》若依法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仍令长官等勘验,违者杖六十。即,如果官员没有存在故意致人死亡的故意,依照律例进行拷讯当中不幸导致人犯死亡的,不需要承担责任。宋朝规定,拷囚后,经过十日之后死亡的,官员不承担责任。
(二)相应责任
存在相应责任的情形包括“拷掠致死”、“锻炼成狱”和“违制拷掠”。
1.“拷掠致死”,即因刑讯而致人死亡的。此种情况又细分为两种,一是因公拷掠,二是因私拷掠。
(1)因公拷掠致死的,由于并非出于官员故意,所以各朝律例都给予较轻的处罚。如《唐律》载:杖数超过法定标准而致死者,科以杖一百。囚有疮病不待愈拷掠而致死者,按“考囚不得過三度”条,当杖九十。属于议、请、减、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等不合捶拷者,拷掠致死,当缴纳铜一百二十斤。孕妇未产而拷掠致死者,科以两年半徒刑,已产未满百日拷掠致死者,当徒二年。宋朝规定:拷讯囚徒十日内致死要负刑事责任。
(2)因私拷掠致死的,由于是出于官员个人私利或私怨而进行拷掠,所以一般都处于较重的刑罚。如,《宋刑统》载:准刑部格:赦节文,其有挟情托法,枉打杀人者,宜科故杀罪。即,徇私枉法而将人犯拷掠致死的,按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而对于故意杀人罪,一般都处以斩刑。
2.“锻炼成狱”,即屈打成招而导致冤假错案,但并没有因为刑讯而直接导致被刑讯人死亡的。对此,一般都必须追求主审官员的责任。如,明:“凡鞫问罪囚必须依法详清推理,毋得非法苦楚,锻炼成狱,违者究治。 ”
3.“违制拷掠”,即违反律例进行拷掠,而没有直接导致被刑讯人死亡的。对此,各朝代一般都以律例的形式规定了相应的责任,不过该条文往往被束之高阁。如,唐朝“若拷达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掠者,杖一百;杖数过者,反坐所剩。”意思是,如果拷打超过法律规定的三次,或者使用法定的杖刑以外方式拷打的,对官员处以杖刑一百。如果杖刑的次数超过法定数量的,对官员处理所超过数额的杖刑。
[1]卜安淳.拷讯犯罪的法文化考察[J].山东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1,(6):47.
[2]李金强,刘涛.中国古代刑讯制度研究[J].文史月刊,2006,(3).
[3]叶孝信.中国法制史[M].上海:复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黄晓玲
DF09
A
2095-2031(2014)03-0101-04
2014-04-16
重庆市高校物证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研究项目“情态证据的运行原理与机制研究”(LCFS140507)
蔡艺生(1981-),男,福建龙海人,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情态证据研究室主任、侦查学院副教授,从事侦查学和证据法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