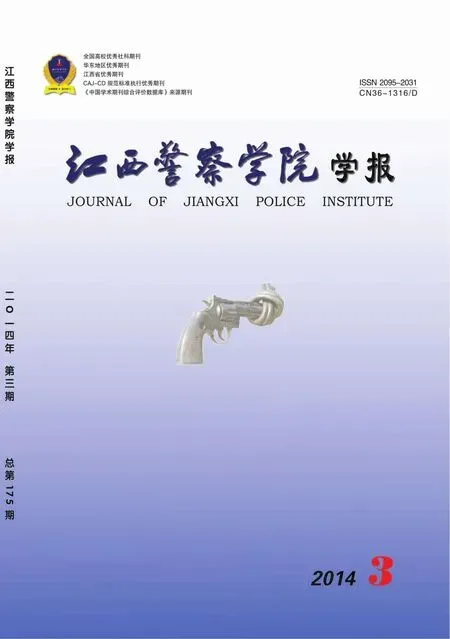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研究
2014-04-16孔祥承
孔祥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研究
孔祥承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北京 100089)
附带监听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我国立法与实践并未作出回答。但在充分汲取域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监听基本原则及刑诉价值权衡为标准进行分析对于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可以通过关联性标准及重罪标准获得证据能力;对于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在一般情况下无证据能力,但在重罪情形下可获得证据能力。同时,附带监听资料若想真正取得证据能力,尚需通过事后补正制度与证据调查程序检验,从形式与实质层面对其进行治愈。
附带监听;同一对象;不同对象;证据能力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八节 “技术侦查措施”,对实施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程序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做出了规定,使一直隐于幕后的监听显现在人们的面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107条规定,“采取侦查技术措施收集的证据资料,经当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的,可以作为定案依据。”这项规定标志着监听资料可以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上,而非像以往那样潜藏于幕后,在暗中伺机侵蚀当事人的权利。
侦查机关依法实施监听时,在某些情形下,发现超出监听令状所记载的犯罪事实,或者发现被监听对象以外的其他人的犯罪事实,这就是所谓的“附带监听”,这种监听又被称为偶然监听或者意外知情。[1]103这类附带监听在一般的监听侦查行为中出现频率极高,这是由附带监听的偶然性、必然性、无法预测性等特点所决定的,同时这也导致在实践中我们必须面对附带监听所带来的证据评价问题。纵观各国法制,仅有少数国家对其作出了规定,而且这些国家对于这种规定制定得也不完善,这类监听资料的证据能力仍然游走于法律的边缘。[2]
监听是把“双刃剑”,一旦违法监听披上国家行为的合法外衣,那便犹如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放任监听的“恶灵”侵蚀我们的生活。附带监听作为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不端监听,人们往往将希望寄托于监听者自身的道德上,相对于对虚无人性的向往,我们更应当将希望寄托于理性的法律规制当中。在监听资料可以步入法庭的今时今日,应当重视附带监听所得资料的证据能力问题。
一、附带监听的若干问题
为解决附带监听的证据评价问题,我们首先需明晰附带监听与其他侦查行为的区别,划定出附带监听资料的范围。
(一)附带监听与他案监听
他案监听,一般是指侦查机关为了监听将来可能发生或已发生但尚不具备法定监听条件的案件(本案),而以具备可监听条件的他罪名(他案)申请执行监听,该监听执行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搜集重大犯罪(他案)的证据,而是为了收集本案的证据。[3]此类监听明显是为了规避监听事前审查机制,不具备附带监听的偶然性特征,这种方式取得的证据应予以排除。不过,要事先察觉他案监听并不容易,对它的解决可依托于事后审查程序,重点判断审查监听所获之材料用于他案还是本案。
(二)附带监听与另案扣押
附带监听与另案扣押并不相同,并不能参照“明显可见原则”进行处理。①又称“一目了然”原则,指在合法搜查中在视野范围内的另案物品可以扣押。此原则的适用有两个要求:一是存在合法搜查;二是此证据意外获知。监听相对于扣押而言,有诸多不同。其一,监听对象为无形物,交流的声音稍纵即逝,不易保存,对于扣押而言,其主要针对的是有形物。其二,附带监听所得一般为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而扣押所得一般为物证。其三,监听侵害公民深层次的隐私,有隐秘性特征,而扣押对象有公示性,侵犯性较轻。
区分附带监听与其他侦查行为有助于我们厘清附带监听的界限,进而从外部确定附带监听资料的范围,以防与其他不端监听行为混淆。
二、附带监听的分类标准
附带监听主要存在两种情形:一为监听对象在监听许可令状记载罪名以外的事实;二为监听对象以外的其他人。这两种类型侵犯的权利、危害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对于附带监听证据能力制定统一标准尚有难度,应当另辟蹊径对其分门别类的进行分析。在既有理论中,一般以监听对象是否同一、监听罪名是否属于法定可监听罪名为标准,通过排列组合,将附带监听分为四种表现形式:同一对象的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同一对象的不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不同对象的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不同对象的不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4]进而对每种附带监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进行个别分析,但是随着我国对监听行为相关立法的出台,使这种标准在现有制度下存在一些问题。
监听许可的申请需要限定对象与罪名,对于超出监听对象的附带监听而言,将其分为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和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将监听罪名作为分类标准则存在一些问题。这种四分法的分类依据主要是以国际通行“罪行限定法”或者是“罪名限定法”②“罪行限定法”是指以罪行轻重为标准,划定监听范围,如法国刑诉法第100条规定,“处两年以上监禁刑可进行监听”。“罪名限定法”是指将可监听以列举罪名的方式加以确定,如《日本〈关于犯罪侦查中监听的法律〉》以附表列举罪名的形式对可监听罪名进行限制。为理论基础,这两种方法对可监听的罪名的限定有详细标准,在我国未对监听立法之时,该分类标准尚称合理,但伴随着监听立法的展开,这种分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我国刑诉法第148条规定以“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作为兜底条款对监听所适用的罪名进行限制,实质是认为只要与前述列举罪名同质的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皆可申请监听,重视的是罪质问题,这种标准过于泛化,未对可监听罪名作出具体限定,体现出我国采取的限定是一种“罪质限定法”,由此看出,在实践中对于可监听罪名的认定范围有极大的弹性,没有相对确定的罪名或罪行标准进行限制,如以毒品犯罪申请监听,意外侦知抢劫事实,那么抢劫罪是否属于可监听罪名,它属于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还是不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适用何种标准,这些在我国“罪质限定法”下,单纯从形式标准层面是无法判断的,在我国以监听罪名这种模糊的标准作为分类依据,只会使分类更加模糊。
综上所述,附带监听四分法在现有立法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此时我们不妨仅将是否超越监听对象作为分类依据,进而讨论其证据能力问题。下文对附带监听所得资料证据能力的分析将具体从这两个种类详细展开。
三、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的取得路径分析
对附带监听种类作出具体分类后,我们便要对其各类证据能力进行分析,在阐释之前,我们应对附带监听资料获得证据能力的几种可能路径进行简要分析。
(一)比较法视野下的证据能力取得路径
监听资料作为证据在我国起步较晚,由此我们不妨扩展视野,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为附带监听资料的证据能力讨论找寻理论依据。美国实务界主张,附带监听原则上不具备证据证据能力,但存在三种例外:一是类似犯罪的例外,二是不可分的例外,三是默许授权例外。③类似犯罪例外,是指若附带监听的罪名与监听许可证上的罪名存在相似性,那么证据资料便可作为证据使用。不可分的例外,是指附带监听罪名与附带监听罪名存在关联性,那么所得资料便可作为证据使用。与此相对应的,美国学界也存在三种观点,即严格限制说、相对限制说、无限制说。④无限制说,认为附带监听资料可作为侦查线索,不可作为证据。相对限制说,认为只有对于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无限制说,认为附带监听资料无需限制,皆可作为证据使用。德国法律界对于附带监听的理论可以总结为四种,即无限制说、部分禁止说、相对禁止说、绝对禁止说。而日本学界则认为只在涉及重罪时,可以使用附带监听资料。
通过这些资料的梳理,我们可知,对其证据能力的评判不能走向全有或全无这两个极端。侦查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逐渐查明事实的过程,先前限定的申请罪名并不一定精确。从这些域外理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特点:其一是对于涉及重罪的附带监听所得的资料一般认可其具有证据能力;其二是对其证据能力的讨论一般采取折中方式,其重点在于折中的具体标准。这些理论成果对我国确立附带监听证据资料标准有极强的借鉴意义。
(二)监听基本原则下的证据能力取得路径
监听的原则贯穿于监听法律制度,指导着监听立法和实践,研析各种监听理论,其都对监听的基本原则有所阐释,如台湾学者曾正一将台湾通讯监察总结出三项原则,一为正当程序原则,认为正当法律程序不仅指公平合理的司法程序,更指公平合理的法律内容,权力机关行使权力时,不得肆意专断;二为比例原则,其还可以细化为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三为法律保留原则,认为干涉公民正常生活的措施应纳入法律规范进行规制。[5]
我国在新刑诉法出台之前,对此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理论界对其探讨颇多,已经形成了一套基本原则理论体系。对于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的讨论来说,只有经过基本原则的考察,才使它们具备证据能力成为可能。对于附带监听证据能力讨论而言,涉及的主要基本原则是比例原则、重罪原则、相关性原则等。①类我国理论界认为监听基本原则分为两类,强制性侦查措施共通的原则,如程序法定原则、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令状原则;监听的特有原则,如必要性原则、相关性原则、重罪原则、隐私权保护、适度公开原则、救济原则、时限原则等。
(三)刑事诉讼价值理念对证据能力取得路径的影响
事实上,对于附带监听所得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也与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刑事诉讼价值有密切关系。
在以监听的基本原则作为衡量标准时,亦考虑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进行价值权衡,因为一国对于附带监听资料之证据能力的规定同时也是该国刑事司法理念的体现,也是该国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问的价值选择的重要体现。在实际讨论附带监听资料的证据能力时,应将犯罪控制与保障人权这两种衡量标准相结合。
域外附带监听的理论与实践为我们的制度建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监听基本原则则为权衡监听资料证据能力提供了标准,刑事诉讼理念为附带监听资料的取舍提供了一种价值衡量手段。这三者综合运用对我国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标准的提出大有裨益。下面笔者将从这几个角度,对两类附带监听所得证据能力进行分析。
四、两类附带监听证据能力分析
(一)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分析
对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来说,其获得证据能力的标准需要进行两个层次的分析,即以关联性标准作为一般标准,以重罪标准作为例外标准。
1.关联性标准
这种标准理论来源于德国实务界提出的 “相对禁止说”以及美国实务界提出的“不可分之例外”为理论基础,认为对同一对象附带监听的证据能力的讨论,第一步需要考量的是偶然所得与监听罪嫌的关联程度来进行判断,若关联性较大,则认可其附带监听所得可获得证据能力。此时应当注意,这种关联性主要是指的某种方法与目的的关系,原因与结果的关系,或两者有某种涵摄关系。
如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申请对甲进行监听,但监听的是甲涉嫌抢劫罪,若该抢劫犯罪是以黑社会组织的形式展开的,我们便认为两者具有关联性,附带监听到的抢劫的犯罪资料有具备证据能力的可能。反之,若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申请对甲进行监听,但监听的是甲涉嫌重婚罪,重婚罪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难以看出存在何种关联性,此时涉及重婚罪的附带监听资料便没有获得证据能力的可能。
相比于“部分限制说”“相对限制说”,关联性标准有着极大的优势,首先,考虑到实务因素,对犯罪的侦查是一个过程,从模糊到清晰,并非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可以事先把罪名查的很准确,就罪名而言,本身存在想象竞合、牵连等关系,僵硬的按照“部分限制说”“相对限制说”理解,会无形之中对很多与监听罪名相关的其他犯罪事实的使用造成制约。[6]其次,我国没有采取国际通行的“罪名限定法”或“罪行限定法”,而采用的是一种“罪质限定法”,这种限定是通过法律判断得到的结果,在采用“部分限制说”“相对限制说”时,由于没有明确标准,不能从形式层面确定何为可监听罪名,其具体适用存在障碍,适用效率低下,详细内容在上文分类标准部分已经进行详细叙述。
除此之外,关联性标准也符合比例原则及相关性原则。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狭义比例原则三部分。对于关联性标准来说,其一,通过关联性标准考察附带监资料对于犯罪侦查效果显著,有利于监听目标实现,符合适当性要求。其二,必要性原则要求监听非为必要情形,不得侵犯公民尊严,但应注意,该原则限制的是监听的发动,在本监听业已合法展开时,其附带监听不存在开启的适当性问题。其三,排除这种附带监听证据,会使侦查成本提高,甚至会严重阻碍案件的进展,而这种附带监听对本监听对象的侵害,却仅仅表现在有限地加深了对他的侵害程度,两种代价相比,前后两者并非不成比例,不会违反狭义比例原则。
相关性原则也为关联性标准提供依据。监听相关性原则主要是指监听的实施必须要与特定的人或特定的案件事实相关,不得对不相关的人和事进行监听。[7]对相同对象的附带监听,首先监听没有超出特定的人,符合与特定人相关。其次,与本监听有关联性的附带监听也与特定案件事实相关,也未超出与特定的案件事实相关。
由此可见,将关联性标准作为对同一对象附带监听资料取得证据能力的可能路径,在理论层面以及实践层面都有很多优势。
在对于附带监听与监听罪嫌之间进行关联性判断时,应当与刑法中的罪数作出区分。如警方接获线报得知甲意图在A日实施抢劫,于是警方以抢劫罪申请对甲进行监听,在监听过程中侦知其预谋另一起在B日抢劫,一般刑法理论会将前后两罪作为连续犯按一罪处理,但是这两次的抢劫没有特定关联性,不存在某种涵摄关系,此时附带监听到的B日抢劫事实不可作为证据使用,实体法中的罪数理论并非考量证据与监听罪嫌之间关联性的判断标准。
2.重罪标准
重罪标准是获得证据能力的例外标准,指无关联性的附带监听资料在涉及重罪时,该资料仍然有可能获得证据能力,有“败部复活”的可能性。
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情况下,超出监听罪名的重罪事实本来也属于可监听的罪行范畴,对附带的重罪事实的赋予证据能力符合监听重罪原则的要求。在附带监听得知事实涉及重罪情况下,因重罪对社会危害性大,且这种监听也未超出将监听适用于重罪的目的,对监听对象的人权侵害较小,赋予其证据能力可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若把这种附带监听资料贸然予以排除,不仅不利于打击日益猖獗的犯罪活动,而且也违背了侦查活动的基本规律,陷入机械和僵化的泥淖。[1]332
总之,对于同一对象的附带监听,应以关联性标准作为一般标准,重罪标准作为例外标准,经过关联性标准判断的监听资料方可作为证据使用;仅在监听到无关联性的重罪时,附带监听资料可以有限度以重罪标准为依据,通过权衡赋予其证据能力。
(二)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分析
对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相当于未经许可,擅自开启对他人的监听,相当于无故侵犯他人的权利,而对同一对象的监听而言,它只涉及对相同对象侵害程度是否可以加深的问题。两类监听相比,对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对当事人的侵害更大,其行为相当于“无证监听”。由此可见,两种附带监听资料处理有着明显不同。
1.一般原则
在一般情况下,对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不宜认定为具有证据能力。秘密监听的实施不仅对当事人内心深处的隐私和人格尊严造成较深程度的侵害,同时,由于被侵害的公民隐私和人权的范围无法具体化和确定化,其权利侵害的影响面也较广。[8]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间的价值选择方面,过分纵容不同对象附带监听资料步入法庭,会导致忽视基本人权的保护情况出现,有时甚至会架空规制监听的法律。因此,基于人权考量,一般不赋予其证据能力,但是这种资料可以作为侦查线索之用。
2.例外标准
对一般原则不应作绝对理解,侦查机关执法的目的在于依法惩戒违法违规人员,恢复被损害的公共法律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法律一方面赋予其相关权力,另一方面以各种形式保障该权力得以顺利实现。而对于侦查机关所获取的资料,赋予其证据能力无疑是对侦查机关执法权的充分肯定与保障。对于不同对象的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资料之证据能力而言,如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问的价值选择方面考虑,当附带监听事实涉及重罪时,对社会危害性大,虽附带监听对象属本监听监听对象以外他人,但若规定其所获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则有放纵犯罪之嫌,不利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
不同对象的附带监听资料,一般不应认定其具备证据能力;在涉及重罪情形时,应由法院根据个案情况,于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以重罪为标准进行权衡后作出判断,例外的认可其可具备证据能力。
五、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取得规则
上文论及附带监听资料证据能力的可能性及相关标准问题,但这种可能性并不意味着符合标准的附带监听资料就一定具有证据能力,其证据能力的取得仍要受到形式与实质层面的制约,要使附带监听资料真正获得证据能力,尚需从形式与实质方面对附带监听资料进行补正。
(一)形式补正方式——事后补正制度
附带监听是监听执行主体超越监听权限进行的,这种监听行为实质上违反了司法审查原则,为治愈这种形式瑕疵,我们可以建立事后补正制度。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获得附带监听资料后,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8条规定,由侦查机关依法向监听决定机关提出申请,监听决定主体对附带监听资料进行事后审查,决定是否颁发事后许可,若决定机关许可补发监听令状,表明监听决定机关事后认可这种行为,可部分弥补程序瑕疵,若不准许,决定机关可不予签发。这种事后补发的监听令状是附带监听资料进入法庭的许可证,只有得到程序补正的附带监听资料方可进入法庭调查程序,在嗣后的严格证明中获得证据能力。
(二)实质补正方式——证据调查程序
在通过事后补正机制治愈程序瑕疵后,这些附带监听资料还要依据《司法解释》第107条规定接受证据调查,就关联性问题以及重罪例外问题,进行质证与辩论。
《刑事诉讼法》第148条将监听令状的决定权交由侦查机关自身,所以,单纯的程序补正并不能使附带监听资料具备合法性,此时还应接受作为第三方的法庭的调查,通过严格证明的法则,对附带监听资料的瑕疵进行实质性治愈,进而最终使其具备证据能力。
这种治愈方式依据有二:其一,司法解释第94条中规定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制作取得有疑问的,且未经必要证明或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依据,通过反面解释的方法,可以认定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只有得到必要证明及合理解释,才有成为定案依据的可能。其二,通过体系解释的方法,类比非法物证、书证的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治愈规范,对于有瑕疵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可通过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方法获得治愈。具体质证程序可由以下几个方面展开①本文将附带监听资料的排除置于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进行讨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规定言词与实物证据的排除,笔者认为对实物证据排除的理解不应仅限于书证、物证的排除,而应将其扩大到整个非言词证据的排除,即排除规则亦应适用于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排除。:
1.辩方形成争点的责任
《司法解释》第96条规定,在排除非法证据时,辩方需要承担一种形成争点的责任,也就是说开启附带监听资料质证程序的主动权在辩方,同时,辩方的举证只需达到合理怀疑程度便可启动该程序②《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表明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辩方举证需要达到的证明标准为“合理怀疑”。。
2.一般质证规则
控辩双方可就《司法解释》第四章第七节“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的审查与认定”中提到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获得的过程、制作程序等问题进行质证,控方可以通过出示、宣读讯问笔录或者其他证据证明附带监听符合关联性标准或重罪标准,辩方就这些证据展开质证与辩论。
3.特殊质证规则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9条规定亦规定在特殊情况下,辩方可提请侦查人员到庭,对侦查人员进行质证,从而查明附带监听资料是否符合具备证据能力的标准。
[1]邓立军.非法监听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的比较法考察[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
[2]张华.附带监听资料之证据能力分析[J].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11,(4):122.
[3]梁世兴.监听与违法证据排除[C].中央警察大学法学论集,2002,(7):134.
[4]陈龙鑫.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比较研究[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0,(4):58.
[5]曾正一.侦查法制专题研究[M].台北:中央警察大学出版社,2006:300.
[6] 李明.监听制度研究——在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之间[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13.
[7]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保障:中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334.
[8]胡忠惠.秘密监听的事后救济问题解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9,(10):53.
责任编辑:黄晓玲
D925.2
A
2095-2031(2014)03-0096-05
2014-01-15
孔祥承(1989-),男,山东烟台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从事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