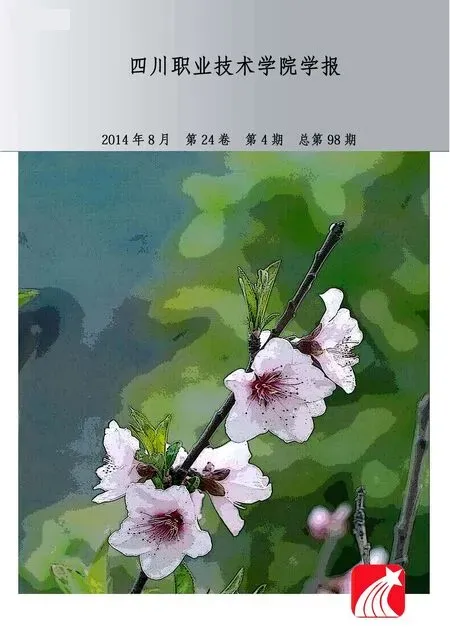比较法视野下探讨沉默权的中国本土化
2014-04-10陈剑武
陈剑武
(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4)
比较法视野下探讨沉默权的中国本土化
陈剑武
(上海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4)
“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早已不陌生,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情况十分常见,而且在司法领域打击刑讯逼供的收效并不明显。本文试图通过杜培武案的产生原由入手,反思冤案的“铸造”过程,以程序正义之名追问冤案的根因——刑讯逼供,以期通过探讨西方沉默权在中国的本土化,为走出刑讯逼供的困境寻求出路。
杜培武案件;刑讯逼供;沉默权;程序正义
云南戒毒所民警杜培武遭刑讯逼供一案从曾经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到逐渐平复,今日似乎已经淡出公众的视野,最终尘封进法律文本的沉思之中。回顾案件的始末,公安机关仅仅凭主观的推测就断定一个人“故意杀人”,并进行了残酷而野蛮的逼供;法院没有任何可靠实物证据,仅凭屈打成招的言词证据,竟然将犯罪嫌疑人判处死刑。原本一桩“铁案”已经尘埃落定,但只是因为真正的凶手被“意外”抓获,并供述了其杀人的犯罪事实,原来的“杀人犯”才被翻案,奇迹般地重获新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公民如何在一次司法系统性的枉法中跌进冤案的深渊之中,似乎还能听到他寄希望于程序正义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发出的呐喊和呻吟,却又只能在绝望的悲哀中等待奇迹。杜培武案可以说是一次司法腐败的“集大成”之作。
1 以“程序正义”的名义追问冤案的根因——刑讯逼供
这个冤案从它水落石出的那一刻起,就在社会舆论和司法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同时,这场瑕疵诉讼将中国的国情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真实而残酷的揭露了中国司法的黑暗一面。审视这场冤案发生和解决的始末,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场在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的必然出现的冤案。让人更为痛心的是,刑讯逼供的对象是一名对法律比较熟悉的民警,熟知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也知道在执法过程中应当履行的程序,但在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过程中,他对法律程序、正义的信任彻底粉碎,他企图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并试图采取一切可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手段,然而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因为他面对的是一群目无法纪的执法者,这才是这个冤案悲哀之处所在,也是该案最值得人们反思之处。试想,国家的司法工作人员尚且如此,在漠视法律的执法者面前,人权保障、程序正义、司法公正……这些人类追求的终极意义上的价值太过苍白无力。而我们作为普通的民众该如何面对司法的黑暗,该如何重新树立起对法律的敬仰感,法律又该如何以一种“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它的公平和正义。
每一种现象的发生总有它合理的因素存在,刑讯逼供在中国有其存在的深刻的社会根源。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的现象屡禁不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确实已成为一项久治未愈的痼疾。[1]再列举一些瑕疵诉讼:佘祥林案件、祁玉林案……我们可以从中清晰地看到,这是社会“体制化”酿造的苦酒,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法律不能承受之轻”。现行立法竟常常成为违法行为的“合法外衣”,甚至知法犯法也找到了法律的依托。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很多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的条款:《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刑法》第247条规定有刑讯逼供罪和暴力取证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有一些法规也对进行刑讯逼供、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规定了追究、处罚办法。但是,现有制度设计中除了大量的“严禁”的正面规定之外,尚缺乏与之配套的制约措施和程序设计,即在制度上还存在较大的缺陷和漏洞,这是不能有效遏制刑讯逼供之风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方面的原因。
此外,《刑事诉讼法》93条中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负有必须如实供述的义务,再加上口供在司法实践中仍然作为“证据之王”,刑讯逼供就具备了极强的“现实合理性”,它的滋生和蔓延似乎找到了法律依托。
2 程序正义的意义
我们可以从新闻传媒提供的关于杜培武案件事实的片断中,来思考程序合法化对于实现法的正义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办案民警仅凭一张“传唤证”就把他“留置讯问”而且一关就是10天的时候,他质疑办案者没有合法的法律手续,但得到的回答是:“想扣你就扣你,要什么法律手续!”
在看守所里,他请驻所检察官当着管教干部和众多在押犯的面为自己验伤、拍照,留下了刑讯逼供的铁证,但检察机关对此证据却故意隐瞒。庭审中,当杜培武提出这个有力的证据时,公诉人竟然说“没有找到”。更加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到了今年6月,检察院对两名主要刑讯逼供者提起公诉的时候,那份原来“没有找到”的证据又冒了出来,而且成了刑讯逼供的主要证据!
杜培武偷偷地把一件被逼供者打烂的衣服夹带到法庭上,并当众展示,但对这一刑讯逼供的重要证据,审判长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几次叫“被告人杜培武出示没有杀人的证据。”[2]
…………
似乎所有枉法行为都能以合法的形式来完成,都离不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执法人员对法律的漠视。[3]这些都不断地证明:为数不少的法律素质低下的侦查人员漠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应享有的法定权利,对其合法权益实施人为或制度上的损害,对保障其合法权益极为不利,更谈不上维护其人格尊严,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对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造成犯罪嫌疑人在诉讼活动中诉讼地位的不平等,是实质上的非程序正义,而且从本质上来讲,这恰恰是坚持了实质上的“有罪推定”,与《刑事诉讼法》第12条所确定的“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原则背道而驰。深追其背后隐藏的社会法治文化中缺失的品质,是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的民众长期漠视“人权”的集中体现。而我们不得不追问:当一个民族失爱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安慰自己有法律作为最后的堡垒来守卫正义,但是当我们连法律的尊严也丧失的时候,我们还将如何心安理得的生存下去。
审视中国的立法现状,交织着利益的冲突与平衡,不得不承认的是,真实存在并且不能回避的法律体制的缺陷、立法的疏漏以及社会法治文化的缺失,已成为中国社会法制化进程的巨大桎梏和障碍,这也为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盛行甚至久禁不止找到了“现实合理性”。
程序正义之路,任重道远。为此我们有时不得不付出血与泪的代价,可是,却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个案正义而牺牲整体法律的尊严和公正。纵观人类的法制史,西方为了追寻正义也经过了一番痛楚的思想的蜕变,在世界范围影响巨大的“辛普森案件”正证明了“程序正义”这个理念的来之不易和法的尊严的至高无上。我们如何保障和尊重人权,正是我们探索人类生存价值的真谛。这也是在尊重司法限度内的程序正义价值的复兴和重塑。而正视这场瑕疵诉讼中所体现的中国国情,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惨痛的教训,为司法改革提供些方向。
3 寻找刑讯逼供的出路——西方沉默权的中国本土化
西方的“米兰达法则”,可以为我们思考中国刑事侦查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和参考。根据这一规则,第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针对讯问保持沉默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第二,警察在开始讯问前必须告知其这一权利;第三,如果嫌疑人表示希望行使这一权利,讯问必须立即停止,直到其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或者其律师到场;第四,放弃保持沉默的权利的行为必须是在嫌疑人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第五,违反米兰达法则获得的证据必须予以排除。[4]这个规则也正体现了“沉默权”的核心要求。
而以此对比杜培武案件,侦查机关既没有积极主动履行告知义务,甚至杜培武连为自己辩护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确是在沉默中“认罪伏法”,倒真得是以彻底沉默的方式配合案件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规定,在运用证据进行定案时应遵循一系列原则: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忠于事实真相;疑案从无。而在摘录的上述案件事实中,我们却看到司法机关公然践踏着法律的尊严,以权压法,知法犯法,同时暴露出中国一部分司法工作者自身法律素养的匮乏和法制理念的缺失。这是刑讯逼供滋生和泛滥的土壤,同时在一个不合理的司法评价机制的作用下,不正之风必然愈演愈烈。我们可以从立法自身的缺陷反思司法腐败的现状,但更应当自省的是,立法正在不断趋于完善,但是为什么司法实践却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中国并不缺少完善、可行的立法,可是有多少执法者能真正做到依法办案?真正能实现程序正义?真正能抬起头无愧于头顶庄严的国徽?
从制度构建的角度去探讨刑讯逼供的出路,首先从立法上需要确立沉默权制度。
社会的法制化进程是建立在法制文化的基础上的,法制的进步又是在社会各种制度自身完善的过程中实现的。我们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刑法,修改宪法,但是在没有建立、完善与之相配合的合理、有效的辅助制度的情况下,人权的保障,救济的实现,制度的改革,社会的进步……这些宏大的立法理念只能是纸上谈兵,成为理想中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从文化的视角上看西方的沉默权制度,它的有效推行和演进是建立在西方发达的法治文化基础之上的,尽管沉默权有助于抑制刑讯逼供,但不等于照搬西方引进沉默权就能彻底根治中国刑讯逼供这个痼疾。我们应当看到和必须承认,现今的中国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文化背景的支撑和相关制度的配合,沉默权制度移植后的本土化实效能有多大,是更值得追问和深思的。这也正是沉默权制度本身的中国本土化模式面临的严峻考验。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立法和司法上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沉默权制度的思想内化于中国的法律体系中,通过完善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制度最大限度减少这种法律制度移植后的“水土不服”程度。
关于沉默权制度的中国本土化,学者对引进该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作了大量的讨论和研究。有学者分析,沉默权规则在中国的现实国情下是完全可以而且应当确立的: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必然会不利于惩治犯罪;二、现阶段我国的侦查技术虽然相较西方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但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关键并不在于侦查技术是否先进,而在于是否承认沉默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重要自然权利,在于是否能将无罪推定原则贯彻到底,在于是否对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予以充分尊重;三、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但是相反却规定其有如实供述的义务,这是司法实践中发生刑讯逼供等现象的根源。因此更需要确立沉默权以保障人权[5]。
第二、需要解决现行侦查讯问程序的结构性缺陷——口供中心主义下的强制取供。主要体现在:如实陈述义务强迫犯罪嫌疑人供述,诱发刑讯逼供;讯问过程全封闭,既缺乏全程连续录音、录像监控,也缺乏律师在场监督,无法防范刑讯逼供[6]。
4 尝试与反思--沉默权制度构建
为解决这样的结构性缺陷,从比较法的视野看,根据英国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尝试和反思:
4.1 警察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允许律师或未成年当事人的监护人在场[7]
“在场”,不是指一定在同一个房间,可以让律师或监护人通过监控的电视屏幕来看到讯问的情况。英国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证明:这确实是一种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方法。除非在犯罪现场抓获或着出现特出情况必须立即讯问以排除险情等,应当允许律师或未成年当事人的监护人在场,以监督警察可能出现的刑讯逼供行为。
对比中国的制度,这里涉及到在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问题,需要探讨在立法赋予侦查讯问时辩护律师在场权。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和申请取保候审。同时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而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着侦查机关对律师的介入和行使辩护权百般刁难,造成控辩双方从案件一开始就存在信息获取和对抗实力上的巨大悬殊,对于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极为不利,这无疑是背离了立法初衷和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
4.2 实行对嫌疑人讯问进行录音、录像制度
英国从1999年以后,进一步要求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像,其中一盘在讯问完毕后当即封存,另一盘随后提交法院作为证据。如果事后对录音、录像的内容提出异议时,可在法官的主持下打开封存的另一盘进行比对,以杜绝删剪或篡改供词内容等弊端。[8]据介绍,自从采用了这种办法后,警察获取的被告人供词在法庭上被采信的概率大大提高,警察在公众中的形象也大为改观。[9]英国警察切实感受到了这一改革措施的优越性,依法办案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英国在沉默权制度实行了多年后,又对其作了极大的限制,几近于取消。但他们设置和实行了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刑讯逼供的问题。[10]英国的这些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当然,从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的角度来说,尤其在全国司法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实国情下,全程录音、录像,并不是诉讼经济的方法。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不能排除公安机关为了方便工作从中作假,反而会使得刑讯逼供下“如实供述”的录像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的铁证,更加不利于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甚至连救济的最后希望都失去了。而面对这样的窘境,司法的公信力又从何来呢?而司法公信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在法治文化贫瘠的中国社会,法律没有获得它应得的尊重和信仰。
第三、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制度上将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从司法程序中排除,以最终实现保障人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学者热议的一项制度,学界对该制度本身的理念和精神是达成基本共识的,只是在排除的程度和范围上还有较大争议,这里不加深入探讨。从共识的角度,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应当一律加以排除。
5 结语
杜培武案只是众多瑕疵诉讼中的一个典型案例,但却集中地反映也明显的暴露出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不能回避和亟需解决的问题。刑讯逼供在中国虽然有一些存在的客观合理性基础,但是由于从其本身的危害上分析:严重损害了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有损国家的声誉;极易造成冤假错案;践踏了法律的尊严等等,必须从立法和司法完善一系列制度加以遏止和禁止。而沉默权制度的引进和适用则能从制度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法定权利,最终实现程序正义和人权保障的双重价值,使司法的公信力和法律的权威得以重塑和复兴。
[1][10]崔敏.关于沉默权与警察讯问权的考察与反思[J].公安大学学报,2001,(06).
[2]司饮山.侦查阶段律师特别权与刑讯逼供[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01).
[3][EB/OL]http://www.historykingdomcom/read-htm-tid-106268.html.
[4][5]易延友.沉默的自由[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6]万毅.程序正义的重心——底限争议视野下的侦查程序[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170—172.
[7]金一.论侦查讯问权与沉默权的冲突与整合——兼论完善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立法构想[J].法制与社会,2011,(26).
[8]王哲.对沉默权与警察讯问权的几点思考[J].新疆教育学院学报,2004,(03).
[9]崔敏.再论遏制刑讯逼供[J].公安学刊.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02).
On Chinese Loc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Sil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aw
CHEN Jianwu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XV Hui Shanghai 200234)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is not unfamiliar, the judicial practice of torture to extract confessions is very common in China, but the effect was not obvious. This paper takes Du Peiwu’s case as an example, reflects injustice“casting”process, in the name of the program justice questioning root causes of injustice - torture,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hinese loc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silence, find the way out of the dilemma for torture to extract confessions.
Du Peiwu’s Case; Extorting a Confession by Torture; Right to Silence; Program Justice
D925
A
1672-2094(2014)04-0026-04
责任编辑:邓荣华
2014-06-11
陈剑武(1989-),男,安徽泾县人,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律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事诉讼法,法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