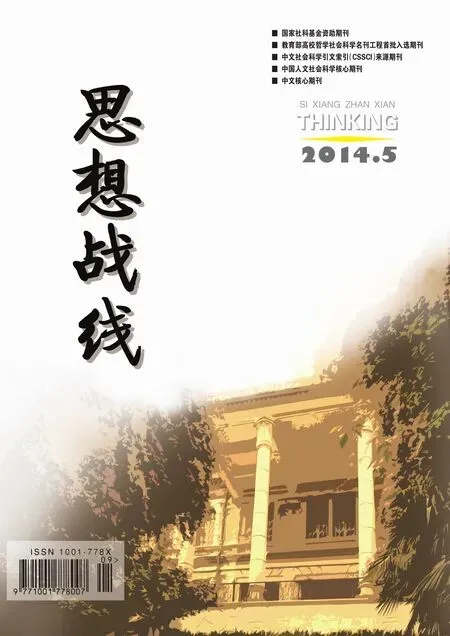清代云南水权的分配与管理探析
2014-04-09董雁伟
董雁伟
水权是指在水资源稀缺的条件下,人们对水资源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及让渡的权利。清代以来,随着云南地区人口的增加和农业开发的深入,农业灌溉用水的矛盾日益凸显。乾隆时期,云贵总督张允随就指出:“滇省山多坡大,田号雷鸣,形如梯磴,即在平原,亦鲜近水之区。”[注]《张允随奏稿》,乾隆二年闰九月十九日,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8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62页。在水资源日益稀缺的条件下,民间的水权观念逐步形成,水权的分配和管理成为农业生产和乡村社会管理中的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历史时期水权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山陕等北方地区,[注]研究历史时期水权问题的代表性成果有: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张俊峰:《前近代华北乡村社会水权的表达与实践——山西“滦池”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等等。参见张俊峰《二十年来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新进展》,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山西水利社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8~170页。对历史时期云南水权问题的研究尚较为薄弱。本文以水利碑刻、契约文书为主要资料,探析清代云南水权的分配、管理及其反映的乡村社会关系。
一、水权的分配
水资源的分配是水权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对天然水源、公共库塘等共有水源使用权的分配与协调。云南历史上,在用水分配方面多有“计亩分流”、“按亩分水”的记载,或以“排”、“份”、“号”、“昼夜”、“时晨”等为序,依次放水或用水平石、木刻分流放水。[注]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云南省水利水电厅编:《云南省志》卷38《水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5页。到清代,农业用水的分配制度已经较为普遍和完备。
首先,在滇池、洱海等主要流域,水源的分配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在滇池流域,松华坝以下的农业灌区都订有分水、放水之例。金汁河从松华坝至燕尾闸“放水次第分为五排”,“五排放水五日,四排放水四日,三排三日,二排二日,头排一日,半月一周,周而复始”。银汁河则从黑龙潭“开沟灌溉分为三排”。[注]黄士杰:《云南省城六河图说》,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2页、第17页。洱海流域自明代以来,已对十八溪军民用水分定水例。[注]《洪武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民分定水例碑文》,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1,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313页。清代十八溪的分水制度则更为周密和详备。如葶蓂溪,由于“其水不甚汹涌,田亩之资其灌溉者不少”,因此溪水多为两村轮用或两岸轮用。莫残溪支流品水,“每逢小满节起,四村按日分水,周而复始,习为常例”。南阳溪,“宝林村之中心有分水处,别为四支”,各支流流经田亩均依照“成规”或“旧规”分水灌溉。[注]《大理县志稿》卷1《山川》,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4年,第101~102页。
其次,清代云南修建的水利设施都订有分水制度。保山诸葛堰是清代滇西有名的水利设施,在用水分配上,采取班次轮放之法,“每值冬末春头,河水消缩。轮放纂泄余沥,其班次悉照开海水规”。[注]《轮放大海水规碑记》,载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41页。其他一般的小型水利设施也有分水制度。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宜良县议定文公河放水章程,“轮流分放,以免争执”。[注]《文公河岁修水规章程碑》,载周恩福主编《宜良碑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玉溪宣统年间修筑金汁沟,“沿沟区段凡三:曰上、中、下,放水以股计,以上昼夜为一股。冬春沟水,上段浸润豆麦外,悉数尽中、下两段轮流注蓄;立夏以后,及遇浑水,仍以习惯,上满下流,先上段放足,以第及于中、下两段”。[注]《重开金汁沟碑记》,载《玉溪地区水利志》,香港:黄河文化出版社,1992年,第299页。即使是村寨内部的小型坝塘,也有放水规定。乾隆年间,大理鹤庆沙登村打通水源,实行按沟分水,“每沟又分为七份,一沟上又碎分为一昼夜,自内而出外,以卯时替换水班,作七天一轮,周而复始”。[注]《沙登村水源章程古记序》,载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电力局编《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336页。道光十四年(1834年),楚雄紫溪镇重修龙箐水利,规定“立夏日起头,各照古规,周而复始,轮流灌放,不得以强凌弱,以长挟幼,错乱古规”。[注]《重修龙箐水利碑记》,载张方玉主编《楚雄历代碑刻》,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320页。
此外,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分水、放水制度,多采用木刻分水或竹筒放水。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施甸保场三沟订立放水“例规”,“以竹筒渡放”。[注]《保场三沟碑记》,载施甸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施甸碑铭录》(内部印行),2008年,第89页。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盈江县拉丙寨村民修建拉丙沟,按面积分配用水,分水口埋设竹木管道,入口孔径按“挡”、“名”、“芒”的大小固定,修沟和缴纳水费由水口分摊,并制定管理规约。[注]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云南省水利水电厅编:《云南省志》卷38《水利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5页。光绪十八年(1892年),祥云县东山恩多摩乍村彝族村民订立水约,“分为四牌。定昼夜为一牌,于每年立夏日起,轮流管照,周而复始”,各人户则按具体日期分水,“第一牌,用亥、卯、未日期,卖菜乍于姓照管于有文。第二牌,用申、子、辰日期,恩哼奔于姓照管于开成。第三牌,用巳、酉、丑日期,龙潭魁姓照管魁文富。第四牌,用寅、午、戌日期,分头上自姓照管魁占春”。[注]《东山彝族乡恩多摩乍村水利碑记》,载祥云县水利水电局编《祥云县水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
大体而言,清代云南地区的分水方式主要有两种,即时人总结的“秉公公放”和“照分数分放”。[注]《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第一种分放方式“秉公公放”,即“终年不立水牌,亦不分昼夜,作为常流水”。[注]《紫鱼村分水碑》,载李兆祥主编《嵩明县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公放之法多以上满下流为原则。如嵩明县所建积水闸塘,“议定芒种日开放,不得前后。一开水之日,顺序而开,上满下流。”[注]《古城屯建立积水闸塘碑记》,载李兆祥主编《嵩明县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该县紫鱼村等村放水也“总以上满下流为定规”,“历久无异”。[注]《紫鱼村分水碑》,载李兆祥主编《嵩明县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玉溪东营等村也规定,立夏之后放水须“上满下流”。[注]《禁止东营开取土石告示》,载玉溪市档案局(馆)编《玉溪碑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页。昆明滇池东岸大小二村,“每年立夏之后,系属两村栽插日期,两村水分仍照古规于石桥以上扎坝,惟止准用松枝筑坝,高以二尺五寸为准,俾其上满下流”。[注]《宏仁村水利诉讼碑》,碑存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宏仁村,2010年抄录。除此之外,还有的地方采取“自远而近”的公放原则。如弥渡永泉海塘即先放沟尾之水,再放沟头之水。[注]《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公放之法虽不轮水期,但能够有效防止“强者无水而有水,弱者有水而无水”,[注]《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实现无论强弱,各得其所,保证用水公平,防止水利纠纷。
第二种分水方式是“照分数分放”,即先核定用水水额、水期,再照分分放。分放之法与云南山区水源渺远、田亩分散的实际相结合,更有利于水资源分配的公平。如腾冲中和区实行“立砰分放”,“强不能多,弱不能少,数百年来并无紊乱”。[注]《四沟遵案碑》,载腾冲县水利电力局编《腾冲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8年,第217页。水分的计算,或以放水时间计,按照“昼夜”、“班”分水,或以尺寸计,以水平石、木刻分流放水。在分水过程中,水分的核定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依照田亩或粮额数,实行照田分水或计粮分水。照田分水,即按照田亩多寡分水。雍正时期,祥云禾甸五村实行照田分水,“有此一份田即有此一份灌溉之水”。[注]《禾甸五村龙泉水例碑序》,载祥云县水利水电局编《祥云县水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巍山洋溪海实行的也是“按户计田,均撬均车,或三轮五轮,周而复始”。[注]《□□洋溪海水例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217页。由照田分水又衍伸出另一种水分核定方式,即“计粮分水”。嘉庆年间,保山一带鉴于涝情,为保证税粮缴纳,行计粮分水之制,“一石一班,到班接水,以酉、卯二时为规”。[注]《论水碑记》,载隆阳区政协编《隆阳碑铭石刻》,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314页。宾川大禾头东山箐水,“定例壹拾肆班,照田粮之多寡,轮流灌溉”。[注]《宾川县水例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633页。赤龙溪,“水口设闸,有水利碑,按田粮之多寡分定时刻,挨轮放水。”[注]雍正《宾川州志》卷4《山川》,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方志篇》卷5,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30页。二是按照水利设施修建中出资、出工的多寡分水。在水权分配中,农户在水利设施修筑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与水权的取得是直接挂钩的。如咸丰六年(1856年)“安宁陈姓族人处理吐退归备荒地放水事宜合同”:[注]《安宁陈姓族人处理吐退归备荒地放水事宜合同》,载吴晓亮,许政芸主编《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8页。
安宁立合同文约人合族人等系和尚庄住人,为因吐退归备得本族陈美荒地壹块,坐落四至俱载明退书,不复重书故。当日言明,无论谁人,其塘未归备之先,原系己业之田地者,无论多寡,随到随放。一自归备之后,无论典当归备得之田地者,无有水分,若要一体同放水者,须照历来所费之资照日□□捐纳。
以上契约反映出,水权除与地权相联系外,还同水利工程的出资(工)相联系。类似的情况在云南其他地区也普遍存在。乾隆时期弥渡民众修建永泉海塘,“出银三两、米三斗,工一百,着水一分”,各户根据贡献程度得水半分至二分不等。[注]《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祥云县黄联署、明镜灯、白井庄等村民众扩建清水堰塘及润泽海,“以拾股修理,每股拼银一百两,每股每轮放水一昼夜”。[注]《清水堰塘润泽海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684页。这种分水方法将各户所出银米和出工额与所得水分相联系,有利于解决水利工程资金短少的问题和保障公平放水。除了以上两种方法之外,各地在分水过程中,还可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形,斟酌处理。例如,地势高下是影响农业用水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分水中也可作为重要依据。如康熙年间,禄丰县中屯、路溪等村发生水权纠纷,最后两村按照地势高低实行“三七分水”,“田近龙泉,而地势颇高”的村寨在十日之内放水七昼夜,而其他“田远龙泉,而地势稍卑”的村寨仅轮放三昼夜。[注]《路溪屯分水碑记》,康熙《禄丰县志》卷3《艺文》,载杨成彪主编《楚雄彝族自治州旧方志全书》,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页。此外,农作物也可作为分水的依据。大理鹤庆下桥村属两熟田,因此“开洞时议定,有两熟田者,故无水班,盖为水有缓急之别,秋田用水时,水期必急,自立夏起轮水班,灌两熟时,水期已缓,就可以上满下流”。[注]《沙登村水源章程古记序》,载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电力局编《大理白族自治州水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第336页。总之,注重公平性和责权对等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是明清云南水权分配的主要原则。
二、水权的交易
水权交易是水权人与用水户或用水户之间进行的水资源再分配。清代云南地区普遍存在个人或村寨之间的水权交易。清代以来,水资源稀缺性的凸显和灌溉用水价值的提高促进了水权与地权的相互剥离,同时也为水权的溢价转让提供了可能。[注]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因此,清代以来,水成为了一种可以转让的商品。民国初年,巍山县庙街所立的《南庄约学堂水碑记》记载水权买卖出现的过程称:[注]《南庄约学堂水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4,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717页。
有田有水,轮牌分溉,通例也,无所谓水租也。水有租者,惟中三约则然。南庄阱水,自古分为十牌,各立名目……有明朝古碑可证。当日按村摊分,想必无租。继因田多水少,而水乃有租矣。又因沟远者难放,而水有买卖矣。
此碑虽然立于民国七年(1918年),但反映的主要是清代以来的情况。碑刻反映出巍山县由于灌溉用水紧张出现了水权的转让和买卖。在用水过程中,当一方缺乏水源或水额不敷使用,就必须通过买卖的方式获得他人的水源,从而导致了水权的让渡和转移。
水权交易主要有水源交易和水分交易两种类型。
水源交易,主要是水源及其坐落地的买卖。在交易过程中,买卖双方明确买方在用水、开凿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标明水源的具体坐落、交易价格并立契为证。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红河三村乡村民买水源契约:[注]云南省红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红河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
卖 契
立卖水源地界立约人周者得、宗枝甫、李三隆,系猛里娘铺二村居住,为因打洞村人跟尾得娘铺水源二箐,打洞荒山无能开成田亩,二寨公同商议,情愿立约卖到打洞村。罗相文、杨运初、罗仲德名下实买,得价纹银肆佰两整,入手应用。自卖之后,任随打洞村众人开放随挖,并无威逼等情。日后别寨不得异言,倘有异言,二寨一力承当。此系二比情愿,恐后无凭,立此卖契文约为据。(下略)
乾隆十六年八月十二日 立卖水源契约人周者得、宗枝甫、李三隆。
在这一交易中,打洞村民罗相文等筹银四百两,向娘浦村伙头周者得买下水源使用及水沟开凿权,开沟引水至打洞村山坡。由于水资源具有稀缺性,而水源买卖又涉及土地权属问题,因此这样远距离购买水源并开沟引水的情况,一旦年深日久,必然引发水权纠纷。
水分交易是与分水制度相对应的一种水权转移形式,即由交易的一方购买另一方所分得的水额,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水源缺乏的情况下,交易的一方通过缴纳“水租”,获得与其他方分沾水利的权利。乾隆年间,蒙自小东山向布依透购买龙潭沟水,“东山薄出谷若干或银若干,向布衣透之人年买斯水,其银俱存公处,以作修沟之用,则水归有用,田不荒芜”。[注]《布衣透龙潭左山沟水碑记》,载唐 立主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京都: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111页。道光时期,禄劝县南村因灌溉需要而又“无掌鸠沟分”,与邻近四村议定分水,“将掌鸠沟水一道每年轮班之外,苗水任放,田水任车,余水永远流通南村”,南村按每亩四十千文的价格出资给四村,以资修理沟坝。双方合同规定:“南村仅放余水,永不致与者老革、旧县村紊乱水班,即或四村田水盈满流出,南村不得借事生端,四村亦不得阻扰决水下河。”[注]《掌鸠河合同碑记》,载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局编《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53~154页。宣统年间,牟定迤西冲水坝订立水规,其中言明“下村本无面分,府判由上村缴银百两与上村,以办上村公益,今后下村始有水分”。[注]《迤西冲坝水规》,载牟定县水电局编《牟定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7年,第113页。
水分交易的另一种情况是在水分不敷使用的情况下由交易的一方直接买断他人的水额,以增加自己的用水量。光绪十二年(1886年),腾冲龙王潭中沟坝水规中就有买卖水分的记录,现据《龙王塘中沟水碑》移录于下:[注]《光绪十二年中沟坝二十八村绅耆同议请示将古规放水轮流先后次序班数》,载保山市水利电力局编《保山市水利志》(内部印行),1993年,第163~164页。
小马官屯古水一班,买得瓦罐村丁水头水半班。
下村南排接连开放古水六班半。内有买得白延水头水一班;买得杨石匠水一班;买得征工水一班。
下村北排接连开放古水八班半。内有破土牲礼水一班;买得冯朝弼水头水一班;买得木连科水头水一班;买得丁□年水头水一班。
竹官屯杜买得上太平水半班。
小村子接连开放,买得冯乡绅水一班。
县公房水一班。跟水头走,不论前后,那处买着接那处放。
上吴姓一般(班)今杜卖与上村南排。
在这种水分买卖中,出价的一方并非购买水源,而是多买水分;导致水分买卖的原因不是缺乏水源,而是水分不足。这种水分的买卖行为在保山地区较为普遍,民国时期对诸葛堰的调查仍称:“但因需水或已足之关系,甲村可向乙村出钱买水灌田,每班水约值数元至数十元不等。此则均由水头经管其事。”[注]严德一:《永昌诸葛堰水利》,载方国瑜主编《保山县志稿》卷11《舆地二》,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61页。
水权交易根据产权分割的不同,也分化为绝卖、活卖、典等交易形式。与土地交易类似,绝卖是一次性卖断水权,不再回赎,如上引《龙王塘中沟水碑》中所称的“竹官屯杜买得上太平水半班”即是水权的绝卖。与绝卖相反,活卖则是水权在买卖和转移之后,原主还对所卖之水保留回赎的权利。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祥云县村民卖水契约”:[注]以下两份契约由杨韧先生收藏并提供,特致谢忱。
立卖水约人吴峰系吴家营住,为因缺用无处凑备,情愿有品甸王第三昼夜庙水六分之一壹分立契除卖与钱家营钱二兄弟世宰名下,实授水价银肆两入手应用。当日两相交明,并无货债准折,其有杂派、夫役、钱文不得遗累卖主。日后有银,照卖水日期赎取,无银任随耕放。不得到放水之期异言,自称原主有银赎原物。若有异言,得约理执。恐后无凭,立此卖水文约为据。
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十二日 立卖水文约人吴峰 仝男吴□□、吴自天、吴性天、吴畏天 亲笔
契约表明,吴家营村民吴峰将品甸王海的水分出卖,卖水方可以在规定的日期赎取。典则是水权所有者将约定期限内水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出让,期满之后,备价回赎的一种交易方式。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巍山县村民转典箐水契约:
立转典排水文约人左联九同侄凤朝、凤书、凤仪、凤廷因有祖遗左姓水全箐一昼夜,坐落响水河内,四十三日轮流分放。先年出典与本村管业,今备价赎回,凭中立约转典与中南庄下甲天醮功德管事杨汝香十三户人等名下管业,受水价银五十两整,入手应用。日后凡有水者,有银五十两执合同照契赎取,无银五十两不得零赎。其银当众兑交,并无准折情由。恐口无凭,立此转典水契文约存照。
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立转典排水文约人左联九 同侄凤朝、凤书、凤仪、凤廷
出典的标的物是“全箐一昼夜”之水。从契约中看出,出典人先将水权典予“本村”,到期备价赎回后又转典与杨汝香等十三户。水权交易中“活卖”、“绝卖”、“典”等交易形式的出现,表明了水资源在交易中已具有与土地同样的属性。同时,水权交易的灵活性、多样性以及对水资源不同层次的产权分割,有效促进了水权市场的形成。水权交易的普遍性和交易形式的多样性说明,水资源已经成为了一项单独的物权。
到清末民初,水权买卖在一些地方已经十分盛行。如大理巍山《下南庄赎水碑》记载:“原本村自古领有南庄大箐水一昼夜,其名即曰南庄水,每牌十二日一轮。本村之水,全箐又分为十二份。先年卖出者已多,而未卖者甚少。”[注]《下南庄赎水碑》,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4,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725页。与水权买卖的盛行相对应,水权混乱的情况更为明显,部分地区出现了“有水已典与他人,其本人仍继续分放者,有典得之水被人赎回,其典主仍朦混分放”[注]《清理郑营民水碑记》,载唐 立主编《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生态关连碑文集》,京都:日本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2008年,第103页。的情况。可见,水权的买卖对原有的灌溉秩序构成了挑战,成为导致水权混乱的一个原因。为维护用水秩序,官府和民间都对水权买卖行为加以禁止。祥云县规定:“水例原照田亩,有此一份田即有比一份灌溉之水。今有卖田而不卖水者,有买田而不得水放者,卖主则无田而卖水,买主则有田而无水,何以灌溉。如有此等,须卖主禀究。”[注]《禾甸五村龙泉水例碑序》,载祥云县水利水电局编《祥云县水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玉溪东营村民也规定,水源“俱照规矩,不准估霸买卖,设有买卖,上卖下罚、下买上罚”。[注]《禁止东营开取土石告示》,载玉溪市档案局(馆)编《玉溪碑刻》,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页。但是由于水资源的稀缺性,市场和经济手段必然成为民间水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水权的买卖在民间已经成为不易之势。
三、水权的管理
(一)以水长为核心的水权管理制度
水长,又称水头、沟头、坝长等,是各地对水权进行分配和管理,并对水利设施进行维护的专门人员。
清代云南各地均有水长的设立。乾隆时期,弥渡永泉海塘,“设坝长二人,放水一分。只得将各沟应通,令近者方开水口。凡寻(巡)沟、分水公平,不容恃强者截挖,如若徇情不公,连坝长恃强之人,一概公罚以修海垦。又递年至八月十六日收集海水,责在坝长,若推诿疏忽,更听赔罚,切勿怨言”。[注]《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呈贡县白龙潭,“捐资择立水长一人”,“以监愚民之雍阻”,还在分水处“设水长一人,巡查分放”,对淤塞水口、偷截水源的行为“赴官禀报,以凭严惩”。[注]光绪《呈贡县志》卷8《水利》,载林超民等编《西南稀见方志文献》第29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84页、第390页。腾冲县樊家营为保证水源分配,“设立石平,造具水册,立承头人,各余水一寸,着修沟看水,颁有告示”,承头人可多分水一寸。[注]《大沟水寸碑记》,载腾冲县电力水利局编《腾冲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8年,第215页。大理也设有与水长类似的“挖巡”,“每年到栽插之天,尊举三人挖巡,工价送定叁仟。自栽插一开,守水三人昼夜招呼,须上满以下流,自首以至于尾,勿得私意自蔽,不可纵欲偷安,要存大公无私之意,倘有护蔽,不论何人,见者报明,齐公加倍重罚。……倘有不遵,犯者,守水三人拿获,速还报明村中头人绅老,齐公重罚银两,究治不贷”。[注]《永卓水松牧养利序》,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3,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1643页。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安宁和尚庄设立水长,以下为“立水长文约”:[注]《安宁承揽水长文约陈兴承揽水沟石坝》,载吴晓亮,许政芸主编《云南省博物馆馆藏契约文书整理与汇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4页。
立承揽水长文约人陈兴系和尚庄住人,为因合村有水沟壹条、石坝一座,自揽到道光贰拾贰年到贰拾叁年止一年一焕(换)。起自独(读)书铺,到和尚庄止。自揽之后,有新塘聚水一座,小心照管,不得违误塘水。合村议定:每田工上捐谷肆合,按门户捐收。水长若至小满、芒种、夏至,小心应办,不得在家私自偷安,不得违误栽种。水浆自灰坝秋水、大沟秋水,小心照应,将灰坝秋水沟倒踏,不得播(扳)扭(扯)众人,壹嘅字内,不得违误。若有违误众人水浆,情愿将水长谷扣除伍斗入公。当众言明,水长田众人任贰拾工,水长典的罗村水长谷壹斗五升不得播(扳)扯众人。若有沟坝洞内之事用着银,伍两内水长借,五两上公家任借。此系二比情愿并非逼迫等情,恐后无凭立此承揽约存照。
道光贰拾贰年正月初十日 立承揽水长文约人陈兴
总的来看,水长由村内人户轮充,并有“水长谷”、“水头水”等作为其任内的报酬和补助。水长的主要职责是水源的蓄放、看守和水利设施的管护,水长在其职责范围内具有禀官和科罚的权力。
水册是水长据以对水资源和用水人户进行管理的文簿。水册中记载用水各方的土地面积、受水份额、受水时刻、灌溉面积等内容,水册由水长保管。明代云南已有水册制之推行,到清代,水册已成为水利管理的主要依据。如祥云禾甸五村龙泉“公计田亩多寡之数,分析用水多寡之份”,设立“宝花水册”,水册内“开载姓名,各注水份于下”,又请当地官员“铃印,并取一言,刻于册首”。[注]《禾甸五村龙泉水例碑序》,载祥云县水利水电局编《祥云县水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腾冲县樊家营大沟水“造具水册”,水册上记载有分水尺寸,由承头人照册管水。[注]《大沟水寸碑记》,载腾冲县电力水利局编《腾冲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8年,第215页。
与水册相配套的水利管理工具是水平,水平有木平、石平之分,广泛用于按尺寸分水的地区。保山诸葛堰“纂口前以木板作水平”,上刻分水尺寸。[注]《轮放大海水规碑记》,载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编《保山碑刻》,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41页。洱源县南涧,“村民于涧口甃石设立水平,石面凿成溜口,谓之水分,昼夜输流,按村落田亩分灌”。[注]光绪《浪穹县志略》卷4《水利》,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183页。嵩明县紫鱼村“于总沟中间挖深一尺,挑宽二尺,用大石一条横放其间,作为水平。又于石上凿出二水口如八字样,放水分流。东口凿宽四分五流入东沟,西口凿五分五流入西沟,各灌田禾”。[注]《紫鱼村分水碑》,载李兆祥主编《嵩明县文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161页。腾冲县樊家营设立石平分水,现存的清代水平石,长9米,顶厚18厘米,水平石上凿有水口11个,水口最窄者6厘米,最宽者130厘米。水平水口尺寸均依照水册,水平与水册相互配合,成为水利管理的主要工具。
(二)以水利规约为核心的水权管理法规
水利规约是水权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傅衣凌先生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控制体系分为‘公’和‘私’两个部分。”[注]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与此相对,清代云南在水权管理中也广泛存在着基层政权订立和颁布的官方规约以及村舍、宗族共同遵守的民间规约。
官方水利规约多见于官方主持修造的大型水利设施。雍正四年(1726年),云南县(今祥云县)正堂张汉督修禾甸五村龙泉并制定水例条款,对各村的放水时间、放水顺序、水权交割以及违制用水的处理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注]《禾甸五村龙泉水例碑序》,载祥云县水利水电局编《祥云县水利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318页。又如乾隆年间,昭通地区新修的闸坝也由官方制订有严格的水利规约。规约规定,每年用水之时各乡头人须赴县城稟请放水,经同意后,始执令旗命闸夫放水;平时只能放外闸之水,若遇旱年,水不够用,方可开内闸之水;不准农民为一己之私放水和闸夫徇私放水,如有违反,则重责不贷。规约被刻于木板之上,分发到各乡,各乡人民无不遵守。[注]昭通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昭通地区志》下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3页。
民间水利规约多由地方绅耆、水头等人主持议定,在水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发挥着习惯法的作用。从形式上看,民间规约有水规、合同、契约等形式。水规是村舍或宗族与用水者议订的共同规范。道光时期的牟定庄子村水规规定,“有越分放水,无论男人妇人,不着自己面分之水而横行乱放,皆理所不容;尤有未至挖水而遂截断水尾亦所不容”,违犯者“一经查出,定罚银十两入公”。[注]《庄子村水规记》,载牟定县水电局编《牟定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7年,第128页。宣统二年(1910年),牟定县上长冲与下长冲村民订立水坝规约4条,对水权分配、开闸日期、水沟界限情形和封坝日期作了详细规定。[注]《迤西冲坝水规》,载牟定县水电局编《牟定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7年,第113页。除了公开议订的水规之外,民众之间还通过私人的合同、契约等方式明确各方在用水中的义务和权利。如光绪时期金平马鹿塘水沟的“具立沟单人户合同”:[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二),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09页。
光绪二十七年苦竹林、马鹿塘、新寨、河头、保山寨众沟户议定开沟。坐落地为平河三家寨子脚大沟水一股,修□□□□□□,议定每个工三毫。偷水犯拿提花银一元,众议罚米一斗,猪肉十六斤,酒三十碗,盐一斤,又如倘有天番(翻)田崩,众沟户议定水口能可以下,倘有田不崩,不许可能上能下,拟各照前处罚。
赵进朝水半口,李德受水二口,
盘金恩水半口,李成保水一口,
李玉德水一口,朱一苗水半口,
陈木腮水二口,李折壹水半口。
(下略)
可见,民间水利规约不仅反映出民间法和习惯法在水权管理中的作用,而且大量水利契约、合同的出现说明,民间在水权管理和分配中出现了议约化的趋势。
水利规约的作用在于保障用水公平、预防水利纠纷。乾隆时期,弥渡永泉乡绅就指出,建立水规的意义在于“恐时势之迁移,人心之变态,强者无水而有水,弱者有水而无水,思患预防而为人心,惟其患以定规制”。[注]《永泉海塘碑记》,载杨世钰,赵寅松主编《大理丛书·金石篇》卷5,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697页。大理《阳南村水例碑》也指出:“天下有利必有争,水利关国赋民生,争尤莫免,故水利所在必定水例。例者,有规有条,利利息争之常道也。”[注]《阳南村水例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2013年抄录。无论官方规约还是民间规约,多被刻成石碑,供民众遵行。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牟定县庄子村将水规勒石成碑就是考虑到“创业不易,守成也难,恐防后来日久年远,惟不知先人之苦,根据失传,故水规细则垂碑,以志不朽云尔”。[注]《庄子村水规记》,载牟定县水电局编《牟定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7年,第112页。石碑具有难以移动、不可改易和可传之永久的特征,将水利规约刻成石碑,有利于体现水利规约的公开性和权威性,这显示了民间水权管理规约化和法律化进程的逐步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水利规约与官府法令存在一个逐渐融合的过程。民间制定的水规通常需要经过官府的酌定而具有更强的法律效力。如前引乾隆时期红河县三村乡村民购买水源的事例,买卖双方立约后,又于嘉庆七年(1802年)禀报元江直隶州署,获准颁发执照1份。[注]云南省红河县志编纂委员会:《红河县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4页。光绪三年(1877年),大理阳南村议定水例并拟定碑记底稿呈官府批饬,当地官员“查所拟水例碑记条款尚属妥协自应,准其勒石以资遵守,合行给示晓谕”,“自示之后务须各照公拟水例条款永远遵守,毋得紊乱争竞”。[注]《阳南村水例碑》,碑存大理市阳南北村,2013年抄录。宣统时期,牟定县上长冲与下长冲民众订立的水规也呈递县、府两级酌定,“县正堂刘批:此水规经本县酌定,上下村均依此规勿违。府正堂批:此水规经定远县酌定,上下两村均依遵守,准盖印,永远收执为据,此批。”[注]《迤西冲坝水规》,载牟定县水电局编《牟定县水利志》(内部印行),1987年,第113页。可见,民间水利规约经由官府批允、公示而成为具有官方效力的法规,这说明民间在水权管理中已经开始积极接纳官方力量的介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间力量与官府力量在水权管理方面的互动和融合。
四、结 语
清代以来,随着云南经济的发展和农业开发的深入,水资源供给不足和工程性缺水问题逐渐凸显,水资源逐渐成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水资源的稀缺性促进了民间水权分配、管理机制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民间水资源交易的兴起,致使水资源商品化,水资源逐步成为一项单独的物权。不难看出,在水权的分配管理中,清代云南与中原地区一样出现了现代“水权登记制度的雏形”,[注]王亚华:《水权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86页。而且在水权管理中出现了民间和官方都参与其中的“第三领域”。[注]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水权的分配和管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水资源稀缺的环境下清代云南乡村社会关系的互动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