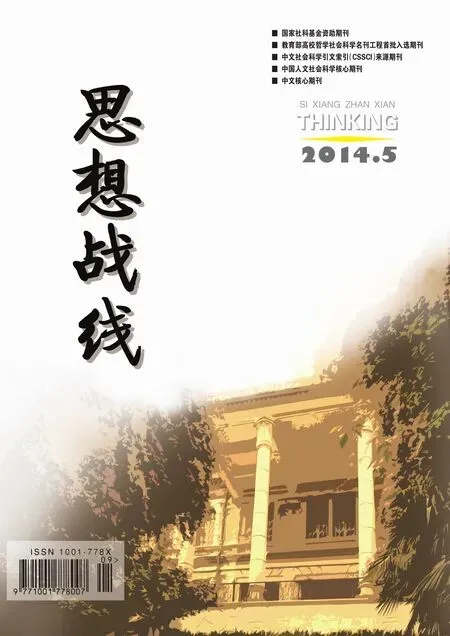文艺复兴与过渡(度)人权时代
2014-04-09徐艳东
徐艳东
在对“人权”概念的当下研析中,回溯“人权”发展的历史常常成为一种不可绕避的思索途径。这便涉及到“该将哪个历史时段确定为人权理念萌发点”这一基础性问题。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人权的发展从理念设计到制度构建分别经历了“发轫于17世纪初的自然权利时代”、“18世纪晚期的政治现实时代”以及“二战后的国际法制化时代”三个历史时期。[注]甘绍平:《人权伦理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2页。这即是说人权理念的真正设计开始于17世纪初。但这并不意味着17世纪之前的历史与人权理念的生成毫无关系。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末)恰恰是“人权胚胎”的正式孕育期。在该时期,因其现实条件的初步成熟,人权观念虽尚未经过人为讨论,但已经自我萌发。文艺复兴与现实人权理念的关系较为复杂,但从主要层面来看,文艺复兴是以一种积极与消极同时临在的方式正向与反向推动着人权理念的最终生成,是一种表面的消极限制,同时又在限制中解除限制,推动人类向着后续的人权时代自由前进。
一、“过渡人权”时代:一种积极意义的临入
文艺复兴的第一个历史特征恰在于向“人之权利”的初始转向。在此之前的中世纪,神权、神之位格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人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在神圣气氛的笼罩下,虔诚的信徒们如奴仆一样向上帝贡献着自身的一切,他们的头脑中只单纯装有“义务”这一词汇,因为在其观念与现实世界中,只有他们的“主”才有拥享“权利”的资格。在这种背景下,“人”这个指代词意味着“贪婪”、“感性”、“纵欲”、“罪恶”与“亟待拯救”。“人”与“权”这两个词素从不曾被链接在一起。即使偶尔被摆放在一起,修饰它们的谓词必然是“极其可耻”、“绝无可能”与“必入地狱”这些负性词语。在中世纪,人权是一个伪词素,当“人”与“权”连用时,类似于“圆的方”的悖念会同时存在于几乎所有人的头脑中。而“神”与“权”在人们的认识中却自动成为了一个基础词素,人们谈“神”的时候,即使没有说出“权”,也意味着已经想到了。自文艺复兴开始,在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强力呼吁下,“人”与“权”这两个词素才首次被“跨时代”地粘连在了一起,而且一经粘连,就绝不可能再出现哪怕是须臾的分离。文艺复兴人开始到处搜寻自己以及先人丢失已久的权利,尽一切可能丰盈自己的权力,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拼命汲取更多的权力。这是一个向着现代“人权”理念过渡的转折性时代。这一时期为以后真正“人权”时代的到来做出了丰厚的必要积淀。这种积淀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权”第一次从上帝那里抽离出来,并与“人”最终链接起来,“人的自由”、“人的尊严”、“人之利益”的合法性第一次获得了论证,并成为了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社会意识形态。“人”第一次以“伟大”和“富有力量”的姿态被人文主义思想家们集体颂扬。乔万尼·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年)毫不隐晦地认为,“人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奇迹”,在“神”那里“人”并非被动,“人”从一开始就被上帝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利,因为上帝在造人时,“他把人这种未定的造物置于世界之中但却不赋予他特定的位置,并使‘人’成为tipo indefinite(未经规定之物),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求和判断选择自己认为合适的位置、形貌以及禀赋”。[注]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De Hominis Dignitate, a cura di Bruno Cicognani, Le Monnier, Firenze, 1943, p.7.费奇诺(Ficino Marsilio,1433~1499年)认为:“(人的)灵魂是自然界中最伟大的奇迹,它是万事万物的中项,它把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它拥有全部的力量。”[注][美]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姚 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3页。伴随着这些对“人”的称颂,文艺复兴中的人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现实的方式展示出了作为人的骄傲情结。[注]详见拙文《“骄傲”与“隔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伦理视阈内的关键词解析》, 《哲学动态》2013年第7期。人终日思考的事情便是“权”与“利”,在“上帝”以及“他人”那里争抢属于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权利,“权”是“人”的专有物以及“人”是“权”的主人的观点普遍流布且被绝对贯彻。
文艺复兴对现代“人权”观念之发轫的另一重要意义还在于:人不仅将“权”从神的位格中夺回到人的群体中,而且“权”还被“个人”从群体一次性地夺回到自我的控制中。“权”不仅与“人”结合了起来,还与“具体的单个人”结合了起来。而我们今天所谈的人权必然是“主观人权”,也就是单个的人所应享有的权利。根据德国人权伦理学家罗曼(Georg Lohmann)的观点:“人权首先是个体的人的权利,这即是说‘主观权利’。”[注]转引自甘绍平《人权伦理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7页。尽管“人权”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宽泛,目前学术界在“人权”之具体含义这一问题上的争议极大,但有一点却是被普遍认可的,即“人权”是“具体的个体权利”,“人权是个体权利的观念恰恰是人权理念的根基性价值诉求……人权要求的核心目标是对单个个体的保护,可以说,只有将人权作为个体权利来理解,才触及到了启蒙了的文明的实质”。[注]甘绍平:《人权伦理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9页。总之,“主观权利”构成了现代“人权”的本质属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文艺复兴时期所形成的关于“单个个体理所当然地构成权利的载体的观念”为现时代人权观念的形成与演化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极其强调“个体”、“个性”与“个人权利”,虽然艺术家大都依赖顾主提供的钱财而生活,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却表现出了高度的自我坚持,他们不会为了金钱而屈从于顾主的意愿并以违背自己艺术趣味的方式去进行被动创作。大画家乔万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代表。人文主义者皮埃特罗·本博描绘他说:“他的快乐就是不对其风格施加任何明确限制,他喜欢作画时任意挥洒”;当画家皮埃罗·迪·科西莫与顾主发生矛盾时,顾主威胁说不付钱,艺术家则扬言要毁画。[注][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刘 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画家雅各布·彭托尔莫最令人恼怒的是:他只在自己高兴的时候为自己喜欢的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工作;作曲家乔斯坤也“总是在自己高兴而不是被要求的时候才谱曲”;根据文艺复兴时期传记家瓦萨里的叙述,大画家马萨乔总是“心不在焉,他甚少在意他人,无论何种情况他都不愿想一下世俗事物,甚至也不在意穿着”;[注][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刘 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90页。画家多纳泰罗为一位威尼斯商人制作胸像,当这位商人认为他要价过高而与他讨价还价时,多纳泰罗直接将胸像扔到地上摔得粉碎。[注][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与社会》,刘 君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93页。
通过对个体之人拥有权利的合法性的充分论证,人类的历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文艺复兴是向着现代人权临入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代。
二、“过度人权”时代与自然道德之缺失
在这里我们需要为“人权”打上必要性的引号,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权”概念尚未具有现代意义上“人权”的实质性。在上一部分,在谈到文艺复兴对“人权”理念演进的积极意义时,我们所强调的是文艺复兴将现代“人权”结构中的“主观权利”不自觉地纳入到其思考体系中,从而成为了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向现代人权的“过渡时代”。然而,人类历史不能逾越式地向前发展,文艺复兴只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时代,只是路上的一个关键驿站,它距离现代“人权”的最终归宿还相距甚远。导致这种距离的直接因素是:个体在论证了其拥有权力的合法性之后,不懂得在一定的范围内合理地获取并保守自己的权利,相反却无度地向外扩张,无限度地扩张自身的权利,从不曾考虑为自身之外的权利主体承担任何应尽的义务。每个人皆如此,经过一番相互厮夺之后,每个人曾经预想的过度化地拥有一些权利的意图最终却被实际占有权利的寡尽一一取代。个体甚至连现代意义上的最基础的消极“人权”(生命、自由、尊严、财产)都难以保有,最终,这种过度化的侵占造成过度化的失去。“伦理利己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鲜明愈烈地被频繁上演,每个人思考的都是自己的权利,拼命逃弃的皆是自己的义务,人们彼此间的不停伤害成为了惟一的结果。
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利最终使人失去现代意义上的最基础的人权。那么,我们不禁要思考,是什么具体因素导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不能真正进入到现代意义的人权殿堂中?我们认为,“自然道德”的缺失是导致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权理念没有真正成型的首因。
人权理念的实际接纳需要一种整体思维观念上的统一性,需要有一个或几个被普遍接受的“共有点”。因为“人权”涉及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实际的相互关系,不是单纯的自己与自己的抽象关系,因此,人权的最终落实需要达成一些“关乎如何交往的”基础性共识。这些共识的达成来源首先便是传统社会遗传而下的自然的道德情感。这是一些蕴藏于集体无意识之中的最深层的道德认同理念,它们为一个“时域”之中的人集体接受并竭力奉行。而文艺复兴时期缺少的首先恰恰是这种统一化的道德共识。文艺复兴是一个道德过度多元化的时代,人人都在秉持着与众不同的道德观念体系。当阿尔贝蒂严厉地谴责“谎言”,认为说谎“既丑恶又有害”(dannoso che brutto),并用厚颜无耻(infame)、遭人鄙弃(sdegnato)、卑鄙下流(vile)等形容词来描画说谎者时,[注]Leon Battista Alberti, De Familia, a cura di Emilio Piccolo, Claccici Italiani, Napoli, 2009, p.50.马基雅维利却认为时事所迫之计做一个伪装者(simulatore)和一个假好人(dissimulatore)是不应受到指责的。[注]Niccolò Machiavelli , Il Principe,a cura di Luigi Firpo,Torino,questa parte citata dal libro elettronico di Letteratura Italiana Einaudi,1961, p.65.布鲁诺也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他对于道德价值的相对主义的立场,在其伦理学作品《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Spaccio della bestia tiofante)中布鲁诺提出:“任何东西都不会是绝对的只有坏的特性……任何东西对于另一个来说可以是坏的,比如有德之诸神对于邪恶之人即是恶的,白昼与光明之神对于暗夜和混沌便是恶的。而在他们(指诸神,笔者注)之间,他们相互也是好的。”[注]Nuccio Ordine, La Cabala dell'asino. Asinità e conoscenza in Giordano Bruno, Liguori Editore, 1996. p.78.
这种道德过度多元化将文艺复兴人引入了一个“去道德的时代”,因为在原有的曾被人们认为牢不可破的神学大厦突然崩塌之后,一时惊愕的人们再也不能找到一种可以秉持终身的公共道德。“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是不对的”、“你认为是对的就是对的”、“对不对并不重要”,都成为了这一时期道德多元化的独特回应。我们不能谴责那时候的人们缺少道德感以及道德智慧,事实上,道德感以及道德智慧的实际生效必然是以社会上客观实存的道德观念为构成之源的。比如在中世纪的神学体系中,《圣经》的教义会明确告知其信徒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基督教中大量流传的信徒、圣徒和典型人物的事迹,成为了其信徒极易相仿的道德样板。基督徒的道德推理经常采用这样的形式:“如果耶稣处在你的位置,他会怎么做?”常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不必作复杂的道德推理的,因为那些生动的典型,为他们的思考和行动提供了快捷的参考方式。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神是他们所遵守的道德法则的惟一来源,他们的宗教教义完全覆盖了他们的道德义务。信仰让他们相信对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存在,他们的行为被置于这些绝对的标准的检测之下。[注]参见程 炼《伦理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页。但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以及天文物理生物学家的笔下,上帝却第一次被置于一种可怀疑的地位。对上帝的信仰是一个绝对的命题,这个绝对命题不能遭受丝毫的缺损性。和其他的事物不同,如果我们怀疑一个普通事物的某部分,并不妨碍我们认可除了这一部分之外的其他部分,比如我们否定一个人的做事能力,却并不一定影响我们对其道德人格的正向判断。但“上帝的全部王国”却是一经怀疑便全部倒塌的,怀疑上帝的最丝毫的点滴观念会瞬时让这个怀疑者的全部世界观、价值观以及实际作为方式发生彻底性的改变。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就面临这种状况,他们不知晓什么是符合道德的,因为道德的标准不再存在,他们失去了效仿的绝对样板,既然什么都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既然权利的观念在每个个体那里已经抬头,那么肆无忌惮地扩充自己的权利便成为了惟一的结果,这种结果导致了对合理人权之拥享的相互摧毁。
这种道德、价值的多元化直接促使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最终远离“人权”的殿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人权”理念不但不排斥多元,甚至支持多元,但却要求在这些多元中要具备某些统一性,或者叫做共识。积极性的“人权”因着不同人的理解而不同,但基本的消极性人权不能被剥夺,这已然成为一个基础性的共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在权利指向方面过度多元化的同时,却缺少一些基本共识,甚至对消极人权中最基本的生命权都不能形成保障性的共识,随意伤害生命成为了那个时代经常上演的悲剧。这种对人权的过度要求与人权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基础性”构成了矛盾。“人权所要保障和满足的是最基本的利益与需求,如不满足,就意味着死亡或者严重痛苦,要么触及到自主性的核心领域”。[注]甘绍平:《人权伦理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第7页。因此,人权是有着基础性的,人权的提炼过程不能出现过度化,否则便如文艺复兴时期一样,最终因过度化的人权追求而与真正的人权理念擦肩而过。
三、“过度人权时代”与人工道德之缺失
导致“人权”观念最终没有在文艺复兴时期生成的另一个原因在于那个时代缺少人工道德得以构建的成熟条件。事实上,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中,人权观念的生成和发展离不开一种人工道德的相应构建。人工道德是现代人权理念构建的基础性要素,而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因素。当社会历史从一种传统的自然存在方式进驻到陌生人相互共在的组群关系时,原有的熟人关系被打破,适用于旧时的自然道德不再生效,此时需要能动地构建起一种人工的普遍道德来维持陌生人之间猝然临在的新型互生关系。而人权观念恰恰是人们面对陌生人社会而自觉构建起来的一种人工道德,在这里,人工道德成为了人权理念最终建成的基质性要素。如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面临的突出问题便是自然或者半自然道德意识(包括古典道德以及中世纪的宗教道德)的全面瓦解,人们的道德观念呈现出了多维度的变质,西方在此刻正式从一个熟人社会转变成为彻底的陌生人社会。中世纪大部分欧洲人皆遵从同一神的圣谕,虽然生活于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但彼此却有着共同的追求,人们所做的一切都为了免受来世的惩罚,在神的护佑下升入天国,由此,虽然受到自然的交通条件的严格限制,不同区域的人们并不能如今天一样经常聚合在一起互相交流信息,互相联谊友情,人们一生只能在一个封闭的地域中结识有限的人,但这些陌生人之间由于共同的信仰彼此间又是那么熟悉,相互间传递着无声的交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世纪的欧洲比中国古代更具有熟人社会的真正实质。但历史走到了文艺复兴,一个完全的陌生人社会却在欧洲猝然建立起来。信仰、价值追求、道德认知、生活方式、政治建构,一切都于顷刻间变得迥然有别。面对着身边本已熟悉的人,人们却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陌生,人际间普遍隔了一层浓厚的迷雾。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人们不再如中世纪一样依附于一两个封建地主而带着子孙终生生活于原地,经常性地流浪于城市间以及变换工作骤然成为了他们新的主要生活方式。知识分子们亦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中世纪隐修的生活方式,意识到“自己不再属于自己”,[注]Eugenio Garin, Il Rinascimento italiano, Cappelli editore, Firenze, 1980, p.219.而是属于人群。他们开始投身于他们本不十分熟悉的政治领域,学着商人一样与各种陌生人打起交道。此刻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已经从熟人社会转型为一个彻底的陌生人社会。
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既然传统的自然道德已经瓦解,如果能有效地适时建立一种人工道德,用一种公共的人工的方式新建一种有效道德,以及一系列与这种人工道德相一致的法律条文和政治观念,或许那个为我们所期望的人权时代至少可以早些临近,但事实上二者的间距却如此遥远。文艺复兴不可能产生出现代意义上的人权意识形态,因为那个时代尚不具备一种构建现代人工道德的必要条件,人们不可能就一些本该属于人的消极权利达成某些共识,虽然这些消极权利已经受到了千年之久的践踏。其原因如下:
首先,构成现代人权基础的人工道德的形成需要人们对历史教训有着真正的洞彻的反思。人工道德的自觉构建动力来自于一种被惨痛伤害的历史事实,来自于一种惨痛的因基本人权受到毁灭性的践踏而引发的理性反思。只有受伤了,受伤者自己以及他们的后裔才有可能思忖如何避免新的伤口。对此可能有人提出说,文艺复兴之前的历史,包括古代频繁的城邦兼并和中世纪高密度的宗教讨伐(如历时极久的十字军东征)以及惨痛的宗教迫害(大批次的人死于耶稣信徒的火炬下)不仅不能说那段历史缺少伤痛,反而应该说两千多年来西欧的人们已经流干了伤口的血。既然可被反思的史实与伤痛如此厚密,为什么没有引起人们的觉醒?事实上我们要说明的是,虽然此前的欧洲人对来自自己的同类的伤害已经领受频繁,但他们并没有对历史之伤做出真正的符合实质性的反思,没有对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做出真正的思考。首先他们对来自战争伤害的反思甚少,或者说这种反思没有被放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这一层面来思考。在文艺复兴之前,不论是西欧古代还是中世纪时期,其冲突的类型往往是整体性的,个体性的冲突未被置于显著的地位。古代战争主要以地区或者民族间的互相侵吞和征服为主要特色,一个民族或种族以一种整体的规模与另一个民族或者集团发生冲突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模式。几乎所有冲突的主动方都打着“正义”和“解放”的旗帜,被动方都高呼着“保卫家园”的正义口号。于此,任何冲突都被冠以“正义”的名义,“正义”只要一经某个领导者的口中喊出,便成为了一个不经检测与反思而立即获得合法性的拥有巨大煽动性的口号。仅仅是这个口号便可以诱使几乎所有的民众出生入死,他们很少思考自己的领导者的口号与事实之间是否应被推敲一番。中世纪的情况较之古代尤甚。甚至连出自领导者之口的“正义”的口号都不再需要,只要“圣战”的领导者轻言一句“去歼灭哪个异教民族或惩罚哪个异端”,所有的信徒便会立即响应,因为他们总是相信宗教首领的命令与“正义”是同一个词汇,宗教首领就是神的化身。他们的信奉逻辑是:因为是神发动了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就是正义的。他们的思维却不能以一种反向的方式运作,转而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因此神才会去发动。
由此,个体极少怀疑过由自己参加的整体性战争的合理性,总是不假思索地认为将自己卷入其中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双方变成了丧失个体性的两个符号,参战的个人在伤害对方的个体时,即使再血腥再残酷,也会认为这种屠杀方式是合理的,是应该如此的,甚至越残忍就越是在伸张正义。他不认为自己是在伤害一个有血有肉的甚至是在真正维护正义的一个人,而是一个他所认为的非正义的符号。同样,当一个人被对方战队里的某个人伤害后,被伤害方的头脑里生成的是一种不假反思的类似于悲剧的崇高感,仿佛正义受到了伤害,但正义的力量却在同伴以及后人的解读中萌生出巨大的力量,鼓舞自己的正义群体投入到一场场新的不经反思便获得正义性的战斗中。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受到了伤害,自己却未感觉到受了伤害,因为崇高的道德感完胜了伤害。在这种群体冲突的模式中,只要杀害和攻击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方式,不需要保持合理的距离以便生成一种拒伤害于其外的更优化模式。这种互相伤害所依赖的核心因素是“力量”,而不是“智慧”,是“进攻”,而不是“斡旋”,这一点倒是和中国古代社会所强调的个人社交智慧有着很大的区别。
此外,普遍化人工道德(人权观念)的建立需要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国际经验,是国际化伤痛的反思结果。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战争使得人类的大部分卷入其中,伤亡惨痛。两次大战的覆盖之广、伤害之重,要求人类集体做出一个反思。人权涉及的是人的全体性,涉及的是属性的人,因此现代人权观的最终建立需要人类大部分的共识。我们不能用这些要求那个时期的意大利,虽然在那个时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国家区域间的贸易交流的展开,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较之之前的历史已经相对频繁,但相对来说仍旧非常封闭,欧洲与其他洲陆的交流更是少之又少,更没用领受过世界性的共同伤害,加之国际间对话机制远远没有建成,这些必然造成那个时代距离现代人权的寓所还相距甚远。
四、结 语
文艺复兴对在现代人权理念的构建过程既具有积极的推进之功,又具有消极的迟滞作用。在考察文艺复兴与人权理念的构成关系上,我们只能将这段历史定性为“过渡(度)人权时期”,并以此来表达其积极与消极意义。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宏观的人权历史构成来讲,这种消极并非意味着阻碍,相反,消极中寓住着积极的推力。[注]在《权力意志》一书中,尼采高度赞扬了文艺复兴式的德性,并将其称为“非伪善的德性”,因为它体现了真正德性的本质:“德性就是要做所有通常受禁止之事,它是所有群盲立法范围内的真正vetitum(被禁止之物)。”他认为“我们以三个多世纪的所有紧张努力,还没有重新达到文艺复兴时期人类的水平”,并号召人们要“敢于为达到文艺复兴的风俗本身而努力”,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有多善就有多恶,他们把“此在的对立特征最强烈地表现了出来”,而这恰是德性在人身上真正的体现形式,恶最大限度地提升着善,恶推动着善的前进。参见[德]尼采《权力意志》上卷,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595页、第597页、第591页、第596页。从该意义上讲,文艺复兴时期“人权”行使的“过度”化恰恰反向造就了其向人权理念的正式“过渡”。人权的“过渡”带来了其“过度”,人权的“过度”又推进了其“过渡”。正是在对文艺复兴及之前的消极历史教训的不断反思的基础上,后世的现代“人权”观念才逐渐生成直至趋向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