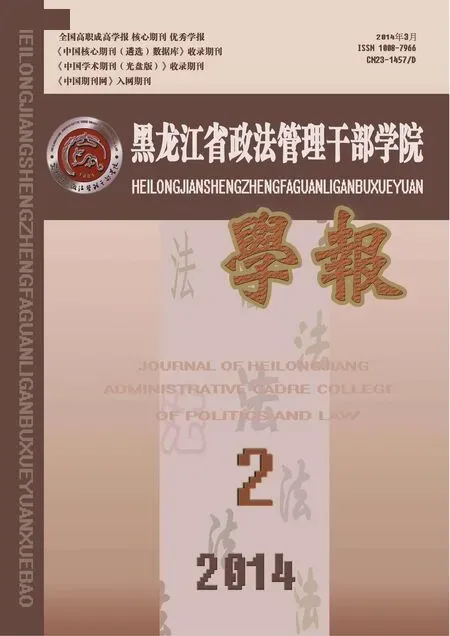公民合理权利期待视角下的搜查权力界限研究
2014-04-08张科军
张科军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公民合理权利期待视角下的搜查权力界限研究
张科军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100038)
在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侦查制度的改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是对于搜查制度的修改却远远没有达到实践中所需要的程度。搜查是侦查人员依法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罪证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搜查活动直接关系到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公民的合理权利期待面对国家强制下的搜查权力必然是脆弱的,应当给予更多关注。从另一方面讲,搜查制度的完善也关系到侦查机关追溯犯罪的能力,进而影响到刑事诉讼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
权利期待;搜查;令状
一、搜查权力概述
在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一项侦查行为是否构成搜查,不是看该行为是否对人身、物品、场所有所干预,而是取决于是否对公民“隐私的合理期待”构成侵犯,监听、电子跟踪等侦查手段都被包含于内,是为广义的搜查。在我国刑事诉讼中,搜查是指侦查人员依法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可能隐藏罪犯或者罪证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寻、检查的一种侦查行为[1]。对于如信息化侦查手段等措施则被当作其他强制处分措施另行制定规范进行规制,是为狭义的搜查。
此外,各国对于搜查的目的大体一致,即侦查犯罪、发现证据和违禁品。但对搜查的性质以及可搜查的范围却不尽相同。搜查在西方国家被看作对物的强制处分行为,与对人的强制处分行为一并构成强制处分制度。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则将搜查规定于侦查一章中,被定性为侦查行为。
无论是搜查含义的狭义化,还是搜查行为的侦查性规定,更多的是考虑侦查活动的需要,以追溯犯罪为本,必然会导致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弱化。这就不难理解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随意搜查、“地毯式”搜查、夜间突袭搜查、“另案搜查”、不通知见证人在场等搜查行为了。
二、搜查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的合理期待
搜查对于查明案件事实的重要性也决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对于被搜查人来讲,搜查带有国家强制性,甚至带有某种程度上毫无征兆的突发性。这就意味着,即便是合法的搜查也涉及对公民权利的干预或侵犯,尤其是对隐私权与财产权的侵犯。但是,搜查不会对公民没有合理期待的权利构成侵害,将财物从一个不认为自己对其享有权利的人处拿走,很难认为对其造成了权利侵害。而公民对一项权利是否构成合理期待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判断:
1.公民必须为保护自己的隐私及财产利益采取一定的积极措施。即公民对自己权利的期待属于表现于外的,对于已经抛弃的财产,个人将不再享有所有权、隐私权或其他权益。比如警察在公共汽车上发现一个装有违禁品的提包,当警察询问谁是提包的主人时无人承认,那么该提包的主人就构成对提包隐私利益的放弃。
2.个人对于开放区域不具有隐私的合理期待。即如果搜查人员通过搜查获得的信息,其他社会成员不通过搜查也可以获取。事实上,该种搜查行为不属于搜查。如,警察对摆在路边等人收集的垃圾进行搜查,就不构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因为,此种信息的获得其他社会成员也可以取得。
3.公民对被搜查的物品或场所享有的权利是合法的。比如,种植大麻的地点很隐蔽,而且他采取了在土地周边围上围墙,并贴上禁止入内标识等“权利”保护的积极措施,但是他对种植大麻不具有合法的隐私权和财产权等权益期待,对其搜查就不构成权利侵犯。即此种情形下,即便公民具有主观的隐私期待,但由于客观上该种期待不具有公众可接受的合法性,也不属于合理的权利期待。
三、搜查权力的内部规制
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合理期待不受任意侵犯,就应当对搜查权力加以必要限制。对搜查权力的规制一般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对搜查的启动条件进行限制;二是对搜查程序的规定;三是对搜查的效果的法律认可。由于学界就搜查的外部规制研究较多,在此,笔者仅就搜查的内部规制展开论证。
(一)搜查的启动条件限制
英美法系国家通常不区分对犯罪嫌疑人和对第三人的搜查。有效的令状可以搜查任何财产,而不论该财产是否由第三人占有[2]。美国通过1791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确立“合理理由”标准①Probable cause,有人译作“相当理由”、“可能根据”、“可成立的理由”等。,若无“合理理由”,人民有权保护其人身、住宅、文件、财产等不受搜查。何为“合理理由”,应依据具体的案件事实来评估其合理程度[3]。美国学者一般认为,合理理由并不要求百分之百的精确,而是比50%的精确率略少一点②Joshua Dressler,Understanding Criminal Procedure,Matthew Bender,1997,p.140M c.Cauliff的“Burdens of pro of:Degrees of Belief,Quanta of Evidence,Or Constitutional Guarantees?”一文中也指出一项对166名美国联邦法官的实证研究表明,法官对合理理由的心证程度平均值为45.78%。。英国在《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1条和执行守则A中规定,根据不同的制定法依据,搜查的证据标准为“怀疑的合理根据”与“合理相信”。
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将对犯罪嫌疑人和对第三人的搜查进行了区分,对第三人的搜查通常需要更高的证明标准。如在德国,对第三人的搜查只有在依据事实可以推测寻找的人员、线索或者物品就在应予搜查的房间里时,才准许进行搜查③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02条,第103条。。在日本“只有足以证明存在应予扣押的物品时”,才允许对犯罪嫌疑人以外的第三人进行搜查。从保护第三者隐私等人权考虑,这种对犯罪嫌疑人以外第三人的搜查只限于存在证据的盖然性较高的场合[4]。意大利也有明确的搜查启动条件:当确有理由认为某人身上藏有犯罪物证或者与犯罪有关的物品时,进行人身搜查;当确有理由认为上述物品处于某一特定地点或者某一特定地点可能逮捕被告人或逃犯时,进行场所搜查。
反观我国,侦查机关通常以立案作为启动搜查的唯一要件,之所以不以证据条件作为搜查的启动要件,主要是认为正是由于证据少,才采取搜查措施来查找证据。这样宽松的搜查条件给予侦查人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即只要侦查人员想要搜查,就能以“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为由实施,无须考虑是否具有搜查必要和事实根据。加之配套制度的缺失,任意搜查势必会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侵害。因而,仅以收集犯罪证据、查获犯罪嫌疑人或仅以立案为条件启动搜查着实太过宽泛,应当依据一定的事实、线索证明搜查的合理性。我国可以参考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明确搜查的启动标准,并对犯罪嫌疑人和第三人分别设置不同程度的搜查要件。
(二)有证搜查——令状的特定化
获取搜查证属于启动搜查的程序要件。搜查的实质要件,更大程度上是侦查机关自己的内心确信,而这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限制。西方法治国家多通过司法审查机制进行诉讼化的监督。我国并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令状制度,因为令状制度的实质是司法审查制,搜查证的批准和签发主体应当是法官。虽然就目前来讲,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实施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于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机制仍然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因而仍具有研究的价值。
令状应对搜查的相关事项进行详细记载已是各国的普遍做法。详细的地点的注明可以对搜查的范围进行有效的限定,但详细的程度合理即可,并不需要达到技术上的精确[5]。《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对搜查证应记载的内容有了较为细致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对令状特定化的要求源于国家不得在必要限度外干涉公民的私人领域的宪法原则④CaigM.Bradley,Crim inalProcedure:AW orldw ideStudy,Durham NC:CarolinaAcademicPress,2007,p.250.。如,在不超过10天的指定时间内执行令状,以及除非法官因合理理由明确授权外,搜查人员应在白天执行令状⑤参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法规则》第41条(e)(2)。。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也规定令状应当载明被搜查的场所,并且应当在可行的情况下标明要搜查的物品或人⑥参照《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 15条(6)(iv)、(b)。。《日本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令状应当记载应予搜查的场所、身体和物品,以及搜查的有效期间⑦参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19条。。
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法规对搜查证也有一些规定,如,除执行逮捕、拘留时遇有紧急情形,搜查应当获取搜查证⑧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二款。。但这些规定仍较为粗疏,没有对搜查证的内容进行规定。况且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自我审查、使用空白搜查证、搜查证内容的抽象化等做法已将本就为数不多的限制性规定束之高阁。没有了外部监督的权力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搜查令状的特定化尤为重要,特定化的令状可以限制搜查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并可以防止宽泛的、地毯式的,甚至对错误场所的搜查。我国可以借鉴西方法治国家的一些合理规定,对我国传统搜查证的内容进行改进,以对搜查权力进行合理限制。除在原有记载事项的基础上,还可以载明搜查的合理根据、执行搜查的执法人员的信息、搜查证的执行期限、执行搜查的时间以及被搜查的具体人、物品或地点等事项。
(三)无证搜查——同意搜查的借鉴
无证搜查主要包括同意搜查、紧急搜查、附带搜查等类型。与有证搜查相比,在无证搜查中,侦查人员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因此,为了防止侦查人员滥用权力,更需要加以细致规定。
我国无证搜查制度过于薄弱,不能满足实际需要。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二款的规定,无证搜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是在执行拘留、逮捕过程中;二是必须遇有紧急情况。我国的无证搜查制度似乎一并规定了紧急搜查与附带搜查两种制度,但必须同时具备处于紧急情形和附带于拘留、逮捕行为两个条件时,侦查机关方能采取无证搜查行为。因此,实践中侦查机关为了规避“在执行拘留逮捕过程中”的约束,并未利用无证搜查来代替有证搜查,而是以《调取证据通知书》的方式,不经过搜查而直接采取提取、扣押证据等非搜查措施达到取证目的[6]。为了有效缓解此种情形,除降低无证搜查的启动门槛外,还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同意搜查制度。
1.同意搜查的意思表示。只有在被搜查人自愿做出真实的同意搜查的意思表示后,搜查人员才能启动搜查。同意与否属于主观意志范畴,“但自愿性属于一个事实问题,需要综合全案情形作出判断”[7]。自愿与否存在一个基础性标准,即不能对其进行压迫和威胁。除此之外,被搜查人的年龄、智力情况、受教育程度,以及搜查人员是否告知拒绝搜查的权利(借鉴此制度的前提是赋予被搜查人员拒绝搜查的权利)、被搜查人员的自由状态等也都是同意搜查意思表示真实性的考察因素。
2.同意搜查的具体范围。由于同意搜查的启动是由被搜查人员的态度决定的,因而搜查的具体范围取决于被搜查人员具体同意的范围也应当是合理的。被搜查人员有权决定被搜查的空间、空间内的物品范围以及搜查方式。比如,如果警察被同意搜查汽车的后备箱,警察就无权搜查驾驶室[8]。但如果被搜查人员对搜查的范围仅作了概括的同意表示,就推定被搜查人同意被搜查该范围内的所有物品。比如,如果被搜查人员同意搜查其汽车,那么警察不仅可以搜查后备箱和驾驶室,甚至于车上传呼机的号码也可以检查[9]。
3.同意搜查的撤回。被搜查人同意搜查后可以对其同意的意思表示进行撤回,因为这仍然属于被搜查人的自由意志的范围。但是,一旦警察找到了相关犯罪证据,被搜查人才表示撤回同意的,不具有撤回之效力[10]。至于撤回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只要在找到相关证据之前,被搜查人既可以明确表示不允许侦查人员继续搜查,也可以在侦查人员进入搜查范围之前将其堵在门外。具体情况还应当根据情况具体分析。
我国在借鉴的过程中可以采取搜查过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并由被搜查人员亲笔在搜查笔录中对其是否自愿接受搜查进行声明(不会书写的由搜查人员载明,并由被搜查人员按指印)。此外,还应由在场的见证人对被搜查人员接受搜查的自愿性进行见证签名。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第三人的同意搜查,笔者认为,只有在被搜查人属于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时才能成立。
[1]陈光中,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96.
[2]Zurcherv.Stanford Daily,436U.S.547,554(1978).
[3]Illinoisv.Gates,462U.S.213,232(1983).
[4][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M].张凌,于秀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74.
[5]United States v.Pelayo -Landero,285 F.3d 491 (6th Cir.2002).
[6]左卫民,等.中国刑事诉讼运行机制实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7.
[7]Schnecklothv.Bustamonte412U.S.218,93S.Ct.2041(1973).
[8]United S tatesv.Rodriguez -Preciado,399F.3d 1118,1131(9thCir.2005).
[9]United Statesv.Reyes,922F.Supp.818(S.D.N.Y.1966).
[10]United Statesv.Jachimko,19F.3d296,299(7thCir.1994).
[责任编辑:王泽宇]
Research on the Boundary of Search Author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Civil Rights
ZHANGKe-jun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had been paid to the reform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ystem during the revision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However, the revision of the search system this time is far from the demands of juridical practice.On one hand, because of the fragility when faced with state power or search authority,which relates to citizens' constitutional rights directly,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of civil rights, require more attention.On the other h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arch system will also enhance the ability of investigation organs to trace crimes and affect the effects of criminal litigation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in turn.
expectations of civil rights;search;writ doctrine
DF73
A
1008-7966(2014)02-0095-03
2014-01-13
张科军(1989-),男,山东临沂人,2012级侦查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