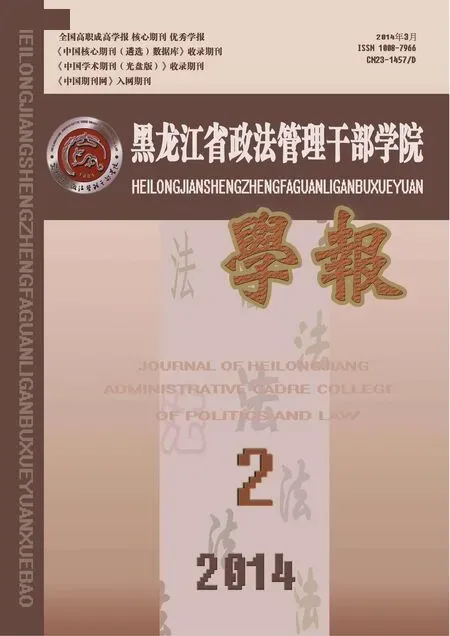物权法定原则起源探究
2014-04-08巩寿兵
巩寿兵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指导中心,西宁810008)
物权法定原则起源探究
巩寿兵
(青海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指导中心,西宁810008)
物权法定原则是近代物权法的原则,只有在近代社会历史情境中,才能寻得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意义。物权法定原则也是现代财产法体系的普遍特征,英美法系的法院在对待创设新财产权的态度也是十分谨慎和保守的。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正当性根据是复合的构成。法国起源说侧重于物权法定原则所因应的特定政治需要,而德国法起源说则更加重视物债二元财产权体系维持的逻辑上的自洽性。政治需要是我国仍然必须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一个重要理由。
物权法定原则;起源;政治需要;体系维持
物权法定原则向来被认为是传统大陆法系物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现在却一直处于饱受非议的状态。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就有物权法定原则的肯定、否认、缓和等多种观点的争论,即便是在物权法正式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后,就此的学术争论仍然时有发生。本文认为物权法定原则必然是为了因应某种特定的“社会情势”而产生的,对其进行研究就必须要考察其产生之时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其所回应的“问题”,才能获得比较妥当的结论。亦即物权法定原则的起源问题,是与理解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根据或者说价值、功能密切相关的,这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视角。
一、罗马法起源说
与民法其他制度一样,若考察物权法定原则的起源,言必称罗马。学者多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源于罗马法。“众所周知,物权法定主义源于罗马法的原则,在罗马法大全中承认具有物权属性的权利仅限定为: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役权、质权、占有以及非占有的抵押权。”[1]258孙宪忠先生亦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是罗马法时就已经设立的法律原则,虽然当时并没有形式意义上的物权,然而对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比如所有权、地役权、用益权等,法律均规定了明确的权利类型和取得方式。非以法定方式取得这些物权者,法律不予保护。”[2]但孙先生的意思似乎是在于强调物权的取得必须以“法定方式”,而非着重于物权种类之法定。按孙先生在此所参考的《法学总论》一书,笔者经详细查阅,该书第48页以下部分,即为该书第二卷,其中第一篇为“物的分类”,主要内容是规范物的所有权的取得问题,第二篇“无形体物”,第三、四、五篇分别规定了地役权、用益权和使用权与居住权。其中并没有对物权类型设限的语句,不知孙先生如何得出上述结论的。
但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物权法定主义所谓之“法定”,必然暗含着一个前提,即规定物权种类以及内容的法律渊源的统一性。否则,令出多门,各种法律渊源之间必多有冲突,物权法定也必然形同虚设。但在罗马法中,这一点并不具备。罗马法中有效的法律渊源各式各样,如法律、长官的谕令、皇帝的敕令、元老院的决议、享有公开解答权的法学家的解答等。如此复杂的法律体系如何能够保证物权法定主义封闭物权种类和内容的既定目标得到切实实施呢[3]?罗马法罗列的物权类型,只能说明当时社会通行的物权种类有这些,故法律予以明确指示,但并不代表法律即已经禁止了再生成新的物权种类和内容的可能性。列明现行通用的物权种类与限制生成新的物权种类和内容应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本文亦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源于罗马法的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尽管许多学者主张罗马法起源说,但是他们在具体论述时却均舍罗马法而言德、法。“要走出困境,需要全面认识物权法定主义。无疑,从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源头上,也即从德国确立物权法定主义的历史与当时整个社会背景中去分析将是有益的。18、19世纪,对德意志来说是一个观念论的体系化时代……那么物权法定主义则是体系化思维的产物。”[4]其次,许多学者都认为物权法定原则是反封建的产物,具有“整理旧物权,防止封建复辟”的功能。而这与罗马法又有何干?最后,后世学者所认为的罗马法中物权法定原则的“自由保护”和“简明化原则”的功能,则显然是将近现代物权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功能附会于过去的罗马法。罗马法中从未确立过正式的、通行的登记制度,何来“简明化”之有?
二、法国法起源说
《法国民法典》是否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法国学者间一直存在着分歧。“19世纪的判例和学说是一种承认契约自由原则与违反公序良俗的例外制约的通说图式,即当事者在不违背法律和公共秩序的前提下,依据契约可以自由创设第543条所列以外的物权。作为实质性的根据是来自于“法律和公共秩序”的权利。但它的目的在于阻止由于法国大革命而被废止的封建权利关系通过当事者的合意再次得到复活。但持反对说的学者把第543条理解为强行规定,是有关公序的法律,当事者不得变更。应该这样认为,这条法律在认可列举物权的同时也做出了限制。因此,该条则常被用来作为物权法定思想的证明。但否定的观点认为,仅根据该条就断定其实行物权法定,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该法律条文仅规定了五种物权即所有权、用益权、使用权和居住权以及地役权;但并未说明其所列范围是有限制的;其次,从事实上看,在《法国民法典》上,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规定地上权是一种物权,但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地上权是物权;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契约自由原则允许当事人设定法律不禁止的任何权利,特别是针对物的并对抗第三人的权利[5]111。
有美国学者也认为,大陆法的类型强制规则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时,当时,可分财产权与封建社会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必须对其进行严格规制和限制。此后,可能由于它适合法学者的学术研究口味,其作为抽象的规则从而有了极强的生命力[6]。尹田先生也认为:“物权法定原则在法国民法上的存在,应当是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否则,我们将有可能无法解释和理解物权法定原则所包含的那些关涉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而且重要的思想。……如予以历史的观察,物权法定原则是反封建的产物。较之于将近一百年以后的《德国民法典》及其他国家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才是整理旧物权和反封建历史重任的真正承担者。”[5]112但须注意的是法国的物权法定主义构造是非常柔软和富有弹性的。这尤其表现在共有形式的任意性和负担类型的任意创设可能性上(如役权),而这往往是造成误解的原因。
三、德国法起源说
如果说物权法定原则在法国民法上尚存有争议的话,那么,在德国民法上就是一种“常识”了。持德国法起源说的学者大都将物权法定原则看作是德意志民族特性和德国概念法学的“个性”的产物。“物权法定主义最先由德国学者提出,并在采用德国模式民法立法的国家中得到推行。然而,即使在德国,物权法定主义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学说和立法的发展过程。”[7]在物权法定主义出现之前,曾有过放任主义的物权立法。依1794年《普鲁士普通邦法》,虽请求物之交付之权利,因占有其物或登记其权利,变为于物之上(直接支配)之权利,有对世的效力。这种做法来源于日尔曼习惯法。在日尔曼习惯法中,事实支配的权利就是物权,占有的取得可以对应任何权利。依据这种规定,占有不动产并加以登记就有成为物权的可能,这样就不存在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的限定了。不过,物权放任主义的做法在《德国民法典》的起草中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物权和债权的严格区分。物权法定主义从物权与债权的对立以及物权法和债权法的独立性出发,作为契约自由反面解释的演绎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1]260。
有学者更从德意志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当时德国的社会背景考察了德国法确立物权法定原则的意义。“由于德意志缺乏民族的同一性和民族的精神,德意志的哲学就在普遍的、抽象的和纯理论的基础上探讨每一个问题。所以,18、19世纪对德意志来说是一个观念论与体系论的时代。这种思考方式,即观念论与体系性共同构成了德意志民族的内在本质性。物权法定主义正是从一个侧面回应了体系化运动。”[8]德国确立物权法定主义的社会背景是,1871年德国统一,但它远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它没有同质性,没有明确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它只不过是按照普鲁士的纪律捆在一起的一些地方政权的集合体。所以,刚统一的德国需要观念上的统一。这需要借助法律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包括财产关系。法律最重要最基本的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秩序静的安全。而且,当时社会市场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物权内容比较简单,可以把它们整理归纳而统一为几种物权,而这几种物权恰好是应当加以法定的。这样,“喜好体系化思考并需要借助法律来统一国民行为”的德国人就确立了物权法定原则[4]。
四、英美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问题
物权法定原则是否是现代所有财产法体系的普遍特征,还是仅为大陆法系物权法特有的理论?英美法系财产法上有无此项原则?对此学者间存在争议。否定者认为,“英美法系对此(物权法定原则)完全陌生”[9];“物权法上,英美法系和欧陆法的德国法最主要的区别是物权法定主义采纳与否,英美普通法采物权自由原则,欧陆法的德国法采物权法定主义。必须强调,有些学者声称美国法也采物权法定原则,则显然是不了解美国物权法”[10]。
肯定者则认为,“各个法系的法律都限定了一套众所周知的类型,使得人们仅能创设那些符合这些类型的财产权。财产法在这个方面不同于契约法,后者允许当事人自由的依其意欲的方式创设合同权利。长久以来,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对财产权的法律限制就一直有清晰的认识,但在普通法系国家,学术文献只是在最近才对这样的限制给予了关注,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才予以承认”[11]。“尽管在普通法法制度下物权法定原则背后缺乏逻辑的强制力,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即就财产权而言,在实践中普通法法院与民法法系的法院的做法是非常相像的:他们将先前被认可的财产权看作是一个封闭的清单,这一清单的修订只能由立法机关进行。这种现象并不能归因于立法机关明示或默示的命令。将其理解为司法自治使然是最好的。自法理学层面言之,物权法定原则在普通法中的作用更像一个法律解释规则(尽管这一规则是适用于普通法的判决制定过程中,而不是制定法或宪法解释中),或者像财产权解释中的一个强力的默认规则。”[12]
“财产权仅能在符合有限数量的标准类型时才能被创造,这一观念在普通法中处于非常奇特的地位。如果我们观察律师和法官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物权法定原则在财产权制度上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在财产权制度的核心——地产权益制度上,很少背离这一原则。重要的例外确实存在,如衡平地役权的创造和公开权,但是在数量上相对一直比较少,并且主要集中在财产法的边缘领域,如非占有权益和非核心知识产权。而且,从实务律师的角度来看,整个财产权制度呈现一幅可供选择而不允许偏离的、固定的清单。说服法院在特殊案件中创造新类型的财产权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然而,如果我们审视正式的原则和测验物权法定原则有效性的少数案件中的推理时,就会发现,这一原则似乎在普通法律师的意识中并没有太大的穿透力。也许关于物权法定原则在美国普通法中所处地位的最佳描述是,这仅仅是一个关于财产法运作的事实。这一事实是如此的浅显明白,如此的牢固,以至于很少被评论。正因为它很少被讨论,普通法律师在这一原则被挑战时,无话可说。”[12]
五、结论
通过以上的考察,笔者认为,首先,物权法定原则是近代物权法的一个原则。只有在近代社会历史情境中,才能寻得物权法定原则存在的意义。罗马法中是否存在物权法定原则是可疑的,即使存在,其与近代的物权法定原则是否具有共同的功能和价值理念,也是值得怀疑的。其次,物权法定原则是现代所有财产法体系的普遍特征,而不独为大陆法系物权法所独有。英美法系的法院在对待创设、变更财产权问题的态度也是十分谨慎和保守的。最后,通过考察大陆法系物权法定原则的起源时的具体社会情境,得出了两项物权法定原则的解释根据。法国起源说的解释多与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需要有关,更加侧重于物权法定原则的“反封建”功能,即以法律的形式废除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封建物权,尤其是土地物权,而代之以蕴含着平等、自由精神的新的物权。也就是说以法律的形式确认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德国起源说的解释则更侧重于物权与债权的财产权区分体系,并与国家主义的法律观,概念法学形式主义的方法论等背景有关。这说明同一法律原则在不同的法律环境下,以及同一法律环境下不同的历史阶段,都会为各种不同的理念、方法论所填充、所支撑,呈现出各具特色的解释根据。就我国物权法而言,基于公有制的土地制度,土地物权体系尚处于成长期,远不成熟和完善。二元制的土地制度设计决定了物权法的生存保障和促进交易的二元价值取向,并由此造成了我国新的土地物权的生成过程远非是“自生自发的秩序”的结果,而更是一个涉及政治安排的宪法秩序的问题。这从目前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小产权房等的热烈讨论可略见一斑。所以,政治需要是我国仍然要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重要原因。
[1]段匡.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法中的物权法定主义[C]//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七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80.
[3][意]阿尔多·贝杜奇.地上权:从罗马法到意大利民法典[C]//杨振山.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与债权之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240.
[4]梁上上.物权法定主义:自由与强制之间[J].法学研究,2003,(3).
[5]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6]Ben W.F.Depoorter&Francesco Parisi.Fragmentation of Property Rights:A Fun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of Servitudes[J].Global Jurist Frontiers,2003,(1).
[7]杨玉熹.论物权法定主义[J].比较法研究,2002,(1).
[8]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65.
[9]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经济理性[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16.
[10]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63.
[11]Henry Hansman&Reinier Kraakman.Property,Contract,and Verification:The Numerus Problem and the Divisibility ofRights[J].Journalof LegalStudies,2002,(6).
[12]ThomasW.Merrill&Henry E.Smith.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The NumerusClausus Principle[J].The Yale Law Journal,2000,(10).
[责任编辑:刘 庆]
On the Origin of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GONG Shou-bing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as a common feature of modern property law, derives its originfrom the modern civil law system, and its value is found only from the modern circumstances. The legitimacy of it is complex. One side, the theory of France civil law set up it for the demand of political revolutions; the other hand, the German civil law adopt it for the needs of distinguishing and system maintaining between the real rights and obligatory rights.
Numerus Clausus;Origin;Demand of political;System maintaining
DF521
A
1008-7966(2014)02-0065-03
2013-11-10
巩寿兵(1979-),男,河北南宫人,法学硕士,讲师,从事民商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