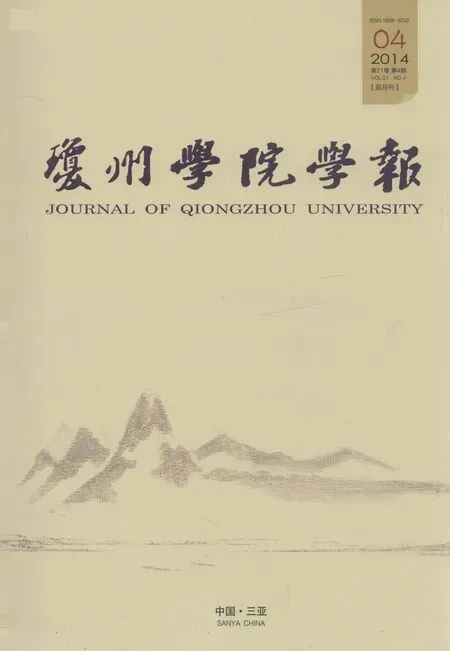诗意旅人心理紊流中的求稳祈向——姜夔诗词中的“归”“老”释读
2014-04-07侯海荣
侯海荣,向 欣
(1.吉林师范大学 博达学院,吉林 四平136000;2.吉林省教育科学院,长春130022)
一个人最大的动荡莫过于心绪的动荡。“江湖并非定居之所,而是‘奔走’之地,钱谦益所说的‘干谒之风’‘奔走阃台郡县’‘要求楮币’云云,都可归之于一个事实:江湖之士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生存状态和环境,都具有不稳定性”。[1]以此为镜,江湖旅人姜夔的心湖中盛满了诸多的波荡不宁,借用一个水力学术语,其心理状态呈现为纷乱的“紊流”状态。紊流与层流分别为液体的两种流态。层流是指管内液体分层流动,彼此平行,有条不紊,互不侵扰。紊流是指液体流动无序,轨迹混乱,互相混掺,不仅沿轴线运动,而且还有剧烈的径向运动,紊流亦称“乱流”“扰流”。液体作紊流运动时,所受阻力大,消耗能量多。此种物理现象似可贴切比拟姜夔的心理流程。“江汉乘流客,乾坤不系舟”(《答沈器之》),“谁能辛苦运河里,夜与商人争往还”(《送范仲讷往合肥三首》),姜夔人在“动”中,心亦在“动”中,他的内心五味杂陈,思绪百结,尤其是江湖游士濒于“行者”的生存状态一直撕裂着他的理想,咬噬着他的内心。本文主要通过考察姜夔作品中抒发的故园之思与暮年之嗟,论述姜夔风尘跋涉,憔悴江湖,瞻念前程,茫然失措,期冀“叶有所落”“老有所安”的求稳心理。
一、莼鲈之思的寻根苦旅
在古代文学史上,思乡母题的包容面甚广,吸附力甚强。征戍徭役、求仕负笈、兵燹灾荒、迁徙移民、经商远行,诸多的“隔绝机制”都是思乡的外部诱因。阳关三叠、茱萸饮酒、胡笳羌笛、子规啼血,成了文学史上怀乡恋土的系列话语。思乡成了身在异乡的众相人等最普遍最惯常的永恒情愫,尤其下层寒士,飘零如羽,更是引发乡愁心理潮动的重要契机。
姜夔的一生是动荡的一生。诗人一句“百年草草都如此”(《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六》),虽数字为虚指,然百年之久,一生之役,劳苦不安,形神毕现。作者将自己的伶仃只影自比“孤鸿”:“孤鸿度关山,风霜摧翅翎。影低白云暮,哀噭那忍听”;“风调心期契钥同,谁教社燕辟秋鸿。暮年孤陋仍漂泊,可得斯人慰眼中”(《次姜尧章饯徐南卿韵二首》)。姜夔流寓四方,身在异乡,归属感缺失,自称为“客”“客子”:“江汉乘流客,乾坤不系舟”(《答沈器之二首·其一》)、“项君声名天宇窄,与君俱是荆湖客”(《送项平甫倅池阳》)、“客来读赋作雌蜺,平生未闻衡说诗”(《次韵诚斋送仆往见石湖长句》)、“分明旧泊江南岸,舟尾春风飐客灯”(《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三》)、“夜深客子移舟处”(《水龙吟》)。自云“楚客”:“奈楚客淹留久,砧声带愁去”(《法曲献仙音》)。自称“行客”:“白头行客,不采苹花,孤负薰风”(《诉衷情·端午宿合路》)。尤其是每逢佳节倍思亲,绍熙辛亥除夕,姜夔雪后夜过垂虹,尝赋诗云:“笠泽茫茫雁影微,玉峰重叠护云衣。长桥寂寞春寒夜,只有诗人一舸归”(《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七》),“沙尾风回一棹寒,椒花今昔不登盘。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新词剪烛看”(《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六》)。因为行走一生,心力交瘁,他还自称“倦客”:“有倦客扁舟夜泛,犹疑水鸟相呼”(《汉宫春·次韵稼轩蓬莱阁》)。
即使在送别友人的作品中依然是伤人又伤己:“涉远身良苦,登高望欲迷。试吟青玉案,不似白铜鞮。露下秋虫怨,风高北马嘶。槎头有新味,人在太湖西。”(《答沈器之二首·其二》)尾联借沈器之家乡鳊鱼的味美表现他的漂泊怀思,亦处处流露出姜夔自身的真切体验与刻骨感受。姜夔希望自己能够停泊靠岸,让脚步驻足,让心灵休憩,身稳心亦稳下来,甚至作者的愿望已经非常朴素,只要安定,田园可居,“桑间篝火却宜蚕,风土相传我未谙。但得明年少行役,只裁白纻作春衫。”(《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八》)频繁的旅途颠簸,诗人将自己的衣服称为“征衣”:“已拚新年舟上过,倩人和雪洗征衣”(《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其五》),征尘劳顿,使其思乡的情感振幅与情感力度格外强势,他会像张翰见秋风起而思鲈鱼一样归心似箭,“鲈鱼应好,旧家乐事谁省”(《湘月》),诗人不断地反刍自己绵长的浪迹阵痛,一句“飘零久”(《霓裳中序第一》),又一句“谁念飘零久”(《探春慢》),当情动于中,伤怀至极,诗人已禁不住泪眼婆娑了,“飘零客,泪满衣”(《江梅引》)。此种谙尽心酸,抒写归思通过两种方式在文本中呈现出来。
第一种是直接方式。据笔者统计,除去诗歌,姜夔长短句中正文用到的“归”字多至35 处,致使“归”成了诗人心中、文中最显赫的一个主题词。如“把酒临风,不思归去,有如此水”(《水龙吟》)、“屡回顾。过秋风、未成归计”(《法曲献仙音》)、“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一萼红》)、“甚日归来,梅花零乱春夜”(《探春慢》)、“乱落江莲归未得”(《霓裳中序第一》)、“满汀芳草不成归”(《杏花天》)等等,不复缕述。
第二种是间接方式。尽管作品字面没有“归”字,但归情归意含纳其中。如“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江梅引》),“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玲珑四犯》),“淹留久,砧声带愁去”(《法曲献仙音》),“甚谢郎也恨飘零,解道月明千里”(《水龙吟》),更近于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姜夔题画诗共有5 首。《赤松图》一首,《与和甫时甫分题画卷夔得剡溪图》一首,《金神夜猎图》二首,《雁图》一首。其中题咏飞雁图的七绝,蕴含的情感非常复杂:“万里晴沙夕照西,此心唯有断云知。年年数尽秋风字,想见江南摇落时。”(《雁图》)夔见雁图而引发联想,开篇冬南夏北的大雁在辽阔旷远的天空形成雁阵飞翔,背景是晴沙万里,夕照一抹。“雁”为候鸟,具有随季节迁徙的特性,古有鸿雁传书的故事,所以鸿雁多用来象征传递音信的使者,雁成为表达思乡之情的特殊符号。古人由雁儿归通常会想到人儿归,此诗应为姜夔目睹雁图中雁字回时,思归之情油然而生。有释者认为此乃哀国之意,见到“夕照”就想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穿凿附会耳。
当代美学认为:“表面看来最富自发性的行为,当它们进行显示时,它们是历史的结果。”[2]姜夔客久思归的答案,大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寻找:
第一,文化心理。农耕文明的显著特点是传承性、依赖性、内向温和性。它与西方海洋文明的流动性、开放性、扩张性甚至侵略性不同,自给自足的农耕方式造成了保守、和平、中庸、稳定的心理特质。思乡意识作为不可忽视的一个文化基因,很早就注入了中国文学的血脉,并形成了传统系列的相关话语,从而强固了华夏民族的乡土文化模式,其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本质乃孤独心态为内在特征的特殊情感体验。
第二,羁旅伤痕。“愁”亦是姜夔作品的一个高频词。姜夔山程水驿,辗转奔碌,据笔者考证,姜夔72首词作竟转换地点23 处之多,愁苦落魄羁绊了他的一生。诚如范成大云,“天无寒暑无时令,人不炎凉不世情”(《请息斋书事》),对于“平生最识江湖味”(《湖上寓居杂咏·其一》)的姜夔,人在旅途,身心俱疲,随着诗人哀愁质素不断累加,其中的望乡情绪自然超越了常人常态而格外强烈。
第三,伦理亲情。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是群体本位的文化,它体现群体的思想、情感、经验、意志、观念以及规范等,而人生价值的参考系统正是建构在群体文化的价值体系之中。社会群体意识感情上有亲疏之别。人在孤独无依时,往往乡愁愈浓,乡情愈炽,唤起的是更具亲和力凝聚力的社会群体意识。
第四,时事丕变。“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其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南宋一朝,时代空气、个人际遇都倍使姜夔经受多重的心灵挣扎,所以他的归思是局外人难以体认的。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是心灵的港湾,家是最大化能够满足人的感情需求与安全需求的温馨驿站。姜夔无数次“归去来兮”的倾情呼唤,已经很难找到统一的具象所指,尽管合肥情侣一直是他心中的重量级主角,但身归何处,家在哪里?它俨然上升至一种抽象的文化高度,它是诗人在思定却动的江湖生态中心理重荷的压力呈示,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无归宿感的彷徨苦闷。
二、凄惶迟暮的生命意识
个体生命意识所体现出来的对时间惶惶不及的紧迫感通常被归结为“逝川之叹”。逝波、白驹、薤露、漏刻,构成了古代文学中兼具哲理与诗意的意象群。日月不居,未尝消歇,尽管万物兴亡归于自然,但罕有纵浪大化,不喜不惧之人,“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成为共同的困惑与共同的期待。惜时之感是千古文人对“记时钟点”的深层关注,它不仅包含建功立业、青史流芳的一面,也存在保存天年,及时行乐的一面,体现的是有限中求无限、相对中求绝对的执著努力。
姜夔作品体现出深深的对于时间亦是对于生命的痛苦思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朝花夕拾的共通情怀;一是叹老嗟贫的心理对比。前者重回忆,后者重慨叹。“心理学认为,回忆是将以前产生的对事物的反映重现出来,是人对储存在大脑中的与自我经验相联系的信息的提取过程,回忆与个体的过去经验密切联系,而回忆的唤起则与个人的当前经历有关。”[3]无论一个人的年少时光是七彩还是晦暗,大抵关涉到亲情、娱乐、理想、友谊、爱恋等几个方面,“正是由于其‘少年心’带有不确定的多极指向,所以使得每一个步入中年以后的读者都能引起感情上的震颤,从心灵深处不约而同地重新升起对于童年的呼唤。”[4]从笔者个人经验观之,武将从武,会使意志更加坚定,文人从文,会令神经更加敏感。姜夔老去无成,志士含悲,当数经磨难,几肩风雨,回首蝶飞凤舞的无邪岁月,词人多情脆弱与多愁善感的心理品质,加之社会尘世的种种激惹,自然会令其打开追忆“少年事”,缅怀“少年心”的情感闸门,正如欧阳修《秋声赋》所议:“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5]譬如,姜夔的“东冈记得,同来胥宇,岁月几何难记”(《永遇乐》),饱含回首往事,逝者如斯之情,等等。
据笔者统计,在姜夔仅72 首长短句中,“老”字多达23 处。白石自称“老子”:“采香泾里春寒,老子婆娑,自歌谁答”(《庆宫春》),“老子那花第一番,常恐吴儿觉”(《卜算子》);自称“老夫”:“却不如漥樽放满,老夫未醉”(《永遇乐·次韵辛克清先生》)等等,作品中时间意识的体现和时间意识的觉醒,从多个层面体现出来。譬如,“叠鼓夜寒,垂灯春浅,匆匆时事如许”(《玲珑四犯》),感慨乌飞兔走,光阴穿梭之悲;“白头行客,不采苹花,辜负薰风”(《诉衷情·石榴一树浸溪红》),抒发人至晚年,沧桑阅尽之意;“谁念我鬓成丝,来此共尊爼”(《侧犯·咏芍药》),刻画出人生迟暮,两鬓霜染的自我想象;“雁碛波平,渔汀人散,老去不堪游冶”(《探春慢·衰草愁烟》),吐露出自己韶华渐去,时不我与的惆怅;“朱户黏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一萼红·古城阴》),传达出蹉跎岁月,一事无成的悲凉;“才因老尽,秀句君休觅”(《蓦山溪·题钱氏溪月》),感怀自己青春不再,江郎才尽;再如“带眼销磨,为近日、愁多顿老”(《秋宵吟》),“一丘吾老,可怜情事空切”(《念奴娇·毁舍后作》),等等。此外还有诸如岁华如许、时序侵寻、流光过隙等表示时光催迫之感的词语。在姜夔的部分作品中,其所谓的垂垂近老,其年不过三十几岁,体现出实际年龄与心理年龄极大的不对等。其对于时间、生命的清醒体认,其发生与两个方面有关。
首先,生命意识是由来已久的文学传统。伤春、悲秋、叹老都是我国古代作家最普遍最典型的情绪体验。溯其根源,缘于物候变化对文学家生命意识的触发。用竺可桢的话说,物候是“大自然的语言”,无论植物的播种吐穗,开花结果,发芽落叶,还是动物的迁徙、始鸣、冬眠,抑或气象的初霜、终雪、结冰、解冻等等,凡此诸多季节性春去秋来的轮回启示,都会唤起作家对生命状态、价值、走向、意义甚至死神的一己彻悟与深层思考。需要指出的是,文学家的这种生命意识也具有相应的地域特点。在四季分明、季相明显的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文学家的季节感受非常敏锐,作品中流露的诸如伤春、悲秋一类的生命意识格外强烈。在四季常青的岭南地区,这类作品殊难寻觅。
其次,从外察到内省,文学家由物候的变迁,常常会引发自己对当下处境以及未来命运的隐忧。天地无穷,人命有终。诚如宋玉悲慨“岁忽忽而遒尽兮,老冉冉而愈驰”(《九辩》),东方朔亦哀叹“年滔滔而自远兮,寿冉冉而愈衰”(《七谏》),面对青春消磨,石火电光,年华老去,来日无多,姜夔在国运短祚,山河易主的南宋时代,既不能振翮高飞,又不能抽身远翥,往不可追,来不可测,独有的“江湖式”人生道路,使其毕生踯躅于出处两难的纠葛之中。当痛感人生之旅在时间之流中行进不息时,苍凉、悲戚的情绪就会弥散开来。
结 语
姜夔从家园意识到生命意识的吟咏感喟,离不开社会成因、文化赓续、心理动源多个层面。故乡之地理版图与心灵版图的双重属性常常令人适彼乐土,时间之一去不返的单维特质又令人倍觉时不我待,二者皆会在广大士人的心理之躯引起巨大摇撼。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隐士》指出:“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必须‘隐’而不得,这才看作士人的末路。”[6]姜夔恰恰属于仕隐不得类于绝境的末路之人。姜夔因感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其怆恻体认的触发及扩大缘于主体对整个人生的失落感、忧虑感、惧怵感。综上,“‘隐’与‘仕’是‘定’的文化,‘江湖’是‘动’的文化”[1],姜夔喜聚不喜散、恋群又恋故、求稳亦求安的文化心理,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个体欲望与社会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是有所依恃实现自我与社会统一的心理诉求。姜夔一直用艺术熨帖着自己的孱弱生命,但是,叶落归根,颐养残年,对待生命的终极关怀,才是浮家泛宅的姜夔心底秘藏的一帧圣符。
[1]赵晓岚.姜夔与南宋文化[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485.
[2][法]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117.
[3]郑杰文.中国古代文学跨学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193.
[4]杨海明.杨海明词学文集[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40.
[5][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十五[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111.
[6]鲁迅.鲁迅杂文名篇[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