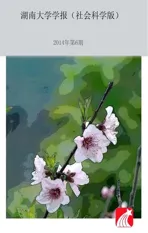孔子之“道”与儒学重构——从朱熹、牟宗三的道统论说开去*
2014-03-31郑治文
郑治文
(曲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道统”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方面。一般说来,儒家的道统观念以先秦孔孟为远源,经中唐韩愈发挥①《论语·尧曰》、《孟子·尽心下》、韩愈《原道》。,并最终由宋儒推向成熟[1](P65-66)。“道统”是什么?不同的儒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有论者认为,儒家“道统”可在即“统”言“道”、即“道”言“统”两种模式下得到诠释和说明。所谓即“道”而言“统”,就是以“道”作为儒学之为儒学的真精神,并以此为要来判分和确立儒家的传承谱系。如熊十力所言:“盖一国之学术思想,虽极复杂,而不可无一中心。道统不过表现一中心思想而已。”[2](P342)就道统之宽泛意义来说,就是表征儒家之中心思想、根本精神、核心观念的传承统绪。确立一个什么样的道统,往往也就意味着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儒学形态。不同时代的儒者围绕着对“道统”之“道”的不同理解,建构了理论形态迥异、义理精神有别的儒学系统。作为宋明“新儒学”创设之关键人物,朱熹以“十六字心传”和孔颜“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作为道统之“道”的主要内涵,并由此整合圆融了呈现道心与人心、理与气、天理与人欲、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二元架构的程朱理学系统。然超越精神的提升、理气心性的圆融,宋明理学虽能成功回应佛老挑战,扭转“儒门淡泊,收拾不住”之颓势,却也将儒学引上了形上超越的极端,沦为“空谈心性”的玄学清谈。与之有类,现代新儒家有感于儒学“花果飘零”之困局,矢志延续道统,复兴儒学,他们遥接宋明,复活程朱陆王之思想睿慧,以形上超越的路径保存、提升、重建儒学,牟宗三即是其中的主要代表。牟氏以儒家内圣学“心体即性体”的圆教模型释道统之“道”,判分先秦儒典,重组宋明儒学,援引西学,提出“内圣开新外王”的构想,完成了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然这种形上保存的方式,虽在继承、发扬、整合、创新中国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却有以心性修养代道德实践的偏执,难于“落实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间”。对此,我们不免会有这样一番思量:朱熹、牟宗三皆以回归孔孟为追求,力图彰明圣学本义,他们既以得悟儒门“道”之本旨,其孜孜以求,费尽心力所构创的所谓“新儒学”为何还有如此偏失?圣学要领究竟何在?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后新儒学”的语境下对其进行总结反思,呼唤儒学重返生活世界,期待儒学活水流向民间,致力于儒学的生活化、民间化、大众化、社会化开展及其当代重构时,如果能静下心来细细品读《论语》,回到孔子的生活世界,真真切切地体验孔学精神,我们或许不难发现,儒门所传之“道”既非朱子匠心独运所提出的“心传”、“心法”那般抽象神秘,亦非如牟氏所悟彻的所谓“心体即性体”那样玄奥精深,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和合”、“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如此而已。倘能明此儒之为儒的真精神,对儒学的当代重建或可提供有益的借鉴和指引。
一 朱熹的“心传”、“心法”及其“二世界”哲学
“道统”是儒学的核心观念和中心思想所在。朱熹以“十六字心传”与“克己复礼为仁”之“心法”作为其立学根基,可以说,其整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正是以此为起点,在此“道”的内核之上生发、展开的。“道统”一词由朱子率先提出,其主要内涵在《中庸章句序》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他说:
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3](P14)
在此,朱熹径直将尧、舜、禹圣贤一脉相传的道统具体化为《尚书·大禹谟》中的“十六字心传”。学界一般也都以之作为朱熹道统论的全面的经典性表述,其实不然。诚如有论者指出的:“盖现有论述皆以‘十六字心传’为朱子道统说之根本性、唯一性表述,而忽视了颜子及其所代表的‘克复心法’在构筑朱子道统学中的应有地位。……故孔颜克己复礼为仁的心法授受实为‘十六字心传’的必要补充,其价值在于彰显了儒家道统以工夫论为核心,由工夫贯穿本体的下学上达路线。”[4](P19-20)应该说,“心传”与“心法”的结合方是朱子道统论之“道”的基本内涵所在,因为讲“道心”、“人心”的“心传”只体现了朱学本体与心性的统合,唯有辅以“克复心法”所彰显的工夫学说,程朱理学才真正成其为一圆融本体、心性、工夫的完整体系。由是,朱学的整个义理架构可以道统中心,“心传”、“心法”两条主线进行分解说明。
就朱熹摘出的“十六字心传”来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谓“道心”是指符合道体天理之心,故“微”;“人心”是指生于形气之偏的私心,故“危”,而“允执厥中”就是要时时省察此“危而不安”的人心,持守“微而不显”的道心,以合乎天理仁义之心为要求,“执中”,无过无不及。不难看出,朱子所传之“道”正是二程“自家体贴出来”的“天理”,其对“十六字心传”的解释不过就是“存天理,灭人欲”一语。因此,以“十六字心传”为突破口,正可以析分出程朱理学“理”与“气”、“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理”与“人欲”的“二世界”架局。朱熹以“理”、“气”二元互动确立其形上根基,并以此论心性而言“一性二分”、“心统性情”,实现了本体与心性的合一。下引几句话最能体现朱熹圆融理气心性的意识,十分关键。他说:
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5](P2755)
论天地之性则是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5](P2688)
由此不难发现,在朱熹的思想世界里,理气心性实已圆融为一,本体与心性合在了一起。这可以说是朱熹以“十六字心传”为纲领所展开的义理建构。以“心传”为根基的理气心性的贯通,辅以“克复心法”所体现的工夫进路,完整确立了程朱理学之规模。这就是说,朱学明分“理”与“气”、“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这种生命二元架局最终要落实于即物穷理、存理灭欲、涵养用敬、变化气质的工夫,即要学做圣人、克己复礼、行仁践义,坚守儒家道德价值理想,最终成圣成贤[6](P74-77)。他说:
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7](P367)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大谈理气心性,看似玄妙漫谈,实则是要以真切工夫的开出为旨归的。就工夫论而言,朱熹服膺伊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说法,以用敬与致知作为其工夫论的两个重要方面。格物致知,即物穷理,虽被陆九渊讥为支离事业,但是如果从朱熹的整个哲学系统来看,这种“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又分明能与其全系统相统一、相协和。
综上可见,朱熹以“十六字心传”和“克复心法”为纲,创构了以圆融本体、心性、工夫为基本特质,以形上超越著称的“二世界”哲学,实现了儒学形态由“实存道德描述”向“道德形上学”的转变。这极大地提升了儒家的哲学思辨水平、开拓了儒家形上超越的世界,由此也就成功回应了佛道的挑战,重建了中华人文价值理想,实现了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然而,程朱对“天理世界”的不断拔举和提升,尤其当朱子大言“理在事先”的时候却也将儒学引上了形上超越的极端,所带来的不仅是使儒学日益脱离“活生生”的“生活世界”而沦为“空谈心性”的玄学清谈;在绝对超验的“天理世界”统治下,所造成的是道德本体之“超我”对自我的压抑和束缚。朱熹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 先 有 父 子 之 理。”[8](P3204)君 臣 父 子 夫 妇 之“理”既先于人而存在,人生而就只有被动地去接受这个“理”,即毫无怀疑地去遵循践履儒家“三纲”之教了。正如杨国荣先生所说:“正统理学以性体为道德本体,并以此为前提,要求化心为性。在性体形式下,普遍的道德规范构成了涵摄个体的超验原则,本体被理解为决定个体存在的先天本质,自我的在世成为一个不断接受形而上之规范塑造、支配的过程。由此导致的,往往是先验的超我对自我的压抑。”[9](P12)由此可见,这种形上超越的追求和提升,也可能会使儒学蜕变为超然于世、藐视世俗、流于空谈、乏于践行的玄虚之学。
二 牟宗三的“心体即性体”及其新儒学
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的系统建构者。他深研道德形上学,会通天台圆融义,终悟孔子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先以心体、性体的圆融为要,判释先秦、宋明两期儒学,重构儒学新道统,又以此为基石,构筑起以肯定“智的直觉”、“内圣开出新外王”、“三统并建”、“良知自我坎陷”为主体内容的儒家道德形上学体系。可以说,悟彻孔子成德之教,识得儒家内圣心性学“心体即性体”之要旨,实现道统重建,是牟宗三现代儒学创新的起点和关键。
其一,以“心体即性体”为要,厘定先秦儒家经典,分别宋明理学之系统,重构儒家道统[10](P15-21)。在牟宗三看来,儒家所谓“道统”乃是泛指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或内圣成德之教,“中国‘德性之学’之传统即名之曰‘道统’”,此“德性之学”的精义,集中凝结为“心体即性体”这一哲理深邃的命题。“性体”是道德形上学的概念,指内在道德性之性,与“天”这一实体相联系。“就其统天地万物而为其体言,曰实体;就其具于个体之中而为其体言,曰性体”[10](P43)。这里,牟宗三发挥了《中庸》“天命之谓性”的说法,以为“于穆不已”的天体下贯到个体之中而成其为性体。此“性体”概念从形上超越的高度确认了道德实践之可能,是儒家道德形上学可以成立的要害所在,正因为有此“法门”,儒家这里才能实现道德与形上学通而为一,确立其“即宗教即道德”的精神特质。与“性体”一样,“心体”亦是儒家内圣学的重要范畴,可以说,性体与心体构成了内圣心性学的一体两面。此“心”非生理之心、心理学之心,亦非所谓认知之心,而是超越自律,内在固有的道德本心,相应于性体而言“心体”。如果说,“性体”主要体现的是儒家内圣学“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第一义,而比较是一个本体论概念的话,那么,“心体”则多显其“践仁以知天”的第二义,而有工夫论之意味。当然,这里本体与工夫须是合而为一,“即心体即性体”,儒家贯通心体、性体的内圣学成为了道德实践和道德形上学的完美体现,也即达到了其“大而化之”的第三义的最高践履境界。确认了内圣学“即心体即性体”的要旨之后,牟宗三以之为主要依据重组先秦儒典、判分宋明理学,进而实现了儒家道统论的重构。牟宗三将先秦五部儒学经典《论语》、《孟子》、《中庸》、《易传》、《大学》判分为两系:《论》、《孟》、《易》、《庸》为一系,它们蕴涵着“心体即性体”的深刻义理,是孔子生命智慧与成德之教的“一根而发”,代表着先秦儒学的本质;《大学》单列为一系,它相对于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而言是“另端别起”、“似是从外插进来”,不合乎孔子生命智慧的方向,并不能代表先秦儒学的本质。论定《大学》之义理归趣及其地位是牟宗三重建道统的重要一环,以此两系“模式”为参照,牟氏将宋明理学也析分成了“两宗三系四组”:第一组为“周张程(颢)”,大致说来,他们学宗《论》、《孟》、《易》、《庸》,由《易》、《庸》返归《论》、《孟》,接续了儒家“即心体即性体”的一本圆融义。这一组作为理学先驱,至此宋明儒学尚未出现分系。第二组是“程(颐)朱”,从程颐开始出现了宋明儒学的分系,原因在于程伊川别取《大学》系统涵摄《论》、《孟》、《易》、《庸》的路向。其后,朱熹一脉相承,进一步拓展深化了这一“别样”的路向。第三组为“胡(宏)刘(宗周)”,牟宗三较为推崇这组,认为五峰直承明道的圆教模型,其后由刘蕺山继之而成为宋明儒学之殿军。第四组是“陆王”,他们深契孟学精神,阳明虽也言《大学》,但那是在孟学系统统摄下来立说的。以上是“三系四组”的提法,至于“两宗”就是将以《论》、《孟》、《易》、《庸》为中心的宋明诸儒作为“大宗”或“正宗”,这包括上述第一、三、四组;而把《大学》作为中心的程朱看作是所谓的“别子为宗”。言至此,牟宗三的道统观也就大体明确了:“道统之道”应该是“即心体即性体”的内圣成德之教,其传承统绪大致是孔孟、明道、胡刘、陆王等[11](P39)。所谓重续道统就要返归《论》、《孟》、《易》、《庸》,“接着宋明讲”,光大儒家圆融心体性体的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
其二,以“新道统”为理论根基,创构现代新儒学体系。既以悟得了儒家“即心体即性体”的道统法门,牟宗三就是以此为内核展开其新儒学架构的。牟宗三接续宋明之“胡刘”、“陆王”而言良知本体,又以“心体”和“性体”作为其不同的表现形式,“心体”、“性体”合为一体,皆是指“良知”本体。他说:
心体是就此良知明觉即是吾人之“本心”说,此本心就是“体”。性体是就此知体、心体就是吾人所以为道德的存在之超越的根据,亦即吾人所以能引生德行之“纯亦不已”之超越的根据而说。……此性体是通过知体、心体而被了解的。故性体是客观地说的,知体、心体是主观地说的。此两者是一。[12](P66)
牟宗三讲“良知”本体,进而也肯定人有“智的直觉”,其所谓“智的直觉”即是“自由无限心”、“知体明觉”或者就是“良知”。在牟宗三看来,正因为人也有“智的直觉”而不只属于上帝,人不仅能认识现象世界,而且能呈现本体世界,不仅能践履形而下的道德,而且能通过道德实践实现自我转化,从而实现超凡入圣。因此,“良知”、“智的直觉”是成就“道德的形上学”关键,正因为人有“智的直觉”、有和合心体与性体的“良知”,道德本体一方面可由内向上翻、将生命存在接通终极价值本源;另一方面又可自上向下“流布”、从至上的道德实体落实到具体万物[13](P209)。显然,牟宗三言“良知”本体、肯定“智的直觉”证成的道德的形上学主要只是“返本”,而对于儒家这套内圣成德之教如何实现现代开展进行全面系统地论证方是牟学之“开新”所在,这主要表现在其“内圣开出新外王”、“三统并建”、“良知自我坎陷”说的提出①牟宗三先生《生命的学问》、《历史哲学》、《时代与感受》、《政道与治道》等论著中有详细论说,兹不赘述。。当然,其义理精神无论多么高明、新颖,皆是本于儒家的内圣成德之教立说,皆是在此“内核”上萌发的新思。也就是说,牟宗三仍是“接着朱熹讲”,先将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归结为内圣之道,以内圣统外王;又将内圣之道归结为形上的本体,以内圣的良知本体开出新的外王。换言之,牟宗三先是识得孔子的生命智慧和内圣成德之教,实现以“即心体即性体”为核心观念的道统之重构,进而开出其道德形上学,提出“内圣开出新外王”等一系列创造性构想,最终完成其新儒学体系构建的。
以牟宗三为主要代表的新儒家在回应西学挑战、实现儒学现代转化等方面无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当其把“接着宋明讲”的新儒学“提到一个超越绝对的地步”时,儒家之道德价值理想就很难“落实在整个历史社会总体间”(林安梧语)而作为一现实道德实践的开启。如比之于程朱理学,我们或许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点。其实,新儒学发展至牟宗三,有类于宋明理学发展至朱熹立“形上绝对”、“超越至上”之“极”,理学遂日成超然于世、清高脱俗的清谈玄学。与此相类,牟宗三的道德形而上学也有此特点,故林安梧称其为“高狂俊逸的哲学家”,“在牟先生的系统中,却把人提到上帝的层次,再从上帝下返到人间,就好像已经究竟地证道了,再作为菩萨下凡人间,而开启现代化的可能性。这样的理解方式,我以为可以用蔡仁厚先生所说的‘高狂俊逸’这句话来形容,牟先生是一高狂俊逸的哲学家,果然!”[14](P295)诚然,牟先生此“高狂俊逸”之哲学,难免也有疏离“生活世界”,以心性修养代替道德实践的偏执。
正是因为有识之儒洞见了这种偏执,牟宗三之后所谓“批判的新儒学”所由出,遂成“护教的新儒学”与“批判的新儒学”之分野。所谓“批判的新儒学”,就是指对新儒学持一“批判继承、创造发展”的态度,在批判继承之基础上创构一面向“生活世界”、面向“历史社会总体之道德实践”的“后新儒学”,从而开启一个“后新儒学的时代”。在此“后新儒学”的时代,我们真切期望儒学能走出书斋,走出讲堂,“来到我们身边,活在我们中间”,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令妇孺皆知,如春风化雨般教化国民[6](P108)。由是,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检视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学的道统观,去觅求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新道统”为纲领实现当代儒学的重建。为此,重读《论语》,返本归源,追寻孔子真正的生命智慧或许是我们首要的理论工作。
三 仁礼合一——回归孔子之“道”,重构当代儒学
细读《论语》,回到孔子的生活世界,真切体验孔学精神,我们或许不难发现,孔子“道”之真义不过“仁礼和合”、“极高明而道中庸”二语,如此而已。就主要内涵来说,孔子之“道”要在“仁礼合一”;由哲理精神而论,孔子之“道”要在“极高明而道中庸”,也即是说,孔子的“仁礼合一”之“道”本身彰显着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
如所周知,孔子的思想起点是礼,其创立儒学源于补礼、纠礼的致思路向。周文疲敝,礼乐不兴,孔子欲兴亡继绝,接替斯文,就必要对“礼”有一番因时制宜、损益革新的处理。孔子之为孔子者,就在于他敏求善思自家体贴出了“礼”背后那个更为重要的根本——“仁”,为古老的礼乐文化重新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当然,“述”礼“作”仁虽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本线索,但这并不意味着仁、礼简单拼凑相加就自然化生儒学,言礼不及仁,非儒也;言仁不及礼,亦非也;仁礼和合,真儒之谓。因此,孔子虽把“仁”界定为礼之本,但并未因仁而废礼,一方面以仁释礼,另一方面又强调以礼来外化仁、落实仁。仁、礼不偏废,内外合为一;“仁”是内化的“礼”,“礼”是外化的“仁”,两者和谐互动、感通为一。如果仁不外化为礼而落实于日用常行间就不能实现其价值,此其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同样,如果外在的礼失去了内在之仁作支撑,那么礼就流于形式、虚文,此其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15](P24),“礼云礼云,玉帛 云 乎 哉?乐 云 乐 云,钟 鼓 云 乎 哉”[15](P185)。可见,仁与礼构成孔子之“道”的一体两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仁”之要在于使“礼”合乎主体内在的心性情感,而不至于流于空有其表、形式僵化的所谓“吃人的礼教”;“礼”之要则在于将主体内在的情感化作外在的力量,落实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中。“仁”的内在情感与“礼”的外在行为合而为一,方是道德实践之整个过程的完成。
由此,“仁礼合一”或许才是孔子的生命智慧和成德之教的真义所在,这也便是儒门所传的“道”,此“道”所内蕴的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深邃哲理:它既高举远瞻,又平实切近;既是终极关怀,又不离人伦日用;既是形上超越之“道”,又是百姓日用之“道”。《论语》中论“道”多与“仁”相连,比如: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15](P36)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15](P67)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而后矣,不亦远乎?”[15](P80)
上引数语明白地指出了道与仁不可分割的关系,据此,以孔子之“道”为仁(须是合着礼的“仁”)道也似无不可。这个仁道,一方面是孔子的终极托付之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以清楚地看到道作为人的“终极关怀”的宗教意涵;另一方面“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分明地揭示了“道不远人”的重要特点,所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5](P74),“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5](P123),此之谓也。当作为“礼之本”的内在的“仁”显发为用而成外在的“礼”时,又可化民成俗,落实于穿衣吃饭、日用常行之间。小至视听言动、举手投足、婚丧嫁娶、送往迎来,大至行军作战、为政治国皆要合乎“礼”。《论语》有言如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5](P123)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15](P13)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15](P38)
当我们一言一行、待人接物都依礼而行时,自可“求仁得仁”、“从容中道”,此即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其实,这也正是芬格莱特所说的礼的“神奇魅力”、“魔术效应”。他说:“人们纯熟地实践人类社会各种角色所要求的礼仪行为,最终便可以从容中道,使人生焕发出神奇的魅力。圣人境界就是人性在不离凡俗世界的礼仪实践中所透射出的神圣光辉。”[16](P1-13)概而言之,“即凡而圣”四字恰切地表述了孔子仁礼合一之“道”的深层意涵,凡俗与神圣相即不离正是其最为显著的特点。[17]
孔子的以上思路在《中庸》中得到了更加淋漓的体现。人与道的关系是《中庸》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而其立论的基点,则是道非超然于人,“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并不是与人隔绝的存在,离开了人的为道过程,道只是抽象思辨的对象,难于呈现其真切实在性。而所谓为道,则具体展开于日常的庸言庸行:“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极其至也,察乎天地。”道固然具有普遍性的品格,但它唯有在人的在世过程中才能扬弃其超越性,并向人敞开。正是在此意义上,《中庸》强调“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即无过无不及,“庸者,常也”。极高明意味着走向普遍之道,道中庸则表明这一过程即完成于人在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18](P1)。“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语虽非出自孔子之口,却最能表述孔子“道”之本旨,可以说,这也正是儒学之真精神所在。儒家传统一方面能“与时偕行”、“日新又新”(变),另一方面又“万变不离其宗”,终不改其“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底色(常),这或许正是其穷变通达、可大可久的依据。恰如颜炳罡先生所言:“‘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儒家的精义、儒家的真精神,是儒家有别僧、道、耶、回处。”[19]如果我们把孔子“道”之“两面”——“礼”和“仁”作进一步分解,就会析出“道德规范(克己复礼)与道德自觉(为仁由己)”、“规范建设与情感建设”、“社会存有与心性修养”、“超越理想与世俗价值”、“礼法规范与社会正义”等多重分疏,在这样的分界中,我们更可以觉察到孔子“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高超智慧,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取法乎中,无过无不及,遂避免了游走两极的偏执,成就了仁礼合一的原始儒学这一阳刚劲健、元气淋漓、生生和谐、可大可久的思想系统。
回顾孔学精神,我们不难明白,儒家的道统之“道”应是此“仁礼合一”之“道”,应是此“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道”。在“后新儒学”的时代语境下我们正需要接续、光大此“道”,确立合乎时代精神的“新道统”,并以此为纲领展开当代儒学的重构。诚如梁涛先生所指出的:“学习宋儒的做法,重新出入西学(黑格尔、康德、海德格尔、罗尔斯等)数十载,然后返之于‘六经’,以新道统说(仁礼合一)为统领,以‘新四书’(《论语》、《礼记》、《孟子》、《荀子》)为基本经典,‘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以完成当代儒学的开新与重建。”[20](P62)①对此,林存光先生有不同看法,参见其《也谈国学研究的态度、立场与方法——评梁涛儒家道统论的“国学观”》(《学术界》,2010年第2期)一文。这里我们比较认同梁涛先生的观点。当然,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可以再做深入讨论。总之,当我们回归孔子之“道”,以之为指引重建当代儒学时,一定要守住儒家的“根”,切实把握儒家之为儒家的真精神,致力于建构一种“心性修养与道德实践”、“德性伦理与规范伦理”、“美德与规则”[21](P27-28)、“形上超越与生活日用”、“理想与现实”、“神圣与凡俗”……平衡互动、通为一体的新儒学。
[1] 朱叶楠.“道统”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失落与重生[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5-94.
[2] 熊十力.熊十力全集[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许家星.朱子道统说新论——以孔颜“克复心法”说为中心[J].人文杂志,2013,(6):19-27.
[5] 朱子全书(第2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 郑治文.文明对话与中国文化[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3.
[7] 朱子全书(第14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8] 朱子全书(第1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9] 杨国荣.心学的理论走向与内在紧张[J].文史哲,1997,(4):10-18.
[10]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11] 杨海文.略论牟宗三的儒家道统观[J].学术研究,1996,(6):39-42.
[12]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M].台北: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
[13] 程志华.中国近现代儒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4] 林安梧.儒学革命——从“新儒学”到“后新儒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5]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M].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7] 李勇强.孔子人性论思想的新探讨——以先秦简帛文献为线索[J].求索,2013,(1):69-71.
[18] 杨国荣.作为哲学的儒学[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3-16(06).
[19] 颜炳罡.民间儒学何以可能[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7f9ee10102drhp.html,2011-07-23.
[20] 梁涛.回到“子思”去——儒家道统论的检讨与重构[J].学术月刊,2009,(2):54-62.
[21] 刘余莉.美德与规则的统一——兼评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的观点[J].齐鲁学刊,2005,(3):2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