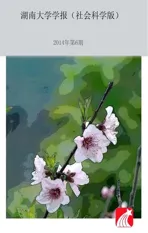何休《公羊解诂》的君主论思想*
2014-03-31郑任钊
郑任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何休(129—182)是汉代春秋公羊学大师,他殚精竭虑注疏《春秋公羊传》,花费十七年的时间写下《春秋公羊解诂》。《公羊解诂》是后世《公羊传》的标准注本,在经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何休所处的东汉末年,是与春秋时代一样的乱世。桓灵时期,“主荒政缪”[1](党锢列传),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政治极为黑暗,人民生活极为困苦。何休本人也被宦官集团禁锢十几年。面对黑暗的政治现实,何休苦苦思索“拨乱反正”的济世良方,期待清明的君主政治的出现,渴望恢复社会的有序状态。《春秋公羊传》本身具有强烈的追求社会秩序的倾向,[2]何休在注解《公羊传》的时候,借《春秋》史事,以公羊家的视域,以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定为核心,阐发了许多有关君主及君主政治的思想和理论,对为君之德、为政之道、君臣关系及君位传承等问题都有深入的思考。
一 为君之德
儒家向来重视君德。在君主专制之下,君主的圣明与否直接决定国家的治理与否。东汉末年的桓、灵二帝就是骄奢淫逸之主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统治使东汉王朝直接走向崩溃的边缘。何休在《公羊解诂》里非常鲜明地指出:“不肖之君为国尤危。”[3](桓公三年)
在阐述君权的合法性时,何休说:
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见刺讥是非也。王者,号也。德合元者称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遥术,无文字,德明谥。”德合天者称帝,河洛受瑞可放。仁义合者称王,符瑞应,天下归往。天子者,爵称也,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3](成公八年)
王者的合法性虽然是来自于天,但其落脚点显然在于“德”,强调的是“德合元者”,“德合天者”,“仁义合者”,实际上是将君德置于核心地位,最终君权的合法性来自于以德赢取民心而天下归往。
何休强调君主身先天下的表率作用,指出“上敬老则民益孝,上尊齿则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于辟雝,天子亲袒而割牲,执酱而馈,执爵而酳,冕而总干,率民之至也”[3](桓公四年),认为君主的德行对民众具有非常巨大的感召力,对社会风气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何休继承了孔子“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4](颜渊)的思想,主张君主应当“先自详正,躬自厚而薄责于人”[3](隐公二年),又说:“王者起当先自正,内无大恶,然后乃可治诸夏大恶,……内有小恶,适可治诸夏大恶,未可治诸夏小恶,明当先自正然后正人。”即要求君主在道德上做出表率,在各方面都要为民之先。
具体而言,君主首先要做到“躬行孝道以先天下”[3](桓公十四年)。
何休在《解诂》自序里称:“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此二学者,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也。”《孝经》以孝为“德之本”[5](开宗明义),孝道是何休在君德中最为重视的内容之一。孝是何休评价君主的一大标准。如他盛赞“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孝子之至也”[3](桓公八年),指责周襄王“出居于郑”是“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3](僖公二十四年)。
何休认为,基于孝的要求,君主应当严格执行三年之丧,做到“子未三年,无改于父之道”[3](闵公二年),三年之中“孝子疾痛,吉事皆不当为”[3](文公二年)。对君主的不守丧行为,何休都予以指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齐纳币”,为鲁文公聘妇,何休谴责文公“丧娶”[3](文公七年),指出“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满二十五月,又礼先纳采、问名、纳吉,乃纳币,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内……有人心念亲者,闻有欲为己图婚,则当变恸哭泣矣,况乃至于纳币成婚哉”。僖公九年,宋桓公去世不久,刚即位的宋襄公就赴葵丘会诸侯,何休指责宋襄公“背殡出会宰周公,有不子之恶”。
何休对孝的推崇与汉代标榜以孝治天下是分不开的。他在《庄公二十五年》借《孝经》之文明确提出了君主“以孝治天下”的主张:“礼,七十,虽庶人,主字而礼之。《孝经》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遗小国之臣’是也。”以孝治天下,孝不仅限于事亲,更扩展为社会伦理、政治伦理,要求君主推其爱敬之心及于臣民百姓。他提出:“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贵有德,为其近于道也;贵臣,为其近于君也;贵老,为其近于父也;敬长,为其近于兄也;慈幼,为其近于子弟也。”[3](桓公四年)何休这里提出了王者治理天下的五大原则:贵有德、贵臣、贵老、敬长、慈幼,就是要以爱敬之心对待臣民百姓。于是贵有德、贵臣、贵老、敬长、慈幼,“上敬老则民益孝,上尊齿则民益弟”,“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也都经由孝道贯穿起来。
其次,君主要做到“以至廉无为,率先天下”。廉而不贪、俭约轻利也是何休在君德中非常重视的内容,《公羊解诂》中再三致意。何休评论桓公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一事说:
王者千里,畿内租税足以共费,四方各以其职来贡,足以尊荣,当以至廉无为率先天下。不当求,求则诸侯贪,大夫鄙,士庶盗窃。[3](桓公十五年)
君主一旦贪利,上行下效,最终就会使人人唯利是图,吏治腐败,民间盗贼横行,造成整个社会贪鄙成风、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恶果,必然会导致社会危机的产生。因此何休主张,君主有正常的租税和贡品足以满足需求,除此之外不应该再索取财物。何休非常强调俭约的重要性,其称“约俭之卫,甚于重门击柝,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此之谓也”[3](宣公六年)。层层防卫,还是难以完全防止盗贼,而上下俭约,却可以从根本上斩断贪利之欲。所以他奉劝君主要“厚于礼义,而薄于财利”[3](宣公十二年),尤其不要与百姓争利,强调“天地自然之利,非人力所能加,故当与百姓共之”[3](桓公十六年),不要把君权变成牟取私利的工具。
隐公五年“公观鱼于棠”,对鲁隐公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张网捕价值不菲的鱼,何休痛斥隐公“去南面之位,下与百姓争利,匹夫无异”。文公七年,鲁文公伐邾娄,取须朐,何休指责文公“贪利取邑,为诸侯所薄贱”。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楚灵王以蔡灵公弑父为由,诱杀蔡灵公,进而灭蔡,何休揭露楚灵王“内怀利国之心,而外讬讨贼”,声明“不与其讨贼,而责其诱诈也”。宣公十五年“初税亩”,何休讥讽鲁宣公“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僖公二十年“新作南门”、成公十八年“筑鹿囿”,何休也都责之以“奢泰”。
第三,君主“当以至信先天下”[3](桓公十四年)。
文公三年“晋阳处父帅师伐楚救江”,楚师围江国,晋军伐楚以救江,却遇楚师不敢战即撤还,次年江国被灭。就此何休认为:“救人之道,当指其所之,实欲救江而反伐楚,以为其势必当引围江兵当还自救也。故云尔。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何休认为,晋国说是救江实质上却没有救江,这是一种欺诈,于是他借孔子之言提出了“信”的重要性。
何休将宋襄公树立为君主守信的典范。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水之战,宋襄公坚持等楚军列阵完毕之后再发动攻击,结果大败。何休称赞宋襄公“得正道尤美”,“若襄公所行,帝王之兵也”,认为这是“王德”的表现,并感伤宋襄公“有王德而无王佐也”[3](僖公二十二年),“守正履信,属为楚所败”[3](僖公二十三年)。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与楚成王盟会,宋公守信而来,楚王却执宋公以伐宋,何休以宋公“守信见执”而直斥楚王“无耻”。
对诸侯的背信失信,何休也都给予了贬斥。成公三年“及孙良夫盟”,何休说:“《诗》曰:‘君子屡盟,乱是用长。’二国既修礼相聘,不能相亲信,反复相疑。”[3](成公三年)指出诸侯之间屡屡盟会,恰恰反映了当时诸侯屡屡失信,互相之间不信任的现实。成公六年“取专阝”,专阝乃邾娄之邑,而上年十二月鲁刚与邾娄有虫牢之盟,何休谴责鲁成公“背信亟也,属相与为虫牢之盟,旋取其邑”[3](成公六年)。襄公二十七年“卫杀其大夫甯喜。卫侯之弟鱼专出奔晋”。卫献公让公子鱼专与甯喜缔约,甯喜迎献公回国,献公复位后却杀了甯喜,何休一再谴责“献公无信”、“卫侯衎不信”[3](襄公二十七年)。
此外,君主还应有纳谏和自省之德。
何休要求君主要善于纳谏,他批评宋襄公“欲行霸事,不纳公子目夷之谋,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见执,六年终败”[3](僖公十六年),惋惜鲁昭公不从子家驹所谏“当先去以自正”之言,“卒为季氏所逐”[3](定公二年)。君主还应当保持自省,经常自我检视“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荣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3](桓公五年)还要善于悔过。何休夸赞秦缪公说:“秦缪公自伤前不能用百里子、蹇叔子之言,感而自变悔,遂霸西戎,故因其能聘中国,善而与之,使有大夫。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此之谓也。”[3](文公十二年)又夸赞鲁僖公说:“僖公得立,欣喜不恤庶众,比致三年,即能退辟正殿,饬过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狱四百余人,精诚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善其应变改政。”[3](僖公三年)
在何休那里,国家的盛衰安危首先就维系在君德上。僖公元年“邢迁于陈仪”,何休认为:“时邢创畏狄兵,更欲依险阻。……王者封诸侯,必居土中,所以教化者平,贡赋者均,在德不在险。”德比险阻更可凭恃,这里更有一种“德者天下无敌”的意味。他提醒君主在日常生活中“当修文德”[3](僖公二十八年),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崇礼乐、养仁义。他说:“礼乐接于身,望其容而民不敢慢,观其色而民不敢争,故礼乐者,君子之深教也,不可须臾离也。君子须臾离礼,则暴慢袭之;须臾离乐,则奸邪入之,是以古者天子诸侯,雅乐钟磬未曾离于庭,卿大夫御琴瑟未曾离于前,所以养仁义而除淫辟也。”[3](隐公五年)
二 为政之道
稳定有序的政治秩序,何休认为这是为政的首要问题。他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3](隐公元年)天下一统于王,王拥有统理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又说:“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3](隐公元年)王者上承天命而统领天下,诸侯上承王命而统领一国,“王者以天下为家”[3](隐公元年),诸侯“以一国为家”[3](定公十二年),诸侯尊王,大夫尊君,上下各安其位,各守其礼,这也就是何休所提的“大一统”的政治秩序。
东汉末年皇权旁落,外戚、宦官两大集团血雨腥风争权不止,政治昏乱,社会动荡,民变四起,统一的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这也是何休汲汲于“大一统”的现实原因。他强调“政不由王出,则不得为政”[3](隐公元年),主张强化君主集权。
襄公十六年,“三月,公会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娄子、薛伯、杞伯、小邾娄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湨梁之盟,虽然各国诸侯都与会,但主盟者实质上却是各国的大夫。何休评论说:“诸侯委任大夫交会强夷,臣日以强,……君若赘旒然。”[3](襄公十四年)又说:“诸侯劳倦,莫肯复出,而大夫常行,三委于臣而君遂失权,大夫故得信任,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3](襄公十六年)当时君权旁落,各国大夫专政,国君就好像挂在旌旗上的饰物一样,徒有其表,就此何休强调君权绝对不能由他人代行。
何休借《春秋》史事对外戚和宦官的专权也多有指斥。文公八年“宋司城来奔”,何休说:“宋以内娶,故威势下流,三世妃党争权相杀,司城惊逃,子哀奔亡,主或不知所任,朝廷久空。”[3](文公八年)僖公二十五年“宋杀其大夫”,何休说:“宋以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政分三门,卒生篡弑,亲亲出奔。”[3](僖公二十五年)妃党也就是外戚,何休将宋国的一系列祸乱都归于外戚争权所生。襄公二十九年“阍弑吴子馀祭”,何休说:“以刑人为阍,非其人。……刑人不自赖,而用作阍,由之出入,卒为所杀,故以为戒。”[3](襄公二十九年)指出以刑余之人充当阍寺,近君左右的危险性。
何休要求强化君主集权,但他强调君主不要事必躬亲,以为“天下之君,海内之主,当秉纲撮要”[3](桓公五年),要君主注意掌控全局,把持关键,避免舍本逐末。在何休那里,君主所要专注的主要就是“德治”。强调君德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上。
他明确提出了“贵教化而贱刑罚”[3](定公元年)的德治主张,认为统治者如果不注重德治,而试图一味依靠刑罚治理天下,那就会刑愈繁而世愈乱,法愈多而治愈恶。他说:“古者,肉刑:墨、劓、摈、宫,与大辟而五。孔子曰:‘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 巧奸伪多。’”[3](襄公二十九年)三皇、五帝根本不用刑罚而天下太平,后世刑罚繁多却仍是“黠巧奸伪多”,孰优孰劣,一目了然。何休谴责鲁隐公“设苛令急法以禁民”[3](隐公五年),将僖公十九年梁“鱼烂而亡”说成是“隆刑峻法”的后果。他说:“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国之中,无不被刑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状若鱼烂。鱼烂从内发,故云尔。著其自亡者,明百姓得去之,君当绝者。”君主治国当以道德感召百姓,严刑峻法只能使民心背离,使国家陷于危机,这与孔子所说的“子为政,焉用杀”[4](颜渊)的“德治”主张是相当一致的。
以德治国,首在“重爱民命”[3](僖公四年)。何休把民众看成是国家兴亡的根本力量和治国的关键所在,提出了“诸侯国体,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3](僖公七年)的思想,表明了“恶国家不重民命”[3](僖公二十五年)的态度。他谴责君主“无恻痛于民之心”[3](桓公十四年)、“视百姓之命若草木,不仁之甚也”[3](僖公二十六年),认为君主有“怀保其民”[3](桓公十一年)和使“百姓安土乐业”[3](桓公三年)的政治责任,民心向背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一旦“民人将去,国丧无日”[3](桓公三年)。因此君主应当多为百姓着想,要“忧民之急”[3](桓公五年),不要一味只顾自己享乐。庄公三十一年“筑台于郎”,何休说:“登高远望,人情所乐,动而无益于民者,虽乐不为也。”他告诫君主不要“奢泰妨民”[3](成公十八年)和“动扰不恤民”[3](襄公八年)、“费重不恤民”[3](定公七年)。
何休提出了“民食最重”[3](庄公七年)的政策主张,以民食为国家安定的根本要素。他指出:“民以食为本也。夫饥寒并至,虽尧、舜躬化,不能使野无寇盗。”[3](宣公十五年)又说:“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复兴,危亡将至。”[3](宣公十年)民以食为天,民食出了问题,国家必乱。他呼吁君主“当奉顺四时之正”[3](隐公六年),不夺农时;同时注意分别土地,教民因地制宜地耕稼,所谓“地势各有所生,原宜粟,隰宜麦,当教民所宜,因以制贡赋”[3](昭公元年),保证和促进农业生产。在保证农业生产的同时,还要关注粮食储备和荒政。他说:“三年耕余一年之畜,九年耕余三年之积,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储,虽遇唐尧之水,殷汤之旱,民无近忧,四海之内莫不乐其业。”[3](宣公十五年)国家有充足的粮食储备,有能力抵御灾害,同时统治者再“当自省减,开仓库,赡振之”[3](宣公十年),这样“虽遇凶灾,民不饥乏”[3](庄公二十八年),民众仍然可以安居乐业;而如果没有储备,像鲁庄公那样“享国二十八年,而无一年之畜”,国家则必然“危亡切近”[3](庄公二十八年)。
何休还要求君主“薄赋敛”,减轻人民负担,主张“税民公田,不过什一”[3](哀公十二年)。他讥刺鲁宣公“初税亩”超出什一是“奢泰多取于民,比于桀也”[3](宣公十五年),批评鲁哀公“空尽国储,故复用田赋,过什一”。他说:“赋者,敛取其财物也。言用田赋者,若今汉家敛民钱,以田为率矣。”[3](哀公十二年)可见,说的是鲁国的事情,矛头却直指东汉之世。他引《论语》“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宣公十年)之言,提醒君主,减轻对人民的赋税搜刮,只有百姓富足了,君主之用才能有保证。对正常的赋税,何休还是予以肯定的,他认为“赋敛不足,国家遂 虚”[3](宣公十三年),是“社稷宗庙百官制度之费”[3](宣公十五年)所必需的。
此外,君主还要关心民众疾苦,倾听下层意见,懂得“刍荛之言不可废”[3](成公二年)。何休主张君主为了解民情,应该亲自巡守:“王者所以必巡守者,天下虽平,自不亲见,犹恐远方独有不得其所,故三年一使三公绌陟,五年亲自巡守。”[3](隐公八年)他甚至还为君主设计了一个体察民情的机制:“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3](宣公十五年)
桓灵之时,“天下饥谨,帑藏虚尽”[1](冯绲传),国库空虚,连年灾荒,国家无力赈济,饿殍遍地,而统治者不顾百姓死活,依旧挥霍无度,竭泽而渔地搜刮百姓,“百姓莫不空单”,又“告冤无所”,纷纷“聚为盗贼”[1](贾琮传),一场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已经暗流涌动。何休这一系列建议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德治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尊贤、用贤,无德小人当道政治也不会稳定。何休强烈主张“达贤者之心”[3](襄公七年)、“通贤者之心,不使壅塞”[3](僖公二十八年)和“深抑小人”[3](桓公二年)。他提出,君主应当礼敬贤者,为人才提供宽松的环境,这样才能吸引各种贤才,使天下诚心归附。他说:“古者刑不上大夫,盖以为摘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刳胎焚天,则麒麟不至。刑之则恐误刑贤者,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贤者之类也。”[3](宣公元年)又说:“礼,盛德之士不名,天子上大夫不名。《春秋》公子不为大夫者不卒,卒而字者,起其宜为天子上大夫也。孔子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3](宣公十七年)
东汉末年,“正直废放,邪枉炽结”[2](党锢列传),包括何休本人在内的正直贤臣纷纷遭到禁锢,不得进用,而佞幸小人却窃踞高位,朋比为奸擅权祸国。对此何休有着切肤之痛,他说:“春秋时,废选举之务,置不肖于位,辄退绝之,以生过失。至于君臣忿争出奔,国家之所以昏乱,社稷之所以危亡。”[3](隐公元年)何休极言不选贤举能、“置不肖于位”的危害,强调这是导致国家昏乱、社稷危亡的祸根。
何休大力宣扬选举制,提倡“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3](隐公三年)和“士以才能进取,君以考功授官”[3](宣公十五年)。他还提出:“诸侯三年一贡士于天子,天子命与诸侯辅助为政,所以通贤共治,示不独专,重民之至。大国举三人,次国举两人,小国举一人。”[3](庄公元年)
对于那种父子相承官职的世卿现象,何休非常痛恨,认为这造成了“贤者失其所,不肖者反以相亲荣”[3](桓公二年)的恶性局面。他对世卿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则正其本。”[3](隐公三年)认为世卿必然导致君权衰落,最终引发臣子擅立君上乃至篡弑君上之祸。他还彰显世卿的危害说:“王者尊莫大于周室,强莫大于齐国,世卿尤能危之。”[3](宣公十年)
何休指出,世卿之所以能在春秋之时造成那么大的危害,主要就在于当时“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贵亲亲”[3](文公元年)。我们注意到,何休提出的王者治理天下的五大原则:贵有德、贵臣、贵老、敬长、慈幼,实际上原本为曾子之说,其原始面貌为“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有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6](孝行)。何休把曾子原先所说的“贵贵”转换成了“贵臣”,抽离了其中爱敬贵戚的内容,由此也突显出何休对血缘贵族政治的警惕。
三 君臣关系
何休认为孔子作《春秋》是要“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3](隐公元年),就是要通过处理好各种人伦问题,使社会回归秩序。君臣关系是君主政治结构的核心,又居于“五伦”之首位,这注定君臣之大伦是维护政治秩序的重中之重的问题。因此何休对“别君臣之义”[3](庄公二十九年)尤为加意,提出“君臣之义正,则天下定矣”[3](庄公二十九年),“君臣和则天下治”[3](隐公二年),认为君臣关系关乎国家的盛衰、社会的稳定,渴望一种良性、和谐的君臣关系。
别君臣首先就是“别尊卑,理嫌疑”[3](闵公二年),明确君臣的上下分际,确立君尊臣卑的政治伦理。东汉末年臣强君弱,皇帝受制于权臣,甚至有弑君之祸,汉质帝即为梁冀毒杀。感于时局,何休对“君道微,臣道强”[3](宣公十七年)极为警惕,疾呼“国君当强”[3](庄公十年)和“抑臣道”[3](襄公三十年),有针对性地提出“臣顺君命”[3](宣公元年),“君不可见挈于臣”[3](僖公二十五年),“臣不得壅塞君命”[3](僖公二十八年),甚至“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3](宣公六年),主张为人臣者应该尽忠君主,不得心怀异志。他表彰荀息“一受君命,终身死之”[3](僖公十年);称赞公孙归父在宣公死后,“不以家见逐怨怼”,还尽臣子哭君之礼,“终臣子之道”[3](宣公十八年);称赞蔡季在蔡侯封人死后,“归反奔丧,思慕三年”,对蔡侯封人曾欲疾害自己“卒无怨心”[3](桓公十七年)。
何休继承《公羊传》“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仇,非子也”[3](公羊传·隐公十一年)的主张,以复君父之仇为臣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隐公四年“卫州吁弑其君完”,而后“卫人杀州吁于濮”,何休说:“国中人人得讨之,所以广忠孝之路。”隐公十一年“公薨”,何休说:“臣子不讨贼当绝,以君丧无所系也。”宣公五年“孙叔得臣卒”,何休说:“知公子遂欲弑君,为人臣知贼而不言,明当诛。”非但弑君,作为臣子知道有弑君的事情要发生而不揭发检举的,即与弑君同罪。
何休之时,“三纲”之义已确立两百多年,且东汉末年皇帝时见挈于外戚、宦官,何休宣扬“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之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他“大一统”政治模式的要求。但何休并没有像董仲舒那样认为“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7](阳尊阴卑),完全取消臣子的独立人格,他还是主张君臣之间能建立起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从这个方面来讲,何休的伦理思想更接近于原始儒家。如他提出君主要“贵臣”、“尊贤”,强调“臣拜然后君答拜”、“天子为三公下阶,卿前席,大夫兴席,士式几”[3](宣公六年)以及“臣于君而不名者有五”[3](桓公四年)等先秦君臣古礼,都是要求君主对臣子尊重和礼敬的一种体现。 他提出 “君臣相与言不可负”[3](僖公十年),也或多或少地把君臣关系摆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
何休明确地主张,臣子对待君主的态度以君主对待臣子的态度为前提,以为“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3](隐公元年)。这明显保留了孟子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8](离娄下)的君臣观念,只是没有孟子那般激烈。
何休还非常可贵地提到了君臣之间的“朋友之道”。《公羊传》在讲伍子胥复仇时有“复仇不除害,朋友相卫而不相迿,古之道也”之文,本来讲的是先秦时期人们复仇的一条规则,即复仇的对象只能限于仇人本身,而且复仇的主体也只能是被害者的儿子,朋友可以帮忙但却不能抢在孝子的前面。而何休却由此做了发挥:“时子胥因仕于吴为大夫,君臣言朋友者,阖卢本以朋友之道为子胥复仇。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3](定公四年)伍子胥为臣,阖卢为君,阖卢为伍子胥出兵楚国居然是为了帮朋友复仇。也就是说,君臣之间是可以像朋友一样相处的。何休还引述孔子的朋友交往之道做注脚,更烘托了阖卢与伍子胥君臣之间的朋友关系。将君臣与朋友相提并论,这即使在先秦也是相当罕见的,唯有埋藏地下两千多年的郭店楚简中有“君臣,朋友其择者”、“友,君臣之道也”[9](语丛一)这样的说法。这无疑是何休君主论中的一大闪光点。
何休更坚持了孔子“以道事君”的观念,以道义来统摄君臣之间的关系,提出“仕为行道,道不行,义不可素餐”,也就是臣子事君是为了实践儒家的道义,是以君讲道义为前提的,如果君不讲道义,那臣就可以选择结束彼此之间的君臣关系,弃君而去。庄公二十四年曹羁“三谏不从,遂去之”[3](庄公二十四年》,何休说:“孔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此之谓也。谏必三者,取月生三日而成魄,臣道就也。不从得去者,仕为行道,道不行,义不可素餐,所以申贤者之志,孤恶君也。”[3](庄公二十四年)认为对待恶君,臣子三次进谏就尽到了臣子的责任,然后可以“谏不从而去之”[3](定公八年)。
宣公十七年“公弟叔肸卒”,何休说:“贤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禄,终身于贫贱。故孔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此之谓也。”对于无道之君,可以选择保持距离,不合作,隐居不仕。
何休进而提出,对于无道之君,臣民甚至可以奋起反抗,肯定了人民诛除“失众”的无道之君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如他评论鲁桓公的所作所为时说:“若桓公之行,诸侯所当诛,百姓所当叛”[3](桓公三年),所谓“百姓所当叛”,就是承认臣民有革命的权力。何休评论晋灵公之死是“灵公无道,民众不悦,以致见杀”[3](宣公六年),评论莒纪公之死是“一人弑君,国中人人尽喜,故举国以明失众,当坐绝也”[3](文公十八年),评论薛伯比之死是“失众见弑,危社稷宗庙”[3](定公十二年),评论莒犁比公密州之死是“密州为君恶,民所贱,故称国以弑之”[3](襄公三十一年)。“无道”、“为君恶”、“危社稷宗庙”、“民众不悦”、“民所贱”的君主必定“失众”,丧失民心支持,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这样的君主被弑,结果是“国中人人尽喜”。可见,何休把无道之君排除在了臣子尽忠的范围之外。对于祸国殃民的无道之君,何休认为人人得而诛之,这与孟子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8](梁惠王下)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
此外,在“国重君轻”[3](桓公十一年)思想的指导下,何休主张臣子对国家的责任要高于对君主的责任。桓公十一年,郑国权臣祭仲受宋国胁迫,拥立厉公突,逼走昭公忽。何休赞赏祭仲“虽病逐君之罪”,但“保有郑国,犹愈于国亡”,是“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也”,存国之功大于逐君之罪。何休还将祭仲逐昭公比作伊尹放太甲,他说:“汤孙大甲骄蹇乱德,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宫,令自思过,三年而复成汤之道。前虽有逐君之负,后有安天下之功,犹祭仲逐君存郑之权是也。”可见,在何休的考量中,国家利益、天下的安定,远在君位和君主个人的安危荣辱之上。
毋庸置疑,作为公羊学大师的何休,其君臣观念很多是承袭自《公羊传》的。《公羊传》的君臣观念大体上反映的还是先秦儒家的观念。[10]而随着君主专制的逐渐强化,到了何休那里,显然已经无法完全秉持《公羊传》的君臣观念了。我们知道,《公羊传》有一个很特异的主张就是臣可向君复仇,明确对伍子胥向楚王报杀父之仇表示赞同,表示“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3](公羊传·定公四年)。而何休在这个问题上明显与《公羊传》产生了距离,何休在解释《公羊传》这句话时说:“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于义得去,君臣已绝,故可也。”[3](定公四年)把臣可对君复仇限定为了诸侯君臣间的特例。由此我们也看出,何休所说的臣子于义可去的对象实际上是不包括天子在内的。与天子的君臣关系既然是不可解除的,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想见,在何休那里,臣民革命的对象实际上也是不包括天子在内的,而只是限于诸侯之君。
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纣就是天子;《公羊传》讲“子复仇可也”,也是没有区分天子、诸侯。何休自己也曾说:“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3](隐公元年)但他在君臣关系问题上却编织了一道防护网,将作为天子的君主与作为诸侯的君主做了区隔。这是何休在历史条件已经改变的情况下,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同时也是一种精心设计。藉由这道防护网,何休可以不用顾虑太多政治束缚,继续阐述先秦儒家的那种君臣观念,又不会对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冲击,为理想在现实之中找到栖身之所。
四 君位传承
君位传承是君主政治的一项重要内容,直接关系到政局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很多王朝到了末年,都会在君位传承方面出现问题,引发政局动荡,恶化本已经弊乱丛生的政治环境。东汉末年亦是如此,质帝、桓帝、灵帝皆为外戚所擅立,以支庶而登帝位,从而母后称制、权奸秉政伴随东汉王朝走向衰亡。
何休目睹东汉末年的这一乱局,非常渴望能建立起一套运行良好的君位传承制度。首先,他认为最理想的君位传承应该是坚持嫡长继承制。在解释《公羊传》“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时,他说:
適,谓適夫人之子,尊无与敌,故以齿。子,谓左右媵及侄娣之子,位有贵贱,又防其同时而生,故以贵也。礼,嫡夫人无子,立右媵;右媵无子,立左媵;左媵无子,立嫡侄娣;嫡侄娣无子,立右媵侄娣;右媵侄娣无子,立左媵侄娣。质家亲亲,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侄。嫡子有孙而死,质家亲亲,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孙。其双生也,质家据见立先生,文家据本意立后生。皆所以防爱争。[3](隐公元年)
何休详细叙述了君位继承人的顺位,最为关键的是他深刻地指出了这套制度背后的意义所在——“皆所以防爱争”,就是为了防止君位继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纷争,消弭可能引发的政治动乱,使权力能够顺利传承,维护统治秩序。正如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所指出的:“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所以求定而息争也。”王国维还指出何休叙述的这套制度过于详密,“顾皆后儒立类之说,当立法之初,未必穷其变至此”。[11]也就是说,何休所说的很可能并非真是古礼,他这种几乎穷尽各种可能的继承人身份的叙述,更突显了他对一套严密的传承制度的渴望。越严密的制度,可以越明确地把继承人限制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还在解释“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3](公羊传·庄公十九年)的制度的时候说:“必以侄娣从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妒,令重继嗣也。”[3](庄公十九年)认为这也是从维护继嗣稳定的角度所做的安排。
当然,最好状况是“国有正嗣”[3](桓公六年),即存在嫡长子。这样依据“立嫡以长”[3](昭公二十年),可以非常明确大位所属,一步就解决传承过程。桓公六年,“子同生”,何休说:“本所以书庄公生者,感隐、桓之祸生于无正,故喜有正。……礼,世子生三日,卜士负之寝门外,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当有天地四方之事;三月,君名之,大夫负朝于庙,以名徧告之。”鲁惠公没有嫡子,这埋下了后来桓公弑隐公的祸根,因此桓公的嫡长子公子同(庄公)的诞生,使鲁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避免了因君位传承引发的动荡。何休强调这对鲁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喜事,也是一件非常隆重的事情。
其次,君主应该在生前尽早确立储嗣,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名分不定产生的纷争。文公十四年“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何休认为:“潘立储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临葬更相篡弑。”指出商人弑舍篡位,就是因为齐昭公潘在立嗣问题上犹疑不决,未能在生前确立储嗣。
尤其很多时候潜在的继承人之间尊卑贵贱的身份差异很小,先后次序并不好确定,则会更容易引起纷争。文公十三年,邾娄文公薨,其二子玃且、接菑争位。何休指出,玃且、接菑“俱不得天之正性”,皆非嫡子,而“二子母尊同体敌”,难分贵贱。最后虽然以“以年长故”[3](文公十四年)玃且获立,但邾娄还是经历了一场动荡,晋国甚至出兵逼邾娄纳接菑,国家一度陷于危机之中。
鲁隐公和鲁桓公兄弟之间也属于这种“尊卑也微”[3](公羊传·隐公元年)的情况,他们的母亲只是左、右媵的区别,尊卑并不明显。按制度是桓公应继位,但他们的父亲鲁惠公死的时候,桓公尚年幼,于是诸大夫“废桓立隐”,终致十几年后桓公弑隐公之祸。何休指出,真正的祸根即在于“惠公不早分别也”,是惠公没有在生前确立嗣君。他提出:“男子年六十闭房,无世子,则命贵公子。将薨亦如之。”[3](隐公元年)在没有当然的嫡长子的情况下,君主必须在年满六十岁或临终之时指定好嗣君。
君主如果生前未能指定嗣君,除了潜在的继承人争位的危险,往往还会使君位废立之权沦于臣子之手,进而造成君权旁落等一系列更大的政治祸乱,而这也是何休更为警惕的。他评论卫襄公说:“世子辄有恶疾,不早废之,临死乃命臣下废之。自下废上,鲜不为乱。”[3](昭公七年)“自下废上,鲜不为乱”,这是何休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愤感慨。
我们从何休对隐公四年“卫人立晋”的态度更可以发现他对“自下废上”的防范。何休说:“晋得众,国中人人欲立之。凡立君为众,众皆欲立之,嫌得立无恶,故使称人,见众。言立也,明下无废上之义,听众立之,为立篡也。”[3](隐公四年)州吁被诛后,卫人迎立公子晋。何休认为,虽然公子晋有民意,被立为君没有什么过恶,但臣子立君从根本上讲是不能允许的,即便是人心所向,也跟篡位一样是没有合法性的。
最后,君主立嗣一定要遵循正当、正道。君主早定储嗣,固然可以减少纷争,但如果不坚持“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一样会招来祸患。何休指出:“废正当有后患。”[3](僖公十年)君主如果背离嫡长子继承制的正道,一定会后患无穷。僖公五年,晋献公为立骊姬之子,杀世子申生,庶子重耳、夷吾逃亡。献公死后,晋国大乱,骊姬之子奚齐、卓子虽先后得立,但先后被弑,于是惠公夷吾立,惠公死后文公重耳又返国与侄子怀公圉争位。晋国祸乱一直延续到十几年后,晋献公杀嫡立庶真可谓后患无穷。
宋国之乱也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宋宣公以其弟缪公贤能,于是不传子而传弟。缪公又感念兄恩,也不传子而传给了宣公之子与夷,最终缪公的儿子庄公冯弑殇公与夷。何休评论说:“言死而让,开争原也”,“死乃反国,非至贤之君不能不争也”。他认为,缪公虽贤,但宣公破坏了传承制度,不传子而传弟,相当于开启了一个纷争的开关,缪公又递相沿袭,以至酿成了宋国的祸乱。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嗣子,除非是圣贤,很难不会去夺回本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样祸乱也就终难避免。据此何休极力强调:“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3](隐公三年)这也就是《公羊传》“大居正”之说,即尊尚守正,强调正当、正道的重要性。
五 结 语
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总结治乱盛衰之由,一直是历代公羊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何休生当末世,天下板荡,因此他对社会安定用意尤深。而在君主专制社会中,君主是国家和社会的核心,君主的德行、施政方略、君臣关系以及君位传承等与君主相关的问题,都会对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借助经典资源,总结《春秋》史事的历史经验教训,阐发了一套具有公羊学特色的君主论思想。他要求君主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以道德感召和安定天下,尤其注重君主在孝、廉、信等方面表率天下的德行。他呼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警惕君权旁落和权臣专政的风险,提倡德政,反对暴政,强调重民恤民和选贤举能。他渴望君臣之间能建立一种良性和谐的关系,在明确君臣上下分际的前提下,主张“以道事君”,强调君臣之间互相的责任与义务,甚至提出君臣之间存在“朋友之道”。他坚持以嫡长继承制为君位传承的正道,主张早定名分消弭纷争,反对“自下废上”。他的君主论思想饱含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郑任钊.论《春秋公羊传》对社会秩序的追求[J].炎黄文化研究,2013,(15):110-125.
[3]何休解诂 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5]唐玄宗注 邢昺疏.孝经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张双棣等.吕氏春秋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赵岐注 孙奭疏.孟子注疏[M].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9]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0]郑任钊.《春秋公羊传》的君臣观念[J].前沿,2010,(22):24-27.
[11]王国维.殷周制度论[A].观堂集林[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