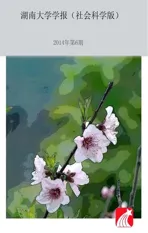《达摩流浪者》
——杰克·凯鲁亚克的一本献给美国寒山的小说*
2014-03-31谭琼琳
陈 登,谭琼琳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达摩流浪者》
——杰克·凯鲁亚克的一本献给美国寒山的小说*
陈 登,谭琼琳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在基于史料的基础上,从变异学角度论述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半自传体虚构小说《达摩流浪者》是如何将中国唐朝诗僧寒山的神秘东方形象、《寒山诗》译者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与主人公贾菲·赖德合为一体的。通过文化迁移的作用,作者成功地将主人公赖德变异,塑造为小说中的美国垮掉派反主流文化的英雄偶像,从而使得现实中的斯奈德成为美国寒山的杰出代表,也使得这本小说不仅是作者献给中国寒山的书,也是一本献给美国寒山的书。
杰克·凯鲁亚克 ;《达摩流浪者》 ; 加里·斯奈德;寒山;美国寒山;变异
《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1958;亦译为《得道流浪汉》或《法丐》)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垮掉一代之王”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一本颇带有半自传体性质的虚构小说。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发生的时间和描述的事件基本上源自于当时垮掉派作家和“旧金山文艺复兴”(“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诗人之间,或者说美国东、西海岸作家圈之间交流的亲身经历。这主要指在肯尼斯·雷克罗斯(Kenneth Rexroth,自取中文名王红公,后被尊奉为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之父)的建议下,来自纽约东海岸的作家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于1955年9月会见了当时正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的校园诗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他们商议10月在旧金山筹备一次新诗朗诵会。金斯伯格和斯奈德分别力荐各自的朋友凯鲁亚克和菲利普·惠伦(Philip Whalen),加上旧金山文艺复兴诗人雷克罗斯、迈克尔·麦克卢尔(Michael McClure)和菲利普·拉曼蒂(Philip Lamantia)一起共同举办了震撼西方诗坛的“第六画廊诗歌朗诵会”(“Gallery Six Poetry Reading”)。[1](p145-148)这次诗歌朗诵会标志着东、西海岸“垮掉一代”作家的第一次融合,并被广大听众、艺术家、评论家、教授所接受。尽管旧金山诗人,如:斯奈德、惠伦、劳伦斯·费林格蒂(Lawrence Ferlinghetti)等并不承认自己是垮掉派作家,[2](p2)但不可否认,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们皆归属于这两种文化的交集圈里,即:“旧金山垮掉派现象”(“San Francisco Beat Scene”)。特别是“第六画廊诗歌朗诵会”之后,当时美国文坛的四股文学力量进行会合,以旧金山为地域中心,展开了一系列创作革新实验活动,形成了50年代中、末期一种奇特新颖的文学交汇现象。这种新型的文学力量聚集包括垮掉派主要作家,如: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威廉姆·伯勒斯(William S. Burroughs)、尼尔·卡萨迪(Neal Cassady)、格雷戈里·科尔索(Gregory Corso);西海岸核心作家,如:斯奈德、惠伦、卢·韦尔奇(Lew Welch);黑山派主要作家,如:查尔斯·奥尔森(Charles Olson)、罗伯特·克雷利(Robert Creeley)、罗伯特·邓肯(Robert Duncan);以及纽约派诗人,如: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等。[2](p1-3)
有趣的是,凯鲁亚克将这一文化现象过程中所发生的零星事件宛如珍珠一样串起来集中表现在《达摩流浪者》的叙事里。凯鲁亚克以《寒山诗》(Cold Mountain Poems)的译者——美国诗人斯奈德为小说主人公贾菲·赖德(Japhy Ryder)的创作原型,以“1955年第六画廊诗歌朗诵会”为交汇起点所形成的“旧金山垮掉派现象”作为主要历史背景,通过“视觉想象”(“visualization”)和“变异”(“acculturation”)的手法,在《达摩流浪者》中将斯奈德、赖德和寒山合为一体,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美国寒山的经典形象,从而使得美国诗人斯奈德和中国唐朝诗僧寒山成为美国50年代垮掉派和60年代嬉皮士反主流文化的英雄偶像。这一经典案例实质也构成了文学交流和异质阐发中的一个有趣的“他国化”现象问题。在比较文学变异学研究领域中,“他国化指一国文学在流传到他国,由于文化观念、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等异质性因素,再通过译介、过滤、接受或阐发之后,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异,即传播国文学本身的文化规则和文学话语在根本上被接受国所同化,从而成为他国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3](p30)本文从变异学角度出发,就思想、内容和人格三种变异形式,综合论述《达摩流浪者》这部小说是如何将斯奈德塑造成为“美国寒山”这一奇特文化的迁移现象,揭示出《达摩流浪者》不仅是一部献给中国寒山的小说,而且也是一部献给美国寒山的小说。
一 寒山、斯奈德与凯鲁亚克的历史交汇
1955年9月8日,当金斯伯格和斯奈德初次见面时,斯奈德欣然接受邀请参加新诗朗诵会,并提出了两个请求:一是让他的同窗好友惠伦参加;二是让雷克罗斯主持。对于这两个请求,金斯伯格自然不会持任何异议,因为他原本就是拿着当时美国诗坛领袖威廉姆·卡洛斯·威廉姆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推荐信前往旧金山拜谒雷克罗斯,并在雷克罗斯的建议下,前往伯克利与斯奈德见面的。在交谈过程中,金斯伯格惊讶得知威廉姆斯早已和伯克利校园三位诗人斯奈德、惠伦和韦尔奇见过面。于是,金斯伯格也向斯奈德推荐他的好友凯鲁亚克参加新诗朗诵会。筹备期间,他们四人于9月23日星期五晚上在旧金山首次聚集,参加了雷克罗斯家里的诗歌沙龙会。那天晚上,凯鲁亚克朗诵了他的散文片断,“铁路大地上的十月”(“October in the Railroad Earth”)。斯奈德首次领略了凯鲁亚克的散文风格,认为“他是一个真正有天赋的作家,那特有的清新语言感将改变我们的散文写作方式”。[1](p146-147)*文中所有英语引文翻译均为自译。这就是评论家后来称誉的“一触即发式/自发式的写作风格”(“spontaneous writing style”),即:“在半疯癫的状态下进行的无意识写作,使下意识处于一种必要的有趣、无羁绊的状态,这样‘现代的’语言受到有意识艺术的审稽”。凯鲁亚克认为,“这种无限制的艺术写作方式在最大程度上能将时空连续统一体中思想流动的过程全部临摹下来”。[2](p44-45)
在10月13日举行的“第六画廊诗歌朗诵会”上,雷克罗斯介绍了上面提到的六名年轻诗人。凯鲁亚克因害羞而谢绝上台朗诵的邀请,只是在台下帮忙叫喊着、张罗着。真正吸引在场观众眼球的是金斯伯格朗诵的“嚎叫”(“Howl”),因为这部诗作发出了一种与时代迥然不同的声音。著名垮掉派评论专家约翰·霍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声称“它带有一种思想的裸露,绝对来自灵魂的深处”;“那是一种只留有最基本意识的感觉”。[4](p3)斯奈德朗诵了一首神话诗“莓宴”(“A Berry Feast”)、神话长诗《神话与文本》(Myths & Texts)中的部分片断和一些寒山译诗。[1](p155) [5](p3-4)对于这次新诗朗诵会的历史意义,斯奈德曾谦虚地预言道,“有一天它将值得一提”。[1](p156)的确,这次历史事件不仅拉开了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而且也奠定了垮掉派作家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同时,它也标志着寒山正式进入美国大众的视线。朗诵会结束后几天,凯鲁亚克前往斯奈德的住处进行拜访,吃惊地发现斯奈德过着比梭罗更为简洁的苦行僧生活,房间里没有椅子,没有床,只有一个充气的帐篷睡袋,上面盖着一块美洲豹皮。[1](p161)斯奈德给凯鲁亚克看了他正在翻译的寒山诗歌,打算去日本之前尽快完成他选修陈世骧教授的中文课所布置的作业。一年前,斯奈德曾翻译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及李白、孟浩然的诗歌,深得陈世骧教授的赏识。当斯奈德提出要翻译稍带白话文的佛教诗歌时,陈世骧教授向他推荐了寒山诗。凯鲁亚克完全被对方的才华和寒山似的简朴生活方式所吸引,因为在斯奈德身上,他看到了中国古代隐士、佛教与美国梭罗、流浪汉的某种神秘关联,而这恰好又是凯鲁亚克和他的朋友不断“在大路上”(“on the road”)奔波流浪的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斯奈德的真实生活方式也促使凯鲁亚克在小说中自然将寒山与斯奈德进行综合比较叙述,最后按照自己的想象和文化移植,穿越时空将他们合为一体。
尽管我们可以断言“第六画廊诗歌朗诵会”见证了寒山、斯奈德与凯鲁亚克的第一次历史交汇,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早在遇见斯奈德之前,凯鲁亚克就研读过寒山、梭罗和部分大乘佛教的教义。1954年,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翻译了27首寒山诗,发表在《相遇》(Encounter)杂志上。[6](p3-8)1955年,斯奈德翻译24首寒山诗时也参看了韦利的译文,1956年去日本后进行了修改,1958年在《常青藤评论》(Evergreen Review)杂志上发表。[7](p68-80)根据凯鲁亚克1956年完成但迟至1997年才出版的《佛法札记》(Some of the Dharma),我们可以读到他当时的笔记里有一句话:“像寒山一样”(“Be like Han Shan”)。[8](p311)1953年,因担心血瘤危及性命,为了静心,凯鲁亚克在图书馆里阅读梭罗的《瓦尔登湖》(Walden),然后根据梭罗提供的一些佛教参考书目,开始涉猎一些大乘佛教的经书,如:《金刚经》、《坛经》、《楞伽经》,并作了大量的笔记,后在斯奈德的鼓励下编辑成《佛语》(Buddha Tells Us)和《佛法札记》。德怀特·戈达德(Dwight Goddard)编写的《佛教圣经》(A Buddhist Bible)也一直陪伴他多年。根据凯鲁亚克的传记作家杰拉尔德·尼科西亚(Gerald Nicosia)的记载,“《金刚经》起到了魔法的作用,驱走了他心中的无名恐惧感”。[9](p458)因此,在与斯奈德会面之前,凯鲁亚克就决心将佛教作为“一种新的标准”来发展“垮掉哲学和风格”(“the Beat philosophy and style”)。[10](p196-222)凯鲁亚克的这种观点和态度影响了他身边的朋友,如:卡萨迪、伯勒斯、金斯伯格、科尔索等。1955年当他开始撰写《杰勒德回忆》(Visions of Gerard),一本关于其幼年死去的哥哥的传记作品时,凯鲁亚克发现毒品不能再帮助他进入超然的境界,因此他转而求助于佛教的冥想。在这种背景状况下,对凯鲁亚克来说,与斯奈德的见面意味着其人生的一大转折,更加坚定了他对佛教的挚爱与系统研习。斯奈德与寒山的某些相似性,如:写诗会友、隐遁山林、生活简朴、心境随缘、徒步流浪、逆向主流等,印证了凯鲁亚克仰仗佛教建立“垮掉哲学”的观点,因为“他想舒缓人们的压力和紧张,指导他们怎样通过冥想和祈祷来回归心灵的宁静”。[10](p196)这样,读者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凯鲁亚克在《达摩流浪者》里将寒山与斯奈德同时融入赖德主人公的描写中,在小说的结尾处幻想自己也成为了寒山似的人物,长发飘逸。[11](p190)凯鲁亚克的誓言,“像寒山一样”,使得“寒山垮掉派英雄形象”通过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在美国大众心目中潜滋暗长,而斯奈德也顺乎自然地成为了“美国寒山”的杰出代表。
二 寒山、斯奈德在《达摩流浪者》中融合的现实
如果说“第六画廊诗歌朗诵会”促使了寒山、斯奈德与凯鲁亚克的第一次历史交汇,那么凯鲁亚克作为全能叙事者在《达摩流浪者》中将寒山、斯奈德进行视象融合的源泉和动机则与凯鲁亚克、斯奈德在朗诵会结束后的一段共同生活经历有关。他们两个人在塔马佩斯山(Mt. Tamalpais)上租了一个木屋度过了将近一个月的世外桃源生活,开心地交换各自写作的经验和感想。除了因凯鲁亚克酗酒,斯奈德与他发生一点小摩擦之外,他们争论的焦点基本上在于斯奈德怀疑凯鲁亚克没有禅宗打坐的实践经历却也能凭空畅谈佛教教义。[12](p214)在斯奈德的鼓励下,凯鲁亚克于1956年很有创意地完成了一部垮掉-佛教经文《金色永恒真经》(The Scripture of the Golden Eternity)。斯奈德对该书评价很高,称赞为“在美国诗学语言之网中最为成功地阐释了佛教的空、无执著、无我的观点”。[13](p216)对于凯鲁亚克的佛教观,我们可以说他的兴趣源于他的自救心理。尽管他对禅宗打坐比较随意,但一开始他就认真热忱地对待佛教的教义。因此,“我们不能高估凯鲁亚克的佛教研究对他的生活和写作的意义。就其实质而言,凯鲁亚克的佛教观并没有从根本上与他的世界观相分离”。[14](p123)凯鲁亚克与斯奈德的零距离接触更加促使凯鲁亚克将佛教作为一个有效的精神替代品,将寒山隐遁林泉的禅宗生活方式看成是一种有效的反传统文化模式,从而让凯鲁亚克自我良好地感觉到他们这群垮掉派作家常年穿梭于美国大地的流浪生活以及去欧洲、北非、南美洲冒险的经历,甚至寻找迷幻草药之事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甚至视为一种光荣的使命感。正因如此,凯鲁亚克一边运用写实的手法在《达摩流浪者》中记载了他与斯奈德、金斯伯格、惠伦等早期垮掉派作家之间的友谊以及他们的理想、痛楚和颠沛流浪的生活,一边采取变异的手法将寒山与斯奈德合为一体,塑造出一个符合新时期使命的反传统文化的英雄偶像。在变异的过程中,由于作者本人是小说中的叙述者雷伊·史密斯 (Ray Smith)的创作原型,诱发的主观视觉想象在读者眼里似乎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事实上,这种主观叙述难免对现实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描述或多或少地会出现偏颇或失误,自然引起凯鲁亚克身边朋友的不满。比如,金斯伯格抱怨他在小说中的角色阿尔瓦·戈德布克(Alvah Goldbook)就存在着精神不一致的问题。[10](p298)
随着垮掉一代的声名鹊起,《达摩流浪者》中的人物原型和历史事件备受美国大众和评论家的密切关注,凯鲁亚克和其他垮掉派作家之间的关系宛如脱缰的野马不受控制而日趋紧张,最后凯鲁亚克不得不断绝了与这些朋友的来往。尽管如此,在《达摩流浪者》出版的前后,凯鲁亚克却特别在乎斯奈德的反应,因为这本小说的主线是围绕寒山、赖德/斯奈德和史密斯/凯鲁亚克三个半真实、半虚构的人物展开的。根据凯鲁亚克、斯奈德和惠伦的现存书信,斯奈德对这部小说的反应大致经历了三次变化。出版前,斯奈德对凯鲁亚克的写作计划有所耳闻,虽不知晓详情,但相信凯鲁亚克的艺术创作动机。在斯奈德的鼓励和建议下,凯鲁亚克将《达摩流浪者》一书献给寒山。[1](p239)出版后,斯奈德给凯鲁亚克的第一封信是1958年10月12日,字里行间充满了鼓励,没有半点生气的口吻。*凯鲁亚克和斯奈德的信件均保留在各自的档案馆里,即:凯鲁亚克资产档案馆 (the Kerouac archives of Kerouac Estate) 和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斯奈德档案馆 (the Snyder archive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关于《达摩流浪者》献给寒山一事见三封信件:凯鲁亚克于1958年6月19日给斯奈德的信件;斯奈德1958年6月30日的回函;凯鲁亚克于1958年7月14日给斯奈德的信件。斯奈德、惠伦和其他一些评论家都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本像剪贴画似的编年史故事罢了,“《达摩流浪者》一书里弥漫着耐心解释的写作风味,好像是写给一本书的编辑看的”。[15](p244)然而,当凯鲁亚克将样书首先寄给惠伦时,惠伦在1958年10月1日给斯奈德的信中特意用大写字母强烈建议他快“关门”(“BAR THE DOOR”),因为书中有关于斯奈德传授其他人体验藏佛“天地媾合/男女双修”(“yabyum”)的宗教仪式而进行的群交场面的真实描写。[1](p239-240) [11](p24-27)假若不是佛教的风行、媒体的关注和大众的追捧,斯奈德可能会一直保持冷静。由于《达摩流浪者》的影响,斯奈德被公认为“美国寒山”而成为美国年轻人的垮掉英雄偶像,这不仅包括年轻人学习他的山林流浪、禅宗打坐、诗歌写作,而且还包括向他讨教如何达到天父地母合一的性交技巧。斯奈德始料不及自己的私生活因《达摩流浪者》的出版而被侵犯,自己无意成为一代人的精神领袖而被全方位效仿。在1959年3月10日的信件里,斯奈德终于在日本打破沉寂,指责凯鲁亚克,因为在那个反传统文化的年代里,没有人会去谈论别人性交的私生活话题。有趣的是,斯奈德采用禅宗方式给凯鲁亚克开出一剂良药:“如果你来这里,我会安排你去种菜砍柴——这远比在地狱里让他们拿着烧得火红的钳子把作家的舌头拔出来要仁慈得多”。[1](p245)由于双方的努力和解释,斯奈德与凯鲁亚克最后和解,并一直保持书信联系。1969年斯奈德返回美国后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谈到他对《达摩流浪者》的看法,认为书中的他被塑造成为非常可爱的人,而现实生活中的他并非如此,书中所描述的一些真实的事件和虚构的故事全都搅混在一块,让读者分辨不清事实的真相。[16](p78)
应该说,十多年后斯奈德做出的这番评价是冷静的、公正的、客观的。凯鲁亚克因酗酒过度于1969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了大量的著作。1958年出版的《达摩流浪者》其社会和政治意义远远超过其文学审美价值,因为斯奈德翻译的《寒山诗》与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在同一年的出版给冷战后的美国青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希望,因为寒山放荡不羁、逍遥快乐、隐遁山林、呵佛骂祖的反传统文化形象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冷战期间,美国与前东欧和前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军事装备竞赛使得本已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偷袭事件、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的美国青年日趋迷惘、恐慌,认为现代的科学技术威力太大,弹指一挥间即可毁掉所有的一切,上帝也无能为力。加之,50年代初期,在艾森豪威尔-麦卡锡(Eisenhower-McCarthy)时代,许多进步人士经常受到政府不公正,甚至莫须有的亲共审查,这也促使新一代的美国青年潜意识地想摆脱主流文化,接受外来文化的熏陶。日本禅在美国的迅速传播犹如一种新的文化破土而出,既顺应当时的时势,也符合个人的理想追求。“在这种语境下,斯奈德的寒山、中国唐朝诗僧、‘山癫’成为了垮掉英雄和反传统文化角色的榜样,……而《寒山诗》译本本身,……则成为了一本冷战书”。[17](p237)凯鲁亚克的《达摩流浪者》真实地再现了这群叛逆青年的生活方式,“在加州,一个避难者惯常躲避传统束缚的港湾,他们成为了一群吟游诗人;在这里,他们追寻个人的彻底自由,尝试新兴的吸毒文化,沉迷美丽的幻想和东方宗教,崇尚群居生活”。[18](p518)《达摩流浪者》对寒山和斯奈德的错综描述和视觉想象像催化剂一样促使斯奈德变异成为了美国寒山式人物的杰出代表。
三 斯奈德:美国寒山的经典变异范例
寒山复活首先得益于斯奈德的独特选译原则和美国化语言的翻译风格。韦利的27首寒山英译诗留给读者的印象是一个集中国儒、释、道精神于一身的普通历史人物——唐朝诗僧寒山,而斯奈德的24首寒山英译诗却再现了中国隐士传统中一个隐居于疑似美国荒野的寒山,且过着忘我山癫生活的神秘诗僧——圣者寒山的形象。寒山在斯奈德译诗中的变异现象跟诗人本人从小生活在美国西部荒野山林的经历有关。钟玲教授认为这是译者的“一些特别曲解”,“带有他个人的偏见”。[19](p101-102)然而,评论家雅各布·里德(Jacob Leed)教授则提出了译文内部风格统一的不同见解,即:斯奈德译文中的寒山形象与美国内华达山脉锯齿崎岖的景致相匹配,而原诗中的寒山形象与钟玲所指的中国江南舒缓秀丽山脉景色相符合,这两者迥然不同的描写在其内部实属风格一致。[20](p179)正是这种译诗中寒山形象本土化的变异,西方读者才会欣然接受并追捧《达摩流浪者》中纪实描写与想象并存的美国垮掉派寒山形象。透过凯鲁亚克在其小说中对主人公赖德的写实描写,现实中的斯奈德自然就成为了美国寒山的化身。
故事以叙事者史密斯逃离令他感到恶心厌倦的洛杉矶城市开始,又以下山回归到他永远无法截断的尘俗世界而结尾,暗示书中的人物角色基本上都是一群在大路上奔波流浪的法丐,尚未步入精神开悟的最高禅境。史密斯把赖德看成是“他们当中的头号法丐”。[10](p10)通过赖德,史密斯逐渐了解禅宗和寒山;经过比较和观察,史密斯明白为什么寒山是赖德心目中的英雄。除了外表长相具有东方人的特征外,赖德的日常生活也烙印了中国诗僧的东方气息,如:写诗品茶、游山独居、论经说道、坐禅冥思等。史密斯与赖德的初次谈话内容就是关于寒山的生活方式和寒山诗的英译。史密斯之所以对赖德的介绍产生共鸣是因为寒山厌倦城市生活和尘俗琐事而隐居山林,而这恰恰又是他本人的真实写照,故潜意识地断定赖德宛如现实中的寒山,[10](p18)并预感赖德“将最终隐匿于山中,岩壁上写诗作赋,或岩洞外对众吟诗诵唱”。[10](p28)这一联想实际就是寒山诗句“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书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21](p314)的真实写照。作者运用这种视觉想象使得叙事者史密斯有意识地将赖德和寒山融合一体,从人格、思想和内容上开始在小说的叙事中将其变异为美国寒山的形象,并让史密斯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去效仿眼前活生生的美国寒山,追随赖德体验寒山式的禅意生活。譬如:当他们一块去登山时,史密斯惊讶赖德在山林石砾中大步跳跃的欢快动作,在他眼里,这宛如中国和日本画中的唐朝诗僧寒山、拾得长发飘逸、疯癫大笑的形象。“贾菲解释道,这种登山方式的秘诀颇似禅宗玄机,任运无思,独自飞舞”。[11](p52)在他的鼓励下,史密斯也飞奔下山,那感觉“极像一千年前中国的山癫”。[11](p68)赖德告诉史密斯,“每一座山就是一尊佛,……千百年来在那里静静地为众生祈福”。[11](p54)于是,史密斯开始全方位地效仿赖德,诸如:品饮中国绿茶、使用中国筷子、尝试中国饭菜等以求了解中国文化;在岩石上和树林里禅宗打坐、研习禅宗公案和佛教经文、登山放逐心灵等以求暂悟或顿悟。在史密斯眼里,“贾菲·赖德是一名伟大的美国文化新英雄”,[11](p27)他智慧超群、学识渊博,懂得“西藏文化、汉语、大乘佛教、小乘佛教、日语、甚至缅甸佛教的知识”。[11](p12)在与赖德接触的日子里,史密斯从最初的佩服到后来不由自主地将寒山、寒山诗与现实中的赖德、美国西部山脉进行跨越时空的联想,在大脑深处产生一种对神秘东方诗僧寒山的迷恋之情。这种视觉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史密斯潜意识地将寒山与赖德融为一体,同时也为他本人逃离喧哗的大都市后,在漫无边际的流浪大路上树立了一个清晰的目标。小说中的这些描述实际上又是基于作者凯鲁亚克对诗人斯奈德个人所具备的性格特征、生活习气和东方智慧的细致观察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中寒山和赖德的融合在叙述者史密斯的视像里已经变异为一个新的美国寒山形象,进而成为史密斯朝圣路上不断追求的目标。
小说的高潮实质为中国寒山形象被重塑为美国垮掉派英雄偶像的变异过程。这是一个解构神秘东方诗僧那种“任运遁林泉,栖迟观自在。……细草作卧褥,青天为被盖。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21](p293-294)的超凡生活过程,其目的是在美国现实社会中建构一个可供美国青年效仿的活脱脱的美国垮掉派英雄偶像。由于赖德准备离开美国远赴日本进行禅修,其原有的在华盛顿州西部卡斯卡德斯山脉(High Cascades)的孤凉峰(Desolation Peak)上担任暑期兼职林火瞭望员的工作就移交给了史密斯。小说的视角将叙事者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迅速转入到一个即将进驻“我的大山世界”中的归隐者,因此,叙事者史密斯“顿觉轻松自由,……像一名中国圣者无羁无绊,远游乌有之乡一样,欢快前往我的大山里”,[11](p170-171)其心境宛如《寒山诗》所云:“出生三十年,尝游千万里。……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21](p447)由于深受赖德的寒山译诗的影响,史密斯有意识或潜意识地将美国西部山脉与中国寒山居住的浙江天台山的自然景色糅合在一起,如:面对天气和山湖,史密斯会有“特别奇怪的感觉,仿佛置身于某种说不出的中国雾之中”[11](p172),情不自禁地发出感慨,“哦,这像中国的清晨”[11](p48);“这是贾菲的湖,而这些是贾菲的山”,并由衷地希望“贾菲能在那里看到他想要我做的一切”。[11](p180)与赖德最后相聚于山里的一个晚上,史密斯在梦境中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清晰地将寒山与赖德进行比较,通过文化迁移,赖德化身为中国流浪汉,混迹于中国古代的集市里,从而有意无意间使之变异成为一名美国寒山:
我清楚地看见一个人群熙攘、尘土飞扬、烟雾缭绕的中国集市,四周挤满了乞丐、小贩;路边摆满了驮着货物的马匹,堆满了泥巴、烟罐和垃圾;地上放满了盛着蔬菜准备贩卖的脏兮兮瓦盆。突然间,从山里走来了一个衣衫褴褛、满脸皱纹、古铜皮肤、邋遢得不可思议的中国流浪汉。……他肩背皮囊,一双赤脚,……一个比中国人穷两倍,却刚毅两倍,给人无限神秘感的流浪汉。千真万确,他就是贾菲。[11](p163-164)
如果我们将上述描述与唐朝台州刺史闾丘胤撰写的《寒山子诗集序》中关于寒山相貌的描述进行比较,不难看出贾菲就是从中国寒山形象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活脱脱的美国寒山。闾丘胤的序中描写道:
详夫寒山子者,不知何许人也。自古老见之,皆谓贫人、疯狂之士,隐居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号为寒岩。……且状如贫子,形貌枯悴。一言一气,理合其意,沉而思之,隐况道情。……乃桦皮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21](p565-566)
贾菲与寒山的融合一体在一定程度上令史密斯不得不猜想贾菲未来的命运:“或许他将离开寺庙,隐遁别处,我们再也寻他不着。他将是另一个寒山子,幽灵般出没于东方的崇山峻岭里,就连中国人见了也害怕他那布裘破敝,形貌枯悴的样子”。[11](p164)这种联想,一方面建构了一个可仿效的垮掉派美国寒山形象,但另一方面也解构了中国寒山神秘超然的圣者形象。当史密斯第一次孤身一人呆在海拔6600米的孤凉山峰顶时,这种联想的潜移默化作用尤显突出。史密斯每天仔细观察大山静谧世界里的自然景观,其心境随着雾霾、彩虹、狂风、暴雨的天气变化而变化着,而独自打坐、静虑禅思则让他的思想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即:从最初上山的欢快转而进入山中独处的孤寂、幻想,进而到后期在林中的偶尔暂悟,这使得史密斯无论在身体上还是思想上都经历了一次类似禅修的洗礼。在精神领袖“他者/贾菲·赖德”缺席的情况下,史密斯“对着山中呼喊寒山的名字,没有回应;对着晨雾呼喊寒山,依然沉默”。[11](p190)这一“中国寒山沉默”的叙事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渲染了“一个美国寒山”变异形象的诞生。当日历表上的画圈显示叙事者史密斯在孤凉山顶苦行僧似地“渐修”了55天时,变异的结果首先是史密斯惊异地感悟自己也像赖德一样似乎成为了一名美国寒山:“我的头发变长了,镜中的我双眼湛蓝,皮肤黝黑,精神欢快”。[11](p190)紧接着,60天过去了,史密斯眼前出现了新的幻觉:
突然,我似乎看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中国小和尚站在那里,在雾中,满脸皱纹的脸上显示出面无表情的幽默。那不是背着背包、满腹经纶、在科尔特·马德拉山上举行疯狂派对的贾菲,远比萦绕于我梦中的贾菲形象更真切。他一语不发地呆在那里。忽然,他朝着难以置信的卡斯卡德斯山空谷大吼:“滚,心灵的窃贼!”[11](p191)
作者凯鲁亚克使用形容词unbelievable修饰Cascades暗示空间地点已“难以置信”地变更为美国西部的卡斯卡德斯山脉,无疑,此时的“贾菲”已经完成了形象变异的过程,远非停留在叙述过去现实和从前睡梦中的那个“贾菲”了。这一视觉形象的变异基于贾菲远赴日本寺庙进行禅修,抛弃了“心灵的窃贼”,达到了如佛教所云“五蕴皆空”的境界。因此,可以说,回归孤凉山的美国贾菲·赖德与回归天台山隐居的中国寒山一样经历了“尝游千万里,今日归寒山”的路程,类似的肉体和精神之旅使得贾菲·赖德在史密斯的幻觉中最终定格为“垮掉派英雄偶像——美国寒山”的经典变异形象。
[1]John Suiter. Poets on the Peaks[M]. Washington D. C.: Counterpoint, 2002.
[2]Edward Hasley Foster. Understanding the Beats[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2.
[3]曹顺庆,罗富民.变异学视野下比较文学的反思与拓展[J].中外文化与文论,2011,(20):20-31.
[4]Steven Watson. The Birth of the Beat Generation: Visionaries, Rebels, and Hipsters, 1944-1960[M]. New York::Pantheon Books, 1995.
[5]Michael Davidson. The San Francisco Renaissance Poetics and Community at Mid-Centu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Arthur Waley. 27 Poems by Han-shan[J]. Encounter 3.3 (September 1954): 3-8.
[7]Gary Snyder. Cold Mountain Poems[J]. Evergreen Review 2.6 (Autumn 1958): 68-80.
[8]Jack Kerouac. Some of the Dharma[M].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7.
[9]Gerald Nicosia. Memory Babe: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Jack Kerouac[M]. New York: Grove Press, 1983; rep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10]Ellis Amburn. Subterranean Kerouac: the Hidden Life of Jack Kerouac[M]. New York:St. Martin’s Griffin, 1999.
[11]Jack Kerouac. The Dharma Bums[M].New York: Viking Press, 1958; repr. Cutchogue, New York: Buccaneer Books, 1986.
[12]David Robertson. Real Matter, Spiritual Mountain: Gary Snyder and Jack Kerouac on Mt. Tamalpais[J]. 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 27.3 (November 1992):209-225.
[13]Rick Fields. How the Swans Came to the Lake: A Narrativ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America[M]. 3rd rev. edn. Boston & London: Shambhala, 1992.
[14]Matt Theado. Understanding Jack Kerouac[M].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2000.
[15]Barry Gifford & Lawrence Lee. Jack’s Book: Jack Kerouac in the Lives and Words of His Friends[M]. London:Hamish Hamilton, 1979.
[16]Inger Thorup Lauridsen & Per Dalgard.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the Russian New Wave[M]. Ann Arbor: Ardis, 1990.
[17]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8]Daniel Hoffman. Ed.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9]Chung Ling. Whose Mountain Is This? — Gary Snyder’s Translation of Han Shan[J]. Renditions 7 (1997): 93-102.
[20]Jacob Leed. Gary Snyder: An Unpublished Preface[J]. Journal of Literature 13 (1986):177-180.
[21]钱学烈.寒山拾得诗校评[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
TheDharmaBums,aNovelDevotedtoanAmericanHanShanbyJackKerouac
CHEN Deng,TAN Qiong-li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China)
This paper i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beat writer Jack Kerouac’s semi-fictional novel The Dharma Bums from the angle of acculturation and historical events. It aims to examine how Han Shan (mysterious hermit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Gary Snyder (American translator of Cold Mountain Poems) and Japhy Ryder (main character of The Dharma Bums) are merged into oneness and thus transferred to an American counter-cultural beat hero in the novel. The paper contends that this novel is not only devoted to the ancient Chinese poet Han Shan, but also to Gary Snyder, an exemplary representative of an American Han Shan.
Jack Kerouac;The Dharma Bums;Gary Snyder;Han Shan;American Han Shan;acculturation
2014-06-15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WW012);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2010YBA051)
陈 登(1958—),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 研究方向:中西文化比较.
I106
A
1008—1763(2014)06—01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