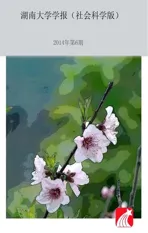朱熹礼理沟通的经典诠释——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为例*
2014-03-31殷慧,张卓
殷 慧,张 卓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长沙 410082)
众所周知,《大学》原为《礼记》中第四十二篇,是发挥礼义的作品。南宋时朱熹强调其作为《四书》中最基础、最优先的地位,并将其作为《四书》注释的第一部,形成了具有深远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理学诠释文本——《大学章句》。自此,《大学》的面貌为之一新,开始打上鲜明的理学印记,成为礼、理融合的经学诠释典范。朱熹认为,《大学》一书之间,“要紧只在‘格物’两字”①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425页(以下《朱文公文集》、《四书章句集注》、《朱文公文集》、《四书或问》均出自此版本《朱子全书》)。本文拟以《大学章句》中“格物致知”的诠释为核心,从哲学、历史、实践三个方面分析朱熹诠释一个经典礼学文本的思路和特点。
一 礼理融合的哲学升华:天理的注入
理(或称天理)是朱熹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和起源,又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标准和法则。在《四书》的诠释中,理的渗透无处不在。在《大学章句》中,朱熹7处用理或天理、事理来诠释《大学》中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在诠释“明明德”时,朱熹说:“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①《四书章句集注》,16页我们知道,郑玄释“明明德”为“显明其至德也”②《礼记正义》卷六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673页。朱熹所释的“明德”既说明了其人性的基础,“得于天”、“具众理”、“应万事”;又解释了“明明德”的必要性:在现实环境中,人性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而昏暗不明,所以需要提撕、振作以复其本性。朱熹巧妙地渗入天人、理事、理欲、性气等,将传统礼学文本进行了崭新的解释。
同样,朱熹引入“事理”、“天理”来释“止于至善”,朱熹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③《四书章句集注》,16页朱熹一方面用“事理当然之极”来解释“至善”,另一方面又强调“止”就是尽“天理之极”。
当然,天理的渗透集中在格物穷理的解释上:“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物格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不尽也。”④《四书章句集注》,17页我们不难看出,朱熹的这一诠释已远远超出汉唐经学的框架。郑玄释格物:“格,来也。物,犹事也。其知于善深则来善事,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⑤《礼记正义》卷六十,1673页显而易见,郑玄所理解的“知”是“知善恶吉凶之终始也”,而朱熹所理解的“知”则是“知理”。因此,郑玄关注的是事之善恶,朱熹则关心的是事之理。影响最为深远、论点更为明晰的是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的格物补传:“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⑥《四书章句集注》,20页朱熹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致知需要格物,也解释了格物何以可能,以及怎样去格物。同时,与其说朱熹在用“即物穷理”重新诠释格物致知,不如说其将格物致知作为手段,用其修养论、方法论继续深入揭示“明明德”、“止于至善”的内涵。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朱子对《大学》之诠释,始终不离乎“止于至善”这一基本立足点⑦郭晓东:《善与至善——论朱子对<大学>阐释的一个向度》,黄俊杰编:《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85-207。实际上,朱熹均在努力以“理”涵盖、统摄汉唐经学中“善”,并着力强调以穷理之“极”来达到善之“至”。
朱熹以天理论、穷理说来释格物致知,强调即物穷理,并须穷至其极,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理一分殊。受老师李侗重分殊胜于理一的影响,朱熹强调于分殊处理会理一,这是其格物说的主要倾向,他说:
万理虽只是一理,学者且要去万理中千头万绪都理会,四面凑合来,自见得是一理。不去理会那万理,只管去理会那一理,……只是空想象。⑧《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七,3692页
某怕人便说理一。⑨《朱子语类》卷五十六,1822页
圣人未尝言理一,多只言分殊。盖能于分殊事事物物,头头项项,理会得其当然,方知理本一贯。不知万殊各有一理,而徒言理一,不知理一在何处。[10]《朱子语类》卷二十七,975页
朱熹之所以怕人只说理一,原因在于只言理一,就会淡化于分殊处穷理的工夫。陈来先生曾指出,如果把注重分殊作为方法论来看,朱熹的格物穷理方法,正是注重由具体的分殊的事物入手,认为经过对分殊的积累,自然会上升到对理一的把握[11]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272页。
通过注入“天理”论,添入“理一分殊”的理事内涵,《大学章句》中的格物穷理说表现出鲜明的理学特征,但这一特征仍然根源于传统经学尤其是礼学的脉络。这是因为,一方面,朱熹作为一位经典诠释者,他常常强调诠释者需要虚心平气,“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12]《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答吕子约》,2213页。另一方面,朱熹又在处处超越、升华传统礼学,“借经以通乎理耳。理得,则无俟乎经。”[13]《朱子语类》卷十一,350页通过探求“本文本意”而领悟到“圣贤之指”,这是诠释者力图忠实经典,探求经典原意的初衷。“无俟乎经”隐含的意思并非是忽略或漠视经的存在,而是指诠释者在“得理”后便获得了重新诠释经典的自信和自得,使“理”和“经”处于融合、互动的状态。正如朱熹所言,“若看得道理透,方见得每日所看经书,无一句一字、一点一画不是道理之流行;见天下事无大无小、无一名一件不是此理之发见。如此,方见得这个道理浑沦周遍,不偏枯。”[14]《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一,3836-3837页领会理的流行后再看经书,经书中处处均是理,这从上述朱熹的格物诠释可略 窥 一 斑 。[15]乐爱国,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二 礼理连接的历史考察:大学格物的基础是小学工夫
与理一分殊、理事关系的哲学讨论相一致,朱熹在挖掘《大学》文本的历史内涵上,着重强调小学的学礼工夫为大学的明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里所言的历史性,一方面是指朱熹在为《大学》注入天理的诠释时,并没有忘记其为礼学文本的历史,力图使礼与理的衔接自然而不着痕迹;另一方面是朱熹注重学习活动的历史阶段性,将小学学礼与大学明理结合起来。
朱熹《大学章句》中强调格物致知说,目的是为了重新明确大学“教人之法”,提出探究知识并最终为道德践履服务的方法。朱熹明晰了礼之为教的层次性,在《大学章句序》中引入了对大学的基础——小学的解释,因此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与其对小学的理解紧密相关。朱熹观察习礼的过程发现,格物是联系小学与大学的枢纽,小学是格物的基础,也是大学“教人之法”的起点。小学主要在礼文的训练中涵养性情,潜移默化地形成规范身体的礼仪,大学则是在学的最高阶段体会礼中蕴含的天理,最终为形成以修身为依归的礼治社会服务。
朱熹关于小学与大学之间关系的阐述,集中体现在《大学章句序》中:
《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若《曲礼》、《少仪》、《内则》、《弟子职》诸篇,固小学之支流余裔;而此篇者,则因小学之成功,以著大学之明法,外有以极其规模之大,而内有以尽其节目之详者也。”①《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大学章句序》,3672页
朱熹从教育史的角度对人的学习阶段进行考察后指出,小学教的是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教的是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己治人之道,这一切都是礼的内容。简言之,小学是习礼之事,大学是明礼之理。从识理、为道这一连贯的学习目标来说,大学和小学是不可或缺且相互依存的,“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无以察夫义理,措诸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②《大学或问》卷一,505页因此格物主要就是重新明晰蕴含在礼事中的人伦之理。
通过历史的追溯,朱熹将理与事的关系协调起来,使乍看上去虚空缥缈的天理有了切实可行的人事基础。朱熹认为,“小学涵养此性,大学则所以实其理也。忠信孝弟之类,须于小学中出。然正心、诚意之类,小学如何知得。须其有识后,以此实之。大抵小学一节一节恢廓展布将去,然必到于此而后进。”③《朱子语类》卷十四,422页他还有一些论述清楚地表达了格物须建立在小学工夫的基础上:
问:“未格物以前如何致力?”曰:“古人这处,已是有小学了。”④《朱子语类》卷十四,455页
古者初年入小学,只是教之以事,如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学,然后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为忠信孝弟者。⑤《朱子语类》卷七,268页
某于大学中所以力言小学者,以古人于小学中已自把捉成了,故于大学之道无所不可。今人既无小学之功,却当以敬为本。⑥《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五,3638页
朱熹认为古人将小学与大学是贯通起来的,礼文与礼义密不可分。后世礼文阙失,小学工夫也淹没不闻,因此必须重新认识小学与大学之间的联系,朱熹提出以敬贯穿小学工夫,格物致知则是大学的首要工夫。
朱熹明确提出,小学的主敬工夫是大学格物致知的精神基础。他说:
“盖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为始。今人未尝一日从事于小学,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后敬有所施,则未知其以何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⑦《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胡广仲》,1894-1895页
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论之,则先知后行,固各有其序矣。诚欲因夫小学之成以进乎大学之始,则非涵养履践之有素,亦岂能居然以其杂乱纷纠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⑧《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答吴晦叔》,1915页
古人之学固以致知格物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则亦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习而已。是皆酬酢讲量之事也,岂以此而害夫持养之功哉?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七《答吕子约》,2190页
格物致知为大学的起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小学主敬涵养、持养践履的基础之上的。从格物的内容上来说,它是自足的;从格物的工夫来说,它是主张操存用力的,并非如时人说论一见“格物”便以为重思虑知识。朱熹力辨:
今且论涵养一节,疑古人直自小学中涵养成就,所以大学之道只从格物做起。今人从前无此工夫,但见《大学》以格物为先,便欲只以思虑知识求之,更不于操存处用力,纵使窥测得十分,亦无实地可据,大抵敬字是彻上彻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间节次进步处耳。[10]《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答林择之》,1978-1979页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同主敬涵养一样是学礼的工夫,而并非是重知识轻践履。朱熹对小学学习内容的开掘综合了先秦经典中对于初级教育的阐述,为大学之道的展开奠定了基础。同时主张以主敬涵养贯穿小学工夫,为格物致知工夫的展开准备了涵养的基础。这样,通过对格物之前的小学工夫的诠释,朱熹将格物穷理的讨论放在了礼文与礼义、理与事紧密相连的背景下,为八纲目的展开打开了礼学的视野。为了进一步探讨古代小学的教人之法,朱熹与刘清之一起编撰了《小学》一书。《小学》的出现,是朱熹对大学成人之教反思的结果,标志着理学教育体系的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朱熹从礼理沟通的角度总结完善了大学与小学的关系论述,这既是对张载、程颐思想的继承,也是对吕祖谦、张栻相关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张载和二程都已注意到礼文之教和义理德行之教之间的难易及先后顺序。张载曾说:“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倦此,若洒扫应对,乃幼而孙弟之事,长后教之,人必倦弊。惟圣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故事无大小,莫不处极。今始学之人,未必能继,妄以大道教之,是诬也。”①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31页程颐曾感慨:“古之学者易,今之学者难。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有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歌舞以养其心,今则俱亡矣。惟义理以养其心尔,可不勉哉!”②《二程遗书》卷二十一上,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268页与朱熹一起编撰《近思录》的吕祖谦曾说:“后生学问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礼仪等学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及先理会《尔雅》训诂等文字,然后可以语上下学,而上达自此脱然有得度越诸子也。不如此则是躐等犯分陵节,终不能成。孰先传焉,孰后倦焉,不可不察也。”③吕祖谦:《少仪外传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70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220页朱熹注意到《礼记》中的其他篇目与《大学》之间的相互印证,很明显受到了吕祖谦的影响。张栻则明确地提出理学教育的为学之序、教学之方就在于将大学的格物致知建立在洒扫应对的基础上,他说:“然尝考先王所以建学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盖甚大矣,而为之则有其序,教之则有其方。故必先使之从事于小学,习乎六艺之节,讲乎为弟、为子之职,而躬乎洒扫应对进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间,优游乎弦歌诵读之际,有以固其肌肤之会、筋骸之束,齐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谓大学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进焉。”④张栻:《邵州复旧学记》,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681页这是张栻在《邵州复旧学记》一文中提出的,而且在给朱熹的信中已经明确提及应该将小学与大学联系起来⑤《南轩集》卷二十一《答朱元晦书》:“某近为邵州作《复旧学记》,其间论小学、大学意,偶亦相类,录呈。今犹未刻,有可见教,尚冀速示也。”见(张栻.《张栻全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年,852页)。
三 礼理融合的实践性:居敬涵养的修养体验
礼重践履,《说文》:“礼者,履也。”《荀子·大略》:“礼者,人之所履也。”《曲礼》首言“毋不敬”。理学重修养功夫,理学家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代表了理学修养论的宗旨。从理学对传统礼学精髓的继承上可以看出,其兴起和成功仍然得益于对传统礼学工夫的领会和把握。朱熹诠释格物致知时,同样注重礼理融合的实践性,经由“圣人之言”去触及“圣人之心”,从而体会“天下之理”⑥《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3805页。有研究者发现,朱熹将读经穷理与个人践履视为一体,注重“实践——体验”的诠释方法,表明了他的诠释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倾向⑦朱汉民:《实践——体验:朱熹的<四书>诠释方法》,《中国哲学史》,2004,(4):91;潘德荣:《经典与诠释——论朱熹的诠释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02,(1):66。
朱熹发挥程颐之说,认为格物的对象极其广泛,即凡天下之物而格,自然牵涉自然界万物。众所周知,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当高的时代,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无疑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求,是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在哲学、学术思想领域的集中体现,这是朱熹格物致知说对《大学》诠释的进一步发展。钱穆曾指出,朱子于事理外又补上物理,此乃是思想之递后而益进。《大学》原文亦似无忽然转变论点,轶出人事界,谓欲善尽种种人事,必先穷究自然物理。此应另成一番理论,决非《大学》原文宗旨所在⑧钱穆:《<大学>格物新释》,《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95-97页。的确朱熹一直强调,无论是人伦之“内事”与自然世界的“外事”,“皆是自己合当理会底”,而且朱熹还提出格内事、外事的比例,“须是六七分去里面理会,三四分去外面理会方可”⑨《朱子语类》卷十八,616页。朱熹认为在理会人事和物事上是有一定比例而且融合统一的。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展开的,因而格物的内容仍然是以礼文中蕴含的人伦之理为主,他说:“格物,莫先于五品。”[10]《朱子语类》卷十五,464页格物的首要任务是反思省察自身内在的仁义礼智,使明德焕发出来,因此格物的最终目的是践履。“格物,须真见得决定是如此。”[11]《朱子语类》卷十五,464页
格物致知的主要内容仍是人事。朱熹说:“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无不各有个天理人欲,须是逐一验过。”[12]《朱子语类》卷十五,467页格物的工夫最终都是应该认识到在应对人事、遵循礼仪中的合礼与非礼之处,辨析何为天理,何为人欲。致知也不过是知得心中之礼义。朱熹说:“致知,不是知那人不知底道理,只是人面前底。且如义利两件,昨日虽看义当为然,而却又说未做亦无害;见得利不可做,却又说做也无害;这便是物未格,知未至。今日见得义当为,决为之;利不可做,决定是不做,心下自肯自信得及,这便是物格,便是知得至了。”①《朱子语类》卷十五,479页格物致知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在正心诚意践履工夫的基础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就格物所代表的活动来说,也是“一种修养的方法”②陈来:《宋明理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13页。
朱熹强调即物穷理,认为“格物,不说穷理,却言格物。盖言理,则无可捉摸,物有时而离;言物,则理自在,自是离不得”③《朱子语类》卷十五,469页。朱熹反复强调,格物所穷之理并非“一个悬空底物”,《大学》之所以不说穷理,而说格物,实际上就是强调“要人就事物上理会”④《朱子语类》卷十五,469页。朱熹格物致知说始终将对天理的探寻附着在现实人、事、物的基础上,体现了对传统礼学思想精髓的把握。
关于格物的主要内容,以及如何展开格物穷理的过程,朱熹有一段话阐述得十分清楚:
“世间之物,无不有理,皆须格过。古人自幼便识其具。且如事亲事君之礼,钟鼓铿锵之节,进退揖让之仪,皆目熟其事,躬亲其礼。及其长也,不过只是穷此理,因而渐及于天地鬼神日月阴阳草木鸟兽之理,所以用工也易。今人皆无此等礼数可以讲习,只靠先圣遗经自去推究,所以要人格物主敬,便将此心去体会古人道理,循而行之。如事亲孝,自家既知所以孝,便将此孝心依古礼而行之;事君敬,便将此敬心依圣经所说之礼而行之。一一须要穷过,自然浹洽贯通。如《论语》一书,当时门人弟子记圣人言行,动容周旋,揖让进退,至为纤悉。如《乡党》一篇,可见当时此等礼数皆在。至孟子时,则渐已放弃。如《孟子》一书,其说已宽,亦有但论其大理而已。”⑤《朱子语类》卷十五,466-467页
在朱熹看来,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礼仪化的过程。在幼小的时候,躬亲洒扫应对之节,熟习进退揖让之仪,目睹事亲事君之礼,演练钟鼓铿锵之乐,在礼乐节文中耳濡目染,一切礼事均充盈其身心。进入成年之后的大学阶段,格物就是对已经内化在身心中的礼仪规范进行再反思,回复到礼文本身,探究其间的规律与本质。朱熹说:“礼,小时所学,只是学事亲事长之节,乃礼之小者。年到二十,所学乃是朝廷宗庙之礼,乃礼之大者。到‘立于礼’,始得礼之力。”⑥《朱子语类》卷三十五,1301页而“得礼之力”,在朱熹看来,这就是大学终身追求的目标与成就。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认为应从人事拓展开去,穷究天地鬼神日月阴阳草木鸟兽之理,这表面上看来,格物的内容是拓展了,但只要熟悉《礼记》,对宇宙、自然、社会规律的探讨也仍然是礼所涵盖的。虽然朱熹也认可探讨自然规律的必要性,但其主要着力点依然是要回归对人伦之理的穷究。
在朱熹时代,由于已经缺乏从小涵养礼文的社会环境,因此学者从小在习得礼仪上存在着不足的缺憾。到了成年就需要补充小学工夫,而此时的小学工夫需要借助先圣整理的经典作为参考,在学习中涵养虔敬之心,并用此心去体悟古人举手投足、进退揖让中所蕴含的道理,最终以礼仪作为衡量标准,蹈礼循行,择善而从。穷理的主要内容实际上就是以《论语》、《孟子》等经典为蓝本,探寻礼之大体以及具体的动容周旋之礼。
正如杜维明先生指出的,不能将“格物”解释成身居局外的观察者对外在事物进行无动于衷的研究。相反,它代表了一种认知方式,认知者在这种方式中不仅被已知事物渗透,而且还被转化了。“格物”就是为了理解我们自身以及周边世界而探索自然现象和人类事物。⑦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42页朱熹的格物说正是如此,并非为了求知识而脱离现实的人事,而是在小学工夫的基础上反刍礼文中蕴含的道理。反思并重新认识进入真正的道德主体的人应该实现的“创造性自我转化”:格至事物,才能了解“所以然”,了解现实的自然、社会、人生的本来面目;格物才能穷理,才能正心诚意,坚定人生应该坚持的应然方向,达到理想的道德、精神境界。格物最终是实现形而下的践履与形而上的理论认识相结合,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这一思想正是对湖湘学派居敬致知思想的批评与修正。胡宏在明理居敬的讨论中提出他的格物说:“格之之道,必立志以定其本,而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内,而知乃可精。”⑧胡宏:《胡宏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8页朱熹一方面肯定了胡宏的居敬致知思想,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格物思想的几点不足:一是虽然用立志、居敬贯穿格物始终,但是至于如何格物,却没有明白细致的说法,有急迫、局促之嫌;二是胡宏的格物致知说主要着眼于主心的工夫,有重内轻外的弊端,应该说得“表里内外周遍兼该”才是;三是在朱熹看来立志居敬都是格物之前的涵养工夫,而致知又是格物以后的事,因此虽然是说格物之道,而实际上又将格物的内涵架空了,因而尚未领悟格物的要领。⑨《朱子语类》卷十八,631-634页从朱熹对胡宏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朱熹吸收了胡宏居敬致知的思想,另一方面,朱熹重新回到程颐的格物思想将格物与居敬、致知结合起来,并深入挖掘格物以前的小学工夫,使自己的格物说内外兼容、小大有序。
应该说明的是,虽然朱熹重视从文字上纠正湖湘学派的居敬格物思想,但他始终强调,“只是做工夫全在自家身己上,却不在文字上”[10]《朱子语类》卷十四,426页。这是朱熹格物诠释思想重践履的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