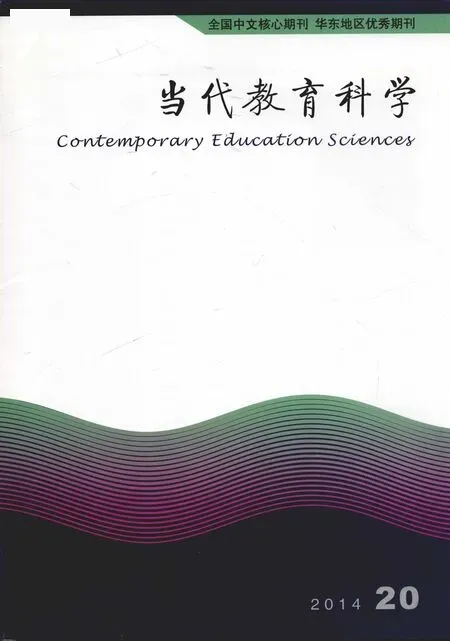论学校教育的使命*
——基于“洞穴人”假设的理论视角
2014-03-30杨日飞
●杨日飞
论学校教育的使命*
——基于“洞穴人”假设的理论视角
●杨日飞
理解存在是理解教育、定位教育价值的出发点。柏拉图的著名隐喻“洞穴囚徒”描述了人的存在景象,在表达人的“洞穴”命运的同时赋予教育根本的重要性。因此,在我国基本实现教育普及的时代背景下,思考教育如何帮助受教育者超越存在的洞穴进而成为主导各自人生的舵手,即,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偏见和成见的探索精神的人变的尤为重要。
教育;存在;洞穴囚徒;可完善性
面对当前中国教育里存在的各种问题,很多人从不同的纬度来探讨教育的本质、价值和意义追求。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仍然有继续讨论的必要。因为,正确地理解教育的本质、价值和意义是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决定着教育发展的方向。否则,我们很容易因为一些功利性的追求得不到满足而陷于教育无用论。如果我们从存在的角度,从存在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出发来思考教育的本质、价值和意义,就会发现,教育是引导个体面向存在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因为只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偏见和成见的探索精神的人。柏拉图(Plato)的著名隐喻——“洞穴囚徒”(Cave Prisoner)对此有重要启示。
一、“洞穴囚徒”描述了人的存在景象
作为西方理念论的创始人,柏拉图在其重要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提出了一个重要隐喻——“洞穴囚徒”。[1]后世的许多思想家通过对柏拉图思想尤其是“洞穴囚徒”这一隐喻的分析确立了自己基本的学术主张,在这方面以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及其衣钵传人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最为鲜明。也许在一些学者看来,在本文中笔者过度地评价了柏拉图这一隐喻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无论从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还是柏拉图所揭示的问题来说,这种评价无疑是比较合理的。
就柏拉图本人的思想来说,第一,“洞穴囚徒”是其所主张的国家治理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具有主观和客观的一面,主观在于个体(确切地说是城邦公民)先天的某种欠缺状态导致了囚徒困境的出现,而在客观方面,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从各个方面制约着人所能达到的发展水平。当然,在衡量这一发展水平时,不仅要把个体对人生使命和人生价值的认识或者以追求无限(以这样一个更为学术性的话语来表达可能更为合适)作为标准,还要以能否站在人性普遍性的高度或者说人类的高度来思考人类的命运作为更为重要的标准,这两方面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标示着人性的高度。而这个高度也决定了对于人类当中的大多数这是一个无法企及的高度。因此,在柏拉图看来,严格的制度安排可以保证在使人类中的卓越者尽其所能发挥作用的同时使那些处于先天匮乏的“囚徒”被迫转向普遍的善,超越眼前世界的局限性,走向一种可完善性的存在状态,从有限走向无限。
第二,“洞穴囚徒”是柏拉图将教育视为影响人的灵魂转向的认识起点。在柏拉图看来,政治治理与统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治理的核心是“参与”、“关心”——每个人都要参与国家的公共治理,每个人都要关心公共生活;而统治在统治者看来是苦役,在被统治者看来是强制。治理凭藉智慧,智慧来自谈话;统治依靠强力,强力来自命令。因此,对于治理者来说,教育是国家的重要事务,因为它不仅涉及到肉体的控制,同时还包括灵魂的安顿。这样才能有机会面向普遍的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重视教育对人的引导作用,正如他重视良好的政治治理法则在促进城邦公民能够各尽其材一样。教育和政治从不同的方面为人达至永恒的善作必要的安排。
就柏拉图揭示的问题来说,它形象地描绘了人的存在景象。用布鲁姆的话说:“……柏拉图式的洞穴图景描述了人类的根本处境。人是其所处时代及其场所中权威意见的囚徒,一切人由此开始,大多数人也在此结束。”[2]实然柏拉图所描述的是大多数人的命运,但在现实世界中,因为权力、多数人的暴政等众多客观因素,使得“洞穴囚徒”几乎是现实世界中一切人的命运,谁若质疑并否定人的这种命运的合理性,谁就会成为意见之徒的敌人,象苏格拉底那样,等待他的命运只有两种:或者闭嘴,或者痛快的死去。柏拉图对洞穴中成功实现灵魂转向的人寄予厚望,希望这个人能够返回洞穴,引导更多的人实现灵魂转向,超越意见世界,勇敢地面向绝对、面向永恒的善。但这个人被看作怪物、遭受囚徒们的嘲笑乃至要被他们消灭掉的事实与其说它隐晦地指明了柏拉图对人性的失望,毋宁说它表达了柏拉图对永恒人性的看法。因为他并没有失望,而是意图通过哲学教诲——一种以对话、引导、启发心智为主的教育形式使人们尽可能地实现灵魂转向。事实上,柏拉图借助哲学的诗性精神向我们委婉地传达了人的存在形象:轻松得令人无法承受。这样的讲述如同小说家的叙事一样,对于听众来说一般有两种情况: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个关于“他人”的故事;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是关于他(们)的事情。尽管这样一种隐晦的教诲方式产生了事实上的差异,但无论是思想还是传达思想的方式无疑都达到了自然的统一,因为它们考虑到了人性的限度。在认识人作为人的命运这个问题上,不是所有人都能站在同一条直线上向前走去,它更像是一个自由市场,不同的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所有人都会错过一些东西,差别仅在所选择的东西的价值。柏拉图对人性的洞识及对人之存在状况的认识决定了“洞穴囚徒”作为存在“原型”的不可否定性,或者说:“洞穴囚徒”表达了人的命运。
二、“洞穴”的意指及造成洞穴的原因分析
在“洞穴囚徒”的隐喻中,囚徒是结果,而洞穴是造成囚徒的原因。因此,分析洞穴的意指及造成洞穴的原因是本文接下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这是我们形成关于人类的恰当观念及人的发展的恰当观念的依据,也是我们进一步定位教育作用的依据。
(一)“洞穴”的意指
从一般意义上讲,洞穴指一种空间上的狭隘状态,在这个隐喻中,则主要指造成人心灵狭隘的原因。本文认为,所谓洞穴主要指“文化奴役”导致人心灵的萎缩及自我判断力的丧失,是人缺乏理性能力的表现。
柏拉图本人并没有就文化奴役本身展开论述,这个工作是由后来的一些思想家来完成的。这可能是因为文明的进程在一定历史时期会表现为文化奴役的显现,而人作为“洞穴囚徒”的命运越来越严峻,中世纪欧洲文明的演进就是良好的证据。还有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对这样一个事实的思考即:文化作为人之自然禀性的必要补充,为人走出自然界、进入人类文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会成为束缚人类天性、造成人的文化奴役的原凶呢?因为它涉及到对人类演进历程的科学分析,而这正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所以能否以人类学的方法为人类所遭受的文化奴役做出科学的诊治将决定谁将会成为一个饱受争议的人。事实上,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分析该问题的方式决定了他将使这个问题更加鲜明化。
在《论科学和艺术》一文中,卢梭较为系统地思考了文化发展对人类社会乃至个体的发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并深刻的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的发展除了在社会生活中增加了许多繁文缛节、并因此而使人变得矫揉造作毁坏了人的善好的天性之外,简直是一无所用。因此他猛烈的批评当时百科全书派对人的真实处境视而不见却片面的夸大文化对人的理性启蒙作用的腐败面容。
在卢梭这里,“文化”与人的天性对立起来了。康德(Immanuel Kant)敏锐的意识到了卢梭所指,并自愿成为“卢梭的伦理思想的火炬手”。他说:“我自以为爱好探求真理,我感到一种对知识的贪婪渴求,一种对推动知识进展的不倦热情,以及对每个进步的心满意足。我一度认为,这一切足以给人类带来荣光,由此我鄙夷那班一无所知的芸芸众生。是卢梭纠正了我。盲目的偏见消失了,我学会了尊重人性,而且假如我不是相信这种见解能够有助于所有其他人去确立人权的话,我便应把自己看得比普通劳工还不如。”[3]从康德的这段话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不是卢梭把自然和文化的概念对立起来了,而是他看到了自然与文化的这种对立,并试图回到人性的原点消除这种对立,使文化成为“人的文化”,改变由传统施加在我们头上的那种文化奴役人的悲惨命运。从卡西勒对卢梭康德之间密切的关系的论述也能够证实:卢梭把文化和自然的观念带入了一个新领域、新世界,并对康德伦理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实然,卢梭对文化的批评颇显过激,但正是由于他的看起来“不恰当”的行为促使人们意识到要合理地定位文化在人或人类发展中的作用,再一次使人们迫切地思考“天性”与“文化”的关系,并直接推动了人们对“启蒙”的探讨。
综上所述,所谓文化奴役一方面指违反人天性的文化对人的发展说造成的戕害;另一方面涉及到科学的文化引导人成长的方式,即如何对人进行文化熏陶。前者的中心议题涉及到文化的功能,它促使我们不断地思考以人为本文化的内涵;而后者的中心议题是教育的功能,它促使我们不断思考“儿童本位”教育的内涵。二者都有助于深化对人的认识。
(二)产生洞穴的原因分析
产生洞穴的原因来自于人天性的不足,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自然欠缺。在学术史上,有一个充满积极意义的词:“可完善性”,卢梭称之为“自我完善的能力”。在教育家们看来,自然欠缺即可完善性内涵着一种自然而普遍的秩序,就像一粒种子在它成长为是其所是所能达到的高度之前已经蕴含着其生命潜力自然展开的普遍秩序。但在一些鲁莽的教育者的眼里,“可完善性”成了他们过渡控制教育对象的借口。他们把人性完善的弹性空间看成是他们作用于教育对象的弹性空间。并因此造就了被教育者的灾难。可完善性在教育家和一些鲁莽的教育者之间产生了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是致命的。在卡西勒的解读中,可完善性既“是人类所有洞见的源泉,也是人类所有舛误的来源”。[4]可完善性既存在于我们类中间,也存在于个人身上,在环境的帮助下,它可以使人的能力不断发展。[5]问题是它给人的发展提供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它既能使人变得坚强有力,也能使人变得软弱不堪,人能够通过这种能力发展自己,同样,如果应用不当,还会败坏人的天性。卢梭认为:“这种能力,当初曾使人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了他终日平平静静无忧无虑的原始状态,然而随着时代的前进,它又使人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谬误;既培养了道德,也犯了过错,最后终于使他成为他自己和大自然的暴君。”[6]可完善性这种人性的坯基不仅预示着人将会变得强大,同时说明了当前的软弱与无知,这种软弱和无知可以变为坚强与善于判断,也可能会因为不恰当的或粗暴的文化作用方式使人生的幼芽失去健全发展的机会,让偏见占据心灵,拒斥整全的教诲,把任意纵性作为存在的标度,而无顾自由之神的指引。这些由天性不足而导致的恶构成了人生的洞穴。
既然囚徒困境主要是因外部不健全文件的作用导致个人理性能力的丧失,那么,必然有一种有效而正当的方式能够满足人类发展的需求,使他们走出洞穴,成为人生的舵手、“自己之王”,不再沦为他人或自己的奴隶。柏拉图从中推出了哲学教育的必要性,而在本文中,我们将进一步重申教育的基本立场:在一种充分尊重教育对象能动意识的前提下引导他们形成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
三、“洞穴囚徒”对教育的启示
尽管“洞穴囚徒”隐喻所关心的是“哲人王”的教育问题,但在我们生活的时代,真正的教育已不再局限于“哲人王”,而应推及到每一个人。在教育普及的前提下我们需要关注已经不是哪些人具有可能的接受教育的资质,而是如何让教育成为每个人获得最大可能发展的条件,并服务于每个人的最好发展。在本文中,我们对最好发展的定位是提升人的理性思考能力,促使人们在生活中能够更好地选择、决断,提升生命质量。为此,教育在促进人获得最好发展的过程中,除了传递必要的知识,就是要引导受教育者从偏见、权威、教条等束缚中获得解放,上升到某种立场,看到存在的局限性并自觉地超越这种局限性。为此:
第一,教师应意识到教育是面向整全存在的事物,它服从于宇宙法则和宇宙精神,因此,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面向整全。
柏拉图说:“教育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education in the highest sense is philosophy)。[7]把教育与哲学连续起来无非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它们的关注对象是相同的。哲学关注整全。作为学科之母,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体的、根本性的。同样,教育所关注的对象也是一个整体,是对象各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和谐发展。其次,它们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相同的。教育同哲学一样,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在对话与交流中获的思想的启蒙和独立的人格的养成。哲学被称为爱智慧,教育被冠以引导人走向真、善、美的活动。爱智慧的表现是就人类社会中一些根本问题进行民主平等的交流,在形成关于研究问题的恰当观念的同时学会思考与判断。引导人走向真善美的表现即把一切事物交给学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教师必然要处理好可见世界同可知世界或者说事实真理与推力真理之间的关系。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引导学生观察并获得关于世界表象的同时发展它们推力判断的能力。
教育要引导学生面向整全,作为教育主体之一的教师就应当避免强制地灌输给学生知识,而应首先意识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习惯和不带偏见和成见的探索精神的重要性。因为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不带偏见和成见的探索精神正是宇宙法则和宇宙精神在人身上的体现,是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前提。因为,一旦独立思考的精神消失了,独裁与专断的恶习就会肆无忌惮的扩散开来,造成落后和愚昧。
第二,就教育目的而言,教育旨在使学生获得启蒙,成为自由的人。
自由是人的根本权利,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完全承担自己的一切责任,履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因为制度、风俗、惯例等都先于社会个体而产生,所以,每个人来到世界的时候都被迫接受许多东西。如果教育不是保证人的先天禀赋得到自由的发展,反而以这些先在的东西作为标准来衡量人性的话,就会剥夺人的自由,导致人的奴役。
那么,教育如何做到保证人的先天禀赋得到自由地发展呢?答案就是两个字:启蒙。所谓启蒙,用康德的话说:“启蒙,也就是人从自我监禁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不成熟是没有别人的指导就无能运用人自己的理智。倘若这种不成熟的原因不是缺乏理智,而是没有别人的指导就缺乏一种决断和勇气来使用它,它就是自我监禁。启蒙的箴言是:Sapere aude!(敢于成为智慧的人)。”[8]换句话说,启蒙就是使人能够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性能力,成为自由的人。
教育要培养自由的人,即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独立判断能力和鲜明个性的人。蒙台梭利指出“谁若不能独立,谁就谈不上自由。”[9]自由的对立面就是奴役,奴役由依附造成,依附源于软弱,软弱因为不能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一个能够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的人,必然会慢慢强大,不会受制于别人。之所以说自由的人是能够正确地运用自己的力量的人,也是考虑到强大的力量必须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如果自我力量的应用妨碍了他人的自由,这同样违背了自由的法则。因此,引导儿童积极的表现自己的潜力,通过儿童的主动活动走向独立,成为自由的人,这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和终极使命。
第三,就教学过程的本质而言,教育是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过程。
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使学生形成丰满的精神面貌,成为一名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但是传统教育却误把传递知识作为目的和衡量学生发展的标准,而忽视了促进学生精神成长的重要性,结果“分数主义”泛滥,导致儿童的天性被束缚,培养出的社会个体缺乏创造力。显然,一种仅从关注儿童饭量大小而不具体考察儿童身体发育状况的教育只能导致肥胖,这正是教育的失败。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曾经把学校形容为儿童心灵的屠宰场,认为“教导青年人的方法变得如此严峻,以致学校被孩子看作恐怖的场所和才智的屠场”,[10]导致学生厌恶书本。虽然这是对古代学校教育特征的描述,但是在当代学校教育领域里也部分地存在类似的情况。实际上,教育表现为对学生精神的戕害主要是由于在教育过程中一味地以“知识”为中心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教育可能造成巨大的教育资源的浪费,阻碍儿童的自由健康成长,甚至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造成阻碍。
在相对封闭、科技并不发达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因为知识是权力、地位的象征,是“上帝”的旨意,需要人为地保守这些秘密,若有人向那些不应该掌握知识的人泄露了秘密,就会受到惩罚。但是到了近代,科技的发展不断地开拓人的视界,知识不再被视为“神启”的秘密,相反,它只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成果。因为人类的认识是通向开放的,所以知识并不具有亘古不变的价值,唯一具有永恒价值的恰恰是认识世界的主体——人。
这种认识是对人类自身的肯定,也是对人的解放。在这种背景下,许多教育家逐渐发现教育应该以人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而不是以知识为中心。因为只有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才能成为促进儿童精神的成长手段,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于是,教学不再局限于以掌握知识、再现知识并通过分数作为唯一衡量标准的过程了。相反,它是教师如何引导学生建构精神世界,把知识转化为认识世界的方法、手段和工具,进一步提升学生掌控环境的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形象逐渐高大起来,活跃起来。
[1][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272-276.
[2][美]布鲁姆.巨人与侏儒[M].朱振宇等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张辉选编:经典与阐释:巨人与侏儒.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8.
[3]《片段》,哈登斯坦编辑,第八卷,第624页转引自[德]卡西尔.卢梭·康德·歌德[M].刘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
[4][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M].顾伟铭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96.
[5][6][法]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58.58.
[7]埃利斯.卢梭的苏格拉底爱弥儿神话[A].罗朗、黄群译.见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经典与阐释(6).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58.
[8]Kant’s Political W ritings,ed.Hans Reiss,trans.H.B.Nisb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54.
[9]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M].任代文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版),2001.119.
[10][捷]夸美纽斯.大教学论·教学法解析[M].任钟印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76.
(责任编辑:曾庆伟)
杨日飞/内蒙古教育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教育哲学、学前教育基本理论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立项课题“多元文化背景下内蒙古民族幼儿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出路”(NGJGH2013007)、内蒙古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儿童教育近现代立场的意蕴及其对中国儿童教育改造的启示”(YJRC12029)和内蒙古师范大学2012年度科研基金项目“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研究”(2012RWYB015)的部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