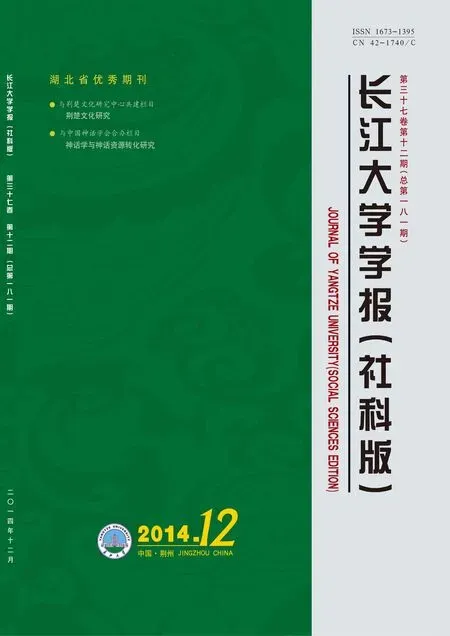扩展中的公共空间:民族旅游对黎族女性的影响研究①
——基于海南省保亭槟榔谷的实证调查
2014-03-25陈丽琴
陈丽琴
(海南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海南 海口 570228)
一、公共空间视角与民族旅游对女性影响研究的契合性
纵观文献,有关民族旅游与少数民族女性角色变迁研究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由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对女性经济地位的影响所引起的女性社会及家庭角色演变,如冯淑华、沙润对江西婺源民族旅游中农村女性就业与发展的研究,发现旅游发展为女性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和收入增加,也相应地提高了她们的政治、经济、教育、家庭和社会地位,促进了她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也有学者从民族旅游给当地社会性别角色带来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杨慧、刘永青对宁蒗落水村旅游与社会性别建构的研究;还有学者从旅游发展与东道主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如林清清、丁绍莲从旅游发展过程中东道主社会权力关系变化及作为旅游吸引物的东道主女性的社会地位变化等。但在实践中,由于参与民族旅游活动中的少数民族女性是个极其复杂的群体,很可能因参与方式和内容或者旅游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使其影响呈现出多样性。因此,笔者借鉴学者们的研究成果,结合海南黎族的民族旅游实践,在对海南保亭槟榔谷进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试从公共空间的角度来分析民族旅游对黎族女性的影响。
“公共空间”主要指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一些具有某种公共性且以特定空间相对固定下来的社会关联形式和人际交往结构形式,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乡村或者社区内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入并进行社会活动或者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集市、寺庙、红白喜事活动等;二是指村庄或者社区内普遍存在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庄的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大会等。作为村民日常生活行动场域的公共空间在乡村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就社会意义层面而言,公共空间是整合村庄交往形态和人际沟通方式的主要平台,是拉近村民心理距离、维持村庄共同价值规范与情感凝聚的主要渠道;就政治意义层面而言,作为体现村民日常生活社会行动关联程度的公共空间中的权力表达,表现在村民、乡绅精英与国家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如“社区精英可以通过公共空间来达到对村落社区的控制,村民则通过公共空间与国家权力结合方式反对精英的垄断控制,抑或社区民众与乡绅精英联合抵制国家权力对公共空间的渗透。”[1]所以,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场域,更是社会的有机整体,可以说,各种形式的社会关联都在此孕育、发生、发展。因此,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信息交流、资源重组、社会关系网络形成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平台。而女性参与民族旅游发展,打破了她们传统的社会角色定位,同时也使她们跳出家庭这一狭窄的活动范围,实现了从家庭到社会、从自给自足经济到市场经济、从无偿劳动到有偿劳动的飞跃。女性的活动场域从家庭扩展到旅游场域,旅游场域为她们建构了新的公共空间,这种新公共空间的建构对她们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共空间所承载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刚好契合了民族旅游对黎族女性的影响。
二、民族旅游开发前的黎族女性公共空间萎缩
马克斯·韦伯将村落公共空间分为两类:正式公共空间和非正式公共空间。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落外部的行政力量,即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及在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行政权力的驱使和影响,如村民会议,因此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化倾向;非正式公共空间的型构动力主要来源于村庄内部的传统文化、习惯与现实需求,因此其形成及在其中所展开的各类活动均受村庄地方性知识及村庄生存理性选择支配,具有浓厚的民间化色彩。
位于海南岛中部五指山南麓的槟榔谷附近的黎族村庄,正式公共空间有村民会议、村民代表大会;非正式空间有村头的小卖部、村里的红白喜事活动、每户住宅前空地、田间、洗衣码头等。由于“汉在外围,黎在腹地”的地理位置,旅游开发前,村庄生活较为贫困,与外界联系甚少,男女老少的交流基本集中在村庄内部。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村庄女性主要利用的公共空间是非正式空间,如在田间劳动、码头洗衣时交流信息。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变迁,槟榔谷黎族村庄的公共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不管是正式的公共空间还是非正式的公共空间,都已经大大地萎缩了。就正式的公共空间而言,随着近些年来相关的农村政策尤其是土地二轮承包和税费改革之后,村集体基本上已完全虚化和空壳化,使得村集体组织的权威大大下降,导致村民与村集体的实质性关联已基本断裂,因此村庄公共活动日益减少。对于槟榔谷这种传统组织资源稀缺的黎族村庄而言,这种变化不仅使得村庄丧失了联结的纽带,而且直接导致了公共权威的式微和公共空间的萎缩。其次,随着农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日趋多元化,村庄异质性增强,这必然使得村民对公共空间需求的面向和程度的差异不断加大,从而提高了村庄公共空间形成与维持的成本。就非正式公共空间而言,许多人的生活面向已经在村庄之外,长年在外打工,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村庄生活之中。随着电器的普及和电视文化的全面渗透,大热天村民聚集门前纳凉聊天的情景不复存在,原先全村共享的河塘边不再聚集村民交流信息和组织活动。同时,年轻人也不再热衷参与红白喜事活动,很多都是老年人在承办。在很多地方,各个传统节日(包括春节),各种集体娱乐活动如舞龙灯、琼剧表演等也在逐步衰落。
总之,在日益向乡村社会渗透的市场经济因素和导致乡村组织权威不断衰弱的农村政策的双重影响之下,槟榔谷公共空间的迅速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大背景下,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以人们经常性的、面对面的沟通所形成的“熟人社会”[2](P33)的乡村已经变成了贺雪峰眼中的“半熟人社会”[3](P15)。
公共空间的萎缩对槟榔谷黎族村庄男女两性的影响都是存在的,但对女性的影响尤甚,因为旅游开发前陆续已有年轻男子外出打工,对于留守家园的女性而言,电视成为她们休闲和文化娱乐的首选。在此背景下,黎族女性与社会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可能发生连锁反应的支持系统都发生了改变,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女性社会网络的缩小和可动用社会资本的减少。女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及活动范围非常有限,一般仅局限于本村和娘家所在的村落,偶尔会因去乡里买东西或者办事而扩展到乡镇。同时,她们接触的人也比较少,主要是家人和周围的村民,和村里的领导几乎不打交道,也很少接触村落圈子以外的人和事。公共空间的有限导致了她们的信息搜集能力和拥有程度的下降,也进一步导致了她们在社会资本积聚方面的劣势。
三、特有公共空间的扩展:槟榔谷民族旅游对黎族女性的影响
(一)保亭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与黎族女性的参与
海南保亭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成立于1998年,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多形态的,集观光游览、文化展示、民俗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少数民族型旅游景区,以经营具有浓烈民族风情的饮食、歌舞表演、文化活动而出名。近在咫尺的槟榔谷的开发,让附近的黎族村寨“越来越深地进入或被卷入一个开放、流动、分工的社会化体系”[4]。旅游经济的发展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了就业机会,增加了经济收入,但从扩展公共空间的角度来说,槟榔谷针对黎族女性主要有两项特殊意义的活动:一是黎族织锦染绣纺织所;二是黎族女子歌舞队。这两项活动为女性活动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特有公共空间。
(二)特有公共空间的扩展:槟榔谷民族旅游对黎族女性的影响
其一,黎族织锦染绣纺织所。槟榔谷的黎族织锦染绣纺织所设置在景区的东南角,占地大约200平方米,墙上泛黄的照片展示着黎锦这项古老技术的发展史,里面陈设着一些纺织工具,80人左右的黎族女性正在织锦。纺织所由当地政府投资兴办,在发展过程中也一直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政府提供原材料和纺织工具,免费进行技术指导。纺织所除了两名管理人员和一名技术指导外,其他人都来去自由,景区附近村庄的女性在农闲、旅游淡季都可以来学习纺织,纺织成品在景区销售或者供应其他景区,按件记工资,工作时间不定,可随来随走。如果每月工作满时,熟练工每月2000元左右,学徒每月最低500元。由于管理极为自由和松散,纺织所对女性具有很强的吸纳性,而且编织的时候可以聊天,村里重大的问题或事情都成了评论的对象和内容,人们在此交换信息,自由发表个人意见,表达对事件的看法。可以说,这里成了信息聚集与交换的集中地。宽松的管理和自由的氛围吸引了附近村庄的很多女性,纺织所因此成了当地黎族女性最喜欢的活动场所。而且,由于每年开展一次保亭黎族织锦染绣技艺比赛,黎族织锦染绣纺织所的公共空间又有所扩展。技艺比赛在弘扬民族文化,抢救、挖掘民族民间工艺的同时,也为黎族女性提供了宝贵的技艺展示和信息交流的机会。参与的过程——报名、寻找合作者、层层选拔、集中秀艺,为女性提供了与外界交流和自我成长的机会,也使得一些有才能的女性脱颖而出,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其二,槟榔谷黎族女子歌舞队。槟榔谷黎族女子歌舞队是专门由黎族女性组成,表演黎族歌舞的团队,成员大约有50人左右。这些女性大多年轻漂亮,性格活泼。固定表演的歌舞有《种山兰的女人》、《插秧女》等。歌舞队的女性都是专职,旅游旺季一天要表演四到五场,淡季表演二到三场,没有表演时多在训练或者研究新的表演节目,每月工资在3500元左右,根据表演场数可适当增减。女子歌舞队对年轻女性而言是极具凝聚力的公共空间:首先,女子歌舞队相对于其他工种在景区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她们对表演的歌舞编排有一定的决定权。作为景区的台柱子,她们有时甚至可以就收入和老板讨价还价,而且歌舞队成员除表演外,其他时间都要聚集在一起训练,因此歌舞队的成员有很强的集体归属感。其次,女子歌舞队的成员有很强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她们年轻漂亮,经过专门训练,气质落落大方,随着歌舞队外出表演的机会增多,她们的眼界和思想不断开阔。最后,歌舞队的很多成员扩展了人际关系,积累了社会资本,找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如三亚黎族风情园的老板ZGL就曾是槟榔谷女子歌舞队的一员,由于在歌舞队表现突出,而后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和集聚的社会资本创办了黎族风情园。
四、公共空间的扩展对黎族女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公共空间视角为研究人及其活动的微观层面提供了中观载体。因为社会资本的生产与人们的活动及其活动场所的范围、频率是密切相关的。当人们处于同一场景和空间时,会受到此场景的规范制约,进而在该规范制约下活动——这使得人们易产生“同感”、“共识”,乃至形成共同的情感空间和价值观念,而这些促使原本分散的个体集结的相互关联网,是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因此,公共空间的扩展对村庄的个体发展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董磊明指出,对于村庄,诸如舞蹈队、篮球队以及老年人协会等文化类合作组织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它们对于拓展农村公共空间、培育社会资本是十分有益的。[5]
(一)社会资本的累积和社交网络的扩大
黎族织锦染绣纺织所和女子歌舞队为女性单个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在其中所呈现出来的群体行动能力、为社会资本积累和个体社交网络的扩大提供了良好的交往平台。“社会资本必定和共同在场情境中发生的互动有关,不同社区或社会的成员之间的任何接触,无论涉及的范围有多么广泛,都涉及共同在场的情境,即共同在场的情境总是承载互动的主要情境。”[6](P238~239)在村庄公共空间不断萎缩的背景下,纺织所和歌舞队为女性社会互动和社交网络的扩大提供了日常活动的场所,逐渐成为信息交流共享、形成新认同的积极媒介。所以,纺织所和歌舞队这样专门为女性提供的公共空间不仅仅是女性谋取生计的平台,更是女性积累社会资本、扩大社交网络的支柱。其一,纺织所和歌舞队的存在使女性的社交平台开始发生转移,社交网络半径扩大,对外互动的广度和深度也相应增加。特别是纺织所,由于没有条件限制,上到60岁、下到15岁的女性都可以参与其中,女性结交的社会圈子扩大,较高的互动频率和较灵活的互动方式也促进了彼此的感情交流。有些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在生病、盖房子、农忙时都能很好地互助,有的甚至超过了亲缘关系,体现了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所说的“功能替代”[7](P78)。其二,随着女性互动频率以及分享社会信息资源、积累社会资本机会的增加,她们为家庭成员特别是男性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赚钱渠道的可能性随之增加,这也为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声望的提高提供了保障。其三,一些黎族女性在增加经济收入、扩展公共空间和积累社会资本的同时,开拓新天地,如合伙或者独立创办黎族民俗文化村、农家乐、家庭旅馆等旅游产品,这些都为当地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性别文化的重塑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二)公共空间的扩展对黎族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性别哲学中,女性生活方式是一个以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女性为中心进行研究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综合性理论范畴,主要探讨女性的生存状况、活动方式和发展等问题,其基本特征是从女性日常生活方式和自身发展的角度来体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作为一幅由社会各要素相互作用而交织起来的动态画面,女性生活方式对于理解和把握“男女平等”等宏观命题具有特殊意义:内隐着价值观念与社会建构的生活方式的变迁,可以从女性日常行动策略的实践层面折射出宏观叙事的男女平等。所以,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在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为男女平等获得一个前所未有的广阔行动空间。基于此,当代西方大师级学者安东尼·吉登斯在“后现代”语境中,提出了“生活政治”概念。吉登斯认为,作为“进步主义的启蒙运动的普遍律令”[8](P10)的解放政治,不仅表现为打破传统非合理社会制度的全面控制,同时它也可以表现为个体对自身生活方式的调整和选择,以及一切有利于自我实现的生活和行动。如果说以“打破父权传统枷锁、推翻性别压迫”为旨归的现代妇女解放运动是典型的解放政治实践,那么广大女性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广泛行使自主权利,即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认同、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哪怕它们是日常生活琐事,都可以成为性别平等的合法内容甚至经常性内容,都可以达到吉登斯所说的“生活方式”的政治。就槟榔谷的黎族女性群体而言,她们的生活得益于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在旅游业中特有公共空间的提供,旅游业的发展与她们的“生活政治”之间紧密的“交互”式关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恰恰是旅游业的兴盛带来了当地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女性生活方式的改变反过来又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繁荣。在槟榔谷的黎族女性群体中,具体表现为:女性特有公共空间的提供为改变黎族女性的日常生活方式提供了平台和机会。可以说,纺织所和歌舞队的存在使旅游开发前沉迷在电视机前的大多数黎族女性的休闲生活得到了彻底的改变。因此纺织所和歌舞队的出现不仅提高了女性的经济收入,还改变了她们的生活方式。随着见识和信息量的增大,相比生活在封闭环境中的女性,她们对生活有更多的思考,主体意识较少受到外部或者家人的干扰。特别是女子歌舞队成员,本身年轻漂亮,外出演出机会较多,因此,她们对编排舞蹈、演出要求都有较大的自主权。也许她们的主体意识不是旨在谋求“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经济运动,但这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实践勃发于社会微观、分散的文化话语系统中,并在集体以及个人的行动中清晰地呈现出女性当家做主的主观能动性。如果运用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理念来解释,那就是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女性,她们解放的政治要求和表达虽不是围绕着某项特殊的政治利益或者经济利益而展开,甚至她们可能都没有这种主动的意识,但谁都不能否认,公共空间的提供给她们带来了生活质量的提高、生活方式的调整,以及她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家庭地位的提高和当地性别文化的缓慢转变,而这正是性别哲学所期望的。
参考文献:
[1]朱静辉.秩序与整合:村落多元公共空间的建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1).
[2]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3]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调查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徐勇.“再识农户”与社会化小农的建构[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5]董磊明.村庄公共空间的萎缩与拓展[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5).
[6](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7](美)默顿.论理论社会学[M].何凡兴,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
[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