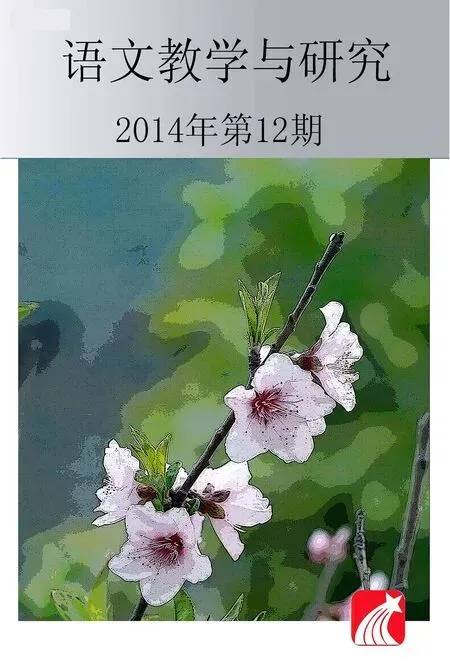归有光何须借书满架
2014-02-06陈凤兰
陈凤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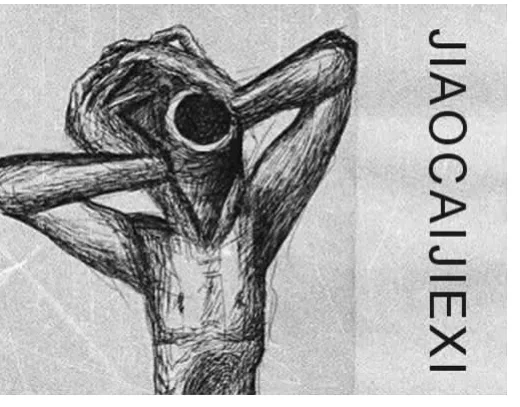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五教材中选用了明朝散文家归有光的名作《项脊轩志》,文中,作者感叹“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坐,万籁有声”。对于这一句话,苏教版教参解释为“借来的图书堆满了书架,我在这里生活悠然自得,有时长啸或吟唱,有时静悄悄地独自坐着,自然界的声响都能清晰地听到”。稍有一点思维的教师和学生都不免好奇起来,为什么归有光要“借书满架”呢?这似乎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呀。
我们首先来了解归有光的家庭背景。归有光1507年出生于一个世绅家庭,家境并不富有,但也算是书香门第。他幼时寄养在外祖父家,从《项脊轩志》文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句“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这一句话,可以看出归有光祖上定是读书为官之人家。归有光年少时便悟性过人,9岁能撰写文章。其父朋友看了他写的文章,就指他有司马迁、班超的遗风。由于聪颖好学,20岁时归有光已经通览了《诗经》 《史记》等六经三史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这也是他得以跻身韩愈、欧阳修等杰出散文家行列的最主要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博览群书的归有光应该得益于他的读书的祖传家风,得益于祖传的古籍藏书。对于嗜书如命的读书人而言,归有光拥有一架子书似乎完全可能,而无须向别人去借书。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讲,借别人的书来放满书架,倒也滑稽可笑。查找《词源》,“借”的解释中有“暂时使用别人的东西”,对这一义项,举了一个例子“借书一痴”。“借书一痴”源自唐代李济翁《资暇集》“古谚‘借书一嗤,还书一嗤’,后人讹为‘痴’”。相当时间内,古人总以为此话理解成“自己有书借给别人看,是傻瓜;借了别人的书还给别人送去,也是傻瓜”。与孔乙己一样认为“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但是礼仪之邦内读书人,以君子遗风为荣,怎么会以占有人家的书籍为荣,还以还书为傻帽呢?宋朝邵博等人最终作出了更正“‘痴’当做‘瓻’,瓻为酒器,借书以瓻为酬”。这样理解才符合“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德习惯。既然借书者都以酒为借书的报酬,足见借书人的愧疚与感激。作为正直耿介的归有光怎么会借别人满满一架子书来充门面,还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呢?这在文人圈里,不是最令人不齿的事情吗?明初宋濂在《送东阳马生序》中说:“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马克·吐温还开玩笑说“书和老婆恕不借人”,归有光如果总借书不还,恐怕也不会再有人借书给他了,哪来的一架子书呢?
那么,“借书满架”中的“借”到底是何意呢?其实“借”的繁体字为“藉”。在辞海中“藉藉”解释为“杂乱众多”。这样的例子课本中也有,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中有这样一句“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解释为许多死人互相压着,说明死人之多,错乱压着。苏轼的《赤壁赋》也有这样一句“相与枕藉乎舟中”,“枕藉”即“物体纵横相枕而卧,言其多而杂乱”。再加上我们所熟悉的“狼藉”的本义就解释为“像狼窝里的草那样杂乱不堪”。由此可见“藉”本意指“错乱不整貌,杂乱众多的样子”。结合作品,文中的“借书”应解为“纵横交错的书或者杂乱众多的书”。一是说作者书多;二是作者谦虚,说自己不会收拾整理,或是专注于书中的世界,懒得收拾整理,以致有些狼藉。
其实,不会收拾整理的何止归有光一个。虽然古人常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在古代,大丈夫孜孜于读书,家中凌乱不堪的例子比比皆是。庾信《寒园即目诗》:“游仙半壁画,隐士一床书。”卢照邻《长安古意》:“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在当时诗中的“床”并不是指用来睡觉的床,而是几案,学案。诗人读过书后,随手就放在桌上,读的书多了,自然就枕藉在一起。现代诗人余光中也说: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结果他的书斋不时闹“书灾”。毛泽东晚年若不是有人帮他收拾,恐怕也会“一床明月半床书”“三更有梦书作枕”啦。
读书人之事,确实有许多掌故。但是归有光的“借书满架”无论从感性还是理性的角度,恐怕都不可以解释为“借来的书籍放满书架”,夸张一点讲,那简直是对归有光人格的侮辱与亵渎。我想全国各种语文教材中,作这种解释的恐怕还有,在此提出,供同仁参考,还望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