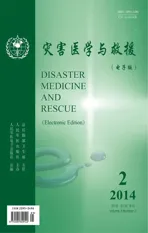院外急救有效实施的伦理问题探讨
2014-01-25盛家鹏,陈志刚
医学兼具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双重属性,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医师之于患者乃子女视于父母[1],正所谓“医无德,不堪为医”。《全球医学教育最低基本要求》中明确指出,医疗实践的核心是“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院外急救工作如何秉承仁爱之心、敬畏之心,本着爱人、重人、亲人的医患之心,解除患者之急、之痛、之病,构建医患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的和谐关系,是院外急救有效实施的伦理行为的核心之重。
1 院外急救首先应尊重患者,加强医患沟通
我国以“120”特服号码为标志进行院外急救医疗服务,遵循现代生命伦理学建立的4个基本原则:有利、不伤害、尊重自主、公正。分析其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其中首先应该检讨的是没有学会尊重患者、未能实现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如今急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促进了院外急救事业的发展,硬件性能取得了快速提升,但软件中的人却不断受到伦理道德元素的冲击,必须制定岗位伦理道德行为规范,培养职业伦理道德,使其在工作中自觉运用伦理道德规范言行,提高医疗服务质量。笔者建议在急救医疗机构中设立伦理委员会,培养正确的院外急救伦理价值观,以医、技、言、行打造一支“德馨、技强、知广、心高”的院外急救队伍[2]。
2 完善流程,应用“不伤害”原则开展急救
刘魁等[3]指出医务人员运用“不伤害”原则,可以具体分析和解决医患伦理难题,并提出了生命伦理学意义上的“不伤害”原则4方面的义务要求:医学作为一种道德事业要求从业人员怀有为患者幸福服务的动机和目的、适当的关怀、风险利益的评估、有害利益的评估。院外急救是为捍卫人权中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在医疗服务的过程中需要执行一定的操作流程,但是由于院前急救现场复杂多变故而存在伤害的风险(包括自身存在的风险和对患者的风险)。风险存在时对急救效果和结果存在重要的影响,甚至有直接导致急救失败的可能。同时,为保障患者的根本利益,尊重他(她)们的价值和尊严,应避免因治疗带来的伤害,做到即使不能使患者受益,至少也不应当伤害他[4]。因而制定《院外急救现场安全条例》和《院外急救现场施救流程》等,首先应该尽可能细化流程并不断完善。同时,应该加入现场风险评估的环节,一方面需尽可能避免自身受到意外损伤影响救治,另一方面也是避免让患者受到二次伤害,而在现场及转送患者的途中更应积极运用“不伤害”原则。
3 对新规范、新技术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对急诊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出现了一些实用的指南和急救技术,比如,《AHA CPR&ECC指南》等。尽管这些指南也在不断地调整和修订,但只有严格按照复苏指南的要求去做,才能获得最高的抢救成功率[5]。作为一个急救人员,当被患者召唤时必须立即展开抢救行动,及时掌握新的医学知识才可能提高抢救成功率,而且在院前急救过程中实践医学新知识时也应及时总结经验,比如《2010年AHA CPR&ECC指南》中将原成人的胸部按压深度3~4 cm改变为“建议为至少5 cm”,按压频率至少100次/分。究竟如何才能确保如此高质量地执行心肺复苏,包括在高速行驶的急救车中,需要广大的院外急救医师不断学习、实践、探索和创新。钱方毅等[6]指出新指南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对所有施救者及患者均适用,应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运用。目前一些新的复苏方法,如胸外提压和腹部提压等方法[7]在积极有序地酝酿与探索,对待这些新的技术,急救医师既要认真学习又要有科学的态度,积极实践认证,争取早日找到一种简便易行、安全有效的急救方法,为患者服务。
4 研究灾害伦理,优化群体伤害施救顺序
众所周知,避祸躲灾时通常遵从老弱妇孺优先的顺位选择原则,但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年纪越小将来对社会的贡献可能愈大,面对同等伤情,在急救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该如何选择呢?从社会伦理学角度分析,同等或相似伤害的情况下应遵从老年人、妇女、小孩优先原则,这对年轻男性来说可能增加了死亡或伤残的危险,对于他们来说将受到更多的伦理道德考验。国际上群体伤害中一般遵循检伤原则,大致分为:立即治疗(T1)、延后治疗(T2)、轻伤治疗(T3)及期待治疗(T4)共4级,分别用红色(T1)、黄色(T2)、绿色(T3)、黑色或白色(T4)来加以区别和显示。有的人认为上述救治的顺序涉及见死不救,是不人道的。但多数专家认为以有限的医疗资源去全力抢救那些实在无法抢救的危重伤病员,而使得更多的那些本来经过紧急抢救可以挽救生命的伤病员失去生命,这才是真正不人道的[8]。王宏等[9]从伦理学角度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伤员的检伤分类原则进行研究后指出,检伤分类符合公平原则、功利原则、科学决策原则,但在检伤标准、伤情与伤势判断、分类流向、分类处置等几个关键环节上必须严把关口,才能避免主观偏差与人为失误,降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伤员伤死率和伤残率。故此正确的选择方案,必须结合伦理学、社会学、医学等多方面进行思考后做出最终的选择。
5 个性化告知,把握现场告知服务的权重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建立,将医患之间的人文关系整体化,根据我国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对患者的医学告知服务是必要的。院前医疗通常针对治疗措施选择、就医意愿、心肺复苏终止、检查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等告知,而且在院前现场救治过程中心理权重的比重是大大增加的,具体表现为院前急救现场情况复杂多变、患者或家人面对突发情况时更容易出现情绪失控,可表现出害怕、恐慌、担心、焦虑,甚至是对死亡的恐惧等。因此现场如何告知,从告知方式、时间到内容的选择等都需要斟酌。比如,我国对于终止心肺复苏未有明确的法律界定,而且当具有同等地位的权利人主张不一致时,只要有一人提出需要继续抢救,就必须选择积极救治,只有当拒绝者的行为妨碍到医师的救治行为时,才能出现不救治免责的法定事由,且此时必须做好“救治因客观受阻而不能”的书证[10-11]。个性化的告知服务是一门艺术,只有熟练运用好这门艺术,准确把握告知度才能做到对患者真正有利,满足院前急救的救治要求,满足医患和社会和谐的要求。
总之,医疗卫生服务同民生息息相关,院外急救在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同时应注重体现社会公益性事业的本质,而医学伦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为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12],院外急救工作者应当努力学习和实践这门科学。
[1]吴孟超.医学发展需重视人文素质[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2,19(6):1-2.
[2]陈志刚.构筑伦理道德防线 提高院前急救质量[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1):61-63.
[3]刘 魁,李 遥.医患矛盾:应用伦理学视角的解答[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0(4):104-107.
[4]颜 婕.转型期医患关系紧张根源分析与对策思考[J].中国医院管理,2010,30(11):87-88.
[5]廖晓星.现场急救中的几个法律和伦理问题[J].中国急救医学,2006,26(6):444-445.
[6]钱方毅,李宗浩.心肺复苏和心血管急救的新观点——解读2010年AHA CPR&ECC指南[J].中国急救复苏与灾害医学杂志,2010,5(11):994-996,1032.
[7]王立祥,孙 鲲,马立芝,等.腹部提压 胸外提压和胸外按压对心搏骤停患者肺潮气量的影响[J].中国急救医学,2009,29(9):784-785.
[8]赵兴吉.院前急救在灾难救援中的作用[J].中华急诊医学杂志,2007,16(11):1125-1127.
[9]王 宏,王海威,陈永鹏,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检伤分类原则的伦理学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1):57-58,118.
[10]宋秋忆,周海滨,宋因力,等.院前心搏骤停急救中各环节医疗纠纷的分析与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5):32-33,52.
[11]张军根,张天乔.院前急救中易被忽视的几个法律问题分析与对策[J].医学与社会,2008,21(4):49-51.
[12]伍天章.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医学伦理学教育体系[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5,18(1):25-27.
(收稿:2014-01-09修回:2014-03-04编校:丁艳玲)
院外急救有效实施的伦理问题探讨
盛家鹏,陈志刚
院外急救;伦理问题
R 052
A
2095-3496(2014)02-0094-02
212003江苏镇江,镇江市急救中心(盛家鹏,陈志刚)
陈志刚,E-mail:cxc_2002@139.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