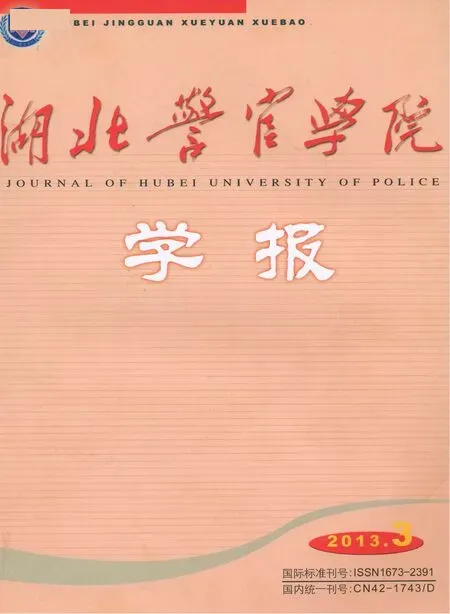盗窃罪既遂标准研究:以新型盗窃为视角
2013-04-11王丽超
谢 婷,王丽超
(华东政法大学,上海200042)
一、盗窃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概述
犯罪既遂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确认犯罪是否既遂,应以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具备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为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将盗窃罪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原来的基础上新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三种行为,由于该罪名属于简明罪状,因此,如何在法条的基础上认定盗窃既遂就成为理论和实践中的难点。
根据德日现有的刑法理论,盗窃罪的既未遂理论学说有以下四种:(1)接触说。以犯罪分子实际接触到盗窃对象为标准,即只要接触到财物即可认定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2)转移说。持该学说的学者认为只要将盗窃对象从其本身所在位置转移即认定为盗窃既遂,反之则为未遂。(3)藏匿说。该学说认为将财物藏匿于某地即可认定为盗窃既遂。(4)取得说。持该学说观点的学者认为犯罪人将财物取得于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的为盗窃既遂[1]。
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盗窃既遂的标准也有四种学说,其中,前三种与德日盗窃既遂认定标准相同,但第四种学说在我国被称为控制说。此外,与上述四种学说不同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失控说、失控说或控制说、失控加控制说以及折中说。(1)失控说。以财物所有人丧失对财物的占有和控制为认定标准。(2)失控或控制说。此学说为复合选择标准,以财务所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或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两者居其一即可认定为既遂。(3)失控且控制说。此观点为复合标准,以财物所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并且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为标准。(4)折衷说。此学说将财物分为普通财物和特殊财物,对普通财物以所有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为既遂标准,对特殊财物(如细小的珠宝)应当以行为人取得对财物的控制权为既遂标准。
目前,我国刑法理论界以失控说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其理由如下:第一,我国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于盗窃罪采用“失控说”更能体现刑法保护法益的目的。从盗窃对象考虑,在所有人失去财物的控制权时,这就已经打破了该财物的所有权,其法律后果等同于盗窃实施者对财物的占有。如果将“控制说”设为盗窃既遂的标准,就会产生放纵盗窃行为的嫌疑。第二,盗窃罪是目的犯,对于目的犯的认定,并不以目的的达成为既遂标准。“目的没有实现,也可能是既遂而不是未遂”[2]。对于盗窃这一行为本身而言,不能把行为人对财物的控制作为区分既遂和未遂的界限;就盗窃罪这一刑法罪名而言,其保护的法益在于被害人对财物的有效控制,以此为出发点,即使行为人未能获得对财物的有效控制也不影响盗窃既遂的成立。[3]第三,从盗窃罪的保护法益上看,盗窃罪保护的是公民的财产权利,当被害人失去对自身财物的控制时,其被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即被侵害,构成了既遂的条件。从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用“重典”的立法精神来看,现阶段我国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党和政府决心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使用失控说而抛弃控制说能更大范围地保护公民合法财产不受侵犯,更能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提供刑法保障后盾。从以上立法意图出发,我国采用失控说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更符合目前我国立法实际要求,体现了我国刑法对盗窃罪用“重典”的立法精神。
二、以失控说评析新型盗窃的既遂标准
由于扒窃、携带凶器盗窃、入户盗窃这三类新型盗窃是《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三类行为,以下笔者即从失控说这一通说评析其既遂标准。
(一)扒窃
扒窃是发生在特定的场合,将他人的贴身物品占为己有的行为。扒窃的场所一般为公共场所,如:街道、公交车、或者饭店、旅馆等公开性较强的场合。扒窃行为具有发生地点的不特定性,认定扒窃行为的既遂标准也应当区别于一般的盗窃行为。对于新型盗窃的既遂标准,按照失控说的原理,行为人只要将财物从被害人口袋或者包中拿出,使得被害人脱离其对原有财物的控制即应当认定为扒窃行为的既遂,如果并未使得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即认定为未遂。
(二)携带凶器盗窃
对于“携带凶器盗窃”的理解与认定,可以参照1997年11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和2005年6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补充规定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解释。据此,所谓“携带凶器盗窃”是指行为人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盗窃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器械进行盗窃的行为。立法者将“携带凶器盗窃”入罪的目的在于其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一般盗窃行为更为严重,携带凶器盗窃中的携带凶器使得人身危险性潜藏于该行为中,携带凶器更容易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从而为犯罪分子“壮胆”。理论界多数认为携带凶器盗窃犯罪的构成要件没有数额和次数方面的限制。首先,从法条的逻辑上看,对于数额和次数的限制性规定已在本条以并列方式列举。其次,与立法本意相悖。之所以将携带凶器盗窃规定为犯罪,主要是考虑到该行为不但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也对他人的生命健康权形成潜在的危害,故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都较一般的盗窃更为严重。达到这一危险,构成犯罪便不需具备数额要求。当然携带凶器盗窃仍然是盗窃的一种,仍然需要行为人将财物脱离被害人的控制范围。
(三)入户盗窃
入户盗窃即行为人潜入户内实施盗窃犯罪的行为。认定入户盗窃的既遂,应按照失控说的标准,即行为人的盗窃行为使得被害人财物脱离其“户内”。按照现有共识,入户盗窃既遂以行为人将被盗财物转移至被害人户外为标准,一旦行为人将财物转移到被害人户外,即认定为入户盗窃的既遂,未能转移到户外的认定为盗窃未遂。此外,对于盗窃对象为小物件时,行为人即使未能将财物转移到户外也算是既遂,只要其脱离被害人的控制范围即可。如何认定户内,应按照区域性质进行划分。倘若是在城市的楼房,户内与户外应以房门为界限。行为人踏出房门即认定控制了被盗财物,走廊及楼梯、小区则不属于户主的控制范围;倘若是在农村,由于人们所住的房子往往含有大院,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户外应该是指院子的大门之外,如果行为人实施盗窃时并未走出院门即被发现并被擒拿,则应当认定为盗窃罪的未遂。
三、简析新型盗窃既遂标准认定,兼论失控说标准的完善
原则上以失控说为盗窃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是科学可行的,但由于新型盗窃罪的特殊性,要正确判定既遂与未遂,不能形式主义,必须不同类型区别对待,即要根据盗窃的场所、时间、对象等不同,做出客观、科学的分析。在笔者看来,理论上关于既遂标准的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并不能起到实际的效用,这或许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差距。下面笔者分三类分别论述如何完善失控说在新型盗窃上的适用。
(一)关于扒窃
扒窃发案率十分高,虽然《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扒窃是行为犯,只要实施了扒窃行为,即认定为犯罪,然而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将其认定为数额犯,有的单位要求扒窃行为必须多次,有的单位要求扒窃数额必须达到800元以上。司法工作人员大多遵循这一潜规则,其理由为:若将每一个扒窃行为入罪,则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使得司法人员每日埋头于数额极小的扒窃案卷之中,影响其他司法工作的正常进行。“扒窃”并非刑法规范用语,它属于行政法概念与犯罪学领域,是公安机关特别是一线反扒民阶段由不同业务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还是由哪一个业务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在即,这一问题如不处理好将会影响到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质量与效率,进而影响到整个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设立,乃至于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事实上,在新《刑事诉讼法》正式通过之前的2011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公布伊始,有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应由检察机关哪个业务部门负责或哪些业务部门负责就已经引起学界与实务部门的讨论,并持续至今。笔者起初的想法是基于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赋予检察机关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一新职能,在检察机关内部再新设一个专门的业务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在学术界,有的立足于检察机关所处的特殊地位,要求完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在明确人民检察院是“法律监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的同时,按诉讼流程确立检察机关自侦、公诉、侦监等业务部门分别履行“法定职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20]有的基于侦查监督部门兼有审查逮捕和侦查监督职能,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仍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即审查批捕部门进行为宜。根据检察机关内部职权分工,侦查监督部门主要履行审查批捕的职能。在批准逮捕之后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实质上是批捕职能的延伸和继续。”[21]也有的建议以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监所检察部门等业务部门中的某一部门为主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其他相关业务部门辅助配合。还有的认为羁押必要性审查应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因为,“监所检察部门均在看守所设有驻所检察室,其职责范围就是监督看守所的监管秩序和保障在押人员的合法权利,其对此的参与属于在本职工作的管理机制内运行。”[22]等等。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从本质上说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检察机关的职责所在(审查后一般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决定是否羁押),它是检察机关作为一个整体,依法履行的一项职能,而不是检察机关内部哪个或哪些部门享有的职权,这是首先需要明确的。至于检察机关通过内部职能配置,明确由哪个部门或哪几个部门行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则是检察机关在宪法赋予其的法律监督职能基础上,细化法律监督职能的结果,以及由此带来的检察机关内设业务部门的职能变化及其分工调整。
基于此,上述哪个观点更有道理,也就是检察机关哪个或哪些业务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更合适呢?
首先,要排斥掉笔者自己最初提出的新设一个业务部门来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设想。因为在当前检察机关机构精简的大前提下,无此必要,而且仔细分析,当前检察机关的一些内设业务部门足以履行好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
其次,笔者也不赞成按诉讼流程确立检察机关自侦、公诉、侦监等业务部门分别履行“法定职责型”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责。按照诉讼流程,分别由不同业务部门根据办案需要动态地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虽有可能强化检察机关内部制约功能,但是,容易滋生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影响办案效率。“分阶段负责的职权体系之所以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主要原因就是,各职能部门做这项工作会导致自身利益受损而缺乏动力。”[23]而由一个业务部门主要负责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其他业务部门协助与配合,承担次要责任,如果对各业务部门的职责划分不清楚或把握不准同样也容易出现弱化内部制约、推诿扯皮等问题。例如,由公诉部门主要负责,则容易对其后期的审查起诉工作产生影响,并且公诉部门审查移送起诉案件时,本身还有查明采取的强制措施是否适当的职责。
再次,笔者也不倾向于由侦查监督部门负责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尽管从目前来看,侦查监督部门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承担审查逮捕职责的部门,在审查逮捕阶段确实还能做到一定程度的客观中立,而且其还有人员配备、熟悉案件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情况等有利条件,但是,侦查监督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最大弊端在于缺乏对侦查监督部门逮捕必要性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制约,而且,侦查监督部门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逮捕决定作出以后,其客观中立性就不存在了,“没有客观中立性,再多的便利也会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搁置。”[24]因此,在自己做出批捕决定后,再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易遭人诟病。
最后,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存在着案件信息掌握不全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情况不了解等问题。不过权衡利弊,从目前监所检察部门职能配置,以及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看,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比较合适,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论证。
三、确定监所检察部门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之分析
笔者之所以倾向于由监所检察部门独立行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其原因除了如前所述检察机关其他业务部门行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可能存在的弊端以外,主要还是考虑到监所监察部门在我国检察机关内部的职能定位、强化检察机关内部制约的需要、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是否有利于监所检察部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等因素。
首先,设置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的初衷与监所检察部门履行职责的目的基本契合。“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作用在于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可见,该规定出台的直接目的是要解决实践中遇到的羁押率过高、超期羁押等比较棘手的问题。”[25]①《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也明确指出:“为强化人民检察院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建议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逮捕后,人民检察院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2011-08/30/content_1668503.htm,2012年11月10日访问。而根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为了有效地履行法律职责,更好地保障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设置了监所检察部门,专门负责对监狱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监管改造罪犯的活动以及看守所羁押监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法律监督,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监所检察制度……人民检察院的监所检察部门在保护被羁押人人权方面的主要工作职责是:(一)监督看守所依法收押和释放,防止当事人被非法羁押和超期羁押,保障公民不受任意拘留和逮捕。”[26]在发现看守所有违法羁押或超期羁押情况时,向监管机关或办案机关提出纠正意见。《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办法》第3条也规定:“人民检察院看守所检察的职责是:……
(二)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期限是否合法实行监督……”。由是观之,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确立的检察机关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与目前监所检察部门的职能基本上是契合的。而且,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厅袁其国厅长所指出的,“刑诉法修改后,新增了诸如居所监视、强制医疗监督等内容,调整了看守所的羁押期限。这些内容改变了监所承担责任的范围,落实在具体制度里,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应该由监所部门承担。”[27]如果把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交给监所检察部门,只需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过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来对检察机关的内部职能分配做相应调整,增加监所检察部门行使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并细化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方法。
其次,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是强化检察机关内部制约的需要。“从具体权能的配置讲,检察权虽是检察机关整体的权力,但在权力运行中进行合理分配和制约是必要的。”[28]因此,在明确检察机关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同时,将逮捕必要性审查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分别交由侦查监督部门和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完善侦查监督业务与监所检察业务之间职能的进一步分工,使它们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配合,又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以强化检察机关内部在刑事司法中的制约,提升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客观需要。如果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交由侦查监督部门行使,其既审查批准或决定逮捕,又对捕后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这显然不及把这两项职能分别交由侦查监督部门与监所检察部门行使,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一种制衡效果好。很难相信侦查监督部门在作出逮捕决定后,还会在后来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中继续保持一定的中立性,去损害自身的利益。“只有内部职能的适当分工,才能有效地实行内部制约,保证检察权的不被滥用。”[29]
最后,新《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为监所检察部门行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提供了便利。为了更好地尊重与保障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维护他们的诉讼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防范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非法行为的发生,新《刑事诉讼法》第91条做了“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的规定,并在第11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由此申言之,对被羁押的被告人的讯问同样应该在看守所进行。一旦这些规定得以具体落实,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讯问将会在看守所进行,这肯定会增加监所检察部门,特别是看守所检察工作的强度,但是与此同时,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也将处于比检察机关其他业务部门更为有利的地位。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驻所检察机构可发挥自身优势,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入看守所起至判决正式执行之日止全程地进行审查和监督,全方位、同步获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捕后的第一手信息,对捕后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表现、思想状况进行跟踪、考察,评估其有无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有无妨害刑事诉讼进程的可能性。各地检察机关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试点工作也大都是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0][31][32]这也为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笔者倾向于由监所检察部门进行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是在检察机关内部各业务部门职能配置基础上,权衡优劣与利弊的结果。检察机关若确立由监所检察部门承担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最为迫切的莫过于调整监所检察部门职能,完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等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明确监所检察部门行使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职能;加强监所检察部门人员的配置,特别是加强派驻看守所检察人员配备;加强监所检察部门与自侦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公诉部门等之间被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信息沟通。同时,完善监所检察部门与看守所的信息共享机制。
[1][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杨百揆,刘庸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17-118.
[2]龙宗智.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68.
[3][4]易延友.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及其完善[J].法学研究,2012(3).
[5]王以真.外国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1.
[6][日]森际康友.司法伦理[M].于晓琪,沈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 10:276.
[7]朱孝清,张智辉.检察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365.
[8]刘春兰,张庆宇.审前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与权利救济研究——以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检察院为蓝本[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5).
[9]王会甫.继续羁押必要性:检察监督机制构建设想[J].人民检察,2010(5).
[10]刘晴,赵靖.检察机关执行羁押制度的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
[11]倪爱静.监所检察:探索建立审前羁押救济机制[J].人民检察,2010(12).
[12]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199-200.
[13]石京学,史金竹.安徽郎溪:探索“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评估”[N].检察日报,2010-11-14(3)
[14]游明得.论侦查法官于强制处分中所应扮演的角色[EB/OL].htt p://old.npf.org.tw/PUBLICATION/CL/089/C/CL-C-089-068.HT M,2012-11-11.
[15]谭世贵.中国司法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0.
[16]卞建林.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完善[J].法学家,2012(3).
[17][20]卢乐云.论“逮捕后对羁押的必要性继续审查”之适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6).
[18]黄太云.刑事诉讼法修改释义[J].人民检察,2012(8).
[19]万春,刘辰.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思考[J].人民检察,2012(16).
[21]卞建林,李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制度的健全与完善[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3).
[22]潘晓燕.变更强制措施程序中应发挥监所检察救济职能[N].检察日报,2012-04-11(3).
[23][24][31]李娜.新刑诉法实施迫近 第93条履职主体仍存争议如何克服高羁押率 专家提出监所检察审查羁押必要性可解“一押到底”[N].法制日报,2012-07-19(5).
[25]陈卫东.刑事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200.
[26]白泉民.监所检察与被羁押人的人权保护[A].白泉民.监所检察实务与理论研究[C].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9:326-327.
[27]黄洁,孔一颖.检察内部诉讼监督分工是难点[N].法制日报,201 2-06-18(5).
[28][29]孙谦.中国检察制度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5,11 2.
[30]龚培华,陈柏新.建立量化评估逮捕必要性司法机制的思考[J].人民检察,2012(18).
[32]但伟.试析羁押必要性审查与看守所检察[J].人民检察,2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