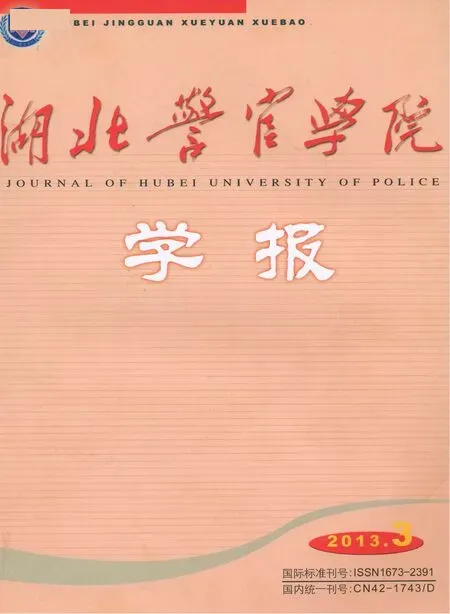论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2013-04-11杨春黎
杨春黎
(河西学院 政法学院,甘肃 张掖734000)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存在价值及产生发展
和解是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通过协商就争议的法律权益达成一致、终止争端的行为。刑事和解是指在犯罪结果发生之后,通过居中的第三方斡旋使犯罪人与被害人直接协商解决纠纷,旨在恢复已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被害人所受到的损害,防止被害人转变为加害人,并最终为犯罪者回归社会,平抑社会冲突而创造条件[1]。刑事和解理论是西方司法改革者在对如何在刑事司法体系中使犯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并能快速适应社会,又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保护而不致再进行行为的转变,出于这种目的,改革者提出此理论并实践于司法实务。
随着世界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被害人权利本位和社区秩序恢复的价值理念日益受到理论和实践界的重视。“被害人犯罪学”诞生于二战后,受此学说影响的国家很多,日本、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和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开始研究刑事和解制度并运用于司法实践。1957年英国的法改革者Margery Fry认为对于遭受人身、财产损害的被害人的权益不应该不重视,要保护并赔偿被害人,他本人也进行犯罪人和被害人的和解工作,目的是使人们重视被害人犯罪学。此学说突出了被害人的主体地位,通过赔偿被害人以实现实体与程序的正义。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最初10年并没有得到全面认同,此理论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犯罪人复归社会思潮的发展,刑事和解制度才真正成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制度改革的方向和法律政策的重要内容。
对刑事和解的实际价值进行解说是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前提。刑事和解制度的首要价值是公平正义。刑事和解制度使被害人处于诉讼的主体地位,不仅得到了经济补偿,更得到了精神抚慰。在我国,被害人在刑事司法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是十分有限的,通常情况下仅限于对加害人的控诉,控诉的实现通常要通过检察院的公权力实现。但处于法庭审判的对抗式的情境中,被告人可能会否认其罪行或缩小责任,且法庭的证据往往经过修饰,无法呈现事实的全貌,法官也只能依据证据法则来判断,“这种截然划分正确和错误的判决结论,很可能表现为两方对抗一方的强制结论,它会导致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难以或不可能再维持下去”[2],或者因证据不足,不能追究被告人的责任,这种情形下,会造成被害人的心理更加不平衡,甚至会造成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在我国刑法中,对被害人的保护最重要的是通过经济赔偿的方式实现精神方面的补偿。而现实是,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后,很难再履行民事责任甚至拒绝履行民事责任,现行机制对被害人的保护很难实现。刑事和解所体现的自愿对被害人的利益恢复,值得引鉴和吸收。
陈光中教授认为,和解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可以减少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很多学者认同此观点,认为和解有利于被害人利益、加害人利益的恢复以及国家与被害人利益的平衡。还有的学者认为刑事和解“节约国家刑事司法活动的成本耗费”,[3]司法领域对此项制度的关注也日益深入,本人认为在利弊之争依然并长期存在的情况下,在现有法律框架下进行观念更新和实践探索势在必行。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现实适应性
1.刑事和解制度的文化理论基础。刑事和解在我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儒学大师钱穆曾指出:“中国人乃在异中求同,其文化特征乃为求和性。”中国社会一直追求和谐,有学者将中国文化的精髓概括为“和合”文化,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到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无不体现了中国的和合文化特性,国人自古厌讼,社会发展至今也以和谐为主旋律,此种思想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思想基础。
2.“慎刑”法制思想和“世轻世重”的刑事政策。夏代已有了“明德慎罚”的法制思想,春秋时期的“以德去刑”,汉代的“德主刑辅”之道,到唐朝“宽仁治天下”的立法原则,孔子对此曾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正进入到高速、平稳发展时期,这为构建刑事和解提供了刑事政策上的有力支持。
三、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一)刑事和解制度构建存在的现实基础
1.加害人有罪答辩是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主观前提。加害人对自己有罪行为的承认意味着其认识到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内心真诚悔悟,给被害人以物质赔偿,兼顾精神性抚慰。
2.参与刑事和解的主体必须自愿。双方自愿是对于当事人真实意愿的实现基础,处于强迫或胁迫的刑事和解,是对被害人的第二次伤害,同时,也不利于加害人的真诚悔过和积极赔偿。
3.事实查清、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和解制度构建的客观条件。刑事和解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处于刑事和解的案件必须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和解双方的一方反悔,不履行和解协议,事后因时间的推移无法查明案件事实而不能保护双方利益。
4.刑事和解制度要在法律和公序良俗的范畴内构建。刑事和解不得违背法律和公序良俗,刑事和解是传统刑法公权力向私权在一定程度上的让渡,对被害人而言,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保护其主体地位和合法权益,对加害人而言,在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下,得以从轻或免于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有利于其回归社会。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
在新西兰、英国、法国、德国以及适用刑事和解制度的其他国家,根据其法律规定,早期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对象主要是未成年犯罪人,后来扩展到成年犯罪行为人,适用的范围仅限于轻微刑事案件。刑事和解的范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范围过宽,有可能瓦解社会对犯罪的认识评价体系,牺牲法治权威,影响国家刑罚权的有效实现[4];范围过窄,不利于充分发挥刑事和解的价值功能。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不宜将刑事和解做泛化解释,应限定一个范围,笔者认为应包括以下几类:
1.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适用于未成年人是各国通常的做法,这也是国际社会在刑事司法领域中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具体准则。未成年人处在身体发育和心理成长期,属于法定的从轻处罚情节,矫正其行为的可能性大,刑事和解作为轻型化、非刑罚化的制度理应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
2.轻微刑事案件。一般指可能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三年作为轻罪和重罪的区分点,我国刑事立法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如根据我国《刑法》第72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也对刑事和解制度有新的解读,如新《刑事诉讼法》第208条关于简易程序条件的规定,以三年作为重罪与轻罪的区别点作出不同的处理。据此,刑事和解通常适用于犯罪轻微,造成较小损失,法定刑低于3年有期徒刑、告诉才处理及轻伤等社会危害性较小的案件。为何以三年为界,笔者认为重罪适用和解,可能会放纵罪犯,同时伤害国家的刑罚权。
3.自诉案件。新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0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判决宣告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本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三项规定的案件不适用调解。”由此规定可以得出,对于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自诉案件,在法院宣判前,被告人与被害人可以进行和解。新刑事诉讼法之所以将自诉案件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是因为此类案件对公共安全不构成威胁,情节轻微易于和解。
(三)刑事和解的具体运作
1.刑事和解制度采用的模式
二大法系国家的刑事和解制度,通常被排除在正式的诉讼程序之外,而是由作为第三方的调停人(法官、检察官、志愿者、警察等)主持的以非诉讼程序存在。具体有以下几种模式:(1)社区调停模式。案件发生后,先由社区的志愿者介入,进行调解,此时与刑事司法没有关系。非可逮捕罪仅适用于英美法系国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于大陆法系国家。(2)转处模式。此模式是采取起诉便宜主义的国家适用的模式,主要针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起诉的案件。案件发生后,在犯罪人被起诉前由和解中介机构进行调解。(3)替代模式。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模式,该模式通常由司法官员在量刑和执行中适用替代监禁刑,目前德国对此有法律明文规定。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内,并没有明确确立刑事和解制度,我国大多数学者赞同以下几种模式,笔者也认为这几种模式在我国现行的司法体系内可行:(1)自愿和解模式。为了兼顾刑事和解的效率与公正价值,对符合和解条件的案件,当事人双方有和解意愿,在自愿的基础上,就经济赔偿达成书面协议,使案件得以解决。(2)法院、检察机关主持和解模式。指主办法官或检察官通过与犯罪人、被害人沟通,就赔偿事宜达成和解协议,从而使案件得以解决的模式。(3)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模式。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受公检法机关的委托,对双方具有和解意愿的轻伤害案件进行调解,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可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2.刑事和解适用的诉讼阶段
(1)侦查阶段控制适用。在侦查阶段应赋予公安机关少量的协商案件处理权,对情节轻微等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案件,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由检察机关审查,增加审查环节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体现,经检察机关审查同意后,作出撤销案件的决定。
(2)在审查起诉阶段积极适用。只要符合和解范围的案件要积极和解。对新《刑事诉讼法》第173条规定的酌定不起诉、存疑不起诉的情形决定不起诉的,可以运用刑事和解来处理,可以考虑将暂缓起诉作为条件,待和解的协议很好地执行后再作出不起诉决定。
(3)审判阶段仅限于自诉案件。有学者认为:“对于公诉案件——法院可在其履行完和解协议的基础上作出无罪判决”。[5]笔者认为,在法院的主持下对公诉案件进行和解达成协议并撤销案件极为不妥。前者是以国家公诉人的名义进行控诉,代表了国家和公共利益;后者代表被害人的利益,依法决定是否将犯罪嫌疑人交付审判、支持公诉以及提请法院改变错误刑事判决的一种权力,这一权力是任何机关都不可侵犯的,人民法院对公诉案件转为自诉处理,其结果是直接剥夺和侵害了检察机关的公诉权。
[1]刘凌梅.西方国家刑事和解理论与实践评价[J].现代法学,2001(1).
[2]赵琳琳.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和解制度[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6(3).
[3]夏琳.刑事和解的利弊分析[J].商法论丛,2008(1).
[4]李建明.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刑事和解研讨会”上的发言[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4).
[5]陈立毅,李苹.理性地移植:刑事和解本土化新论[J].湖北社会科学,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