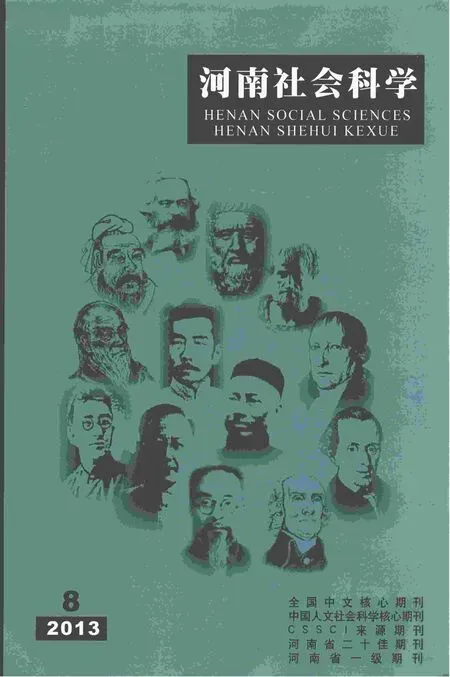对《野草在歌唱》的拉康式解读
2013-04-11李红新
李红新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5)
多丽丝·莱辛(Dorris Lessing)是英国当代文坛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女性作家,《野草在歌唱》是其成名作。作品通过对玛丽悲剧一生的描写,揭露了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制度戕害下女性的毁灭。国内学者多是从女性主义、生态主义或后殖民主义的视域对作品进行分析,本文运用拉康关于主体形成的理论,对作品进行新的解读。
一、拉康的主体思想
拉康把人的主体性分为三个层面: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想象界产生于“镜像阶段”,镜像阶段出现在婴儿主体意识形成的某一个神秘的瞬间:618个月大的婴儿在镜中看到了自己的镜像,发现以前零散的感觉被镜子整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婴儿会把镜中的影像认同为“自我”,并开始迷恋上这个自身以外的“理想自我”。想象界里“自我”的建立是通过想象将自我投向所看到映像的心理阶段,从此婴儿开始慢慢能够区分自我与身体、自我与他人和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婴儿开始有了自我/他者的概念。此时的“他者”是指婴儿面对的非我介体(镜中的像,父母的面容等),是小写他者。但是需要指出镜中的映像是虚幻不真实的,具有欺骗性:镜子中的“自我”并非真正的本然自我,而是镜中的一个幻想影像。
主体的真正形成是在象征界,当婴儿形成“他者”思想,形成与“他者”认同的自我后,就开始进入象征界。象征界是通过语言,与社会和文化密切相联的语言能指世界,象征着父权制度下的一种秩序。拉康认为婴儿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的内在根源是镜像自我的虚构性。在母子一体的世界中,婴儿在心理想象中独自占有着母亲。父亲的出现改变了母子理想的二元格局,打破了婴儿对母亲一厢情愿的独自占有关系,造成婴儿的匮乏感。婴儿于是通过压抑对母亲的欲望,从虚幻的想象界进入以父亲的权威为最高符号的象征界,即“父亲的法律”。主体开始从对母亲的认同转变为对父亲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主体认同的不是具体的父亲,而是父亲拥有的权力和秩序。所以对父亲的认同就是对他者的认同;只有通过与他者相认同,主体才能获得自我认同。
二、镜像中理想“自我”的迷恋
按照拉康的理论,想象界源于幼儿时期的镜像经验,却能深入影响成人对他人和外部世界的经验;童年时期的家庭环境及个人体验会深刻影响日后自我主体的形成。玛丽的童年是在没有温暖、充满不幸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父亲是一个收入低微的下层职员,酗酒成性;母亲含辛茹苦操持家务,终因时日艰难,憔悴而死。不幸的童年使玛丽对自由幸福的美好生活特别憧憬,因此,她迫切地想冲出家庭的藩篱,寻求自由的天地。在离开家住进寄宿学校后,她像一只逃出鸟笼的小鸟,自由而快活。当父母相继去世,她不仅不感到伤心悲痛,反而感到是一种解脱。
玛丽厌恶母亲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母亲又作为镜子,影像出了玛丽虚幻、想象的自我。她心中的理想自我是不像母亲那样整日含辛茹苦,为衣食所困;是一个可以独立生活,经济富足,没有家庭关系困扰的自由女性形象。由此看出,玛丽所追求的理想生活不过是为了弥补童年幸福生活的缺失折射整合的理想镜像而已。父母去世后,玛丽找到了一份做老板私人秘书的工作,生活平静舒适,薪水相当可观。在少女阶段,玛丽和当时南非其他女孩相比无疑是幸运的。但是玛丽一直陶醉其中,甚至对这种镜像式的幸福产生自恋式的认同,以致30岁的玛丽依然走不出十几岁少女的青涩。她依然保持着少女的发型和着装,还是少女般的羞怯天真,对于男人更是完全不放心上。想象界镜像中的理想自我只是想象关系的一种幻想性虚构,但是能使人获得一种现实感,玛丽因此迷恋上了理想自我,自我长期停留在想象界。
三、象征界认证“自我”的迷失
随着年龄的增长,玛丽对这种幸福单身生活的自我迷恋注定是不会长久的,因为这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一件极不正常的事情。到了30岁还孑然一身的玛丽,在白人社会里简直是个另类。周围朋友的相继结婚和周遭同事的嘲笑和议论,使她意识到她必须要被象征秩序里的他者认同,实现被他者认证的“自我”。她首先需要找个男人结婚,这样才符合常人的标准,茫然中她和白人农场主迪克草草结了婚。
玛丽的结婚标志着她开始试图走出想象界,进入象征界,实现自我认证。象征界是父权制度下的一种秩序,只有通过与大写他者(社会象征秩序)相认同,主体才能获得自我认同。进入象征界的过程就是接受父权社会的规则和秩序,确立社会和文化意义上主体地位的过程。表面看来玛丽嫁了人、结了婚,在象征界完成了一次自我认证,但结婚对玛丽来说不过是堵住悠悠众口。童年的记忆使玛丽对家庭、婚姻和男性丧失了信任感和安全感,这种心理发展上的障碍使玛丽虽然结了婚,却无力去爱,无法履行象征界的女性角色。玛丽结婚不是因为和迪克真正相爱,缺乏正常婚姻的感情基础,“他们的婚姻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彼此之间缺乏真正的了解”[2]。丈夫迪克虽然善良老实,却自卑无能,认为玛丽是从城里下嫁过来的,在玛丽面前忍气吞声,这更使玛丽越来越瞧不上他。这样的夫妻关系可谓是水火难合,和当时的南非社会秩序也是格格不入。丈夫迪克懦弱无能,无力担当,妻子玛丽也不谙为妇之道,对贫困凄惨的农场生活无所适从,他们的生活只能是贫困压抑。
玛丽对象征界的“自我”认证困窘越来越感到茫然迷失,于是幻想有朝一日回到城里,因为玛丽单身时曾在城里找到过一份做老板私人秘书的工作,生活平静舒适,薪水相当可观。终于有一天玛丽下定了决心,离开偏远闭塞的农场,回到了城里。这可以说是玛丽在象征界争取“自我”认同的又一次尝试。可是她却发现她已很难在城市立足了,城市还是那座城市,而她在别人的眼中却不是原来的她了。玛丽感受到了现实对她的无情嘲弄,她再也融不进这座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玛丽当年为了实现他者的认同结了婚,嫁了人,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女性,却发现自己又被象征秩序放逐流离,被她所熟悉的城市无情抛弃,她只能回到迪克的那个破烂、压抑的农场,做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女人。
四、主体的异化疏离
玛丽越是在象征界迷失自我,内心就越摆脱不了想象界的完美魅惑。无法被他者认同,玛丽自然而然地又退回到了想象界,因为“想象界是完全属于女性的世界,在这里没有任何规章的约束”[3]。迪克生病以后,玛丽开始接触农场,她发现迪克并不懂如何经营农场,这是造成他们贫困的根本原因。如果玛丽能够主动参与经营管理农场,或许她们的生活就会发生变化。但玛丽把当初那个敢于冲出家庭牢笼、寻求独立自由的自我隐匿了起来,她把决策权全部留给了丈夫。每当农场里有一些棘手的事情迪克向她征求意见寻求帮助时,她都置身事外。迪克的平庸无能使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糟糕,随着梦想的一次次破灭,玛丽彻底绝望了。在象征秩序下越是生活窘迫,越摆脱不了想象界的纷扰迷离,越容易认同母亲,玛丽开始怀疑她的人生只是母亲镜子的影像,是母亲命运的翻版。
玛丽无法摆脱长期浸淫心理的完美想象,无法认同父亲,无法获得主体的自我认同,无法认同菲勒斯的能指秩序。这里的菲勒斯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父权秩序。丈夫迪克的名字在英文中有男人阳具之意,相当于生理上的菲勒斯。但是丈夫的软弱无能也无力拯救玛丽,帮助玛丽认同父法,顺利融入象征秩序。失败的父亲形象和无能的丈夫形象使玛丽对家庭、婚姻和男性丧失了信任感和安全感。可是在潜意识里她和大多数女性一样,渴望被人关爱,渴望正常的夫妻生活。对男性信任感的丧失只是性意识暂时的蒙昧压抑而已,是欲望的力比多矢量还没有找到明确的指向。这就为摩西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黑仆摩西是莱辛小说中塑造的第三位男人形象。摩西是《圣经》中的先知,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莱辛这样的设计意味深长,似乎这个男人是专门来拯救玛丽的。玛丽有一次无意间看到了摩西在树荫下冲凉,“那罩满雪白皂沫的又黑又粗的脖子,那在水桶跟前弯着的健壮的背”[2]。摩西健壮的身躯立刻点燃了玛丽沉睡的力比多欲望,激发了郁积已久的力比多骚动,玛丽开始有些魂不守舍。因为从摩西身上她感受到了男人应有的勇敢坚毅和无所畏惧,感受到了男人对女人的精心呵护和关心体贴。摩西身上独有的情趣和魅力,摩西为她营造的浪漫和温馨,使她感受到了作为女人被异性关爱的幸福,她接受了和摩西的暧昧关系。
这种幸福是虚幻的,是玛丽经历了童年记忆中阴暗的家庭生活和婚姻中压抑的夫妻生活后的幸福欲望。根据拉康的理论,有欠缺才会有所欲望。因为幸福缺失而整合的理想体验,可以使玛丽获得一种暂时的满足感。但是这种虚幻的幸福欲望无法在象征秩序下得到认同。当时南部非洲种族歧视盛行,黑白沟壑分明,白人和黑人之间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决不允许在种族隔离社会中白人和黑人之间有暧昧苟且之事,这就是象征界的社会文化。
主体的形成正是需要借助象征界来接触社会文化,通过与他者的相认同,才能获得主体的自我认同。玛丽因为个人的经历,在象征界里迷失自我,自我主体长期处于疏离状态,无法完全认同南非的象征秩序,但她身上也带着种族歧视的印记,尤其因为玛丽并没有获得完全健康的主体发展,更容易陷入他人的认同。所以玛丽也像其他白人那样粗暴地对待黑人,而每次对黑人发威短暂的快意后玛丽却又会被更加痛苦的绝望吞噬。在和摩西的畸镜之恋中玛丽更是感觉到了空前的异化疏离。一方面感受着摩西的关怀和幸福,一方面又背负着沉重的罪孽,在虚幻的幸福和象征秩序的双重压迫下,玛丽的主体不断异化,精神趋向分裂。玛丽开始生活陷入混乱,精神变得恍惚。当他们的秘密被白人青年托尼窥探到之后,她的本己自我迷失隐匿,疏远主体异化表征,她感到白人尊严受到玷污,无情地叫摩西滚开,而摩西则举刀杀死了玛丽。
五、结语
玛丽童年的不幸生活,使玛丽对镜像中的理想自我产生了迷恋,长期停留在想象界;玛丽想要进入象征界,实现他者的主体认同,却在象征界迷失自我,无法很好地认同象征秩序。玛丽的自我意识和主体认同始终处于一种断裂状态,而且渐行渐远,主体不断异化,精神趋向分裂,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以拉康的思想阅读玛丽,玛丽的悲剧似乎不可避免:女性既然无法在父权的象征秩序里得到他者的认可,死亡就成了唯一的结局。
[1]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2]多丽丝·莱辛一蕾.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赵一凡,等.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