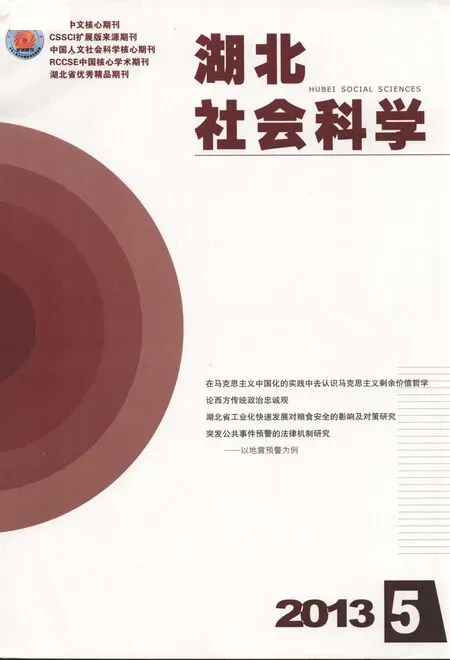论采光权的法律保护路径
——以扩大化解释现行民事权利制度与权利制度创新两种路径为视角
2013-04-10周小桃
周小桃
(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六盘水 553004)
论采光权的法律保护路径
——以扩大化解释现行民事权利制度与权利制度创新两种路径为视角
周小桃
(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六盘水 553004)
现实司法实践中,关于采光权的纠纷频繁涌现,但现行法律体系对于采光权的规定却极为简单而粗略。事实上,采光权在现行权利体系中仅为一种应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现行的法律规定滞后于社会现实,不能很好地应对现实社会矛盾。学界有将采光权规定为民事权利(物权),也有论者认为采光权是环境权的一种(环境人格权),这种权利的定性上的差异并不影响采光权的救济,只是从不同角度为采光权的保障与救济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扩大化解释现行民事权利制度和进行专门的权利制度创新来救济与实现采光权。
采光权;救济;相邻权;环境人格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公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权利需求的丰富和权利意识的增强,公民对居住环境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与城市建设用地的日趋紧张、城市新建楼房之间的间距越来越小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构成了矛盾的根源,随之而来的是采光权纠纷的频繁发生。而我国法律关于这方面的规定过于简单,存在许多法律空白。现行的法律理论与制度体系对于公民之间的采光权纠纷这一新型的权利纠纷尚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现实中频繁涌现的采光权纠纷不能很好地纳入法律通道予以解决。因此,迫切需要对于采光权的性质与权利救济的法律制度诉求进行细致剖析,以更好地维护采光权这种重要权利。
一、采光权的法律性质与现行救济路径
1.采光权的法律性质。
采光权由于尚不是现行权利体系中一种确定的、内容明确的法定权利,仅为一种应然权利。所以,学界对于采光权也存在着多种称谓,一般还称之为阳光权,即自然人享有的免受噪光危害及居所获得充足阳光照射的权利。享受天然的阳光本是每个人应有的自然权利,但由于人类居住环境越来越拥挤、人工光源的大量使用,这一权利因不能得到保障而凸显了法律加以规定和保护的必要,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相关的判例。
正因为采光权并没有成为现行法律体系中明确规定的权利并进行具体的内容设计,所以,现行研究中对于采光权的法律性质如何并无定论,存在着争论。由于民法理论和制度已经发展非常完善和成熟,所以,对于很多新型利益被定性为民事权利,纳入到民法保护框架之内,很多学者对于采光权的保护也主张此种思路,认为采光权是民法上的权利,并认为采光权是一种物权。[1](p33)从民事权利角度定性采光权,认为采光权作为相邻不动产间的采光利用关系的一种权利,是所有权的扩张;随着环境法发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有了自身独特调整领域,环境权利成为了一种区别于传统公权私权划分的新型人权逐渐被法定化,环境法学者认为阳光是一种环境要素,而且是一种最为重要的环境要素,采光权是人与阳光进行交往的权利,因而采光权也被环境法学者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环境权——环境人格权。
权利的定性是为了寻求权利保护与救济的更好路径,无论是将采光权定位为民事权利——物权(相邻权)还是将其定位为环境权——环境人格权,这两种思路很难用对与错去进行划分,因为,对于采光权的定性是决定将其纳入传统民法还是新型环境法律规范中进行保障的,而法律规范来源于人类对于人类所必须享有的利益的认识,从而形成的对于人类行为规则的设定,这个过程是前后连贯的而非截然二分的过程。当一些新型的利益类型不能被既有的规则很好地予以保障时,必须设计出新的规则,但并不否认既有规则在保障新型权益中的重要作用。采光权作为人类生存与生活,为了保障人体生命健康所必须享有的利益,在当下社会被更深刻地认识和受到重视,它作为个体公民所应然享有的权益,是应当受到民法制度的保护,当传统的民事权利制度在保障这种新型权益上难敷其用时,应当重新认识采光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之处,从而设计出新的规则类型,但并不否认既有民事权利制度所起到的作用。
2.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对于采光权的保障。
正因为采光权是一种新型的、尚未法定化的权利类型,所以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关于采光权的规定有两类。一类是私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83条不动产的相邻方处理相邻关系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89条关于建造建筑物的标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第97-103条对邻地利用的规定;另一类是公法,如《城镇个人建造住宅管理办法》第6条城镇个人建造住宅不得妨碍毗邻建筑的规定,《建设部提高住宅设计质量和加强住宅设计管理的若干意见》,其中第7条规定住宅设计应重视室内外环境,提高居住的舒适度的规定,以及不少地方法规也涉及到采光权,如《长沙市居住建筑间距和日照管理规定》。
上述对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关于采光权规定与保障可以梳理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将采光权明确规定为一种法定权利,更遑论对于采光权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第二、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对于采光权的保障,是通过以保护相邻关系,或者是对“建造建筑物”等民事权利行使行为中的附加义务的规定来间接保障公民的采光权益的,或者说通过排除性规定的内容来实现公民的采光权益的;第三、在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公法与私法的相关规定都间接涉及到公民采光权益的保障,但私法是公民权利的直接来源,而公法的规定是以私法对于公民的权利规定为基础的,从私法角度规定了何种利益是公民应然享有的权益并对之进行法定化,公民则主要是通过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方面提出国家环境资源管理的要求,从而保障公民的人身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如何确定采光权的权利性质并对之具体内容进行详细设定,是保障采光权的前提和基础,而这一工作依靠单纯的公法的管理性的规定是难以实现的。如果将其定位为民事私权,必须首先论证其逻辑上能符合民事权利的运作逻辑并进行详细的制度设计,如果将其定位为新型的环境人格权,则也需要首先论证其内在的权利构成并进行详细的制度设计。
二、尚未被法定的作为“应然权利”的采光权的救济思路
采光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并不是一种法定化的权利,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是应然权利,因为阳光是大自然的恩赐,谁也没有权力加以剥夺,公民享有的接近阳光、引入光线、居所获得充足阳光照射是保障自身身体生命健康所必须享有的正当权益。当采光权这种尚未被明确法定的权益受到侵犯时,我们不能因为其没有被法定化而不对之予以救济。环境学者在论述环境侵权救济的“法外之权”中,通风权、采光权、宁静权、安稳权等新型的具体环境权利来源于人类的本能需要,是一种“本能权利”。在环境问题凸显之前,公民的环境意识非常落后,在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和物质条件严重匮乏的情况下,人类对于环境资源更多的是经济利益的索求,但这不能否认附加于环境资源上的生态利益和其他性质的利益,各种环境利益对于个人具有极其重要的生存和生活价值。当然,各种环境利益的发现和享受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尽管这些权利目前尚没有法定化,但也不能否认其作为“本能权利”的存在,这些权利可以通称为环境权。[2](p30)当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该如何进行救济?合理的思路是将现有民法制度与生态化的民法制度进行整合。具体而言须考虑以下两个方向的路径选择:即现行民法制度的生态化拓展或建立新的环境资源保护的民法制度。如在知识产权法领域,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新型的知识产权不断得到重视,知识经济不仅对以往资源经济时代形成的价值概念、分配原则、生活方式、管理机制、政府政策等带来冲击,而且会引起有关法律规范这一“游戏规则”在国际范围内的重构。当代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变革,不仅凸现出现行制度的改革,而且面临着崭新制度的突破。如长期以来传统知识一直被简单地归属于共有领域,任由他人自由而免费获取、利用。近年来,国际社会十分重视传统知识的保护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采用现行制度保护,即在著作权及邻接权、专利权、植物品种权、外观设计权、商标权、地理标记权和反不当竞争等规定中作出有利于保护传统知识的解释或对接;二是采用专门制度,即建立一种专门制度,为适应传统知识的本质和特点而创设独立法律制度,又具体可分为单一保护制度和多种保护制度。[3](p52)对环境权民法保护以及侵权救济的制度,可借鉴知识产权制度的设计。
三、采光权救济的具体路径选择
案例1:2002年3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62名法官,以市规划局批准在他们家属楼旁建设18层高楼影响采光为由,把兰州市规划国土资源局告上了法庭。由于原告方是62名法官,给原告身份涂上了暧昧的色彩,也使本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指定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异地审理此案,白银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调解,此案最终以原告撤诉而果。
案例2:2002年初,三栋新建高层建筑耸立在江苏省检察院49户检察官们入住的两幢七层楼前面,使得两幢楼房的通风采光受到影响,2002年12月49户检察官向鼓楼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历经两审,均以原告败诉而告终;2006年年初,49户检察官又以开发商所建建筑侵害其采光权为由,将开发商推上被告席,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经过法院的几多周旋,检察官们终于获得三万余元的赔偿。
现实司法实践中,提起采光权侵权诉讼极其常见,但大多都是原告胜少败多,即使经过数年漫长时间费尽周折,也基本上都是原告得到寥寥数额的赔偿。导致目前采光权纠纷审判实践现状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至今还没有保障采光权的具体规范。我国法律体系虽然在一些法律条文中规定了采光权的内容,如前所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规定,以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也存在有关采光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大多是从产权界定的角度出发,明确了相邻建筑权利人享有获得适当日照所带来的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的权利,以此确定受害方的采光权是否受侵害。在处理采光权损害赔偿过程中,因为缺乏相对统一的执法尺度,案件的结果大多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事实证明,采光权受到侵害时从现行法律制度体系得不到及时的合理的救济。因此,可以说采光权实质上也仅为一种“道德权利”或“应然权利”。如何救济采光权?如上文所言,可以有两种法律路径:
1.采光权救济的完善现行民事权利体系的路径。
我国现有的民事立法对于采光权仅为概括而简略的规定,所以所有对采光权保障和救济的探讨仅为学理上的分析,目前民法学界基本上把采光权作为相邻不动产间的采光利用关系的一种权利,对于采光权的立法调整模式,多数学者将采光权的探讨置放在相邻权的制度框架内。[4](p396)现行的法律并没有把采光权正式作为相邻权的一种,而只是作为实现相邻权的具体形式,因此,可以在现行法律权利体系中正式把采光权性质确定为物权,物权反映的实际上就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形式主义的权利,是国家授予人的空白的权利委任状,人可以在其上任意书写,只要不违反国家法律,人与物的任何关系就是合法的。这就是近代物权法的基本特征。正式确立“采光权”的物权性质后,相应的制度设计就必须在《物权法》等具体法律中对采光权进行规范,规定有关采光侵害的理论构成,增加采光侵害的私法救济内容,具体化规定责任承担的方式,以方便于法律实践操作。
(1)采光权侵害的认定。
日光照射之利益侵害达到何种程度,受害人提起的采光权诉讼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这是采光权诉讼中首先面临的问题。
我国法律对采光权侵害并没有规范化的标准。因此,司法实践在采光权侵权的认定问题上,有人认为虽然新建建筑遮挡了原建筑的采光,缩短了原来建筑享受阳光的时间,但只要原建筑的采光时间达到了有关规定认可的最低时间要求,就不能认定采光侵害;也有人认为,虽然新建建筑遮挡了原建筑的采光,但只要新建筑是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是合法建筑,就不能认定为侵害采光权。但在当今住房市场化的形势下,特别是近几年房屋价格上涨,而采光权系房屋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遮挡势必造成房屋贬值,因而笔者主张,只要新建筑和设施缩短了相邻建筑的采光时间,就应考虑相邻方的采光权是否受到侵害。
(2)采光权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
当采光权侵害认定后,法院将面临这样的问题,是判决排除妨害,拆掉房屋还以阳光,还是赔偿损失,被侵害人继续忍受缺少阳光的日子,这其实是采光权救济模式的选择问题。追求效率是经济学的最高准则,经济学家们从科斯定理的效率原理中找到了解读法律制度的钥匙,那就是应该将财产权赋予交易成本较高的一方。科斯定理可衍生两个法则:财产法则和补偿法则。财产法则系指“除非事先获得权利人之同意,否则法律禁止他方当事人侵害这个权利”;与财产法则相对应的是补偿法则,系指“即使未取得权利人的事先同意,相对人仍可侵犯权利人之财产权,但必须依法作出适当的赔偿”。[5](p246)法院裁定停止侵害、排除防碍、恢复原状相当于财产法则,而赔偿损失,则相当于补偿法则,因而法院在处理采光权纠纷案件中,是适用财产法则抑或补偿法则,取决于何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
在引入财产法则和补偿法则概念后,规范采光权侵害的责任承担方式并不复杂。具体来说,在救济采光权的过程中,不能概括地适用《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等民事救济方式,应该通过具体法定的方式来具体规定,救济采光权的民事责任方式,除了通过拆除致害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降低高度(如对建筑物加高部分的拆除、对树木修剪等)、责令停止施工等措施来实现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形式外,当双方的利益差距比较大或从维护社会财富出发,还可以考虑通过置换产权、另行安置不动产等做法。
(3)损失赔偿的标准。
法院在适用补偿法则时,必须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核定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但现行国家法律层面补偿标准是空白的,部分地方性法规在确定补偿标准方面则是滞后的或欠缺合理性。如,北京市对被遮挡阳光的居民住房补偿最高金额为2000元;2010年新出台的《长沙市居住建筑间距和日照管理规定》对采光侵权的赔偿最高额为房屋评估价格的14%。阳光作为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的,但房屋内的阳光是稀缺资源,而且采光度直接关乎居民的身心健康,遮光会影响人的精神面貌和人格,影响其生活状态,采用人工采光办法会增加诸如电费、取暖费等其他费用的支出。因此,区区几千元“买断”居民的采光权实难让人心服口服,亦不能体现采光权的价值。
对赔偿金额的标准应有一个合理的规制,赔偿的数额应以能够足以赔偿受害人的损失为准,在具体的案件审理中,综合考虑采光侵害的程度,受害方精神上的影响,采光权侵害前后房屋的价值变化等因素,公平合理确定赔偿的金额,但最高不应超过住宅重置价格。
2.采光权救济的民事权利制度创新的路径。
具体来说,要救济受到侵害的采光权,首先要把采光权进行法定化,再把采光权的救济纳入现行的法律权利救济制度框架之中。对于采光权的救济,除了在现行的民事权利体系中重新定位与设定采光权的具体内容之外,另外的处理路径是把采光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身权利——即环境人格权在立法中具体体现出来。采光权是与人类生命和健康息息相关的权利,是人在居室中对阳光充分需要的权利。采光权不是谁赋予的,而是作为人来讲与生俱来且必需、必要的权利。采光权对于人的生命和健康的价值是不能用简单的数字和经济来衡量的。因此必须设定为人格权予以救济这项与人的身体和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权利,但这项人格权又与传统人格权不同,而是环境人格权。环境人格权是在传统民法人格权基础上,扩展人格的概念后建立起来的。环境人格权可以界定为主体所固有的、以环境人格利益为客体的、维护主体人格完整所必备的权利。[6](p254)环境人格权是以环境资源为媒介、以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和美学价值为基础的身心健康权,是一项社会性私权,包括了采光权、宁静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通风权、眺望权和自然景观权等。可以在环境人格权的理论和制度框架中设计出采光权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具体内容,以在现实法律实践中实现和救济该项权利。
[1]吴亚平.采光权的法律性质思考[J].法学论坛,2006,(11).
[2]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吴汉东.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变革与发展[J].法学研究,2005,(3).
[4]王利明.物权法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5]孙国富.采光权的意定与法定[J].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6,(3).
[6]吕忠梅.沟通与协调之途——论公民环境权的民法保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周刚
DF523.1
:A
:1003-8477(2013)05-0144-03
周小桃(1971—),女,贵州六盘水师范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