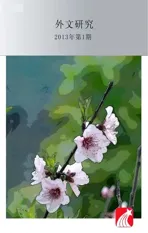从1949-1977年中国译史上的翻译需要审视“中华学术外译”
2013-03-20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友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友贵
从1949-1977年中国译史上的翻译需要审视“中华学术外译”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王友贵
本文尝试提出“翻译需要”及其定义,然后把翻译产品的需求方分成三层主体,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时期”(1949-1977)划为“全盘苏化”、“急转向和皮书”以及“续皮书”3个阶段,分别考察背后的翻译需要,需求方三层主体的关系、不同主体需要的变化及其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评述翻译的整体效果,最后针对21世纪初的“中华学术外译”重大工程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翻译需要;全盘苏化;三层主体;中华学术外译
一、“翻译需要”之界说以及翻译产品的需求方主体
观察20世纪后半叶中国翻译文学史,有一种内在元素或推动、或制约翻译。这种元素在我国的翻译研究、译史研究中尚未得到专门关注,它便是翻译需要(translation needs)。我以为,历次中国的翻译潮,无论潮大潮小潮起潮落,都跟它有关,不过我们对它关注甚少。
无论是Mona Baker(2001)主编的《劳特里奇翻译百科全书》还是林煌天(1997)主编的《中国翻译词典》都未收录这个词条,也就谈不上给定义。我试图给它下一个简单定义,作为抛砖引玉的尝试:翻译需要是翻译活动得以开始、延续、完成的一种内在决定力量;它的产生可以启动、推动翻译,它的改变可以改变翻译走向,它的消失可以终止翻译。
我认为,翻译需要是贸易需要的一种,因此它可以分为输出国需要和输入国需要两大类。二者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大不同。两类需要里边,输入国的需要居主导地位。通常情况下,翻译活动能否持续取决于输入国是否有持续需要。如果单单输入国有需要,翻译多半会发生,除非相关国际法、输出国的法律明文禁止,这是第一种情况;如果输入国产生了翻译需要,输出国也产生了需要,翻译必定活跃,这是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好的情况;如果输入国没有需要,而输出国单方面有需要,翻译活动要么不发生,要么由输出国强行开展,效果往往不佳,这是第三种情况。要想扭转第三种情况,即效果很差的局面,输出国唯有努力在输入国制造、培育需要,而不是强行开展翻译活动。一旦输入国有了翻译需要,情况才会改观。
翻译活动的终端成果为翻译产品。产品的使用主体往往是产品的主要需求方。需求方可粗略地划为三层主体:1)普通读者与民间团体;2)翻译家、编辑、知识精英和农工商各界领袖;3)官方。前者人数最多,包括一般知识人和粗通文字的普通公民;中者人数不多,主要指翻译家和编辑、握有话语权的知识精英和农工商界领袖;后者人数最少权利最大。三者的关系,在本文考察的共和国第一时期(本文把共和国最初的1949-1977年划为第一时期,1978-1999年划为第二时期)非常特别,前者和中者的独立性严重削弱,后者握有决定权;前者里边的民间机构要么不存在要么名存实亡(譬如作家协会、红十字会其实不是民间机构),前者依赖后者;中者里边的农工商领袖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到1977年跟后者没有分别,因其自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多由官方委派;中者里边的翻译家和知识精英的主体性遭遏制,逐渐发展到完全服从后者。因此三者的关系构成一个尖塔,塔底是人数最多的前者,中间是中者,塔顶是官方。众所周知,第一时期重大翻译活动的启动或终止往往自上而下。
二、“全盘苏化”以及此后两个阶段背后的翻译需要
第一时期外译汉和汉译外的翻译活动严重不对称(亦无必要对称),本文聚焦外译汉,汉译外仅适当引入做对比,不拟展开讨论。*这方面的研究,可参看倪秀华:《建国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中国翻译》2012年第5期。
第一时期的外译汉可进一步细分为三段。1949-1959年即“全盘苏化阶段”;1960-1965年为“急转向和皮书阶段”;1971-1977年为“续皮书阶段”。1966-1970年外译汉基本停止,同期汉译外仍在有限进行。众所周知,第一时期外译汉最活跃、最重要是在第一阶段。
所谓“全盘苏化”阶段,具体到翻译史上可从如下统计数字获得证明。据《全国总书目》第1卷(1949-1954)对大陆正式出版的图书搜罗的结果(新华书店总店 1955)*本文计算总数的方法跟一般的算法有别。本文的统计方法如下:1)学习参考资料、选集、全集中的分册分别计算;同一原作的中译本上、中、下分册,只计为1种;2)同一译本重印、再版分别计算;3)同本异译分别计算; 4)本统计包括外汉对照书,如“俄汉对照”,但不包括汉外对照图书,如《华俄辞典》;5)不包括(乙)类“分类目录”中的图画、年画、连环画图书,不包括少数民族文字图书、外国文字图书、苏联出版的中文图书。,甲类“分类目录”总共出版16 642种图书,乙类“专门目录”收入5 167种;甲类里边有翻译图书5 514种,占甲类出书总数的33.13%。乙类里边的“少年儿童”栏目另有353种翻译图书,若用乙类里的“少儿”图书总数770种和甲类总数16 642种之和作为基数,这5年零3个月翻译图书(即5 514 + 353 = 5 867)的比例高达33.69%。
检阅《全国总书目》第1卷(1949-1954),几乎所有领域都有翻译图书;不唯如此,但凡有翻译图书的领域,译自苏联者少的占七八成,多的达九成多;且在绝大多数领域中,如科教领域的物理学或化学,工业领域的汽车制造或炼钢,分量最重的部分必然译自苏联。所谓分量最重,指该领域的基础理论、指导性著作、行业运作规范、标准一类的著作。检阅清楚地显示,所有翻译图书中,译自苏联的著作在各行各业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唯一的例外是少数从德文翻译的马恩著作。
“全盘苏化”阶段背后的翻译需要首先源自官方,产生于新政府制定的全面改造中国的国策。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并非什么都否定,但是在所有领域向老大哥学习产生了空前的翻译需要。这个阶段官方最大的成功在于推广需要和采取措施满足需要。她一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来推广需要,如政务院出版总署颁发的相关通知、文件证明了政府在推广、培育翻译需要方面所做的努力(胡愈之 1996: 415-418, 1999: 4-5);又如50年代初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迅速使中者、前者承认、接受变化,促使他们把官方之需转变为自己之需。可以说,政府在推广、培育需要方面空前成功,因“向苏联学习”在50年代初很快成为大多数知识人的共识,继而成为那些追求进步的青年人、尤其是读者中间的青年学子的迫切需要。
由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开始之前就开始了天翻地覆的转变:后者(官方)的需要,随着政府的大力宣传和推广,在国家发生巨变的过程中借势转变为中者、前者(普通读者)之需。由于翻译需要变成了三层主体的共同之需,“全盘苏化”阶段的翻译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非常成功,一举改变了中国。
1960-1965年的“急转向和皮书阶段”是明暗两大翻译模式的混合。这是本阶段翻译的突出特征。“急转向”指明的、公开出版的翻译突然转向,“皮书”指暗的、“内部发行”的翻译活动。具体一点说,前者指公开翻译苏东国家的图书锐减,转向介绍其他国家的图书;后者指“内部发行”的“灰皮书”和“黄皮书”,“灰皮书”指历史哲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的翻译产品,如《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从第1到20辑(哲学研究编辑部 1964-1966),“黄皮书”指文学产品,如沈江、钱诚译苏联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第1部(爱伦堡 1963)。
从本文所做部分年度的统计看,《全国总书目》(1960)甲类总数11 372种,加上乙类“少儿”图书584种,合计11 956种,全年翻译图书1 183种,译书所占比例降至9.89%(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1)。翌年的《全国总书目》(1961)甲类总数5 725种,加上乙类“少儿”图书406种,合计6 131种,是年翻译图书484种,后者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为7.89%(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 1962)。与此同时,“内部发行”开始增加,虽然要准确统计这部分书有困难,但可以肯定,自1960年起,尤其是从1961年到1964年,“内部发行”的翻译图书明显增加。
“皮书”的存在证明了两件事情:一是翻译需要依然存在,但前一阶段的巨大需要遭人为遏制;二是官方需要在第一时期具有决定性作用,其证明是方兴未艾的“全盘苏化”被官方紧急叫停,个中原委盖因中苏两党关系恶化,普通读者懵然不觉,大陆翻译不得已转向以前不被重视、或重视不够的国家、地区或翻译品种。如过去不介绍的关于苏联国内政治、历史真相的书籍,以“灰皮书”形式出版,其数量与重要性都明显上升;再如公开出版的文学翻译转向“亚非拉”文学等。
这次转向还是自上而下,譬如在文学领域,官方开动宣传机器提升“亚非拉”文学的重要性,提倡大力翻译“亚非拉”。但中者里边的核心构成,如翻译家,没有感觉到这个需要。由于转向幅度太大,时间短,加上政治运动的干扰,译者没有像第一阶段那样把它转变为自己之需,导致需要之塔的中间层隔膜、阻滞,没有把它传递给底层,也没有转变为底层(前者)之需。所以这短短6年时间,由于顶层官方的需要没有转化为中者、底层的需要,公开出版的翻译产品整体上不成功(也就是说,公开译作没有影响)。譬如普通读者(前者)仍喜欢读以前出版的俄苏文学或法国文学,“亚非拉”文学整体上没能成为其新爱。此外,新的输出国,如菲律宾,似乎没有感受到输入国突然产生的需要。二者间的合作很少,即便有也是个别的、小范围的,民间机构之间和政府之间未见卓有成效的合作。没有第一阶段中苏或中波(波兰)之间那样的有效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本期公开翻译不成功。
1971-1977年为“续皮书阶段”。所谓“续皮书阶段”,盖因“内部发行”的选材标准、翻译目的、运作模式跟第二阶段并无二致,不过是前阶段中断之后的继续。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在于第三阶段“内部发行”的总量弗如第二阶段多,同时公开出版的图书数量更小,影响更有限,导致“内部发行”的影响放大。后者甚至发行过杂志,如专登社会科学哲学类译文的《摘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第1-22期(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编译组 1975-1976)和专登文学作品的《摘译》(外国文艺)1971年第1期到1976年第12期(《摘译》编写组 1971-1976)等。
重启第三阶段的翻译首先是官方之需。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重开翻译*参看张福生:《中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特殊岁月——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23日第10版。张福生在文中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批从干校回来工作的俄苏文学编辑王之梁先生讲,1971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组建,恢复工作。当时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确指示尽快出版三岛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内部书’的名义出版了三岛的4部作品。”。应该指出,本阶段官方有需要,普通读者也有需要,但二者不吻合,且错位严重;中者也不分享官方之需。中者里边参与翻译活动的译者和编辑,与其说是自发需要,毋宁说是完成任务(陈丹燕 1998: 213)。本阶段读者的需要(前者)表现得畸形。那是一个无书可读的时代,少数求知欲旺盛的青年什么书都想读,“内部发行”尤其渴望。他们的强烈需要没有渠道供其公开表达,也得不到满足,只能偷偷摸摸地读,弄到一本读一本。官方的需要,原本旨在让一定级别的干部和少数知识分子适当了解外部世界,了解“敌情”。然而这些预期读者是否有自发的需要,目前的材料无法提供证明。后来公开承认有需要的那些人都来自普通读者(前者)(查建英等 2006; 徐晓 2009: 44; 沈展云 2007: 13; 多多 2009: 88)。
由此可以看出,第三阶段三层主体的需要发生如下错位:一是官方对前者(普通读者)之需,既缺乏关心,也无措施去满足,读者的需求降到最低依然得不到满足;二是官方之需也没有转变为中者之需,文革时期后者(官方)对中者独立性的彻底剥夺已经使其失去了翻译兴趣,中者要么自身难保,谈不上需求,要么有需求也不敢表白,成为“沉默的中层”。需求的错位导致了如下结果:第三阶段的翻译活动,“内部发行”在底层(前者)部分人中间大受欢迎,使得部分“皮书”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公开出版并广受欢迎;与此相对,第三阶段“公开出版”的产品由于跟底层、中层的需要不对路,整体上不成功。
三、21世纪初的“中华学术外译”
“中华学术外译”作为文化工程正式提出是在2010年。此后,不断响起各种呼吁,推进的力度不断加大。假如以共和国首29年的主要翻译活动外译汉做底,同时参考汉译外基本不成功的历史*据“新华网”2012年9月28日华春雨文:“外文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60年来,外文出版社用43种文字翻译出版了3万余种图书,包括领导人著作、党和政府重要文献、中国国情读物、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文学经典等,受众覆盖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跟以往一样,这篇报道再次用单方面的数量喻示成功,用时间的长度代替译入语国接受的态度和程度。完全不足为凭。,请允许笔者尝试讨论一下“中华学术外译”后面的翻译需要。
在这项文化工程中,中国成为输出国,英、俄、德、法、西(后来把日、韩、阿拉伯语也包括进来)语等国家成为目标输入国。迄今笔者没有看到一份信度较高的调查报告,抑或基于有信度的调查写成的文章,说明输入国的需要。当然,我们在报纸和其他媒体上读到日益增加的文化交流的信息,报道中外签署图书输出协议一类的可喜消息。然而这类协议,大多涉及中国经济文化著作的输出,较少涉及中华学术。
那么,那些大声疾呼的人,包括官方相关机构的发言人,基于什么对“中华学术外译”如此充满信心呢?是基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是基于中者的强烈需要?还是基于输入国普通读者(前者)的强烈需要?
如果是基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那么,按翻译常规主要参与者应该是输入国的译者和学者,中国作为输出国无需吆喝,只需配合与支持。如果是基于中者——理应以输入国的中者为主,不过本文退一步,把输出国的中者也算上——的需要,目前并无证据证明。吆喝本身恰恰证明了输出国中者里边的译者普遍没有此需。以目前的情况看,在输出国中者内部,少数知识精英的确表达过这种需要,但这种人大多不是优秀翻译家,更非翻译史专家,对翻译的规律不了解;输入国中者里边的知识精英似未表达过类似需要,尤其重要的是,输入国的大多数译者没有表达过类似需要,而多数译者的反应跟普通读者的需求密切相关。不知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推断,目标国家读者的需求不大?回到前边提出的问题,关于输入国读者是否有需要,目前我们只能推测如下两种可能:第一种情况是目标国家里边跟中国打过交道的人开始有了初步的需要,不过他们的需要跟“中华学术”关系不大,充其量是文史地理类的普及书籍,第二种是目前没有明显需要。
如是说来,当下的“中华学术外译”没有认真考虑输入国需求主体需要与否,它似乎体现为输出国官方之需,以及输出国中者里边少数知识人响应政府号召发出的呼吁。但这两层主体似乎忽略了如下两个从翻译史得来的重要经验。一个是输入国一定要有持续的需要,翻译活动才能持续有效地进行;另一个是即便在“全盘苏化”阶段,实施翻译的主体是输入国的译者和学者,即中国的译者和学者,而不是苏联的译者。
还需特别指出,在所有可能推动“中华学术外译”的因子中,最重要的因子似乎没有出现。它就是输入国是否产生较强烈的翻译需要。我们独独缺少对这个因子的调查和准确了解。
这个阙失具有根本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对至关紧要的输入国——姑且以英语国家为例——的三层主体的需要,即普通读者,译者、编辑、知识精英,以及官方的需要,都不清楚,不摸底。我们只知道,在他们那里,三层主体的关系跟我们这里不同,从决定翻译活动的重要性来看,前者(读者)最重要,中者也很重要,后者(官方)无关紧要。
如是看来,21世纪启动的“中华学术外译”的文化工程,与其说是应输入国的需要而动,毋宁说是应输出国的需要;与其说是应输出国译者需要而动,毋宁说是应输出国官方需要;与其说是“应需而动”,毋宁说是“一厢情愿”。它没有汲取翻译史提供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基于上述对翻译史的检讨,我们有理由表达如下担心:“中华学术外译”工程似乎基于陈旧的“政府万能”的思维定式和行为模式,它对需求了解不准确,它有浪费资源之忧,事倍功半之忧,且不说它还可能弄巧成拙,即在轰轰烈烈中把非学术的东西当作“中华学术”译出去。
本文的建议是,与其轰轰烈烈地开展“中华学术外译”,不如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力,包括提升“中华学术”的整体品质,同时有意识地在目标国家培育需要,持续不断地培育。两项工作都需要漫长的过程,我们只能做细水长流的心理准备,因为目标国家根本没有发生我国经历过的那种“全盘否定”或“自我否定”。
Baker, M. 2001.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M]. London: Routledge.
〔苏联〕爱伦堡. 1963. 解冻(第1部)[M]. 沈江,钱诚译. 北京: 作家出版社.
陈丹燕. 1998. 上海的风花雪月·白皮书时代的往事[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多 多. 2009. 1970-1978北京的地下诗坛[A]. 刘禾编. 持灯的使者[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胡愈之. 1996. 出版总署1952年工作总结[A].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2)[C].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胡愈之. 1999. 出版总署关于1953年的出版工作和1954年方针任务的报告[A].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C].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林煌天. 1997. 中国翻译词典[Z].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倪秀华. 2012. 建国十七年外文出版社英译中国文学作品考察[J]. 中国翻译(5).
上海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编译组编. 1975-1976. 摘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1-22 [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沈展云. 2007. 《灰皮书,黄皮书》中“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M]. 广州: 花城出版社.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 1961. 全国总书目(1960)[Z]. 北京: 中华书局.
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编. 1962. 全国总书目(1961)[Z]. 北京: 中华书局.
新华书店总店编. 1955. 全国总书目(1949-1954)[Z]. 北京: 新华书店总店.
徐 晓. 2009. 《今天》与我[A]. 刘禾编. 持灯的使者[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查建英等. 2006. 八十年代——访谈录[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摘译》编写组编. 1971-1976. 摘译(外国文艺)[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福生. 2006. 中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特殊岁月——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N]. 中华读书报08-23.
哲学研究编辑部. 1964-1966. 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第1-20辑)[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版本图书馆编. 1988. 1949-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Z]. 北京: 中华书局.
H159
A
2095-5723(2013)01-0072-05
(责任编辑 姜 玲)
2013-01-27
通讯地址: 510420 广东省广州市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