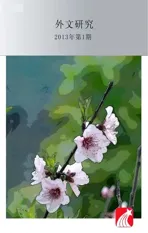小说、文学与民族的文化崛起
——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2013-03-20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文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文飞
小说、文学与民族的文化崛起
——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文飞
一部小说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两个出色例证。正是在这两部小说于19世纪60-70年代相继面世之后,整个世界才开始真正意识到俄国文学和俄国文化的价值和力量,西欧和世界对俄国的整体看法也迅速由惧怕、轻蔑、责难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对于正在努力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当下中国而言,托尔斯泰和他的小说成就以及整个俄国文学在19世纪中期的崛起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俄国文学;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文化崛起
俄国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所长弗·叶·巴格诺院士(2012: 144-161)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做的题为《西方的俄国观》讲座中曾提及:西方的俄国观在神圣同盟时期形成,后一直呈现为“哥萨克威胁”之敌对形象,直到19世纪70-80年代,随着俄国文学的崛起,尤其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长篇小说的面世,俄国和西欧的知识分子才普遍意识到,俄国人不仅富有智慧和文化,甚至肩负某种特殊的全人类使命,换言之,俄国文学的辉煌成就使西方针对俄国的轻蔑、责难和声讨迅速转变为好奇、同情和赞赏。这样的论述使我们意识到,在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崛起中,文学曾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在俄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无可替代之作用的正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巨著。
纳博科夫在美国的大学中曾这样给他的学生们讲解俄国文学:他拉上窗帘,关闭所有灯光,然后打开教室屋顶中间的灯,说“这是普希金”;他打开左侧的灯,说“这是果戈理”;他再打开右侧的灯,说“这是契诃夫”;最后,他冲到窗前,一把扯开窗帘,指着从窗口倾泻进来的灿烂阳光,大声地说道:“这就是托尔斯泰!”(Аксенов 2001: 647)
世界文学史上也有这样一个说法,即有史以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先后出现3个高峰,分别为古希腊罗马文学、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创作被视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成就,他因此也就成了一位屹立于文学峰巅之上的文学巨人。
托尔斯泰于1828年9月9日生于俄国图拉州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他幼时便失去父母,在姑妈的监护下长大,接受了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6岁时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后转至法律系,但因迷恋社交、迷恋哲学而荒废了学业,终在1847年退学,回到划归他所有的他母亲的遗产——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并在这里度过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1851年,他以志愿兵的身份去高加索地区服兵役,参加与当地山民的战斗,两年后被提升为准尉。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他自愿来到前线塞瓦斯托波尔,在要塞中任炮兵连长,表现十分勇敢。1856年,他以中尉军衔退役,此后游历西欧诸国。回到自己的庄园后,他先后进行了一些旨在解放农奴的改革,但因未得到农民的理解而收效甚微。1862年9月,他与莫斯科一位医生的女儿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别尔斯结婚,从此过起了恬静、淡泊的庄园式家庭生活。婚后不久,早已开始文学创作的托尔斯泰打算以十二月党人为对象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但是不久他却发现,若不对十二月党人的前辈进行研究他便难以理解十二月党人,于是他便将目光投向更远一些的俄国历史,即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经过近6年潜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终于在1869年面世,并获得巨大成功。
但在这之后,托尔斯泰却开始对生活的意义感到怀疑,对贵族的生活方式感到反感,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世界观转变过程。在《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复活》(1889-1899)以及众多的小说、剧作和文章中,托尔斯泰卓越地表达了他对不合理社会的抨击和批评,宣传了他以博爱和不以暴力抗恶为核心的托尔斯泰主义。1910年11月10日,对贵族生活深感绝望的80余岁老人托尔斯泰终于决定离家出走。几天后,老人因在旅途中感染肺炎而病逝于梁赞至乌拉尔铁路线上一个名叫阿斯塔波沃的小站。依据托尔斯泰的遗嘱,他的遗体被运回故园,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一片树林中。童年时,托尔斯泰曾与哥哥一同在这片树林中寻找传说中那根能给人带来幸福的“绿魔杖”。如今,走进这座已辟为博物馆的托尔斯泰庄园,沿着幽静的林中小径,可以一直走到托尔斯泰的墓前。托尔斯泰的墓上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只有一片萋萋的芳草,然而,这里却无疑是俄国文学的一处圣地,俄国文化的一座丰碑。
在俄国这样一个以“文学中心主义”现象著称的国度里,人们崇尚文学,崇拜作家。若论被“神化”的程度,普希金恐怕无人能及,他早已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图腾;以深刻揭示俄罗斯民族性格、乃至全人类性格中复杂的“双重人格”而见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已逐渐赢得堪与托尔斯泰并列的文学地位;而就其创作影响悠远的“现代感”而言,契诃夫时而会让我们感觉到,他有比托尔斯泰更为亲切、更加自然的一面。20世纪的俄国文学,又相继造出了高尔基、索尔仁尼琴、甚至布罗茨基等“新神”。然而直到今天,在所有这些“伟大的”俄国作家中,“最伟大的”桂冠却非托尔斯泰莫属。托尔斯泰的伟大不仅在于其文学创作的规模和成就、风格和影响,更在于他身体力行的存在方式和作用于现实的思想力量。
托尔斯泰一生笔耕不辍,留下一笔巨大的文学遗产,其全集洋洋百余卷,仅就作品的数量而言,俄国作家中就鲜有能与托尔斯泰比肩者。在他所有的作品中,知名度最高者当属他的3部长篇小说,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在这3部小说中,人们在论及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及其悲剧命运时提及最多的是《安娜·卡列尼娜》,在分析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世界观时关注最多的则是《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借助爱情故事和复杂的心理刻画构成一部杰出的家庭小说和社会小说,《复活》通过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探索构成一部杰出的道德小说和教谕小说,但就由众多的人物、广阔的画面、厚重的笔力和深邃的历史感等构成的磅礴的史诗氛围而言,后两部小说仍不及《战争与和平》。提起作为一位作家、作为一位长篇史诗作者的托尔斯泰,人们首先想到、首先阅读的恐怕还是他的《战争与和平》;无论是在托尔斯泰本人的创作中,还是在所有俄国小说、乃至世界所有小说中,若要挑选出一部“最伟大的小说”,人们往往还是都会首先提及《战争与和平》。
《战争与和平》,仅从小说的题目来看,这就是一部史诗。自人类出现以来,战争与和平便成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主题,如同生与死、爱与恨之于个人生活。托尔斯泰的小说广泛地描绘了自1805年至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这里的“战争”,是指1805-1812年间俄国与法国之间断断续续的战事,直到库图佐夫最终击溃拿破仑;这里的“和平”,是指这段时间中俄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从贵族阶级的舞会、出猎和爱情,到普通士兵的战斗生活和农民的日常劳动。托尔斯泰出身贵族家庭,青年时代又长期生活在上流社会的社交界,他写起这一阶层的生活、刻画这一阶层人士的心理来,自然是得心应手;他刻意接近下层人民,主动去体验平民的生活方式,这使他又具有了一般贵族所没有的对人民生活的熟悉和理解。托尔斯泰长期在军中服役,并担任过下级军官,他因之能生动地写出战场上的细节,也比别人对战争及其意义和性质有着更深的理解。可以说,无论是对“战争”还是“和平”,托尔斯泰在写作这部巨著前都已经有了深厚的积累和深刻的体验。
《战争与和平》可以被视为托尔斯泰此前所有创作的集大成者。在写作《战争与和平》之前即已创作出的、并为他赢得广泛声誉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青年》和军事题材的小说《塞瓦斯托波尔故事》,就可以分别被视为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方面生活体验的结晶,是史诗《战争与和平》的铺垫。《战争与和平》中关于家庭和爱情之温情脉脉的诗意描写,是他自传体的《童年·少年·青年》之氛围的延续;将战争表现为一种非浪漫主义的残酷现实,同时又着力刻画、渲染俄国战士们的英雄主义之壮美,这一面对战争的文学态度我们曾在《塞瓦斯托波尔故事》中有所目睹。此外,托尔斯泰在《两个骠骑兵》、《哥萨克》等作品中体现出的对“自然人”的赞美,又被他投射在娜塔莎、卡拉塔耶夫等人的身上;而他在《琉森》、《家庭幸福》等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上流社会和“欧洲文明”的厌恶,他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写到的贵族地主的“改良”试验,在《战争与和平》中均有改头换面的再现。
《战争与和平》以卡拉金、罗斯托夫、鲍尔康斯基、别祖霍夫四大贵族的家庭生活为情节主线,恢宏地反映了19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生活。作者将“战争”与“和平”的两种生活、两条线索交叉描写,让他的500余位人物来回穿梭其间,构成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作者歌颂了俄罗斯人民抗击拿破仑入侵的人民战争的正义和胜利,并将俄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置于战争的特殊时代,通过其言行和心理,塑造出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小说中出现最多的四大家族以及与四大家族有各种联系的贵族人物被作者大致分成两类:一类为趋附宫廷、投机钻营的库拉金家族,他们漠视祖国的文化,在国难当头时仍沉湎于寻欢作乐;一类是另外三大家族,尤其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安德烈和彼埃尔,他们是接近人民、在危急关头为国分忧的人物,他们甚至能挺身而出,为祖国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在赞美这一类型的贵族精华的同时,作者也描写了普通人民中的杰出代表,这些普通的官兵在战争中体现出的朴实勇敢、高尚忠诚的品质,与那些身处高位却卑鄙渺小的贵族统治者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战争与和平》对战争的大场面描写是无与伦比的,作家在短短的一两个章节中,就能将数万人拼搏的战场描写得有声有色。作家又能在几段看似简单的叙述性文字中,准确地交代出一个个关键的政治事件和历史转折过程。与此同时,托尔斯泰又能深入进多个人物的内心,让客观的历史画面描写与微观的人物心理历程相互媲美。托尔斯泰笔下人物的性格发展合情合理,他的这一艺术手法后来被车尔尼雪夫斯基概括为“心灵的辩证法”。车尔尼雪夫斯基概括出的托尔斯泰的另一杰出的艺术才华,即“道德情感的纯净”,在《战争与和平》中也有突出体现。通过彼埃尔、安德烈等人深刻的内心反省过程,他们似乎能看到托尔斯泰苦苦追求自我灵魂净化的轨迹。与对道德情感的描写相关的,还有托尔斯泰的道德学说,即所谓的“托尔斯泰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是在托尔斯泰晚年最终形成的,但其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如博爱、不以暴力抗恶、自我完善等,在《战争与和平》中已有鲜明体现,如作者通过卡拉塔耶夫的形象就宣传了他的勿抗恶思想。《战争与和平》就某种意义而言,也是托尔斯泰本人追求道德完善之过程的再现。
在托尔斯泰本人的创作中,《战争与和平》构成一个高峰,他之后的创作就某种意义而言,均为这部作品之延续。托尔斯泰的许多论者均热衷谈论托尔斯泰创作中的“转变”,认为在《战争与和平》之后,他的创作出现了某种自“战争”向“和平”的转变,即从战争史诗转向社会小说,从家庭的诗意转向社会的现实,从乐观的英雄主义转向悲观的精神求索,从客观的叙述转向主观的内省,甚至从文学和艺术转向了哲学和宗教。这样的描述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吻合托尔斯泰艺术和生活之路的实际轨迹,似乎还是一个有待深究的学术问题,这里不便展开论述,但我们能够断言的是,所有这些所谓的“转变”均始自《战争与和平》,换句话说,正是《战争与和平》开启了托尔斯泰在这部作品之后的整个创作探索过程。其实,他后期创作中的诸多因素,无论是爱情悲剧还是社会抨击,无论是道德探索还是精神自省,我们都可以在《战争与和平》中窥见其端倪。
在整个俄国文学的发展历史中,《战争与和平》是第一部具有全欧洲意义的小说。俄国文学史家德·斯·米尔斯基(2013: 353-354)曾说:“这部作品同等程度地既属于俄国,也属于欧洲,这在俄国文学中独一无二。欧洲长篇小说史或许会将这部作品归入国际范畴而非俄国范畴,归入自司汤达至亨利·詹姆斯和普鲁斯特的发展过程。”一方面,这是一部由俄国人写作的反映俄国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它刚一面世,便令欧洲和全世界的读者感到新奇,人们既津津有味于小说中的人与事、“战争与和平”、历史和沉思,也为小说所体现出的巨大的艺术表现力所倾倒,这样一部小说竟然出自此前在欧洲似乎并不主流的俄国作家之手,更是让人惊讶。在此之前,欧洲当然已经熟知普希金的诗歌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但伟大如《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的横空出世,还是会给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也就是说,《战争与和平》构成了俄国小说、乃至整个俄国文学崛起的标杆。另一方面,这部作为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就之高峰的俄国小说,却又最具有全人类性。就内容而言,它不仅是一曲宏伟的俄国贵族的“英雄田园诗”(米尔斯基语),同时它也在抒写整个人类的爱与恨、生与死、战争与和平;就形式而言,它综合性地继承了之前欧洲小说的丰厚传统,将长篇史诗这一艺术体裁发展到了极致,使得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小说家们只好在《战争与和平》之后另辟长篇小说写作的蹊径。正是《战争与和平》在世界文学史中所具有的这样一个地位和这样一种意义,才使得有人称它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毛姆语),“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史诗,近代的《伊利亚特》”(罗曼·罗兰语)。
1873年,因为史诗巨著《战争与和平》而享誉文坛的托尔斯泰再接再厉,开始创作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自1875年起刊载于《俄国导报》,最终在1878年推出单行本。《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3部长篇小说中承上启下的一部,是托尔斯泰整个创作的核心之一,也是世界范围内被读者阅读最多、被论者评说最多的小说之一。
《安娜·卡列尼娜》的内容早已脍炙人口:魅力聪颖的贵族小姐安娜经姑妈撮合,嫁与比她大20岁的高官卡列宁为妻,婚后生活平平淡淡,却也规范圆满,夫妻之间缺乏爱情,但儿子谢廖沙的出生却给安娜带来了幸福和慰藉。8年过后,前往莫斯科调解兄嫂不和的安娜与贵族青年伏伦斯基热烈相恋,美丽端庄、诚实坦荡的安娜并未将这场爱情视为上流社会并不鲜见的逢场作戏,而是当作其情感追求和人生幸福的归宿,她因此遭遇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强大压力,并默默承受着自己内心的道德拷问和良心谴责。实为花花公子的伏伦斯基逐渐厌倦这场爱情,同时丧失了家庭和爱情、名誉和纯洁的安娜最终选择卧轨自杀。作为安娜和伏伦斯基爱情纠葛之对照,托尔斯泰还设置了另外一条情节线索,即列文和吉娣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年轻的地主列文是一位有良心的贵族,他幻想社会的公正公平,他在自己庄园实施的土地改革虽未获成功,但他的宗法制家庭生活理想却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这两对男女的爱情和生活,不仅是两种爱情观和生活观的比对,同时也折射出托尔斯泰对于家庭和社会、爱情和道德、理想和现实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艺术再现。
关于《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人们已说得太多,无论是安娜的爱情悲剧还是小说的“拱形结构”,无论是列文形象中的作者自传色彩还是安娜持续绵延的“内心独白”,无论是托尔斯泰在创作过程中对安娜的态度之转变,还是小说中所蕴涵的“家庭思想”之构成和内涵,均已获得汗牛充栋的评说。而在这里,笔者着重想谈的,就是这部作品在托尔斯泰本人小说创作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俄国文化史中的意义。
首先,如前文所述,《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3部最著名长篇小说中承上启下的一部。将托尔斯泰的3部长篇小说当作一个整体、一个过程来看待,便可以更具体贴切地感觉出《安娜·卡列尼娜》的独特之处。比如在写作时间和作品篇幅上,《战争与和平》写了6年(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写了4年(1873-1877),《复活》则写了10年(1889-1899);《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之间相隔6年,而《复活》的创作则在《安娜·卡列尼娜》面世10余年之后方才开始。也就是说,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越写越慢(《战争与和平》虽然写了6年,但篇幅却数倍于后两部小说),相互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篇幅则越来越小。比如在作品的题材和体裁方面,“《战争与和平》的史诗性(民族和祖国的命运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和《安娜·卡列尼娜》的长篇小说形式(作品的情节基础是女主人公的命运)在《复活》中相互结合,构成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即托尔斯泰在书信和日记中自称的‘大场景’、‘大呼吸’小说”(Николаев 1990: 303)。也就是说,从《战争与和平》的历史场景到《安娜·卡列尼娜》的“家庭思想”再到《复活》的道德说教,从史诗到小说再到“忏悔录”,大致便是托尔斯泰长篇小说创作在题材和体裁上的演进过程。再比如,3部小说在风格和基调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战争与和平》中的那种激越的热情,向上的精神,欢乐明快的色彩,在《安娜·卡列尼娜》中见不到了,取代它们的是惶惑迷惘、冷峻悲怆的情调” (曹靖华等 1992: 559)。而到了《复活》中,托尔斯泰的“思想转变”(обращение/conversion)也已完成,所谓“托尔斯泰主义”亦大致形成,《复活》中的氛围于是又宁静了下来,不再有《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焦虑和不安定性。值得注意的是,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在将《复活》与托尔斯泰之前两部长篇做对比时就毫无保留地更推崇前者:“《复活》显然远逊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尽管篇幅不小,它却并非托尔斯泰用力最甚、关注最多之作品……认为《复活》是衡量托尔斯泰后期创作天赋之标尺,这一看法不妥,《复活》应被视为他最不成功的作品之一……《复活》并非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因为源自《福音书》的大量道德观念并未有机地融入作品的构成……其最佳之处并非晚期托尔斯泰的典型特征,它们更像是《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之特征,不过稍次一等。”(Mirsky 1926: 21-22)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战争与和平》知名度最高,《复活》则时常被称为其创作之“巅峰”,其实,如若说《战争与和平》以深厚的历史感见长,《复活》以深刻的思想性著称,那么,《安娜·卡列尼娜》让我们倾倒的则首先是与作者和主人公同时具有的复杂感受和紧张情绪相伴的“生活流”;如若说《战争与和平》过于宏大的篇幅以及结尾处的哲理议论或许让人难以阅读,《复活》过于直露的教谕性质或许让人心生某种抵触,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则因其有趣的故事和完美的叙述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欲罢不能。《安娜·卡列尼娜》是托尔斯泰在他思想探索最为紧张、创作精力最为旺盛、艺术技巧最为纯熟时创作出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探索最鲜活、最典型的体现。
其次,《安娜·卡列尼娜》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同时也是俄国近现代文化崛起过程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我们过去通常是在文学史框架中看待《安娜·卡列尼娜》的,而较少将它置于文化史、思想史和一个民族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中去评估其意义,其实,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和俄罗斯形象的形成过程中,以《安娜·卡列尼娜》等作品为代表的托尔斯泰创作,以及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19世纪俄国文学,无疑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正是《安娜·卡列尼娜》等俄国小说让整个西方意识到了俄国文学和文化的强大力量。1846年,果戈理(Гоголь 1990: 184)曾发出预言:“再过十来年,您就会看到,欧洲人来我们这里不是为了购买大麻和油脂,而是为了购买欧洲市场上已不再出售的智慧。”应该注意到,在果戈理出此言的19世纪中期,彼得大帝欲西化俄国的改革早已完成,叶卡捷琳娜的扩张政策使俄国版图急剧扩大,亚历山大的军队更是开进了巴黎,可俄国在文学和文化上似乎仍未完全融入欧洲,俄罗斯民族似乎仍未被接纳为欧洲文明大家庭的平等一员。直到30余年后的19世纪70年代,果戈理的预言方才应验,因为恰在此时,在普希金的诗歌、别林斯基的批评和屠格涅夫的小说之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又相继面世,这些伟大而又完美的艺术作品使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意识到了俄国文学的伟大,并进而意识到了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的伟大。
在果戈理的预言之后第一个敏锐感觉到这一变化的人,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而促使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文学事实,正是当时在《欧洲导报》上连载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7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冈察罗夫在彼得堡街头相遇,两人迫不及待地就刚刚开始发表的《安娜·卡列尼娜》交换看法。“很少兴奋”的冈察罗夫此次有些反常,他情绪激昂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道:“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作品,是空前的第一部!我们的作家中有谁能与他媲美呢?而在西欧,有谁能写出哪怕一部与此近似的东西来呢?在他们那里,在他们最近几年所有的文学作品中,甚至追溯到很久以前,哪里有能与此并列的作品呢?”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3: 199-200)陀思妥耶夫斯基深有同感,他在此后所写的《〈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意义特殊的事实》一文中转述了冈察罗夫的意见,并进而写道:“在这个我自己也赞同的判断中,使我感到惊讶的主要一点是,针对欧洲的这一见解恰好与当时许多人自然产生的那些问题和疑惑相关。此书在我眼中很快成为一个可以代替我们向欧洲做出回答的事实,一个可以让我们展示给欧洲的梦寐以求的事实。当然,有人会嚷嚷着讥笑,说这只不过是文学,一本小说而已,如此夸大其词,拿着一本小说去欧洲露面,未免可笑。我知道,有人会嚷嚷,有人会讥笑,但是请安静,我没有夸大其词,我目光清醒:我自己也知道,这眼下只不过是一本小说,只不过是所需之整体中的一滴水,但对于我来说重要的是,这一滴水已经有了,如果一位俄国天才能够创造出这一事实,那么很自然,他绝对不会无所作为,时辰一到,他便能创造,能给出自己的东西,能开始道出并道尽自己的话语。”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3: 199-200)陀思妥耶夫斯基接着说,《安娜·卡列尼娜》即那一个在欧洲世界面前构成“我们之特性”的东西,即一种新话语,“这一话语在欧洲无法听到,然而欧洲又迫切需要倾听,尽管它十分高傲”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983: 199-200)。
一部小说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和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国际形象和世界地位产生多么重大的意义,《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提供了最为出色的例证。当下,中国的经济腾飞已成为公认的世界奇迹,我们的小康社会已初步建成,而文化软实力的加强似乎还任重道远,在这样的历史关头,俄国文学于19世纪后半期的强势崛起似乎仍能为我们提供出某种参照。
Аксенов М.Д. 2001.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для детей(Т. 9)[M]. Москва: Аванта.
Гоголь Н.В. 1990. Выбранные места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с друзьями[M].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 1983.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Т. 25)[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Николаев П.А. 1990.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M]. Моск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е.
Mirsky, D.S. 1926.ContemporaryRussianLiterature(1881-1925)[M].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曹靖华等. 1992. 俄苏文学史(第1卷)[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德·斯·米尔斯基. 2013. 俄国文学史(上卷)[M]. 刘文飞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弗·叶·巴格诺. 2012. 西方的俄国观[J]. 刘文飞译. 外国文学评论 (1).
I512
A
2095-5723(2013)01-0048-06
(责任编辑 张 红)
2013-01-27
通讯地址: 100732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