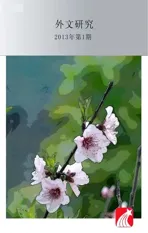篇际性研究对互文性批评的启示
2013-03-20河南大学刘辰诞
河南大学 刘辰诞
篇际性研究对互文性批评的启示
河南大学 刘辰诞
篇章学的篇际性研究和文学理论的互文性同源。篇际性探索一篇章与其他篇章间的关系如何在作者和读者的交际中为交际目标服务,从而为分析篇章的生产和理解过程提供一定的社会、心理和认识图式;而互文性理论则重视社会的、历史的、认知的、文化的百科知识性对话,分析视角过于宽泛因而缺乏可操作性。既然互文性和篇际性的研究目标都是文本,而后者比较注意程序化操作的研究方法正是前者所欠缺的,那么两者就存在互相补益的可能性。本文意在寻找可行的路径,使篇际性的程序化方法能够帮助互文性批评去粗取精、更趋科学化。
篇际性;互文性;文学批评;科学化
一、导语
篇际性(intertextuality)是de Beaugrande & Dressler提出的篇章性(textuality)七标准之一,指当前篇章及其参与者与曾经直接或间接经历过的既往篇章之间的关系,这些既往篇章或篇章知识会被作为生成当前篇章的语境因素之一参与篇章构建,作为情景性的重要因素渗透到篇章生产者和接受者双方的共有知识和语言共识之中,决定着一个篇章是否关联、是否具有意义,从而给篇章的生产和理解过程提供一定的社会、心理和认识图式,使篇章的交际功能得以顺利实现。文学批评领域的互文性与篇章语言学的篇际性同源,中文译文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互文性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为文学作品的阐释服务,被视为文学文本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性。互文性的内涵比较宽泛,强调文本的异质性和对话本质,是一种文化的一般形态,这种形态是一个复杂的代码网络,具有异质弥散的文本实现形式。每个文本因其与另一文本有着千丝万缕的相关,因此互文性似乎无处不在(Bloometal,转引自辛斌 2000: 15)。篇章语言学的篇际性和文学批评的互文性两者的研究有共同之处,那么篇际性研究和互文性研究之间一定能够互相启发。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提及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的中译文时,所论如果是篇章语言学的研究就用“篇际性”来表述,如果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则用“互文性”来表述。
二、篇际性及其研究方法
篇章语言学认为,对于作者而言,篇章生产过程必然有赖于作者对既往其他篇章知识的了解,对于接受者而言,篇章理解过程也必然离不开有关其他篇章的知识,即“每一个篇章都是对其他篇章吸收和转换的结果”(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223)。就篇章的宏观系统性而言,任何篇章都不可能作为单独的个体而存在,它存在于与其他篇章的关系中,一个篇章中,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存在着其他篇章。de Beaugrande & Dressler从篇章动态交际程序出发对篇际性展开研究,认为当前篇章会将以前的篇章作为生成或理解篇章的语境因素之一。例如司机在行程中看到“Resume Speed”(恢复速度)这样的交通标示时,他对这一标示性篇章的理解要建立在此前已经有过同类篇章知识的基础上,否则接受者(司机)不会理解“Resume Speed”这一小篇章的意思。对于这样的理解过程,篇章语言学研究其心理操作程序,研究既往篇章的建构图式(schema)如何在人们对当前篇章的认识中建立起桥梁。对于篇章生产而言,这个图式称为“构思图式”,指导作者构建篇章的表达方式,对于接受者而言称作“心理图式”,指导篇章接受者在某一个或某一些框架内完成对篇章的理解。
篇际性的表现形式之一是,一个类型的篇章中往往含有其他类型的篇章,比如《独立宣言》这一篇章最突出的功能是“论说”,即引导读者接受美国应该解除政治束缚这样一种信念,但其中含有对美洲殖民地状况的“描写”,又有对英国的活动的“叙述”。文学篇章也是如此,其中往往也会同时含有描写、叙事、论说等类型的篇章型式。篇际性理论认为,文学篇章是“与公认的真实世界版本有替代性(alternativity)关系的一种篇章世界”(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226)。这个“替代”的目的是诱发人们对世界组织不以现实世界的客观形式来认识,而是将其看作从人类社会认知、交际和协商演变而成的事物。
既往篇章知识对篇章建构和解读过程的篇际性影响因素大致分为三类(de 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 223-230): 1)某些篇章类型在同一篇章中的同现,如描写类篇章、叙事类篇章等可以出现在其他篇章类型中;2)引喻(allusion),即运用引述或参照名篇的方式组织或解读篇章;3)对话中对方说过的话语。
篇章参与者对既往篇章的知识在篇章生产和理解中的运用和依赖通过中介(Mediation)过程运作,所谓中介是指作者或读者将当前信念和目标注入交际情景模型的程度。当前篇章和既往篇章之间的时间跨度和处理活动区域越大,中介就越大。运用和参照特定的著名篇章时中介较小,在答问、争辩、总结或评价其他篇章时,中介微乎其微。
可以看出,篇际性侧重于研究篇章(文本)之间所具有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篇章生产和解读中的作用以及其作用程序,认为包含文学篇章在内的任何类型的篇章都具有这种属性,当前篇章的生产和接受离不开以前的某个或某些篇章,既往篇章给当前篇章的生产提供图式,给解读提供语境,研究其间“中介”的介入过程。比如上述《独立宣言》的例子,作者在组织这个篇章时就要熟悉描写和叙事篇章的特征及其在论说篇章中出现的作用和功能,用以加强论说的力量,帮助其更好地达到论说的目标。相应地,读者在接受这一篇章时,也要依赖知识域中的描写和叙事类篇章知识,以更好地理解作者意图,对《宣言》的说理和论辩有更好的理解。在这个过程中,篇章参与者通过中介,即对篇章知识的认识图式达到对当前篇章的组织和理解。
被援引或参照的篇章和当前篇章的生产时间跨度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比如1600年左右Christopher Marlowe写过一首《牧羊人恋歌》,内容是一个牧羊人表达其炽热爱情,开头一段是这样的:Come live with me and be my love, /And we will all the pleasures prove /That valleys, groves, hills, and fields, /Woods, or steep mountain yields。牧羊人把溪谷、山岭、树林当作无边的欢乐,用来吸引他心爱的人儿来与他同享,接下来牧羊人许诺心爱的人各种鲜花和山村的嫁衣。不久以后Sir Walter Raleigh模仿此诗写了一首《仙女对牧羊人的回答》,说如果牧羊人说的是实话,她愿意放弃现在的快乐与牧羊人生活在一起做他的爱人:If all the world and love were young, /And truth in every shepherd’s tongue, /These pretty pleasures might me move /To live with thee and be thy love. Raleigh使用了与Marlowe原诗一样的表层形式(相同的韵律和相等的诗节数),而且还引用了原诗的许多语言表达形式,如“To live with thee and be thy love”句中,除人称代词换了第二人称外,与原句的请求“live with me and be my love”一样。很显然,对Raleigh诗的理解和审美领悟必须以对Marlowe原诗的理解和了解为前提。1612年,英国著名诗人John Donne 也借用了Marlowe原诗的形式写了下面这首诗, 只是把牧羊人换成了渔夫:Come live with me and be my love, /And we will all the pleasures prove, /Of golden sands and crystal brooks: /With silken lines, and silver hooks。渔夫用与原诗同样的形式,表达他认为的快乐:金色的沙滩、晶莹的溪流,到处是丝质的鱼线和银质的吊钩,与牧羊人心目中的快乐即山岗、溪谷、树林异曲同工,渔人的愿望因此憨态可掬。John Donne的诗与Marlowe的原诗相隔时间比Raleigh和Marlowe之间的时间跨度大,也就是说,“中介”更大,因此John Donne诗的头两句与Raleigh的完全相同,这样才能够使读者在建构篇章理解程序时更容易利用篇际性因素,不然篇际性因素的可靠性就要减弱。1935年Cecil Day Lewis 仿照Marlowe的原诗写了一首讽刺诗,诗中的说话人是一个没有技能的体力劳动者:Come,live with me and be my love, /And we will all the pleasures prove, /Of peace and plenty, bed and board, /That chance employment may afford. /I’ll handle dainties on the docks /And thou shalt read of summer frocks: /At evening by the sour canals /We’ll hope to hear some madrigals. Marlowe原诗的意境是牧羊人或劳动阶级生活的欢乐和嬉戏场景,大自然是他们嬉戏的道具,而Lewis这首诗的宗旨与原诗完全背离,表达的是劳动者的艰辛困苦,祈求的是平安和起码的生活条件,其讽刺意义在戏仿原诗的表达手法中加强了作品的力量,在与原作传统的对立中,强烈揭露了1930年代经济萧条时期的“现实世界”。
这几首诗的引用和戏仿能够激活解读者头脑中关于原诗的知识,包括语言形式、诗歌韵律、意义等,这些知识自然会参与到解读者的即时处理过程中。篇际性研究通过这样的实例分析从认知操作的角度来说明篇际性其实是一种记忆关联,篇章的某些符号、结构或意义担当触发器(trigger)的角色,引发对以前语篇的记忆或联想,从而引发作者和读者在建构和解读篇章时的心理操作过程。
第三类篇际性因素是对话中对方说过的话语。由于这些因素发生在对话中时,中介微乎其微,文学批评的互文性一般不讨论此类“互文”性,因此本文不详谈。
篇章语言学研究中对篇际性研究做过较深入研究的社会语言学家Fairclough从批评话语分析的角度将篇际性区分为“表层篇际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深层篇际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Fairclough 1992: 104)。所谓表层篇际性指在篇章的语言层面中清晰可见其他篇章的痕迹特征,其他篇章较明显地存在于所分析的篇章中;深层篇际性只是隐含其他篇章的语言特征,通常指一个篇章中各种体裁或语篇类型规范(conventions)的复杂关系,例如法律篇章的高度正式和严密的语言结构在其他篇章类型中的使用。表层篇际性包含5个范畴,即话语引述、预设、否定、超话语和反语(Fairclough 1992: 119)。深层篇际性体现在它包含了形成一定篇章的各种篇章规约结构,诸如与不同篇章实践相关的体裁、话语和文体等。
篇际性研究虽然比较微观,但其最终目的不是要建立一个客观的篇章序列,而是对建构某一篇章类型与其他篇章类型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进行评价。因此,篇际性研究者强调,其研究目的并非对某一语言或结构的出处追踪求源,而在于指导生产者和解读者对其他篇章的表现形式加以利用,通过一篇章形式与他篇章类型间的关系欣赏和评价当前篇章的价值和作者的交际目的,重视篇际性因素为篇章生产者所有意察觉的心理过程,因而程序性较强,有助于批评家对篇章进行有效的鉴赏和评价。
三、互文性及其批评方法
文学批评理论领域的互文性理论是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在我国文学批评领域它还被译作“文本互涉”、“文本间性”。这一理论打破传统的文本自主、自足的观念,对文本及主体进行解构*樵 歌,http://my.ziqu.com/bbs/665006/messages/4585.html.。叙事学家Gerald Prince在《叙事学词典》中对互文性下了一个较为通俗易懂的定义: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但是综观国内外文学批评领域关于互文性的研究,这一术语的内涵和研究领域远非这么简单。
首先提出互文性概念的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认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镶嵌品那样构成的,每一个文本都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一切语境,无论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心理学的、历史的,都变成了互文本,文本的边界消除了,每一个文本都向所有其他文本开放,从而这一文本与其他文本都互为互文本。(程锡麟 1996: 72-78)
克里斯蒂娃提出这一观点是受了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启发。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诸问题》中认为陀氏的小说中语言的不同方式和评价“现实”的不同方式并存和相互作用,是“复调小说”,体现了“文学的狂欢节化”(the Carnivalization of literature),像狂欢节认可种种文化行为和话语的综合性混合那样,复调小说容许这样的“对话”。“文学的狂欢节化”这一概念实际上就是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之间的系统性、“互文性”联系。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促进了互文性理论的迅速发展。但是这两种探讨互文性的方式都缺少主体——说话者、作者、读者——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巴特(Roland Barthes)和克里斯蒂娃把主体引入互文性关系的空间。克里斯蒂娃认为,互文性是增强语言和主体地位的一个复杂过程,一个为创造新文本而摧毁旧文本的“否定”过程。她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指出,一个文本作为表意实践的条件总是以其他话语的存在为前提的。巴特在S/Z一书中把文本界定为“跨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和“多主体性的”(multisubjective),文本分为两类,即“可读的”(lisible)和“可写的”(seriptible)。“可读的”文本是可以进行有限的多种解释的文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进行阅读的,是半封闭性的。“可写的”文本则不能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来阅读,已有的解码策略不适合于这类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表意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程锡麟 1996: 73)巴特认为,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其他文本程度不同地以多少可以辨认的形式存在于这一文本之中。
热奈特(Gaerard Genette)提出一个新的术语“跨文本性”(transtextuality)。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文字是“跨文本的”,或者说是一种产生于其他文本片段的“二度”结构,他提出了跨文本性的5个主要类型:互文性、准文本、元文本性、超文本性和原文本。其中互文性包括引语、用典和抄袭。元文本性(metatextuality)指一个文本与此文本所谈论的另一个文本联系起来的“评论关系”(commentary relation)。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指把文本B(“超文本”,hypertext)同文本A(“前文本”,hypotext)联系起来的任何关系。(程锡麟 1996: 76)
尽管理论们家对互文性的界定和阐述不尽一致,但他们都把互文性关系的研究看作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十分注意读者和批评家的阅读活动在文本意义生产活动中的作用。卡勒(Culler)在实践和理论上,对互文性理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在《符号的追寻》中认为,与其说互文性是指一部作品与特定前文本的关系,不如说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或一种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见,互文性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论观点。狭义互文性的代表人物是热奈特,他认为互文性指一个文本与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狭义互文性是用互文性来指称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具体文本之间的关系。广义互文性把“文本”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作用包括进互文性,认为文学文本是对社会文本的阅读和重写。广义和狭义其实是互文性概念的两种潜在可能性或两极性。卡勒认为这种双重焦点造成了互文性理论的两难处境:互文性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文本空间,是一个难以使用的概念,但当人们缩小其范围使其更加有用时,又会陷入传统的实证主义的来源研究。(程锡麟 1996: 72;秦海鹰 2004: 26)最广义的互文性当属巴赫金的对话原则或理论界所说的“互话语性”(inter-discursivity),最狭义的互文性则要算热奈特所说的文本“共在关系”,而里法特尔的互文性理论则兼有广义和狭义的双重性质,因为他一方面用互文性来定义文学性,认为只有经得起互文阅读的文本才称得上是文学,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在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中寻找可以考证的互文本。
互文性理论对文艺作品的结构研究注重读者和批评家的作用,认为批评家参与创造了所阅读的作品,建构了它的意义,才使作品得以存在。也就是说,传统文学研究以作品和作者为中心,注重文本的作用,互文性理论则注重读者和批评家的作用。传统文学研究一般都力图找出文本的“正确”意义,互文性理论则拒绝明确或固定的意义。传统文学的影响研究注重一个文本对其他文本的具体借用,而互文性理论除此以外还研究那些无处不在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范围。(程锡麟 1996: 2-7;黄念然 1999: 15-21)
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开阔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是互文性理论的弊病也显而易见:互文本究竟是文本本身,还是进入文本中的另一个文本?一些研究者认为互文本是“一个吸收了多种文本、但仍以一个意义为中心的文本”(Jenny 1976: 267),也就是说,互文本是当前文本。另一些研究者把互文本视为处在互文性关系中的各种文本的总和(Arrive 1972)。也有研究者为了避免把互文本实体化,提出互文本即一个文本与另一个文本之间的“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如果把当前文本当作文本甲,那么与文本甲发生文本关系的另一个文本乙并不因此就叫作互文本,只有文本甲和文本乙之间的关系或“区间”才叫作互文本(秦海鹰 2004: 19-30)。尽管现在的基本共识是把一个文本所吸收的其他文本叫作互文本,使这一概念比较容易把握,但是究竟什么才是互文本,仍然没有一定的界定。互文性理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它的研究尤其是广义互文性的研究过于虚无所致,它的这些缺陷必然导致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
德里达(Derrida)对哲学文本的解读、罗兰·巴特的解构写作与阅读实践、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女性主义者的研究以及解构主义文学批评实践都是互文性理论在批评实践中运用的表现。但是德里达、巴特的批评实际上还是属于哲学思辨的范畴。比如巴特的S/Z是对巴尔扎克的《萨拉辛》的详细阅读,是罗兰·巴特最成功的批评之作,其中对批评和文学科学或者说诗学科学做出了区分:前者试图阐释并给作品指派一种意义,后者研究文学话语的功能特性,研究使我们能够阅读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潜在系统。巴特并不是在阐释《萨拉辛》,而是在研究文学话语运作的方式,以及阅读系统的本质,强调阅读就是意义的生产过程,就是通过多种方式组合读到的词语以生产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为多种“代码”所左右,能够在多个层面创造出可理解性,例如读者通过“行动代码”把词组织为行动,通过“阐释代码”把文本的一些元素视作秘密的建构,允许其他元素加入,通过“语义代码”,把语义特征分组以形成角色和主题,通过“参照代码”,把文本各要素放进社会分类,使叙述者和读者共享的社会知识在阅读中产生效应,通过“象征代码”使文本要素产生象征作用。巴特给出这5种代码并加以思辨性的阐释,但没有可操作性程序支持其批评实践。从这种意义上讲,巴特的批评实践实质上仍然是属于哲学理论。至于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女性主义者的研究所涉及的互文性批评,其实是把文本的解读置于历史或现实的语境中进行审视,把语境在阅读中的调控作用全部作为互文对待,模糊了文本本身的互文性要素,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狭义的互文性理论的批评实践,包括研究对早期文本的参照、同一文本两个故事的交叉、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间的循环、结尾或开头的增殖、文本与社会语境的排比、语义单位如主题和思想的排比、比喻与原意的排比等等。(佛克马等 1988: 108-112)这些所谓狭义的互文性批评与文本关系比较密切,但是流于检索性列举。
国内的互文性批评也大多是追随西方的传统,要么止于哲学思辨,要么流于包罗万象的检索性列举。例如,“‘拼图’中诞生的诗歌——梅利尔诗歌《迷失在翻译中》的互文性解读”一文(王卓 2006: 90-94)是以互文性理论为框架对《迷失在翻译中》(LostinTranslation)一诗的批评。文中寻找的“指涉”和“语言碎片”实际上就是狭义互文性批评中常常提到的所谓“拼贴”。该文显然是把形式互文性因素如“拼贴”手法(包括结构上的拼贴和诗歌韵律上的拼贴)、修辞格、词的多义性与意义互文性因素都作为诗中的互文性的表现手法进行挖掘。然而这样无所不包的互文性批评方法与传统的作者创作意图、文本主题思想、作品的语用含义阐释究竟有多大的区别?并且文章只是着重指出哪些是互文性因素,而没有触及这些互文性因素在创作和阅读过程中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和程序帮助作者达到创作目的、怎样影响读者的期待而完成审美过程的。这些都是互文性批评方法应该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再如,“勃洛克长诗《夜莺园》的互文性和叙事密码解读”一文(夏益群、蒋天平 2009: 62-65)对《夜莺园》进行互文性和叙事理论分析,考察夜莺、玫瑰与驴这3种物象在诸多文学作品中的意象表现,认为《夜莺园》中夜莺与玫瑰的物象—意象转化的组合遵循的是文学传统中的意象象征模式,而将驴与夜莺置于同一浪漫诗意的层面,夜莺和驴由物象转变为意象并置也是互文性的结果。文章认为勃洛克(Blok)的诗和费特(Фет Афанасий Афанасьевич)的诗不仅有夜莺和玫瑰这两个相似的物象,而且在情感上都是相似的,这也是互文性的表现。“身体的再现——论拜厄特小说《太阳的影子》中的父亲形象”一文(徐蕾 2009: 116-124),采用互文批评方法对英国当代女作家拜厄特(A. S. Byatt)的小说TheShadowoftheSun中的父亲形象进行了互文性分析,提出“父亲”的身体形象和《圣经》中参孙的身体形象之间存在互文关系,把人物形象的相似性视为互文性。“从迈克·朗利诗歌看互文写作与文学创新”一文(夏延华 2009: 81-87)以当代爱尔兰诗人迈克·朗利(Michael Longley)的诗歌为例,把文学作品表现出的情感的相似性看作互文性,并称之为“情感互文本”。“从对《死者》的重写看欧茨的创作观”一文(单雪梅 2009: 111-117)把美国当代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儿·欧茨(Joyce Carol Oates)对文学大师詹姆斯·乔伊斯的经典短篇小说《死者》(TheDead)的重写看作是互文性写作的成功实践,探讨其中形式描摹的互文性特征,也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视角移植看作互文性的体现。
从上面所举出的国内外互文性批评的例子可以看出,互文性批评要么脱离文本形式本身,过于重视社会的、历史的、认知的、文化的百科知识性对话,要么几乎无法绕过传统意义上的来源和影响研究。这就造成了互文性理论的两难处境:要么繁杂无章、缺乏可操作性,因其所表示的广大而不明确的文本空间而成为一个难以使用的概念,要么陷入传统的实证主义的来源研究。(程锡麟 1996: 72;秦海鹰 2004: 26)
四、篇际性对互文性方法科学化的启示
篇章学领域和文学批评领域的篇际性和互文性都是研究篇章(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相互解释的关系对创作和解读的影响。篇章语言学的研究侧重于篇际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对篇章交际过程——包括篇章生产和解读过程——的影响,研究程序易于把握,操作所涉及的心理程序和分析程序。文学批评领域的互文性理论主要关注文学文本的对话性和杂语性本质,关注历史文化意识对文本形式、结构和阅读策略的影响,目的是揭示文本本身存在的创新性和合理性、作者的创作源泉和手法、读者的阅读方式和心理等,注重“历史载入篇章和篇章载入历史的过程”,因此就显得纷繁,思辨性强而程序性弱。无所不包的批评方法显然会导致研究缺乏有效性和科学性,那么比较注意程序化操作的篇际性研究一定能够给互文性批评以有益的启发。
首先,篇际性研究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对篇际性因素也有明确的界定,例如不同篇章类型在同一篇章中的同现、篇章生产和解读过程中所要依赖的既往篇章知识、篇章对篇际性因素的依赖程度,文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在篇章生产和解读中的作用以及其作用程序、其间“中介”的介入过程,即便是研究语境在篇际性影响过程中的作用,也离不开“互文本”:即认为既往篇章本身就是语境因素之一,给当前篇章的生产提供图式,触发文化或历史语境。文学批评理论中的互文性既可以聚焦于互文本本身,也可以聚焦于互文本置身其中的那个文化空间,把包罗万象的历史、文化都作为互文本,这双重焦点造成了互文性理论的两难处境(程锡麟 1996: 72;秦海鹰 2004: 26),甚至连互文本和本文本的概念都纠缠不清。
其次,在篇际性研究中,具体的篇际关系在某一篇章建构过程中可能是重要的线索,但是寻找篇际关系不是目的,目的是对建构某一篇章类型与他类型相关关系的全局价值进行评价。对于篇章生产者而言,篇际性的理论意义在于指导生产者根据篇章内部的逻辑关系和语义结构对他篇章的表现形式加以利用。对于解读者而言,篇际性理论可以指导其通过一篇章形式与他篇章类型间的关系解读作者的交际目的或欣赏当前篇章的价值。而互文性研究过于强调读者,轻视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地位。广义互文性批评实践实质上仍然是属于哲学理论范畴,而狭义互文性批评实际上也有任意界定互文因素之嫌。这样任意界定互文因素的批评方法与传统的作者意图、文本主题思想、作品的语用含义阐释区别不大,不能突出互文性批评的优势,使得互文性批评失去了自身独特的品格,或落入传统批评的窠臼,或不知所云。这也许是互文性理论常常遭到非议的原因之一。
互文性方法如果能够像篇际性那样在理论和操作上令批评框架也更为清晰可辨,更注重操作程序,注意理论内涵的界定,就会更为科学、有效。那么,互文性批评可以从哪些方面从篇际性研究中汲取启发呢?除上文介绍过的篇际性研究的程序性方法外,“批评语言学中互文性的描述方法”一文(范胜福 2009: 102)介绍的批评语言学的篇际性研究的社会与历史分析、形式分析和解释与再解释过程3种分析模式或许对互文性研究更加科学化有一定的助益。社会与历史分析用来描写文本出现的社会及历史语境,包括时空场合、社会结构等诸多因素;形式分析则包括对文本语言各层次形式结构的描述;解释与再解释过程则使文本形式与社会历史诸因素建立连接,以期从社会历史诸因素中找到对文本形式合理统一的解释。文本形式的描述在整个分析模式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整个解释过程中相对“客观性”的过程。文本的内部声音(intra-vocalization)与当前文本相对应,而外部声音(extra-vocalization)与互文本相对应,按照Halliday的分类系统、及物系统、情态系统和转换系统对互文性的意识形态传递功能进行描述分析。及物系统“把经验世界分成易操作的一组过程”(Halliday 2005: 106),情态系统用以描写人际功能。以HONDA广告为例:Which means the folks who live in your neighborhood will come to the only logical conclusion.(引自黄国文 2004)此广告所展现的语场为劝说购买某种产品;基调是邻里之间,不构成社会等级;话语方式为口语。可以看到当前文本与一般广告文本通过体裁的篇际性转换,产品生产者将最初的等级性社会关系改变为邻里之间的非等级社会关系,拉近了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从而更好地传递了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广告文本可以如此,文学作品当然也可以根据作者的目的对这样的篇际因素加以利用,这样的分析程序也就自然可以为互文性批评所借鉴。
Fairclough提出:任何一个话语实例同时被视为1)一个篇章;2)一个话语实践实例;3)一个社会实践实例。篇章维度着眼于对语言特征做具体的描述,话语实践维度对篇章联结作者与读者的互动过程进行描述,社会实践维度结合社会语境揭示其中的意识形态含义。(Fairclough 1992: 189;丁建新、许伊 2007: 128)互文性批评如果以这3个维度为框架,分析便既有微观语言层面的描述,又有宏观社会层面的解读和阐释,就会提高批评的程序性,即科学性。国内有学者曾用篇际性方法对《爱丽斯漫游记》进行了互文性分析,“揭示其中秘而不宣的意识形态运作及对儿童读者主体位置构建的潜在影响”(丁建新、许伊 2007: 127-131)。儿童文学作品并不仅仅是为儿童提供阅读的愉悦那么简单,而且是一种“文化产品”(Taxel 1995: 159),是成人借助语言符号为媒介以倡导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工具。传统上,成人总是鼓励儿童采取一种移情式的阅读策略,完全认同作品中主人公的体验和态度,使儿童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被作品所宣泄的成人意识形态所操控,导致主体性或自我的丧失。《爱丽斯漫游记》恰恰是以一种反传统、反社会化的姿态独树一帜,处处机锋,这种反传统精神与该作品中的“互为话语性”(即互文性)不无联系。影响儿童文学话语形成的“互文本”大致有3类(Stephens 1992: 86-87):第一类包括传统的叙事形式和体裁,如民间故事、传奇、现实主义文学等;第二类包括神话、圣经故事、寓言等;最后一类是各类社会、文化话语。下面是the Mock Turtle向Alice介绍了它所学的课程的情形:
“I couldn’t afford to learn it,” said the Mock Turtle with a sigh. “I only took the regular course.” “What was that?” inquired Alice.
其中,Δθt为第t次训练时参数的更新量,ρ为动量因子,η为初始学习率,gt为初始梯度.本文中,动量因子ρ采用经验值0.9,梯度gt会随ρ而改变,在不同的训练阶段学习率也不同,用以灵活地提升网络训练速度.
“Reeling and Writhing, of course, to begin with,” the Mock Turtle replied,“and then the different branches of Arithmetic-Ambition, Distraction, Uglification, and Derision.”
…
“Well, then,” the Gryphon went on, “if you don’t know what to uglify is, you are a simpleton.”
…
“Well, there was Mystery,” the Mock Turtle replied, counting off the subjects on his flappers, “Mystery, ancient and modern, with Seaography: then Drawling—the Drawling-master was an old congereel, that used to come once a week: he taught us Drawling, Stretching, and Fainting in Coils.”
(Carroll 1994: 114-115)
显然该童话文本植入了一种我们熟知的社会话语类型——课堂话语,如 Reeling,Writhing,Ambition, Seaography等。而这些名称无论对于Alice还是读者都是陌生而奇特的,但又不至于造成无法理解的困扰,因为它们属于课程“语义场”,因而存在着语义上的类属联系。语言的功能之一就是“构筑社会现实”(Fairclough 2001: 269),我们常常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意指”(signify)特定的经验领域,一方面这样的类属联系可以使儿童读者与现实中的课程如阅读、写作、地理等相对应,另一方面又能够刻画这些“海龟”的特征。作者完全可以启用我们所熟知的课程名称,即令其“自然化”(naturalized),但是将一套实质上任意的编码视为自然的编码接受时,我们会变得顺从,缺乏批判力,在没有对意义进行审视的情况下便予以接受(Fowler 1996: 57)。换言之,这种情况下读者所占据的将会是一种相对被动、缺乏批判力的主体位置,而社会化的效果也得以最大化。Carroll对课程名称进行“异化”(defamiliarization),构成对课堂话语的戏仿(parody),使词汇层面上的语言游戏上升为话语类型之间——“互文”——的对话,以这种方式表达对维多利亚时代压制个性发展的教育体制的不满,也为儿童读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具有批判力的主体位置:他们不再受控于篇章,而是在阅读中积极参与文本的构建,获得一种全新的认知体验。此外,其中的儿歌戏仿、动物对法庭文本的模拟等“互话语性”的典型例子,使这部童话成为一种新颖独特的话语。
作为一种叙事文本,必然有叙事视角:全知型叙事、第一人称叙事或聚焦化(focalization)。(Stephens 1992: 56-57)《爱丽斯漫游记》属于第三种类型,事件与情节几乎都是从Alice的视角表征的,Alice成为感知主体,即“聚焦者”。如果读者对聚焦者的体验和态度产生认同感,其主体性就会因此丧失,从而被聚焦者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所淹没。这是对儿童实施社会化的有效策略之一。在《爱丽斯漫游记》中,尽管Alice作为聚焦者见证了Wonderland中形形色色、稀奇古怪的动物,并在很多时候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但是动物们都坚持自己特有的逻辑,不因为Alice的评价而改变。Carroll让Alice充当聚焦者去体验这个世界,却不让她的声音压制其他声音。因此,他的作品便带上了“复调”(polyphony)的色彩,文本编织的不是杂体混声的狂欢世界。儿童读者体验到的不再是说教者的声音,获得的不再是被动的作为社会化对象的主体位置。
上面的分析依据的分析范式,关注的是某特定语篇是以何种方式“占用”话语常规(包括语域、体裁、风格等)以及这种“占用”引发的意识形态效果,结论具有说服力,其分析比简单指出什么地方是“话语常规”或“文化碎片”、“文化语境”等更具有“程序性”或者说“科学性”。时下互文性批评要么是诘屈聱牙的理论思辨,要么是主观判断何为互文性因素的倾向,是否可以参照这样的分析模式加以改善?笔者认为是可能的。
英国18世纪的著名讽刺作家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的散文“A Modest Proposal”流传至今仍脍炙人口。文章从头至尾保持以平静温和的口吻和建议式文体风格表现揭露残酷社会现实的讽刺性主题,这正是互文性文本的典型表现。斯威夫特时代,爱尔兰的天主教佃农遭受着英国地主的残酷压迫,过着赤贫的生活且人口众多,对政府是一个不小的负担。作者在引言中说,“为了避免爱尔兰穷人的孩子不至于成为父母或国家的负担,使他们给大众带来利益”,特提出一个“温和的建议”。而他的建议是,可以将大部分1岁儿童投放市场,包括食用,这样可以给贫穷的佃农母亲们带来收入。当介绍到“一个健康的哺育良好的儿童1岁时是最为可口……,无论是蒸、烧、烤还是煮”时,谁能不毛骨悚然?但是作者所用的语言仍然一样文雅,口吻一样平静,“自始至终文雅得体、有理有据的文体保持不变”(Hollenbeck 2009)。文中叙述者以精确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问题:“我计算,一共有200 000对夫妇,减去其中30 000对有能力养活孩子的夫妇……”,这给读者的印象是,该建议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斯威夫特憎恨当时的道德缺失,却将这样一篇充满对现实刻骨憎恨、对其进行辛辣讽刺和无情攻击的檄文以这样的文风表现出来,正是作者对互文性因素巧妙利用的结果。这样的手法在文学史上并非绝无仅有,英国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先令历险记》(AdventuresofaShilling)以优雅流畅甚至很抒情的文体来辛辣揭露他不喜欢的克伦威尔时代。菲尔丁(Henry Fielding)在其小说《汤姆·琼斯》(OnTheHistoryofTomJones,aFoundling)中用很严肃认真的文体和口吻历数汤姆的三宗罪责以“支持”Mr. Allworthy关于汤姆“生来该杀”的观点,而这“三宗罪”是:偷摘果子、偷农场一只鸭子、从少爷口袋里偷一个球。对于十来岁的孩子这根本不是什么罪恶甚至连错误都说不上,但是作者却用很严肃的文字来叙述,其讽刺效果跃然纸上。显然这里的互文性因素不仅是语言层面的篇章类型的互涉,更是意识形态即文化方式的互涉。分析这样的作品的互文性时,最好从文本本身互文入手,分析不同的文本样式为什么出现在当前文本中、它们以何种方式出现在当前文本中、它们的出现对于解读当前文本具有什么样的意义,等等。最好不让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脱离当前文本的语言互文性而任意地将其断言为互文因素,那是语境研究应该做的事情。如果牵涉到解读过程必需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也要从因互文本的出现而引发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因素进行讨论,会比把任何引起对文本有不同阐释的因素都牵强地归为互文性要科学得多。这样的批评程序可以使“互文性”的本来意义“文本互涉”不至于被淹没。
五、结束语
篇际性研究侧重于篇章内部的语义结构关系和既往篇章的各种形式与当前篇章的关系,探索一篇章形式与其他篇章类型间的关系如何在作者和读者的交际中为交际目标服务,从而欣赏当前篇章的价值,而互文性理论将文本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注重“历史载入篇章和篇章载入历史的过程”。互文性理论讨论的文本间对话多脱离文本形式本身,过于重视社会的、历史的、认知的、文化的百科知识性对话,因此就显得繁杂和缺乏可操作性。互文性理论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它的研究尤其是广义互文性的研究过于虚无所致,必然导致研究方法上的一些问题。既然互文性批评和篇际性研究的目标都是文本,而后者比较注意程序化操作的方法正是前者所欠缺的,那么两者就有融通的空间和互相补益的可能性。应该说明,篇际性的方法对于文学批评传统来说并不一定处处适用,本文作者所提出的一些建议也未必恰当,但我们相信篇际性的程序化研究一定会给互文性批评一些有益的启发,使互文性批评去粗取精、更趋科学化,以便更好地为文学创作、欣赏和评价服务。
Arrive, M. 1972.LeLangagesdeJarry,EssaideSemiotique[M]. Paris: Klincksieck.
Bakhtin, M. 1984.ProblemsofDostoevsky’sPoetic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Barthes, R. 1974.S/Z[M]. New York: Hill and Wang.
Carroll, L. 1994.Alice’AdventuresinWonderland[M]. London & New York: Penguin Books.
Compagnon, A. 2004.Literature,Theory,andCommonSense[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uller, J. 2006.ThePursuitofSigns[M]. London: Routledge.
de Beaugrande, R. & W. Dressler. 1981.IntroductiontoTextLinguistics[M]. London: Longman.
Fairclough, N. 1992.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 2001.LanguageandPower(2ndedition)[M]. London: Longman.
Fowler, R. 1996.LinguisticCritic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enette, G. 1982.Palimpseste[M]. Paris: Seuil.
Halliday, M. A. K. 2005.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Hollenbeck, A. 2009. Literary analysis: A modest proposal, by Jonathan Swift[OL]. [05-07]. http://www.helium.com/items/1441384-style-in-swifts-modest-proposal.
Jenny, L. 1976. La strategie de la forme[J].Poetique27.
Kristeva, J. 1969.Semiotics:ResearchesforaSemioticAnalysis[M]. Paris: Seuil.
Prince, G. 1989.ADictionaryofNarratology[Z].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Riffaterre, M. 1979.LaProductionduTexte[M]. Paris: Seuil.
Stephens, J. 1992.LanguageandIdeologyinChildren’sFiction[M]. London: Longman.
Taxel, J. 1995. Cultural politics and writing for young people[A]. S. Lehr (ed.).BattlingDragons:IssuesandControversyinChildren’sLiterature[C]. Portsmouth: Heinemann.
程锡麟. 1996. 互文性理论概述[J]. 外国文学(1).
丁建新, 许 伊. 2007. 童话叙事中互为话语性的批评性分析——以《爱丽斯漫游记》为例[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
范胜福. 2009. 批评语言学中互文性的描述方法[J].科技信息(6).
佛克马等. 1988. 20世纪文学理论[M].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黄国文. 2004. 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黄念然. 1999. 当代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J]. 外国文学研究(1).
秦海鹰. 2004. 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 外国文学研究(3).
单雪梅. 2009. 从对《死者》的重写看欧茨的创作观[J]. 当代外国文学(2).
王 卓. 2006. “拼图”中诞生的诗歌——梅利尔诗歌《迷失在翻译中》的互文性解读[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
夏延华. 2009. 从迈克·朗利诗歌看互文写作与文学创新[J]. 当代外国文学(1).
夏益群, 蒋天平. 2009. 勃洛克长诗《夜莺园》的互文性和叙事密码解读[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
辛 斌. 2000. 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J]. 外语研究(3).
徐 蕾. 2009. 身体的再现——论拜厄特小说《太阳的影子》中的父亲形象[J].当代外国文学 (1).
I06
A
2095-5723(2013)01-0062-10
(责任编辑 姜 玲)
2013-02-20
通讯地址: 475001 河南省开封市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