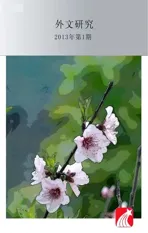重温詹姆逊的“民族的寓言”
2013-03-20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逢振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逢振
重温詹姆逊的“民族的寓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逢振
民族的寓言是美国著名理论家和批评家詹姆逊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但迄今仍有许多人误解。本文通过分析阿赫默德对詹姆逊这一概念的批判,说明它不同于传统的寓言概念,也不同于民族主义;它是一个关于断裂和异质的问题,是梦的多种释义的问题,而不是象征的同质性的再现问题。
詹姆逊;阿赫默德;民族的寓言;第三世界文学
1986年,《社会文本》(SocialText)发表了詹姆逊的文章“跨国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三世界文学”(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正是在这篇文章中,詹姆逊提出了“民族的寓言”(national allegory)这个重要的概念。但是迄今为止,仍有不少人对这个概念缺乏正确理解。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没有抓住这篇文章的本质;许多人只是从通常意义上内容的角度来理解,而实际上这是一篇关于形式内容的文章。
文章发表之后,在美国引起了不少批评:艾贾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詹姆逊的一些支持者也多有抱怨,如克林特·伯恩汉姆(Clint Burnham)和西恩·侯默(Sean Homer)等。但是,这些人似乎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他们都把“民族的寓言”错误地理解为“民族主义的寓言”。出于这种理解,他们认为詹姆逊是说第三世界的作家都是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但这并不是詹姆逊所表达的意思。关于这一点,不妨看看他的《侵略的寓言》(FablesofAggression:WyndhamLewis,theModernistasFascist);在那本书中,他清晰地概括了他的“民族的寓言”理论。
在“詹姆逊的他者性修辞和‘民族的寓言’”(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中,艾贾兹·阿赫默德愤怒地批判詹姆逊,并且矛头不仅指向詹姆逊一人,还把爱德华·萨伊德也捎带了进去,仿佛整个后殖民研究领域都存在问题。在阿赫默德的批判中,至少有3点需要反驳:第三世界并不存在;民族的寓言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第三世界有许多文学作品不是民族的寓言。
阿赫默德关于不存在第三世界的指责,在他的文章中似乎谈得最充分。他分两部分从两方面论述。一开始,他有一种精神上的愤怒,或者说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好像詹姆逊背叛了他;因为,他写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向认为我们——詹姆逊和我——属于同类,尽管我们不在一起工作。但是,当我读到他的文章的第5页时(特别是那句“我认为,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必然是寓言的……”),我意识到他所进行的理论阐述,除了其他东西之外就是我自己”(Ahmad 1987: 65)。对阿赫默德来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人我长期以来非常喜欢,虽然相距遥远,一直视为同志,而他自己却认为他是我的文明化的他者”(Ahmad 1987: 66)。这一指责颇有意思的是,当阿赫默德指责詹姆逊坚持的3个世界理论时,他自己却继续否认它的前提。如果第三世界的概念对他没有意义,如果它确实不存在,那么他自己又何必认同于第三世界?同理,如果他自己不是詹姆逊的文明的他者,那又何必不遗余力再去证明呢?换句话说,如果第三世界这个术语并不要求阿赫默德是其中一员,与他并不相干,那么他个人就不可能接受它,而他的否认必然属于一种不同的、更客观的类型。就此而言,他否认第三世界存在的意图不攻自破,因为这等于否认了他所依赖的东西,即他自己来自第三世界,因而说话具有权威性。
事实上,尽管阿赫默德声言第三世界并不存在,但他这么说本身就等于同意了詹姆逊的观点——也许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单凭经验否认第三世界的概念,但在这个语境中那是徒劳的,因为詹姆逊并不认为他所说的第三世界是最初阐述的3个世界中的第三世界。正如桑地亚戈·考拉斯(Colas 1992: 258)所指出的:詹姆逊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段,即后现代主义,取消第三世界是他用以证明这种看法的主要标志之一。当然,第三世界是否曾经存在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它现在显然已不复存在。其实,当詹姆逊说他是以本质的描述方式使用第三世界这个术语时,他实际上已经表明第三世界本身不再存在,他已经有效地汲取了原始的内容,把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空洞的能指符号。换句话说,他的意思是这个术语还不能作为一个充分形成的概念,它仍然处于纯粹的指称和更确定的概念之间。
但是,阿赫默德在他的结论中认为,即使他“接受詹姆逊对全球分为3个世界的划分”,他仍然要坚持“在第一世界的全球后现代主义的内部”也存在“一个真正的第三世界,或许两三个第三世界”(Ahmad 1987: 24-25)。显然他的含义是,詹姆逊认为第一世界是一个“幸福的地方”,那里不存在财富和条件的差别。这当然是对詹姆逊的误解,因为詹姆逊多次明确阐述过,晚期资本主义的特点就是它的不平衡性。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不断以副产品的形式制造出第三世界,因此它越是发展,造成的第三世界就越多,直到最后第三世界失去所有的地理特定性,变成一个有些像是表示新阶级的术语。
虽然詹姆逊没有提出一个总的第三世界文学的理论——因为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太大,很难归纳到一个单一的范畴——但他并不赞成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可选择的立场。在他看来,不论各个民族的文化多么不同,它们都不是独立自治的,“它们在与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的生死斗争中都遭到封锁——这种文化斗争本身反映了那些地区的经济境遇,这些地区在不同的资本阶段,或者有时委婉地说成现代化的不同阶段,都受到经济渗透”(Jameson 1986: 68)。詹姆逊拒绝多元主义,因为如果不拒绝,就等于说某些第三世界民族的悲惨命运不是第一世界国家的自私行为造成的。
关于民族的寓言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詹姆逊在他的文章中根本没有说第三世界的作家都是民族主义者,或者只能是民族主义者,虽然他确实说第三世界的作家执着地关心“民族境遇”。民族境遇不等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只是民族境遇这一庞大而复杂的问题的组成部分。因此,应该说这一点是阿赫默德的错误理解,或者说他故意把詹姆逊的文章中并不存在的一种立场和观点强加给了詹姆逊,因为他不顾文章多层次的分析辩证,跳过民族境遇以及相关的问题,简单地把民族的寓言等同于民族主义,声称詹姆逊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唯一理想的意识形态。其实,按照詹姆逊的阐述,民族的寓言并不是对这一问题本身的思考,而是把它用于解决更普遍的再现问题的方法。换句话说,詹姆逊的文章更多的是论述文学历史,而不是政治历史。
詹姆逊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非殖民化时期,第三世界的作家面临的政治问题,本身在文学形式方面就是“封闭的叙事”(Jameson 1986: 76)问题。知识分子明白,在这个时期,艰难赢得的民族独立并不一定会结束暴力、贫穷或者与殖民统治相关的属下性。正如历史记载所表明,在争取独立中形成的人为的团结,在独立后又发生分裂,甚至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内战。这意味着虽然外国侵略者不复存在,但国家内部却发生了政治分歧——有些可能过于激进,有些可能过于保守,有些则可能过于反动。“因此,在受到伤害的独立之后,激进的非洲作家,如乌斯曼或者肯尼亚的恩古吉,发现他们自己又陷入鲁迅那样的困境,他们对改革和更新社会充满激情,但尚未找到变革和更新的力量。我希望人们明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学的困境,一种再现的双刃剑:不难辨识说另一种语言、带有明显殖民占领标志的敌人;但如果那些人被自己的人取代,与外部控制力量的联系就非常难以再现。”(Jameson 1986: 81)这就是说,从文学的、历史的视角看,每一种政治境遇都应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美学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则可能甚少。
其实,阿赫默德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替代民族主义的东西,他只是提出一个模糊的“非民族主义”的范畴,在他看来与反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相对的只是“其他的东西”。如果说詹姆逊确实赋予民族主义以特殊的地位,那么阿赫默德并没有提出具体的理由说明他是错误的。实际上,阿赫默德不仅很少注意“民族的”的含义,而且更少注意“寓言”的含义。至少可以说阿赫默德的“寓言”概念非常奇怪,因为詹姆逊称之为寓言的文本,他认为是关于那些假定被寓言化了的东西。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他提供的关于并非所有第三世界作品都是民族的寓言的证据:
从1935年到1947年,在这一走向非殖民化的关键岁月里,我想不出任何一部乌尔都小说是以直接的方式或完全是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据我所知,所有那个时期的小说主要都是描写其他的东西:封建地主的残暴,充满宗教“神秘”的房屋里的奸杀,放贷者对农民和下等小资产阶级的压榨盘剥,女学生面对的社会和性的挫折,等等。反对殖民主义的主题交织在许多这样的小说里,但从来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重点。(Ahmad 1987: 21)
如果采取辩证的态度,阿赫默德肯定可以把这些“其他的东西”转换到它们的对立面,甚至“女学生面对的社会和性的挫折”也可以从更大的社会历史基础方面来理解,例如作为后殖民批评的一个转义,表示这种性的挫折源于传统社会,只是由于世俗化的资本主义的渗透,在传统本身遇到危机的时刻写进了文学。但是,如果只是把寓言化的事物作为寓言,显然是对寓言狭隘的甚至错误的理解。因为,倘若像阿赫默德那样把寓言化的事物作为寓言,那么他可能会认为鲁迅的《阿Q正传》只是描写了一个具体的人物,没有任何寓言的批判作用。如此,詹姆逊所列举的民族寓言的例子,都不是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验,而是关于“其他的东西”。然而,如果不像詹姆逊那样把鲁迅的作品读作民族的寓言,显然就很难理解鲁迅作品的真正意义。詹姆逊讨论了鲁迅的3部作品:《狂人日记》写同族相残或疯狂,或两者兼而有之;《药》写20世纪初中国传统医生中庸医泛滥;《阿Q正传》写一个“苦力”的日常生活——如果对这些作品只是就事论事,而不是把作品作为寓言解读,显然不是鲁迅试图表达的社会意义。同样,乌兹曼的小说《扎拉》(Xala)虽然没有明显地描写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历,但如果不考虑它的社会背景,那就不可能理解主人公所处的困境。
当然,詹姆逊这里所用的寓言概念与传统的概念不同,但正如他所说,没有任何理由一定要与传统的概念相同。“如果寓言对今天的我们再次成为适宜的,与现代主义的象征主义或甚至现实主义本身那种庞大的、里程碑式的联合对立,那是因为寓言精神的深刻的不连续性,是一个断裂和异质的问题,是多种梦的释义的问题,而不是象征的同质的再现问题”。(Jameson 1986: 73)这里有一个更深刻的论点,就是说,它涉及整个后殖民批评,因为不论阿赫默德是否喜欢,后殖民批评也依赖詹姆逊所用的那种阅读策略,它的力量源于有说服力的再阅读方式,即把西方经典的偶像解读为种族主义和权力不平等的寓言。如果坚持阿赫默德那种生硬的寓言概念,那么人们可以说《曼斯菲尔德庄园》并不像爱德华·萨伊德所说的那样是关于奴隶的,而是关于一个年轻姑娘的社会和性的挫折。甚至说是关于她的性挫折也有些勉强,因为作品并没有明确提到这一点,而是读出来的。实际上,今天人们从后殖民批评或女性批评来阅读这部作品,都是把它作为寓言来解释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詹姆逊的观点,我们不妨再回到他的文章本身,考虑一下他写文章时的背景。虽然文章是纪念罗伯特·C·艾略特的演讲,但其意义决不只是为了纪念。应该说,文章是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整个人文学科语境的一种反映。当时人文学科面临着一种身份危机,起因是究竟什么构成人文学科研究的客体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所有旧的文本都强行纳入该研究领域,恐怕会毁掉人文学科本身。当然,这场危机因后结构主义而日渐激化。詹姆逊自然也参与了争论,他认为,限定人文学科的不是它研究的对象,而是对它们研究的方式,因此不应该在其构成上限制可以或应该研究的东西。而对人文学科经典的反复肯定,基本上是反对动摇它的基石的,也就是反对动摇伟大的经典作品作为研究客体的地位。
詹姆逊的策略是,如果经典除了自称具有全球观点还想有所作为,那它就应该力求融合世界各地的文学,而不是排除第三世界。也许这可以看作是詹姆逊对一些保守批评家的回应,例如他在文章中提到的威廉·本内特——本内特排除了一切印度、非洲、中国和拉丁美洲的作品,声称它们不是伟大传统的组成部分,虽然他自称一直在研究世界文学。詹姆逊认为,阅读、讨论和思考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可以带来某种新的感受和启发。
其实,即使把詹姆逊的文章置于纪念艾略特的语境,同样也有助于对文章的理解。艾略特以讽刺和乌托邦作品著称,对詹姆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詹姆逊论科幻小说的文章中尤其明显。在詹姆逊看来,科幻小说继承了现代主义,并直接关系到他在民族寓言部分对第三世界的定义。他指出,非常有意思的是,促动第一世界科幻小说的东西,恰恰是阻碍第一世界读者阅读第三世界小说的东西:对他者的恐惧(人口众多)和对自己当前生活方式的迷恋(反对乌托邦政治)(Jameson 1975: 221-230)。詹姆逊对科幻小说和乌托邦倍感兴趣,因为他觉得随着现代主义的结束政治小说也正在灭亡。
在谈过阿赫默德对詹姆逊的指责以及他的文章背景之后,自然我们应该回到詹姆逊的文章本身,特别是他的总括性的前提:“所有第三世界的作品都必然是民族的寓言” (Jameson 1986: 69)。由于他在文章中没有明确解释“民族的寓言”是什么意思,我们需要回到他更早的作品《侵略的寓言》来寻求答案。在这部作品中,詹姆逊所说的民族的寓言指的是对一种更普遍的问题的特殊的解决方法,而这种普遍的问题就是封闭的问题。按照詹姆逊的看法,每一个作家都有两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如何开始和如何结束。自从现实主义的模式被破坏之后,这两个问题就变得非常尖锐,因为一度支配叙事构成的严格的规则被颠覆了,作家只能从一些碎片创造他们的参照系。早期的“史诗”作家,例如司各特,拥有一个现成的史诗结构的安全的模式,他们可以在这种模式中或多或少地随意加入各种不同的历史素材,只需按照公式注意开始和结束的问题;然而当代史诗作家,例如詹姆斯·乔伊斯,不得不诉诸更平凡的方式。根据詹姆逊的解读,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诉诸一种寓言的结构,因为他构成句子的方式(即详细记录内心的日常生活)意味着没有特定的或合乎逻辑的封闭形式。若无史诗寓言的奇想,乔伊斯强加的任何封闭形式都将是难以容忍地随意性的。乔伊斯小说中的引喻与《侵略的寓言》中所说的刘易斯的民族寓言,可谓是解决同一问题的不同方法。
关于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从詹姆逊的著作中援引另一个例子。他在论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文章中写道:“在史蒂文斯的作品中,地名同时也是产生意象的所在和场所:类似福楼拜的巴伐利兹莫,关于异域的白日梦,对爪哇、特恩特派克、基威斯特、奥克拉荷马、田纳西、于卡坦、卡莱罗纳等地方的联想——以及语言本身另一层面的系统性的形成(由彼此关联生成的地名,对它们的联想现在作为证明者的词语领域,其背后掩盖着一个活跃的更深层的系统)”(Jameson 1984: 14)。这个更深层的系统就是第三世界的异域情调。不过这里并不是要指责他的东方主义,而是说明在什么程度上第三世界的异域情调是作品结构上的需要。按照詹姆逊的理解,在史蒂文斯的作品中,所谓第三世界的素材(例如爪哇等地)不仅仅是某个不曾到那里旅游的个人的幻想,而且此人还渴望变化。其实,这也是作品达到封闭的一种方式。(Jameson 1984: 15)同样,兰波那种令人产生幻觉的关于非洲和远东的描写,也是结构的需要,其目的也是为了达到封闭的效果。简单说,在史蒂文斯的作品中,那种可能陷入枯燥的现实主义的日常意象通过与他者的并置而增加了新意,“爪哇茶”对于消费社会的读者比“茶”更有吸引力(Jameson 1986: 71)。显然,在詹姆逊看来,这同样是形式问题而非内容问题。
当然,人们可以从批评家而不是作家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事实上,詹姆逊在《侵略的寓言》中就是这么做的。所有的批评家都会看到,在伟大作家的风格创新和最终构成的叙事客体之间,存在着某种断裂或不连续性。对于这种断裂,不同学派的不同批评家有着不同的论述。詹姆逊认为,若要“把这种断裂理解为我们文化中的一个客观事实……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把风格和叙事之间的鸿沟历史化,它可以看作是形式历史中的一个事件”(Jameson 1979: 7)。从历史辩证的视角看,他的说法很正常,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利用了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著作进行论述。他提出,风格可以理解为等同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分子概念,而叙事可以理解为克分子。无疑这里两个术语都要从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在他所用的语境中意思是排空它们特定的内容而考虑它们的形式。
确切地说,詹姆逊用分子的概念指句子的生产“本身被作为一种象征行为,一种在词语的层面上揭示或打开窗口的实践”(Jameson 1979: 8)。詹姆逊的论点是,句子不是现成的,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需要一种特殊类型的机器才能运转。通常这要采取一种障碍或禁忌的形式(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言,机器只有停止和不断停止才能工作),例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为了表现内心世界而自我强加的规则(Jameson 1979: 81)。然而一旦运转起来,它就变成了一种无限性,一种不可穷尽的力量,一种无法停止的生产;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话说,它就像是欲望本身那样,为了意义的存在不可能受到足够的阻碍,除非有某种抵消它的力量发生作用——这就是把叙事作为克分子来理解的情形。而正是某种上层建筑的形式,通过创造一种确定的、然而是活动的界限,使句子的生产达到某种封闭状态。这里需要抓住的关键是,纯粹的句子生产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分裂,一种个人的疯狂,没有任何其他读者可以充分参与其中。克分子机器所做的是发明一种工具——詹姆逊称之为“里比多机制”——它在集体层面上运作,使其他读者能够“投入”文本;这也就是说,无论一个文本看上去多么像是“个人的”,也总是有一个集体的或公共的层面,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它先在的客观结构,即句子生产用以创造封闭而挪用的那种模式。
实际上,詹姆逊从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大三元结构(分子、克分子和飞行路线)中汲取了两部分,故意无视其中飞行路线的概念,从而形成自己的二元论,把两部分协调成一种新的分析方法,以辩证的方式思考风格和叙事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用法中,分子层面表示此时此地的直接观察或局部欲望,单个句子的生产时间,个人的词或个人的笔触的电波冲击,局部的痛苦或快乐的震颤,突然的迷恋、集中发泄、幻想,或者对弗洛伊德的非集中发泄的同样直接的压制。对这种微观的、碎片的、直接的心理生活,在克分子中有一种对抗的力量(大量的分子从克分子构成更大的有机统一体),它表示所有那些大的、抽象的、中介的、甚至可能是空洞的和想象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我们寻求重新容纳分子:个人身份连续性的幻觉,心理或个性有组织的统一,社会本身的观念,以及艺术作品有机统一的概念。(Jameson 1979: 8)
实际上,詹姆逊对每一个文本的解读都提出两个不可分开的问题:促动句子生产过程的分子机器的真正性质是什么?导致句子生产达到封闭,使我们可以阅读的那种克分子机器的真正性质是什么?但是,由于克分子还不是“里比多机制”,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詹姆逊的辩证方法。
辩证阅读的目的就是要抓住风格和叙事之间断裂的特殊性质,把这种断裂作为形式历史的一个事件。“福楼拜的名字对这种发展是一个有用的标志,在这种发展中,叙事文本的两个层面开始分开,并获得它们自己相对的独立自治;其中叙事语言在修辞和方法上服从于叙事再现的情况再不是想当然的事情”。(Jameson 1979: 8)在这种意义上,刘易斯的作品继续与支配福楼拜的形式问题进行搏斗,但他们也有明显的不同,刘易斯无法追随福楼拜,不可能继续选择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现实主义风格——除非不惜在风格上严重地倒退。因此,刘易斯被迫沿着詹姆逊所说的那种无情节的艺术小说的方向,不断地进行他的风格实验,为了达到艺术的丰富和创新,甘愿冒根本不可阅读的危险。实际上,几乎所有现代主义者都有类似的情况:为了追求创新,他们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造成了不可读性。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需要一种更强的叙事遏制形式而不只是人物,从而使某种类型的句子生产能够投入,甚至有些像精神病似的喋喋不休。所谓更强的形式是指它独立于句子生产过程,虽然这种结构或“里比多机制”通过夸大的风格压力而被迫发生作用,但它仍然像显微镜的镜头那样,使我们能够看到一杯水所包含的大量细菌,而不是成为任何反馈的部分。换句话说,“里比多机制”可以看作是文本的透镜,通过它使文本变得可见。
在刘易斯的作品中,这是民族扮演的角色——他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的民族—国家体制用做他的透镜。为了不使内容影响聚焦,最好锁定于詹姆逊所说的民族的寓言,从作用方面进行探讨。在刘易斯的实例中,詹姆逊自己的方法是:在刘易斯的作品中,民族是一个先在的客观构成,其作用类似于弗洛伊德解释无意识时所说的地志学概念:“弗洛伊德的模式不仅是寓言,而且可以表明它们为了修辞比喻的表达,要依赖精制的、先在的、城市地志的再现以及政治的国家的力量。这种城市的和市民的‘机制’——常常泛指弗洛伊德的‘隐喻’——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再现的客观前提,因此也与无意识本身的真正‘发现’一致,它现在可以看作已经预设了维多利亚后期城市的客观的发展——工业化,社会阶层形成和阶级两极分化,复杂的劳动分工”(Jameson 1979: 96)。这种弗洛伊德分析的价值,依赖于或至少部分地依赖于我们自己对城市的理解,依赖于我们自己今天的经验。德勒兹和瓜塔里更进一步,他们说弗洛伊德的主要错误是把城市仅仅作为一个隐喻,作为一个地图而不是集中居住的地方。詹姆逊对这个问题更明智一些,他具体说明了刘易斯的模式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法,因为美学的困境仍在继续,甚至不可能解决。
所谓美学的困境是指风格和叙事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风格迅速进化,另一方面种种可能的叙事结构相对滞后。不过,这种差距并不只是美学的,它还反映了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心理本身的碎片化,詹姆逊认为这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传统生活方式在多方面的恶化,尽管最终可能是进步的。第一个受伤害的是19世纪现实主义的设想,至少在美学领域是如此。现实主义设想“源于内部的民族经验是相对可理解的和自足的,它内聚于它的社会生活,对其个体公民命运的叙事可以期望达到形式的完美”(Jameson 1979: 94)。这种可理解性消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帝国主义。詹姆逊认为,帝国主义与现代主义是携手前进的,它们相互影响并相互决定,不仅有局部的、特殊的方式,而且也有普遍化的方式。特别是,帝国主义造成某种“意义的消失”,因为宗主国的主体由于资本转移到殖民地而使他们不可能把握整个境遇。不论多么放大个人经验,也不论多么强化自我审视,都不可能弥补殖民生活的神秘影响,它封闭在遥远的地方和[大部分是]无法到达的国土(Jameson 1988: 11)。
对于宗主国的主体,在日常生活的困惑中总有某种失去的东西。这里也许可以把詹姆逊的看法颠倒过来加以延伸。我们知道,帝国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殖民化的城市与宗主国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虽然它们的实际经验及其价值观完全不同。然而,不论在孟买还是都柏林,不论在新加坡还是悉尼,由于帝国主义固有的时空差距,那里个人主体的经验都有与宗主国的人相似的地方,这就是:他们都无法把握自己的整体境遇。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都缺少自我统治的能力:由于受不在场的统治者的统治,被殖民的人们很少能看到掌握他们生活和生命的人。如果这种情况“作为艺术的内容,总会有某种东西缺失,然而在缺失的意义上,如果只是把缺失成分补上去,它永远不可能恢复或构成一个整体:它的缺失可以比作另一个维度,像一个镜子另一面的外部,它在结构上就缺失,不可能弥补或弄好”(Jameson 1988: 12)。在詹姆逊看来,这正是现代主义本身的构成性问题。实际上,他甚至认为,“只有那种以反思的方式观察这一问题并经历这种形式困境的新的艺术,才能首先被称作现代主义”(Jameson 1988: 12)。
综上所述,民族的寓言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形式方面的努力,它力图架起一座跨越鸿沟的桥梁,鸿沟的一边是一个既定的民族—国家内部日常生活实在的记录,另一边是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实质上是跨国范围内结构性的发展趋势”(Jameson 1979: 94)。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詹姆逊对今天世界各地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所处境遇的判断。但这种境遇是复杂的,因为今天在全球化的压力之下,民族—国家面临着消失的可能,或者说去领土化与无国界的经济。因此,对于民族的构成及其有效性的质疑,必然扩展到包括与它相关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问题。当前,多种情况表明,民族作为社会构成正在迅速被一种想象的全球国家概念的趋势所取代。哈特和奈格里把这种想象的全球国家称之为“帝国”,这种说法虽然生动,但并不一定正确。这种情况也许应该说是[后]民族—国家的境遇,但不是因为民族—国家并未消失,而是因为它们自然的合法性时期已经过去。
如果民族—国家的政治重要性确实因全球化正在衰微,那么也许可以认为民族的寓言也随之消失。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如果民族—国家的概念不再要求自然的合法性,那么它也就不再成为争论的基础。哈特和奈格里用“民众”的概念来表示民族—国家的衰微,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民众尚未出现。民众的运动性是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乐观主义的基础,但它最终实现只能是民族—国家终结之后的事情。从这种乌托邦的观点出发,任何试图恢复民族—国家利益的努力都会被视为反动的;但在当前的历史阶段,这无疑是令人怀疑和需要讨论的问题。不过,民族—国家衰微的趋势确实是存在的,甚至日益明显;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20个大国为解决危机的共同努力,都说明了这种趋势。当沉思民族—国家终结之后的未来时,面对这一巨大问题的思想难免不令人颤抖,因而不可能不回到已知的过去。这不仅是一个怀旧的问题,而是想象的失败。就此而言,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或假想: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越是变得脆弱,在文化上越是坚定地回归已有的传统。
Ahmad, A. 1987. Jameson’s rhetoric of otherness and the “national allegory”[J].SocialText17.
Colas, S. 1992. The third world in Jameson’s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J].SocialText31/32.
Jameson, F. 1975. World-reduction in Le Guin: The emergence of utopian narrative[J].ScienceFictionStudies2/3.
Jameson, F. 1979.FablesofAggression:WyndhamLewis,theModernistasFascis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Jameson, F. 1984. Flaubert and postmodernism[A]. N. Schor & H. Majewski (eds.).FlaubertandPostmodernism[C].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Jameson, F. 1986.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ism[J].SocialText15.
Jameson, F. 1988.ModernismandImperialism[M]. Derry: Field Day Theatre Co.
I712
A
2095-5723(2013)01-0034-07
(责任编辑 李巧慧)
2013-02-05
通讯地址: 100732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