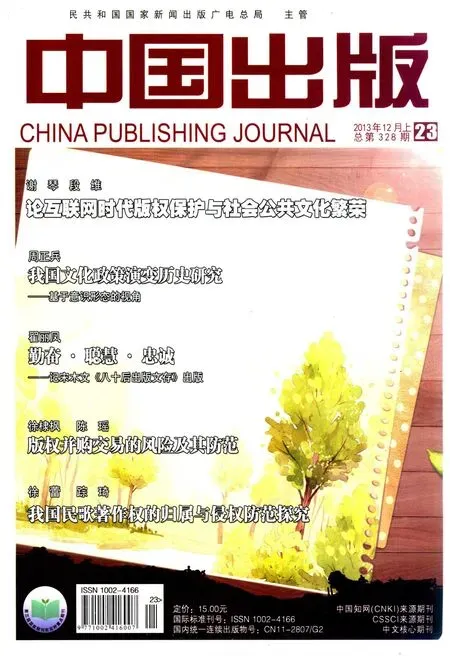勤奋·聪慧·忠诚——记宋木文《八十后出版文存》出版
2013-01-30翟丽凤
文/翟丽凤
宋木文新著《八十后出版文存》(商务印书馆2013年9月出版),收文75 篇,大都是作者进入80高龄后写出的,故以《八十后出版文存》(以下简称《文存》)命名。我目睹并参与这部著作的写作编选过程,颇有感触,深得教益。
心甘情愿为《文存》打杂
我同宋木文相识于1979年,同在一个机关工作30 多年,彼此比较了解。2009年8月,我俩结婚后,相互了解也更深了。他每天要看10 多种报刊,对感兴趣的书籍也细心阅读,有时还要写点读后感。他的勤奋学习、善于思考、笔耕不辍的精神,深深地感动着我。他从原新闻出版署署长岗位退下已经20年,在80 高龄之后,还心系国家新闻出版事业,为反思历史和面对现实而用心撰稿。他的文章内容平实而深刻,简约而丰富,没有空话套话,以自己的语言分析和探讨问题,凸显其为人做事的风格和特点。
2010年3月,宋木文和我商量,想把2007年4月以后发表的文稿整理编选出来(即《亲历出版三十年——新时期出版纪事与思考》未收文稿),以便于考虑是否可以送去出版。我当即表示赞成和支持。那时他写的文稿,都由我打字,以电子版发给报刊社。我就表示,你整理文稿,我帮你打字吧!
当时我还在新闻出版总署版权管理司巡视员岗位上,主要利用午休和业余时间,为他的文稿打字、校对、查阅资料,有时还请司里年轻同志帮忙。这部约40 余万字的书稿,除节假日家里儿孙齐上阵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打印编排大都是由我完成的。我周六、周日不休息,有时要干到晚上九十点钟,真有些头昏脑涨。宋木文对新写文稿和新增题记,常有增补,反复修改,我不免心烦。可看到他整天坐着写,腰疼了就上医院理疗;有时早晨4 点钟就起床,提笔记下脑海中浮现的灵感和词句,我终于心甘情愿地干起来,并从中还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幸福。
2011年10月,我们将分类编排的全部文稿,以电子版和纸质打印稿,送商务印书馆。样稿排印出来后,我帮他校对了两遍,他又请老朋友吴道弘(人民出版社资深编审)通读校正了大部分文稿。2013年2~3月,我们在海南岛三亚、海口期间,还在责编郑殿华寄来的三校稿上作了认真的校订,用特快专递寄回北京。2013年6月底,付印前,宋木文又阅读了部分文稿(主要是新增文稿及照片安排和说明),并感谢责编和有关同志严格把关。
今天看到这部内容丰富、装帧厚重的《文存》,我感到,这是宋木文继《亲历出版三十年》之后,又一部有历史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力作,不禁为我能为这本书“打杂”而油然欣喜。
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宋木文有些文章,在报刊发表时,我曾阅读过。这次通过对文稿的打字、校对,我感受到《文存》虽多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回顾历史,而作者内心却深含着对现实的思考。从他在各篇文章之前精心写出的题记中,可以看出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胡乔木在大转折年代的理论贡献》一文,是为补正吴江的两条重要史料而写的,而论证的实质是“文革”后关于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是与非,及其重大意义。宋木文很重视这篇文章,收入《文存》时,写了长篇题记,又多次修改,交出版社后又作了两次增补。一次是在得知吴江逝世之后,回顾吴江主持的《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他思想转变的重要影响,强调吴江的“治学之路和曲折人生,具有启迪意义,是值得给予重视和研究的”。一次是在阅读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吴江别集》之后,对吴江近年所作《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等文作了肯定性评价,说他“深为吴江同志力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观察、论述一些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说服力所吸引”。我对这样的理论问题认识不深。他对我解释说,肯定吴江的《慎言“民主的普世价值”》是有现实针对性的。同时也表明,他与吴江虽有争论,但不存成见,不以人划线,该肯定的就应当肯定。这时我才注意到,凡报刊发表关于“普世价值”的讨论文章,他都认真阅读,有的还剪下来留存。2013年7月19日,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蒋建国为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征求部分老同志意见座谈会上,宋木文在发言之后,同与会的杨牧之在会议通知的背页上,用笔就“普世价值”问题交换意见,他写道,“有没有普世价值的争论,已经不在于其本身的是与非,而在于以其理论观点达到某种对现实的主张。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杨牧之就回应,“确实如此。这个问题的背景太深了”。宋木文给我看过后,还解释了几句。这张通知上,因记有他俩关于普世价值问题交流思想的手迹,就至今还同他在这次座谈会的发言提纲《我的一点看法》一并保存着。过了几天,我又听到他同来家商谈口述出版史的一位青年同志谈“普世价值”,说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是多元的,而其主导思想又必须是一元的,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统领,不能让以“普世价值”名义出现的西方民主政治那一套,占领我们的舆论阵地。我在一旁听着,感到他说得非常认真,接着又高声地说,要警惕思想理论政治上的改旗易帜;如果丧失警惕,就有可能出现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政治后果。宋木文的这番话,给我很深的印象。
此外,《文存》中的多篇文章及其题记,都有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建言。
以下是作者在《文存》中的一些论述。
肯定弘扬是指对多元开放条件下各种积极意识形态的肯定弘扬。在多元化社会思潮、文化、价值观中,有许多正确、积极、进步的因素,如多元化社会思潮中的爱国主义思潮、改革开放思潮、社会主义思潮;多元化价值观中的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观等。对于这些积极进步的因素,高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必须要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弘扬,引导大学生认同和接受这些积极进步的因素,树立起正确的义利观、奉献观和价值观,科学理解和认识人生的价值意义,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根本利益与暂时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
①他在新闻出版总署纪念建党88 周年大会上,以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身份发表感言,联系实际谈体会,说走改革开放前的老路,或者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都不行,并且高声表示,要把坚持理想信念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愿同大家一起共庆建党90 周年、100 周年,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反响。(第556-559页)
②他以魂要附体、强魂健体,畅谈学习和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的体会,并论述编辑在强魂健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第568-578页)
③他以由一个部门和系统实现建设出版强国目标存在诸多困难,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之前即提出建议,“如果由更高层级统一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各个方面军同心协力去做,岂不是更好”。(第571-574页)
④他在致王蒙信中畅谈读《中国天机》的感受,说从中读出了“中国从昨天走过来取得胜利,中国从今天走下去取得新的胜利,全在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是否正确,全在党与人民群众能否保持密切联系,全在党在历史转折关头能否与时俱进”,建议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一读王蒙这部新著。(第426-435页)
⑤他致信中央领导同志并中编办,建议不宜采纳有人提出建立“三合一”的大文化部体制,并提出新闻出版与广电机构设置的意见,在得知决定组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之后,又建议“从法制建设到监管实践进行多方面整合,逐步建立和完善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大传媒监管体系,推动各种媒体在新的条件下自主互动协调发展”;并表示“这是个系统工程,要经历内外调整、重新组合和融合的过程。合并已在上头开始,整合更需要全方位推进。但依其主客观条件,前景定会看好”。(第139-151页)
⑥他为陈昕新著《中国图书定价制度研究》作序,呼吁以书价破题促改革,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导向往往比文化的导向更强大”,要更加重视用高质量高品位主旋律精品力作占领图书市场,要有更强势的舆论导向。(第386-394页)
⑦他谈《中国文库·新中国60年特辑》出版的启示,呼吁要“高度关注出版的文化担当和政治责任”,指出对那种以钱为本、将写作和出版都纳入资本市场的高调鼓吹,要保持高度警惕。(第356-360页)
这一切都表明,宋木文心系党的理想和信念,心系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治久安,心系新闻出版事业的繁荣发展。
交友、处事有真情
我很仔细阅读《文存》最后两组文章,即:“思念故人”和“生活·信念·友情”。前者是他用心书写的对老领导、老朋友、老同事的思念,他说此次为编稿集中重读,“有一种回归历史和倾心交谈的感觉”;后者是他“历经八十多年风雨之人的政治信念、生活态度、处事原则、交友之道的真实书写”。
我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宋木文与刘杲。我来出版局工作时,就知道宋木文与刘杲关系密切,工作中相互支持,30 多年来一直这样,但我的了解只是一些表面,并不知道其中的深意与深情。近几年来,由于宋木文不会使用电脑,刘杲与宋木文之间就通过我的信箱交换信息和意见(对刘杲发来的信息和意见,宋木文称之为“特供”),使我对他俩的关系与所关心的问题有了深一层了解。2011年5月27日是刘杲80 大寿。杨牧之代表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桂晓风代表中国编辑学会,先后举行三次活动,宋木文都出席,并作发言。《文存》中以《我与刘杲的共事与友情》收了这三次发言。他在题记中说,“在发言中评价了刘杲的成就和贡献,而贯穿其中的主线是我同刘杲长期保持的同事加朋友、原则加友情的关系。这是我一直珍视和维护的”。这样说是有根据的。一是时间长,从1972年以后就一直在一个机关工作,从一线退下来后又在各自的岗位上相互支持;二是经受了职位调整的考验,1975年前后在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刘为正宋为副,在以后更长时间里是宋在前刘在后,但都能做到相互理解与支持,对后来人们在评论由宋木文担任主要领导职务那个时段的工作时常会将宋刘的名字并提,宋木文不仅表示非常赞成,而且总是强调刘杲“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也最多最有力”;三是在国家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时,或者在思想文化战线出现大的调整与变动时,无论对国家总的形势,还是对具体的重大方针政策,他俩都能保持高度一致,彼此还起着互助互补的作用。宋木文对刘杲的评价,也实实在在,“在出版界,一个人兼有出版管理与立法、版权管理与立法、编辑出版理论建设三个方面的贡献,是很难得也不多见的”。宋木文的确非常珍视友情,对随文配发的两张亲密交谈照片,还用心写了说明,“在刘杲八秩寿喜宴上。瞧,咱俩有说不完的话”!吸引我看了又看。
宋木文与潘国彦。宋木文说他同潘国彦有30 多年共事经历,相互了解与知心。我看他是爱潘国彦博览群书,勤于写作之能之才。潘国彦申报副编审职称,宋木文提议破格评为编审,得到评委会一致通过。《文存》中收了一篇《思念“捉刀者”——忆无私撰稿人潘国彦》,如实公布为精装珍藏版《万寿大典》所写之序,系出自潘国彦之手。在长篇题记中又说明曾错用“捉刀”典故,在讲了自我发现又经专家指正后,动情地说出他的心境,“近年来回忆往事,常常使我感悟到友情的珍贵。人的一生,要多交一些朋友为好。以诚相待,可以增添友情;心怀坦荡,必会相遇知己。多为朋友着想、做事,不求回报,但求理解与知心,这样才能活得安心与顺心”。我目睹了这件事的全过程甚至其中的细节,我以为,这真实地体现了宋木文的交友之道与处事原则。
宋木文与石宗源。尽管他们直接接触时间不长也不算多,但他们却结下了深厚的友情。2013年3月28日传来石宗源在北京逝世的噩耗时,我们正在海口,随即停止原来安排,以他和我的名义向治丧办发去唁电,接着他写我打字,晚上8 时,就以电子版发出情意真切的《宗源人品永存》的悼文,在第二天向石宗源遗体告别之日发表在《中国新闻出版报》上。此文收入《文存》时,将近日翻出的2009年11月11日,为感谢宗源从贵州送来心脑保健药品和报告近期个人状况所写的信补入题记,“我从媒体感受到,您通过处理平时工作和突发事件掌控着贵州发展的大局。我以小翟和我的名义向您致敬,并祝愿贵州在您的任上有更好的发展,造福于人民”。他说他想不到宗源竟提前离开贵州,便发出“好人并非都是一路平安”的感叹。为此文配发的一张三人照,他亲自写出说明,“2012年(壬辰年)迎春时节同宗源亲密合影(右为翟丽凤)”。
最后,我还想说的是:宋木文对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忠诚的。他的勤奋、聪慧,也与他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相统一。因而在年逾80 高龄,还能够勤奋而又敏锐地观察现实,反思历史。《八十后出版文存》的撰写与出版,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