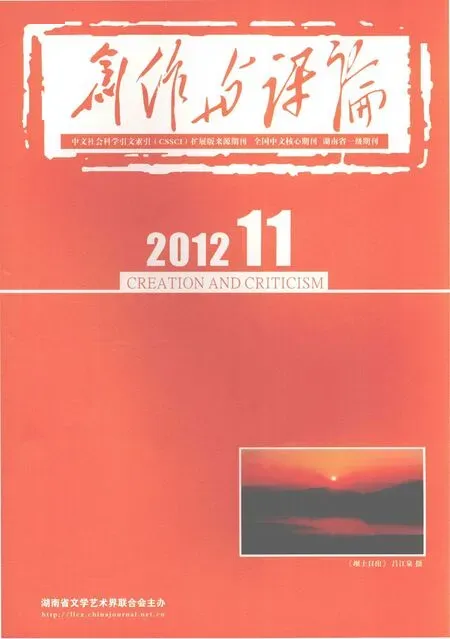《白鹿原》的戏剧改编、电影改编及其缺失
2012-11-24刘于锋
■ 刘于锋
小说《白鹿原》是一部具有多重蕴含的作品,曾被改编为秦腔现代戏、话剧、舞剧等艺术形式,由于受到特定的艺术形式的限制以及改编指导思想的影响,虽然各有千秋,但在故事的选取、情节的剪裁、人物的安排以及对原著精神内涵的呈现程度和间离程度等方面并非全无瑕疵,也遭到不同程度的诟病。
作为更为大众化的艺术形式,电影《白鹿原》能否真正满足观众的观赏期待与审美需求,也肯定是见仁见智。从“做戏”的角度来看,电影抓住了能体现白鹿原各种矛盾、各种势力交织的焦点所在,选取祠堂、戏台等代表性的场景反复表现,尽量减少旁枝末节,使整个故事在有限的时间内得到很好的演绎。戏剧、电影的改编又存在一定的问题和遗憾,如何既能忠实原著又能符合新的艺术形式的规律,应该是改编者的努力的方向。
一、文学形式的视听转换:《白鹿原》的戏剧改编
小说《白鹿原》具有多重蕴含,对改编者的挑战也较大。陈忠实先生认为“要尽可能准确的把准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机构形态;在不同的心理机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①;更具妙趣的是,原有的结构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冲击的时候,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是这个活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人物的个性来……”②那么在文学改编时,对原作这种凸显时代、道德、心理、价值等多方面的精神意蕴的综合把握、对人物命运的再次挖掘与塑造犹为重要。对小说的改编,重要的是要把原著中体现人物个性与历史变迁有机的结合起来,并能符合戏剧的表现要求。戏剧改编的成果已有2000年由西安市秦腔一团首演的大型秦腔现代戏《白鹿原》,2006年北京人艺演出的由林兆华导演、孟冰编剧的话剧《白鹿原》,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推出、和谷编剧的大型舞剧《白鹿原》。都是从小说的文字形式转化为视听形象,而这几部作品的改编也各有侧重。
秦腔现代戏《白鹿原》由丁金龙、丁爱军改编,在剧本的文学性安排上,主要突出白鹿两家的内部斗争,全剧共分六幕。第一幕写出写白嘉轩阻止黑娃、田小娥进祠堂拜祖。第二幕交代在农民运动的发展形式下,白灵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参加革命运动,被白嘉轩锁在屋里最终逃走。第三幕述田小娥求鹿子霖打听黑娃下落,鹿子霖垂涎小娥美貌而逼其就范,鹿子霖且欲利用田小娥勾引白孝文以达到报复白嘉轩的目的。第四幕,白孝文受到勾引来到小娥窑洞,被白嘉轩发现而受到族规的严惩,父子分家,孝文染上大烟,将地卖给鹿子霖,田小娥被鹿三杀死。第五幕,黑娃回来为小娥报仇,知是父亲鹿三所杀后也无可奈何。十几年后,破落的孝文受到田福贤推荐做了县保安全文秘,父子相认如初。鹿子霖因受到兆鹏的牵连而被抓,白嘉轩不计前嫌多方打听。第六幕,鹿子霖从白家买下的“风水宝地”的地又回到白家。整部戏把几十年的故事放在六幕中来演绎,使两家的矛盾冲突得到了集中的展示。话剧与秦腔剧本相比,对改编的要求也更高。
孟冰改编的话剧《白鹿原》与秦腔相比,更加注重故事的连贯性,从情节上来看,话剧对小说的依附性也较强。以白嘉轩与鹿子霖换风水宝地开始;兆鹏反对家长包办婚姻,黑娃、田小娥被拒绝拜祖;白鹿原成立农会批斗田福贤、鹿子霖;国民党政变,农会受到打击;鹿子霖与小娥发生奸情且陷害孝文;田小娥被鹿三杀死,黑娃找白嘉轩讨命;话剧还重点展示兆鹏、兆海与白灵间的复杂情感关系等等。
舞剧《白鹿原》主要以肢体语言来展示,从剧情上说,以田小娥与黑娃、孝文的感情为线索,主要塑造田小娥的叛逆者的形象,“主要围绕田小娥与黑娃、白孝文两条情感脉络的主线而展开,力图通过塑造田小娥这位被封建礼教所扼杀的叛逆者形象而揭示其所带给人们的文化反思。”③
二、以祠堂、戏台为焦点:《白鹿原》的电影改编
电影对原著有所截取,《白鹿原》选取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开始这个时间段,对剧中重要人物也有所删减,如朱先生、白灵、兆海、孝武等。人物的削减使改编更容易操作,剧本突出展示白嘉轩对仁义的坚守、鹿子霖的栽赃陷害明争暗斗以及兆鹏、黑娃、田小娥的叛逆。在故事和人物的剪裁上要比话剧更为简洁、突出。秦腔、话剧、舞剧《白鹿原》等舞台艺术形式具有剧场性、即时性、一次性的特点,表演要面对现场观众一次性完成,剧场布景的转换也要当场完成,而电影则可以随时选择场景、转换场景。秦腔《白鹿原》将剧情控制在六幕的篇幅内,在戏剧冲突上做深做透,话剧《白鹿原》则对情节较少裁剪,造成戏剧冲突不集中的印象,而电影则不受此束缚,电影《白鹿原》把祠堂和戏台作为反复使用的场景,从“做戏”的角度看,反复用来集中突人物的戏剧冲突,是改编较为突出、较为成功的地方,尤其值得肯定。
祠堂是家族势力的传统因素和族内斗争的象征,集中体现了家族的规约与惩罚的功能,电影用一次诵读《乡约》、三次惩罚、一次婚礼仪式使祠堂的功能得到具象化的体现。乡约与祠堂并非不好,恰恰体现了约束族人的功能。作为规约功能,电影以诵读《乡约》作为故事开头:“德业相劝、见善必行、问过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伺父母、能教子弟、能守廉洁、能救患难、能决是非、能解斗争、能与利除害……”陈忠实先生在《〈白鹿原〉创作手记》中提到乡约、族规家法是“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在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②白鹿村的乡约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家族规定,如果触犯,就会受到族内的惩罚,执行惩罚的人就是族长。剧中的三次惩罚都与白孝文有关,第一次是白孝文小时因调皮,白嘉轩以族长的身份在祠堂将其鞭打,是为了让他知道族规家法、仁义廉耻;第二次是白孝文在祠堂以族长的身份惩罚狗蛋、田小娥;第三次则是鹿子霖为了颠覆白嘉轩族长的地位,利用田小娥把白孝文拉下水,白嘉轩白孝文的惩罚最终导致父子离析。同时,把孝文与兆鹏的婚事是在体现家族权力的祠堂前举行,兆鹏可谓是家中要求婚姻自由的“逆流”,选择这个场景,更有象征意味。正是祠堂代表了家族势力,作为族长,白嘉轩才有权拒绝田小娥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进祠堂,而黑娃在白鹿村组织的农会权力的大增,在鹿兆鹏的引导下,黑娃与田小娥代表“婚姻自由”的“逆流”砸掉代表家族势力的祠堂,又显示了原有的家族势力受到新兴理念和力量的冲击。
如果说,电影以祠堂为中心来展开戏剧化的安排是体现家族内部的各种力量的反复,那么以戏台为中心展开的故事,就是更多的来体现白鹿村遭受的变动与外部整个社会反复无常的艰难变迁,原著中白嘉轩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白鹿原》第十四章),而事实就是如此,电影集中通过戏台这一具象,使走马灯似的权力变化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戏台的功能原本是演戏娱乐,但在电影中又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势力变更以及历史更替都在戏台上活生生的体现出来。把戏台作为历史变迁的见证,是电影的精心安排,戏台就在祠堂的对面,发生的几次重要事件无不放在戏台、戏楼的背景中。辛亥革命成功,电影以白鹿村的皇粮被兵匪所抢来体现,皇帝下台,白嘉轩以及白鹿村的村民们无所适从的站在寂静矗立的戏台下,电影把镜头定格此处;鹿子霖升为乡约,在戏台前宣布白鹿原革命,与祠堂对举,是白鹿两家的权力较量,也是新的格局与传统势力的较量;反革命军匪手下的杨排长进驻白鹿村,在戏台上逼迫白嘉轩敲锣交军粮;1926年白鹿村成立农民协会,权力格局又发生变化,农民运动将田福贤推上戏台斗争;1927年国共合作失败,波及到白鹿原,黑娃等农会成员又称为田福贤在戏台上镇压的对象,白鹿原的种种动荡、种种更替,都集中在这个“戏台”上来表现,电影以戏台来展示白鹿原走马灯似的权力更替,也抓住了陈忠实先生将戏台称为“烙锅盔的鏊子”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实质。
白鹿原本身就是一个大戏台,各色人物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以白鹿原的变动见证二十世纪前几十年的社会变革,所以白鹿原的牌坊又成为电影反复单独呈现的场景。祠堂、戏台、白鹿原牌坊这几个场景在电影中反复交替出现,就是要展示家族势力的明争暗斗,展示当时各种政治力量在白鹿原这几个舞台上反复无常的翻来倒去,历史的变动在白鹿原这个舞台上被反复演绎,来呈现出复杂的厚重图景。
三、过于依附与意蕴削减:《白鹿原》改编的缺失
从传播的角度和观众的期待程度来说,秦腔、话剧、舞剧相对于电影还是“小众艺术”,秦腔属于地方戏,在陕西一带流行,所以秦腔《白鹿原》的流传仍有地域局限性。话剧作为以语言为中心的表演形式,对观众群体的选择也较为“挑剔”。而舞剧《白鹿原》以肢体语言为主要表达方式,对原著的改编应该是长于象征、抒情,而短于叙事。
从剧本的艺术改编上说,秦腔剧本的改编主要围绕白鹿两家为风水宝地而展开的几十年的明争暗斗,其他方面的主题则只是陪衬而存在,把原著要揭示复杂主题单一化了。话剧过多依附原著而较少剪裁,所以在演出后即受到批评,有人认为话剧的主题变成了“田小娥与鹿兆谦、鹿子霖、白孝文三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龌龊和荒淫”,“展示白鹿原上那一幕幕最能展示人性恶的尔虞我诈,展示在风云际会之际的人格分裂中所迸发出的荒唐与卑屑,消解了崇高的历史含义,也消解了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的伦理意义。”④被认为与原著的多重主题发生了偏差。同时,话剧的展示也过于“低俗”,鹿子霖要看白嘉轩的“那东西”;鹿子霖要骂白嘉轩六个“狗日的”,孝文媳妇被奶奶训斥不能和孝文“耍的那么欢”,要“十天耍一回”等等。由于拙于剪裁,在有限的表演时间内在舞台上表现大量无关要旨的内容,势必显得重点不明。舞剧《白鹿原》与原著的精神内涵走的最远,把波诡云谲的风云激变以及时代变换中的道德、价值、人格的坚守与退却缩小到了塑造叛逆者的形象,是对原著精神理解的严重偏差,当然,这也是受到舞剧本身的艺术形式的限制而造成的。也是衍生艺术与原著精神不可缝合的缺憾。
小说《白鹿原》被认为是史诗风格的著作,电影将部分人物删减,从故事的编排上说有利于剧情的集中安排,有利于突出重点事件而减少旁枝末节,在“戏剧性”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是对史诗风格的展现角度来说,却不能不是说一个很大的遗憾,如原著中朱先生是白鹿原精神领袖般的人物,对时局了如指掌,具有强烈的责任感,是儒家人文精神品格的代表,是儒家精神的坚守者,也对白嘉轩具有精神指导的作用,而电影将朱先生抹去,对原著在表现儒家精神层面上大为削弱。白灵是个反叛传统,具有新思想而且能付诸行动的人,反对白嘉轩为其安排的婚姻离家出走,其行动也在反叛着以朱先生所坚守的儒家文化精神,是“白鹿精灵”式的人物,而电影将白灵删去,无疑也很大程度上又删去了反叛传统的精神内涵。总体上说,像具有代表意义的人物的削减,削弱了原著对史诗精神的表达。
小说《白鹿原》有丰富的解读性和衍生性,其他艺术形式都可以各取所需,不管改编如何成功,任何形式的改编都会对原著的精神有所损伤。可以说,有了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这些改编是《白鹿原》的不幸,因为任何一种改编都不能完全展示突出原著的精神内涵;也可以说有了这些艺术形式的改编是《白鹿原》的幸运,因为小说有了更多的途径传播。那么,怎样的改编能够忠实于原著又不泥于原著?怎样既能突出特定的艺术形式本身的特点又能把握原著宏大深博的精神内核?怎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打造出最能符合观众审美期待的作品来?这些重要的问题都对改编者提出了挑战,或许是以后的小说改编应努力的方向。
注 释
①卢衍鹏:《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②陈忠实:《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小说评论》2007年第4期。
③蔡梦:《乐舞交响白鹿情——记舞剧〈白鹿原〉创作研讨会》,《人民音乐》2007年第9期。
④杨云峰:《人文精神的曲解——简议话剧〈白鹿原〉的舞台表现》,《艺术评论》200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