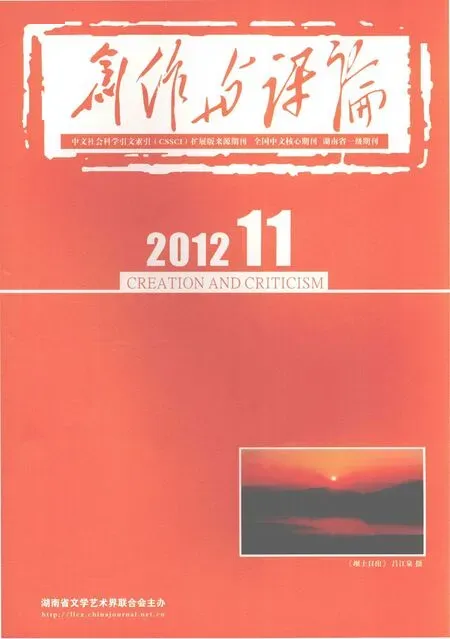我在走着一条孤独的路:陈和西谈自己
2012-11-24肖欣
■ 肖欣
陈和西一直在寻找一个安放自我的精神家园,那里妥贴、温暖,散发着令人沉醉的自由气息。凭着一颗执着而沉静的心,他划着他的艺术之桨,穿渡现实,划向理想的彼岸。
他觉得有些累了。他说:我在走着一条孤独的路,越走越难。
一定有很多人想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他和他的画,象征着每一个人心底放不下的那些东西。
他并不孤独。他和梦想、追求、艺术的永恒之美在一起。
一
几乎,每一个星期,他都要背起画板,去那些或远或近的小村庄写生。秧田里温润的泥土清香、午后农家院子里打着盹的小狗、池塘边被秋风吹荡的芦苇……,这样的景物与他有着天然的亲切。他喜欢呆在乡村,喜欢满身尘土的味道。这种喜欢透过他的画笔,渗进他的画布。人们说,看他的风景油画,就像回到家,有着彻底的放松与舒展。当城市化的进程轰隆隆地推进,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他的画是没有家园的人最好的慰藉。而他的故事,也要从浏阳那个童年的小山村说起。
我的老家在湖南浏阳县的一个小村庄,在山与山之间的那种小愣子里。说山,并不是什么大山,只是一些小山坡,红色的泥土路蜿蜒在郁郁葱葱的灌木丛中,能让远游他乡的人记住一辈子。村子不大,也就三四十户人家,我的祖辈在这里算是大户人家了。我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五岁多父亲就将我带到了他工作的株洲“331”厂,偶尔放假时才回乡下。那时,我祖母还在。我常在睡梦中醒来,静静地看老祖母在昏暗的灯光下靠着墙角纺纱,纺车嗡嗡地响着,老祖母的影子在墙上拖得很长。这种祥和、温馨和恬静让我迷恋一辈子,自然也深深地渗进了我的画。
在工厂,当时我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很少,他的举动 、言行,跟我们都不太一样,是我们这些小孩子心中的偶像。他喜欢打篮球,我有事没事就喜欢看他打球,很羡慕,也很崇拜。我到现在还每天要上场打篮球,可能就是那时候受了他的影响。我也常到他家去玩,感觉到知识分子家庭就是不一样,说话、做事,都有规矩。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种文化的吸引、文明的吸引,有一种潜在的影响人的力量。这对我的影响很大。
我爱画画,也说不上受什么影响,可能有一点天分。从上小学开始,我的美术课基本上就是满分,自己也蛮喜欢,比较得意。但画画在当时是不受重视的。父亲见我画,总要说:画什么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自己也没有特别地下功夫,只是觉得好玩而已,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当宣传委员,出黑板报。后来我到了株洲当工人,在车间里还是出黑板报,用粉笔画雷锋、焦裕禄、铁人王进喜。大家围着看,说:咦,还蛮像。后来就到厂办去画宣传画,那是水粉画,没接触过,就到处找书本,自学。那时候厂里搞了一个美术组,我们美术组几个人,每到周末,大家一起到郊外去写生,一起讨论。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年轻向上,富有朝气的团队,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一群志同道合,有共同理想的朋友,人生的路能走得正,方向对,是很难得的。这点很重要。
当时我也想过能否到学校里正规地读几年书,对自己也是一个提高。我有一位一直很关心我的姨妈,带了我的画作,给中央美院的一位老教授看。教授说,这个孩子不错,专业达到了美院二年级学生的水平。但是当时大学生都要工厂推荐,我出生不好,根本不可能被推荐。我姨妈回来告诉我,我心里很难受。所以1977年出来消息说要恢复高考,我是很激动的,一心想要考上大学,我利用一切能利用的时间复习,结果一考就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当时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看我们这一批正式考上来的学生,像看外星人一样。很多老师虽然已经解放了,但是大家怕政策又有什么变化,教学上不敢大胆地恢复。学生们呢,也是悄悄地发狠学习。
二
变化,再变化。连环画,水粉画,风景油画……数十年来,陈和西埋头走着一条求变创新的艺术之路。他所体会到的焦虑与困难,正是真正的艺术追求者必然经历的自我突破前的阵痛。破茧才能成蝶。蝶变前的历程,的确就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战斗。
在湖南油画界,陈和西还是老大哥式的灵魂人物。他组织大家搞展览,搞各种活动。他说,他喜欢大家在一起愉快地做事。随着近几年艺术市场的兴盛,陈和西的画作也越来越受到市场的追捧,画作的市场价格一路走高。但在他看来,钱只是意外的收获,最重要的,是保留有价值的艺术,保卫那种安然的画画的生活方式。
毕业后,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我很想画画,做梦都在画画,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想去做。但当时真不知道如何去画?不知道到底画什么?也许是方法太多,倒反不知道使用哪一种了。当时人们觉得画连环画是训练基础的好办法,对构图、造型都有帮助。我就想不如先画连环画。第一套画我记得是画的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的《童年》,没想到被当时很有影响的《连环画报》发表了,编辑还来了一封信,鼓励我画下去。这下子来了劲头,一画竟画了十年,在中国连环画界小有名气了,大家都知道,湖南有个画连环画的陈和西。现在我的一些连环画作品,都还是高考学生要临摹的作品。但画连环画很辛苦,眼睛越来越吃力。我决定金盆洗手。不久后,我到湖南师范大学进修,跟朱辉老师学习。朱老师是搞水彩画的,但水彩笔是软的,我是学油画的,油画笔是硬的。我就跟朱老师说,我画水粉画吧。后来我决定改风景油画,一直画到现在。
在中国油画界,人们一直在谈论油画的中西结合。中国的传统意象与韵味,如何与油画这种西方的艺术形式相融合?融合到什么样的状态?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与探索的问题。我是个碰到挑战,就想要竭尽全力去做好、做到位的人。风景油画我从1993年画到现在,仍然觉得还有好多问题没有解决。画到一定程度上,较劲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自己跟自己较劲。作品的好与坏,自己心里有一个标准。外在的成功与否,与你心里面这个好与坏没有关系。
我觉得自己在走一条孤独的路,越走越难。越走觉得问题越多。有些容易一点的,可以少花点时间解决,但解决了这一个,下一个又冒了出来。过去是有时间有精力,但看不到问题,一头雾水。现在的难题则是,我能看到问题、也知道解决的办法,但却没有精力、没有时间去做到。退回去二十年,以那时候的时间精力,这些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缺的就是时间、精力。
现在我有点精疲力竭,但又总觉得自己再去做一下,再努力一下就好。这个事情我很焦虑,纠结。这种心态持续了好几年,也在慢慢调整。一个一个问题,一个一个新方法,我都在尽量地去发现,去解决。
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自己要做得好当然很重要,但人有时候还有一种责任感,有些事情,你不动,就没有人去动。有一个团队,大家一起做事情,一块高兴,不论做得成不成,做得好不好,我们去做了,努力了,就是好事情。“大南方画派”是我们想要打造的一个新的概念,想要联合长江以南的几个省份一起来做,包括湖北、广西、福建、江苏、广东等在内。这些地方都有一种婉约、内秀,与西北黄土高坡那样的地理风景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活动,在广东搞展览,去广西写生等。这个也是一件大事情,也要花时间,花精力,我们会慢慢一步一步来做。
至于艺术市场,作为画家,当然渴望能卖作品,并能卖得出好价钱。这是市场的一种认可。但是一旦真正进入了市场,你又会觉得市场好坏并不重要,钱多钱少并不重要,不必因此就影响自己的心态。好价钱不能代表成功,钱也并不能带来太多快乐。如果作品卖多了,还真的会有一种恐慌感,因为你希望保留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我现在觉得,钱只是我的艺术创作的一个意外收获,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这种画画的生活方式。
三
2012年4月6日深夜,陈和西通过电话接受采访,我几乎不加任何修饰,如实地记录下他说的话。我相信很多年后回过头来看,他在这个春天的夜晚,说过的关于自己的话,依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因为它们很真,真得有些叫人心痛。
“心痛”是我在多年前观看陈和西的风景油画时,留下的一个感受,有一篇文章《安静的力量》为证。我很奇怪过了这么多年,对于陈和西,我依然会不自觉地使用“心痛”这个词。岁月流逝,人事恍然,我会因为一个人和他的画而心痛什么?都市红尘的喧嚣里,我们不是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无动于衷了么?我想,陈和西对于我的意义,或许是因为他和他的画作都尤其鲜明地呈现,不管时代怎么变化,总有这样的人,坚持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走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活出了自己的意义。而大多数像我一样的随波逐流者,却离自己曾经的梦想越来越远。
因此,我很珍惜陈和西式的真诚与朴实、执着与痴迷。这样的品质使他哪怕在声名日盛的时势中,亦有一种安之若素、举重若轻的气势包围着他,保护着他。成功对人也是一种考验,它有时候会变成细小的针尖,扎破那些轻飘飘的浮在空中的气球。但陈和西显然立定了根本,他的气场在渐渐强大,呈现在他的画作里,则是越来越气象万千、内外兼备的锦绣繁茂,有一种仿佛膨胀起来的生机感。数十年来,他孜孜于从大自然中汲取的生机与能量,正慢慢输送到他的画面深处,让笔下的景物连接大地,肌理饱满,有了清晰的可感的生命力。虽然它们在画作上呈现的姿态,也许模糊、也许冲淡、也许不过寥寥几笔。
“我在走着一条孤独的路,越走越难。”陈和西的夫子自道,是所有真正的艺术追求者的真切生命体验。艺术不是一条简单的路。它直抵人类最深遂的精神之谷,最高妙的意识之巅,任何一个走上此路的创作者,必然经历一层又一层炼狱般的精神磨炼,直到脱胎换骨。艺术家的痛苦,我以为象征人类精神世界体验的最终极。没有人能真正帮助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他们的独自苦斗,他们的深切痛苦,我们都只能默默注视,奉献上我们的敬意。
很多人半途而废。很多人虽得盛名,但内在已朽。真正的艺术之神非常苛刻,也非常挑剔。留下来前行的人,是人类精神火种的传承者。成功的世俗标准对于他们毫无意义,艺术有一套自已的选择方法。现在,陈和西所需要的便是时间。精力,其实也就是时间的另一种姿态。我们就和时间一起来等待,这位执着的跋涉者所能到达的艺术之境。